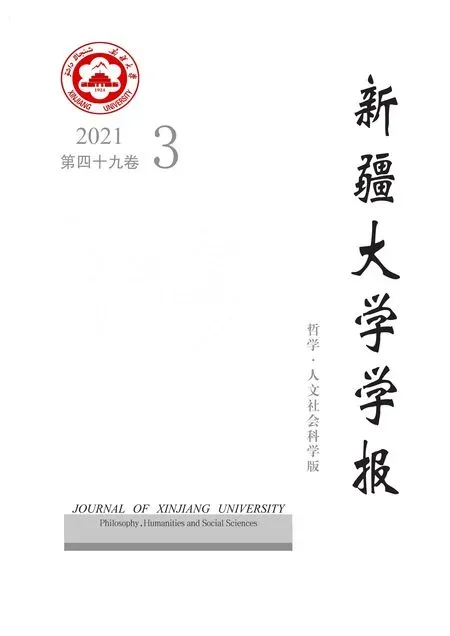乾隆年间辟展同知设置考*
2021-11-30王启明
王启明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有关辟展同知(厅)的设置年代,赵泉澄先生《清代地理沿革表》据吏部会议奏折指出,“乾隆三十六年,于辟展地方设辟展厅,移兰州府河桥同知驻扎,无属领”[1]110,并在按语中指出:“《一统志》作乾隆二十六年,《清续文献通考》作乾隆二十四年,误。”[1]117赵泉澄先生有关乾隆三十六年(1771)为辟展同知(厅)之设置年代虽然正确,但并未指驳乾隆二十四年与乾隆二十六年错误之原因。综览清代相关文献记载,乾隆二十四年设置辟展同知之说法,除赵泉澄先生所提《清朝续文献通考》外,尚有《新疆图志》卷二《建置二》“乾隆二十四年,设辟展办事大臣及同知”[2]与《清史稿》卷五一《地理志·新疆》“乾隆二十四年,设建六城,于辟展置办事大臣、管粮同知”[3]之记载。①案:《清史稿》中华书局点校本“乾隆二十四年,设建六城于辟展,置办事大臣、管粮同知,仍以吐鲁番广安城为回城”断句有误,应如正文所引断句为当。而乾隆二十六年设置辟展同知之说法,除赵泉澄先生所提乾隆《大清一统志》外,同期所修《西域图志》卷三〇《官制二》亦有辟展“同知一员,乾隆二十六年设”[4]。以上两种说法,确如赵泉澄先生所言有误,因这类“同知”实为临时派遣辟展专办粮饷、粮务之“管粮同知”,②案:有学者虽指出辟展“同知由内地派往轮流更替担任”,但并未加以论证,参见傅林祥、林涓、任玉雪等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5页。亦无辟展专属印信。为此,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乾隆年间辟展地方“粮饷同知”之设置缘起与其经过。
一、临时派遣之同知
从康熙末年到雍正年间,清朝与准噶尔在吐鲁番盆地互有争夺,最后以清朝撤兵、迁徙当地百姓,准噶尔得其地而暂告结束。③参见王启明《天山廊道:清代天山道路交通与驿传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9-110页。至乾隆十九年,准噶尔内部动荡,清军次年顺利进军伊犁,但稍后阿穆尔撒纳反叛,清朝不得不再次进军准噶尔。至乾隆二十二年,定边将军成衮扎布等奏“臣等奉旨于进兵时,先行勘定地方派兵屯种,并令厄鲁特等无从退回复踞旧地。臣详看吐鲁番直通伊犁,兼与各回城声息相通,应即于吐鲁番派兵屯种。现在额敏和卓亦驻扎此处,尚有辟展地势宽展,即将臣等所带绿旗兵屯田”[5]卷536,770。次年,乾隆据舒赫德等奏称“辟展秋收丰稔,已行文黄廷桂派绿旗兵四百名,今岁广为垦种”,上谕指示“屯田一事实为要务”[5]卷554,9,并一再“谕永贵等于屯田处所广为垦种,以裕军食”[5]卷559,87。尤其当清军乾隆二十三年开始进军天山南路反叛之大小和卓,人马急需粮料,上谕指出:“塔勒纳沁既可种豆,由此推之,辟展、吐鲁番、托克三、乌鲁木齐等处想皆可以试种。若得成熟,于牧养更为有益。可传谕永贵等将辟展等处节候地气测验确实,即于明春播种。”[5]卷570,239当年收获非常可观,据办理屯田侍郎永贵等奏“本年辟展等五处屯兵共三千六百名,屯田三万三千五百四十五亩,每亩收获一石九斗至一石四斗不等,共收谷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余石,较去年多收六千七十余石”[5]卷573,289。辟展、吐鲁番地处军事后方,负有供应前方军粮之责,屯田种粮可免内地供应之烦费,但办理屯务粮饷收支迥非一人所能应付,因此急需人手。《清高宗实录》有如下记载:
据永贵奏,行文黄廷桂派参将游击等官二三员、千把总等官四五员,以备差委。并酌派应差兵役二三百名。又辟展同知伊星阿一人管理收支等事,未免竭蹷,请添派谙习粮务同知二员、杂职二员协办等语。屯田伊始,差务颇繁,所需官员自不可少。至听差兵役等,则现在屯田兵丁未必日事耕作,自可通融调换,何必多为添派。可传谕黄廷桂、永贵,所需文武官员照数发往,再派兵一百名以备差遣。[5]卷572,276-277
据上,在“广为垦种以裕军食”的政策下,吐鲁番盆地开始大量屯田,但缺少人手,因此辟展同知伊星阿奏请添派熟悉粮务同知二员,上谕指派陕甘总督黄廷桂、办理屯田侍郎永贵照办。而引文中出现的辟展同知伊星阿同样属于临时派遣之管理粮饷事务人员,并非经制实缺同知。次年乾隆因“屯田粮石关系军需,定长等所报碾出数目有较上年加增者,皆承办之员实心经理所致,著加恩将都司玛呼等交部议叙”[5]卷584,477。而且管理屯田副都统定长在辟展屯田收获后,奏请积贮,应建仓堡,据“查辟展已有旧设仓堡,仍需添葺。其喀喇和卓新建仓二十四间,托克三(即托克逊——引者注)二十间,哈喇沙尔十五间,乌鲁木齐二十四间,各筑堡一。辟展添仓三十间。及修葺旧堡,照巴里坤修城例赏给银两”[5]卷601,738。辟展屯田及粮储制度就此建立。不久,随着乾隆二十四年底清军歼灭大小和卓,清廷开始考虑当地经制之法,如当年十一月上谕:
西陲大功告成,一应事宜必期熟筹可久。从前哈密、巴里坤、辟展等处办理粮饷台站诸务,俱由内地派员经理,今军需事竣,而新隶版图均有专责,若仍行兼办,致本任久悬,殊非常制。且甘省各营伍官职较他省独多,原为地属边疆起见。今准噶尔、回部荡平,屯田驻兵,自伊犁以达叶尔羌,向日之边陲又成内地,则文武员弁均应依次移补,方与舆地官制俱为合宜。其哈密、巴里坤以西应需用道、府、同知若干员,一半于内地事简处裁汰移驻,一半酌量添设。驻兵屯田各营应设将弁等亦一体筹办,庶于国计、边防两得经久之道。著传谕杨应琚或途遇兆惠等详悉会商,或与舒赫德等悉心酌议具奏。[5]卷601,748
据上引文,此前所见辟展同知、通判等官均为内地派遣之临时官员,兼办粮饷等事务。如当年四月,管理辟展事务的定长奏报吐鲁番当地办理钱粮收放、往来文移,为昭信守,需钤盖印记,其奏称“te bar kul i jeku caliyan be icihiyara lin too i dooli hafan lergin.eiten jeku caliyan i baita be icihiyara de gemu ini tesu tušan i doron be baitalambi.dewen ne liyang jeo.juwang lang ni dooli hafan sindaha be dahame.bahaci.lergin i kooli songkoi tesu tušan i doron be gaifi baitalabuci.jeku caliyan i baita de akdun ombi.”(今办理巴里坤钱粮临洮道员lergin,办理一切钱粮之事时,皆使用他本任印信,今德文既已补放凉州庄浪道员,应照lergin之例,带其本任印信使用,于钱粮事务可昭信守)[6]第37册,304,足见当时辟展尚未设置经制官缺,因无当地辟展专属印信。而当时天山南北悉平,版图扩大,又不可使本职久悬,急需设官置守,“方与舆地官制俱为合宜”,并拟通过设置道府州县官员治理新疆,因令陕甘总督杨应琚与将军兆惠等人商议。至乾隆二十五年,舒赫德、阿里衮等针对乾隆上谕,奏陈新疆各地道府官员设置计划中,辟展设同知一员、托克逊巡检一员、哈拉沙尔通判一员,俱归哈密兵备道统辖,①参见舒赫德、阿里衮等《奏为遵旨会商新疆所属等处应裁应设文武官弁事》,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02-0003-001。果如此,归属哈密道的辟展同知当为直隶厅建制,②案:传统观点一般认为直接归属布政使司的厅为直隶厅,但近来有学者指出清代新疆之直隶厅往往归属于道,参见鲁靖康《清代厅制再探——以新疆为例的考察》,《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第93-94页。但稍后乾隆否定了自己原拟施行的道府厅州县治理制度③案:有关清朝平定新疆初期拟用州县制度之设想,参见聂红萍《从甘肃总督到伊犁将军:乾隆朝对新疆治理的探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第54-55页。,转而寻求军府制度。
在此背景下,属于军府体系的经制官员——办事大臣制度开始设置,据乾隆二十五年九月上谕:
现在乌鲁木齐有安泰办事,永瑞、定长亦俱前往。据舒赫德奏请以德尔格暂驻辟展,将彼处一应事务查核明白,交代辟展承办官员,方可赴乌鲁木齐等语。辟展办事仍须专员兼辖,可传谕德尔格查核事竣,仍驻扎辟展,兼辖文武官员,一切事件与舒赫德、定长商办,有应行陈奏者,准其具折奏闻。并传谕舒赫德、定长等知之。[5]卷621,981
随着辟展屯田副都统定长前往乌鲁木齐办事,舒赫德奏请以德尔格暂管辟展,待当地事务查核明白后,再前往乌鲁木齐办事。但上谕认为如此办理,辟展便无专员负责办事,所以令德尔格驻扎辟展,管理文武官员一切事件,并被赋予“具折奏闻”之权,稍后又铸给清、汉、回三体驻扎大臣关防。①参见官修《清高宗实录》卷635,乾隆二十六年四月辛卯,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93页。不过,在清代档案中德尔格之具体官衔为“驻扎辟展郎中”[5]卷632,59,乾隆朝满文寄信档中常作“pijan de tefi baita icihiyara icihiyara hafan(驻辟展办事郎中)”[7]第2册,215、590,有时也译作“pijan de tefi baita icihiyara icihiyara hafan(驻辟展办事侍郎)”[7]第3册,443、568,尚非后来常见之“baita icihiyara amban(办事大臣)”称谓。细阅《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pijan de tefi baita icihiyara amban(驻辟展办事大臣)”称谓似乎于乾隆三十年第一次出现。②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5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67、630页。但这种细小的差异不过强调其兼任职衔而已,辟展办事大臣乃其本职。因为乾隆二十五年大学士傅恒在奏定回疆驻防大臣养廉银时,奏折所附“现在西路办事大臣名单”中明确列有辟展“德尔格总理”,与其它回疆各城一致。③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40页。此外,乾隆五十一年吐鲁番领队大臣在追忆乾隆二十六年补放罗布淖尔伯克时,提及时任官员为“pijan de tefi baita icihiyara amban(驻辟展办事大臣)”[6]第174册,303,可见均视其为辟展办事大臣无疑。然在乾隆二十五年之前,《清高宗实录》中常有诸如“办理屯田侍郎永贵”[5]卷569,213、“屯田大臣永贵”[5]卷572,272及“办理屯田副都统定长”[5]卷584,477等记载,足见屯田为该大臣之主要职责,侍郎及副都统则为其本职官衔,自然不能视为经制职官——“辟展办事大臣”。果真如此,本文起首所引《新疆图志》“乾隆二十四年设置辟展办事大臣”之记载则有误,而今日所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乾隆二十五年九月以前目录中出现之“辟展办事大臣”称谓亦有不够精准之处。至乾隆四十四年,清朝趁苏赉满犯罪之机,将辟展办事大臣裁撤,在吐鲁番改设领队大臣(meyen i amban),归属乌鲁木齐都统管辖,相比此前辟展办事大臣,其地位有所下降。
在乾隆否决设立府厅州县制度的情况下,新疆地方官员设立辟展同知及巡检的计划就此搁置,此后辟展粮务仍由内地临时派遣之同知等兼办,此种情况至少又延续了十年,如乾隆二十五年户科题本中仍有“办理辟展粮务庄浪理事通判乌林保造报管理屯田军台驻扎效力官员支过盐菜口粮”之记载,④参见甘肃巡抚常钧《题请核销乾隆二十五年辟展并所属供支官兵俸赏及运送银缎茶布兵丁衣帽等项用过银两事》,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档号02-01-04-15491-009。及乾隆三十一年陕甘总督吴达善奏请补放乌鲁木齐通判时,声明当时“陕省六府仅设通判三员,内满洲现止一员,已委在辟展管粮”⑤参见陕甘总督吴达善“奏为循例请敕部于候选通判满员内拣补乌鲁木齐通判事”,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12-021-0260。,再如乾隆三十五年陕甘总督明山奏“甘肃地方佐杂人员差委本多,兼有派赴新疆办理粮饷诸务,所遗之缺均须委员署理”⑥参见陕甘总督明山《奏请拣发佐杂人员来甘差委事》,乾隆三十五年四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16-0050-057。,足见包括辟展在内的新疆各地仍有由甘肃派遣佐杂人员前往办理粮饷等事务者,进而导致甘肃出现人员不敷差委之状况。
二、实缺同知的设立
清朝乾隆二十四年统一天山南北后,吐鲁番盆地东部之辟展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回部东境门户,全属城堡甚众”[8],即如辟展所属齐克塔木等处亦“商贾云集,铺户益多,所住房屋自十间至百间不等,应照辟展例取租,每间每月取租银五分,贮备公用”[5]卷872,700,作为辟展东境一处军台的齐克塔木的商贸景象尚且如此兴盛,则比之居民与城堡更加众多与宏大的辟展城更是内地商旅聚集之地,并由此导致辟展交纳赋税使用内地制钱,而非南路回疆其它各城之普儿钱(pul),实因该地自清军平定后,“有内地人来往通衢,远近商人,遐迩趣赴,则我朝之钱法遂行”[9],这也是对包括辟展在内的新疆东部“口外已成内地”的真实写照①参见官修《清高宗实录》卷771,乾隆三十一年十月丙寅,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473页。。在此背景下,陕甘总督明山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上奏道:
辟展地方为新疆南北两路咽喉,东连哈密、巴里坤,西接乌鲁木齐、伊犁,并南路回疆各城,凡一切官兵过往供支及转运饷鞘绸缎茶封农具军装、递解发遣人犯,兼有经收吐鲁番回民交纳贡赋粮石,且现在另案酌议辟展地方遇有相验命案,责成该处粮厅按例查办,是辟展一处差使络绎,政务殷繁,实为新疆要地,向系内地差派丞倅一员管办经历,并杂职一员以资巡查,俱系三年差满,仍由内地派换。查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处管理粮饷地方事务,均系额设实缺官员,而辟展地处中权,为出入总汇之区,其冲要事繁,悉与哈密等处无异,仍属差员经理。非惟与体制尚未画一,且差派之员甫经熟谙,又须更易生手,于事恐属无裨,兼之内地距辟展窎远,三年一换,往返亦多旷费,自应照哈密等处之例,酌裁内地冗员移驻辟展,设为实缺,以重责成而垂永久。②参见陕甘总督明山《奏请裁汰内地冗员移驻防新疆冲要事》,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12-0141-002。
据上,不难看出辟展自清军平定西域已有十余年,因当地交通咽喉地位使得差使络绎,政务殷繁,而且遇有命案,只能由内地派遣至辟展的临时粮饷同知(粮厅)处理相关事务,明显与体制不符。即便陕甘总督明山在此之前已经意识到这种困境,且曾奏准将“辟展管理街道县丞一员亦定三年更换”[5]卷867,633,但同知一缺仍因临时派遣人员任职时间过短,非哈密等处实缺可比,难成永久之策。针对前引明山之奏,吏部等议复后,上谕批示:“辟展为新疆南北冲衢,政繁差重,向以内地派往丞倅杂职经理轮流更替,于事无益,请裁兰州府河桥同知并平番县苦水巡检,均移驻辟展,隶安西道,定同知为冲繁二项边远紧要满缺,巡检亦在外调补。”[5]卷881,805-806如此,辟展同知正式作为实缺职官。同年七月,新任署理陕甘总督文绶便奏请以廷毓调补辟展同知。③参见署理陕甘总督文绶《奏请以廷毓调补辟展同知事》,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12-0144-070。次年四月,朝廷更是“添铸辟展同知、巡检关防印信”[5]卷906,114。稍后清朝修建辟展衙署,据称“辟展设立同知、巡检,系新改实缺,向无衙署,必须添建,以资办公”,其“应建辟展同知衙署一座,共计大小房五十六间,连照壁围墙等项照例细加确估,共需工料银三千七百一两零”④参见陕甘总督勒尔谨《奏报建盖辟展同知衙署需用银数事》,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37-0032-014。。此后,档案中即见辟展同知履任,并采买粮石。⑤参见陕甘总督勒尔谨《奏明辟展同知请采买小麦两万石缘由事》,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0758-023;陕甘总督勒尔谨《奏为查明兵部员外郎福重于前辟展同知任内并无迟延造册等情请准开复处分事》,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12-0170-043。
至于辟展同知之行政归属问题仍需探讨,前述乾隆三十六年吏部议准辟展同知归隶安西道,至乾隆三十七年“军机大臣等议准陕甘总督文绶疏请安西道移驻巴里坤,改为屯田粮务兵备道,照旧兼辖哈密、辟展、乌鲁木齐等处”[5]卷907,128,若依此奏,归属安西道的辟展同知在行政级别上应为“辟展直隶厅”,但次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请“巴里坤地方近来生息增繁,兵民子弟敦书讲射,渐已蔚然可观,请照乌鲁木齐迪化、宁远二厅封题代试之例,专设学额”。上谕进而指出“今既议定学额,而原驻仅一同知,尚于体制未合,自应将巴里坤改设为府,乌鲁木齐改为属州,或将安西府移于巴里坤,而改安西为州,并令统隶,于边郡规模尤为闳远”,最后定议巴里坤改设知府,乌鲁木齐同知改为知州,且“附近之辟展同知、哈密奇台两通判均归巴里坤新设知府管辖”⑥参见官修《清高宗实录》卷926,乾隆三十八年二月癸亥,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443-444页。。经此行政调整,归属镇西府的辟展同知在行政级别上属于“辟展厅”,即从设置之初的属道直隶厅降为属府散厅。但稍后因乌鲁木齐“地方辽阔,事务繁剧,知州一人兼管莫及”[10]11,同年九月巴里坤道移驻迪化州⑦参见官修《清高宗实录》卷942,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己巳,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747页。,但并未改变辟展归镇西府的隶属关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四十一年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奏请“将巴里坤道改为分巡镇迪粮务道”[10]11后,同年十二月吏部等议复“哈密、辟展二处钱粮由巴里坤道申报都统”,并将“分巡巴里坤粮务兵备道改铸分巡镇迪粮务兵备道兼管哈密辟展之关防”①参见官修《清高宗实录》卷1023,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丁巳,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709页。案:当年底,陕甘总督勒尔谨所造《甘肃省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分粮价清单》中仍开列“巴里坤道”,参见陕甘总督勒尔谨《呈甘省各属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份粮价单》,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39-0088-009。次年二月甘肃粮价清单中不再见有巴里坤道,参见陕甘总督勒尔谨《呈甘省各属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份粮价单》,乾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单,档号04-01-39-0088-011。因为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收到陕甘总督勒尔谨咨文内开“查口外哈密以西钱粮,自四十二年为始由新疆大臣核办,所有镇迪道属粮价应由乌鲁木齐都统具奏以归画一”,参见乌鲁木齐都统《奏为遵照办理具奏乌鲁木齐镇迪道属各县奏(春)季粮价情形事》,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24-0071-057。,如此,辟展改归镇迪道所属,似应升为“辟展直隶厅”,但无相关之记载。若仍隶镇西府,当为辟展散厅,但令人疑惑的是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造报乾隆四十三年所属镇迪道地方各月粮价清单中开列镇西府属之宜禾县、奇台县及哈密厅、迪化州、昌吉县与阜康县粮价时,并无任何辟展之记载。②参见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呈乌鲁木齐等处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份粮价单》,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单,档号04-01-24-0071-040。至乾隆四十四年,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奏请移驻吐鲁番满洲事宜时,曾言“辟展同知应移驻吐鲁番,所属地方事向由镇西府详道,但该府驻札巴里坤,相隔数站,往来需时,应令径呈该道,由道转详乌鲁木齐都统”[5]卷1085,583,似乎辟展厅在此稍早时期仍归镇西府管辖,行政级别仍为散厅。但乾隆四十四年粮价清单中依然无辟展之记载,同年九月粮价清单中则明确开列“吐鲁番厅”③参见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呈乌鲁木齐等处乾隆四十四年九月份粮价单》,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单,档号04-01-24-0071-022。但八月粮单中无。,实因该月新任吐鲁番领队大臣与原辟展办事大臣完成交接任务、东部辟展职官体系西迁至盆地西部吐鲁番所致④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40册,《吐鲁番领队大臣图思义等奏交接辟展办事大臣印务折》,乾隆四十四年九月十三日,第427页。。就此由之前集中处理粮饷事务的辟展同知转为兼管理事回民事务的吐鲁番同知。
综上,作为经制实缺的辟展同知设置时间确为乾隆三十六年,正因如此,与其连带设置之辟展巡检也载录于《三州辑略》当中。⑤案:辟展巡检“三十六年,由内地裁汰平番县苦水巡检缺移驻”,参见和宁《三州辑略》卷2《官制门·吐鲁番同知》,载苗普生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5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第222页。而此前各类文献中出现的辟展同知均为内地临时派遣之专管粮饷、粮务同知,职能单一,在辟展亦无专属印信和署衙,且有其内地本职官衔,因此不能视为“额设实缺”之辟展同知。
三、结 语
清朝乾隆年间统一新疆后,逐渐确立了以西路伊犁将军、东路乌鲁木齐都统及南路回疆参赞大臣为代表的上层军府体系管辖天山南北。但在下层民政领域,大体上在乌鲁木齐周围及天山北麓东部一线施行直接管理的府州厅县制度、在南疆塔里木盆地维吾尔社会中施行间接管理的伯克制度、在靠近内地的东疆(哈密、吐鲁番)维吾尔社会及天山中部土尔扈特等蒙古部落中施行间接管理的札萨克旗(盟)制度。然而乾隆三十年代前后,作为南疆门户的吐鲁番盆地完全涵盖了以上所述清朝治理新疆社会的各项制度,如属于军府制的辟展办事大臣(baita icihiyara amban)、属州县制的辟展同知(uhei saraci)、属札萨克旗制的吐鲁番郡王(turfan junwang)及属伯克制的吐鲁番小伯克等,⑥案:有关吐鲁番小伯克的论述,参见张莉《“办事大臣——小伯克”:在军府制与札萨克制之间——乾隆二十六年吐鲁番地方民众管理体系的调整》,《西域研究》,2018年第4期。此乃清朝治理当地社会所采取的“因俗而治”政策的集中反映。但在吐鲁番盆地政治中心从东部辟展西迁吐鲁番之前,曾在库车履任的椿园在其《西域闻见录》中描述吐鲁番盆地所属六城皆为札萨克郡王额敏和卓之子苏拉满之阿拉巴图(满语:albatu,意为“奴仆”或“属人”),属于“世袭土司,非回疆各城随时升调去留之可比”[11],于此可见当时对吐鲁番民众进行直接管辖的是当地的札萨克郡王,但这一理民体系属于典型的“世袭土司”性质,而乾隆三十六年新置“额设实缺”辟展同知毫无疑问属于可以“随时升调去留”的流官性质,而在此之前的临时兼办辟展同知已经处理“一切官兵过往供支及转运饷鞘绸缎茶封农具军装、递解发遣人犯,兼有经收吐鲁番回民交纳贡赋粮石”事务,设立辟展同知以后,朝廷更是“酌议辟展地方遇有相验命案,责成该处粮厅按例查办”①参见陕甘总督明山《奏请裁汰内地冗员移驻防新疆冲要事》,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12-0141-002。。当该同知乾隆四十四年裁改吐鲁番同知后,其关防文曰:“吐鲁番同知兼管理事回民事务之关防。”②案:当地官府曾获得铜制关防一颗,有“细看篆文吐鲁番同知兼管理事回民事务之关防,毫无损坏,知是旧日吐鲁番同知关防”,参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合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使得同知具有管理部分吐鲁番回众百姓的权力,实为流官同知对土司札萨克郡王的管辖权的初步摄取。缘此,实缺辟展同知的出现就不单是一种州县职官的设置而已,实为日后吐鲁番“改土归流”的实施创设了必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