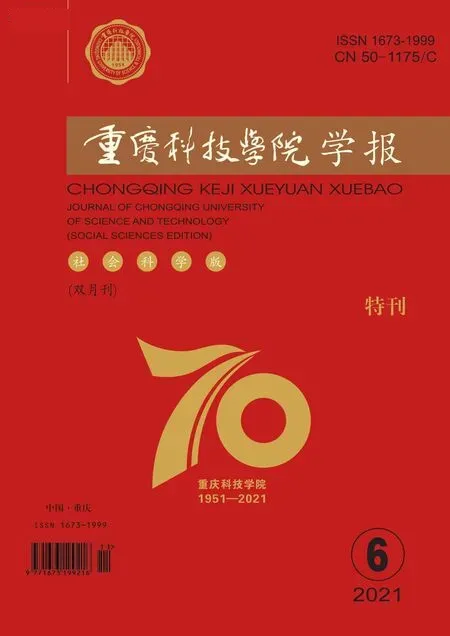论成己与成物
——基于“天命之性”的本体论视角
2021-11-29宗卫华
宗卫华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太原 030006)
西方思想家看待世界常常突出主体与客体世界的二元对立性,这便使得他们非常重视知识、理性与逻辑。人是有限的存在,通过形而下的知识、规律试图找到形而上的统一性,常常会遇到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很多哲学家往往不得不求助于上帝,通过信仰的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一样,同样存在如何看待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只不过儒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通过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来看待世界,而是以“己”“人”“物”所建构的“成己”与“成物”活动来显示这个问题。儒家学说认为,在“成己”与“成物”活动中,“成”由之以成的根据是由“天命之性”所确证的,“人与物之本性同”[1]1493,故在“天命之性”视域中的“成己”与“成物”活动所重视的往往不是世界的对立性,恰恰是世界的统一性。本研究试图以《中庸》视域中的“成己”与“成物”活动来说明世界的这种统一性以及人的在场性,从而为我们理解自身与世界提供另外一种向度。
一、“己—物”关系:对《论语》“己—人”关系的继承与扩充
“成己”与“成物”出自《中庸》。《中庸》曰:“诚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2]35杨国荣解释道:“成己主要指向自我的完善,它具体表现为以仁道为根据塑造自我,从而体现了‘仁’(所谓‘仁也’);成物在广义上既指成就他人,也涉及赞天地之化育,二者都以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为前提,其中包含对人与物的把握,从而体现了‘知’(所谓‘知也’)。”[3]成己、成物问题中隐含着主客关系,然而回溯儒学思想史便可以发现,对于主体与对象的问题,孔子于《论语》中早已有关注。在《论语》中,主体、对象虽呈现为“己—人”关系;但在内容上,《论语》之“己—人”关系与《中庸》之“己—物”关系⑴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成己,仁也”,按杨国荣先生所言,己之“成”在于“以仁道为根据塑造自我”。“己”,便是语词“我”,在这里指代人的主体性,“己”之“仁”是通过“成”的工夫显现出来的,这便是《中庸》文本中对于己的论述。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仁”与“己”的这种关联并非是从《中庸》开始的,而是从儒学发端之际就已产生了。孔子及其弟子对“己”与“仁”的关系多有言及,具体体现于《论语》中。子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2]100(《泰伯》)“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2]125(《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89(《雍也》)“己”是认知主体,也是道德主体,还是实践主体;不仅如此,在“己”与“仁”的关系中,孔子通过工夫论来说明“仁”对于“己”的真实有效性。因此,《中庸》中的己、仁与《论语》中的己、仁是一脉相承的;《中庸》中“成己,仁也”的命题便是直接从孔子“为仁由己”的思想中继承而来的。
“成物,知也”,根据杨国荣先生以上所说“成物在广义上既指成就他人,也涉及赞天地之化育”,且认为成物“包含对人与物的把握”,这也就是说成物之“物”不仅仅指万事万物,亦涉及到人。杨国荣先生对物的这种广义理解在中国哲学中实则是有依据的。先秦时期《荀子·正名篇》曰:“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4]“共则有共”是说共用的名称之外又有共用的名称,如此“推而共之”以至于“无共然后止”,所止之处便是“大共名”,是那“物”,此时“物”的意义类似西方哲学中“存在”这个范畴,在概念上内涵无限小,外延无限大,从而能够囊括一切,人亦必然包含其中。如此,《中庸》的“成物”思想不仅仅涉及天地万物且含有“成人”在里面。
对于“成人”这个主题,早在《中庸》之前,孔子及其弟子就已探讨过。《论语》曰:“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恶。”[2]130(《颜渊》)“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2]142(《宪问》)以动宾结构来看“成人”,对人而言意味着如何去“成”?这里孔子予以人之善、人之知、人之情、人之勇、人之艺、人之礼乐来作答,说明孔子看到,“成人”就在于成就人的全面人格,这不仅涉及德性、认知,还涉及审美与事功等各个方面。
孔子以“仁”论“成人”,内含着对善、知、勇的重视。对于这一点,《中庸》的作者子思和孔子一样,亦非常重视仁、知、勇对于人的意义,其曰:“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斯三者”就是知、仁、勇三德;“天下国家”,朱熹曰:“天下国家,则尽乎人矣”[2]31。可以看到,《中庸》这里所说的修身、治人、治天下就是在说“成人”。知、仁、勇对于“成人”的意义显而易见,此“三达德”意义上的“成人”亦被《中庸》进一步归纳为“诚”,即“所以行之者一也”。当以“诚”来说“成”的活动时,“成”的对象便不仅由人推扩到物,而且“成”的内涵亦被引申为帮助人与万物实现其当行之道。强调实现人与万物的当行之道在《中庸》中也就是“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性”是人之为人,物之为物由之以“成”的根据。就人而言,《中庸》曰:“道不远人”;朱熹说:“道者,率性而已。”[2]25是故人之“成”在于尽性、修道,这亦是《中庸》对“成人”的关注,但这里“成人”的界限实已推扩开来,“成人”的意义在于“成人”能够影响“成物”,其中所隐含的逻辑关系是:“尽物之性”以“尽人之性”为逻辑前提;“尽人之性”以“尽其性”为逻辑前提。“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在境界上表现为一个拓展与提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成人”便隐含于“成物”之中,并通过“成物”来体现。如此看来,《中庸》的“成物”思想不仅继承了《论语》的“成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了“成人”的界限,由人及物,从而由“成人”拓展到了“成物”。
由于《中庸》中的“己”与《论语》中的“己”一脉相承,且《中庸》又继承并拓展了《论语》中的“成人”思想,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成物”论,那么从渊源上来看,《中庸》中的“己—物”范式必然可以追溯到《论语》中的“己—人”关系,可以说“己—物”关系是由“己—人”关系在推扩中实现的。
二、“性”通人与物
孔子言“成人”未及于“成物”,说明他对人的关注要远远多于对自然中万物的关注,这在“厩焚不问马”这件事中就有最直接的体现。而子思则不然,相比于孔子,他给予了自然物更多的关注。就物而言,其曰:“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参即三,即人与天、地为三,是《中庸》要达到的价值理想。这意味着从孔子到子思,对人的认识已有了一个质的上升,表现为对“己—物”统一性的看待,而这种统一性在《中庸》一开篇就呈现了出来。
《中庸》首章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此是由生生上说,在生生过程中性由天所命,万物各禀其性以生。这里“天命之性”是形而上的体,说万物生便已落到用处,此由体至用,本体论的下贯路线是《中庸》开篇就着力建构的,于生生之中便已为“己—物”奠定了本体论、存在论的统一性基础。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本体论的下贯路向,《中庸》才能保证万物的统一性。然而,如何理解这种统一性呢?二程、朱熹有“通人、物而言”的说法,其实这就是对“己—物”统一性的确认与表达。二程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天降是于下,万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谓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5]29朱熹曰:“人与物之性皆同,故循人之性则为人道,循马牛之性则为马牛之道。若不循其性,令马耕牛驰,则失其性,而非马牛之道矣,故曰通人、物而言。”[1]1494二程、朱熹所表达的“通人、物而言”的内容其实包含3个方面:其一,体用论中体的统一,在“己—物”关系视域中作为本体的性只能有一个而非多个,且这个性为“己”“物”所共有。其二,道的呈现方式具有统一性,在“己—物”关系中道的呈现全然在于自然,万物皆有其当行的自然之道。其三,体用相即,“己”“物”之道的呈现不离本体之性。形而下之用始终不离体的统摄,故“通人与物而言”在强调“己—物”统一性的同时,更深层面的意义在于为上达路向(成己与成物)确立了所有可能的先天根据。
在《中庸》中,天命之性不掺杂一丝人为因素,为“己”“物”奠定了本体论与存在论的基础。而“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率性与修道就“己”“物”自身而言,若从工夫论、实践论上说,都是上达工夫,但有层次之不同。《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由本体存在论至于工夫实践论,此间存在着不同层面与向度的转换。这种不同路向的转换就像张载所说:“‘自明诚,’由穷理而尽性也;‘自诚明’由尽性而穷理也。”[6]张载认为,由诚而明体现的是天道,是诚体的自明性,此所谓“由尽性而穷理也”。理,即是《中庸》所谓的道,是事物的条理,由性至于道,显示便是天道下贯路向,此即“率性”之谓也。修道,即是穷事事物物之理然后尽其性道而上达路向。性本体视域下这两种路向与可转换性的确立为“成人”与“成物”建构了所有可能的形而上根据。有了这一根据,“成人”与“成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现实的。然而,如何理解“成人”与“成物”在上达路向中与天命之性的这种关联呢?
三、“成己”与“成物”的意涵
在“成己”中,“己”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己,而是“诸己”,也就是承认每个人作为“己”都是主体。对于人而言,我们从一开始就具备“天命之性”,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性。在知与行过程中为己之人便不断使自己具备社会之品格,由此也意味着人脱离了生物的状态,不断使自身进入到社会中来。这一过程对于人来说是必须的,人皆无法避开这个过程;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人才具有成为人的端绪。同时,“天命之性”作为人的本体论存在意义,具有最高价值。人的生活虽然离不开社会的品格,但其终极价值却也需要“天命之性”的诠释,这样人的生命才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才能体现出生命的源动力。所以,“成己”便是指在承认“天命之性”根性的前提下,承认自己作为社会的存在,需要由社会状态重新升华到“己”的本体论状态,也就是要重新得到“天命之性”的提携,在上达工夫中实现“尽其性”。故而,人的生活不仅仅是社会化的状态,也不仅仅是本体论的状态,而是中国哲学中体现的“天人之际”的状态。也许生活本来就是由各种各样的矛盾所牵引着,在“成己”这个话题中,人既要依托社会来生存,又要想尽办法逃离这样的社会,不得沉溺其中。可想而知,对“成己”来说,最难的就是要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最终以求得中庸的生活方式。
“成物”不同于“成己”。“成己”在于强调自己的主体自成性;而对“成物”来说,此时的物不管是作为对象的他人来看,还是作为对象的它物来看,皆是被成就者,成的主体皆属于“己”而非作为对象的他人或它物。因为就作为对象的它物而言,人与它物虽然皆禀性成形,但在气化流行中,人却与它物所受之气不同。人所禀之气最清,它物在禀受时会受浊气的影响,以至于受到染蔽,同时也会产生惰性,这便使得“天命之性”在它物中不能完全贯彻下来。如同牟宗三先生所说:“在人处,义理本然之性能在气质里面有多样的表现,此以直线表之,即示本然之性能进到气质里面来;在物处,无此中直线,即表示本然之性不能进到其气与质之里面来有多样之显现,只收缩而为其存在之理,使之成为如是个体之定然之性。”[7]105由于受“气异”的影响,“天命之性”在作为对象的它物处便会收缩为个体的存在之理。基于此,在“成物”的活动中,作为对象的它物难免有所缺陷,无法至于明达于诚。是故,作为对象的它物的价值及其意义最终只能由生命通透的“己”,也就是“圣人”实现出来。对作为对象的他人来说,本然之性虽然能进入到其气质当中来,但总有人“习心”太重同样会使其“天命之性”受到染蔽,故需要有圣人立教,教其明而后诚,此一为教之道就是“成物”的第二义,即成(就)他人。
尽他人、它物之性,实现他人与它物的价值,在现实中往往不能凭空产生。杨国荣先生在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一书中,就将“成”的可能性依托于意义世界之中。当他人与它物皆有其主体对象并处在人化世界中时,意义便随之生成,此意义境域常常于“事”中呈现出来。对于“物”与“事”的关联,郑玄在注疏《大学》之时有言:“物,万物也,亦事也。”[8]后来,朱熹和王阳明也继承了这一思想。朱熹亦言:“物,犹事也。”[2]5王阳明言:“物即事也。”[9]47王夫之亦言:“物,谓事也,事不成之谓无物。”[10]很多思想家在看待“物”与“事”时便将它们统一了起来。这里的统一不是在“物”处于本然形态时的统一,亦不是“物”只保持自身物理性质而独立于人的统一,在这两种状态下,“物”的状态不能呈现出意义与现实性。“物”如果要呈现自身的意义,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出来,只有在与人的关系情景中才能显现。而这也正是人们将“物”当成“事”的意义所在,只有将“物”理解成“事”,他人、它物与主体才能融合起来。而要于“事”中成“物”,建构其意义世界便需要人于“物”处“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由此《中庸》中才有此感叹:“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2]36
其实,“成己”与“成物”虽然有着不同的指向,但作为实践论,“成己”与“成物”在整个过程中则是统一的,不可割裂。人无法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处于社会之中便意味着必然要接触作为对象的他人与它物,故“成己”往往在“成物”中才能实现其价值理想;同样,“成物”的实现必然以“成己”为前提条件。如果自身的生命未挺立起来,那又怎么能够超出自身的界限去“成物”呢?作为过程性的统一,“成物”的过程便意味着“成己”,“成己”的过程同样亦归属于“成物”的过程,“成己”与“成物”相互渗透。
四、“尽性”而“成己”与“成物”
既然“天命之谓性”中蕴含着“己—物”由之以“成”的当行之道,那么以“尽性”为最高实现理想,“己”在上达的路向中如何才能具体实现“成己”与“成物”呢?
《中庸》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2]34“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2]39“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是“赞天地之化育”与“与天地参”的另一种表述。这里《中庸》认为唯“至诚”才可“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这便涉及到何为“至诚”以及“诚”与“性”是何关系以及在“成己”与“成物”中怎样实现“天命之性”等问题。
何为“至诚”?程颐有言曰:“无妄者,至诚也”[5]822,后来理学、心学代表人物皆继承了这一说法。朱熹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2]32王阳明亦曰:“夫诚者,无妄之谓。”[9]235以“无妄”释“诚”,就是指明“诚”的本真状态,不掺杂任何的私欲杂念。不掺杂任何的私欲杂念并不是说“诚”具有某种命定论的色彩。人作为主体本身就具有自主性,具有自主选择的能力。这里以“诚”说人与物,当且仅当是在指明“成”的目的指向性,说明人与万物在“成”的过程中皆有其应然的存在状态,皆应按当行之道去实现自身。而这种应然性与当行之道便是“天命之性”或“性”。
“诚”与“性”是何关系?就此来看,“诚”乃是就“性”说,是“性”的另一呈现方式,就像牟宗三所说:“性与天道皆只是一诚体。性与天道是形式地说、客观地说,而诚则更是内容地说、主观地说”[7]341。“诚”与“性”虽有各自特定的意义指向,但就本体论而言是一个东西。其实,《中庸》言“诚”,本就有着不同的维度。其言“诚者,天之道也”,朱熹说到:“诚者真实无妄,天理之本然也”[2]32。诚者,“天理本然也”,这便是由本体论的层面上说“诚”,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诚”与“性”“天”其实是一个东西。是故二程、牟宗三皆是在“诚者”的意义上谈“诚”与“性”的相关关系的。除此之外,《中庸》亦言:“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说到:“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2]32“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这是由工夫上说的。“诚”,于《中庸》中有着明确的分层以及指向性。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中庸》讲:“自诚明,谓之性”;在用的层面上,其又言:“自明诚,谓之教”。由诚而明,即朱熹所言“所性而有者,天道也”[2]33;由明而诚,即朱熹所言“由教而入者,人道也”[2]33。由诚而明是“天命之性”下贯的路径,由明而诚则为尽性上达的路径。前者为天道流行,后者为人道工夫。
由于“成己”的施与者是诸己,“成物”的施与者却不是诸己,而是圣心开显的“己”,即“圣人”。在圣心开显的情形下,“己”才能成就他人与它物之性,“成己”与“成物”才具有现实性。为了使“成己”与“成物”成为现实,诸己如何达于圣心开显的状态呢?此便属于“诚之者,人之道也”的范畴,是人道工夫的直接展现。对于“诚之者”而言,人道上达工夫在《中庸》中有两处呈现。其一,《中庸》曰:“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2]32“择善固执”是“诚之”工夫展开的一个方面。朱熹曰:“择善,学知以下之事。固执,利行以下之事也。”[2]32“择善”“固执”呈现的便是知与行的问题,此知行问题后面被《中庸》看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朱熹认为:“此诚之目也。”[2]32也就是说,“诚之”工夫便由学、问、思、辩、行组成。朱熹曰:“学、问、思、辩,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2]32此“诚之目”在朱熹看来皆不离知与仁。而《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学、问、思、辩、行在于说明“诚之”工夫的可施行性;同时也说明此工夫论的施行不仅在于知,更在于仁,在于德,这便是“诚之”工夫论的第一个方面。其二,《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2]34朱熹曰:“其次,通大贤以下诚有未至者而言也。”[2]34诚有未至,是故需要行“致曲”之工夫,以“致曲”为工夫,“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2]34,则能形、著、明、动、变,以至于化。朱熹曰:“形者,积中而发外。著,则又加显矣。明,则又有光辉发越之盛也。动者,诚能动物。变者,物从而变。化,则有不知其所以然者。”[2]34由此来看,形、著、明为内在的方面,而动、变、化皆为外在的方面,整个过程表现为“诚之”工夫,其实已经在“尽性”了。诸己经过这个过程便能明,自明而诚便可以优入圣域、“成己”“成物”了,此便是“诚之”的第二个方面。
可以看到,在“成己”与“成物”中,“‘诚’不仅是一种存在状态,而且是一种生成过程。‘诚’作为存在状态意指人性的终极实在,而作为一个生成过程,则意指人在具体日常事物中实现这种实在的必然道路。所以‘诚’不仅象征着一个人在终极意义上的应然,而且象征着一个人最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具体方式。”并且,“‘诚’一旦自我完成,它就不局限于个人,也不局限于人类这个领域。‘诚’是有个自我决定的完成过程的,它的力量是自己生成的,它的运动方向也是由内部决定的。”[11]就“己”而言,“成”的整个过程虽然“己”都在不断实现和完成自身与他人、它物,但其意义其实也就在于以“诚之”工夫为前提,实现自身“天命之性”的同时,能够帮助他人与作为对象的它物实现出其“本然状态”;他人、它物之“成”的可能性还是存在于他们自身之中。“天”作为本然状态当然不能直接实现出来,但天理流行的过程在下贯可以表现为“性”,当万事万物在“诚者”之“成”的助援中显现自身的时候,“性”不仅在人这里流行起来,亦在万物中实现出来。
而当“性”于“生生”中显现出来的时候,其自身之中本就内含着差别性。由此,就人来说,我们应承认这种差别的存在,做到“以人治人”,让万物皆以其当行之道来显现自身,而不是对待外在对象的时候都千篇一律。就像《中庸》所说的:“诗云:‘伐柯法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2]25作为斧柄,手里拿的斧柄和即将要做成的斧柄原理一致,它们都得成为斧柄;即使是这样,即将做成的斧柄毕竟和已经握在手里的斧柄不可能完全相同。即将要做成的斧柄在材质、长短、粗细上都不能取决于已经握在手里的这根斧柄,而是取决于即将要成为斧柄的这根木头的材质,以及与之相配的斧头的真实情况。因此,斧柄的可能性就存在于斧柄自身之中。
这里《中庸》以斧柄喻人,对个体来说,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它物,都有不同的展现方式,都有呈现不同本性的可能性。个体的存在法则只存在于个体自身之中,某个个别的存在法则不应强加于所有对象。众人、所有事物的法则也不一定适合于所有个体,所以,自己与他人或它物相交接时只能以“以人治人”(以其当行之道)的方式打开。正如朱熹所说:“若以人治人,则所以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初无彼此之别。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25君子在处事中需注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承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且推扩开来至于物,便意味着以物之道来看物。这便需要在面对每个个体的时候做到随其性而行。“以人治人”既然承认多种本性共同展开的可能性,那么“自我”的法则与他人、它物之本性都同时在场。以自我的法则能够实现“我”自身,承认了这一点,也就承认了他人、它物的法则同时也在场,他人、它物的法则也就有可能抵达他人、它物自身。所以,这里不存在为了实现自我而牺牲他人或它物的情形,也不存在为了实现他人、它物而限制自我的现象。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世界,也可能某个个体在不同时段有着多重世界,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完完全全接纳自身以外所存在的可能性,承认不同当行之道的合理性;同时,给自己以可能性,给世界以多样性。
注释:
⑴涂可国先生提出了“己—人”范式与“己—物”范式。参见涂可国《儒家成己成人说新解》(《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56-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