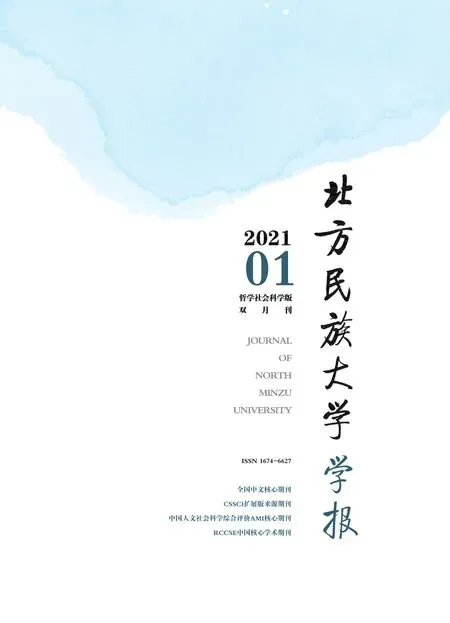从礼仪到象征:阈限理论在西方学界的学术发展路径
2021-11-28张峰峰
张峰峰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人类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性社会科学,自其诞生以来,一直充满着无限的理论张力和活力,这既体现在古典进化论学派、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文化心理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人类学学派的多元性方面,也体现在多种学科与人类学交叉结合所形成的各大小分支学科中,如体质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心理人类学、教育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景观人类学、分子人类学、旅游人类学、情感人类学等等。凡此种种,莫不反映出人类学重要的理论价值,其研究方法、视角所体现的特殊性和普适性对多个学科都带来了重要借鉴和启发。在这其中,本文议及的阈限理论及与之相关的过渡礼仪、仪式过程、交融、近阈限等概念原本作为人类学仪式研究中的重要理论,但在国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广泛普适性,频繁地见诸多个学科的研究中,可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借鉴意义,为解析多种特定的时间、空间单元以及多样的体验、经历带来有益的启迪。国内学者虽多将阈限理论应用于仪式研究中,但较少论及阈限理论在国外学界的新发展。本文追溯了阈限理论及相关概念的发展线索,重点梳理近年来国外学界对相关理论的新发展。
一、从范热内普到特纳:阈限理论的发展线索
阈限理论源自法国民族学家、民俗学家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1873~1957)出版于1909年关于礼仪过程研究的法文著作Les Rites de Passage(Rites of Passage)[1],中译本为《过渡礼仪》[2],过渡礼仪又被译作“通过仪式”“通过礼仪”等。范热内普通晓18种语言,掌握了世界多地的民族志,他认为,当时的学界虽然论及礼仪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但却缺乏对礼仪的分类研究。这是基于他对19~20世纪之交诸多人类学家或民俗学家研究成果的认知,包括弗雷泽(Frazer)、泰勒(Taylor)、哈特兰(Edwin Hartland)、朗格(Andrew Lang)等[3](23)。范热内普认为,可将某个单独的礼仪视为感应性礼仪或感染性礼仪,也可以从泛灵论(animism)或动力论(dynamism)的角度进行划分,还可将其视为直接礼仪或间接礼仪、主动礼仪或被动礼仪,故而,同一礼仪可以用若干方法加以阐释。在此基础上,他重点讨论了礼仪的进程特征,针对个体从一个确定的境地到另一个同样确定的境地、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的过渡仪式进程,单独归纳出过渡礼仪。过渡礼仪可分为分隔礼仪(阈限前preliminal)、边缘礼仪(阈限,liminal)、聚合礼仪(阈限后,postliminal),三者可作为过渡礼仪的完整模式,却又并非同等重要,一些边缘礼仪本身也被划分为独立阶段,他将诸种礼仪的属性归纳为巫术—宗教性质,并结合世界各地的民族志材料,研究了地域过渡、个体与群体、怀孕与分娩、诞生与童年、成人礼仪、订婚与结婚、丧葬等各类过渡礼仪,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然而,范热内普的上述研究成果问世后,在较长时间内未能得到主流学界的重视,这与法国社会学、人类学界的派系之争、观点差异等有重要关系,也与范热内普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有关。法国学者贝尔蒙特(N.Belmont)在为范热内普所作传记中指出,其著作被同时期学者低估,马塞尔·莫斯(M.Mauss)指责该著作者除了各地的过渡礼仪外,无任何发现,也指责将这一定律视为统摄所有宗教表象的说法,指摘其将这视为自古希腊至尼采所有哲学思想本身的节律和来源。实际上,范热内普仅针对特定民族即钦族(Lushei)提及了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的概念,因为他们并非将生命模式视为直线型的,而是循环型的,自生到死,再由死到生。莫斯勉强接受了过渡礼仪的概念,但认为它仅仅是一种自明之理,还否认了作者提出的礼仪中必然存在的分隔、边缘、聚合这三种序列,他还批评了英国人类学派纵横于整个历史及民族志,而不是致力于分析数个典型的、准确研究的事实中[4](62~63)。诸如此类的评论使得该著在此后几十年内皆湮没无闻。
根据丹麦学者托马森(B.Thomassen)所做的学术史回顾[5](47~70),《过渡礼仪》一书出版之时,法国人类学界正由杜尔凯姆(E.Durkheim)及其外甥莫斯所领导的社会学年鉴学派占据统治地位,范热内普长期受到莫斯等人的压制并颠沛流离,未能在法国知名学府和科研院所谋得任何职务。他仅在瑞士纳沙泰尔大学担任学术职务,他在欧洲和北美的诸多大学做过演讲,但其中无一所法国大学。这也导致其本人长期默默无闻,其学术贡献鲜为外界所知。范热内普曾多次刊文批判杜尔凯姆的研究,阐明杜尔凯姆在理论层面存有缺陷,在资料收集方面缺乏批判性,但却未收到杜尔凯姆的正面回应,并于20世纪20年代由人类学转向了民俗学研究。范热内普的研究在1960年前的主流人类学界影响甚微,鲜有学者参阅。据考证,美国人类学家劳丁(P.Raudin)于1937年较早地参考了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理论[6](39~60)。另如,美国学者尤因(J.Ewing)在1958年发表的论文虽然运用了过渡礼仪这一术语,但其文章对范热内普及其礼仪研究理论未做任何提及[7]。
直至1960年,即范热内普离世3年之后,亦值其代表著作出版半个世纪有余之时,其英文版方由美国学者翻译并出版,该书由维兹德姆(M.Vizedom)等人翻译,人类学家金伯尔(S.Kimball)在序言中以长文加以推介[8]。该译本的出版无疑促使当时的英美主流人类学界重新发现了范热内普这样一位天才式的学者,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利奇(E.Leach)、尼德海姆(R.Needham)、普理查德(E.Pritchard)等在阅读该著后,皆曾质疑范热内普为何未能在法国人类学界受到足够的关注[9]。这也体现在以格拉克曼(M.Gluckman)为代表的英国曼彻斯特学派对范热内普的关注方面,正是由于英美学者的推崇和宣传,范热内普才能够为主流人类学界所熟知。尤其是特纳(Victor Turner)对礼仪研究理论加以深入发展,将其运用于个人研究中,并提出了更多相关概念,对阈限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范热内普离世后,法国学者贝尔蒙特(N.Belmont)专门为其立传[10],称其为法国民族志的缔造者、法国现代民俗学的奠基人,该传记的英文版于1979年问世[4]。美国学者朱瓦特(Zumwalt)于1988年为范热内普撰写了学术传记,称其为波格拉莱(Bourg la Reine)的隐士、法国民俗学大师。该传记篇幅虽然不长,却较为集中地展现了范热内普的生平、主要学术成果,总结了他在民族志、民俗学方面的贡献,进一步揭示了他与法国学界的关系,指出他在1924年之前主要从事民族志研究,此后则主要从事民俗学研究[3](18~19)。
金伯尔在《过渡礼仪》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当时(1960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过渡礼仪理论尚未融入社会学理论思想中,除了应用于心理学领域外,其他学科很少利用该理论进行分析[8](XIV)。这一事实也体现在与特纳同时代的英国人类学者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研究中,她于1966年出版了代表性著作《洁净与危险》[11],在该书中,她虽借用了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但全书并未使用阈限(liminal)一词,而是使用边缘(marginal)一词来指代之。这表明,当时的学者只是初步接触到范热内普的相关理论,但并未深入发展阈限理论,即使在人类学界,阈限一词也尚未流行开来。然而,随着特纳的推动和发展,阈限理论逐渐在人类学及其他学科中广为流传。
特纳本来也是曼彻斯特学派的成员,他在格拉克曼的指导下前往赞比亚的恩登布部落做田野调查,并于1955年取得博士学位。1963年,他在等待赴美签证的过程中,阅读了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在此过程中,他不禁将个人境遇与书中提及的阈限礼仪阶段相联系。这是因为,当时的特纳已经辞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工作,准备赴美任教,但他因曾拒绝在“二战”中服兵役,未能顺利获得美国签证,唯有苦苦等待,这时的他正处于漂泊不定的状态中,因此,特纳在切身体验中深受范热内普过渡礼仪理论的启发,于是在正式抵达美国任教后,他进一步发掘了过渡礼仪研究的学术价值,强调了过渡礼仪中阈限阶段的重要性,从中提炼出阈限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对赞比亚恩登布人的仪式研究之中。需要指出的是,特纳与范热内普的理论侧重点存在不同,朱瓦特即指出,特纳更强调置身于有序世界之外的阈限方面,即介于有序普通生活类型之间的模棱两可的阶段。范热内普所设定的边缘礼仪或阈限礼仪,是为了阐释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程,更聚焦于不同阶段之间的模式化关系,而不是聚焦于缺乏秩序的阈限阶段中[3](25)。特纳早年供职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主要受到英国人类学的影响,与法国人类学界内部学术斗争并无关联,因而能够客观评价并发展范热内普的理论,他本人受益于格拉克曼的指导,格拉克曼强调对社会情境的研究,这启发了特纳提出社会戏剧理论,南非人类学家库珀(A.Kuper)指出,在以格拉克曼为中心的曼彻斯特学派中,特纳对中非的研究最富创造力[12](149~166,186)。
特纳对阈限理论的深入发展突出地体现在其《象征之林》[13]一书中,该书第四章“模棱两可:过渡礼仪中的阈限阶段”,结合理论和民族志,深入阐释了阈限仪式的过程和状态,其后,他又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14][15],进一步发展了阈限理论,特纳特别发展了范热内普所论过渡礼仪的中间阶段,在阈限概念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多个相关概念,如近阈限(liminoid)、交融(communitas)、反结构(anti-structure)等,这就使得阈限理论逐渐超出了仪式、礼仪研究的范畴,具备了广泛的象征意义,成为象征人类学领域的重要理论。根据特纳的阐释,阈限具有不清晰、不确定的特点,其实体既不在此处,也不在彼处,而是处于法律、习俗、传统和典礼所指定或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间的地方;交融为具体性、历史性和特异性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卑微与神圣、同质与同志的混合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模式,结构与交融的差异,即世俗与神圣的区别,二者存在多重意义的对立,交融以阈限或边缘的形式进入结构的缝隙或边缘处;交融主要有自生的交融、规范的交融和空想的交融三种形式。
特纳发展了范热内普的阈限理论,使之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广为人知,不仅成为人类学界的重要术语,也被广泛地运用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初,特纳主要在恩登布部落社会的仪式研究中运用阈限理论,实际上,阈限理论的价值远超小型社会,跨越了狭义人类学的限定范围,也不仅仅运用于民族志研究中[6](46)。特纳还研究了复杂工业社会背景下的近阈限行为,这首先表现为实验性或理论性科学研究本身,与之相关的技术创新,即创意产品,产生于实验室或研究机构;近阈限又主要表现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休闲业,包括戏剧、音乐、小说、电影、运动、艺术等方面。他指出,与近阈限相比,阈限主要源自部落制和农耕社会,表现为机械性的团结及集体性的体验,是为了融入整个社会过程,具体表现在教堂、宗派、某些运动的活动中,以及俱乐部、兄弟会、神秘社会的入会方面;而近阈限过程主要产生于工业社会,基于契约关系,强调个体化,由过渡礼仪分离而出,表现为个体性的创造或休闲活动中的产品,具体表现为大规模工业社会中的艺术、运动、消遣、游戏等内容[16]。一部分学者延续这一视角,将艺术、剧场、休闲等作为近阈限现象加以研究,这集中体现在格拉哈姆·约翰(Graham John)主编的《特纳与当代的文化表演》一书中,在该著中,多位学者结合媒介、旅行、戏剧、购物、体育运动、音乐表演等进一步阐释和运用了特纳的相关理论[17]。
无疑,特纳为推动阈限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他在仪式研究中的具体实践和运用,使得学界对范热内普本人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也发掘出阈限理论的应用价值。近年来,以丹麦学者托马森、匈牙利学者绍科尔采(A.Szakolczai)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进一步将阈限理论运用于实际研究中,他们也结合学术史的追溯,对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了新的诠释,拓展了阈限理论的适用范围,深入探讨了其理论内涵。
二、托马森、绍科尔采等学者对阈限理论的新发展
特纳在晚年意识到现代工业社会不同于其所研究的恩登布部落社会,其关注视角由部落社会转向了复杂工业社会,并提出了近阈限的概念。美国学者蒂弗勒姆(M.Deflem)指出,近阈限是复杂工业社会中个人或特定群体付出的结果,具有持续生产性,它源自经济、政治和结构性过程的边界之外,它通过向社会秩序提供社会批评或为社会秩序的革命性重构提供建议[18]。托马森则指出了近阈限理论的缺陷,他认为,将现代社会中的阈限主要理解为艺术、休闲,使得阈限中一些明确存在危险性或存在问题的方面退出相关理论;特纳对近阈限的讨论,简化了传统与现代象征体系间的对立;与阈限经历相比,近阈限体验属于选择性的,它与对个人危机或个人身份变迁的处置并无关联,近阈限缺乏阈限的关键阶段,即过渡;特纳轻视了阈限时刻或体验会在多大程度上平等呈现于政治或社会转型中,即在文化之外,以一种狭义方式理解这一术语[19]。
绍科尔采亦提及,特纳所发展的阈限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得主流人类学家认为阈限在小型部落制社会之外并不成立。特纳认为,更先进的社会只拥有近阈限而非主体性的阈限情境,而且特纳对阈限持乐观态度,这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颂扬矛盾性、变动性、不确定性和创造力,解构了严格和僵化的社会结构,而这些社会结构通常被认为具备过去的和传统的特点[20]。从中可见,近阈限理论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显得狭隘,正是基于这些问题,托马森发展了阈限的类型,列出了多种阈限,他认为,多种模棱两可或模糊不定的事物,均可被视为阈限,并将其广泛地运用于时间和空间研究中。他将阈限划分为三大类,即体验型阈限、时间维度的阈限、空间维度的阈限。其中,根据体验性阈限的不同主体,将其划分为个体、社会群体和全社会(全部人口或各文明)三大类型;根据时段的不同,将时间维度的阈限划分为某个时刻(突发事件)、某个阶段(数周、数月、数年)和某个时代(数十年、数代人或数世纪);根据空间大小,将空间维度的阈限划分为特定地点或门槛,区域或地带(国家间的边疆地区、寺庙、监狱、机场、海洋度假胜地等),国家或更大地区与陆地(美索不达米亚、地中海、古巴勒斯坦、古希腊的爱奥尼亚等)[19]。这种划分方法使阈限研究对象广义化,使得不同主体与不同时间、空间单位,因其所处的特殊临界状态(模棱两可、模糊不定),皆可被视为不同的阈限类型来加以研究。
实际上,在托马森的相关研究出现之前,多位学者已将广义的阈限理论运用于其个人研究中,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Eisenstadt)曾与特纳有过合作经历,他意识到阈限概念可以用于理解变迁以及大规模变迁背景下的延续性问题,他指出,要把阈限发展成一个概念性的工具,还需要进一步明晰,这个小型社会礼仪模式背景下使用的概念必须扩展成真实世界里的大型阈限[21](371)。英国学者唐南(H.Donnan)和美国学者威尔逊(T.M.Wilson)在国际边疆、边界研究中指出,阈限是一种空隙状态,即由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生存状态转变的经历,由此借用阈限空间来比喻国际边界中的生活状态以及边界在其社会系统中的角色[22](66)。
2000年以来,绍科尔采将阈限理论运用于个人和集体阈限、时间和空间的研究中,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出版了《反思性历史社会学》一书,在该著中,绍科尔采借用阈限理论,对诸多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家的人生经历及其学术路径进行了重构和解析。在此基础上,以现代性视角论及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准入仪式、资格测试与通过仪式间的内在关系,阐述了埃利亚斯所提出的变迁时期与阈限性境遇的类似性,就沃格林所提的间体(Metaxy)概念与阈限性的内在相似性进行了说明,还特别论及福柯所关注的边缘性研究,阐释了边缘性与阈限性的紧密关系。在这些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作为永久阈限的现代性这一概念,认为有必要将阈限概念从狭义拓展到广义,“这一概念很有可能成为社会科学里最普遍和最有用的概念之一,堪比于结构、秩序和机制等为人熟知的概念”[23](318~319)。绍科尔采借助阈限理论,对现代性的内涵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剖析,凸显了这一理论的活力和价值。绍科尔采又以长文讨论了阈限性在人类学、哲学和社会学中的跨学科联系,表明阈限有助于研究秩序瓦解背景下的事件或境遇,也有助于理解机制或结构的构成,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对阈限性的忽视,以及社会、政治生活对阈限性的忽视,皆会对全面理解现代性造成严重障碍。他通过追溯康德、尼采、狄尔泰等人对体验的论述,总结出阈限性并非源自德国的理想主义、法国的理性主义、英国的实证主义,而是源自法国的社会和文化人类学,阈限性应该成为社会思想和哲学领域内的一个关键术语,其应用范围可以与韦伯的卡里斯玛(charisma)、福柯的话语相比[24]。
在新近的研究中,绍科尔采通过阈限理论解析了一种被称为社会繁荣的另类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由此理解全球化的现代发展历程。他指出,产生于人类学过渡礼仪的阈限性尤其有助于历史社会学家,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展现方式:如何以一种连贯的方式去解析过渡时刻所发生的事物,即当现存边界消解而新的边界产生的时候,韦伯所提出的反常情境可以被视为现实世界中的大规模阈限时刻。而纯粹的顿悟就是那些神圣的体验,即那种并未被直接称为突发的阈限境遇的体验过程[25]。近年来,在国外学界,阈限一词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的一个重要术语,用于指代模糊的、过渡的或时空的中间地带[26](3)。
托马森也在相关研究方面居于学界前沿,近年来,他发表了多篇论文,从学术史角度集中追溯了范热内普、特纳的生平经历及其学术贡献,讨论了范热内普与杜尔凯姆、莫斯的关系,从广义上提出了多种类型的阈限,在他的推动下,《过渡礼仪》一书的法文版出版一百周年之时(200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等机构主办的《国际政治人类学》杂志以专版发表了多位学者有关阈限研究的论文,托马森、绍科尔采等学者皆在其中刊文,该专版标志着国外学界在阈限理论研究方面进入了新阶段。此外,托马森将雅斯贝斯(K.Jaspers)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解为一个阈限历史阶段,认为轴心时代的创举实际发生在地理阈限区域内[27]。他还借助阈限理论阐释政治革命,认为政治革命代表着大规模阈限情境,可以从阈限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认识政治革命的完整过程,而阈限所代表的事件、思想和事实本身可以被推至不同的方向,阈限理论具有将政治变迁理论推至不同方向的潜力,人类学也可以丰富并补充政治科学[28]。
托马森的著作《阈限与现代:中间状态中的生存》汇集了他近年来对阈限理论的研究成果,更为系统地发展了阈限理论。在该著中,他认为,阈限理论具有推动社会和政治理论向新的方向发展的潜能,他将阈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将其与结构、机制理论相提并论[5](1)。在该书中,他从学术史角度系统讨论了特纳对阈限理论的发展和贡献,阐释了广义上的不同类型的阈限,补充了仿习(imitation)、分裂演化(schismogenesis)、机智人物(trickster)等概念,表明类似术语具有阈限的某些特征。他对阈限理论的直接发展主要表现在提出阈限空间(limivoid)这一概念,他重点分析了休闲娱乐业中的蹦极。蹦极作为一种接近死亡过程的特殊体验,是一种极限运动和冒险旅行,也是一种临界体验,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阈限空间的概念,将其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包含边界含义和临界体验[5](168~169)。托马森的相关阐释使我们对阈限理论的缘起和发展的理解更为立体和丰富,无论是他在学术史上的发掘和贡献,还是他对阈限理论在当下的适用性分析,皆有助于深入认知阈限理论的内涵,进一步利用相关理论分析同类事物或过程。
阈限理论已经逐步超越了人类学的学科范畴,成为一种具有广泛象征意义的概念,后殖民主义研究代表人物霍米·巴巴(Homi Bhabha)指出,阈限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具有重要价值,它可避免身份称呼上的两极分化,如上层与下层、黑与白等名称即存在随意性,同时,其重要性表现在阈限性和混杂性是相伴而生的,不同固定身份间的空隙为文化混杂创造了一种可能,即存在无须假定的或强加性层次化的区别[29](145~146)。这表明,阈限理论有助于深入认知后殖民主义的一些关键性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阈限理论即被运用于组织管理方面的研究,如瑞典学者卡斯滕(C.Garsten)根据她在瑞典和美国所进行的调查和访谈,以阈限视角研究了现代组织中的弹性员工和临时工[30]。加拿大学者巴姆博(M.Bamber)等结合阈限理论,以英国20所研究型大学中专门从事教学的教师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大学的内部管理[31]。上述研究系阈限理论在管理学领域的具体运用,不定状态的概念不同于过渡性阈限或固定阈限,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了阈限理论。
在由霍瓦特(A.Hovath)等主编的《打破边界:阈限的多种多样》[32]一书中,多位学者结合社会过程和政治视角,运用阈限概念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研究,如门内尔(S.Mennell)运用阈限理论重新考查了美国19世纪的西进运动,将其称为美国的民族体验,并努力寻求阈限与弗里德里克·特纳(F.Turner)“边疆假说”之间的关联性。罗曼(C.Roman)分析了法国大革命中对路易十六的处决事件,对国王的被审判和被处决以及事件所散发的创造性精神力量进行了阈限分析。彼得森(M.Peterson)将革命视为一种阈限体验,探究了埃及革命所呈现的复杂具体的社会戏剧。维德拉(H.Wydra)分析了革命情境下的权力真空问题。马尔科苏(M.Malksoo)将阈限引入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将战争与战事视为大型的阈限体验。
上述研究仅为近年来国外学界在阈限理论运用方面的代表性成果,由于相关成果较多,无法一一列举,从中可以管窥阈限理论在国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价值和潜能,相关理论的实际运用通常与中间性的身份和地位相关,也与特定阶段的过程或过渡相关。阈限概念已运用于冲突研究、国际关系、文学、商业研究、咨询、心理、教学、戏剧、休闲、艺术及流行文化等多个领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一种关键性分析工具[32](7~8)。这也印证了前文议及的绍科尔采的一些学术判断和预见,《过渡礼仪》的中文译者张举文也曾指出:“不能静态地看待过渡礼仪中的‘边缘’,但可以将此概念应用于对非仪式性的社会现象的分析,如‘移民’、‘散居民’或‘族群互动’等,这一点在当下具有特别意义”[2](序言15)。他所指的边缘应即阈限,从中可推及阈限理论也可运用于全球化过程中的跨国主义、跨国移民、散居族群等方面的研究,亦有助于从新的理论视角定位边疆、边界的特殊性,可以进一步推动国际边疆、边界研究,还可用于界定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段,突出阈限理论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等。
三、结 语
阈限理论虽于20世纪初即发端于人类学,但因派系之争,长期未能受到主流学界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学界对范热内普本人及其理论的“重新发现”,加之特纳的实际运用和推动,阈限理论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具备了广泛的象征意义和价值,成为政治人类学、象征人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术语,远远超越了人类学礼仪研究的范畴。近年来,以托马森、绍科尔采为代表的学者从相关学术史的梳理着手,结合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和全球化、后现代性等视角,多方面深入发掘和阐释了阈限理论的内在学理性和学术价值,进一步将其运用于实际研究中,取得了诸多成果,促进了阈限理论的深入发展。而阈限一词也逐渐成为国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高频词,广泛地见诸多种学科研究成果之中,过渡礼仪、阈限、近阈限等术语也广泛出现在国外大众传播媒介中,俨然成为耳熟能详的阐释工具和概念。这些新近的研究趋势凸显出阈限理论蕴藏的强大理论活力和生命力,对于分析和研究多种特定情境或事物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