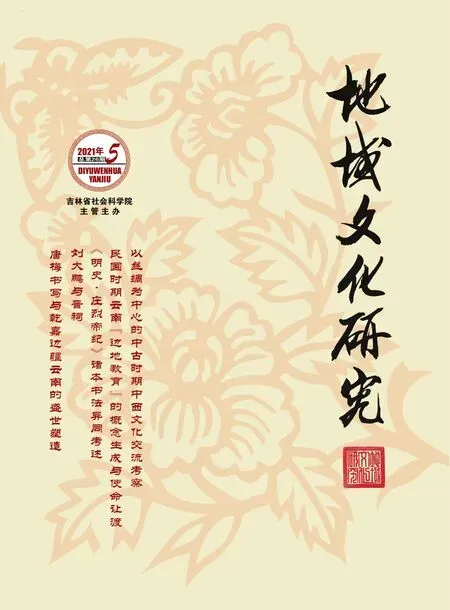先秦“孔颜之乐”美学思想探微
2021-11-26吴鹏
吴 鹏
自先秦孔子建立“仁”教以来,一直将“仁”视为实现“孔颜之乐”境界的重要标志。从“三月不违仁”与“吾与点也”等论述中可以看出,“仁”是“孔颜之乐”的核心。它一方面结合了“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的道德伦理情感,同时也提供了指导人实践活动的道德理性原则。孔子能够将“仁”发用为“游于艺”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乐仁”境界,也就呈现出了个体人格之美。所以,“孔颜之乐”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乐”的美学境界,就在于能够将“乐”之境作为个体情理交融的状态,同时也是将“仁”呈现于现实世界中,与现实的情感结合所产生的那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之“乐仁”境界。具体到人身上,就形成了孔、颜以及曾点的完美人格形象,具有高尚的品德与丰富的美学内涵。
一、“乐仁”:儒家境界的美学基础
在儒家的思想道德观念中,能够实现“仁”的一定是具有高尚道德品质与勇于承担天下大任的君子,而其所呈现的境界也不脱离日用之常。它是后世的儒学者一直致力探索并通过自身生命来实践过的境界,并能为作为后世行为的典范。因此,达到“仁”之境界的圣人必能将“仁”作为生命实践的目的并将其贯彻始终,以足以为后世师法。事实上,“仁”作为人的社会伦理不仅能够作为人的实践行为依据,而且本身也带有一定的道德伦理情感,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体。故在孔子及其弟子中,作为“孝悌”的情感与作为伦理价值的“仁”具有一致的作用。所以《论语》中强调:“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57页。。在宰予认为三年孝期过长且安于锦衣玉食时,孔子怒斥其“予之不仁也!”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26页。可以看出,孝悌之情感是“仁”的表现,而“仁”作为孝悌情感的来源,具有判定现实行为是否正确的绝对的标准。所以,在家国一体、以血缘为基础的政治观念上,“仁”实际上能够作为社会各个层面、各种活动的价值来源与判断基础。故无论是“孝悌”之情感,还是是否“犯上作乱”的判断依据,实际上都要以“仁”这种社会普遍的伦理为基础。同时,“仁”的另外一种作用就在于,它能够在现实中检验人的道德动机,即是所谓孔子的“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③(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02页。也是《孟子》中所提到的“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④(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27页。指明了“仁”作为一种生命价值是需要内在的认同并以此作为实践活动的准则。
从“仁”而言,在孔子看来,自己所传述的“仁”的道理都是不言自明的,是内置于人自身之中的先天道德。由此他才说:“子曰:‘予欲无言。’子贡:‘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⑤(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26页。在这个问题上,的确触动了孔子之道的本质问题,所以孔子弟子会叹言:“子罕言利与命与仁。”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9页。子贡也会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⑦(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4页。可见,“性与天道”与“仁”之问题,对孔子来说,更加接近“指点语”,也就是“能近取譬”⑧(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9页。是不可以语言说的道体本身,而只能从日用之常的表现来呈现“仁”之体。所以孔子才说“吾道一以贯之”⑨(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1页。的时候,曾子所回的“唯!”⑩(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1页。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⑪(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1页。都也只是随事而发的指点语,而不是对“仁”本质的归纳。故子贡在请教“一言可以终身行者”时,孔子也是随事而发,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18页。。而仲弓在请教“仁”时也说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⑬(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02页。故可以推断出,所谓“一以贯之”,并不是说用“忠恕之道”来定义“仁”,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事情来将“仁”道说清楚,说明白,并通过日常之道来上接“天道”。这实际上也是“仁”之沟通天道与人事,实现“天人合一”境界的标志之一。故在《礼记·中庸》中强调:“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⑭(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27页。可以看出,“忠恕之道”作为“仁”的表现,它只是“仁”在现实层面上的呈现而已,而不是定义“仁”的手段,所以“一”所指的是通过现实层面的“忠恕”,能够与“仁”合一,而非“定义”之意。所以,有子也会说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⑮(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57页。也是从道德情感来指点出“仁”的本质。在孔子这里,我们可以说,“仁”是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统一体,而人能通过现实层面的具体之事物,能够体贴到“仁”之天道,抑或是通过自身之实践来呈现出“仁”之道体,让其贞定于人的活动之中。
这里的“为仁”并不是指“行仁义”抑或是通过外在的、具体的“仁事”来达到“仁”之境界,这里的“为仁”指的是“由仁义行”,即通过“仁”作为自己的道德动机来为目标,在具体的生命活动中呈现其为生命价值取向的思想,也就是《孟子》中的“由仁义行”。故“仁”对个体的最高的要求就是“由行仁义”的状态,也就是将其作为道德动机并在现实活动中予以实现的境界。能够将“仁”的原则“随心所欲不逾矩”并以此达到运用自由的状态,也就是呈现出“乐”的境地了。所以,“仁”在现实中,经由人呈现出来,并达到融合现实的情感与实际情况,呈现出“仁”本体的时候,也就达到了“乐仁”之境界。在此,“仁”是本体,同时也为“仁”之境界提供了现实的情感支持;而“乐”作为主客体交融的呈现,同时也是作为个体的人自由地将内心之中的伦理道德——“仁”呈现于现实世界中的那份从容不迫而又愉快的自由。这实际上也就是人在现实中所呈现出来的道德伦理情感与作为社会理性观念的“仁”的本体之间的无间的融合,达到了“人与对象世界的普遍性求得一致,人的感性与对象世界的个别性求得一致”。因而,个体在这种一致而又自由的情感中,表现为美学的形态,呈现出完美的人格境界。故“仁”又可以呈现出“乐”之境界,也就是一种美学境界的状态。
因此,“仁”自身能够作为一种社会道德伦理,而在宗法制的社会政治结构中起到价值判断作用;另一方面,它自身也是“孝悌之情”等基本的道德情感的表现。因此,作为个体而言,要是达到了这种自由的境界,并呈现出“乐”的状态,也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也就达到了美学上所要求的感性与理性交融的状态了。“乐”之境界所表现的正是道德理念与道德情感不分,而社会伦理秩序与个体道德体验相融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人不需要现实的功利,也不需要深一层次的思考,他只要当下见到现象,便可以从这种现象中体会到符合“仁”体的道德理念,并在这种感性与理性交融的状态中来去自如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而这种“上下贯通、内外不分、真善同一”的境界,也就是从道德理想出发,通过个体的行为所展现的形上形下一致的“由仁义行”绝对完美人格境界,也就是“仁”体通过孔、颜等人所呈现出来的自由境界,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审美境界。
二、“颜子之乐”:“乐仁”境界的完美体现
“孔颜之乐”作为一整套的由先秦时期儒家文化所影响下的理论,以孔子之“生而知之”的道德规范“仁”为目标,以颜子、曾点提供的、所能通过“学而知之”来呈现的孔子之“乐”境界为手段,为后代人能够由此而达到“圣人境界”提供理论基础和工夫论上的启示。故可以说“孔颜之乐”实际上是由本体、工夫与境界兼具的“颜子之乐”与“曾点之乐”共同组合而成的,而二者实际上都得到了孔子之深契,并呈现为孔子之境界的不同表现。研究“孔颜之乐”之境界,不仅要深刻体悟境界的内涵,同时也要注意境界的本体、情感以及个人的工夫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对“孔颜之乐”境界所呈现出来的状态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深入探究“孔颜之乐”的全部内涵。
《论语》中有确定的记载“颜子之乐”与“曾点之乐”的先秦文献并不多。但这点文献也对中国古代经学发展以及古代人格观念、道德伦理甚至是对幸福的观念,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尤其在宋明理学的记载中,无论是本体宇宙论,还是工夫境界论,都以最终达到个体的“圣境”为目标,故对“孔颜之乐”的境界论研究可谓众多。但对于原点的分析有时过于粗疏,尤其是对“孔颜之乐”的境界对象与外在环境“贫困”的认识上,还有一定的欠缺。然而无论如何,都离不开对最初《论语》中所记载的关于“孔颜之乐”的记载,因此,对其进行研究,以正本清源,是本文力图达到的目标。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孔子之“乐”境界与颜子、曾点之“乐”境界的同异问题。尽管孔子提出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3页。的人生境界,另还有“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5页。的志向。从这些材料来说,孔子所呈现出来的“乐”境界在其个人身上也是有具体之呈现的。但如果仅从境界来讲,无论是“孔子之乐”还是“颜子之乐”,抑或是“曾点之乐”,实际上都是属于儒家“圣人境界”的不同之表现,而未有本质上的区别,故能够放在一起。同时,孔子之“乐”境界都是能够为颜子、曾点所深深领会到,甚至于深刻地契悟到他们生命中的。故在“乐以忘忧”的境界上,颜子也可以达致“贤哉,回也!”的境界,而曾点也可以达到“吾与点也”的状态。可见,“乐以忘忧”能够被视为孔子直接表现自身之境界的指点语,但作为境界而言,也可以被颜子、曾点之“学而知之”的后生所领会。故在探讨“孔颜之乐”境界时,我们可以分开来讲,但作为一整套“孔颜之乐”理论来说,孔子之境界也要和颜子、曾点的境界一起来说。这样,既能体现孔子之“乐”,也能够与其所深契的颜子、曾点之乐境界分享统一内涵——“仁”。现存的、能被确定的先秦的文献中,有多处提到了“孔颜之乐”问题,并涉及了情感与境界的相关范畴。一般认为,关于孔子、颜子之“乐”境界的有两处,它们是: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③(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2页。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④(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8页。
之所以说这两条语录所述的是“孔颜之乐”,是因为孔子、颜子在贫困的环境中固守“道”,而对外在的物质环境没有太大的追求。如果从本质来讲,都是对“仁”之本体的喜爱,并坚持将其付诸自己的生命活动之中,不论何“时”都不会放弃的勇气。但问题出自于“贫困”。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只有在贫困中才能体现出一个人固守“仁”的品质,这样未免对孔子之道的理解过于狭隘。这实际上就是“孔颜之乐”境界的德福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宋明理学家在“天理”的观念下,对“孔颜之乐”的德福关系乃至于道体与“时”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在这里已经初步显现该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仁”道的“乐”应该是处于任何环境之下的,因此曾子才会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⑤(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7页。因此,无论是贫困还是富贵的条件下,都应该恪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质,故孔子云:“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3页。、“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⑦(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58页。。“仁”应该体现在任何“时”,而不是只局限于“贫困”。从这点来讲,实现“孔颜之乐”境界是亘古不变的,但外在的环境是否是贫贱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无论何种环境下都能够恪守“仁”道。故孔子曰: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1页。
可以看出,贫与富与君子无绝对的关系。君子能够在任何时刻都能固守道德。的确,面临诱惑的时候,有时富贵给予人的欲望能够让人放弃对“道”的追求。但孔子认为:“女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8页。也就是不同意自己的弟子做只知道外在礼乐而不懂其内在精神的“小人儒”。故君子必须时时刻刻固守得“仁”道,做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而不能随意放弃或面临诱惑时刻意去自暴自弃。所以,“贫困”不是“孔颜之乐”绝对的条件,以上的引文也不能概括“孔颜之乐”的所有情况。其重要的内容在于无论任何时候都能恪守“仁”道,而不在于是否“贫困”。在孔子的志向中,特意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重点在于“不义”而非“富贵”,孔子反对在不义的社会中为求得财富而出卖自己的灵魂,相反地,他也不赞同在国家清明的时刻,儒者再迂腐地认为“贫困”是“贤”的表现。其中,衡量标准是“仁”而非是否“贫困”。
事实上,身处富贵之乡有时也更会磨炼一个人以成“仁”为目的,而身处贫困之际出卖自己灵魂的无耻之徒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占少数。故“不问英雄出身”不是说贫贱出身就一定品格高尚,而出身富贵也不是说一定弱不禁风。在孔子弟子中,子贡虽然擅于货殖,但其心仍在货殖上,不能如颜子一样全身心地扎在对“仁”的契悟中,所以尝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③(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4页。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子贡对道体的契悟不如颜子,故在“性与天道”的问题上,他不能如颜子一样能够领悟得透,故孔子强调“天何言哉”④(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26页。,说明他对自身的“仁”还没有“如愚”的颜子一样能够有所彻悟。正因如此,他才认为子贡是“女器也”、“瑚琏也”⑤(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3页。,已为国之器却未尽君子之美。或评价子贡“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无欲加诸人”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4页。时,认为“赐也,非尔能所及也。”⑦(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4页。可见,孔子并不认为子贡能够达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⑧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可见“仁”道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道相同,后者是前者的一种特殊表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02页。)的“仁”道。孔子虽然在另则语录中鼓励其能做到此⑨《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18页。),但并不认为他现在有这个境界。因此,相对于颜子的“愿无伐善,无施劳”⑩(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5页。的表述,可见子贡差之远矣。
所以,“孔颜之乐”的关键就在于,能够如孔子、颜回一样能够将“仁”切入自己的生命活动中,做到在任何“时”都能够按照“道”的要求来成就自己的意识与实践的行为,并进入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乐”境界中。因此,在“三月不违仁”的说法中,“三月”不仅可以理解为“时间”,还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时”,也就是身处任何状态,无论贫贱还是富贵,都应以“仁”为志向,以达到“乐”的自由境界之中。故同上文所说,“孔颜之乐”的本体在于“仁”,而其中个体因为践行了“仁”而达到的主体之境界称之为“乐”。这样,“孔颜之乐”实际上就是实践“仁”以达到的“乐”之境界的完美之体现。故孔子曰: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1页。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里也有“乐以忘忧”的表述。“乐”明显属于对“仁”进入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而“忘忧”则是不去计较现实的功利得失。可以说,“忧”的并不仅仅是“贫困”,而且可能还有对功利的计较,这实际上和上文所引用的“贤哉回也”与“乐在其中矣”的境界如出一辙,都是对实践“仁”以达到的“乐”之境界的体会。
同时,对于“乐仁”的问题,《论语》中也有着很多叙述。首先应该认识到“好仁”与“乐仁”之间的关系。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9页。上文已述,对于“仁”而言,真正能够契悟“仁”的状态是“乐”,也就是进入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美学境界之中。故在“好仁”与“乐仁”之境地中,能够将生命切入到仁境界中的,才可以被称之为“乐仁”。在提到“好仁”同时,孔子总带有勉强之意味:“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③(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1页。可以看出,无论是“好仁”还是“恶不仁”,实际上都是“力足”才能到达的境界,而对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而言,这实在是相差的很远。可能正因为如此,孔子才对自己的弟子对话说道: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④(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8页。
可以看出,冉求在这里对孔子之道产生了畏难情绪,实际上也就是将“仁”道当作外在自己的“道”,而没有契入自己生命中去。这样,实际上只能空学习到没有内在情感与道体的礼乐,这样当然离孔子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相差很远。
而对“乐仁”来说,《论语》中也存在不少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我们也看出孔子对“乐仁”之境界给予了很高的赞叹,认为其真正切入了生命中本真的层面,是真能达致“仁”的表现: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⑤(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1页。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9页。
可以看出,以上两选文具有很明显的联系。“仁者安仁”的意思在于,具有“乐仁”境界的人同时也能够将“仁”作为自己生命的目的来实践它,并自始至终维持它,由此,这样的人能够常处于“乐”之境界中。在孔子眼中,“知者”要比“仁者”差一个档次,在这则语录中,“知者”实际上以“仁”为目标,这就是将其外在于生命活动了。因此,尽管“知者”能够修得礼乐之典章制度,但却仍然未能进入到“乐仁”之境界中去。故孔子在后一则语录中强调:“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里的比喻强调“仁者”能够如山一样稳重,可见其内化入自己生命的“仁”一刻也不能放弃,并能够将“仁”道实行一生。而“知者”虽然也能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就其境界而言,却只能如流水一样,不能固守一定的境界,因此达不到“乐仁”境界所呈现出来的稳重的特征。可以说,乐所呈现的,是真能将“仁”进入到自己生命活动中,并彻底地呈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极高境界。而对于实现人的个体而言,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带有美学意味浓厚的个体形象。
三、“曾点之乐”:“孔颜之乐”的另一种呈现形式
与孔子、颜子之乐相对应的“孔颜之乐”境界,还有曾点之乐。前文已述,曾点之乐作为孔子所深契的境界,即是“孔子之乐”的一种形态,同时也是“乐仁”之境界的一种表现。从这点来讲,他所呈现出来的境界,相对于颜子之气象显得更为洒落且豪放,在《论语》中记载: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晳后。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00页。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与颜子的“愿无伐善,无施劳”与“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都是处于“百姓日用之常”的情况之中,都是在“仁”道上能够体会其乐,并能真正深入到生命之中的境界。但如果对比颜子之志“愿无伐善,无施劳”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5页。曾点之志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显得是那么的洒脱和和畅,它实际上已经摆脱了现实功利的困扰,也没有那么多的忧国忧民的大任在里面,有的只是在志向实现后自我享受和畅快的情绪。可能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会将其视为道家哲学影响下的人生观念。从曾点之志与其他三者之志的对比来看,他的确具有在功成名就后的自得自乐之情。但是,如果这样就说曾点之乐就能超越一切,乃至于进入到道家的“出世”境界中,这实在是没有太多的依据。应该说,曾点之乐,是在经历了前三种志向完全实现后,体验到的每个人都能共享王道政治的喜悦。这里的“曾点之乐”与“志向”的实现有关,而从“志向”来讲,前三者的志向都是有关政治的,而这种政治不是政治的权谋,不是政治的统治术,更不是如法家的“治国之术”那样的维护君主利益而牺牲百姓民众利益的“霸道”。这里的政治应该是王道政治,是“人伦政治”,是每个人都能“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5页。,即通过孔子之道,能够保证自己内心天生的人伦道德通行天下,每个人都能尽自己人伦上的义务的政治。故“曾点之志”也当然隶属于这个意义下的孔门之志,而不能拐入道家的人生观念中,认为其“超越一切”。这样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所以,正确地理解“吾与点也”之乐应该在综合其他三者之志向与其志向实现后而达到的喜悦之情上来说。从境界来讲,它不是“超越”的,更不是“避世”的,而是要求积极地践行孔子的道德观念,并将其实行于天下中的志向。不过在这个志向中,由于曾点的个人性情,他在这个志向中体会的是天下之道德情感都能全部实现后的期待,是道德情感完成后体验的那种幸福和道德动机全部得以满足后的情感。从这点来讲,这种“境界”是道德境界,它所体会的情感是道德情感,当然不是所谓的消极避世的观念了。如果从喜悦之情来讲,这是在孔子之“仁”理想实现后每个个体都能达到“乐仁”境界且王道政治得以实现后的喜悦之情,也是万物各得其所后的欣慰之情。一如《易传》所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把一切人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志向,而实现全部人的幸福后,自然会得到一种极高的道德满足感,由此而产生的喜悦之情,也就是“曾点之乐”的最高生命的体验感了吧。其实,这也是孔子志向的满足,如同“愿无伐善,无施劳”与“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一样,都是将一切人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志向,其志向广大,能够承受得起安顿天下、为所有人的幸福谋利的伟大抱负。因此,这一点上,正是孔子“乐仁”的实现,也是曾点之乐之所以为“孔颜之乐”境界的一种特殊的呈现。
综上所述,本文将“孔颜之乐”分为孔子、颜子与曾点之乐境界进行分别之讨论。应该说,这三者实际上都是“乐仁”境界的不同之表现,是“孔子之乐”在不同层面上的呈现。如此来说,“仁”实际上统摄了“孔颜之乐”的境界,并可以在不同的外在条件下呈现出不一样的人生观念。但无论如何,对“仁”的持守与呈现是无论任何条件下都一致的。因此,在这种德福观念的影响下,孔子和颜子都有着很强的道德表现。在“乐仁”,也就是孔子“从心遂于不逾矩”的情况下,人达到了生命的本真,并在生命中不断地实现“仁”之观念,这也就达到了“孔颜之乐”的境界。与此同时,“曾点之乐”则从孔门其他弟子的志向出发,以孔子的“仁”为己任,将天下家国的责任担在身上,并强调通过自我志向的实现天下之安康。这样,个体的幸福与天下的幸福就联系在了一起,于此呈现出了“曾点之乐”的样式。总之,无论是哪一种样式,都是“乐”之境界的呈现,都是“孔颜之乐”的表现之一,具有强烈的美学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