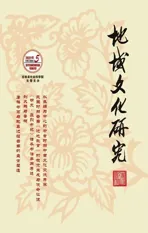《明史·庄烈帝纪》诸本书法异同考述
2021-11-26贾俊侠胡培欣
贾俊侠 胡培欣
学术界在《明史》编纂的相关领域已经取得了诸多的研究成果。对《明史》版本的探究拓宽到了各阶段的不同稿本,并考证了稿本的作者、年代等信息;对预修《明史》的编纂人员进行了广泛研究,不仅对万斯同和王鸿绪的贡献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同时也将视角覆盖到其他数十位纂修者,考察其史学思想及对《明史》编纂的影响;对《明史》具体内容的编纂和书法的了解也更为深入,纪传志表都有所涉及,特别是列传部分。此外,对于《明史》纂修与民间修史的关系,政治因素对《明史》编纂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都较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
尽管史学界对于《明史》的编纂和书法研究成果颇丰,但关于《庄烈帝纪》①崇祯帝本纪的篇名,不同版本有所差别,416卷本作《庄烈皇帝本纪》,王鸿绪本和殿本作《庄烈帝本纪》,为行文方便,除特指某一版本时,均简称《庄烈帝纪》。的专门考察尚未有人涉及。《庄烈帝纪》的主人公是明朝崇祯皇帝。崇祯帝名朱由检(1611—1644),字德约,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为光宗朱常洛第三子,年幼丧母,稍长丧父。兄长天启帝朱由校在位时,封为信王。天启帝驾崩后,朱由检继统,定年号为崇祯,以元妃周氏为皇后,史称崇祯皇帝。崇祯帝即位后,铲除魏忠贤及阉党势力,勤于政务,临朝不辍,躬行节俭,孜孜求治。然而彼时明朝已积重难返,外有强敌窥伺,内有民变环生,朝廷吏治腐败,边疆武备废弛,臣僚陷于党争,百姓困于催逋,加以天灾四起,饥馑横行,终无力回天。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军攻入京师,三月十九日,崇祯帝于煤山自缢,明朝灭亡,史称甲申之变。清兵入关后,将崇祯帝礼葬,迁入原田贵妃墓,称思陵。清廷先上庙号怀宗,谥端皇帝,后去庙号不用,改谥庄烈愍帝。南明弘光朝初上思宗烈皇帝,寻改毅宗,隆武帝时又改为威宗。
由于对《庄烈帝纪》诸本书法的认识尚未明朗,笔者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庄烈帝纪》诸本书法为中心,先梳理《庄烈帝纪》诸本的编纂历程,再立足史料,对比分析,归纳提炼出《庄烈帝纪》书法的异同,进而探究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明史·庄烈帝纪》诸本编纂始末
《明史》是“二十四史”当中的最后一部,也是清代官修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对于这部官修正史,历来评价颇高。清人赵翼曾说道:“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①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60页。钱大昕也称赞其“议论平允,考稽详核,前代诸史,莫能及也”。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219页。可见在清代之后学者们的心目中,《明史》一书具有较高的编纂水准及史料价值。但是,《明史》却也是历代官修正史中编纂时间最长的一部,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至乾隆四年(1739)方告完成,前后跨度将近九十五年。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史》漫长的编纂历程中,还衍生出了数部明史稿本,这些明史稿本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庄烈帝纪》的编纂与《明史》整体的纂修息息相关,其同样也在长期的编纂过程中形成了数篇不同的稿本。下文将结合《明史》纂修的背景,对《庄烈帝纪》诸本的编纂始末予以梳理。
(一)编纂的缘起与准备
《明史》的编纂肇始于顺治二年(1645),当年五月“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纂修明史”,③赵尔巽:《清史稿》卷4《世祖本纪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8页。但很快趋于停滞。康熙四年(1665)重开史馆,参修《明史》的杨椿对此有所追述,其曰:“未数十卷,会修《世祖章皇帝实录》,遂罢”。④杨椿:《孟邻堂文钞》卷2《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清嘉庆二十四年红梅阁刻本,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页。这一阶段,由于清政府尚未夺取全国,战争仍在进行,加之缺乏史料,不具备编纂的客观条件,因此纂修工作并未真正推进。由于史馆内崇祯朝史料贫乏,此阶段也针对性地访求明季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邸报、野史、家传和集记等,这为日后《庄烈帝纪》的编纂提供了史料基础。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统治已日渐稳固,遂于当年三月在保和殿举行了“博学鸿词”考试,授予彭孙遹、邵吴远、汤斌等五十人为翰林院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负责纂修《明史》。同时“以学士徐元文、叶方霭、庶子张玉书为总裁”。⑤赵尔巽:《清史稿》卷4《圣祖本纪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对此,《清实录》有更为详细地记载:“乙未,命内阁学士徐元文为《明史》监修总裁官,掌院学士叶方蔼、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官。”⑥《清实录》卷81《圣祖仁皇帝实录》(一)康熙十八年五至六月,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35页。可见自此《明史》编纂工作进入了真正执行的阶段。但崇祯朝没有实录,史事纷杂,难以纂修本纪,当时的纂修官朱彝尊便明确指出:“明史成书,莫难于万历之后,稗官踌驳,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祯一朝无实录依据,尤难措手。”①朱彝尊著,王利民等点校:《曝书亭全集》卷32《史馆上总裁第七书》,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393页。考虑到直接纂修崇祯本纪的困难,纂修官汪楫“言于总裁官,先仿宋李焘《长编》,凡诏谕、奏议、邸报汇辑之”②朱珔:《小万卷斋文稿》卷19《汪楫传》,清光绪十一年嘉树山房刻本,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56页。,也就是说打算先纂辑长编,作为编纂本纪时的依据。“乃取崇祯十七年事,凡诏谕、奏议、文集、邸报、家传辑为长编,由是十六朝史材皆备”。③朱彝尊著,王利民等点校:《曝书亭全集》卷73《汪公墓表》,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700页。于是便诞生了《崇祯长编》。《长编》的编纂者主要有汪楫、万言、乔莱等六人,其中万言“八年不调,专董其事”。④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正如《清史稿》所言万言几乎“独成《崇祯长编》”。万言是万斯年之子,少与叔父万斯大、万斯同从黄遵羲学,以古文著称,受总裁官徐元文举荐进入明史馆,与修明史;汪楫、乔莱等,均列十八年“博学鸿儒”一等,授翰林院编修,这样的团队势必保障了《崇祯长编》的编修质量。之后明史馆又组织编纂了《崇祯实录》,其作者不详,记事较《崇祯长编》为简。《崇祯长编》和《崇祯实录》的成书,标志着编纂崇祯本纪的准备工作完成。
(二)416卷本《庄烈皇帝本纪》的编纂
约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一部纪传志表俱全的《明史》编成,因卷数为416卷,习惯称为416卷本《明史》⑤万斯同:《明史》钞本416卷,现藏国家图书馆。影印本收在《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第0324-0331册。对于钞本学界说法不一:朱端强、衣若兰、王宣标等先生经考证认为国图所藏旧题万斯同416卷本《明史》系总裁熊赐履康熙四十一年进呈本,秦丽先生则认为国图所藏此钞本系雍正初年明史馆为校正之用而誊录的康熙四十一年熊赐履进呈本的副本。见秦丽《国家图书馆416卷本〈明史〉新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1期,第62-69页。从编修情况看,应为明史稿本。。这部《明史》是所有纂修人员心血的结晶,而万斯同在其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万斯同为黄宗羲弟子,以布衣身份入馆修史,不食清廷俸禄。因熟谙明史,馆内“建纲领,制条例,斟酌去取,讥正得失,悉付斯同典掌”。⑥钱林辑、王藻编:《文献征存录》卷1,见《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08》,明文书局据清咸丰八年南通州王氏有嘉树轩刊本影印,1985年,第80页。时任总裁的徐元文也说:“季野万子惠然北来,止余邸舍十年矣。同心托契,儗于兰金,编校之事,蒙实赖焉。”⑦徐元文:《含经堂集》卷14《季野万子惠然北来》诗,清康熙年间刻本,第2页。不过,此时《明史》尚属草创初成,“又人各为说,以故其书缺而不全,涣而不一,稿虽就而未敢以进也”。⑧杨椿:《孟邻堂文钞》卷2《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清嘉庆二十四年红梅阁刻本,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页。康熙四十一年(1702),时任监修总裁熊赐履为早日竣事,将草成的明史稿稍作修改,随即进呈给皇帝。然而康熙帝阅后并不满意,甚至指责“《明史》伪妄,不足信也”,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59页。这令《明史》编纂工作蒙上了阴影。416卷本的《明史》本纪共26卷,其中《庄烈皇帝本纪》4卷,字数2万余,卷帙浩繁,是目前存世最早的崇祯本纪。另一部约略与此同时且含有《庄烈帝纪》的明史稿本是313卷的《明史纪传》,其现存版本为乾隆年间钞本,原《庄烈帝纪》已佚,乃据殿本《明史》抄补,故下文中不再论述。
(三)王鸿绪本《庄烈帝本纪》的编纂
康熙后期,《明史》编纂工作陷入停滞,原纂修官陆续故去,康熙帝的支持也明显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王鸿绪承担起了主要的编纂工作。早在明史馆开馆之初,王鸿绪便被任命为纂修官,康熙二十一年(1682)又升任总裁,其后虽两度致仕。康熙四十一年(1702)万斯同去世后,王鸿绪承担了主要的编纂工作,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陈廷敬去世后,《明史》的纂修工作几乎由王鸿绪一人担负。“自蒙恩归田,欲图报称,稍尽臣职,因重理旧篇,搜残补缺,荟萃其全。复经五载,始得告竣,共大小列传二百五卷,其间是非邪正,悉据已成之公论,不敢稍任私心臆见。”①王鸿绪:《王鸿绪为进呈明史列传全稿事奏折》,见《明史稿·奏疏》,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据雍正四年敬慎堂刻本影印,第1页。康熙五十三年(1714),王鸿绪将修改后的《明史列传稿》呈交朝廷。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鸿绪再次奉诏还朝,继续进行修订工作,最终将纪传志表汇成一体,成《明史稿》310卷,于雍正元年(1723)六月上呈。因此本进呈皇帝时为王鸿绪署名,故称其为王鸿绪本。②学界对此稿本的编撰者是万斯同还是王鸿绪持有争议,因刊印时均题为王鸿绪著,笔者暂采其意以王鸿绪本称之,至于作者在此不做赘述。相关论述请参阅以下成果:民国李晋华《〈明史〉纂修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31-33页;侯仁之《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见姜胜利《明史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86-314页;黄彰健《明清史研究丛稿》卷3《明外史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365-405;;黄爱平《王鸿绪与〈明史〉纂修一王鸿绪“窜改”、“攘窃”说质疑》,《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53-61、73 页;黄爱平《万斯同与〈明史〉纂修》(《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第36-42页;黄爱平《〈明史〉纂修与清初史学——兼论万斯同、王鸿绪在〈明史〉纂修中的作用》,《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83-93页;郭朝辉《〈明史·西域传〉编纂考述》,《中国典籍文化》2016年第3期,第28-36页。
王鸿绪“自简任总裁,阅历四十二年,或笔削乎旧文,或补缀其未备,或就正于明季之老儒,或咨访于当代之博雅。要以恪遵敕旨,务出至公,不敢无据而作。”③王鸿绪:《王鸿绪为明史告竣进呈事奏折》,见《明史稿》第1册·奏疏,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据雍正四年敬慎堂刻本影印,第3页。从奏疏可以看出,310卷《明史》稿本的编纂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王鸿绪本《明史稿》本纪共19 卷,其中《庄烈帝本纪》2 卷,1.6 万余字,就内容而言较前本大为精进,但仍留存一些缺陷,有待继任的纂修官予以完善。
(四)武英殿本《庄烈帝本纪》的编纂
王鸿绪的《明史稿》上呈后,清廷并未结束修史工作。雍正元年(1723)七月,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徐元梦、朱轼为总裁,继续纂修《明史》。雍正十三年(1735),张廷玉进呈《明史》,因雍正皇帝大行,下诏延期,再行修订。乾隆四年(1739)七月,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领衔奏上《明史》332卷。因此书由武英殿监督刊印,故称武英殿本《明史》。至此,历时近百年的《明史》编纂工作正式结束。殿本《明史》本纪共24卷,主要由汪由墩、吴麟负责编纂;殿本《庄烈帝本纪》共2卷,在之前稿本的基础上,对内容、体例、史事做了细致的笔削、校订工作,极大提高了编纂水平,虽然仍有缺憾,但已称得上是一篇上乘的本纪。
此后《明史》也有过修补改订的工作。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乾隆皇帝在阅览《明史·英宗本纪》本纪时,只觉“于事迹要领,不能胪纪精细,于史法尚未允协”,命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珅以及刘墉等人“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词义精当”④《清实录》卷1032《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上,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7年,第841页。,因成《明史本纪》补纂。乾隆五十四年(1789),清廷将经过全面修订的《明史》“钦定”后收入《四库全书》,即所谓四库本《明史》。此时,《明史》本身业已完成纂修多年,故本文中不论及后出修订之《庄烈帝纪》。
二、《明史·庄烈帝纪》诸本的相异书法
据上文可知,在《明史》的编纂历程中共诞生了三种不同版本的《庄烈帝纪》,分别为416 卷本《庄烈皇帝本纪》、王鸿绪本《庄烈帝本纪》和殿本《庄烈帝本纪》。由于三本《庄烈帝纪》成书于不同的阶段,参与纂修的人员不尽相同,且后出版本往往会对前稿做大量改动,因此《庄烈帝纪》诸本的书法各有特征,互不相同。探讨诸本书法的特点,分析其间差异,以窥诸本编纂书法的演变脉络以及清廷对明末历史的认知。
(一)416卷本《庄烈皇帝本纪》书法
1.记事丰富、详尽,略显琐碎
416卷本在《庄烈皇帝本纪》中所记载的事件内容远较王鸿绪本和殿本要丰富得多。例如天启七年(1627)九月条下记有“甲子朔,魏忠贤辞位,不许。平辽总兵官毛文龙奏事,求代,语甚激骜,帝优容之。丙寅,谕奉圣夫人客氏出居私第。己卯,南京副都御史杨所修劾兵部尚书崔呈秀及延绥巡抚朱童,蒙旨切责之”。①万斯同:《明史》卷23《庄烈皇帝本纪一》,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集类》第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2页。这一段字数虽不多,但交代了四件事,牵涉到朝廷内外多个重要人物,其中在时机未成熟的情况下对魏忠贤及其党羽假意安抚,关系到日后清查阉党的行动;对毛文龙骄横无理的容忍暗示其日后被袁崇焕矫诏所杀的部分原因。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崇祯帝初即位时政治局面的动荡以及崇祯帝处事不惊的能力和其大智若愚的智慧。而这一段在王鸿绪本和殿本的《庄烈帝纪》中均无记载。
416卷本《庄烈皇帝本纪》记事的丰富详尽虽使事件发展过程清晰可循,却也相应地造成了琐碎的弊病。例如关于对农民军的记载就极为烦琐,如崇祯七年(1634)春正月条下:“癸巳,降丁王刚等至太原挟赏,戴君恩张宴大会,引斩之。时贼党称老回回、紫金梁已死,侦之,则尚在东山;西山有翻山鹞、姬关锁、掌世王三贼,寻生得献俘。而岢岚大贼显道神尤横,会旱,饥民多从之,贼势复炽。壬辰,都司周元儒败贼于应山,贼自郧阳渡江薄谷城。明日贼六路并集于襄阳,又一枝自淅川围均州。”②万斯同:《明史》卷24《庄烈皇帝本纪二》,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集类》第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6页。这种对细节和过程的细致描述,多不厌其烦地记录在本纪中。对此,王鸿绪曾有过批评:“纪者以编年为主,惟叙天子一人……或兼他事,巨细必书,洪纤备录,昔人谓是传体有乖纪文。往见《庄烈纪》稿颇犯此病,不知诸臣传中更何着笔?”③刘承干:《明史例案》卷2《王横云史例议上》,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见徐蜀编《明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2.叙事完整、具体
416 卷本《庄烈皇帝本纪》叙事相对比较完整、具体。以崇祯帝即位前所经历的大事为例,416卷本作:“天启二年八月丙戌,封信王。六年十一月甲午,出居邸。十二月戊申,冠。明年二月庚子,册周氏为元妃。”①万斯同:《明史》卷23《庄烈皇帝本纪一》,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集类》第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0页。王鸿绪本作:“天启二年八月,封信王。六年十一月,出居信邸。七年春二月,册周氏为元妃。”②王鸿绪:《明史稿》卷18《本纪十八·庄烈帝纪一》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据雍正四年敬慎堂刻本影印,第1页。殿本乃作:“天启二年,封信王。六年十一月,出居信邸。”③张廷玉等:《明史》卷23《庄烈帝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9页。显然,416卷本的叙事更为完整具体,不仅记叙了崇祯帝授封信王,出居王邸,加冠,册封元妃四件大事,而且交代了事件具体的年月和日期。相比之下,王鸿绪本省去了日期,只标明事件的年月,并删去加冠一事。殿本却只保留了封信王与出居信邸二事,更连天启二年(1622)的月份也一并省去了。可以看出从416 卷本到殿本,叙事呈现出不断简略、模糊的特点。
3.常引用诏敕或奏疏原文
416 卷本在记述时往往引用诏书、谕敕或奏疏,原委清晰可查。如崇祯元年(1628)五月条下,416卷本作:“乙酉,谕吏户兵三部官员‘更调太速则民滋扰,今后藩臬郡邑务择人地相宜,如旧制久任。言官荐举人才多徇私市恩,吏部可据荐剡置籍,其后隳职连坐举主。辽黔兵役未罢,加派已多,可造兵饷简明册进呈,若有司私派,抚按即行参处’。”④万斯同:《明史》卷23《庄烈皇帝本纪一》,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集类》第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3页。对此事,王鸿绪本作:“乙酉,复藩臬郡邑久任及举主连坐之法,禁有司私派。”⑤王鸿绪:《明史稿》卷18《本纪十八·庄烈帝纪一》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据雍正四年敬慎堂刻本影印,第2页。殿本作:“乙酉,复外吏久任及举保连坐之法,禁有司私派。”⑥张廷玉等:《明史》卷23《庄烈帝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0页。三种本子相较来看,王鸿绪本与殿本皆直言政策的内容且很简单,唯有416 卷本原封不动引用了崇祯帝诏敕的原文,使读者不仅知晓政策的内容,而且明白政策实行的原因以及皇帝于其中的考量。
(二)王鸿绪本《庄烈帝本纪》书法
1.不书影响不大之事
王鸿绪本《庄烈帝本纪》对416卷本进行了大量删繁就简的工作,对于战争胜负、朝廷政令和宰辅以下官员任免中影响不大之事不做一一记录。例如416 卷本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条下有“壬申……以阎鸣泰为兵部尚书”,“丙子,勒奄党刑部尚书薛贞致仕”,“己丑……改苏茂相为刑部尚书,以黄思诚为左都御史”⑦万斯同:《明史》卷23《庄烈皇帝本纪一》,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集类》第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1-262页。等记载。这些官员并非内阁辅臣,他们的此次任免也没有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虽然416卷本将他们的任免一一记载,但王鸿绪本只字不提。
2.删去论赞、书“朔”和“赐及第”体例
416卷本与殿本于纪传后皆有论赞,而王鸿绪本则删去了论赞的书法。对此,王鸿绪自己解释道:“篇中所述,贤否已是昭然。叙而复断,更无逸事,何须烦黩?昔人谓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惟加文饰而已。至于甚者天子操行,具诸纪末,继以论曰,接武前修,纪论不殊,徒为再列旨哉。”①刘承干:《明史例案》,民国四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木板重刷。王鸿绪本不仅没有论赞,还取消了416卷本中月日之后书“朔”的体例。以崇祯六年(1633)为例,“六月辛酉”“十二月己未”②王鸿绪:《明史稿》卷18《本纪十八·庄烈帝纪一》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据雍正四年敬慎堂刻本影印,第10页。后皆删“朔”字,后出的乾隆年间殿本对此予以补回。此外,王鸿绪本删去固定记载“赐及第”事的书法。如416卷本崇祯元年(1628)条下的“夏四月癸巳,策试天下贡士,赐刘若宰等三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③万斯同:《明史》卷23《庄烈皇帝本纪一》,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集类》第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2页。崇祯四年(1631)三月条下的“己丑,策试天下贡士,赐陈于泰等三百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④万斯同:《明史》卷23《庄烈皇帝本纪一》,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集类》第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0页。等记载,王鸿绪本全篇删去,后来殿本又予以恢复。
(三)武英殿本《庄烈帝本纪》书法
1.弱化或美化明清间的军事冲突
明朝末年,明朝与清政权的军事冲突十分激烈。在崇祯帝即位前,后金已经夺取了明朝的辽东重镇沈阳和辽阳,明朝甚至一度放弃了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崇祯帝即位后,清兵又多次入关侵扰,掠夺人畜,计有崇祯二年(1629)、七年(1634)、九年(1636)、十一年(1638)、十五年(1642),五次入关。崇祯十四年(1641)至崇祯十五年(1642),明清双方更在关外进行了大规模会战。清政权的军事打击使得明朝两线开战,左支右绌,更进一步加重了明朝内部的社会危机,这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清朝是最终胜利夺取天下的一方,因此,在最终刊行的殿本《明史》里,清王朝有意识地弱化或美化对明朝的军事行动。若以殿本《庄烈帝本纪》记崇祯二年(1629)清兵入关事与王鸿绪本对比,殿本不载“参将周镇战殁”,“其日,复破抚宁”,“遂破玉田”,“大清兵破良乡,知县党还醇死之”,“大清兵破张湾城”,“大清兵破香河”等事,固然有精简字数的缘故,其实更多是存在弱化军事冲突的目的。此外,王鸿绪本中“大清兵破遵化”,殿本将“破”改作“入”;王鸿绪本中“大清兵破永平”、“大清兵破滦州”,殿本将“破”皆改作“克”。这些均是为了美化清兵攻掠的行为。
2.史实取舍多参考《崇祯长编》
殿本《庄烈帝本纪》对同一件事情的记载,有时会出现与416卷本和王鸿绪本记载不一致的情况,尤其是在史事的系时上。如,416 卷本崇祯元年(1628)三月条下:“乙丑,施凤来、张瑞图并致仕。”⑤万斯同:《明史》卷23《庄烈皇帝本纪一》,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集类》第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2页。王鸿绪本:“乙丑,施凤来、张瑞图致仕。”⑥王鸿绪:《明史稿》卷18《本纪十八·庄烈帝纪一》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据雍正四年敬慎堂刻本影印,第2页。殿本:“癸未,施凤来、张瑞图致仕。”⑦张廷玉等:《明史》卷23《庄烈帝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0页。殿本所记日期与前两稿相异,经笔者查阅勘对发现,造成相异的原因与三种本子所参考的史料有关,416卷本和王鸿绪本《庄烈帝纪》主要参考《崇祯实录》之史实,而殿本却以《崇祯长编》之史料为主。例如《崇祯实录》作:崇祯元年三月“乙丑……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並免,遣行人送还,赐金币廪役。”①《崇祯实录》卷1,见《明实录》第88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0011页。《崇祯长编》则作:“癸未……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屡疏乞归,俱允之。”②万言等:《崇祯长编》卷7,见《明实录》第91册·附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0372页。可见,殿本采用了《崇祯长编》的说法;再如,416 卷本崇祯元年(1628)六月条下:“辛丑,钱龙锡至许显纯伏诛。”③万斯同:《明史》卷23《庄烈皇帝本纪一》,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集类》第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3页。王鸿绪本:“辛丑,许显纯伏诛。”④王鸿绪:《明史稿》卷18《本纪十八·庄烈帝纪一》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据雍正四年敬慎堂刻本影印,第2页。殿本:“壬寅,许显纯伏诛。”⑤张廷玉等:《明史》卷23《庄烈帝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0页。此事,《崇祯实录》作:“辛丑,诛锦衣卫都指挥使许显纯。”⑥《崇祯实录》卷1,见《明实录》第88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0024页。《崇祯长编》作:“壬寅,诛许显纯。”⑦万言等:《崇祯长编》卷10,见《明实录》第91册·附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0567页。不难看出,殿本史实多与《崇祯长编》相合,而416卷本和王鸿绪本则与《崇祯实录》一致。表明殿本《庄烈帝本纪》与前稿相比,在史实取舍上更多来源于《崇祯长编》。
总而言之,《庄烈帝纪》诸本的书法各具特色。在内容上,416 卷本最为丰富,王鸿绪本较为详尽,殿本最为精简。在体例上,416卷本常引用诏敕和奏疏的原文,王鸿绪本和殿本多直书其事;王鸿绪本删除了论赞、书“朔”和“赐及第”体例,416卷本和殿本则予以保留。在史实取舍上,416卷本和王鸿绪本源于《崇祯实录》,而殿本则以《崇祯长编》参考为多。在文字表达上,416卷本和王鸿绪本更直接一些,殿本更富有文学性和政治性,尤其善于在细节处美化清朝。
三、《明史·庄烈帝纪》诸本的共通书法
《庄烈帝纪》诸本在编纂的过程中,因编纂人、编纂时间、历史背景及编纂目不同,书法自然有所调整或不同,但作为官修正史,定然有一以贯之的修史原则,体现在编纂书法上自然也会有所沿用和继承。因此,《庄烈帝纪》诸本的书法在相异性外也具有共通的地方。探讨诸本的共通书法,有助于了解编纂中诸本书法的沿袭与取舍关系。
(一)大量记载明末的自然灾害
崇祯帝在位时期,自然灾害频出屡现,诸本《庄烈帝纪》中都有大量记载,就连文字最精简的殿本,也保留了许多自然灾害的记录。查阅诸本记载,除常见的地震、日月食外,雨灾、风灾、旱灾、饥荒以及蝗灾等灾害的记录也十分频繁。416卷本:崇祯四年(1631)春正月“乙亥朔,大风霾”;⑧万斯同:《明史》卷23《庄烈皇帝本纪一》,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集类》第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9页。同年(1631)五月“壬寅,大同襄垣诸县雨雹,大者如卧牛、如大石,死人畜甚众”。⑨万斯同:《明史》卷23《庄烈皇帝本纪一》,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集类》第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1页。七年(1634)三月“给事中黄绍杰劾温体仁为相以来,无岁不旱,无日不霾,无地不灾”。①万斯同:《明史》卷24《庄烈皇帝本纪二》,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集类》第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7页。九年(1636)四月“乙亥朔,滦州地屡震”。②万斯同:《明史》卷24《庄烈皇帝本纪二》,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集类》第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十四年(1641)二月“辛亥,谕各处抚按捕蝗”。③万斯同:《明史》卷25《庄烈皇帝本纪三》,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集类》第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7页。王鸿绪本: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丙戌大风霾”。④王鸿绪:《明史稿》卷19《本纪十九·庄烈帝纪二》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据雍正四年敬慎堂刻本影印,第5页。同年(1640)“秋七月庚辰,直省旱蝗。”⑤王鸿绪:《明史稿》卷19《本纪十九·庄烈帝纪二》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据雍正四年敬慎堂刻本影印,第6页。殿本:崇祯元年(1628)七月“壬午,浙江风雨,海溢,漂没数万人”⑥张廷玉等:《明史》卷23《庄烈帝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0页。,崇祯五年(1632)“六月,京师大雨水。壬申,河决孟津”⑦张廷玉等:《明史》卷23《庄烈帝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5页。;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陕西、山西旱饥”⑧张廷玉等:《明史》卷23《庄烈帝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6页。;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甲申,祷雨。丙戌,大风霾。诏清刑狱”⑨张廷玉等:《明史》卷24《庄烈帝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8页。崇祯十四年(1641)“六月,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旱蝗,山东寇起”⑩张廷玉等:《明史》卷24《庄烈帝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9页。。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大量有关自然灾害的叙述,欲以表明明朝气数已尽,突显出明朝灭亡的必然性。
(二)贬低明末农民起事军的地位
明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事,终于颠覆了明朝,而清廷趁机倾巢入关,击溃了农民军,最终成功夺取天下。因而对清廷而言,要强调的不仅不是江山取之于明,恰恰相反,是剿灭了农民军,替明人报了君父之仇,从而将对农民军的绞杀与自身的正统地位联系在一起。正如康熙遗诏中所言:“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剪灭闯寇入承大统……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⑪《清实录》卷275《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695页。所以在《庄烈帝纪》诸本中,提及农民军皆用“贼”“流贼”“流寇”之类的污名化字眼,农民军行动多冠以“陷”“掠”“犯”“屠”等字。农民军头目也常代以“邢红狼”“混世王”“满天星”“不沾泥”“过天星”“双翅虎”“紫金龙”“老回回”“显道神”“扫地王”等之类的诨号而不采用可以考证的真名。
(三)不言崇祯帝失德,强调明清之际的天命转移
清廷对于崇祯帝的评价和政治定调可从416卷本和殿本《庄烈帝纪》的论赞里看出,虽然有诸如“帝又卞急,性生重以猜愎,乖张锲刻,动见纷拏”⑫万斯同:《明史》卷26《庄烈皇帝本纪四》,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集类》第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6页。这样的批评,但总体上依然肯定他“慨然有为”,赞扬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厉励,殚心治理”⑬张廷玉等:《明史》卷24《庄烈帝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5页。的表现。认为明朝的灭亡不是从他开始的,也并非因为他失德,而是“大势已倾,积习难挽”的结果,崇祯帝不过“适身当其厄”,亡国的责任应由万历和天启二帝承担。这与《流贼传》里的观点相吻合,其曰:“庄烈帝励精有为,视武宗何啻霄壤,而顾失天下,何也?……庄烈帝承神、熹之后,神宗怠荒弃政,熹宗暱近阉人,元气尽澌,国脉垂绝。向使熹宗御宇复延数载,则天下之亡不再传矣……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①张廷玉等:《明史》卷309《流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948页除此之外,《庄烈帝纪》诸本的论赞里还蕴藏着明朝的灭亡和崇祯帝的殉国是天命转移导致的观点,如“岂非天命哉”“而天命既去”“岂非气数使然哉”等词语,这些都强调了天命和气数的影响,暗喻明朝的灭亡是上天的意志。“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②张廷玉等:《明史》卷24《庄烈帝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5-336页。,则彰显清朝是新的天命所在,明清间已经完成了天命的转移,以此来建构清朝的政治合法性和正统地位,为清朝的统治所服务。
四、《明史·庄烈帝纪》诸本书法异同的原因
《庄烈帝纪》诸本既有相异之书法,亦有共通之书法,此已详见上述。而《庄烈帝纪》作为《明史》本纪的最后一篇,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多的关注,因而除了客观编纂原因影响它的书法外,其他诸多因素也会干扰它的书法。
(一)本纪编纂的客观准则
本纪的编纂与列传不同,以时间为线索,叙事应紧紧围绕皇帝,强调简明扼要,文约旨丰。《史通》有言:“又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③刘知几著、浦起龙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内篇》卷2《本纪第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5页。这是本纪编纂的客观准则。而416卷本《庄烈皇帝本纪》为最初之作,编纂时大量抄撮史料,泥沙俱下,未及精简。后出的王鸿绪本和殿本为了使《庄烈帝纪》更符合本纪的形态,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进行精炼,最终至殿本《庄烈帝本纪》才算称得上叙事简明。而这一书法改变的过程,正是本纪编纂客观准则促成的结果。
(二)纂修者个人的考量
作为编修的负责人,纂修者的考量无疑会对《庄烈帝纪》的书法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416 卷本《庄烈皇帝本纪》编纂的过于烦琐,就与万斯同主观上的放任有关,其编纂《明史》时的一个观点是“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④《清史列传》卷10正编七《王鸿绪》,见《清代传记丛刊》第9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398页。这直接导致了记事琐碎的结果。王鸿绪修史时删除论赞和“朔”等体例的行为也是出于其自身编修时的考量。殿本《庄烈帝本纪》一改前稿的史实取舍,转以《崇祯长编》为依准,这显然是纂修人员仔细考量后的安排。
(三)当时的政治环境
《明史》是官修史书,明史馆的纂修人员也都是在清廷统治下进行工作,因此,编纂时不得不考虑现实的政治环境。《庄烈帝纪》内容多涉及清廷,编纂时尤需小心谨慎,务要贴合统治者的心意,体现清朝的得国之正。其时文字狱屡兴,士人不免自危,如果文字触怒当权,轻则下诏切责,重则斧钺加身,毕竟“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①刘知几著、浦起龙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7《曲笔第二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况且为君父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②刘知几著、浦起龙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7《曲笔第二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2页。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编纂者又岂敢据实而书?以此观之,《庄烈帝纪》不论是美化明清间残酷的军事冲突,还是贬低农民军,塑造清廷为崇祯帝报仇的形象,抑或是宣扬明清易代乃天命转移的结果都不足为奇。
综上所述,作为一位亡国之君的本纪,《庄烈帝纪》的编纂至关重要,对崇祯帝的评价和政治定调事关清朝的正统地位和政治合法性。崇祯帝在位期间农民军和清朝的行动都必须有一个妥善的编写准则,否则无法表明天命所归。因此,从416 卷本到王鸿绪本再到殿本,《庄烈帝纪》始终深受政治环境和统治者意志的影响。对天灾人祸的大量描写,对农民军的极力贬损和宣扬明清间的天命转移,都是这一政治性因素作用的体现。纵使如此,《庄烈帝纪》还是一篇在体例和内容上都值得肯定的作品,大体史料价值上,416 卷本和王鸿绪本为长,内容表达和体例结构上,殿本为优。今天通过研究《庄烈帝纪》诸本的书法,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体会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