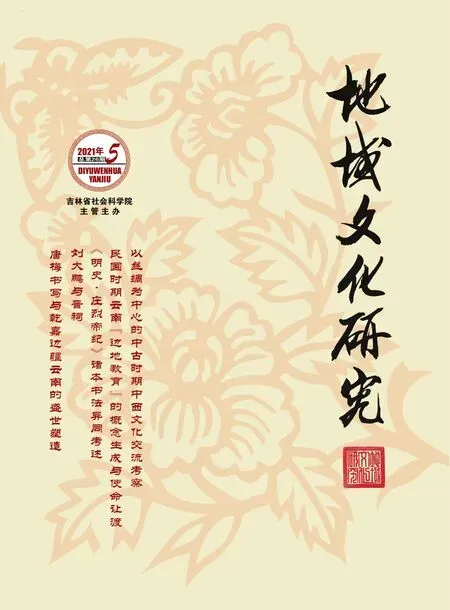通感与心感
——中国古代通感理论的现象学阐释
2021-11-26廖雨声
廖雨声 张 洁
一、心与通感研究
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通感现象的存在,并将其与心感联系在一起。《礼记·乐记》:“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把歌声与抗、坠、槁木、矩、钩、贯珠这些非听觉的感觉联系起来,来描写歌声给人的通感体验。孔颖达曾经给这段话做注:
“故歌”至“贯珠”,此一经论感动人心形状,如此诸事。“上如抗”者,言歌声上飨,感动人意,使之如似抗举也。“下如坠”者,言音声下响,感动人意,如似队落之下也。“曲如折”者,言音声回曲,感动人心,如似方折也。“止如槁木”者,言声音止静,感动人心如似枯槁之木,止而不动也。“倨中矩”者,言其音声雅曲,感动人心,如中当于矩也。“勾中钩”者,谓大屈也,言音声大屈曲,感动人心,如中当于钩也。“累累乎端如贯珠”,言声之状累累乎,感动人心,端正其状,如贯于珠,言声音感动于人,令人心想形状如此。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49页。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孔颖达十分注重“心”在音乐欣赏中通感体验的作用。他如此描绘通感体验经历的过程:听到歌声,我们的“心”为这一歌声感动,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抗、坠这样的重量感、钩这样的触觉和贯珠这样的视觉体验。“心”在我国古代美学思想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诗书礼乐都本于此。《礼记·乐记》曰:“乐者,心之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艺术的产生从根本上说就是心有所感,由于艺术本于心,“乐由中出,故治心。”艺术实现其效果也是通过作用于心,通过音乐以“治心”。“心”在艺术产生和欣赏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整个艺术活动都围绕着心。在艺术体验中,通感的产生也借助于心的作用。在心的作用下,听觉有了触觉、视觉、运动觉等感觉体验。孔颖达的注疏就是明确地用心感来解释通感。
虽然如此,对通感的系统理论探讨直到20世纪才出现。在借鉴中国古代美学资源时,用心感或者心觉来解释通感是国内艺术通感研究采取的主要途径。在“心”的作用下,各种感觉实现了沟通与融合,从而产生了通感现象。由此看来,心感与通感研究的关键是弄清“心”在通感产生过程中的作用,而这又要求我们首先弄清“心”的基本内涵。“心”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含义是纷繁复杂的,据张立文先生的疏释,从总体来看,“心”起码包含以下几重内涵:一、心为心脏,又为思维器官。心开始为象形字,原意为心房。同时,“心之官则思”心具有思维能力,但它仍属于身体的生理器官。二、“心”是一种主体意识,这时候的心超越了具体的器官,是人的思维、判断能力。《墨经·经上》曰:“闻,耳之聪也,循所闻而得意,心之察也。”“言,口之利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说的就是人能够根据说听、所说的而推断出其意,心则是人的推断能力。三、“心”为一种心理情感状态。比如说《易经·井卦九三爻辞》:“井渫不食,为我心恻。”恻,《说文》云:“痛也”。井中的污泥被清理,水复清洁,却仍不被饮用,心里感到悲痛。四、“心”为伦理道德观念。这以孟子为代表,他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这些道德观念都是人所固有的。五、心为天地万物的本原或本体。佛教说万法唯心,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弼说“天地以本为心也”,都是把心看作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源。①张立文:《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心”的含义如此复杂多变,导致当代的研究者在论述心在通感中的作用时,其立场和解释途径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比如陈育德的《灵心妙悟——艺术通感论》把心当作一个自明的概念,未加界定就用来解释通感。②陈育德:《灵心妙悟——艺术通感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7页。王丽在其博士论文《艺术通感与儿童艺术教育研究》中宣称,心是“广义的思维活动、情感、情绪等的综合,是内在精神活动的总称。”③王丽著:《艺术通感与儿童艺术教育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51-67页。在论文实际论述中则主要是指心理能力,包括表象、想象和情感等。这是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对古代心的概念做出的解释,王丽解释了心理因素对通感的内在发生所起的推动作用。陈宪年认为,通感不仅包括五官感觉,也包括心觉。但在他的论述中,既有佛教思想中的“心”,也有儒家和道家所说的“心”,更有西学中的内在感觉、内在感官等概念,以致心成了一个笼统而庞杂的概念,其意义和所指模糊不清。④陈宪年:《从感觉到心觉》,《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仇小屏把心觉看作是心理的整体功能,认为由五官之觉提升至心觉,在心觉中获得内在统一,才是美感的目的和极致。⑤仇小屏:《篇章结构类型论》(增修版),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157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当代学者对于“心”的看法尽管存在着众多的分歧和差异,但其共同特征是把“心”视为一种精神实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主观心灵,心感或心觉则被看作多种情绪和心理活动的总和,至于这种心理活动与五官感觉之间的差异,则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探讨。由于这个原因,学者们尽管一致公认心感与通感之间有着内在关联,然而这种关联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心感究竟如何使通感得以可能?这些关键的理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在这方面,现代西方的现象学理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二、心的现象学阐释
把“心”看作主观的精神实体,不仅是中国学者的观点,也是西方传统思想的共识。近代的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从而确立了主观与客观、心灵与肉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这种二元论的观点尽管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就通感问题而言,一旦身体被看作纯粹的物质,那么感觉就变成了纯粹的器官行为,感官之间的界限就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现象学思想的产生则为超越这种二元论思维方式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胡塞尔认为,意识行为具有意向性的特征,也就是说意识总是指向某种对象的,因而意识活动的产物——意向对象——就不同于实在对象,它既不是纯客观的,也不是纯主观的,而是介乎于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之间。梅洛—庞蒂进一步指出,意向性并不是心灵或自我的意识活动,而是身体的某种功能。身体何以能够自发地指向对象呢?这是因为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并不是物质性的肉体,而是肉体和心灵的统一体。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新的存在类型”。①梅洛-庞蒂著,罗国祥译:《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84页。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身体具有某种暧昧性或两重性:它既可以成为客体,也可以成为主体:既是看者又是可见者;既是触摸者又是可触者,或者说它就是这两者之间的交织。正是身体的这种两重性使其成为身体—主体(body-subject)。这种身体—主体的感知活动与通常所说的五官感觉有着本质的区别:五官感觉依赖于单一的感觉器官,并且每个器官都各司其职,互不干涉;身体的感知则是一种整体性的行为,必须通过各感觉器官之间的相互协作来进行。这正如梅洛—庞蒂所说的,“我的身体不是相邻器官的综合,而是一个协作的系统。”②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trans.by Colin Smith.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 2002.p.27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身体的感知天然就具有通感特征,至于单一的感觉活动恰恰是从这种原初的感知活动中分离出来的。
或许有人会说,梅洛—庞蒂所说的整体感知乃是一种身体行为,这与中国古代思想所谈论的心感不是正好相反吗?然而在我们看来,现象学所说的身体与中国思想中的心恰恰是相通的。从词源学上来看,在中国古代的甲古文中只有心的象形字,而心部字很少。这个时候人们大致只把其看作生命的器官,也就是说心与身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到了金文,心部字大增,它反映了人的思维认知的发展,与思维有关的字不归于脑,而归于心。③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修订版),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8页。这一发展变化即是心的含义不断扩充的过程。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无论心具有哪个层面上的意义,当它与感觉相联系时,它始终还是与身体器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其中“心之官则思”被人们广泛谈论,赵岐注:“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谓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欲之事来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为小人也。此乃天所与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谓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欲也。善胜恶,则恶不能夺之而已矣。”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14页。人们总是用身体五官与世界打交道,知觉是所有意义的根源。但是眼耳鼻口这些器官不能够有效识别外部的世界,容易沉迷于感官的享乐之中,于是被外物所蒙蔽,成为小人。心这种身体器官却能够思考,能够帮助揭开外物对其他五官之上的遮蔽,使得我们的欲求不仅仅追求感官的享受,而且也在追求仁义道德。由此可以看出,心和耳目口鼻一样,都属于身体,心与身并无本质区别。
不过,中国古代思想家并没有把心与感觉器官混为一谈,他们始终强调心的统一性,认为五官感觉必须处于心的支配之下。孟子说过:“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这表明在他看来,身体的各种器官并不是相互平等的,而是有着等级和贵贱之分。具体地说,心是贵体、大体,耳目之官则是贱体、小体,心是比耳目等器官更高级的。不同的感知觉必须在心的支配下发挥作用。荀子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心是耳目口鼻这些形体的君主,即主宰着它们。不仅如此,它还是“神明之主”,神明,“天赋智慧也,《庄子·天下篇》:‘神何由降?明何出?’梁启超云:神明,人之智慧也。”②熊公哲:《荀子今译今注》,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433页。可见,“心”还控制着智慧。《管子》继承了这一路径,认为“心之在体,君之位也”,在整个身体中,心的地位就像是君主一样,占统治的地位。只有“心处其道”,九窍才能正常发挥自己的功能。此时的身体才是有精神的。
那么,“心”为什么能够发挥“君主”的作用呢?这是由于“心”并不是一种实体意义上的肉体器官,而是各感觉器官所构成的整体。庄子就对心的这种非实体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庄子·天地》中说:“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悛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从这段话来看,庄子注意到五色、五声、五臭、五味这些感官欲望的追求会使人丧失虚静自然的本性。因此,他提出了“心斋”这一重要思想:“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就是说,只有把心当作感知活动的主体,用心感来取代五官感觉,才能克服五官感觉的局限性,避免感官欲望对于心的扰乱和损害。由于心摆脱了感官欲望的困扰,因而就处于虚静的状态,从而能固守自己的本性。不过,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要把心与五官剥离开来,使其蜕变为主观的精神,而是要使心成为五官的主宰者,从而克服五官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使其成为和谐的统一体。这样的五官,所提供的便不是纯粹的物质欲望和刺激,因为心把生气和灵性灌注给了五官。钱穆曾经指出,“中国人言心,非身上一器官,乃指此身各器官相互配合而发生之作用言。此一作用,乃可超于各器官,或说超于身,超于物,而自有其作用”,③钱穆著:《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72页。我以为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在庄子看来,这种虚静的状态只有未经物欲熏染的原始初民才能保有,但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指的就是肉体与心灵之间的和谐状态,也就是梅洛—庞蒂所说的身体—主体。身体的感知活动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外界的物质刺激,而是能够自发地与世界进行相互交流。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心与身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或者说它们之间具有某种同一性。当代学者把“心”归结为情感、情绪、思维等心理活动,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思想中二元论观点的影响。当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这种二元论的思想基因,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认为肉体的欲望会导致人的堕落,应该加以扼杀,这与西方的身心二元论可说是异曲同工。不过,中国传统思想归根到底并没有把身体与心灵视为截然对立的实体,而是十分强调两者的一体性。就心这一范畴而论,它既是指人的心灵,又是指人体中的心脏器官:“中国文化所说的‘心’,指的是人的生理构造中的一部分而言,即指的是五官百骸中的一部分在心的这一部分所发生的作用。”①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上海书店,2004年,第211页。从二元论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然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此却采取了辩证的观点。王廷相说过,“知觉者,心之用;虚灵者,心之体”,这就是说,心既有实体性的一面,又有虚无性的一面:就前者而言,它是一种肉体器官,是知觉活动的主体;就后者而言,它又是一种非物质的灵性,因而是肉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有与无的统一体。我们认为,这种辩证的观点与现象学的方法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
三、心感:通感形成的根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把“心”确定为身体—主体的一种意向综合能力。那么,心感与通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列子·黄帝篇》中的一段话为此提供了精辟的说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释。”这段话言简意赅,内涵却十分丰富。其前半部分描述的就是典型的通感现象:眼睛能够听见,耳朵能够嗅闻,鼻子能够言说,也就是说各种感觉器官可以跨越彼此的界限,承担起其他感官的职能。那么,这种现象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一言以蔽之,曰“心凝形释”,也就是说心具有一种凝定、整合的功能,它能够把各感觉器官的功能统一起来,从而使它们之间在物质形体和运作机制方面的分野涣然冰释。两千年前的古人能有如此深邃的洞察力,真令人叹为观止。
不过,心究竟是如何打破感官之间的界限的,这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白虎通》中说,“目为心视,口为心谈,耳为心听,鼻为口嗅,是其支体主也”,这就是说,心之所以能够把各种感觉整合起来,是因为感觉器官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都是为心服务的,是心的一种机能。问题在于,各种感觉器官毕竟有着截然不同的生理机制,其把握和传递信息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心为何能够克服它们之间的差异呢?这是由于心本来就不是与感官相分离的独立实体,而是由各感官构成的整体——身体。准确地说,感知活动的主体并不是感觉器官,而是身体—主体。身体在感知事物的时候,本来就是通过各感官的相互协作来进行的,比如我们要观看一个事物,不仅需要眼睛这种视觉器官,还需要把身体移动到恰当的位置,有时还需要用手把物体拿到眼前并前后翻转,这说明视觉活动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视觉器官,而是整个身体,其他感知活动自然也不例外。
或许有人会说,即便感觉器官之间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关系,然而在具体的感知活动中不是仍然需要各司其职吗?在日常生活中确乎如此,设若某人随意混用不同的感官,势必使自己的生活陷入混乱。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一现象恰恰说明,感官的分化和独立乃是人类生存活动的需要,因而反过来佐证了感官之间先天的互通性。这正如梅洛—庞蒂所说,“通感感知是通则,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仅仅是因为科学知识转移了我们体验的中心,为了从我们的身体组织中和作为物理学家觉察到的世界中推断出我们要看的,听的和感觉的,以至于我们不再会看、听,而且更一般地说,不再会感觉。”①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trans.by Colin Smith.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 2002.p.266.也就是说,我们原初性的感觉都是通感,只是后来的科学知识和生存活动将感觉分裂成了各种细致的感觉。那么,原初的感觉器官何以能够互通呢?梅洛—庞蒂对于脑损伤病人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发。他在《知觉现象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病人施耐德的大脑枕叶在战争中被炮弹的弹片所伤,导致他只能完成一些工厂里的日常工作,却无法按照指令在一个虚拟的情境中完成指定任务。具体地说,当被要求用手指指向自己的鼻子的时候,他必须先用手指接触到鼻子,然后才能指向鼻子,一旦要求他省略这个步骤,他便不知所措。这个例子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病人的感觉器官并未受损,感觉能力也很正常,但却无法完成正常的感知任务。病人所遇到的困难在于,他只能通过感官与对象的直接接触,才能感知对象,也就是说,他的感知活动蜕变成了单纯的器官行为。这从反面告诉我们,感知活动不仅需要具备正常的器官反应能力,还要求身体能够给器官提供某种额外的指令,使其行为包含某种虚拟性。
人们通常把想象视为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但在我们看来,身体—主体同样具备自身的想象力。如果说心灵的想象力是一种对心理表象进行加工和改造的能力的话,那么身体的想象力则是对各种感觉器官及其行为进行支配和筹划,使其实现身体的各种指令和意图的能力。施耐德的例子告诉我们,任何正常的感知行为都不是纯机械性的,而是包含着虚拟性的一面,它要求器官不仅能够对刺激做出正常的反应,而且能够主动地指涉、把握对象,也就是说必须具备某种意向性的功能。这也是身体意向性的一种具体表现。“身体同时通过其整个表面和全部器官承担触觉体验,并且进行它一种特定的触觉‘世界’的典型结构。”。②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trans.by Colin Smith.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 2002 p.369.在中国古代对心觉的解释中,心本身并不能产生感觉,无论心是作为心理或者作为身体整体,感觉总是与特定的感知器官联系在一起。心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在想象力的作用下,把耳目口鼻相互连通。当我们用眼睛在看的时候,身体自动地召唤其他的感官,共同参与到感知中来。与一般心灵的想象力相比,想象力始终与身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也可以称作“知觉想象”。於可训认为,“知觉想象是通过联觉、统觉等心理形式完成的。联觉解决各种感觉的横向沟通问题,统觉则解决对当前的事物的感觉与过去的感觉经验的纵向联系。这本身就意味着是对对象的单一的感觉反应(视、听感觉)的补充和强化,因而就直接可感知的形式而言,知觉想象对艺术对象确有一种“超越”作用。”③於可训:《艺术接受活动中的想象与评价》,《文学教育》2008年第11期。在这里,他把知觉想象的功能分成了联觉和统觉,并把它们只看做是心理形式,显然还没有超越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局限,但他毕竟注意到了想象力在综合感觉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因而还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美学因其注重深层体验的圆融性,尤为重视通感。佛教认为,人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陷于尘世易被污染,只要消除这种污染,达到心之澄明,六根就能互用,此亦所谓圆融之境界。心之澄明是通感圆融之根本。澄观《华严经疏》云:“统唯一真法界,谓总该万有,即是一心。”老庄思想追求混沌、太一,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对世界的感知脱离了原来的混沌与整一。这种求“包含着对自然万象的天然生机的肯定,包含着对人与物浑的秩序中所获得的原初体验、当下感知、自然生发的纯粹境界的肯定。”①刘绍瑾:《复古与复元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要达到这种境界,“虚其心”“心斋”是根本的途径。圆融、混沌这些基本思想都是将通感视为原初性的体验,尘世与文明奴役了我们的身体,使其成了囚笼,丧失了原有的想象力。要获得原初的通感,必须回到理性之源,那就是人与世界通过身体的最初交流,相信身体的想象与知觉功能。
比如中国美学中的神思范畴,它描述了艺术创作时主体突破时空限制,达到艺术自由的境界。刘勰说:“寂然凝虑,思接千里;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但神思具有其不可忽视的一面:它始终与“感”联系在一起。文学创作时神思运行,可以突破感知的时空限制,这正是身体想象力的作用。神思具有当下体验性,这种体验正是我们身体的当下感知,身体的参与使得审美感知突破时间与空间,突破单一感官的限制。因此,神思具有了身体的性质。西方的想象理论与神思相类似,但正是神思的这一特点与西方传统的想象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传统的想象力认为,它是一种意识与心灵的功能,与身体无关。康德说“我们有一种作为人类心灵基本能力的纯粹想象力,这种能力为一切先天知识奠定了基础。”②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0页。就是代表。在身体想象力的作用下,创作者可以把视觉与触觉沟通起来。比如,杜牧“天阶夜色凉如水”,王维“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都是视觉与触觉的沟通。
在审美知觉中,欣赏者暂时将艺术作品和日常生活隔离开来,只将目光关注到作品上,“我不再把作品看成是一个应该通过外观去认识的物,而是相反,把它看成一个自发地和直接地具有意义的物,亦即把它看成一个准主体。”③杜夫海纳著,韩树站译:《审美经验现象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432页。这是知觉与对象的直接相遇,天然地是一种原初性的通感体验。以音乐欣赏为例,在听众的接受活动中,感性通过身体而得到呈现,整个身体都参与到接受中来,不仅耳朵听,眼睛也发挥其作用,甚至整个身体都伴随着音乐产生运动。通过综合作用,我们获得了超越于听觉的多元化、立体化的感觉享受。
通感何以可能?这是一个困扰着中西思想界的学术难题。有关“心”以及心感的理论无疑为我们理解通感现象提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资源,然而如何把这种古典的资源与现代的思想方法结合起来,还是一条尚待探索的新路。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所迈出的显然还只是一个试探性的步伐,我们真切希望学界同仁能够批评指正,以期把对通感问题的研究继续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