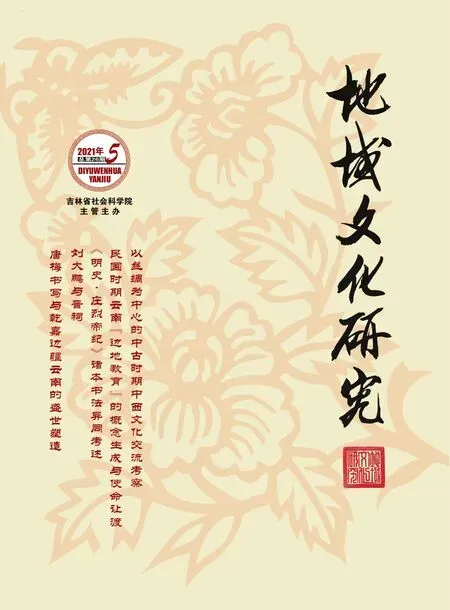《论语》“不愤不启”章诠释辨析
2021-11-26郭瑾
郭 瑾
两千年来,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基本上由儒家教育承担,而《论语》则是儒家的基础教材。“盖千年来,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以代六经”。①康有为:《论语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页。《论语》中不仅蕴含圣人之道,更是记录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载体。无古不成今,知今需鉴古。重新挖掘、梳理、审视这些教育思想,不仅能还原传统教育的原始意义,为现代教育理论奠以基石,更能使经典本身得以延展,为今后教育发展开示道路。
《论语·述而》篇第七章:“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此章虽然简短,却被奉为孔子启发性教育的经典表述。按照一般的理解,此章表述之意为:“孔子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出来却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东方,他却不能由此推知西、南、北三方,便不再教他了。”②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5页。然而,此章语言因对话语境的缺失,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对“不愤不启”章的解读倾向各有不同,注疏成果亦相当丰富。东汉郑玄认为“不愤不启”章体现了孔子“学思结合”的教育思想;宋代理学家们在“内圣之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不愤不启”章阐发的是孔子“学贵在自得”的教育理念。而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现代学者则从孔子“一以贯之”的儒家思想层面,推测“不愤不启”章传递的核心内容是德行教育,认为此章反映的是孔子对弟子德行教育的高度重视。虽然后世学者多追随郑玄、宋理学家的观点,但笔者认为“孔子重视弟子德行教育”的现代诠释也同样具有深刻意义及思想价值。
追溯“不愤不启”章诠释史的演变轨迹,其实不难发现,历代注疏或以经文所载之言依文解读,或以所持学派思想附会诠释,虽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的内涵蕴意,但也容易造成后世学者对“不愤不启”章理解的局限与偏差。因此,本文通过辨析“不愤不启”章的历代诠释,揭示此章在不同学者、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不同蕴意,并慎重评判其价值与不足。围绕经义文献,以“文本还原”的方式将“不愤不启”章置于整本《论语》所呈现的教育背景下全面理解此章。从孔子的教育方式出发,结合当时的教育内容与教育目的深入挖掘、全面分析,旨在为“不受重视”主张“德行教育”的现代诠释提供些许支撑,并为今后的《论语》相关注释工作提供另一层面的思考与探究。
一
自汉代以来,《论语》作为经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目,对其注疏及考证成为历代学者的重要议题。东汉郑玄师从京兆第五元先、东郡张恭祖、扶风郡马融等多位著名大儒,其学术思想融合了古、今文学家众家之长。自郑注出,经生皆从郑学,郑玄笺注的《论语》为各家所传承。郑玄认为“不愤不启”章所揭示的是学习与思考的关系。据《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载:
郑曰:孔子与人言,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①何晏集解,刑昺疏,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0页。
郑玄注“愤”、“悱”为“心愤愤”、“口悱悱”,一种“由心生”、“从口出”的状态。南朝梁皇侃在《论语义疏》中则将其具体训解为:“愤,谓学者之心思义未得而愤愤然也……悱,谓学者之口欲有所咨而未能宣,悱悱然也……”②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58页。由此得出,“愤”、“悱”为学者经过自主思考仍不解其中之意,心思义而不得、口欲说不能言的一种状态。学生呈现此状态后再给予启发的效果最好,“如此则识思之深也”。郑玄认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孔子强调受启发之前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对“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句的诠释,郑玄注曰:“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按照字面之意理解,当启发时举示一角,学生不能思考出其同类三角,孔子就不再教他了。然而孔子“则不复也”的原因仅为“学生不能思考出其同类三角”,这样的解释似乎难以符合情理。那么郑玄此句注释背后的深层蕴意是什么呢?
研究郑玄注《论语》时必须要注意一点:现世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注疏》是由三国魏何晏集解,宋刑昺注疏,清阮元校勘而成的。其中所载的郑玄注经过历代学者的援引集解、辗转抄写已并非原貌。且因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兼具儒学思想与玄学特点的《论语集解》一经问世便颇受欢迎。而由郑玄笺注的《论语》原本却日渐衰微直至亡佚。因此后世对《论语》“不愤不启”章的郑玄注记载原文已不得而知。直到20世纪初,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了众多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经文献专家整理校勘后由王素先生编著出版《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一书,当代学者可借此窥探《论语》郑注本原貌。至此,唐写本中关于“不愤不启”章郑氏注(以下简称“唐写本郑氏注”)的记载,与现世流传的《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中的郑氏注(以下简称“十三经注疏本郑氏注”)可互为补充,相互论证。据《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载:
孔子之教,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发为说之。如是则识思之深。复,重也。说则举一隅人不思其类比方而来,则不复重教之。不以三嵎返,是学而不思之也。①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76页。其中“□单个缺字”;“不详字数的缺文”。
对比发现,《唐写本郑氏注》与《十三经注疏本郑氏注》所载稍有不同。唐写本注“孔子之教”处,十三经注疏本作“孔子与人言”。唐写本中载有“复”和“不以三隅反”的注释,十三经注疏本却无。可以看出,不同于《十三经注疏本郑氏注》中的“其人不思其类”,《唐写本郑氏注》明确注有“不以三嵎返,是学而不思之也。”由此推测,郑玄认为孔子不再教的原因绝不是简单的“其人不思其类”,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在启发时学生只学习而不思考。然而,《唐写本郑氏注》的形成年代毕竟与郑玄所处的东汉相距较远,那么《唐写本郑氏注》“不愤不启”章所呈现的是郑玄真正的注释本意吗?
郑玄笺注的《论语》原本亡佚后,众多郑学爱好者都深感遗憾。乾嘉时期汉学兴盛,清代学者或辑佚整理校勘,力求恢复郑注原貌;或以现存其他儒家经典郑注为参照,深入探究郑注《论语》原意。清代黄式三在其《论语后案》中曰:
《礼·学记》:“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郑君《注》曰:“使之悱悱愤愤,然后启发也。”《易》:“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郑君《注》曰:“弟子初问,则告之以事义,不思其三隅相况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师而功寡,学者之灾也。渎筮则不复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和义而干事也。”②黄式三撰,张涅、韩岚点校:《论语后案》,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74页。
“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出自《礼记·学记》篇,讲的是教师应时常静默观察不必多说话,使学生存其心。郑玄在注解此处时,认为其表述正好对应《论语》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句所述之意,遂将此直接注为“使之悱悱愤愤,然后启发也。”“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此句出自《易经·蒙卦》篇中一则卦辞。这里先暂不探讨卦辞中所蕴含的卜筮预意,单从郑玄为其所作之注释可以看出,郑玄将教学过程与卜筮占卦比较。“不思其三隅相况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师而功寡,学者之灾也。渎筮则不复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和义而干事也。”学生不能一隅三反而滥问,是渎乱学务。渎乱学务被视为“勤师功寡”、“学者之灾”,渎乱学务则不再施教。那不再教的原因是什么,郑玄表达得很清楚“欲令思而得之”。
据此,《礼记》与《易经》中的郑氏注,恰好与唐写本“不愤不启”章的郑氏注相佐证。郑玄认为“不愤不启”章讲的是孔子“学思结合”的教育观。启发前学生应有所思,待其自主思考后再给予启发指导的效果最好。刘宝楠将此概括为:“已是用力于思,而未得其义,乃后启发为说之,使人知思之宜深,不敢不专心致志也。”③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0页。授教启发时也要学习与思考相结合。教师的“教”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不能完全代替学生去思考作结论。当教师以“一隅”示之,学生却“不以三嵎返”,说明学生还停留在被动接受、不主动思考的状态,因此不再施教,留出时间和空间让学生继续深入思考。
郑玄对“不愤不启”章如此诠释,其根源在于其秉承儒家“学思并重”的教育观念。郑玄认为好的启发教育是和谐的师生关系、轻松的课堂氛围以及积极独立的思考。因为只有经过思考才能对知识理解得更加透彻。“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思而得之则深。”①郑玄注,孔颖达等疏,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1页。反之,如果不用心思考、理解消化,所学知识也难以保持。“学不心解,则亡之易。”②郑玄注,孔颖达等疏,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页。因此,郑玄在诠释“不愤不启”章时着意于揭示学习和思考的关系。认为授教启发前学生要先有所思,授教启发时也要学思并用。郑玄这种“学思结合”的诠释观点被众多学者所沿用。宋刑昺曰:“……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其说之也,略举一隅以语之。凡物有四隅者,举一则三隅从可知,学者当以三隅反类一隅以思之。而其人若不以三隅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矣。”③何晏集解,刑昺疏,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0页。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当心愤愤、口悱悱时,已是用力于思,而未得其义,乃后启发为说之……‘不复重教之’者,言教之既不深思,则不复重教之。”④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0页。现代学者金池则认为“不愤不启”章全章以“学思结合”为中心论点,前后两句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其在《〈论语〉新译》一书中认为不能举一反三则不再教的原因,是因为要学生独立思考,达到“愤”、“悱”之态。⑤金池:《〈论语〉新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95页。
从孔子的教育原则、教育方法而论,郑玄释义的“学思结合”的观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就孔子整体的教育思想而言,仅从学习与思考的关系论证,理解诠释的角度与范围则较窄。再加上原本《论语》郑注已亡佚,一些现代学者对通行流传的“不愤不启”章郑注,或表意理解,或过渡引申,从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的错误曲解。有的学者认为“其人不思其类”不再教,与孔子的教育家形象相违背;⑥持此类观点的论文有:胡乐乐《孔子〈论语〉教育思想的五个新解》,《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肖建云《孔子的“教学不复论”新探》,《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年第2期;李波《“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正诂》,《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还有学者则认为郑玄对“不愤不启”章的注释是错误的。⑦持此类观点的论文有:聂振弢《“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新解》,《中州学刊》1985年第3期;聂振欧《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这些观点显然是对郑注和孔子教育的极大误解,但也从侧面说明仅以“学思结合”这一面向去诠释此章是远远不够的。
二
到了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们承续儒家教育理念,结合宋代理学思想,从“内圣之学”的角度为“不愤不启”章赋予超越前人的新诠释,认为此章传递的是孔子“学贵在自得”的教育理念,为“不愤不启”章增添了一层深邃的哲理蕴意。
程颐在谈论“不愤不启”章时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待其诚至而后告也。‘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既告之,必待其自得也。愤悱,诚意见于辞色者也。”⑧程颐、程颢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44页。与郑玄不同的是程颐将“愤悱”之态概括为“诚意见于辞色者也。”何为“诚意”?《说文解字》中“诚”与“信”互训。“诚”有“诚信、真诚”之意。如“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中庸》中的“诚”字开始延伸至道德哲学领域。“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刘寒在《〈中庸〉之“诚”蕴含的道德教育思想》一文中将其概括为:“《中庸》在抽象的‘道’的高度上论述了‘诚’的内涵,使之成为一个标志着儒家最高理想——‘天人合一’的哲学范畴。”①刘寒:《〈中庸〉之“诚”蕴含的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探索》2016年第10期。
程颐继承《中庸》的思想,认为“诚”既指天道、天理,也指个体自身修养工夫。就个体修养工夫而言,程子释“诚”为:“无妄之谓诚,不欺其次矣。”②程颐、程颢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2页。又曰:“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③程颐、程颢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6页。由此可见,古人把“诚”作为君子的评判标准,是学者修养之工、立身之本。学者要想成为圣人,自当以“诚”来涵养德行、提升学业。因此,程颐所言的“诚意”不仅仅指对待学业的“真诚”态度,亦是学者在追求“学以成圣”目标的一种自我修养工夫。“愤悱,诚意见于辞色者也。”当欲求而不得的“愤悱”之态在言语与面貌上呈现时,说明学者的内在积极性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治学修业的真诚态度与自我修养工夫已具备。这时再对其施加教育,不再是外在的强行灌输,而是主动的内化吸收,使教育效果最大化,程颐称其为:“……待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④程颐、程颢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8页。何为“沛然”?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做出详细解释:“此正所谓时雨之化。譬如种植之物,人力随分已加,但正当那时节欲发生未发生之际,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这些子雨来,生意岂可御也!”⑤朱熹著,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武汉:崇文书局,2018年,第654-655页。朱子对“沛然”的解释可谓形象生动、跃然纸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如同正在萌发而等待雨水滋润的万物一样,当学生欲求而不得,求知欲达到最为饱满的状态时,教师再予以点拨启发,犹如醍醐灌顶,随即茅塞顿开。
对“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句的理解,程颐曰:“既告之,必待其自得也。”何为“自得”?程颐曰:“学莫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⑥程颐、程颢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6页。“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⑦程颐、程颢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9页。程颢亦言:“学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言三隅,举其近。若夫‘告诸往而知来者’则其知已远矣。”⑧程颐、程颢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2页。概括言之,二程提到的“自得”,是一种“求于内”的自我获得能力。这种“自得”能力使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不仅仅停留于“一隅”、“三隅”上,而是自我独立思考后更深入的理解,是个体实现内在超越的透彻领悟。像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一样,达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的境界。
二程以学者“诚”之修养工夫为先决条件,以“自得”为教育目标的观点为朱熹所继承。与此同时,朱熹在此基础上继续生发下去,将“不愤不启”章所含蕴意定位在孔子劝学诲人处。将“诚意之见于色辞者”的“愤悱”与代表“自得”的“一隅三反”融为一体,进一步强调“不愤不启”章所揭示的是孔子“学贵在自得”的教育理念。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上章已言圣人诲人不倦之意,因并记此,欲学者勉于用力,以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愤悱,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待其诚至而后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复告尔。’又曰:‘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能坚固;待其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5页。除对“愤”、“悱”等字的训释更为翔实外,朱熹又言:“上章已言圣人诲人不倦之意,因并记此,欲学者勉于用力,以为受教之地也。”朱熹认为此章承接“诲人不倦”,孔子意在指点学者勤勉用力之处在“愤悱”,亦在“一隅三反”。而勤勉用力处自是学者“自得”处。朱熹在与其门人讨论时曰:“(愤悱)此虽圣人教人之语,然亦学者用力处。”②朱熹著,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武汉:崇文书局,2018年,第654页。“愤悱是去理会底。”③朱熹著,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武汉:崇文书局,2018年,第654页。“举一隅,其余三隅须是学者自去理会。”④朱熹著,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武汉:崇文书局,2018年,第654页。“愤悱”由学者自身内部得来,“一隅三反”则靠学者自己在实践中所得。朱熹认为,无论是内部自身的“自得于己”还是外部实践的“自己之得”皆为“自得”。如不待其“自得”而强行教之告之,必然是徒劳无益的。“若不待愤悱而启发之,不以三隅反而复之,则彼不惟不理会得,且听得亦未将做事。”⑤朱熹著,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武汉:崇文书局,2018年,第654页。至此,程朱学者对“不愤不启”章“学贵在自得”的诠释趋于完善。
宋理学家将此章蕴意归于“自得”究其原因在于其倡导“内圣之学”的理学思想。宋代学者以“诚”、“敬”作修养工夫,追求道德人格的自我强化与自我完善,以期能够“学以成圣”,因此格外强调“自求自得”。这种“学贵在自得”的诠释观点后世亦不乏呼应者。如明蔡清《论语蒙引》中曰:“凡物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若不能以三隅来相反证,则其不能自力,而了悟之途犹塞,便不再告也。”⑥高尚榘:《论语歧解辑录》,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55页。现代学者钱穆《论语新解》则指出“自得”效果因人而异:“上章言孔子诲人不倦,编者以本章承其后,欲学者自勉于受教之地。虽有时雨,大者大生,小者小生,然不沃不毛之地则不生,非圣人之不轻施教。”⑦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157页。然而,程朱理学的诠释亦有它的局限性。宋理学家因受“天人合一”的影响,在解读经义时不免常常附会义理学说。将“愤悱”之意与学者“诚”之修养工夫混为一谈,使其晦涩难懂,易生曲解。有的学者认为朱熹此种解释“似是而非”。认为“愤悱”之下给予指导,“不以三隅反”时却不再教而待其“自得”,前后行文不一致。⑧杨新勋:《〈论语〉诂解五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5期。还有的学者认为秉承“不告说”而待其“自得”是在推卸教学责任。⑨肖建云:《孔子的“教学不复论”新探》,《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年第2期。那么现代学者认为“不愤不启”章传递的是孔子德行教育的观点又是否合理呢?
三
不同于郑玄和程朱先贤的诠释方式,现代学者从孔子“一以贯之”的儒家思想层面,推测“不愤不启”章传递的是孔子对德行教育的高度重视。李泽厚在谈及《论语》此章时说:“或曰,此章并非讲知识,仍是讲德行,即道德应举一反三,以约控博,才是‘一以贯之’亦通。”①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第126页。董子竹在《论语正裁》中亦认为此章孔子是在启发引导学生识“明德”,而不是知识。②董子竹:《论语正裁》,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32页。此观点的提出为理解“不愤不启”章提供了另外一种全新的思路。但因现代学者多是推测并未详细予以论证,所以此观点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在系统辨析了郑玄、程朱先贤等注疏的价值意义以及局限后,本文将此章诠释定位于“德行教育”这种观点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对《论语》章节内涵的解读,既不能脱离文献经义本身,也不能脱离孔子整体的教育思想。孔子推崇以礼治国、以德安民,目的是将弟子培养成“仁德”君子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其教育内容自然以“德行教育”为主。因此,本文试图从经义文献入手,以“文本还原”的方式将“不愤不启”章置于整本《论语》所呈现的教育背景下。从孔子的教育方式出发,结合当时的教育内容与教育目的进行深入挖掘,全面分析此章所藏的原初蕴意。
孔子被尊为“先师典范”、“万世师表”,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其独特的教育方式。纵观《论语》可以发现,孔子的教学方式常以对话形式展开,对话内容也并非现实教学过程中真正意义的知识讲授,更像是圣贤尊者在对世人传授道义、指点迷津、开启智慧。在与其弟子的对话中可以发现,孔子常以“隐言”、“慎言”甚至“不言”的方式启发弟子。所谓“隐言”,即不直言相教,或隐喻作比,或引经据典,表达含蓄委婉。《论语·述而》中,子路问孔子如果率军打仗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共事。孔子言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以“赤手空拳与老虎搏斗”和“不用船只而冒险渡河”为喻,劝诫子路切勿鲁莽无谋。“慎言”,即相教时出言谨慎,言简意赅,字字珠玑。《论语·子路》中,子路向孔子询问政务,孔子仅以“先之,劳之”四字回答。子路对此回答有些不满足,请求老师再多讲一点,孔子又仅答二字“无倦”。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程子曰:“子路问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请益,则曰‘无倦’而已。未尝复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孔子所言“无倦”二字与之前的“先之,劳之”意义相当,并无其他实际意义。孔子追加毫无意义的两字,目的就是以此来启发子路,告诫其切勿急功近利、贪多无厌。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无论“隐言”相教还是“慎言”引导,孔子的教育目的都是为了开启学生思维,激发学生深入思考。下面再来看另外一种特殊的启发方式——“不言之教”,也就是“不愤不启”章着重探讨的“则不复也”的教育方式。
《论语·阳货》中,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对弟子说:“我想不说话了”。孔子为何“欲无言”?朱熹认为:“学者多以言语观圣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实,有不待言面显示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发此以警之。”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9页。按照朱熹的理解,天理已显现于圣人,不能只知圣人“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故孔子以“不言”警示之。有学者认为“予欲无言”章是“孔子晚年在体悟‘性与天道’这一道德修养主题时的一大‘发现’”①杨柳新:《不言之教——〈易传〉中的儒家道德修养思想》,《人文杂志》2011年第2期。。其思想来源于《易传》,是一种指向语言之外的形上之思、道德信仰及其实践智慧的自我修养过程。②杨柳新:《不言之教——〈易传〉中的儒家道德修养思想》,《人文杂志》2011年第2期。对这种形而上的道德修养方式暂且不论,单从教导弟子来看,孔子认为在教育过程中一些语言是非必需的,如“上天从不言语,四季照常运转,万物依然生长”。其意在告诫弟子切勿只关注教师“言语”传授,学习中更应该独立思考,切身体悟。因此,孔子在传道授业解惑时,这种“不言”的教育方式是确实存在的。不仅如此,从“予欲无言”章还可以看出,孔子公开表示“我想不说话了”,说明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孔子会刻意选择这种教育方式。就此括而言之,所谓“不言之教”,是孔子在某个特定时期或场合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不同于以往的言语相教,其以“静默”或“无言”的形式教育弟子,看似“无教”实际却是超越文本的深层蕴意的传授。实际上,“不言之教”也并非真的完全摒弃语言,当子贡不解其中之意加以追问时,孔子又以“四时运转、万物生长”为喻来点悟弟子。因此,孔子声称“予欲无言”只是暂时不言。那么孔子到底会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不言之教”呢?请看《论语》中两个典型的教学案例。
据《论语·子路》载: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据《论语·颜渊》载: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论语》中孔子与弟子樊迟的对话共有六次,这是其中的两次。对话的先后顺序已不可考证,但是从对话的内容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弟子时,在不同的教学情境下所采用的不同教育方式。第一则对话中,樊迟向老师“请学稼”、“请学为圃”,孔子回以“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后便不再作答。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杨时语:“(樊)须之学疑不及此,而不能问。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复。”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2页。孔子认为礼、义、信为治国之要,“君子谋道不谋食”,樊迟求学于圣人门下,却将稼穑之事作为治学方向足以显示其志向浅薄。杨时所言“不能以三隅反”指的是樊迟所思所学的“一隅”仍停留于“小人”阶段,还未能推及至“三隅”的君子之志,更不能理会君子当以礼修身,以道安民的深层蕴意。孔子不再言说,一方面意在提醒樊迟所问不当,另一方面欲令其思考其中深意。第二则对话中孔子的教学方式则与第一则明显不同。当樊迟向老师“问崇德,修慝,辨惑”时,孔子马上给予回答并夸赞其“善哉问”。为何这次樊迟所问,孔子却选择“直言相教”呢?刑昺义疏曰:“‘子曰善哉问者’,其问皆修身之要,故善之。”④何晏集解,刑昺疏,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9页。樊迟所问崇尚仁德、修善邪恶、辨别疑惑皆为君子之道。能提出此问,表明樊迟已然意识到这三方面对君子修身立本的重要性,遂孔子继续教之以增进学识。
《论语·雍也》中,孔子曾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当樊迟问学“稼穑之事”,此时尚处于“中人以下”的“小人”阶段,“小人,谓细民,孟子所谓小人之事者也。”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2页。“骤而语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将妄意蹄。”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页。骤然与还停留于“小农”志向的樊迟,谈超出其理解范围的君子之道,可能会使其陷入更深的疑惑。而当樊迟“问崇德,修慝,辨惑”时,所问见所思,说明樊迟对君子立身之本已有一定的基础理解,达到“能以三隅反”的程度,因此孔子“可以语上也”,此时教之则能助其对君子之道理解的更加透彻。从“不言”到“直言”,可以看出孔子对教育方式的慎重选择。其实,从樊迟的案例已经可以推测出,孔子认为的“愤悱”、“一隅三反”绝不仅仅是要求学生要具备知识层面的理解消化及学习迁移能力,还包括在思想精神层面对孔子倡导的儒家思想的基础理解与君子之道的初步认知。那么孔子认为的“一隅三反”究竟是什么?请参看下面两则经典教学案例。
据《论语·学而》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据《论语·八佾》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第一则中子贡向老师请教贫富之道时,子贡经孔子“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的点拨推及出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必须经历如同《诗经》中所述的打磨象牙、玉石那样精益求精的艰难过程。孔子听出了子贡对道德修养由浅入深的理解与领悟,遂而夸赞并言可以与他讨论《诗经》了。第二则中子夏向孔子询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所载意义,孔子说:“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子夏由女子仪态必须用礼来熏陶而推及,得出君子要以礼修身的深层道理。由此获得孔子的夸赞并言可以与他讨论《诗经》了。两则教案中,子贡由“礼”联想到“诗”,从贫富之道推及道德修养境界;子夏由“诗”联想到“礼”,从女子仪态推及君子立身之本。子贡和子夏所问之初就已经显示出对“礼”或“诗”的思考,举一反三通过“礼”与“诗”之间的相互联想,足见他们对君子当“学礼以立”、“学诗以言”的深入理解,达到了孔子认为能继续施教,即“始可与言《诗》已矣”的程度。综合孔子以上所有的教学案例来看,我们发现“不愤不启”章所论述的不仅仅是常规意义上的知识传授,还有塑造“仁德”君子的德行教育。当弟子还处在“不以三隅反”对立身之本还不清楚的蒙昧状态,说明其在认知水平、理解程度上尚未达到可以与之谈论更高深的君子之道。对于君子德行教育的重视态度使孔子选择“则不复也”的教育方式,意欲为其留出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
其实,以君子“德行”为主要教育内容在《论语》中是显而易见的。从《论语》中所呈现的教学情境来看,孔子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主要来源于西周时期的官学教育,而“六经”则由“删述《六经》”的孔子整理创立。在“六艺”教学方面,孔子有关“礼”的教学场景最多;在“六经”课程方面,则多以“诗”为中心展开。以“礼”和“诗”作核心教育内容源于孔子的教育思想。晚年的孔子期望通过教育来培养君子贤才扩大其政治影响。孔子政治上主张以礼治国、以德安民,教学方面自然以确定社会等级制度、规范行为准则的“礼”教和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着重道德教化的“诗”教为主。无论是“礼”教还是“诗”教皆是对弟子德行的培养。孔子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将弟子培养成有才干、有道德、有理想的君子,从而实现自己伦理和谐、仁爱崇礼、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因此,孔子对弟子的德行教育非常重视,这种高度重视体现在对好学颜回早逝的沉痛惋惜;对洒脱曾晳“风乎舞雩,咏而归”志向的强烈认同;对没有阻止“伐颛臾”冉有的深切责备;对停留于“小人”之志樊迟的“不言之教”上。
从郑玄注“学思结合”的教育思考,到程朱理学“学贵在自得”的延伸拓展,再到现代学者“德行教育”的高度重视。“不愤不启”章不仅呈现了一个生动的教育过程,而且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学者的诠释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展现出《论语》多面性、开放性的思想魅力。毋庸置疑,郑玄、程朱等先贤时哲对“不愤不启”章的阐释在《论语》诠释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基于《论语》经义文献和孔子整体教育思想角度提出的“孔子对德行教育高度重视”的观点也同样富有意义。孔子之所以被称为“万世师表”,孔子之学之所以被称为“圣学”,正是在于孔子的教育思想从来都是多元的、包容的。本文不同于以往对文本某一章节或某一教育理念进行解读,而是选择回归经义文献并置于整体教育背景下进行全面分析的诠释方式,更有助于挖掘经典背后所藏的原初蕴意及孔子伟大的教育思想的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