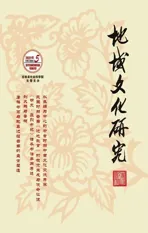唐梅书写与乾嘉边疆云南的盛世塑造
2021-11-26李超
李 超
云南素有“花枝不断四时春”的美誉,其中山茶为明人吟咏最多。但值得注意的是,清中期之后,昆明黑龙潭龙泉观的两株俗传唐梅,风头超过山茶,上至总督巡抚,下至黎民庶众,都对其爱赏有加,文人题咏不绝。时人檀萃《滇海虞衡志》品第滇南花卉,虽称:“滇南茶花甲天下……此花宜为第一”,但又称:“红梅莫盛于滇,而龙泉之唐梅、腾越之鲁梅,见于画与传者,光怪离奇,极人间所未有,此花宜为第二。”①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1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0页。区区唐梅为云南红梅增色不少。道光昆明进士戴䌹孙还将这两株唐梅写进《昆明县志》,使其永远流芳。②戴炯孙:《昆明县志》,见《云南府县志辑》2,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86页。那么,龙泉观的唐梅何以走进大众的视野?它呈现给边疆云南怎样的景观?这一文化现象背后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深层原因呢?③关于唐梅,程杰《论昆明黑龙潭唐梅的历史景象和文化意义》(《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3年增刊第1期)一文重点考述景点的起源和盛衰演变。本文着眼于清人对唐梅的书写及其蕴含的深层内涵。希望本问题的探讨,能为云南地域文学研究,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考。
一、雍乾时期龙泉观唐梅的被发现
云南俗传唐梅,还有大理灵会寺和腾越鲁家,但远不及龙泉观出名。④灵会寺唐梅仅见张汉《大理灵会寺唐梅》和高奣映《唐梅》两诗,鲁家唐梅仅见彭崧毓《鲁梅歌》。龙泉观得名源于龙泉山,《昆明县志》称:“龙泉山,在县东北三十里,一名太极山,山水萦合,仙灵窟宅,上有真人宫,下有黑龙潭,其上有五老山。”①戴炯孙:《昆明县志》,见《云南府县志辑》2,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18页。阮元《云南黑水图考》认为黑龙潭附近即汉祠故址。关于龙泉观修建时间,明人王景常《龙泉山道院记》称:“元初,尝构祠崇之,中遭兵难,祠毁……今西平侯沐公以为,此邦微是泉,禾稼且槁死,而祠宇弗葺,神灵不栖。岁甲戌,肇于泉之旁,构祠以栖神。乙亥,又择地之高亢,构道院一区,以为之镇。”②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可见龙泉观元时就建成,明初之后几经修复。历代官员重视龙泉观的原因,正如刘彭年《重修龙泉观记》所称“滇民足食之源,水旱祈祷之所也。”③萧霁虹:《云南道教碑刻辑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7页。
但是元明云南史料包括诗文,均无道及龙泉观中有唐梅之事。甚至一部《天启滇志》之艺文志,咏花诗以茶花居多,绝少梅花。④明人杨慎《滇春好》称:“滇春好,百卉让山茶”,担当《咏山茶》称:“山茶按谱甲于滇”,邓渼《滇中茶花记》称:“滇茶甲海内”,并作《山茶花诗一百韵》,唐尧官有《茶花赋》,俞纬《滇南赋》称“山茶葱郁于峰巅”。清初,顺治朝布政使彭而述有《龙潭曲》,康熙朝总督范承勋亲到龙泉观祈雨,并作《庚午十月游黑龙潭拟古》,同时张毓碧作《重修黑龙潭庙碑记》,都未提到唐梅。而仅有时任乡试主考李澄中《归自龙泉观道中纪兴》、释本元《游龙泉观》分别有“梅花十月似春前”“古梅花作萧疏影”之语。
古梅走进大众的视野是在雍乾之际。先是总督鄂尔泰《蔡魏公昆季同王昆贤、谭武庵游龙泉观道院,登绝顶探梅还,聊纪一绝句用赠魏公》⑤鄂尔泰:《西林遗稿》卷6,《清代诗文集汇编》2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25页。诗,这是有意探梅,据其所写方位,应该就是后人所谓唐梅。其后,从军滇南的著名学者王昶于乾隆辛卯(1771)作《龙泉观》诗,末云:“古梅五百秋,亦与长生期。惜逢春已暮,不值花葳蕤。森森两翠柏,根脉含清漪。何当采其实,服食同隐芝。”诗注云:“观前梅二、柏四,皆四五百年物,旁有流泉绕之”。⑥王昶:《春融堂集》卷1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明确交代古梅两株,五百年历史。再其后,乾隆四十二年(1777)云贵总督李侍尧《龙泉观古梅记》称:“自潭之左折而上,岩壑环互,竹树葱倩。林罅鸱吻,翼然为龙泉观。层墄累楹,有侐其宇。中植红梅二,根干纠结连蜷,殆难状喻。花复瓣如重台,视群梅小异。相传为李唐时物,余丁酉春奉命来滇,廉得其概。而薄领殷凑,不暇径诣。顷阅度六河水利,地接花所,破萼旬有余矣。与午桥中丞,便证所闻。舒带坐南荣下,古香在树,落英沾衣。譬诸涉瀛登阆,不足方其乐且适也。余维滇之卉木,甲于直省,梅尤称首。兹花为唐为宋,不载志乘。睇视树身,如冶铁然,要非近代物也。余与中丞先后下车,即知是花顾寝弥年月,星记且一周矣。始因阅河过之,而艳述之。事之在耳目,前而未能测识者,岂尠也哉。爰写生家,象梅之形与石,而为之记。”⑦曹善寿:《云南林业文化碑刻》,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42-148页。而巡抚裴宗锡《黑龙潭龙泉观唐梅碑跋》曰:“余念是梅,蔚然滇中,且数百年。时眼恒卑之,不相矜许”。⑧曹善寿:《云南林业文化碑刻》,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跋文题目疑为编者所加。读这一记一跋,可以得到二点信息:一梅花到底植于何年,史志并没有确切的记载,因而唐梅之说,仅是径直沿用传闻,因此记文用“古梅”之称;二梅花之美,总督大人以为能识其妙者并不多,巡抚以为当时世俗轻视它,因而总督不仅艳述之,并且请化工描摹刻石,多少有广其声誉的意味。这应该是古梅被浓墨重彩书写的第一次。另外还有宦滇官员吴大勋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作《滇南闻见录》称:“黑龙潭之岭上有红梅二株,干已剥蚀殆尽,仅存枯皮,古质斑斓,横卧于地,离奇夭矫,如虬龙,如横峰。而花朵攒簇,又如锦片,如火球。坐玩其旁,清芬袭人……不知植自何代。相传以为唐梅,疑或然也。”①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页。他描绘唐梅姿态与花香,于唐梅之说,在疑与然之间。从以上所述,可见这两株古梅至少是明以前甚至元以前物。为什么之前罕有人提及?它是一直存在,还是经移植而来,抑或枯木逢春?难以考证。但自总督李侍尧象梅刻石之后,唐梅渐进成为昆明一大文化景观,开始活跃于边疆云南督抚官员和文人士子之间,被书写不绝。
二、乾嘉云南督抚官员、士子对唐梅的书写
先是上层督抚官员对唐梅的书写。包括诗咏、记文、图画。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时任云南巡抚刘秉恬《公余集》有黑龙潭古梅诗11 首,他于查看河事之便或公余,常与同僚赴龙泉观赏梅,刘秉恬1首径直用了《唐梅》的标题。其对梅之爱可见一斑。其《石刻梅花亭》云:“壁间写出一林春,逼近传容自得真。风雨年来多剥落,对亭惆怅与谁伦。”②刘秉恬:《公余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8页。所见应该就是前总督李侍尧命写生家所摹刻之梅。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时任云南巡抚谭尚忠作《游龙泉观梅花记》,记文中“山腰建太极亭,有李钦斋节相古梅记石刻”句,③值得注意,此句见柯愈春编纂《说海》第七册收录谭尚忠《游龙泉观梅花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2226页,应该是谭尚忠初稿,而在《纫芳斋文集》同文中未见此句。前有“于簿书检校竟……总督富方厓、布政使王兰泉、盐法道杨养斋诸公及余相与会于东郭饮酒,而行观所谓龙泉观梅花者”。嘉庆初年,初彭龄抚滇,有咏唐梅诗,并将石梅拓图邀众文士题咏。嘉庆五年(1800),在滇做官的著名学者桂馥有感唐梅无人爱护,故作栏加以保护,钱塘人钱杜有诗《滇中黑龙潭有古梅两株,唐时物也,未谷为设阑楯,索余图永之于石》为记。至此,唐梅作为自然景点被逐渐确立。嘉庆九年(1804)上任云贵总督的伯麟,其《退思斋吟草》中有关于唐梅诗9 首,其《同陈望坡中丞游龙泉观》,陈望坡即时任巡抚陈若霖,其《题硕致堂别驾龙潭游观图》,硕致堂即硕庆,号味农,他公差到滇,为黑龙潭写下“两树梅花一潭水,四时烟雨半山云”的名联,此联更增添了唐梅的景观效应。嘉庆十二年(1807)任云南布政使的蒋砺堂,与同僚在唐梅下践行前巡抚谭尚忠之子、学使谭兰楣。嘉庆十八年(1813)来云南任知府的宋湘数次游观唐梅并有题壁诗。嘉庆十七年(1812)到任的学使顾莼有多幅唐梅图在士林中流传,诗人郭尚先《题顾南雅学士所画黑龙潭唐梅》,诗序云:“余丙子(1816)使滇,与望坡、吴羮二前辈同游近华浦,酒间谈黑龙潭唐梅之奇。”④郭尚先:《郭大理诗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49页。可以说,乾嘉时期,唐梅成为官员游玩、迎来送往的一个景点。
上层的风尚带动滇南文士欣赏唐梅之风。嘉庆初,诗人李观、段琦都有咏唐梅诗,诗人谷际岐、余萃文、袁文揆、严烺都有和初彭龄赏唐梅之作。谷际岐时在朝做官,是初彭龄的座师,谷有《初颐园中丞以滇南龙泉观古梅图索题为书长句》《再叠初颐园中丞滇南龙泉观赏梅韵四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刘大绅与五华弟子的咏梅风雅。嘉庆十七年(1812)壬申,应总督伯麟邀请,从济南辞官归来的刘大绅入主五华书院。刘大绅爱赏花,诗集中写梅诗众多,仅龙泉观梅花就有9首,从其《为硕致堂刺史题黑龙潭观梅图》诗题,可知他是总督座上宾。他提倡风雅,有意将上流雅集风气传递给子弟。其弟子戴淳有《寄庵先生命邓售之画唐梅图即席题咏分得清字》诗,李于阳有《九月二十四日侍寄庵夫子游龙泉观邓君鸿文写梅花一幅诸弟子各分韵赋诗为先生寿得山字》诗,均记载刘大绅生日于龙泉观的一次雅集。刘大绅在梅花未开的九月赏梅,极赏老梅古瘦清癯的精神,正是其夫子自道。师生的雅集,诗书画交融,如邓鸿文即画家邓售之,他挥毫,为雅集添兴;雅集还乩仙鬼怪之事相杂,李于阳《戊寅孟秋十有二日诸同学侍寄庵夫子小集即园,即事成诗分韵得之字》,即园为李于阳寓所,诗注“时请乩仙”,事情虽不发生在唐梅身上,但说明他们的雅集有市井谐趣的一面;雅集还助长了五华弟子群体诗歌创作,当时咏唐梅的诗人,还有戴絅孙、马之龙、倪绣、杨载彤、侯锡珵、马骏、杨松麓、牛焘等五华子弟,一些相同的诗题如《问讯龙泉观唐梅》反映群体的雅好。
总体来说,较之数十年前裴宗锡所说“时眼恒卑之”,滇人对唐梅态度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此多的关注,如此多的唐梅书写,主要聚焦于三方面内容:
第一,友情和乡愁的慰藉。唐梅常常慰藉滇南文士远游人的乡愁。如谷际岐《再叠初颐园中丞滇南龙泉观赏梅韵四首》其一云:“不见唐梅久,家山枉复青。金樽闲处倒,玉笛梦中听。有客探春信,无人寄驿亭。一般风月主,独让扣仙扃。”①谷际岐:《西阿先生诗草》卷2,见《丛书集成续编》第176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524页。在安徽望江作县令的大理人师范《题万春田合画龙泉观唐梅图大幅》云:“几时相从潭水边,持画对真两称快。”②师范:《师荔扉诗集》,见《丛书集成续编》第177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265页。在京任职的宜良人严烺《陈卧庐明经画梅见寄题诗答之》云:“为语龙泉两唐树,他时重共话咸酸。”③严烺:《红茗山房诗存》卷7,见《丛书集成续编》第138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239页。曾任安徽怀宁知县的大理人沙琛《黑龙潭值老梅盛开,感怀旧游,用壁间芷湾太守韵次之》,其中回忆往昔友朋,云:“一从薄宦各奔走,云摇雨散尘涨天。花晨月夕忆往事,难忘胜慨花蕃鲜。”④沙琛:《点苍山人诗钞》卷7,《丛书集成续编》第138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53页。
第二,发千古之思情,或仙隐脱尘,或默照禅理。此前,王昶、李侍尧的文字其实就有仙隐之思。而与谭尚忠一同赏梅的盐法道杨养斋即杨有涵,其《远香亭诗钞》有《冬日偕诸同人游龙泉观梅花》诗,称:“老干蟠虬龙,嫩蕊坼琼路。奇香袭肺腑,远闻数百步。……我时偕朋侪,各有沧州趣。”⑤杨有涵:《远香亭诗钞》卷33,清刻本。描写在花下留恋,慰藉仕宦烦扰,生出隐逸之想,是官员内心另一面的反映。而刘秉恬《乙巳封印后一日诣黑龙潭赏梅诗》称:“闲情封印后,逸兴赏梅花。两树花全发,空山色欲然。朱颜非淡泊,铁杆自盘旋。愈老神逾茂,于斯可悟禅。”⑥刘秉恬:《乙巳封印后一日诣黑龙潭赏梅诗》,见《云南林业文化碑刻》,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80页。保山诗人袁文揆《癸亥二月次初颐园少司寇壬戌除夕龙泉观赏梅原韵即以送别》,称:“影动潭澄月,香留风定天。自邀尘外赏,默契饮中禅。”⑦袁文揆:《时畲堂诗稿》卷4,见《丛书集成续编》第117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438页。则又是静悟禅理。
第三,赞美贞骨,寄托风调雨顺、民风和乐情怀。谭尚忠《游龙泉观梅花记》最值得玩味。文章极写丰收雨余之乐,结尾以古梅作结,谓“滇之人,无贤否贵贱,莫不珍异爱惜之”,①柯愈春编纂:《说海》第七册,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2227页。并称赞梅花“经千岁,秉清华之气,得乎日月雨露之精,清幽自守,贞固独成,是以老而弥劲,花光烂发,益具精神。然未尝离人独立,自矜孤介。入轩盖通途,而其不磷不淄,历岁深且久者犹是也。于是诸公相与饮酒花下,尽醉而归。过金华诸村,居民闻,争持短炬照行者,如奉其父母,不知其为官长也。既归,方厓公曰,是丰乐象也,不可以不记。”②谭尚忠:《纫芳斋文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文章既凸显了老梅清幽自守、老而弥劲的品格和操守,更有对风调雨顺、民丰和乐时局的赞美。伯麟《题硕致堂别驾龙潭游观图》称:“此图常展观,潭梅若亲睹。望君调鼎羹,望君作霖雨”。③伯麟:《退思斋吟草》卷6,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29页。也是风调雨顺的期盼。
三、从唐梅书写管窥乾嘉文人的盛世心态
自宋人林逋以来,梅花被强化了气节、意志的象征含义和作为士大夫人格图腾的文化属性。④程杰:《论中国梅文化》,《杭州学刊》2017年第2期。滇南的赏梅之风,自然是受中原传统审美风尚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是入滇官员把中原的审美风尚带到了滇南。但是明代以来,滇南吟咏最多的是山茶,咏梅并不出众。为何到乾嘉开始兴起唐梅的吟咏呢?这背后或许有更深层的原因。
从大背景而言,与清王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分不开,更与盛世期许相连。清世祖十二年(1655)曾谕礼部:“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天平。”⑤《清世祖实录》卷91“顺治十二年三月壬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借助文教,赢取儒家士子的支持,这是历代封建王朝,尤其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策略。乾隆皇帝深谙汉文化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何瑜先生认为:“乾隆时期大规模仿建江南园林的举措,不能简单看作太平天子的爱好与奢靡,……它成为长期的‘治世之资’和‘警示之园’。”⑥何瑜:《清代园居理政与文化认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乾隆皇帝对梅花的酷爱也传递出这样一种关联。有研究表明,乾隆是中国历史上与梅花最亲密的皇帝,他令宫中遍植梅花,曾六赴邓尉赏梅,还精于赏鉴梅画,尤其钟爱唐人宋璟《梅花赋》。⑦林雁:《论乾隆皇帝与梅花》,《现代园林》2006年第6期。而宋璟正是“开元盛世”的贤相。梅之属性,《尚书·说命》云:“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宰相之职与梅之属性相似。梅花之清与骨,又典型符合儒家士大夫之人格审美。乾隆这位有为君王爱梅,是否在向江南士大夫示好?其渴求贤能,借汉文化塑造如同唐代“开元盛世”般的大清气象明显。总督李侍尧的艳述并石刻古梅,正可以看作来自君王自上而下的力量。《滇南杂志》记载:“鲁梅者,腾越州鲁家之梅也。在城中西偏,其梅甚古,传为千余年物也。李制军侍尧曾图其形,上之内府。”⑧曹春林:《滇南杂志》卷13,嘉庆十五年刊本.李侍尧绘图显然是呈送君王,是揣摩迎合圣意,更有向君王传递边疆盛世的讯息。史学界认为,历史上虽有“康乾盛世”之说,但云南是在经历了三藩之乱、改土归流,到乾隆朝才有了盛世的景象。因此,乾隆朝,吟咏古梅与歌咏太平就自然而然发生了。李侍尧之后,继任督抚借古梅渲染太平气象之意明显。巡抚刘秉恬眼见“潭里千鱼跃”,发出“梅亦舍知识,争开润太平”的感慨。①刘秉恬:《乙巳封印后一日诣黑龙潭赏梅诗》,见《云南林业文化碑刻》,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谭尚忠《游龙泉观梅花记》描绘如欧阳修《醉翁亭记》般的与民同乐,当时在滇官员多有跋语,如汪如洋认为:“读此文数过,觉乐岁桑麻宛然在目。”同游者王昶则说:“偕总督富公暨诸僚佐谈笑于樽俎间,以写其与民同乐之意,而岂适其游观哉?犹忆乾隆辛卯二月,昶以从军在昆明,时春日不雨,明公德步祷于潭,故昶有‘会须鞭蜿蜒,为我播优渥’之语。今土膏将动,岁稔而时和,风日恬熙,鱼鸟咸若,古梅连蜷盘屈,咸得迎春以出,资气以华,盖昌时之风景,而郅洽之休徵也。”②谭尚忠:《纫芳斋文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0页。对比17年前从军滇南时所见古梅的情景,他不得不赞美眼前这太平昌和的盛世景象。杨有涵跋语中认为古梅可见“政通人和,雨旸时若,动植怿茂”。因此,官员群体都认为古梅发出了丰岁治世的信息,或者就是一种盛世象征符号。当然,古梅与盛世的联想,也可以起到美化督抚官员政绩的作用,上述题跋即有此意。吴嵩梁《题顾南雅画黑龙潭唐梅为望坡尚书作》称:“尚书昔秉中丞节,岁丰民和政无阙。悬知此树即甘棠,争看穿花飞彩蝶。”③吴嵩梁:《香苏山馆古体诗钞》卷14,清道光间刻本。也有借唐梅颂政绩的意味。而且,乾嘉时期,有从古梅到唐梅的称呼变化过程。程杰认为,唐梅之称,是因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是汉民族中央政权与云南少数民族部落政权以一种羁縻关系实施有效统治,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形成国家政权与民族关系的历史典范。④程杰:《论昆明黑龙潭唐梅的历史景象和文化意义》,《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3年增刊第1期。此说极有见地,这也符合乾隆帝的盛世期许。
那么督抚官员怎样用唐梅塑造边疆的盛世景象,或者说唐梅吻合了哪些盛世的因素呢?
唐梅的适时而开、馨香无比暗合了边疆涵濡教化、风俗丕变、文教大开、民族融合的盛世之义。有一则材料值得拈出,是在滇做官、后因铜事罢官的檀萃《滇海虞衡志》中的一段话,称“昔人谓滇花无香,余不禁为花白其诬,岂昔之花无香,而今之花有香,亦沾濡于大圣人明德之馨香欤!”⑤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1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8页。其语带讥讽,却一针见血指出当时统治阶层有意借花香渲染滇南儒家教化的成效。在多数官员们看来,唐梅“迎春以出,资气以华”,正是濡染朝廷儒家教化的结果。谭尚忠文章中记总督富方厓之语,“芳馨袭袭,与余辈气味相投”,⑥谭尚忠:《游龙泉观观梅花记》,见柯愈春编纂《说海》第7册,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2228页。这芳馨正是儒者所推崇的清芬之气。而记中“居民闻,争持短炬照行者,如奉其父母,不知其为官长也”,一派官民熙洽之景。而对比清初督抚官员之于云南的印象——“滇省汉土交错,最称难治”⑦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25页。,至乾隆朝,民风变化何其迅速,这不都是圣朝儒教之功?!文教大开方面。滇南于乾嘉时期,的确人才辈出,这与历代督抚、学使重视边疆儒学教育分不开。⑧廖国强:《清代云南儒学的兴盛与儒家文化圈的拓展》,《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乾隆中后期,汉族钱沣、白族谷际岐、白族师范、白族王崧、回族沙琛、汉族袁文揆等皆一时翘楚。袁文揆《滇南诗文略》的编撰集人文之盛。时任巡抚初彭龄序中称滇士“沐浴咏歌……岂非圣泽涵濡风会日趋于上之验哉?”并认为“由是而涵濡乎朝廷道德之泽、礼乐之化”。⑨袁文揆:《滇南诗略》,《丛书集成续编》第150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45-46页。嘉庆朝也不逊色,尤其学使顾莼注重五华书院弟子的培养,“忆昔莅南中,文教谁比烈”,其成就人才甚众,著名者有“五华五子”。当时昆明诗坛无比繁荣,且汉族、白族、回族、彝族文人聚集,形成多民族文人交融的格局。
唐梅的贞骨还暗合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的坚定信念。嘉庆初昆明诗人钱允济《龙泉古梅歌》描绘古梅姿态,云:“五老峰前泉清泠,龙气嘘云云冥冥。云中老梅撑纵横,双珠蟠结苍龙形。一株偃蹇呼不起,欲逐潭龙卧潭水。一株夭矫势凌厉,更恐飞入苍冥里。萧瑟古傲各尽态,若木四照差可拟。山灵呵护延灵根,万片丹霞照赤鲤。花气氤氲彩云乡,仙人来下灵为房。”①钱允济:《触怀吟》卷上《龙泉古梅歌》,见《丛书集成续编》第136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684页。诗中“天边魑魅那能窥,昆明劫火烧不死”,言语铿铮,凸显唐梅之傲骨,自有局势稳定不可动摇的力量,而诗歌末尾“收拾余香畀晴昊”,更有晴空万里的盛世清明之感。其后,道光朝总督阮元作《访黑龙潭看唐梅二律》,这是咏黑龙潭唐梅最著名的诗篇,流露边疆稳定的含义。其一云:“千岁梅花千尺潭,春风先到彩云南。香吹蒙凤龟兹迪,影伴天龙石佛龛。玉斧曾遭图外划,骊珠常向水中探。只嗟李杜无题句,不与逋仙季迪谈。”其二云:“铁石心肠宋开府,玉冰魂魄古梅花。边功自坏鲜于手,仙树遂归南诏家。今日太平多雨露,当年万里隔烟霞。老龙如见三沧海,试与香林较岁华。”②阮元:《研经室续集》卷8,《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06页。二律赞美古梅的冰姿,感叹古梅的遭遇。诗中的春风一句或许受到钱允济的影响,已然有朝廷文治武功的教化含义在。阮元任云贵总督十年,正是边疆云南局势动荡时期,深谙汉学的他,借助老梅的沧桑变迁,从维护清王朝的角度出发,发出了国家安定统一的深意和美好的愿望。这与他推举《爨龙颜碑》,“从碑文‘向义中州’的精神内涵寻绎儒家精神,去解决边疆诸多矛盾、维系边疆和谐”③参考饶峻妮、许云和《〈爨龙颜碑〉由隐而显的历史过程考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3期。,可以说是同位的思考。
滇南文士对边疆盛世的认同也始于乾嘉时朝。嘉庆初石屏诗人罗觐恩歌咏唐梅“独抱冰心卧榛莽,不受六诏烟尘汙……彩云既烂始出见,压倒孤山三百株。”④昆明市政公所:《民国昆明市志》,1924年,第354页。他认为唐梅是在彩云烂漫的盛世当下才会如此绽放。《滇南诗文略》的编纂,袁氏兄弟正是有感于“滇人士沐浴咏歌、涵濡国家教泽百六十年”的“一道同风之盛”。⑤两句分别见袁文典、袁文揆《滇南文略序》,《丛书集成续编》第15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3页,第7页。这也代表了当时滇南文士的普遍认识。而对比此前数十年,诗人孙髯翁《大观楼长联》“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的句子,对清朝政权充满了嘲讽的意味。说明时过境迁,边疆治理日渐成效,滇南文士已从心底认同边疆盛世景象。
而从道咸之际唐梅枯陨,时人的寄托,更能反衬那份盛世的情怀。唐梅随势运而衰。道光二十九年(1849),云贵总督林则徐《咏唐梅》诗注称:“黑龙潭有唐梅二株,嘉庆乙卯余使滇中尚见之一,一株已枯,而旁出小茎,引一大株,犹根蟠郁之盛,今此株亦只剩枯根尺许,为之慨然。”联系他三十年前任云南乡试考官时所见,发出了“老梅认取陈根在,卅载鸿泥一梦中”⑥张一鸣:《林则徐在昆明遗闻轶事三题》,《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昆明:昆明市政协文史委,2010年,第147页。的世事沧桑感。到了咸丰二年(1852),云贵总督吴振棫《龙泉观看梅花》诗注称:“唐梅传为开元时物,今已枯折矣。”⑦吴振棫:《花宜馆诗钞》卷15,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其《东风第一枝》词序称:“黑龙潭唐梅闻三十年前尚存,今枯根亦仆矣。甲寅上九命侣往游,惟野梅数十枝,烂若晴雪而已。”咸丰十年(1860),在滇官员吴仰贤仍有《唐梅》,诗云:“广平昔作梅花赋,开元宰相饶风度。掷笔一去千余年,唐代梅花开如故。一株旧落天南陲,苍茫甲子不可知。翠羽翔空发古艳,老蛟露脊无丑枝。花落花开几弹指,蒙颠段踬空尔为。君不见黄台瓜摘台亦圮,沉香亭北牡丹死。唯有此梅岁岁开,山人白衣尚姓李。”①吴仰贤:《小匏庵诗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8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吴仰贤是咸丰二年(1852)进士,咸丰五年(1855)任浪穹知县,屡徙昆明等地。他所见应该不是先前唐梅主干,而是孙枝。②朱庭珍《宋柏行》云“唐梅变化去已久,只有此柏堪代兴”,说明古梅已死。时间可以肯定是在道光朝后期。程杰认为“龙泉古梅主干便已枯死,而其他野梅和古梅孙枝渐次长成,观中梅花转入新一轮的景象。”从“花落花开几弹指,蒙颠段踬空尔为”来看,多少受阮元诗旨影响。当时“咸丰六年丙辰滇乱作,阅十有八载而难始平”,③罗瑞图:《滇南诗略序》,见《丛书集成续编》第150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35页。面对边疆兵乱,作为封建统治阶层一员的诗人对于国家的稳定仍抱有必胜的信念。滇南文士吟咏唐梅也依然延续。晋宁进士何彤云《黑龙潭古梅歌》称:“呜呼!和羹自古须此材,蒟酱乃使西南开。金马去已久,碧鸡不再来。余此一树好枝格,不知几生始修得。莫更踊跃变化入潭中,使我华山昆水无颜色。”④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145,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63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48页。他深处内忧外患的衰世,只有一种家乡安好的祈盼。著名诗人石屏朱庭珍有6 首咏唐梅之作。其《唐梅行》,既赞美梅的雄姿,又爱其仙姿。作为诗人,他更爱梅所蕴含的盛唐之气格,此中或许也有对大唐盛世的美好向往在。其《补唐梅歌》云“孤立自可奴群芳,底用儿孙冒初祖。后来居上世岂无,漫道今人不如古。”⑤朱庭珍:《穆青堂诗钞》卷中,见《丛书集成续编》第137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521页。补唐梅是在主干死后,其余孙枝替补。他字里行间寄寓后来居上之意,但也只能是个人的强作慰藉,徒生希冀而已。
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认为,乾嘉一直到道咸年间,云南诗坛的唐梅书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样一种书写不要平常略过,不能简单目之为文人的风雅爱好。督抚官员、文人的书写传播,不但确立了唐梅作为自然景点的存在,也催生了唐梅的文学文化景观现象。在这些书写中,由于作者身份不同,流露的情感有所不同,但也出现了借助唐梅寄托霖雨期盼、丰收雨润的思想倾向。从李侍尧、谭尚忠到阮元,唐梅被督抚官员用来塑造盛世太平的符号意识日益明显,且逐渐强化、深入人心。滇南士子也在乾嘉时期产生了边疆盛世的自觉认同感。可以说,唐梅见证了边疆云南时局的兴衰,百余年的唐梅书写,既呈现了清代云南文教、民族风俗的发展变化,也充分反映了边疆文学的繁荣。所以,区区两株唐梅,看似其小,却有见大的价值和意义,值得关注和研究。晚晴民国,关于黑龙潭唐梅的吟咏仍延续着,林槐、张鼎、杨恩第、尹叶蕃等滇南文士仍有咏唐梅之作,⑥林槐《龙泉观唐梅歌》、张鼎《唐梅》、《玉照堂壁刻唐梅图歌》、杨恩第《玉照堂壁刻唐梅图歌》、尹叶蕃《唐梅》均见《滇诗丛录》。云南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有《龙泉观唐梅赋》和数首咏唐梅诗,有桑梓情深,也有岁月无情之慨。他们相对道咸的唐梅书写,更只能是一种“盛世”的遥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