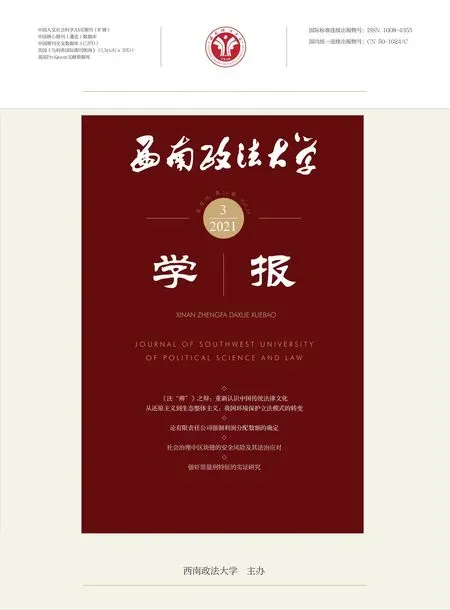破产管理人对待履行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的选择权
2021-11-21陈选
陈 选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401120)
商标许可使用在当今经济社会中是十分常见的商业模式。许可双方当事人借这一模式“各取所需”,商标权人通过被许可人的商标使用,实现收取许可费用、扩大经营范围、提升商标知名度等目的,被许可人借助他人已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完成快速进入市场,实现资本积累等计划。许可过程中商标资源的优化又会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如商标影响力增大对产品品质的反向促进为消费者对商标的信赖利益提供了保障。然而商标许可使用过程中会遇到诸多不确定因素,譬如商标权人多重许可引发使用权冲突,被许可人实施商标权疏于品质控制等,都将可能影响商标许可的顺利开展。除此之外,许可合同本身的法律效力稳定性也是另一影响商标许可进程的关键。本文将视线放在破产程序中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的处理上,破产管理人对待履行商标许可合同的选择权行使不仅涉及破产程序的整体推进,更关乎商标许可双方当事人利益实现以及相关公共利益维护等问题。商标作为知识产权具有区别于一般破产财产的特殊性,因此商标许可使用合同面对破产管理人选择权,尤其是解除权的“待遇”是否应同其他合同一样,或者是否应考虑作出合理调整,以在实现多方利益平衡的基础上更注重发挥知识产权价值的问题(1)王华:《论破产程序中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处理——以管理人为主要视角》,载《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64页。,有必要加以探讨。
一、破产程序中的待履行商标许可使用合同
(一)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的界定
“待履行合同”源自1978年《美国破产法》第365条中的“executory contract”一词,可作破产申请受理前已成立但尚未履行完结的合同之理解。学理上通常借此来概括本国破产法赋予破产管理人或债务人选择权的合同。有关这类合同的认定,美国破产立法中并未给出明确标准,且实务中也未有统一结论。法院判定时通常采用的是“实质违约”标准或叫康特利曼测试(Countryman Test)(2)Countryman Vern,Executory Contracts in Bankruptcy:Part I,57 Minnesota Law Review 439,460 (1973).,认为双方当事人均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并且任意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行为均会构成实质违约时,才符合未履行合同的要求。除此标准以外,有时法官还会站在“结果导向”的角度作出判断,例如把判定相关合同为“待履行”是否有利于破产财产这一结果作为标准进行考量(3)See In re Riodizio,Inc.,204B.R.417,424 (1997).,又如成本——收益分析:根据管理人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来确定是否属待履行合同,而非首先对“待履行”设置标准。(4)Jay L.Westbrook,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Executory Contract,74 Minnesota Law Review 227,281(1989).总之,有关该类合同的认定标准多样且暂时未实现统一,不过无论采何种标准,法院在实务中最终都需根据具体案情,综合分析得出涉案合同是否属“待履行”之结论。
我国《破产法》将待履行合同阐述为“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5)《破产法》第18条。”。该定义把由管理人决定合同状态的合同限定在双方当事人都未履行完毕的双务合同范围内。之所以作此限制,原因是破产程序开始后此类合同的处理若依破产债权、债务人财产的一般规定进行,极易出现以下情形:管理人提出合同相对方继续履行合同的要求时,相对方依《合同法》第66条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这一“自救措施”;合同相对人要求管理人代为继续履行时,管理人又以《破产法》第16条有关破产程序中禁止向个别债权人清偿的规定为由拒绝履行。即便合同相对方依约定需承担先履行义务,其也可因破产债务人申请破产而主张自己行使《合同法》第68条赋予的不安抗辩权。换言之,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双务合同容易随着一方申请破产陷入“胶着状态”。考虑到破产程序为集体清偿程序,合同相对人的未履行给付可作为债务人财产,因此这种合同在破产进程中不宜搁置(6)刘颖:《反思〈破产法〉对合同的处理》,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3期,第53页。,赋予管理人决定权是更具效率的做法。另外,虽然该定义较笼统,但可以认为其同康特利曼测试的本质是一致的——以合同自身为出发点考量其定性。笔者认为这种判断方式相比于从结果反推的认定模式更具合理性,理由在于合同定性与处理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合同履行结果对破产进程的推进效果,或是履行与否将形成的利益对比等问题应属于管理人所应考量的因素,而非对合同定性进行反推的理由。至于如何判断合同是否“未履行完毕”,我国立法亦未给出明确标准,事实上因现实案情多样且复杂,统一标准的提出也具有较大难度,美国法院视个案实际考虑经济实质来判定的做法是具有参考意义的。
(二)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的“待履行”之判断
根据我国破产法中待履行合同的定义,商标许可使用合同首先就合同类别上来说自是未被排除其外,因此“待履行”判断的关键就在于许可双方义务均未履行完毕这一点。商标许可使用关系中,许可方的主给付义务在于发放授权使用书,而被许可方的主给付义务在于支付相应时期内的使用费。除此以外,当事人还负有诸如质量监督、信息披露等从给付义务。在判断是否为待履行合同时,考察对象为主给付义务还是从给付义务的履行,本文认为并非是绝对的。详细地说,主给付义务的履行对于合同实际违约似乎更易产生实质影响,因其决定了债之关系的类型,而从给付义务的影响多体现于对主给付义务的补助,以确保债权人利益获得最大满足。(7)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但是,由于现实中具体案情的复杂性,有时候从给付义务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也同样会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结局。例如,商标许可人的质量监督义务在商标许可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商标权人质量监督不力导致被许可人贴附许可商标之产品的品质无法达到商标权人自身商品一致水准,这一情况涉及到误导、欺诈消费者等直接撼动商标许可合法性的问题,因而该义务的持续履行要求往往就会令商标许可合同认定“待履行”成立。(8)Amanda E.James,Rejection Hurts:Trademark Licenses and the Bankruptcy Code,73 Vanderbilt Law Review 889,896 (2020).故在分析具体案情前,很难明确依何种义务的履行作为判定标准才是合理准确的。
曾有美国法院提到,因为被许可人业已履行的义务超过了未履行义务,使合同双方实质上受益,达到了“总体上已履行”的程度,所以终止合同并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该合同也因此并非待履行合同。(9)See In re Exide Techs.,607 F.3d 957,963 (3d Cir.2010)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我国判断特定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待履行”与否的实务中同样具有适用价值,根据不同义务的履行情况,对许可合同产生的总体效果及对方当事人获益产生的实际作用来综合判定,而非固守以某一特定义务的履行情况作为考察对象是更为恰当的。
二、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处理的一般规则:管理人实施单方选择权
待履行合同种类多、范围广,各国破产立法对此类合同的处理通常采用一般规则与特殊合同类型例外规定相结合的方式。而所谓一般规则,即是赋予破产管理人决定合同状态是继续履行或解除(例如美国《破产法典》中称为“拒绝履行”)的积极与消极两种选择之权利。如美国《破产法典》第365条(a)、德国《破产法》第103条、日本《破产法》第53条均体现了这一规则。我国《破产法》第18条亦作此规定,依该条文,管理人在对待履行合同的状态进行选择时仅受制于一些偏向程序性的要求,例如其作决定及通知必须符合一定时限规定,选择继续履行合同时必须提供担保(10)《破产法》第18条。,行使选择权向债权人委员会或在未设立债权人委员会时向法院报告等。(11)《破产法》第69条。选择权本身并不存在明确实施标准上的限制。与此相对,相对方对合同状态经管理人决定后的结果除接受外并无选择权,这一方享有的保障仅体现在对管理人作出决定可实施催告权以及在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时要求其提供担保的权利上。显而易见,现有规则下的合同相对方、破产财团两端,利益天平明显往后者一方倾斜。
赋予管理人单方选择权这一特别权利的首要目的以及制度价值在于实现破产财产利益最大化,进而最大程度保护一般债权人的整体利益(12)李永军:《论破产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限制》,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74页。,其依据的逻辑基点是团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具体来看,管理人的积极选项即继续履行合同目的,在于突破破产法禁止向个别债权人清偿的规则,从而使特定合同状态免受合同相对人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与不安抗辩权所导致的“胶着状态”,将合同相对人的给付收归破产债务人财产;其消极选项即解除合同目的在于突破“合同法”规则使债务人财产摆脱对自身增值或保值不利的负担过大的合同。(13)刘颖:《反思〈破产法〉对合同的处理》,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3期,第54-55页。因此,无论作出何种选择,都是以最大程度扩充或保留破产财产作为首要目标。这反过来又为管理人选择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衡量视角,若合同继续履行对破产财产而言是一个好的“交易”,那么继续履行之决定会为债权人会议或法院所支持,反之若解除合同使债务人免于义务履行相比于继续履行而言对其财产更有益,则解除是更佳选项,这一衡量的标准被称作“商业判断测试”(business judgment test)。(14)Amanda E.James,supra note ①,at 896-897.
此外,这一规则从效率的角度看对破产进程的推进是有益的。破产程序的推进及终结直接影响债权人利益清偿,债务人主体消灭,破产费用支付及破产案件审结等诸多方面的结果,因此必须是有效率的。若没有管理人的单方选择权,破产程序中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双务合同很容易陷入“胶着状态”。破产立法中在赋予管理人选择权的基础上,又对这一权利的行使期限提出了要求,如我国《破产法》第18条规定了管理人的通知期限,同时为对方当事人设置了催告权。这进一步使得破产管理人选择的作出是及时而不拖沓的,避免了选择结果悬而未决,令合同状态长期不确定,使合同相对方无所适从之局面。
必须注意的是适用这种建立在团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逻辑之上,以追求破产财团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一般规则时,也有必要考虑到利益的平衡问题。一方主体的合同利益会随着另一方进入破产程序而充满不确定性,“合同相对人是完全得到合同利益还是只能获得债权分配的利益,依赖于破产管理人的选择,此时会产生幸运的合同相对人,也会产生相对不幸的合同当事人。”(15)丁文联:《破产程序中的政策目标与利益平衡》,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以商标许可使用关系为例,如申请破产的是商标权人,则商标可能被归于破产财产,被许可人就此丧失商标使用权;若进入破产程序的是被许可方,商标权人则或将失去许可使用费这项收益。要实现破产财产最大化,通常就意味着相对方的利益需要适当程度的退让,此时这种程度的把控就十分关键。从公平的角度看,利益失衡的局面若达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管理人的选择权结果就是值得质疑的。(16)李永军:《论破产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限制》,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77页。此处所谓“难以接受”可理解为在利益平衡检验中,相对方因合同解除承担的损失显著不成比例地高于破产财产的获利,造成了明显不公平的局面。(17)许德风:《论破产中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载《法学家》2009年第6期,第97页。举例来说,管理人解除合同的决定将彻底破坏相对方继续经营的基础,与此同时带给破产财团的利益却是微不足道的,这项拒绝决定就显得合理性不足。(18)韩长印:《破产宣告对未履行合同的效力初探》,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3期,第52页。
三、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处理的特殊规则:管理人解除权受限
在处理待履行合同的一般规则之外,考虑到某些合同类型的特殊性,其他法律所依据的前提及目的等因素,也有必要设定例外情形,对管理人的解除权设置合理的行使条件。
(一)域外破产管理人待履行合同解除权受限的相关规定
1.针对知识产权许可合同实施解除权受限
域外破产立法中已有针对待履行知识产权许可合同解除限制的规定,以日本与美国“破产法”为例,《日本破产法》第56条指出,“就设定租赁权以及其他以使用、收益为目的的权利的合同中,破产人的对方当事人具备就该权利进行登记、注册以及可以对抗第三人的要件的情况,不适用该法第53条有关待履行合同选择权的一般规定。”可见,知识产权许可使用关系中,破产债务人的合同相对方若具备登记对抗要件,则其许可相关权益不受管理人解除权之影响。
美国《破产法典》在1988年增加了第365(n)条之规定:知识产权许可合同的许可方进入破产程序时,破产管理人可作出拒绝该合同继续履行的选择,此时,被许可方也同样具有选择权,一是接受此拒绝履行的决定,将该契约视为解除或终止,二是许可期满前继续保留知识产权实施权。该规定不同于日本将相关合同直接排除在管理人选择权之外的做法,赋予了破产相对方“复选权”,即便在管理人拒绝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如被许可人愿意,依然可继续实施知识产权。该制度首先符合破产法有关破产财产增值与保值的目标,因债务人可继续获得许可使用费这项收益用于破产债务偿还,其次也消除了被许可人在知识产权权利人破产时需要面临停止实施知识产权的“糟糕境遇”的忧虑,(19)Jarrod N.Cone,A Sunbeam of Hope:The Seventh Circuit’s Solution Overcoming Disparaging Treatment to Trademark Licensees under the Bankruptcy Code,20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347,361 (2013).进而避免由此可能对知识产权发展与许可产生的“致冷效应”(chilling effect)(20)Alexander N.Kreisman,Calling All Supreme Court Justices! It Might Be Time to Settle This “Rejection” Business Once and For All:A Look at Sunbeam Products v.Chicago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the Resulting Circuit Split,8 Seventh Circuit Review 36,46 (2012).,因而益处十分明显。不过,依该法第101(35A)条,不同于商业秘密、专利、版权、植物新品种等,商标权并不属于美国破产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因此商标被许可人也就暂时无法适用实施权保留机制,其是否可以继续实施商标权就留给破产法院来决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商标许可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品质控制这一密切关联。(21)James M.Wilton & Andrew G.Devore,Trademark Licensing in the Shadow of Bankruptcy,68 The Business Lawyer 739,757 (2013).具言之,商标并非发明创造,它只是来源与质量的识别。商标保护不同于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其根植于标识与消费大众的联系中。只要商标作为具有区别性的来源指示在使用,且该使用该商标的产品品质受到控制,商标就是值得保护的。(22)Clayton A.Smith,It’s Not You,It’s Us: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rademark Goodwill to Properly Balance the Results of Trademark License Rejection,35 Emory Bankruptcy Developments Journal 267,274-275 (2019).因此,商标许可使用获得合法性的关键在于商标权人对被许可人提供的贴附许可商标的产品品质实施监督。商标权人进入破产程序将使其履行质量监督义务的能力削弱,单独保留被许可人商标使用可能造成无法保证商品品质,误导消费者之后果。况且商标权人质量监督义务的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还将令其构成商标“裸许可”(naked licensing),面临商标权被剥夺的局面。(23)Dawn Donut Co.v.Hart’s Food Stores,Inc.,267 F.2d 358,367 (2d Cir.1959)因而割裂这一联系后单独保留被许可人的商标使用权将引发对商标许可合法性的质疑。但是,这种将商标排除在破产程序实施权保留机制外的做法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中均出现了商标被许可人也应享有这一权利的声音,其典型为2012年作出判决的Sunbeam一案,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认为“破产法第365(g)条的拒绝履行应属违约,因此非违约一方的权利应获得保留。”(24)Sunbeam Prods.,Inc.v.Chi.Am.Mfg.,LLC,686 F.3d 372,377 (7th Cir.2012)换言之,破产程序中未违约的商标被许可人通过合同获得的许可权利,并不因相对方的违约行为而消除,这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该案随后被诸多学者、评论家及律所评论为“商标被许可人的一束阳光”,修改《破产法典》相关条文的观点也愈发普遍。实践中类似的例如In re Exide Technologies案等,认为剥夺被许可人继续使用商标的权利具有不公正性,因此法院应运用其衡平法权力使商标许可获得保护的判决也有出现。(25)See In re Exide Techs.,607 F.3d 957,967-968 (3d Cir.2010)
2.针对不动产租赁合同实施解除权受限
以美国、英国、德国与日本破产程序中不动产租赁合同的处理为例,多国在破产程序中对不动产租赁关系中的承租方多给予了倾斜性保护。美国《破产法典》第365(h)条提出,不动产出租人在破产时,管理人可选择拒绝租约,但这种拒绝受到限制,承租方有选择是否继续占有、使用的权利,在其并非自愿决定搬离时,出租人不得收回不动产。不过如承租方选择继续租用,则出租方依原合同所应负担的义务将获免除。英国《破产法》第179条规定,除非发出放弃通知后14日内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或法院裁定生效,否则破产清算人对租赁合同所作放弃之决定无效。前文中曾提及的《日本破产法》第56条对租赁合同在此方面也给予了特殊待遇:有关待履行合同解除的一般规则不适用于租赁合同。《德国支付不能法》对此问题则设计了区分承租人、出租人破产的详细规则,该法第112条规定,承租人破产时,如破产程序开始时租赁物尚未交付,管理人和合同相对方均有权终止合同,如破产程序开始时租赁物业已交付,出租方不得以承租人欠租金或财产状况恶化为由终止合同;该法第108条第1款规定出租人破产时,租赁关系应以对破产财产有效力的方式延续。可见尽管实际规则各自有别,但本质上这些国家的“破产法”对管理人针对待履行租赁合同的解除权均设置了限制,租赁关系获得了更强保护。
商标许可使用合同与不动产租赁合同具有诸多相似性,例如使用者权利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准物权性质,合同目的实现均需依赖继续性履行,两类合同都体现出浓厚的社会性色彩,合同关系的存续对社会主体的生活与生产的根本“生存”利益直接相关,以及合同双方当事人地位通常呈现出出租方强于承租方的对比等。基于此,上述几国破产立法对管理人针对不动产租赁关系的单方拒绝权或解除权加以限制的模式,对我国管理人选择权在商标许可使用合同方面的规则完善也具有参考价值。
当然除上述两类特殊类型合同外,他国立法中也有如“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等其他特殊待履行合同之规定,囿于文章篇幅且考虑到对我国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在破产程序中的处理规则的直接借鉴价值,本文暂时仅就上述两类特殊待履行合同加以举例与阐释。
(二)我国关于限制管理人待履行合同解除权的规定
我国现行立法中,仅有《保险法》对人寿保险合同在破产程序中免于破产管理人选择明确作出陈述:“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或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及责任准备金,必须转让给其他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能同其他保险公司达成转让协议的,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接受转让。”(26)《保险法》第92条。该规定的作出主要出于此类合同的社会保障性质,并且由于投保人数量巨大,如管理人可单方解除人寿保险合同,则受波及公众利益范围过广,甚至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27)兰晓为:《破产法上的待履行合同研究》,武汉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2页。
因此,在我国,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并无法适用待履行合同处理的特殊规则,这类合同在破产程序中仅可“享受”由管理人决定合同状态的一般“待遇”。
四、对破产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加以限制的必要性
(一)解除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对破产财产增值或保值的不确定性
管理人实施选择权的首要原则就在于破产财产利益最大化。破产程序中由管理人解除合同这一不以合同相对方违约为解除合同前提的情况在合理性上是遭受质疑的。具言之,通常的观点是当一方主体拒绝履行合同时,仅由非违约一方享有法定解除权,即合同的法定解除是非违约方的救济方式。管理人因自己一方违约却享有法定解除权,显然于上述通常原则不相符。(28)张尧:《破产管理人选择权行使规则之解释论》,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70-71页。且从解除合同效果看,管理人解除合同将消灭自己一方的给付义务,该解除权也将违反禁止矛盾行为之原则——因一方当事人之行为致使另一方给付不能,他须为给付不能这一后果承担责任,而非得到权利。(29)庄加园,段磊:《待履行合同解除权之反思》,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5期,第131页。而之所以法律会肯允这一规则存在,目的就在于以牺牲少数主体即合同相对人的利益来换取多数主体即破产债权人利益的保全,并且帮助破产方实现重整,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一个具有效益的局面。因此,如若解除合同的增加或保全破产财产的前提不在了,则实施这一“不公平”解除权的理由也便一同消失了。(30)兰晓为:《破产法上的待履行合同研究》,武汉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0页。商标许可关系中,双方当事人都有申请破产的可能,所以在分析合同解除对破产财产的影响时,也有必要区分情形展开。
当进入破产程序的是商标权人且管理人选择解除合同时,则商标权人即破产债务人对商标享有的所有权不会发生任何变动,可与此同时,商标实施权收回将使得获得稳定的许可使用费这一项收益渠道就此切断。与之相对,如保留这一许可关系,这一部分财产得以继续稳定增加,商标价值得以继续发挥甚至增值,同时商标权人即破产债务人履行许可合同又不至明显增加债务。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的解除于增加破产财产是不利的。当被许可人进入破产程序且管理人选择解除合同时,破产债务人即被许可方将终止商标实施权,其与该商标有关的经营业务随即停止。最直观地看,由于其申请破产说明其整体资产、经营状况不佳,因此终止商标使用对其财产来说可能是一种“及时止损”即保值的做法。但若换个角度,许可使用权的存在意味着这一条变现途径的存在,这对于其恢复经营、增加财产也可能是有益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解除合同也并非绝对地有助于破产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
综合以上两种情形,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的解除对于破产财产并非绝对有利,更何况,管理人在现实中本身也存在判断失误之可能,选择继续履行的是对破产财产不利的合同,摆脱的却是有利的合同。(31)参见庄加园、段磊:《待履行合同解除权之反思》,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5期,第132页。当出现财产减损的消极影响时,待履行合同解除以牺牲小部分主体利益来成就总体效益的大前提就不具备了,从这个角度看,管理人选择权的行使也应有所规制。
(二)管理人解除商标许可合同存在的公共利益受损可能性
公共秩序稳定,社会公益得到保障是一切社会关系正常维系,社会活动正常开展的前提。当发生私人、公共利益的冲突时,后者必须优先获得保障。若破产程序中,管理人针对待履行合同实施解除权可能会损害公共利益,而合同的存续又为社会公益所必需时,针对此合同的解除权就应受限。(32)丁文联:《破产程序中的政策目标与利益平衡》,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
商标权同公共利益密切关联。商标法上的公共利益指同商标权之取得、运行密切关联的不特定多数人所享有的普遍性的利益,它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商标法中公共利益在最高层级的体现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商标法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脱胎而出,维护公平竞争为商标立法的根本宗旨所在。(33)张玉敏:《维护公平竞争是商标法的根本宗旨》,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2期第23卷。商标法律制度中包括遏制商标抢注、打击“假冒”与“反向假冒”、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等内容均体现出了这一宗旨。其次,商标注册与权利限制的内容也体现出对商标权人的竞争者,以及不具竞争关系第三人享受商标的“符号利益”的保护,这也是具有高度公益色彩的一个面向。最后,商标法上公共利益当然还包括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利益。这一方面可陈述为,商标通过发挥其识别功能,使消费者建立一定认牌购物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对商品或服务的品质形成反向激励,进一步增进消费者福祉。(34)黄汇:《商标法中的公共利益及其保护——以“微信”商标案为对象的逻辑分析与法理展开》,载《法学》2015年第10期,第76-77页。
在明确了商标法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内容后,即需对破产管理人解除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对这些利益的影响加以评估,若可能造成损害,则其在这方面的解除权就有受限之必要。首先管理人解除合同最直观的影响体现在对稳定市场秩序的破坏上。非破产债务人一方的合同当事人在进入商标许可使用程序时都基于合同对约定期限内许可关系稳定存续这一状态具备心理预期。也正是基于这种心理预期,其会为商标许可使用的开展给予投入。而管理人的单方解除权显然会破坏这种预期,成为埋在许可交易中的一颗“炸弹”,对商事主体进入许可市场构成阻却,不利于商标许可交易的发展。此外,商标许可使用关系终止所影响的商事主体也不止于许可当事人,关联主体例如上游或下游供应商、经销商等利益都将遭受波及,最终对于相关市场的原有秩序亦可能造成破坏。事实上,正因为商标许可使用牵涉交易秩序的维护这一公共利益保护问题,商标法律制度中设置了诸如“转让不破许可”(3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等侧重对许可关系加以保护的规则。(36)张扬欢:《论知识产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载《电子知识产权》2019年第10期,第43-44页。在破产程序外,如存在对某一合同关系不可解除的规则,则在破产程序中要赋予管理人对这类合同的解除权,就须论证破产程序中解除合同的所要实现的目标重要性高于相关立法中的保护合同关系所要追求的目标,否则后者就应受到尊重。显然此处许可关系的存续对市场秩序维护的重要性应是高于破产财团利益的,因而此时赋予管理人解除权无法获得有效论证。
除此方面外,不特定消费者利益受损是另一显著不利影响。首先,若被许可人通过长期使用对商标价值作出了重要贡献,以至于在消费者眼里被许可人就是特定产品的提供者,则管理人对许可合同的解除就将让这种认知产生偏差。其次更重要的是消费者针对特定产品最基础的消费动力来源于其性能或品质上的优良特征,尽管当前随着商标财产属性的增强,商标自身逐渐成为消费的对象,但产品基本属性依旧是绝大多数购物消费的目标。这种基本属性的生成与产品直接提供者的关系最为紧密。商标许可使用中,产品直接提供方同商标权人并不统一,消费者对特定产品的喜爱,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对特定商标、品牌的依赖,实际上来自于对特定产品直接提供者的依赖。据此,若商标权人申请破产后,破产管理人单方解除商标许可关系,被许可方即产品直接提供者的商标使用权就此终止,对消费者而言“认牌购物”的基础便不复存在了。哪怕后期相关产品更换生产者,通过质量监督措施可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品质水平的一致,但消费者的信赖基础已经受到动摇,更不用说在一些品质高度依赖生产者技艺的领域例如食品制作,生产者的更换将直接导致产品质量稳定性下降,消费者不得已作出购物行为调整等一系列后果。换言之商标所指征的产品将不再是其曾经为消费者认可的那个产品。(37)Clayton A.Smith,It’s Not You,It’s Us: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rademark Goodwill to Properly Balance the Results of Trademark License Rejection,35 Emory Bankruptcy Developments Journal,267,294(2019).综上,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对管理人的单方解除权有必要设置合理限制。
(三)管理人解除合同对作为相对人的商标被许可人的不公平性
在限制管理人解除权的第一项理由中笔者曾提到过从合同法的角度看该权利的合理性是遭受质疑的,其对于非违约一方的合同相对人而言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性在商标权人申请破产,被许可人为相对人的情形中尤为显著。具体来说,由于商标的价值建立在市场主体对其进行的使用上,换言之商标这一权利是在“使用”中产生的,故而对商标“使用”的保护才是商标法价值基点与立法动因所在(38)黄汇:《注册取得商标权制度的观念重塑与制度再造》,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第188页。,让使用者从商标价值当中获益也永远是商标法的保护目标。(39)阳贤文、曹新明:《商标许可中利益分析理论探析——王老吉案之启示与回应》,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1卷第6期,第51页。我国当前商标立法中有诸多内容体现了对商标使用价值的肯定及保护。例如将导致消费者混淆作为构成商标侵权的核心要件,在“市场中”进行商标侵权判定而非仅对原被告的商标及商品进行对比,体现了对“商标生命在于使用”的正确认知。(40)黄汇:《商标使用地域性原理的理解立场及逻辑适用》,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92页。还如《商标法》第32条的以遏制非诚信“抢注”为目的的注册禁止条款,第59条第3款的在先商标所有人继续使用商标的权利,分别体现了对在先使用的消极与积极保护。(41)黄汇:《商标使用地域性原理的理解立场及逻辑适用》,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85-89页。在商标许可中,商标权人让渡了一定期限的商标使用权,在此过程中被许可人作为商标使用权的实际实施者为商标相关的经营业务展开投资与付出。因此不同于商标价值的创造者为商标注册人、商标受让人及商标继承人这三种情况下商标价值创造者同商标权人具有同一性的情况,许可中商标价值创造者与商标权人是相分离的。(42)骆福林:《论商标权人与商标价值创造者的利益关系——由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公司iPad商标案引发的思考》,载《知识产权》2012年第10期,第66页。被许可人在通过勤勉经营积累商誉从而增加商标内部价值的同时,还可能创造了一系列同商标许可相关的衍生增值利益,例如有影响力的产品包装、广告语等,使得相关品牌价值得到巨大提升。基于这样的商业现实,许可期满后商标增值利益在双方当事人间的分配等问题也随即出现,影响力极大的王老吉和加多宝商标利益纷争即是典型。而回到本文探讨的商标许可过程中许可合同状态受破产管理人解除权影响的问题,在被许可人非为破产债务人的情形中,其为开展商标使用进行了前期准备,在使用中创造了商标的增值价值,却面临着非基于自身违约的原因而被迫终止商标使用业务开展的风险。一旦破产管理人选择解除合同,为实施许可合同进行充分准备的被许可人将遭受致命打击,除了停止商标使用将产生的经济收益减损,其投入的各种生产设备、原材料及人力等损失由于在直接损失范畴外,甚至将无法被列为破产债权。(43)徐家力:《企业破产与知识产权许可研究》,载《青海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156页。因此,在破产程序中处理待履行商标许可使用合同,需要考虑到商标价值形成机制、商标法立法动因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对商标许可中的商标价值实际维护与创造者即被许可人一方的利益不能因追求破产财产利益最大化而过分忽视。
五、管理人对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实施选择权的规则完善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破产法立法指南》里指出,破产法须与其依赖并维护的法律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相辅相成。尽管破产法通常是自成一体的,但其运行的结果不得与其他法律的前提形成根本冲突。倘若破产法确实希望形成一种不同于,甚至根本性地偏离于其他法律的结果,则这种结果必须在认真考量并采取自觉政策后形成。(44)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立法指南》,第10页,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media-documents/uncitral/zh/05-80721_ebook.pdf,2021年6月10日访问。前文的分析表明破产管理人针对待履行合同的单方解除权可能与商标许可制度体现的利益保护目标相冲突,因此有必要提出二者的更优融合设想。
(一)对破产管理人选择权的实施设置原则性要求
破产管理人实施选择权需考量被许可人使用商标的情况,在综合分析合同状态对破产财团、公共利益与许可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具言之,被许可人对商标的使用情况在管理人决定过程中是十分关键的考量因素。在许可合同订立后,被许可人开展商标使用前的这一时间段内,被许可方对商标依赖性不强,同时也因未开展与许可商标相关的经营而对商标价值的实际贡献不大。管理人解除合同的决定对其造成的损失相对不会过于严重,对消费者利益与相关市场秩序的影响也同样由于许可经营未开展而几乎可以忽略。因此,此时对商标许可关系给予倾斜保护的必要性不大,由破产管理人以最利于破产财团的方式,即以破产财产最大化为目标确定合同状态即可。与此相对,在被许可人实际进行了商标使用后,商标已融入其日常生产经营中,商标价值同其使用行为密切关联,相关市场秩序及消费者信赖也就此建立。管理人此时作出的解除合同之决定对多方主体利益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商标的使用是破产管理人针对这类合同实施选择权所必须关注的。当然,被许可人使用商标的情况不简单指是否已使用商标这一点,还包括使用的时长、使用的方式、使用的效果等。具体地说,商标的核心在于其是商事主体同其消费者之间的关联的反映。(45)Clayton A.Smith,It’s Not You,It’s Us: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rademark Goodwill to Properly Balance the Results of Trademark License Rejection,35 Emory Bankruptcy Developments Journal,267,298-299 (2019).这一关联的产生并非在朝夕之间,也并非轻而易举,而必须基于一定的使用程度。被许可人履行许可合同的时间长短,获得授权的商标使用权的排他性程度以及其对许可商标的经营状况等多种因素都将最终对自身与消费者的联系,及同商标的关联程度产生影响。因此,在处理破产程序中的商标许可合同时,对这些同商标使用情况相关的因素进行考量,无论对于被许可人利益的保障还是对许可相关的公共利益的维护都是十分必要的。当然,由于商业实践的复杂性,管理人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衡量很难有固定模式或标准,其可参考诸如被许可人提供的贴附了许可商标的产品所拥有的市场份额、消费者调研数据等事实因素来作出判断。
其外,管理人作出选择需平衡各方主体的利益。当申请破产的是商标权人时,在被许可人对商标的使用情况良好的前提下,通常许可关系存续对各方主体利益均可产生有利影响:许可双方可继续获得许可收益,许可使用费及商标价值的增加对破产财产有益,许可关系存续使相关公共利益得以维护。而当商标被许可人破产时,情况相对复杂。合同的继续履行对各方主体可能都将是有益的:对被许可人即此处的债务人来说,许可合同继续履行所带来的收益可能将是其复苏的曙光(46)徐家力:《企业破产与知识产权许可研究》,载《青海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154页。;对建立在商标许可基础上的消费者信赖与市场秩序来说,其将不会面临突如其来的变动;对商标权人而言,其所享有的收取剩余期限许可使用费的权利属“因管理人或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47)《破产法》第42条。,即共益债务,可获债务人财产的随时清偿。(48)《破产法》第43条。但是,毕竟被许可方申请破产,就意味着其使用商标的能力将很大程度打折,哪怕其曾经的商标使用情况良好,也无法保证申请破产之后的实际经营状况。从这一角度看,继续履约也存在对破产财产、商标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都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况且若进入清算程序,被许可人可开展的活动也仅限于清算所需(49)《公司法》第183条。,无法满足继续经营商标的需求。因此在可能出现这些损失的情况下,仅为维护被许可人使用商标的权利而不允许管理人解除许可关系,也未免有失偏颇。故笔者认为管理人实施选择权也需做到在不同主体利益间尽可能地实现平衡,作出总体上公平与效率兼具的决定。
(二)为作为相对人的商标被许可人提供主动保留商标使用之可能
该规则具体阐述为:在商标权人申请破产的情形中,已使用商标的被许可人针对破产管理人作出的解除合同之决定有提出继续保留商标使用权至合同期满的权利,经法院批准后,方可继续实施。
首先,给予作为相对人的商标被许可人保留商标使用权的可能性具有多种合理性。第一,利于平衡许可当事人利益。商标权人破产,意味着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状态基于原许可关系中地位相对强势一方的原因产生了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合同地位稍弱一方即商标被许可人的利益受损,且或许因被许可方为规模较小或新兴的商事主体,许可相关利益会对其整体生产经营起决定性作用。停止一方与许可商标相关的经验业务,导致的利益损失又绝非仅仅体现在经济损失上,其在经销商、零售商以及消费者心中的声誉也或将随之受损(50)Darren W.Saunders,Should the U.S.Bankruptcy Code Be Amended to Protect Trademark Licensees,94 The Trademark Report 934,940 (2004).,因此这种利益影响对其而言可谓是“生存性”的。仅赋予强势方合同状态决定权会令利益失衡加剧,故同样应考虑到许可中相对弱势一方的“复选权”问题。第二,商标实际使用者即被许可人作出继续实施的决定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发挥商标价值。具体地说,商标价值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标使用人的使用意愿与积极性。在商标权人申请破产的前提下,很难说被许可人的实际使用意愿究竟如何。其或许考虑到商标权人的资产与经营状况欠佳的情况而对商标使用价值产生疑虑,其也可能认为商标状况尚可,且考虑到自身为商标使用所作的投入,暂不愿意停止商标使用。因此,如在破产管理人决定解除合同后,商标被许可人不接受这一解除决定,选择继续使用商标至许可期满,则说明其认为随后继续实施商标权是更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因此通常不会消极使用商标,这对于商标价值的继续发挥与发展是有利的。商标价值的更好发挥从大局上看对各方主体利益也都是有益的。
另外,本文认为只有在实际使用商标后,被许可人才享有这种继续保留商标使用权的“复选权”。商标价值通常与商标权人联系紧密,大多数情况下,商标最初的价值来源并积累于消费者对商标权人所提供产品的认可。如商标权人申请破产后不实际参与商标经营而被许可人继续使用商标,对一部分作出购买行为是基于对商标权人的信赖的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混淆与误导。并且,商标许可之所以获得合法化并逐步发展的一大关键在于商标在许可人质量监督义务下由传统的物理生产来源标识转变为品质控制来源标志。而一旦商标权人进入破产程序,其履行合同的能力打折,质量监督义务履行能力也将随之减弱甚至丧失,若此时被许可人的商标使用继续,可能出现产品品质下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后果。这也是当前美国破产法中把商标权排除在“知识产权”实施权保留机制之外的最主要原因。(51)董涛:《破产程序中知识产权许可协议“法律待遇”问题研究——美国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0期,第161页。但毕竟考虑到许可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的需求,以及继续实施商标权具有正面的商业与社会效应,还是有必要给满足合理条件的非为破产债务人的商标被许可方保留商标权实施的可能。而这种条件限定为“已使用商标”的理由依旧在于“使用”使得被许可方与商标建立了较深的关联性,也使得相关的公共秩序与公共利益得以形成。破产管理人的单方解除之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导致多方主体利益失衡或受损的后果。
最后,已使用商标的被许可人有权提出保留使用权之申请,但其需要获得法院的批准才可最终继续实施商标权。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破产程序中的倾斜保护需提供给对商标价值作出实质性贡献的被许可人。并非使用了商标的被许可人均对商标价值作出有益贡献,唯有开展了勤勉经营,对商标实际付出与投入过的被许可人才是在破产管理人单方解除合同将产生的不公平局面中,需要予以“扶持”的主体。且许可商标的经营状况直接关涉破产财产价值,破产债权人利益,故保留实施权的主体必须具备继续开展良好经营的能力。设置“经法院批准”的条件,对于筛选这样的商标被许可方是更为有利的。第二,法院的批准有助于保证被许可人所提供的贴附了许可商标的产品的质量。商标许可中,商标权人与商标实际使用者相分离,为保证商品或服务质量,保障消费者对商标的信赖利益,双方都负有维持产品质量水准的义务:商标权人的质量监督以及被许可人的品质保证义务。(52)《商标法》第43条。而在商标权人申请破产的情形中,质量监督义务的履行就存在较大困难。因这一义务的履行需要商标权人对被许可人使用商标开展实质性的管理与检查工作,仅停留在合同监督条款层面的“纸上监督”是不够的(53)陈选:《商标许可人质量监督义务探析》,载《电子知识产权》2017年第10期,第49页。,这就意味着必须以一定成本的付出作为保障,而对破产债务人来说或许难以实现。有学者建议只有在商品质量控制的责任无需由商标权人承担,或者说由被许可人一方负责控制产品品质时,被许可人才有权保留商标使用权。(54)Timothy J.Keough,Note,You’re Asking the Wrong Question-The Effect of a Licensor’s Rejection on the Trademark License,47 Suffolk University Law Review 165,185-186 (2014).但笔者认为,由于被许可人只享有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因而欠缺质量控制、维护商誉的长期激励,且商标权人基于商标许可切实地获取了利益,故而商标权人对产品质量必须承担管控的责任。当其在此义务上的履行因申请破产而陷入困境时,管理人的辅助甚至代替履行十分关键。当然管理人出于专业局限性等原因,在经法院许可后,可聘用必要工作人员来实际实施质量监督,这也符合《破产法》第28条之规定。但无论如何,在商标权人申请破产的前提下,由该主体一方进行质量监督的不确定性都会增加,基于此,被许可人一方的品质管理就显得尤为关键了。通过设置被许可人保留商标使用权需获得法院批准这一要求,在商标权人质量监督可能有所欠缺的情况下,可为产品品质提供多一层的把关,从而更好发挥商标价值。具体来讲,若法院认为被许可人不具备保证相关商品或服务质量的能力,则不应批准被许可人提出的保留商标使用权的请求,反之其请求应获批准。(55)Kayvan Ghaffari,The End to an Era of Neglect:The Need for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Trademark Licenses,87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1053,1081 (2014).
当然,实际上作为理性的商事主体,商标被许可人会综合多方因素后作出最符合利益需求的判断、选择。在商标权人申请破产,被许可人自身未使用商标而管理人决定解除合同时,被许可人在考虑到商标价值稳定性与因解除合同可能承担的有限损失后,通常也会选择接受解除合同的决定。
结语
待履行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在破产程序中的解除事关许可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变动,也牵涉消费者对商标的信赖利益以及与许可相关的市场秩序等公共利益维护问题。当前我国对此问题适用《破产法》有关管理人待履行合同选择权的一般规定,这一做法存在明显局限,故应在考虑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特征的基础上,对管理人针对该类合同的单方选择权设置适当条件,以更好促进破产财团利益、合同当事人利益以及公共利益间的多方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