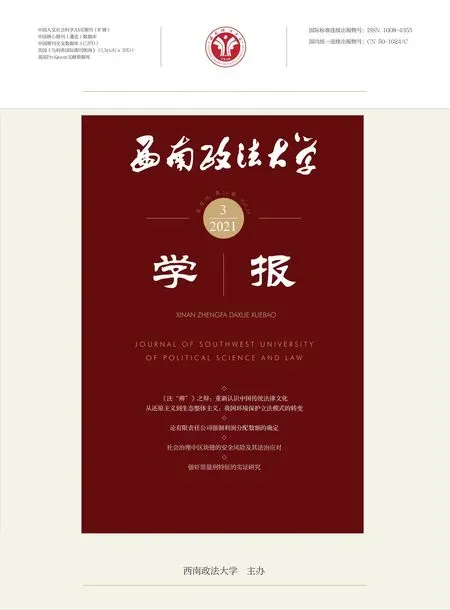论消费者评价利益的权利保护模式及规则构造
2021-11-21李超
李 超
(南京大学 法学院,南京 210093)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第39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公示信用评价规则,为消费者提供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的途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的评价。”该条所称的“消费者对其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的评价”简称“消费者评价”,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并使用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下简称平台经营者或平台)内的经营者(以下简称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接受其服务后作出评论或评级的行为。实务部门对《电子商务法》第39条的解读是,该条规定了消费者的“评价权”:“规定了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提供消费者信用评价义务,保障了消费者享有对电子商务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的权利。”(1)仲余年、张雷:《浅析〈电子商务法〉实施背景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19年第9期,第51页。
然而,电子商务法起草组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条文释义》认为,第39条设定了平台经营者对消费者评价应当履行的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2)参见电子商务法起草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条文释义》,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122页。并未明确规定消费者评价是一种“评价权”,甚至未见与“权利”相关的字眼。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电子商务法》第39条所保护的特殊利益——消费者评价利益,是指通过行为规制模式(给平台经营者设定义务)保护的法益,还是指采用设权模式保护的权利,将产生截然不同的规制效果:在行为规制模式下,只要经营者的行为未达到行为规制的要件要求,都是经营者的行为自由,这恰好平衡了消费者、经营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将评价利益权利化,意味着将压缩经营者更多的自由空间,而此种自由空间对当下平台经济发展同样非常重要。况且,在消费者已经享有诸多法定权利的前提下,消费者评价权的概念真有存在必要吗?是否会导致所谓新兴权利的泛滥?
综上,本文提出的问题是:消费者评价利益的法律属性为何?采用行为规制保护模式是否已经足够?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作系统解答。
二、消费者评价利益的法律属性
对评价利益的准确识别,是讨论评价利益是否需要保护及如何进行保护的逻辑前提。本文首先以涉消费者评价的裁判文书为切入点,从裁判文书中整理出法院对评价利益法律属性认识的基本立场,在此基础上厘清评价利益的法律属性。
(一)消费者评价利益法律属性之裁判分歧
本文的案例主要选自2015年9月2日至2020年9月2日期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有关消费者评价的裁判文书,涵盖《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前后与消费者评价相关的案件。通过梳理发现,目前法院就评价利益的法律属性问题,存在如下三种观点:
1.消费者评价利益不是独立利益
该观点认为评价利益不能作为独立的利益进行保护,只能依附于基础合同法律关系或平台管理而存在,一旦这样的基础丧失,就没有保护的必要。例如,在“钟杰焕诉京东公司案”中,钟杰焕在京东门店购置一台电脑并作出差评,京东公司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删除了评价,钟杰焕要求京东公司恢复评价内容,并赔礼道歉。法院认为,由于涉案电脑已经进行退货退款处理,该商品评论的事实基础随着买卖关系的解除而消失,故京东公司删除商品评论并无不妥。(3)参见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2019)桂0405民初757号民事判决书。又如,在“王至宗诉华杰公司、天猫公司案”中,天猫公司对王至宗的信用等级进行调整,使其无法对华杰公司追评,王至宗认为这是对其人格的侮辱,造成了精神损害。法院认为,天猫公司对信用等级的调整属于平台的内部管理行为,未违反禁止性规定,并不存在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4)参见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4民初14773号民事判决书。
2.消费者评价利益是一种法益
该观点认为评价利益是一种法益,当此种法益受到侵害时,只能对其作较为宽松的保护。
第一,认为评价利益是一种约定利益,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予以保护。例如,在“思雨公司诉梁跃文、淘宝公司案”中,梁跃文在确认评论内容不实后,与思雨公司协商删除评论,却遭到淘宝公司的拒绝。法院根据《淘宝网评价规则》的相关规定,承认消费者可以对评价内容进行处分。(5)参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0民终222号民事判决书。
第二,对平台经营者删除评价的行为作宽松审查,只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使对评价利益造成了损害也不进行保护。例如,在“朱江诉淘宝公司案”中,朱江发表的差评被淘宝公司误判为广告不予展示,朱江认为淘宝公司将骂人(某公众人物)的部分用星号替代即可,评价的整体内容应保留。法院认为,尽管淘宝公司将朱江的评价认定为广告并删除存在不当之处,但该内容包含不文明用语,整体删除并无不当。(6)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8845号民事判决书。当然,对于平台经营者实施的明显不合理删除评价的行为,也有法院将其视为对消费者民事权益的侵害,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2条进行保护。(7)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32066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判决最终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并发回重审。
第三,将评价利益定性为“反射利益”,在评价利益受到损害时,不承认消费者据此享有请求权。在“刘慧诉淘宝公司案”中,刘慧因交易订单关闭而无法进行评价,要求被告淘宝网赔礼道歉。法院认为,根据《电子商务法》第39条的规定,即便淘宝公司存在限制刘慧进行评价的情形,其承担的责任也是行政责任,故该案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8)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民初5876号民事判决书。
第四,认为评价利益是判断经营者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素之一。在“淘宝公司诉美名公司案”中,美名公司组织商户开展“免费试用活动”,试用用户并未支付对价但伪造了大量的消费者评价信息,于是,淘宝公司以美名公司组织商户虚假宣传为由诉至法院。法院认为,美名公司组织的虚假宣传行为使淘宝平台的数据失真,干扰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亦使不诚信的商家基于虚假的用户评价不正当地获得了竞争优势和交易机会,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秩序,并使消费者对淘宝平台的评价降低,损害了淘宝公司的合法权益。(9)参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初3845号民事判决书。
3.消费者评价利益是一种权利
该种观点认为评价利益是消费者对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质量享有的一种“法定权利”或“公正评论权”。该类案件主要指当消费者就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发布差评后,平台内经营者以其名誉权受损为由诉至法院,法院必须在评价利益和经营者名誉权之间进行平衡,从而需要界定评价利益的法律属性。
第一,法院首先肯定评价利益的存在,只要消费者作出的差评未达到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均是消费者的自由。例如,在“申翠华诉王铮韵案”中,法院分析认为,消费者有权凭借自身的购物体验感受对商品给予差评,消费者评价具有主观性,但只要不是基于主观恶意的目的,经营者不能过分苛求消费者必须给予好评。(10)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1854号民事判决书。
第二,法院在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6号,以下简称《名誉权解释》)第9条后,直接使用“法定权利”或“公正评论权”的概念。例如,在“美明宇月子公司诉李某、张某、汉涛公司案”中,法院认为,根据《名誉权解释》第9条规定,消费者作为网络用户对于商品质量和服务进行批评、评论,是消费者的法定权利,只有消费者借机诽谤、诋毁并实际损害他人名誉方可认定为侵害名誉权。(11)参见梅岭:《〈电子商务法〉十大典型案例发布》,载 《中国质量万里行》2020年第1期,第12-13页;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849号民事判决书。亦有法院未交代权利来源便直接认定评价利益就是“公正评论权”,(12)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申2576号民事裁定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终5468号民事判决书。但结合前述判决可推知,所谓“法律规定”就是《名誉权解释》第9条。在该类案件中,法院不仅肯定了权利的存在,还要求平台内经营者对评论内容的真实性、消费者有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并对消费者评价的一般性失误给予容忍。(13)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民初3999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同时强调,消费者评价在不构成名誉侵权的情况下,也应遵守网络道德规范。(14)参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126号民事判决书。
(二)消费者评价利益法律属性之厘清
鉴于司法裁判对评价利益的法律属性存在较大分歧,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以正本清源。
1.消费者评价利益并非法定权利
总结上述裁判可以发现,法官在解说评价利益的法律属性时,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证思路:在讨论评价利益受到侵害应如何救济时,对权利问题避而不谈;在讨论评价利益与名誉权的冲突时,则会使用权利的概念。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评价利益真的是“法定权利”或“公正评论权”吗?
第一,法院使用权利的概念并不代表权利真的存在,仅是为了增强裁判的理论深度与说服力。因为《名誉权解释》第9条已经确定了清晰的名誉侵权构成要件,在要件之外兼为消费者的自由,法院使用权利概念并不影响裁判结果。法院只是为了表明,当评价利益与名誉权发生冲突时,基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经营者的名誉权应适度容忍。因此,仅通过确定评价利益的外延并不能据此断定此种利益就是权利。
第二,法院回避权利的概念要么是受制于现行法律文本的要求,要么是无须再使用权利的概念。一方面,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应当尊重现行法律文本。例如,现行《电子商务法》第39条等条文只是给经营者设定了义务,并未出现“权利”的表述,由于义务并不当然指向权利,也可能指向法益,故从经营者义务中无法直接推导出权利。另一方面,在有些案件中,法院运用合同解释的方法就可以解决争议。例如,在前述“淘宝公司诉思雨公司名誉权纠纷案”中,淘宝拒绝删除评价的争议完全可以在《合同法》框架内解决,再讨论权利的问题显得多此一举。(15)参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0民终222号民事判决书。
第三,不排除法院是出于利益协调的需要或裁判正当性的考量,在个案中推动权利概念形成与立法进步。例如,在前述“枣玛露脊骨汤珠江路店诉三快公司案”中,法院并不简单地止步于权利概念的描述,还尝试将“公正评论权”的内涵提炼为“好评权”和“差评权”,以回应利益协调的现实需要。(16)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申2576号民事裁定书。但《名誉权解释》毕竟制定于1998年,在当时,连互联网都未曾普及,司法解释的制定者们根本无法预料消费者评价这样的新事物,也无法预料会引发如此广泛的利益冲突。因此,法院对第9条的解释未免有“旧瓶装新酒”的可能。法院能否在个案中直接确定权利的存在,关涉立法权和司法权如何配置的问题,法院理应谨慎对待,不能僭越立法权。
第四,裁判分歧的根源在于法院对评价利益本质属性的认知分歧。消费者评价毕竟是在数字经济兴起后才引发广泛关注,与传统依靠消费者之间口口相传的“口碑”不同,消费者评价信息在平台上同商品和服务同时展现、持久传播,直接关涉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和平台经营者等多方主体,加大了利益识别难度。消费者评价到底属于言论、交易信息,还是平台数据产品,几乎混杂在一起,难以辨别。由于法院对评价利益认识的不同,也就采用了不同的认定或保护思路。如果同时期的理论观点被法院采纳,也可能加剧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研究认为消费者评价只是一种对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平台和政府治理兼有重要功效的“信息工具”。(17)国内将消费者评价视为信息工具的讨论,可参见刘绍宇:《论互联网经济的合作规制模式》,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73-74页;赵鹏:《平台、信息和个体:共享经济的特征及其法律意涵》,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第72页;宋亚辉:《网络市场规制的三种模式及其适用原理》,载《法学》2018年第10期,第93页。国外将消费者评价视为信息工具的讨论,参见Yonathan A.Arbel,Reputation Failure:The Limits of Market Discipline in Consumer Markets,54 Wake Forest Law Review 1239,1239-1254(2019).如果法院受该类理论的影响,产生评价利益间接保护、弱保护或不予保护的裁判思路也不足为怪。
综上,在司法语境下,评价利益很难直接等同于“法定权利”,充其量只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特殊利益,此种利益究竟为何,仍需进一步剖析。
2.消费者评价利益是消费者享有的言论自由
评价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并非依附于合同关系或平台管理而存在的附属性利益,也不同于作品或数据等被客体化的利益,而是消费者享有的言论自由。
第一,评价利益不是依附于合同关系或平台管理的附属利益。根据前文有些法院的观点,评价利益只能依附于基础合同法律关系或平台管理而存在,当合同关系解除或平台管理调整时,评价利益便丧失或被剥夺,故评价利益只是一种附属性的利益。该类观点只承认评价利益的信息属性,否定评价利益的人格属性,进而否定消费者对评价利益的支配权。虽然消费者评价在展示经营者口碑、助推经营决策等方面具有重要信息价值,并能转化为流量关注乃至经营收入等经济价值,但这只是站在经营者的立场片面考量而得出的结论。在信息工具主义本位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将完全抹杀消费者评价的主体性价值,消费者极可能沦为免费生产评价信息的机器。事实上,消费者发布的每条评论不论是好评还是差评,都应该被关注和尊重,并不在于能否给消费者带来经济利益,也不在于内容的优劣或是否独创,而是直接关乎消费者的表达自由和人格尊严。在数字经济所谓“免费模式”的掩盖下,评价信息的分享表面上是自发的、无利润的,但那些真诚细致、娓娓道来和图文并茂的评价信息都是每个消费者生活轨迹和消费体验的真实记录,是一种被需要和被关注后的满足感。因此,那种认为评价利益并非独立利益的观点,只是将利益客体化对待,完全是本末倒置。
第二,评价利益不同于作品利益或数据利益。(1)消费者评价是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自由表达,同作品一样,其生成过程反映了消费者的思想。为了保护信息主体的权益,鼓励信息的创作和传播,当其创作成果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要求的构成要件时,其可以享有著作权。(18)参见毛立琦:《数据产品保护路径探究——基于数据产品利益格局分析》,载《财经法学》2020年第2期,第97页。当然,消费者评价通常只对商品或服务作出简单的事实描述或有限的观点表达,主要在于展现消费者完成购物体验后的思维、思想和情感。一般而言,消费者评价很难达到“独创性”的标准,出于鼓励评价信息流通和防止事实或观点垄断的立场,应当严格认定其独创性。但是即使评价内容并不符合独创性要求,并不意味着其不值得保护。(2)评价利益也不同于数据等财产性利益。即使评价内容未达到作品的独创性要求,也不宜作为财产性利益转让。在实务操作中,便有平台经营者试图混淆评价利益与一般财产性利益的界限,通过与消费者签订格式条款的形式,要求消费者将评价内容无偿转让,平台经营者借此享有对评价内容的控制权。(19)参见《携程旅行网服务协议》第6条。更有甚者,有法院将评价信息直接认定为经营者享有的一种经营利益。(20)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1072号民事判决书。通过此类安排,平台经营者可利用“作品”权利或评价信息的权属,达到控制消费者评价的目的。
第三,评价利益是消费者享有的言论自由。消费者评价是消费者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对商品或服务作出的个性化表达,其依托于平台的核心交互技术和商业模式而发展和普及。由于评价信息具有易汇聚、易留痕和易扩散的特点,评价内容也被客观化或数据化,成为决定平台内经营者口碑、流量、收入的主要途径。(21)参见Lucille M.Ponte,Protecting Brand Image or Gaming the System:Consumer Gag Contracts in an Age of Crowdsourced Ratings and Reviews,7 William & Mary Business Law Review 59,62-71(2016).但这只是改变了消费者评价的呈现方式和传播媒介,未曾改变消费者评价的实质——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自由发表的言论。根据言论自由的一般要求,除法律禁止发表的言论外,消费者原则上均可就商品或服务自由发表言论,并通过网络媒介传播言论。(22)参见 Lucille M.Ponte,Protecting Brand Image or Gaming the System? Consumer Gag Contracts in an Age of Crowdsourced Ratings and Reviews,7 William & Mary Business Law Review 59,114-115(2016).消费者能够选择言论是否在网络空间中呈现,以及以何种方式呈现,而不必担心遭受经营者的事先限制和事后报复;消费者能够自由接收和获取真实言论,以促进其表达自由之实现;消费者能够使自己的言论被传播、倾听和关注,以体现消费者之独立人格。这是消费者在平台市场上向强势的经营者行使“消费主权”和“发布命令”的有力武器。如果消费者不能对商品或服务自由地表达思想,消费者便会沦为没有人格自由的人,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如果消费者遭受和体验了不良的商品或服务却无处诉说,这是对人性的压抑。如果消费者享受和体验了很好的商品或服务却无法赞美,也是对人性的压抑。如果消费者不能畅快地沟通和互动,将压制消费者的个性和创造力。
三、消费者评价利益的行为规制保护模式及其缺陷
虽然评价利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35条的涵摄范围内,但将利益保护的选择权预留给了部门法。前已述及,当评价利益同名誉权冲突时,法院已通过《名誉权解释》第9条将《宪法》第35条在侵权法的框架内进行了转化,通过严格的侵权构成要件设置和举证责任分配,既能对评价利益进行倾斜性保护,又能在个案中灵活平衡利益冲突。但我国现行立法并未止步于此,当评价利益受经营者侵害时,立法者构筑了更为精细化的行为规制制度架构。
(一)消费者评价利益行为规制保护之架构
1.平台内经营者干扰评价的行为规制架构
由于消费者评价对展示平台内经营者的口碑形象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其流量乃至经营收入,而消费者在作出评价时,往往容易受到在先评价的影响,产生所谓羊群效应、认知偏见或框架效应。(23)参见Abbey Stemler,Feedback Loop Failure:Implications for the Self-Regulation of the Sharing Economy,18 Minnesota Journal of Law,Science & Technology 673,688-697(2017).这使得平台内经营者易利用技术手段删除不利评价,提高自身商誉,或组织对竞争对手的恶意评价,贬低对方商誉,从而对评价活动进行干扰。基于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平台内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消费者评价作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若经营者通过虚构消费者评价,帮助平台内经营者进行虚假宣传,同样在禁止之列。第11条进一步规定,如果平台内经营者编造或传播竞争对手的虚假评价信息或误导性评价信息,还可能因构成商业诋毁而被禁止。《电子商务法》第17条重申,平台内经营者不得以编造消费者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24)参见《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4条。
2.平台经营者删除、篡改评价的行为规制架构
针对平台经营者删除、篡改消费者评价的行为,可分为事前控制和事后控制两类。
第一,事前控制平台经营者基于格式条款获得的删除、篡改评价权限。《电子商务法》第39条第1款规定,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公示信用评价规则,为消费者提供评价的途径。该款既是给平台经营者设定的积极作为义务,又是对平台经营者建立内部评价规则作出的法律授权。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约束和限制消费者评价的方式、内容评价规则,是否构成对消费者言论的事先控制,进而克减或侵害其评价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第1款之规定,平台经营者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显著提示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第2款、第3款则规定了格式条款的无效制度,并将“不公平、不合理”作为实质判断要件。另根据《合同法》第41条规定,格式条款还应受不利解释制度的制约。此外,根据《电子商务法》第33条、第34条规定,平台经营者格式条款的制定,应在其首页显著持续地公示;格式条款的变更,应在显著位置公开征求意见,并采取合理措施确保各方及时充分表达意见。
第二,事后控制平台经营者擅自删除、篡改评价。《电子商务法》第39条第2款规定,平台经营者不得删除消费者评价。但此处的“不得删除”并非一律不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7条、《民法典》第1194条、《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10条等规定,平台经营者对违法或侵权评价仍须履行审核、过滤和管理等义务,平台经营者仍享有删除评价的权限。为有效控制平台经营者的评价管理权限,《电子商务法》第81条第1款第4项规定,平台经营者擅自删除消费者评价的,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25)参见《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5条。
(二)消费者评价利益行为规制保护之缺陷
如果现行行为规制制度足以保护评价利益,再由法律明确规定评价利益为法定权利便显得没有必要。因此需要进一步追问,既有行为规制制度是否足以保护评价利益?
1.《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仅间接保护消费者评价利益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11条仅将评价利益分别纳入虚假宣传行为和商业诋毁行为的行为规制架构下进行保护,评价利益被客体化对待,保护效果不彰。
在前文分析的法院裁判观点中已经表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主要是保护经营者的利益,评价利益仅是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和平台数据权指向的客体,消费者本身并不能独立占有此种利益,即使消费者评价受到了平台内经营者的不当干扰,也只能通过其他经营者提起诉讼获得有限、间接的保护。同理,对于经营者实施的虚假宣传行为,即使消费者能通过民事欺诈制度获得救济,所保护的也只是知情权和选择权,对于评价被替代或者被干扰等直接侵害评价利益的行为,仍然无法通过民事欺诈制度予以保护。针对平台内经营者利用消费者评价实行的商业诋毁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已经明确规定此种行为直接损害的是竞争者的利益。尽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已将“消费者合法权益”纳入该法的法益保护目标,也只是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断要素,消费者并不能因此而获得请求权。(26)参见张占江:《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范式的嬗变:从“保护竞争者”到“保护竞争”》,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1期,第221-222页。即使通过《侵权责任法》第2条“一般条款”的“中介”间接保护消费者言论在理论上不存在障碍,但从可行性角度来看,背俗侵权只有在构成故意时方可被问责,并需要有纯粹财产利益上的损害,且何为“善良风俗”也不易认定,操作上较为困难。(27)参见张红:《基本权利与私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60-261页。
《反不正当竞争法》确立的行为规制模式存在上述结构性缺陷,同当下客观情势难相匹配。一方面,广泛存在且备受诟病的“刷单炒信”行为大行其道,平台内经营者实施的替代、强制、诱导、误导等多种干扰评价行为,要么直接剥夺了消费者的评价机会,要么使消费者作出违背真意的评价,要么对消费者评价的作出造成严重误导。另一方面,受制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规制架构,消费者无法享有请求权,只能依赖于少数经营者提起诉讼而获得间接保护。其后果是,评价利益被“败德”的平台内经营者利用制度缺陷不断盘剥和侵蚀。
2.《电子商务法》等不足以保护消费者评价利益
通过检视发现,以《电子商务法》第39条为核心所构建的平台经营者删除、篡改评价行为的事前和事后控制体系同样不足以保护消费者评价利益。
第一,格式条款体系并不足以防范平台经营者滥用评价管理权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第2款将“不公平、不合理”作为是否限制或排除消费者权利或加重消费者责任的判断标准,但该判断标准过于抽象,难以解决评价利益被不当限制的问题。由于法院对评价利益法律属性的认识分歧较大,给评价利益的保护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如果承认评价利益只能依附于基础合同法律关系或平台管理而存在,那么评价利益将完全在平台掌控之中,可任由平台进行限制或剥夺,很难谓之不公平或者不合理。如果只将消费者视为免费生产评价信息的机器,认为消费者对评价内容并不享有支配性利益,评价信息可随意转变成被平台任意支配的数据财产,很难谓之不公平或者不合理。如果仅认为消费者接受了免费评价服务而未支付任何对价,平台经营者对评价内容的控制不过是一般的服务行为,很难谓之不公平或者不合理。即使评价利益可直接等同于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但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在基本权利尚未通过私法转换之前,也无法直接适用于私人合同。(28)参见 Alan E.Garfield,Promises of Silence:Contract Law and Freedom of Speech,83 Cornell Law Review 261,347-358 (1998).因此,也难以被视为限制或排除了消费者权利。此外,《电子商务法》第33条、第34条赋予了消费者作为相对方的合同解除权,但从实效来看,平台的特殊地位使相对方对其具有依赖性,导致单方解除权缺乏抑制平台滥用单方变更权的实际作用,征求意见与先期公示又缺乏真正的约束力,特殊提示义务则被实质性地抛弃。(29)王红霞、孙寒宁:《电子商务平台单方变更合同的法律规制———兼论〈电子商务法〉第34条之局限》,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37页。
第二,以行政规制为主导的事后控制体系并不足以对平台经营者形成制约。其一,在实体义务设置层面,《电子商务法》第39条对评价利益和平台管理权的边界界分不清,《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平台对评价信息的技术处理,以“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为限,但具体指向、可删除评价的情形及限度等缺乏清晰的界定。一方面,由于平台仍有一定的评价管理权限,为平台不当删除、篡改评价提供了便利。例如,有偿删帖者通过伪造材料,要求平台删除评价的情况十分常见,更有甚者,有偿删帖者还可以勾结平台内部人员进入操作系统直接删除评价。(30)参见朱虹:《揭开“有偿删差评”的利益链条》,载《人民日报》2020年9月24日,第19版。另一方面,《电子商务法》第39条中“不得”的表述,也为消费者滥用评价机制提供了可乘之机,甚至形成“职业差评师”这样的新群体,他们将恶意评价发布到各类平台,以行敲诈勒索,或成为打压竞争对手的“帮凶”。(31)参见吴睿鸫:《既要惩治有偿删帖也要规制恶意差评》,载《检察日报》2020年9月25日,第4版。上述困局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行为规制模式并不能“因案设法”,难以精准应对样态各异的市场行为,并可能因为对策行为而被规避。(32)参见宋亚辉:《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研究——〈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解释论》,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2期,第97页。其二,在实施机制配套层面,仅靠单一的行政规制路径,并不能充分保护评价利益。《电子商务法》第81条已明显排除消费者请求权,并在司法裁判中得到确认。较之私人诉讼而言,尽管行政规制具有较高的执行效率,能够对特定不法行为进行快速查处,但也面临难以克服的缺陷:由于行政机关不直接参与市场主体交易活动,难以获取平台经营者的违法信息,只能依赖消费者有限的投诉或举报。又由于评价利益长期被客体化对待,受到侵害的消费者很难有动力向行政机关提供违法信息。即使投诉或举报信息是充足的,行政机关受制于有限的规制资源,对投诉信息也设置了严格的条件。(33)参见《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15条。其三,经验事实证明,单一行为规制模式收效甚微。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19年3月15日发布的《信用消费与消费者认知调查报告》显示,有72.4%的受访者曾遭遇过平台或商家“默认好评”,35.6%的人遇到过商家主动联系要求撤销或修改评价,34.2%的人的评价会被隐藏或删除。(34)参见张贵峰:《网购被“默认好评”有损信用消费环境》,载《中国商报》2019年3月20日,第2版。另外,消费者因发差评“被报复”“被报警”“被起诉”的极端事件亦时有发生。(35)参见舒云:《消费者评价权不容落空》,载《法治日报》2020年9月23日,第5版。
四、消费者评价利益的权利化保护路径
鉴于既有的行为规制模式不足以保护评价利益,迫切需要法律确认“消费者评价权”,推动评价利益从客体保护向主体保护回归,为消费者提供明确的利益导向和激励。
(一)消费者评价利益权利化的可行性
单纯的一种利益需求或主张并不能成为权利,只有它们被群体或社会普遍认同时,才能成为权利。(36)参见李拥军:《论权利的生成》,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第81页。评价利益是否需要权利化,不能仅从逻辑上推导,还需要获得经验事实的支撑。
1.消费者评价利益的权利化有实务经验支撑
本文前述的“美明宇诉李某、张某、汉涛公司案”,曾被评为“《电子商务法》实施元年年度十大典型案例”之一,主要理由是:“……法院经审理肯定了消费者评价权为消费者的法定权利,并且对评价权的行使和侵害名誉权之间如何界分进行了清晰的说理论证。”(37)梅岭:《〈电子商务法〉十大典型案例发布》,载《中国质量万里行》2020年第1期,第13页。尽管在“权利未法定”的情况下,法官能否从《名誉权解释》第9条中推导消费者评价权的存在尚存疑问,但法院为什么不去采纳已经被法律确认的消费者批评监督权,而是另起炉灶,使用消费者评价权的概念呢?换言之,如果仅把消费者评价权作为增强裁判说理的修辞,没有必要遴选为典型案例,这不正好反映了将评价利益权利化的真实呼声吗?文化和旅游部在2020年8月20日发布的《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在线旅游规定》)第13条,更是直接采纳了“正当评价权”的概念,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屏蔽、删除评价,不得误导、引诱、替代或强制评价,持续保存和公开评价,对于删除的评价信息,还应当记录和保存。该条通过“确权+义务配置”的规范构造,已然勾勒了消费者评价权的轮廓。尽管通过部门规章直接“设权”并不妥当,也不排除就是参考现行审判经验的结果,但这种制度尝试恰好为新权利的孕育提供了观念和制度准备。
2.消费者评价利益权利化有域外法方面的经验借鉴
在美国,经营者为了防止消费者发布负面评价损及声誉,通常在消费合同中事先加入“反评价条款”并约定严苛的违约责任,这类条款因压制消费者言论自由、降低商业效率、扰乱市场公平竞争而备受诟病。(38)参见毛琦:《美国〈2016年消费者评价公平法〉述评》,载《经济法论丛》2019年第2期,第415-417页。2014年9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率先启动消费者评价保护立法,在《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1670.8条中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在合同中约定“消费者放弃发表任何表达的权利”的条款,否则需要支付民事罚款,该条明确提示评价权受到损害的消费者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39)参见California Code,Civil Code - CIV § 1670.8.2016年10月,马里兰州通过了直接以权利命名的“Right to Yelp”法,该法第14-1325条也明确禁止经营者在合同中要求消费者放弃“任何发表评论的权利”。(40)参见Md.Code Ann.Com.Law § 14-1325.2016年12月,美国国会在总结各州立法和实务经验的基础上出台《消费者评价公平法》,成为世界上首部专门保护消费者评价的立法。该法于2016年4月由两党议员联合提出,10月在众议院通过,12月在参议院未经删改通过,历时仅8个月,在美国两党长期角逐和争斗激烈的背景下,实属少见。《消费者评价公平法》第2(a)(2)条将消费者通过书面、口头或者图像展示等方式对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作出的评论,以及采用电子手段作出的性能评估或类似分析,均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41)参见Consumer Review Fairness Act §2(a)(2),15 U.S.C,§45b(2020).2017年2月,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简称FTC)发布的法律实施指南重申了该法保护消费者评价权的努力:“《消费者评价公平法》保护消费者在任何论坛(包括社交媒体)上分享其对企业商品、服务或行为的真实看法的能力。”(42)参见FTC,Consumer Review Fairness Act What Businesses Need to Know,FTC website(Feb.2017),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nsumer-review-fairness-act-what-businesses-need-know,2020年12月20日访问。在法律实施方面,该法在整体上确立了以FTC和州检察总长为主的公共实施机制,但为确保同州法律衔接,该法并不排除消费者根据州法律规定享有的请求权。(43)参见Consumer Review Fairness Act §2(g),15 U.S.C,§45b(2020).
(二)消费者评价利益权利化的具体路径
即使评价利益需要法定化为一种权利,是否就必然需要独立为一种消费者评价权?换言之,如果我国法律体系中已经有其他权利包含或相当于消费者评价权的内容,则无需再确立一种权利概念。在提出消费者评价权概念时,需要明确其同消费者批评监督权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再提出权利化的立法方案。
1.将评价利益“寄生”于消费者批评监督权中进行保护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权利+义务”的方式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对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的批评监督权。第15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第17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听取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意见,接受消费者的监督。”有人或许会认为,既然已经有了消费者批评监督权,消费者评价权充其量就是批评监督权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延伸,因此,消费者评价权没有单独提出的必要。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两种权利的共同点,忽视了二者的根本性差异。
第一,评价利益可短期内“寄生”于消费者批评监督权之中。由于消费者评价同样具有信息传递、监督和抗辩的功能,同消费者批评监督权十分相似。这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权利现象:新权利在被法律确认之前,可“拟制”于类似权利之中得到保护。(44)参见李友根:《论经济法权利的生成——以知情权为例》,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6期,第61页。在前述名誉权纠纷的案例中,法院援引的1998年《名誉权解释》第9条,可以溯源至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5条规定的消费者批评监督权。虽然法院创制了“法定权利”或“公正评论权”的概念,但实际上仍是在消费者批评监督权的框架下保护评价利益,体现为“寄生”关系。例如,在“芭赫公司诉汉涛公司名誉权纠纷案”中,法院指出,经营者对消费者作出的负面评价,相较于普通人有更高的容忍义务,“不能因为两句言论不当就否定消费者对经营者提供的服务进行批评监督的权利”。(45)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民初3999号民事判决书。通过“寄生”的保护方式,既灵活回应了新兴权利兴起的现实诉求,又不曾逾越“依法裁判”的边界。因此,在立法尚未将评价利益上升为法定权利之前,将其“寄生”于消费者批评监督权中进行保护,是比较稳妥和易让人接受的路径。基于此,对于经营者利用格式条款不当限制消费者评价的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将经营者不当限制消费者评价的行为解释为“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批评监督权”,从而便于对格式条款进行实质审查。
第二,消费者评价与消费者批评监督权存在本质差异。对此,有学者对两者作了初步区分:“消费者评价虽然也可以产生监督的效果,但其目的主要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潜在消费者的选择提供重要信息指引。”(46)应飞虎:《消费者评价制度研究》,载《政法论丛》2018年第1期,第119页。虽然此种区分有一定道理,但仅基于信息功能的区分并不能厘清二者的本质差异,需要作进一步区分。一是主体不同。消费者评价的主体是具有真实消费体验的消费者,要求作出评价的消费者同经营者的产品或服务之间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消费者批评监督权的主体,既可以是与经营者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消费者,也可以是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消费者。(47)参见李适时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权益保护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二是对象不同。消费者批评监督权指向的对象不仅包括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还包括经营者合规及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消费者评价指向的对象主要限于对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发表评价,经营者合规或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可能是影响评价作出的因素,但并非直接评价的对象。三是内容不同。消费者评价包括评价过程自由和评价内容完整两部分,评价过程自由包括发表好评、差评或不予评价,评价内容完整包括不受经营者删除、篡改。消费者批评监督权只能吸收差评,却不能吸收发表好评或不予评价。(48)参见李超:《论消费者评价权》,载《河北法学》2021年第5期,第159-160页。四是功能不同。消费者批评监督权仅具有同经营者名誉权对抗的抗辩功能,其受到侵害并不能获得请求权。消费者评价在理论上不只限于抗辩,还可以获得请求权。如果将评价利益“寄生”于消费者批评监督权之中,针对诸如评价被误导、引诱、强制、替代、删除及篡改等直接侵害评价利益的行为,消费者均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基于上述根本性差异,对评价利益的“寄生”保护只是暂时的,最终分离是必然的,因此,需要在利益保护制度方面另觅出路。
2.通过行为规制与设权结合进行综合保护
评价利益的权利化并非完美无瑕,因为法律上确权不等于事实上确权和支配。消费者较之经营者而言,缺乏平等的谈判地位,评价利益极易被强势主体不当限制乃至剥夺。由于评价利益不能被等价转换为经济利益,评价权也容易被消费者抛弃。虽然评价权保障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但无法为经营者提供确定性指引,相反,既有的行为规制模式恰好能够为经营者提供确定的指引。若对评价利益采取“积极确权+行为规制”的综合保护模式,则权利化带来的结构性缺陷也能够被有效克服。
美国对评价利益权利化保护并非一蹴而就,也经历了从行为规制到设权保护的演变过程。在反评价条款产生之初,FTC只能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节的授权,将反评价条款纳入虚假广告的规制框架,以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公平的或欺骗性的贸易,但该法并未给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提供私人救济。(49)参见Lucille M.Ponte,Protecting Brand Image or Gaming the System:Consumer Gag Contracts in an Age of Crowdsourced Ratings and Reviews,7 William & Mary Business Law Review 59,120-122(2016).FTC执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但它只有在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才能提起诉讼,而不会在消费者受到孤立损害的情况下提起诉讼。(50)参见Michael Flynn,The Lie,the Bigger Lie,and the Biggest Lie-Unfair and Deceptive Trade Practices of Trip Advisor and Other Online Review Websites,36 Journal of Law & Commerce 23,586(2017).仅凭FTC一家之力,并不足以回应反评价条款普遍侵蚀消费者评价利益的严峻形势。正因为如此,《消费者评价公平法》应运而生,该法通过积极确权的方式对消费者评价利益进行专门保护,很好地搁置了《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应否介入合同领域的宪法问题,杜绝了经营者对消费者评价事先施加的不合理限制。有学者评论道:“《消费者评价公平法》是‘言论强化’立法的极好范例,它促使消费者有权对与其交易的企业畅所欲言,这样做是正当的——因为保护高价值的言论可以改善我们的社会。”(51)参见Eric Goldman,Understanding the Consumer Review Fairness Act of 2016,24 Michiga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Law Review 1,15 (2017).与之同时,该法也兼顾消费者评价权同平台内经营者名誉权、平台经营者管理权等相关权利的关系。例如,《消费者评价公平法》第2(b)(2)(B)条规定,对消费者评价权的保护,并不排除经营者因消费者的侮辱、诽谤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52)参见Consumer Review Fairness Act §2(b)(2)(B),15 U.S.C,§45b(2020).第2(b)(2)(C)条规定,平台经营者有权删除其拥有、运营或以其他方式控制的网站或网页上的消费者恶意评价。(53)参见Consumer Review Fairness Act §2(b)(2)(C),15 U.S.C,§45b(2020).
从美国经验来看,正是采取“积极确权+行为规制”的综合保护模式,并通过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的结合,取长补短,以期全方位保障评价利益。本文认为,除了对消费者评价权进行“寄生”保护外,我国也可以在既有行为规制架构的基础上构建“积极确权+行为规制”这一综合保护模式。具体可以从如下进路展开:
其一,法院可继续援引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通过该要件的灵活性,在个案中平衡和协调消费者评价权与经营者名誉权的冲突。通过侵权构成要件的管道,在侵权法领域落实消费者言论保护的要求,并据此厘定消费者评价权行使的边界,防止消费者评价权被滥用。
其二,对于消费者评价权受经营者不当干扰、删除、篡改等问题,则有短期方案和长期方案供选择。首先,以《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4条、第15条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丰富既有行为规制制度架构。鉴于《在线旅游规定》第13条局限于旅游服务领域,与当下平台经济跨类经营难相匹配,市场监管部门和文化旅游部门应当加强执法协调,尽可能打破因部门立法而形成的监管规则壁垒,实现执法标准的统一。由于《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5条有关平台可对评价信息采取技术处理措施的情形与标准仍十分模糊,而司法实践中已经产生大量可供借鉴的案例群,对这些案例的类型化整理工作势在必行。其次,鉴于现行法律并未赋予消费者请求权,对经营者侵害评价利益之行为,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可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的授权,代表消费者提起公益诉讼,以弥补行政监管之不足。最后,从长远来看,应当通过修法确认消费者评价权。由于《电子商务法》侧重于对经营者的行为规制,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认消费者评价权更能实现法体系之协调。例如,可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5条之后新增第16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进行评论和评级的权利。”
五、结语
基于前文的研究,本文认为司法案例的变迁表明,评价利益是消费者享有的基本法益。虽然此种法益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由于此种法益对消费者极端重要且易受侵害,有必要将其法定化为“消费者评价权”。司法案例和部门规章的经验支撑,使评价利益权利化具有可行性。在消费者评价权未被法律确认之前,稳妥和可行的做法是,将其“寄生”于消费者批评监督权中进行保护,但这种“寄生”保护只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我国宜确立行为规制与设权保护相结合的综合保护模式,以全方位保护评价利益。囿于本文主题和篇幅,本文只对评价利益的识别及保护路径选择等问题作了初步回答。鉴于新兴权利问题研究的新颖性与复杂性,有关消费者评价权的内涵、性质、权利行使、权利冲突、权利限制、权利救济等问题,尚需要继续专门撰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