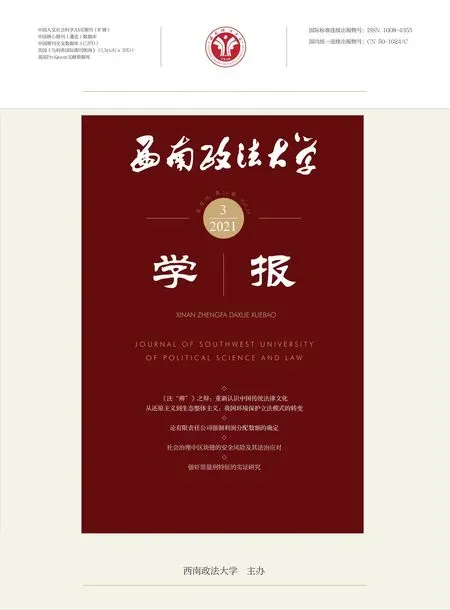以“结婚”为手段套取车牌指标之行为定性研究
2021-11-21李瑞华
李瑞华
(东南大学 法学院,南京 211189)
一、案例引入与问题意识
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充斥着某些合法违法交织的事件,这对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例如,某市“结婚买卖车牌指标案”。该案大致案情为:某市的“车牌中介”利用街头广告、QQ、微信等发布车牌指标信息,买方通过“车牌中介”与车牌持有人取得联系并交纳定金。随后,买卖双方结婚,待变更车牌后,再离婚,并支付尾款,“车牌中介”与车牌持有人按比例分成。涉案人员存在短期内多次、频繁结离婚的现象,从而变更过户一定数量的车牌。据悉,在车务中介公司有两份协议书,一份《婚前协议书》,该协议由标主和买标者签订,双方约定,婚后财产除双方婚姻前拥有的机动车及该市个人机动车普通号牌外,其余财产将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属于双方个人财产,不进行分割。另一份协议是与中介公司签订的《XX市车牌指标过户服务协议》,该协议提到,买方先交定金,待领结婚证后付一半的钱,尾款则在车辆行驶证变更之后支付。整套流程完成后,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对于本案,该市公安部门通报称,共抓获嫌疑人166人,其中124人以结婚为手段骗取、买卖小客车指标,因涉嫌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并有67人被批准逮捕。(1)孙莹:《以“结婚”为手段买卖车牌指标,67人已被批准逮捕》,载京报网2020年12月28日,https://news.bjd.com.cn/2020/12/28/38961t100.html。
当然,该案的确存在违法行为,但是否如司法机关所认定的,本案相关当事人构成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还值得深入探究。但由于本案为民事、行政乃至刑事交织的案件,因而在讨论该案是否构成犯罪时,也须探讨如下问题:第一,本案结婚、离婚是否合法合理,是否为通谋虚伪婚姻;第二,以结婚为手段套取变更过户资格是否合法;第三,本案涉及的小客车车牌与《小客车指标通知书》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公文;第四,“变更过户”车牌指标的行为是否能认定为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中的“买卖”。
上述问题的解决,既可全面分析本案当事人之行为,也可明确民法典时代民刑等交叉案件之认定立场。因此,下文笔者将首先分析本案涉嫌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之法益范围,然后判断本案的“变更过户”“买卖行为”等是否符合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的构成要件,继而界定本案在民法典时代违法性的认定路径,以期对违反民事、行政等非刑事法律的行为之责任承担进行正确界定。
二、行为未侵犯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的文书的保证功能法益
本案当事人是否涉嫌《刑法》第280条之“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即该案当事人的行为是否侵害本罪法益进而构成犯罪是对其出入罪认定的逻辑起点。如能首先将法益概念确定的话,则刑法的保护客体即有具体的范围,此即刑法的目的,亦能透过法益的保护而获得实践。(2)陈志龙:《法益与刑事立法》(3版),作者1997年自版,第2-29页。且法益判断的内容,作为刑法思考的基础,通过对法益的理解有助于刑法的解释与适用。(3)Vgl.suhr ZurBegriffsbestimmung von Rechtsgut und Tatobjekt im Strafrecht,JA 1990,S.303.Baumann/Weber/Mitsch,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11.Aufl.,2003,§3 Rn.10.因此,为正确界定本案当事人的行为,应首先考察域内外文书犯罪的法益理论,(4)虽然域外文书犯罪探讨的法益大多集中于“伪造文书罪”中,但这与我国《刑法》第280条的法益内容实质是一致的。因而本文主要介绍域外伪造文书罪之法益,以期确定我国《刑法》第280条之法益。并明晰其法益内容,以确定当事人的行为是否侵犯本罪法益。
文书类犯罪所欲保护的法益为何?这是伪造文书罪所面临的难题。(5)山口厚:《文書偽造罪の現代的展開》,载山口厚、井田良、佐伯仁志:《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Ⅱ》,岩波書店2006年版,第149頁以下。同时,德国学者Freund认为,如果伪造文书罪法益问题能够厘清,其不仅使刑法文书概念之标准能够理解,而且是构成要件所规范的行为样态能够容易掌握,参见Freund Urkundenstraftaten 1996,Rn.17.当前,对于该罪侵犯法益的见解大致有“公共信用说”“法律交往的安全性与可靠性说”等,现详细分析如下:(6)当然,对于伪造文书罪的法益,还有财产法益的观点,Vgl.Tröndle/Fischer,Strafgesetzbuch und Nebengesetze,52.Aufl.2004,§267 Rn.1.还有从文书本身的功能思考法益的观点,Vgl.Puppe,Die Fälschung technischer Aufzeichnung,1972,S.175.等等。
第一,“公共信用说”。(7)对此见解,参见仇晓敏、孙越:《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有关问题辨析》,载《人民司法》2019年第1期,第65页;甘添贵:《刑法各论(下)》(修订4版),三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1页;[日]西田典之、桥爪隆:《日本刑法各论》(第7版),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01页;松澤伸:《文書偽造罪の保護法益と“公共の信用”の内容——最近の判例を素材として》,载《早法》2007年82巻2号,第36頁;Vgl.Helle,Die nachträgliche Veränderung einer Urkunde durch ihren Aussteller,2001,S.17f.;Puppe,in:Neumann/Schild,Nomos-Kommentar zum Strafgesetzbuch/2.2.Aufl.2003,§267 Rn.3f.公共信用说是我国刑法学理论与实务中的有力见解。(8)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8页。实务见解参见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5)沙刑初字第719号刑事判决书;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2015)都刑初字第325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2014)茂信法刑初字第141号刑事判决书;等等。该说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要想保持健全的社会生活,公共信用的维护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现代社会生活主要由法律关系构成,在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大多须以文书记载,来表示或者证明其存在,并以经济交易生活中的行为最为显著。其中,此时的文书是具有公信力的物。因此,文书犯罪所侵害的并不是个人法益,实质上破坏的是文书在社会生活中显现的公共信用。因此,须通过保护对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性的各种文书之公共信用,来谋求基于文书所体现的公共信用之社会生活的安宁。
第二,“法律交往的安全性与可靠性说”。这是德国理论与实务界对于伪造文书罪保护法益的支配性见解。(9)林山田:《刑法个罪论(下)》(修订5版),作者2006年自版,第415页。德国的见解可参见Otto,Grundkurs Strafrecht,Die einzelnen Delikte,6.Aufl.2002,§69 Rn.1.该说认为,文书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法律交易证明的可靠性与安全性(非为财产法益的保护),文书犯罪保护法益是透过刑法对文书的变造和伪造行为的处罚,以建立文书的真实性与不可伪造性、不可编造性,并确保文书在法律交往中的安全性与可靠性。由于文书在证明上是可信赖的,而使彼此之间的法律交往具有安全性;更由于文书是可靠的,也足以确保参与法律交往者的可信赖,而不是用以保护法律交往本身。
第三,“对于真实的权利说”。(10)Vgl.Rheineck,Fälschungsbegriff und Geistigkeitstheorie,1979,.S.112f;Bettendorf,Der Irrtum bei den Urkundendelikten,1997,S.31f.该说认为,对于真实(真相)的权利,“真实的扭曲”并非仅仅是犯罪手段,而是他本身即为一种法益侵害,亦即“对于真实的权利”应视为具有重要性的法益。
第四,“保护机能与证明机能说”。(11)李茂生:《再论伪造文书罪中有关有刑伪造以及保护法益的问题》,载《刑事法思潮之奔腾——韩忠谟教授纪念论文集》,韩忠谟基金会2000年版,第316-317页;吴耀宗:《伪造文书罪保护法益之研究》,载《月旦法学杂志》2006年第128期,第135-137页。该说认为,文书具有意思传达机能以及意思表达固定化机能,才会在社会中被大众所用,并具有安定性,进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制度。现代社会生活中或者经济交易活动中,由于各种文书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各种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关系,都有赖于文书的稳固与保证或者证明功能。所以,文书类犯罪的保护法益应该是以“公众对于文书的保证机能的信赖”为主,而以“公众对于文书的证明机能的信赖”为辅。
第五,“文书制度说”。(12)曾淑瑜:《刑法分则实例研习——国家、社会法益之保护》(修订2版),三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246页;Kienapfel,Zur Abgrenzung von Urkundenfälschung und Urkundenunterdru?kung,Jura 1983,S.186.由于文书公共信用的概念较为抽象,有学者主张文书类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文书制度。因为文书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存在于一定的领域,它在维护交易安全之外,还是社会大众公认的一种制度,即文书作为民众社会交往的工具被普遍接受时,逐渐形成文书制度,并能够促进社会生活的运作。文书所形成的社会生活制度能够将某个直接可识别的、法律上重要的表示(文书)加以固定,并能够凸显出其视觉可见的证据价值与持续性,因而“文书制度”法益值得提倡。
但上述观点有待商榷,无论是我国的“公共信用说”,还是域外的“法律交往之安全性或者可靠性说”“文书制度说”等法益观,三者并无实质差异。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文书具有公共信用,才使得普通大众认为在交往或者交易中可以获得保障,法律交往之安全性或者可靠性不过是公共信用的进一步发展而已,而文书制度是文书在法律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角色”,也是法律交往过程中的形式固定化。然而,第一,无论是公共信用还是制度等法益,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法律交往者的信赖利益。(13)Arzt/Web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2000,§30 Rn.1.这种可信赖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法律交往的安全性与可靠性。但刑法上各类犯罪的保护法益,几乎都可以说成是社会大众对于社会秩序的一种信赖,例如贪污贿赂犯罪是保护社会大众对于国家公务的不可收买性的信赖、抢劫罪保护的是社会大众对于生命财产安全的信赖。第二,不同种类的文书在社会生活与法律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书所勾勒出的社会制度是当今社会生活的一种“必需品”。但按照“制度”的观点,刑法所保护的各项公共法益均可称之为相关制度。且上述见解太过抽象、空泛,(14)Steinmetz,Der Echtheitsbegriff im Tatbestand der Urkundenfälschung,1988,S.44;Jakobs,Urkundenfälschung,2000,S.5.本质上并没有将文书类犯罪所侵犯的法益说清楚,无法作为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法益的解释标准,难以具体适用。
而且,主张“对于真实的权利之侵害说”与“公共信用说”所欲达到的保护目的是一致的。由于文书的制作须有特定的章程、式样以及需要加盖印章等才具备相应的效力,正是因为文书制作的复杂性、权威性以及有效性,才使得其具有真实性,并可作为法律交往的前提,从而在法律交往中具有公共信用。但文书的真实之权利尚不足以作为刑罚处罚的基础,还需附加其他内容。而且,文书的真实性是文书制度的关键内容,即文书的真实性实际上是文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按照理论一贯地推导出来,那么,文书本身应该成为犯罪攻击的客体;但这样的结论只能正确说明变造文书以及毁损或妨碍文书使用的情形,却无法说明文书伪造以及行使的情形,因为将这种行为样态视为对于文书之攻击或者文书制度的攻击,都是令人无法理解的。(15)Steinmetz,Der Echtheitsbegriff im Tatbestand der Urkundenfälschung,1988,S.45;Hinrichs,Beweiszeichen und Kennzeichen,1996,S.19.
对此,笔者主张,文书类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是文书的保证功能。所谓文书的保证功能,是指文书应保证文书内容真实,保证持有者使用文书时实现文书内容所指称的事项,从而实现文书之功能。一方面,文书具有保证功能,其最终目的是使持有文书者能够找到可归责之主体。普珀(Puppe)教授认为,如果文书上所显示的表意人,实际上并未作出该表示,则此份文书就无法产生其本来依法所应有的法律效果;而该份文书若依法可能产生其他法律效果(例如伪造者的损害赔偿责任或者无权代理责任),但这种法律效果却无法从该文书本身看出来,因为伪造者并未在文书上表明自己是谁。(16)Puppe,in:Neumann/Schild,Nomos-Kommentar zum Strafgesetzbuch/2,2.Aufl.2003,§267 Rn.6.显然,文书持有者对文书归属的信赖(文书制作人)应通过文书的保证功能实现,当文书的可归责主体明确而具体时,既可保证文书在法律交往中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又能使文书具有真实性。当文书制作并流通于社会时,那么对该文书负责的相关单位以及人员便可以由文书之形式保证找到;如果我们连应该担保负责的人都找不到,讨论一份文书的真假,并无实际意义。(17)Geppert,Zur Urkundsqualität von Durchschriften,Abschriften und insbesondere Fotokopien,Jura 1990,S.271.另一方面,采用文书的保证功能法益与我国处罚文书犯罪秉持的立场相融通。从我国《刑法》第280条的规定来看,只要行为人买卖的是国家机关公文,即可构罪,而无需对文书进行实质判断,由此可见,我国处罚文书犯罪所采取的是形式主义的立场。所谓形式主义,指的是文书制作的名义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文书制作的体式具有规范性,能够对外界展示出相关的法律效果;而实质主义指的是文书的内容为真实,而不问文书的制作名义、制作范式等。采形式主义之立场,就在于通过文书的外观保证文书的真实性,使文书固定的式样具有难以被伪造性等;另外,文书的形式主义也保证文书在法律交往中能够取得相应的公共信用,进而形成相应完备的文书制度。由此看来,文书的保证功能实质上衍生了文书之信赖力、保证了文书的真实性进而使其在法律交往中获得相应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并因此形成完备的文书制度,因而具有可采性。
结婚套取车牌指标案的当事人利用真实有效的文书到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变更过户,完全按照文书登载的内容进行相应的法律行为,以获得期待的信赖利益。由于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的法益是“文书的保证功能”,若当事人依照真实有效的文书进行法律交往,却不能获得期待利益,且要受到刑事非难,不但损及文书保证功能中有关公信力、文书的真实性、可靠性以及安全性等各项内容,还使得所形成的文书制度几近混乱。或许有人认为,以结婚为手段套取车牌小客车指标即便形式合法,实质却是一种损害社会大众利益的“买卖行为”。但即便主张实质刑法观的学者也认为,实质的犯罪论在建立形式的、定型的犯罪论的同时,还应建立以实质可罚性为内容的实质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是从实质上判定是否存在值得科处刑罚的法益侵害。(18)刘艳红:《实质刑法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5页。可见,其核心在于否具有值得刑法处罚性,本案当事人之行为是否具有刑事处罚性、“变更过户”是否具有“买卖”的性质,则有待进一步对构成要件进行解释。
三、本案中“通知书”“车牌”“变更过户”要素的界定
本案中的“民用机动车车牌”“小客车指标通知书”“变更过户”等要素,与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的构成要件要素相关,需要结合本罪之法益对其做进一步说明与解释。
(一)《××市个人小客车配置(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是国家机关公文
需要明确的是,想要购车上牌,需要先登录××市小客车指标管理调控系统参与小客车指标摇号,经过摇号,中签后下载《××市个人小客车配置(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该《通知书》由××市交通委下设的××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出具,是个人缴纳车辆购置税、外地车辆转入××市,办理车辆购置税档案转移、开具二手车销售发票、办理车辆赠与公证的必要凭证。本案当事人频繁结婚即是为了获取该《通知书》,因而对《通知书》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公文的解释,是认定“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的关键之一。
何谓“国家机关公文”,相关规范有详尽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发(2000)23号〕第2条规定:“行政机关的公文(包括电报,下同)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19)该规范由国务院于2000年8月24日印发,于2012年7月1日失效,但这仍对“国家机关公文”的定义具有借鉴意义。2012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公文条例》)第3条规定:“党政机关公文是党政机关实施领导、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公布法规和规章,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请示和答复问题,报告、通报和交流情况等的重要工具。”从上述规定来看,国家机关公文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公文是国家机关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等的重要工具和媒介;二是公文具有特定的效力;三是公文具有特定的规范格式。同时,《公文条例》第8条规定的15种公文类型中,明确“通知”是“适用于发布、传达要求下级机关执行和有关单位周知或者执行的事项,批转、转发公文”。
那么,《通知书》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公文?从“通知书”颁发机构来看,“××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设置机构是××市交通委,并由公安、发展改革、科技、经信等行政主管部门协助实施相应的职能。(20)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2020年《调控细则》)第4条的规定,“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小客车数量调控的统筹协调工作”。这说明,《通知书》的颁发机构“××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具有行政管理职能,该《通知书》是××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市民申请车牌指标等公务的重要媒介;从《通知书》的内容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在有效期内完成车辆登记手续,具有特定的规范格式,(21)《通知书》标示着指标编号、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业务类型、有效期等特定格式,其中还有特别提示“请您在有效期内办理完成车辆登记手续,逾期未办理完成的,视为自动放弃更新指标”。符合国家机关公文的特点;从《通知书》的效力来看,持有《通知书》的个人具有被授予及更换车牌登记手续的资格,有关执行机关应按照《通知书》内容为该个人办理手续,该《通知书》具有特定的效力;从文书的保证功能来看,《通知书》可以找到相应的归责主体,具有公信力,并能保障法律交往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等。综上所述,《通知书》具备国家机关公文的特征、功能与效力等,应认定为国家机关公文。
(二)民用机动车车牌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民用机动车车牌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有不同的见解。有论者指出,机动车号牌属于国家颁发的合法证件,只是一种交通标志,并不能证明机动车的身份,不能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22)杨晓:《甲、乙的行为是否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兼论同一位阶〈司法解释〉的适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7期,第88页。但相反观点指出,机动车号牌是国家机关颁发的法定标志,并能证明机动车的车主身份,宜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23)孙道萃:《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司法认定》,载《天津法学》2013年第1期,第79页。当然,还有类似的观点,参见杜文俊、陈洪兵:《文书伪造犯罪的构成要件解释论》,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105页。但该种观点的支撑理由是机动车车牌是一种法定标识,进而认为应将民用机动车号牌列为国家机关证件,并依据《刑法》第280条第一款的具体规定处理。然而,认定车牌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观点并未涉及车牌所承载的内容,仅从车牌的式样、标识等表面要素论证,值得商榷。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何谓“证件”,一般而言,证件是指国家机关制作并颁发的用以证明身份、职务、权利义务关系或其他有关事项的证明文件,如结婚证、工作证、护照、户口本、营业执照、驾驶证等。由此可知,证件是有权机关所颁发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证明文件,其核心要点是证件登载着相关的权利义务内容。(24)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8页。从这一点来看,民用机动车车牌并未记载相应的权利义务内容,而仅是便于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查询该所属车辆的登记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该车辆的所属地区、该车辆的主人等登记信息,是作为区分标识的牌照。由此看来,“民用机动车号牌不具备权威性”“民用机动车号牌不足以使公众对其产生合理信赖”,(25)仇晓敏、孙越:《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有关问题辨析》,载《人民司法》2019年第1期,第69页。进一步证实其仅是作为区分标识存在。此外,民用机动车车牌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相关司法解释亦有明确规定。其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证件”的范围是“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26)参见该司法解释第2条,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累计三本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累计达到第一款规定数量标准五倍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中的“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未将机动车车牌作为国家机关证件使用;其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伪造、变造、买卖民用机动车号牌行为能否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罚问题的请示》的答复明确指出,“伪造、变造、买卖民用机动车号牌行为不能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罚。”(27)其理由大致如下:第一,《刑法》第280条第1款规定了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第281条规定了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将警用车辆号牌归属于警察专用标志,属于警用装备的范围。第二,从刑罚处罚来看,将机动车号牌认定为证件,将使对非法买卖普通机动车号牌的刑罚处罚重于对非法买卖人民警察、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的刑罚处罚,这显失公平,也有悖立法本意。该司法解释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未将民用机动车车牌号码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可见,民用机动车车牌作为国家机关证件既无权利义务上的属性,也无规范上的依据,而且,本案相关当事人被公安机关以涉嫌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刑事拘留,从侧面印证了本案中的机动车车牌并非国家机关证件。
(三)“变更过户”不是本罪的“买卖”行为
在通过结婚套取车牌指标案中,当事人结婚后凭借《通知书》变更过户,待过户成功,双方旋即离婚,司法机关据此认为,频繁“变更过户”应认定为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中的“买卖”行为。因此,本案中的“变更过户”的认定,将成为本案当事人是否构罪的关键节点。
就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中的“买卖”而言,有观点指出,买卖是指购买或者出售国家机关制作或者应当由国家机关制作的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28)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8页。其中的核心要义是“购买”“出售”,同时,《辞海》还将“买卖”解释为“生意”。(29)需要注意的是,借鉴《辞海》中关于“买卖”的定义是为了准确在刑法领域内使用该词语,参见辞海在线查询,http://www.cihai123.com/cidian/1067315.html,2021年6月10日访问。另外,“买卖为主要之让与之债,其以对合同目标之财产权的有偿让与为主要给付义务之内容。其目标可区分为物、权利及不具权利地位而有财产价值之信息或无体财产或用管线供应之电、水、气体、热力等。”(30)黄茂荣:《买卖之目标及其〈民法典〉之合同类型的配置》,载《北方法学》2020年第5期,第19页。换言之,“买卖”本质是一种契约关系的表达,一则,《民法典》第595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据此可知,买卖合同是一种有关于物权交换的行为;从买卖合同的条文表述来看,买受人和出卖人之间的物权交换是一种“购买”“出售”行为,实质是一种契约关系。二则,“从契约法的角度而言,契约是交换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社会交往范式,它以法律的手段实现平等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合意平等、对价有偿、诚实守信,保证契约实现的有效,实现民事往来及商业贸易的有序与规范。”(31)魏琼:《契约文明起源考:以古代西亚为中心》,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3期,第108页。因此,买卖行为实际上是平等主体间对价有偿的契约关系。
但“过户”指的是当房屋、车辆及记名有价证券等动产或不动产所有权移转时,至相关机构办理更换物主姓名的手续。“过户”应具备如下几个要件:其一,过户是转移所有权的一种方式;其二,过户需要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其三,过户需要法定程序;其四,过户需要到相关的法定机构中进行。总之,“过户”是发生在行政机关与申请人之间的不平等主体间之法律关系,因此,“过户”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而非民事法律关系。
对此,不难发现,“过户”与“买卖”并非对应关系,一方面,“买卖”是以契约为表现形式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过户”是通过行政手段转变所有权的行政法律关系。另一方面,“买卖”的核心是购买、出售,而“过户”的核心是申请—转移所有权。可见,二者并不相同。因此,本案的“变更过户”并不是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中的“买卖”要素。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本案有《婚前协议书》与《××市车牌指标过户服务协议》两份协议,可能有人据此认为,本案当事人以结婚为手段获得的车牌指标实质上是买卖车牌的行为,且《××市车牌指标过户服务协议》是一种买卖合同,合同之目标物是转让车牌指标之权利,这符合买卖中“购买”“出售”的要件。但这种见解不无疑问,从实质上来看,《××市车牌指标过户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在当事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夫妻一方的车牌过户。(32)据“黑中介”介绍,“签订协议后,先交定金,领结婚证后付一半的钱,尾款在车辆行驶证变更之后支付,整套流程完成后,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参见:《北京市车牌“黑市”:“闪婚闪离”背后的灰色买卖》,载中新网2020年12月9日,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0/12-09/9357684.shtml。这并不是一种契约关系,而是夫妻间转移相关权利的行为。即便当事人与“黑中介”签订了协议,但该协议应视为当事人对婚前婚后相关财产的约束。也有人会认为,协议中的对价即是买卖的对价,因为协议明确记载当事人在车牌过户之后可以获得相关的酬劳。然后据此认定本案当事人构成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中的“买卖”,诚然,取得“对价”确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但不能认为有对价即是买卖行为。本案的协议实际上是变更过户协议,当事人取得《通知书》后获得更换车牌指标的资格,依此《通知书》可在婚姻存续期间以法定程序变更过户,可见,这一行为并未侵犯本罪文书的保证功能之法益,也不是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的构成要件要素。然而,此行为方式既然不是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中的买卖行为,却也存在欠妥之处,亦即当事人之行为是否还违反其他法律,这涉及违法性的问题,值得探讨。
四、本案及类似案件中缓和违法性一元论的运用
对于违法性的判断,在刑法体系上具有重要的功能,简而言之,违法性的判断,主要在于判断犯罪是否成立。行为若不具有违法性,则犯罪不成立;行为具有违法性,则需要进一步检验罪责问题。(33)林钰雄:《新刑法总则》,元照出版社2019年版,第228页。因此,对于违法性的判断,将涉及该行为是否违法甚至是否构罪的判断。这对本案违法性的判断尤为重要。然而,不同法域之间的违法性判断是秉持违法性一元论还是多元论的立场,在民法典时代尤为重要,将是妥当解决民刑交叉、行刑交叉案件的重要方法。
(一)民法典时代缓和违法性一元论之提倡
违法性是要在不同法域“一元”地把握,还是可以“相对”判断,对此,德国学者罗克辛将上述违法性判断理念之间的对立概括为两个命题:(1)在刑法中,民法性的或者公法性的许可或者侵犯权,是否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排除一个符合行为构成的举止行为的违法性?(2)一种对确定举止行为的民法性的或者公法性的禁止性存在,是否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举止行为一旦同时满足了一个刑法规定的行为构成,也就表现了刑法上的不法?(34)罗克辛认为,一个在民法上或者公法上被禁止的行为,在同时满足了一个行为构成时也应当受到刑事惩罚的做法,既不能显示这种考虑的必要性,也并不总是能够显示出刑事政策来的。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页。罗克辛认为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肯定,然而,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不能一概做肯定回答。这体现了其缓和违法一元论的观点。但当前德国的主流理论是违法统一论(违法一元论),(35)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3版),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15页。违法一元论认为,违法是对整体法规范、整体法秩序的违反;而日本的主流观点是“违法相对性论”,即各种法律基于其固有的目的,而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36)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3版),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15页。在“违法相对论”的内部又有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与多元违法论。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认为,在某个法域中属于违法的话,虽不意味着在刑法上变成了不违法(基于法秩序的统一性的违法一元性),但为了肯定成立刑法上的犯罪,必须具备适于处罚的质和量上的违法性,不单是在失去一般意义上的违法性的场合如此,若失去此种意义上的“可罚的违法性”,则应该否定犯罪的成立。(37)山口厚:《刑法总论》(第3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7-188页。违法相对论基于违法多元性,认为根据法域的不同,违法性的评价亦不同。(38)前田雅英:《刑法総論講義》(第4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第91页以下。违法究竟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两者的对立点在于:究竟是否有贯通所有阻却违法事由的统一原理存在?但阻却违法的原理不仅系阻却违法事由的解释原理,其亦可作为违法与适法界限的一般原理,阻却违法共通原理与此一般原理属于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此,有论者认为,阻却违法原理应以社会相当性说为基础,而以目的说与利益衡量说为辅助原则,将此三种理论根据结合而形成各种阻却违法事由的理论根据。(39)余振华:《刑法总论》(修订3版),三民书局2017年版,第241页。这种理论根据的确立,实质上是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缓和的违法性一元论具有适用价值。
民法典时代呈现出大量的民刑、行刑交叉案件,本案即呈现典型的民行、行刑交叉事项,这涉及不同法域间违法性判断问题。其一,缓和违法性一元论中的法秩序统一之原理显得尤为重要。一般认为,法秩序要具有统一性,即由宪法、刑法、民法等多个法领域构成的法秩序之间互不矛盾,更准确地说,这些个别的法领域之间不应作出相互矛盾、冲突的解释。(40)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补正版),钱叶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因此,以刑法处罚其他法域、特别是民事法上被允许的行为,从刑法的最后手段原则来看,是不妥当的。其二,缓和违法性一元论的目标在于,对于刑法之外的法域被认为不属于违法的行为,否定其刑法上的违法性;对于在刑法之外的法域中被认为属于违法的行为,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刑法上违法性的特殊性(可罚的违法性),该行为仍可能在刑法上并不违法。(41)山口厚:《刑法总论》(第3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8页。如此一来,可以衔接不同法域间的违法性问题,坚持违法一元论的基本立场,并在法秩序作统一解释下避免向民众发出法律规范内容混乱的提示,使民众之行为具有可预期性。“由于民法与刑法所共同关注的基本生活事实是一致的,……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刑法可能需要以之为基础对相关概念进行重新但又不一定等同于民法的解释。”(42)刘艳红:《人性民法与物性刑法的融合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120页。从这一点来看,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的观点在民法典时代也是妥当的。
(二)缓和违法性一元论的运用
首先,缓和的违法性一元论助推犯罪概念的更新,并结合犯罪之概念具体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之坚守。缓和违法性一元论所要求的是,肯定成立刑法上的犯罪需要具备适于处罚的质和量上的违法性,质和量上的违法性即是某行为是否具有值得刑罚性。而犯罪的概念一般是指被科处刑罚的行为。但这里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犯罪属性之内涵。有论者指出,“被科处刑罚”的属性,可以称之为“可罚性”。可罚性内涵了“当罚性”与“要罚性”,而且,要尽可能地将根据合目的性的观点考察行为是否符合刑罚这种法律效果的“可罚性”考虑纳入“犯罪”概念内部,并且作为实质性构成要素的违法性或者责任的领域,才是最理想的。(43)松原芳博:《犯罪概念和可罚性:关于客观处罚条件与一身处罚阻却事由》,毛乃纯译,冯军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要罚性”与“当罚性”实质上是缓和的违法性一元论质与量的要求,两者是吻合的。就“质”的方面而言,由于刑法具有强烈的制裁效果,发动刑罚应充分考虑当事人之行为是否侵害法益,并具有值得刑罚性,这是达到违法性“质”(要罚性)的要求。由此体现刑法之谦抑性,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从“量”的方面来说,达到犯罪程度而应科处刑罚之违法性,必须达到“当罚性”的程度。
其次,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可以使立法者、司法者在整体法秩序指引下做出合法合理的解释。在缓和的违法性一元论看来,违法乃是当事人之行为与法规范间对立冲突的事实,其行为已显现对于“法规范所宣示的禁止及诫命”的敌对状态,亦即违法系指行为人所为的行为与整体法秩序冲突,行为不违法则指该行为与整体法秩序并无冲突。(44)余振华:《刑法总论》(修订3版),三民书局2017年版,第227页。缓和的违法性一元论作为违法统一性的解释指针,对同一行为在不同法域中的违法性具有统一性的解释机能。在运用缓和违法性一元论解释某行为违法问题时,可以发挥对现行法的批判检讨功能,以节制刑罚的扩张,充分利用刑法之外的其他法律作为规制手段,尤其是当立法者欲制定或者删除某一刑法罪名时,完全可以从违法论的角度,考虑该行为是否有其他法律予以规制或者运用其他法律规制能否达到与刑罚规制一般的效果,换言之,民法典时代,可以从缓和违法性一元论的思辨进行理性沟通,迫使立法者或者适法者阐明法条的立法背景、立法理由、适法缘由等,以便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并在适法时合法合理合情。民法典时代的立法,应汇集对某一事件是否违法,是否值得刑罚性等方面的不同智识,凝聚合理的立法政策共识。就刑法领域而言,根据法秩序的统一性和无矛盾性,刑法上各种公私权利的所有容许和豁免,基本上都可以起到正当化事由的作用。但也有例外情形,由于刑法乃是有着特殊要求的特定法律领域,因此,刑法上适用的正当化事由,并不总能适用于其他法律领域。(45)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第6版),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156页。也就是说,某行为虽然不构成相应犯罪,但基于法秩序统一的观点,该行为可能违反行政法或者民法等法律规范,由此可以使违法的认定全面而具体。
而且,从整体法秩序或者从所有的法领域而言,违法性虽然具有统一性质,但由于不同法域间的违法性之形式存在不同类型与不同的轻重程度,因此各个法领域间对违法性的要求也就不同。特别是在民法典时代,案件呈现违反不同法域之交错现象,某一行为呈现出违反整体法秩序的情况,而民法、行政法乃至刑法所要求的违法性程度有所不同。这恰与缓和的违法性论的观点吻合:具有刑法上违法性的行为,通常在其他法域内同样会被认为具有违法性,然而在其他法领域内被认为具有违法性者,在刑法上则未必具有可罚的违法性。正如论者指出,因为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有助于我们将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等主要法域的相同或相似的概念放置在同一个理论基点上进行审视和评价,在法律领域形成统一的尺度,并可对社会生活进行普遍和统一的调控;当然,基于社会分化和法律分化的基本要求,考虑不同法域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上的独特性,坚持各法域追求法律目的之自主性,能够在法秩序的统一性和违法判断的相对性之间找到一个适中的平衡点。(46)王昭武:《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第177页。总而言之,所谓的法秩序一致性其实是为了让多数法规范的适用之间取得一种“符合实际(sachlich)的协调关系”。(47)Demko,Zur Relativität der Rechtsbegriffe,2002,S.154.同时,这也有助于对某一行为先做整体法秩序的违法性评价,再进行是否值得刑罚性的可罚性判断,以此彰显民法典时代违法之统一性机能。
具体到本案而言,本案当事人的变更过户、频繁结离婚等行为,一方面没有达到刑事违法性所要求的“质”与“量”,刑事要罚性与当罚性存疑;另一方面,在缓和违法性一元论看来,频繁结婚套取车牌指标一定程度上扰乱了车牌管理的公共秩序,侵害了他人获取车牌指标资格的权利,在法秩序整体上存在违法的可能性。因此,本案当事人的行为虽不具备刑事违法性,但违反了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规范,其应承担何种责任,仍须继续判断。
五、本案中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承担
在出罪之后,本案当事人的结离婚、套取车牌指标之行为等需继续分析,以便确定其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
(一)结婚离婚行为之分析
本案当事人频繁结婚、离婚,并以此为手段套取车牌指标。成立婚姻关系仅是为了利用法律漏洞获取车牌指标,并非真实地长期共同生活、组成家庭的正常婚姻关系。有人据此认为该行为是“通谋虚伪婚姻”。所谓通谋虚伪婚姻,系指男女双方缔结婚姻时约定不建立婚姻共同生活的情形,其特点是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属于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的情形。(48)金眉:《论通谋虚伪结婚的法律效力》,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3期,第183页。通谋虚伪婚姻的本质应是一种虚伪行为,而虚伪行为的认定,将直接关系到通谋虚伪婚姻的法律效力问题。
对于虚伪行为,有学者指出,在虚伪行为中,表意人仅仅是虚假地发出了一项需受领的意思表示,而受领人对此是同意的。在这里,双方往往不仅对这种保留心照不宣,而且还着意加以约定:表示出来的内容不应产生法律效力或成了法律行为的内容。(49)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46页。也有学者认为,虚伪行为通常是指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之的虚假的意思表示,虚伪行为具有如下三个要件:一是表意人与相对人为虚伪的意思表示;二是双方当事人明知对方为虚伪的意思表示;三是双方认可虚伪的意思表示。(50)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王泽鉴:《民法总则》,作者自版2020年版,第386页。可见,虚伪行为具有两个意思表示,一个是表面的意思表示,且这个意思表示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相关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另一个则是存在于当事人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并非为他人知晓,是一种“灰色”的表意。
对于通谋虚伪婚姻的效力,学界有三种观点:其一,无效说,即虚假婚姻就是虚假民事行为,应当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51)杨立新:《对修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30个问题的立法建议》,载《财经法学》2017年第6期,第7页。其二,可撤销说,认为为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宜将双方当事人无意建立家庭、履行婚姻共同生活义务的虚假婚姻,作为可撤销婚姻;(52)陈苇:《亲属法与继承法专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其三,有效说,由于法律规定了结婚的自愿性要件,应采“意思表示主义”,男女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即可证明婚姻有效,不应有其他条件;登记之后婚姻始为有效,而不论其结婚之目的。(53)王礼仁:《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页;[日]栗生武夫:《婚姻法之近代化》,胡长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具体到本案,当事人的结婚是否为通谋虚伪婚姻或者假结婚。在本文看来,当事人之婚姻当属有效,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本案当事人基于自愿结婚,符合《民法典》第1046条“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之规定,结婚有效;同样,离婚亦属有效,《民法典》第1076条“协议离婚”、第1078条“离婚登记”均规定了离婚应当“自愿”,本案当事人自愿离婚,婚姻登记机关在查证当事人自愿离婚后发给离婚证。且当事人并无禁止结婚、婚姻无效、受胁迫结婚、隐瞒疾病的可撤销婚姻等情形。可见,当事人的结婚、离婚均符合法定要件。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结婚、离婚只需自愿并于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即可有效,并不要求追求当事人之结婚、离婚的内心意思表示,婚姻登记机关询问当事人结婚、离婚之内心意思既不可能,也难以实现。相反,由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当事人结婚、离婚的内心真实意思表示,将有违《宪法》第49条规定的“禁止破坏婚姻自由”之意涵,同时也将破坏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显然,并不能一方面倡导婚姻自由,另一方面却又去追寻结婚之内心真实意思表示,并以事后查明的内心意思来否定婚姻之效力,尽显矛盾,更不利于婚姻自由。
其二,我国现行法制体系中,并没有明确的假结婚概念。假结婚虽然可以作为婚姻无效或者可撤销的理由之一,但是很少有关于假结婚特别详细的规定,尤其是所谓通谋虚伪婚姻,现行法制并未涉及。且成文法上也很少规定真假结婚的标准,民法典也只是规定了婚姻成立的要件。传统上也未将假结婚作为法律概念。据此,认定本案当事人为通谋虚伪婚姻或者假结婚,并无规范上的依据。
其三,结婚是否就意味着组建“家庭”,或者说,结婚必然代表着婚姻的形成;这里涉及到“家庭”与“婚姻”的概念,但这些概念随着社会变迁和权利的扩张而变得模糊。例如,欧洲各国近年来身份法的发展,演变成一种“共同生活契约”(民事凝聚协议,PACS),冲破了传统的“家庭”与“婚姻”对结婚、离婚的框定。“共同生活契约”在身份关系、财产制度、社会保险和税收方面,都有别于“异性婚姻”组建的家庭,是一种新的社会组成单位,(54)See Stephen Ross Levitt,New Legislation in Germany concerning Same-Sex Unions,7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469,2002;Greg Taylor,The New Gay and Lesbian Partnerships Law in Germany,41 Alberta Law Review 573,September 2003.亦即只要当事人之间具有共同生活的意向,并建立共同生活契约,即可受法律保护,这类似于我国的“事实婚姻”;另外,虽然“家庭”是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之亲属团体,但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冲破了“家庭”的固有属性。例如,浙江等地出现的“两头婚”(55)所谓“两头婚”即是近年来在江浙一带悄然兴起一种新的婚姻形式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小夫妻成家后依旧与双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通常各住各家。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小孩,第一个随父姓,由男方抚养为主,第二个随母姓,由女方抚养为主。参见陈广江:《对“两头婚”无需“捧杀”或“棒杀”》,载光明时评网2020年12月22日,https://guancha.gmw.cn/2020-12/22/content_34484748.htm。并未组建传统的以共同生活为目的之家庭。亲历“两头婚”的基层妇联工作人员表示,这类家庭后续矛盾相对少。(56)喻琰、严兆鑫:《亲历“两头婚”的基层妇联工作人员:这类家庭后续矛盾相对少》,载澎湃新闻网2020年12月2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490688。基于此,若仍以组建共同生活家庭关系为婚姻之核心,显然不利于社会婚姻模式之变化发展。
其四,实务中即便对所谓的“假结婚”骗取拆迁款、彩礼等行为认定为犯罪,但并不据此认定婚姻无效。(57)参见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2015)濮刑初字第381号刑事判决书;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人民法院(2019)新4221刑初105号刑事判决书;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2017)豫1426刑初396号刑事判决书;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2018渝0237刑初138号刑事判决书;等等。可见,本案中的当事人之婚姻并非无效。而且,本案当事人之所以通过结婚手段套取车牌指标,是因为《〈XX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2017年《调控细则》)第33条规定:“已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为个人的,因婚姻、继承发生财产转移的已注册登记的小客车不适用本细则。”这意味着,婚姻期间(不论时间长短)对车牌指标变更过户的,应适用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规范;而当事人按照该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的行为,完全符合相关政策要求,并无不当。
(二)民事责任之承担
尽管本案当事人婚姻有效,但其通过结婚手段套取车牌指标的行为显然违背公序良俗原则。一方面,当事人通过合法婚姻获取不属于自己的相关公共产品,已然损害本属于他人获得的车牌指标之机会;另一方面,本案当事人利用法律规范的漏洞(2017年《调控细则》)套取车牌小客车指标,明显违背公序良俗。公序良俗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基本原则,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以及基本道德、落实社会核心价值的基本原则,所谓社会公共秩序或社会性价值,也就是社会共同体利益;在刑法上的表现即是集体法益。(58)刘艳红:《公私法一体化视野下公序良俗原则的刑法适用》,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4期,第144页。按照该种见解,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章中的罪名,即是集体法益中的典型内容,并进一步阐明,刑法典第六章是公序良俗的刑事立法化之体现,这也印证了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案例大都发生于本章罪名中。但是否可以据此认为,本案当事人违反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即可认定为侵害刑法之集体法益?然而,民法之公序良俗原则在刑法适用的功能应定位为弱调节性补充原则。(59)刘艳红:《公私法一体化视野下公序良俗原则的刑法适用》,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4期,第147-148页。虽然公序良俗原则在民法解释中的查漏补缺功能,也可以运用于刑法适用中,但这种解释功能不能逾越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定,在运用公序良俗原则解释刑法个案时,一方面可以弥补刑法构成要件不明确的缺憾,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个案正义的实质解释原则,嫁接个案正义与普遍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因此,并不能认为违背民法之公序良俗原则,即为侵害刑法上的集体法益,而受到刑罚处罚。加上公序良俗原则的抽象性、不确定性、伦理性、主观性等特质,基于民法公序良俗原则与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天然的违和性,应尽量在出罪时运用公序良俗原则。(60)刘艳红:《公私法一体化视野下公序良俗原则的刑法适用》,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4期,第149-150页。正如前述,本案当事人之行为并未侵犯法益。但通过结婚手段套取车牌指标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对于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民法典》规定了其效力及承担责任之方式。《民法典》第8条规定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第132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第153条第2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179条则规定了“停止侵害”等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61)第179条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继续履行;(八)赔偿损失;(九)支付违约金;(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一)赔礼道歉。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由此可见,本案中当事人变相获得的车牌指标,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当属无效。另外,于2020年《调控细则》对这类行为有详细规定,即第五章“监督和失信责任”提到,存在买卖、变相买卖小客车指标确认通知书行为的,将公布指标作废,三年内不予受理指标申请。对于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所获得的车牌指标,该实施细则所规定的“作废”,实质上是对《民法典》“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实践贯彻。因此,当事人所获得的车牌指标更新通知书作废之后,其过户车牌之行为也就相应的无效。另外,2020年修订的《实施细则》也规定,夫妻间办理车辆变更登记、离婚析产办理车辆转移登记时,婚姻关系须存续期满一年且受让方名下没有本市登记的小客车的,方可转移登记。(62)参见2020年《调控细则》第22条、第33条、第35条。这是对频繁结婚、离婚的限制,是下位法律规范对上位法实施过程中的细化。当然,XX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以要求相关当事人停止侵害,并赔偿频繁申请车牌指标所造成的损失,以便消除行政主管部门因当事人频繁申请而造成的恶劣影响,以恢复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
(三)行政责任之承担
当然,本案当事人责任承担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责任?而本案承担行政责任的核心要素是“变更过户”以及“频繁结婚、离婚”,对此,需详细分析。
首先,“变更过户”是在车管所进行的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行为。而车管所隶属于公安交通管理局,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限。本案当事人通过2017年《调控细则》中有关夫妻间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进行车辆过户之漏洞频繁过户,其行为扰乱行政管理秩序。从宏观上来说,频繁将个人拥有的车牌指标变更过户给多人,其本质是变相地转让行为,该转让所浪费的行政管理资源也是一种“变相”地扰乱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之行为,更是变相地攫取社会公共资源,打破了正常的过户秩序;从微观上来说,当事人利用个人的车牌指标变更过户,损害他人获得车牌指标的机会或者资格,属于损害社会一般人利益的行为。总之,变相的变更过户行为既扰乱社会公共利益,更损害社会一般人的合法权益。这完全可以适用行政处罚法之规定,通过减损当事人之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63)参见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7月15日实施)第2条的规定,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另外,本文所指的《行政处罚法》乃新法。同时,2020年《调控细则》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所获得的车牌指标按照“作废”处理。这是符合《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的种类与设定”之规定的,《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警告、罚款等具体种类,第9条至第14条则规定了不同行政法律、规章以及地方性规范文件等可以设定相应行政处罚的范围与种类,其中第13条规定了省级政府以及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是由××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其中第7条规定了“指标有效期为12个月,不得转让”,并在该条规定了“取得的指标无效”之情形,(64)参见《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第7条,指标有效期为12个月,不得转让。指标有效期内,不得重复办理配置指标申请登记。单位和个人(含家庭申请人)对办理指标申请时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提供虚假信息的,取得的指标无效,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2020年《调控细则》“指标作废”“亲属关系存续满一年”等即是对暂行规定第7条的细化,其设定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按照2020年《调控细则》设定的罚则可以达到与刑罚处罚相同甚至更好的效果,一方面,使违规获得车牌指标“作废”,另一方面,车牌指标被作废之后,相关责任人三年内不得提出指标申请。这既有指标作废的行政处罚,又有申请时间的限制,特别是三年内不得提出指标申请,是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的进一步细化。更确切地讲,这是对《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吊销许可证件”的细化规定,按照《行政许可法》第12条的“公共资源配置”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规定,对车牌指标按照“申请—许可”的方式进行配置,当事人利用法律漏洞获得的车牌指标,完全可以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吊销许可证件,亦即作废处理。
其次,对于频繁结婚、离婚的行为,民政局等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做出一定的限制。当然,由于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因而民政局等行政机关并不能以当事人频繁结婚、离婚为由对其按照《行政处罚法》相关的罚则进行处罚。但是可以适用民法典中婚姻家庭编第四章关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即《民法典》第1077条“离婚冷静期三十天”之规定,在当事人频繁离婚时,行政机关可以适用该条款对其劝诫。近日,上海市政协委员提议“结婚前应该设置结婚冷静期”,(65)林上军:《结婚也不妨试行冷静期》,载新华网2021年1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1-01/19/c_1126997555.htm。以保障婚姻登记生效前给予配偶获取信息披露的知情权及其他权利。这或许可取,以便给频繁结婚、离婚行为设定一定的期限,从时间上限制当事人的频繁婚姻,从而使其不能利用地方性规范文件的漏洞寻得不应有之利益。也就是说,XX市民政部门完全可以按照婚姻冷静期限制当事人的频繁结婚、离婚,从而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限制当事人利用婚姻关系频繁变更过户,减少此类规避法律规范之事件发生。同时,2020年《调控细则》所规定的配偶作为车牌指标受让方的,其“亲属关系存续满一年”方能转让,实质上也是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限制,以便遏制通过频繁的婚姻关系套取车牌指标的行为。
六、结语:民法典时代更应发挥刑法之谦抑价值
在本案中,当事人频繁结婚、离婚套取车牌号码,通过民法典规定的承担责任方式、离婚冷静期、相应行政法规规定的亲属关系存续期间、行政处罚罚则等限制过户车牌指标、“作废”处理,并在三年内不得申请车牌指标。这已然使频繁结婚、离婚套取车牌指标的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已经对“文书的保证功能”之法益达到了与刑法保护相同的效果。这充分说明,民法典时代,民法要扩张,刑法要谦抑。(66)王利明:《民法要扩张 刑法要谦抑》,载《中国大学教学》2019年第11期,第34页。刑罚制裁是法律制度中最严厉、最痛苦的方式,是法律制裁的最后手段。在不动用刑罚手段同样能够达到制裁目的时,刑法自当“退让”。因此,只要存在其他对法益能够产生同样保护效果的手段(如民法、行政法)时,刑法就不应扮演保护法益的法律手段。(67)许泽天:《刑法总论》(初版),新学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6页。因而,对于该类案件,由刑法规制并不是最佳手段。从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可知,刑法对社会共同生活的行为与秩序之规制功能仅是片面性的。
对现代社会而言,许多人常盲目地相信或期待刑罚制度可以像万灵丹一样,解决所有眼前恼人的社会问题。其实,这样的错误期待,常让刑事法学者感到不安与无奈。(68)王皇玉:《刑罚与社会规训:台湾刑事制裁新旧思维的冲突与转变》,元照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当前,《民法典》正全面而稳健地施行,不仅可以有效缓和刑法的“肥大化”,而且通过《民法典》的相关责任条款进行制裁也能获得良好的效果。例如,某检察机关根据《民法典》第1036条的规定,将出卖公开的企业信息谋利之行为不认定为犯罪。(69)卢志坚、白翼轩、田竞:《出卖公开的企业信息谋利 检察机关认定行为人不构成犯罪》,载《检察日报》2021年1月20日,第01版。但若仅根据相关司法解释(70)即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规定,则该行为人之行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由此可见,正确适用《民法典》也是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得到正确发挥的有效途径。在“追求社会安定秩序”的气氛催化下,更要坚定地摒弃刑罚万能主义,而充分运用非刑事措施指导社会治理。推崇运用刑罚进行社会治理,免不了会使刑罚轻重失去尺度,最终忽略刑罚剥夺个人生命、自由、财产的本质,甚至把个人贬抑成为为达虚幻的预防犯罪目的之工具。这显然与刑法的谦抑原则相背离。正如刘艳红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人性民法的映照下,如何防范和尽可能减少刑法工具主义对法治的危害,化去物性刑法中可能存在的违背人道、人本、人文的理念、立法及制度,成就物性刑法的人性化,无疑是当下刑法学所应认真思考的问题。”(71)刘艳红:《人性民法与物性刑法的融合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120页。可见,刑法不应成为替代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管理法、危害防治法、最先保障法。(72)刘艳红:《实质出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4-97页。违背刑法谦抑主义将导致刑法的早期化,挤占民法典等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由此产生的刑罚万能主义进一步得到扩展,显然违背民法典时代的刑法谦抑价值,并不可取。因此,民法典时代,更应彰显刑法之谦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