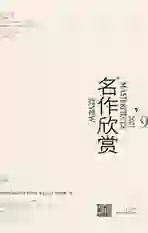元好问诗歌通释三则(十四)
2021-09-15查洪德
摘 要: 这三组诗都作于金亡之后。《俳体雪香亭杂咏》写汴京城破后诗人入览宫中所见。庄严神秘之宫,满怀深创巨痛,却以俳体写来,以笑言痛,读之令人悲戚动容。《癸巳五月三日北渡》写诗人亡国后被押往羁管地聊城路途所见。诗人以诗史之笔、绝句之体,记录亡国惨痛,以及战争造成的生灵灭绝,田园废弃,文化、社会、经济遭受的毁灭性破坏。从细节到全景,笔力非凡,字字泪血。《自题中州集后五首》是《中州集》编成后的题诗,说明编纂宗旨,寄寓内心感慨。诗人对比南北,彰显北方诗的价值。这组诗不仅是论诗文献,作为诗来欣赏,也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气盛格高,简洁准确,深切动人。
关键词:元好问 丧乱诗 《中州集》 论诗诗
《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选六)
这组诗题《俳体雪香亭杂咏》,很特别。俳体,俳谐体,本义是一种诙谐幽默、蕴含讽谕的游戏之作,杜甫有《戏作俳谐体解闷》诗二首。元好问借用这一题目,以戏语寓深慨。雪香亭,是金后宫深处的一个亭子,按杨奂《汴故宫记》:“纯和殿,正寝也。纯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可知雪香亭的位置。元好问本诗题下注:“亭在故汴宫仁安殿西。”所指位置同。天兴二年(1233)四月,崔立献城投降,在金后妃出宫后,诗人入览宫中,满怀深创巨痛,写了这组丧乱诗。丧乱诗的沉痛,故国宫廷的庄严,从这两个方面说,都不应该与“俳体”即俳谐相联系。也许在元好问心中,加上“俳体”二字,写到故国内宫时,可以不必那么神圣与庄严;特别是涉及一些批评性的语言,可能容易被接受些。另一方面,他似乎要以诙谐言痛楚。以笑言痛,让人感到,那是心底流血。
内宫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国破后,元好问才有机会进入,看到内宫诸多建筑,其中传说中的雪香亭以及周围之景,不管是依然如故还是经乱残破,对元好问来说都是很大的刺激,由此触动情感,写了这些诗,放在一起,作为一组诗,题名“雪香亭杂咏”。所谓“杂咏”,即这些诗之间不一定相互关联,所以未必一定都是写雪香亭,也不一定全与内宫有关,第一首“沧海横流万国鱼”,第三首“落日青山一片愁”,就无关乎内宫。但每一首都因国家败亡而作。本组诗十五首,这里选六首。
第二首:
洛阳城阙变灰烟,暮虢朝虞只眼前。
為向杏梁双燕道,营巢何处过明年。
洛阳,东汉时的京城,这里代指汴京。汴京变成灰烟,指都城被焚毁。暮虢朝虞,即虢和虞的灭亡只在朝暮之间。虢与虞都是西周诸侯国,《公羊传·僖公二年》载:晋献公拟攻虞与虢,担忧的是“吾欲攻郭(虢)则虞救之,攻虞则郭(虢)救之,如之何?”谋臣荀息献计,先向虞借路灭虢,回程即可灭虞:“君若用臣谋,则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尔。”这二句是说,汴京已破,哀宗所在的宋州,恐怕也朝夕不保。听口气,似乎在讲历史故事。后两句,杏梁,指文杏木所制的房梁,显示屋宇的华贵。晏殊《采桑子》词:“燕子双双,依旧衔泥入杏梁。”营巢何处,即何处营巢,意思是汴京的城阙宫殿都毁于战火,燕子也无处可营巢了。不说人无居所,而说燕子无处筑巢,这体现的就是“俳体”特点。在元好问心里,对于国破,真是如此淡漠吗?绝非。因为他从燕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不知自己将栖身何处,何以度日。不忍正面言说才以物代人。
第三首:
落日青山一片愁,大河东注不还流。
若为长得熙春在,时上高层望宋州。
大河,黄河。陆机《赠冯文罴》诗:“发轸清洛汭,驱马大河阴。”熙春,指汴京城中的熙春阁,建于北宋徽宗年间。元陆友仁《研北杂志》:“汴梁熙春阁,旧名壶春堂,宋徽宗称道君时居撷芳园中,俗呼为八滴水阁。”刘祁《归潜志》载,蒙古军围汴京时,城中楼亭多拆为防御之材,“所存者独熙春一阁耳”。宋州,归德府,在今河南商丘南,当时金哀宗驻宋州。这一首的表达方式很特别,是诗人登上熙春阁所见所思,但“熙春”二字在第三句才出现。前两句都是登阁所见,登阁西望,“落日青山”,金帝国大势已去,留下的只有“一片愁”。转首东望,“大河东注”,逝者如斯;“不还流”,历史不能倒行,逝去的永远逝去了,历史就是如此残酷。“若为长得熙春在”一句,含义太丰富了。“熙春在”,汴京多少亭台楼阁都已拆毁烧烬,唯余“熙春在”,一片废墟中孤零零的熙春阁“在”(熙春阁之外的无数楼阁都已不“在”),是欣慰还是哀痛?“若为长得”,熙春阁能“长”“在”吗?更重要的是接下来“时上高层望宋州”,汴京破了,哀宗皇帝在宋州,似乎还为金国存一丝希望,所以元好问想时时“望宋州”。但前提是,不仅熙春阁要“在”,在宋州的朝廷也要“在”,他才会“望宋州”,但事实上,这两者恐怕都不会“长”“在”,“时上高层望宋州”只是他的愿望,“若为”,若是。若是长得,隐含之意的不能“长得”。
第八首:
杨柳随风散绿丝,桃花临水弄妍姿。
无端种下青青竹,恰到湘君泪尽时。
第十一首:
罗绮深宫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谁妍。
人生只合梁园死,金水河头好墓田。
第八首和第十一首都是有关后宫女性的。第八首用象征手法,第十一首则直接说破。
第八首,杨柳、桃花既是宫中景物实写,也比喻后宫无坚贞之质的女性。妍姿,娇妍的姿容。唐沈既济《任氏传》“: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末句用典。湘君,湘水之神,相传为尧之女、舜之妃。晋张华《博物志》载:“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这句是说,宫中所种都是青竹而无斑竹,因为湘君泪已流尽,无泪洒于竹上,隐喻金宫后妃已泪尽而亡。第十一首,罗绮深宫,代指宫中奢华的生活。二十年,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自燕京迁都汴京,至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汴京沦陷,整二十年。桃李,比喻女子美色。曹植《杂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蒋子正《山房随笔》引此句作“更将颜色向谁怜”,颜色指容貌。梁园,即梁苑,西汉梁孝王的东苑,故址在今开封东南,即汴京所在地,故用以指汴京。宋陈师道《骑驴》诗之二:“独无锦里惊人句,也得梁园画作图。”任渊注:“梁园,指汴京。”金水河,此金水河在汴京西。《河南通志·开封府》:“其上源即荥阳之京水也。宋建隆二年,命将军陈承昭凿渠引水,过中牟,凡百余里,抵都城。”
第八首是讽刺,第十一首是赞美。诗人讽刺宫中的“杨柳”与“桃花”都无坚贞之节,她们不管城破国亡,只知道搔首弄姿,这是对那些乐于被玩弄的宫人的无情讽刺。宫中也有“有节”的竹,国破君迁,后宫之“竹”没有像传说湘妃竹那样变成斑竹,因为后妃们已经泪尽且被掳,没有泪溅竹上。诗人赞美那些殉国的后妃。元人蒋子正撰《山房随笔》载:“金国南迁后,国浸弱不支,又迁睢阳。某后不肯播迁,宁死于汴。元遗山曰:‘桃李深宫二十年,更将颜色向谁怜。人生只合梁园死,金水河边好墓田。”“更持桃李向谁妍”(更将颜色向谁怜),“更”是疑问表否定,意思是说“怎还能”。她们的选择是死在汴京,葬在京郊,绝不离开生活了二十年的汴宫。这样的悲壮,元好问也以“俳谐”道出。
第十三首:
暖日晴云锦树新,风吹雨打旋成尘。
宫园深闭无人到,自在流莺哭暮春。
锦树,春日花开似锦之树。杜甫《锦树行》:“霜凋碧树待锦树。”旋,旋即,立刻,瞬间。宫园,这里指后宫。《敦煌变文集·八相变》:“太子恒在宫园,不知世间之事。”自在,安闲舒展貌。流莺,即黄莺,“流”言其鸣声圆润流转。到这一首,诗人才写到内宫遭受摧残后的破败。原本的春日锦树,花繁叶茂,经过叛乱的“风吹雨打”,立即“成尘”。其实树并未“成尘”,“成尘”是元好问的心理感受。原本豪奢、神秘的内宫,现在竟寂无人迹,流莺在暮春哀鸣啼哭。莺没有“哭”,是诗人听来像“哭”,因为诗人的心在哭,听到的一切声音都如哭声。
第十五首:
暮云楼阁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
白发累臣几人在,就中愁杀庾兰成。
古今情,古今兴废盛衰引发的伤怀之情。地老天荒,天荒地老,形容经历时间之长久。李贺《致酒行》:“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累臣,被异国拘系的臣子。庾兰成,六朝诗人庾信,字子山,小字兰成。他初仕梁,后出使西魏,正值西魏灭梁,被留用。元好问以之自况。这一首是这组诗的总结,最后归到诗人自身。眼前暮云中的“楼阁”,经历过多少世事变迁,王朝兴替,又有多少人经受过盛衰兴亡的心灵震荡与冲击,即使“地老天荒”,亡国之恨,也无平复之时。古有庾兰成,今有元好问,以及与他们命运相同的无数亡国之臣,他们痛苦地活着,每人心中都有一篇《哀江南赋》。元好问笔下的《俳体雪香亭杂咏》,也正如庾信的《哀江南赋》。
这组诗,读之令人悲戚动容,难以释怀。王士禛《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偶有所感各题一绝于卷后凡七首》之六(裕之)评元好问:“载酒西园追昔游,画栏桂树古今愁。兰成剩有江南赋,落日青山望蔡州。”前两句化用元好问的《西园》诗句,后两句则指这组《俳体雪香亭杂咏》(点出的是第十五首与第三首)。如此则在王士禛看来,《西园》与《俳体雪香亭杂咏》,可以代表元好问诗。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癸巳五月三日,这在元好问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癸巳为金天兴二年(1233)。这年四月,金汴京守将、西面元帅崔立向蒙古军献城投降。四月二十日,“崔立以梁王从恪、荆王守纯及宗室男女五百余人至青城,皆及于难”(《金史》);二十九日,将金朝旧官羁押出京,暂居南青城,元好问在其中。五月三日,他们离开青城,前往羁管地聊城。北渡,渡过黄河北上。这组诗写北渡路途所見。
自蒙古军再次围城,元好问就困居汴京城中,直到城破。这次出城北渡黄河,才目睹了城外战后惨状。一路走来,他看到了国破之际的巨大灾难。蒙古军蹂躏过的国土,惨不忍睹。他以诗史之笔,写了这组诗,记录亡国惨痛,以及蒙古军掳掠杀戮造成的生灵灭绝,田园废弃,文化、社会、经济遭受的毁灭性破坏。诗题的核心词是“北渡”,诗写北渡所见,从诗人眼中写来,三首诗各有特定视角,特写与全景配合,从细节到全景,集中且全面展示战后惨相。
其一:
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
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第一首关注人,战争的灾难,承受者首先是人。蒙军的罪恶,最集中体现在对人的杀戮与掳掠。累囚,缧囚,被绳索捆绑的囚徒,这里指被蒙军掳掠囚系的人口或战俘。累,同缧,绳索,引申作捆绑。旃车,用毡作车衣的车子,这里指蒙古军用的车辆。旃,同“毡”。红粉,妇女化妆用的胭脂和铅粉,代指美女,被蒙军掳去的女子。回鹘马,蒙古军骑的马。回鹘,或作回纥,古代族名,隋唐时我国境内铁勒族(匈奴后裔)建立的部落联盟,唐德宗贞元四年(788)改称回鹘,此处借指蒙古。这一首写蒙古军的人口掳掠。前两句,路途所见,两个镜头,分别选取了道旁与道上,道旁“满”是被宰割者,“僵卧”地上,寂无气息;道上奔突的宰割者“似”汹涌“水流”,跋扈张扬。后两句接续写出掳掠者与被掳掠者,分别用强悍的“马”与孱弱的“红粉”代指,镜头所对,不是掳掠者的凶悍,而是被掳掠者的哀痛与无奈,写出不能承受之悲。三个特写镜头,所写是具体情境,读者却可推而广之,想到整个中原,处处如此。简单的四句诗,写出了国家破亡之际,人的大劫难:男人被劫杀,女人被掳去。
其二:
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
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第二首写物,重点写文物,毁灭文明,是滔天之罪。一群不知文化为何物的人,根本不懂文物与文化的价值,毁灭文物与文明,毫不怜惜。随营木佛,被蒙古军运去的木雕佛像。大乐,也称太乐,即太乐署,主管伎乐及朝廷大典所用的音乐。编钟,打击乐器,钟数有多至十六枚者,各应律吕和依大小顺序排列,悬于一木架上,故称编钟。市,街市,城中商铺集中的地方。几何,多少。浑载汴京来,汴京浑载来,将汴京之物全都运载而来。浑,整个,全部。这一首从物的角度写出对中原文化的大洗劫。前两句写两种代表性文物:木佛,社会大众的信仰;编钟,宫廷庙堂的礼器。木佛的神圣、编钟的庄严,被蒙古军抢来之后,便“贱于柴”“满市排”了,文明竟遭如此亵渎。靠信仰与礼乐治国的金朝灭亡了,野蛮冲决了文明,作为文人元好问,内心之哀痛,无以言表。木佛、编钟之外,还有多少神圣与庄严被洗劫与毁灭呢?后两句以不答为答:不要问掳掠了多少,大船装载,似乎把整个汴京都搬去了。汴京,大金国的都城,一国财富之荟聚,天下文物之渊薮。百年积累,一朝荡然。
其三: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
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第三首写战争对社会与经济的全面破坏,家园被毁,桑梓之地成荒漠。桑梓,桑树和梓树,古人宅旁种植桑梓,这里代指中原人赖以生存的家园。《诗经·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朱熹《诗集传》:“桑、梓二木。古者五亩之宅,树之墙下,以遗子孙给蚕食、具器用者也。”龙沙,本指白龙堆沙漠,在今甘肃、新疆之间,也泛指边塞之地与荒漠。此诗后元好问自注:“桑梓其翦为龙沙乎!郭璞语。”河朔,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尚书·泰誓》:“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孔安国传:“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河朔是金统治区主体,这里代指金后期的版图。生灵,即人口、生命。沈约《千僧会愿文》:“生灵一谢,再得无期。”这一首,诗人放眼整个旧金版图,那是什么景象:第一句,人没了,白骨纵横;第二句,家园毁了,荒沙满目。这是全景扫描。后两句又由全景推出特写,用“数家”的仅存写出天下生灵近于灭绝。“几年”之间,天下毁灭。无限江山,唯“数家”残存,这是怎么样的惨象!写“数家”之存意在万家之不存。最后一首,由眼前实见之有限,推想“河朔”万里之无限。
诗人要用一人目之所见写出天下劫难,所选的诗歌体式却是绝句,以有限文字反映如此无限的內容,真是难之又难。但看元好问这三首诗,随目之所击、心之所思写来,未见吃力。但读过细思,很佩服诗人笔力非凡。
三首诗84字,字字泪血凝成。
《自题中州集后五首》(选三)
《中州集》,元好问所编金代诗歌总集,十卷,收金代诗人251家,诗2066首。金亡后,元好问以保存一代文献自任,辛勤搜求史料,编纂成书,《中州集》是其重要成果之一。编此书的目的,是“以诗存史”。故其体例,前列作家小传,介绍诗人生平创作与有关评论,而后收其诗作。题名“中州”,以金据有中原,故以“中州”代指金。《中州集》编成,题诗于后,说明编纂宗旨,寄寓内心感慨。诗共五首,选三首。
其一:
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
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
邺下,指邺城,在今河北临漳境内,东汉建安时为曹操封邑,一批著名诗人聚集于此,有“建安七子”,也称“邺下七子”。曹刘,曹植与刘祯,建安诗人的代表。这里以建安曹、刘作为历史上北方(中州)诗人的代表。江东,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东北流向,习惯上称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东晋及宋齐梁陈建都建康(今南京),因以江东代指东晋南朝。诸谢,一般指晋谢安、谢石、谢玄,这里指诗人谢灵运、谢惠连、谢朓。以“诸谢”代表前代南方诗人。韵尤高,情韵高远。华实,华美与质实。刘勰《文心雕龙·章表》:“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飞采;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诗品,诗之品第高下。吴侬,吴地自称曰我侬,称人曰渠侬、个侬、他侬,因称人多用侬字,故以“吴侬”指吴人。刘禹锡《福先寺雪中酬别乐天》诗:“才子从今一分散,便将诗咏向吴侬。”这里代指南方诗人。得锦袍,夺得优胜。《隋唐嘉话》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
其三:
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
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
骚人,即诗人。呕肺肝,呕出肺肝,比喻倾尽心力。乾坤清气,天地间清灵秀淑之气。古人认为,诗乃天地清气所成。唐释贯休《古意九首》之四:“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宣和阁本,宣和指宋宣和殿,是北宋皇室藏书藏画之所,宣和阁本指《淳化秘阁法帖》。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太宗留意字书。淳化中,尝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汉晋以下古帖,集为十卷,刻石于祕阁,世传为《阁帖》是也。”长沙帖,即《潭帖》,庆历八年(1048)由永州僧希白在潭州据《淳化阁帖》模刻而成。一般认为,《潭帖》乃摹《淳化阁帖》,想当然认为《淳化阁帖》为优。但苏轼看法相反,其《跋希白书》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风味,故长沙法帖,比淳化待诏所摹为胜,世俗不察,争访阁本,误矣。”希白书即《潭帖》,也称长沙帖。元好问乃承苏轼之见。这里借来言诗,肯定世俗不识而实际高妙的诗作,也是为北宗诗张目。
其五:
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
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
平世,太平时期。稗官,小官。小说家出于稗官,后因称野史为稗官,这里指民间采集史料的人与其所辑史料。史笔,指史官记载的史册,这里指金朝的实录与国史。百年,指金存国时间,金从公元1115年立国,到1234年为蒙古所灭,计120年。遗稿,指金诗人遗留下来的文稿,即《中州集》中所收诗稿。空山,杳无人迹之山。这两句说,百年诗人诗稿,上天护佑,得以保存,但国已亡,无人珍惜,只有抱向深山,掩泪自读了。
元好问具有强烈的存史意识和史家责任感,《金史》说他“晩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中州集》就是在这样的使命感驱使下编成的,也确实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后来修《金史》,不少内容都采自《中州集》。以个人之力,编纂一代诗歌总集,既要有诗人眼光,存一代之诗,还要有史家见识,存一代之史,当然极其不易。尽管有前人基础(元好问自叙称,《中州集》是在魏道明、商衡所编《国朝百家诗略》基础上编成的),还是花费了元好问大量心血。在编者心里,它是很珍贵的。要表达珍惜之意,就要揭示书的价值。如何说明书的价值呢?书中收录作品的水平,就是书的价值。要说明书中所收作品水平之高,需要“对标”。《中州集》所收是北方诗,对标的当然是南方诗。这组诗的前三首都是在南北对比中,彰显北方诗的价值。
第一首先从历史上说起。北方的建安诗人“气豪”,南方晋宋诗人“韵高”,北以气胜,南以韵高,各具特色。但如果从文质相兼而得其宜的角度评价,则北方建安为优。说古是为了道今。南北分治时期的金、宋诗,当如何评价呢?南方宋人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看不上北方的金诗,“江南士人曩尝谓,淮以北便不识字。间有一诗一文自中州来者,又多为之雌黄”(张之翰:《书吴帝弼饯行诗册后》)。在元好问看来,就像建安诗高于宋晋诗一样,今日之金诗,也不亚于南宋诗。元好问的逻辑是,诗为天地清气所成,诗之难,在于“乾坤清气得来难”,而北方富有清刚之气,如此则天然胜于南方。俗眼观物,不识其真,评诗也是如此。北宗诗就如“长沙帖”之有味,俗眼只知“阁本”,有识之士才能辨其高下。“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两句喻指宋、金诗高下,其意甚明。最后一首依然在强调《中州集》的价值,不过换了一个角度:《中州集》文献珍贵,但不为时人所重:“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太平年代没有人搜集野史,朝廷有史官纪事。如今是国史烧残,野史也无。一代文献,如何流传?幸好一些才士遗稿,天意留存,神灵护持,得以搜集来编入《中州集》,可茫茫尘世,有谁关注?有谁珍惜?只能独自“抱向空山掩泪看”了。一语道尽才士之悲凉、志士之孤独。
这组诗共五首,我们选三首,不是把它作为论诗文献,而是作为诗来欣赏。以诗论,这组诗气盛、格高、理明,第一首前两句,概括南北诗的特点,简洁准确。“乾坤清气得来难”,拿唐释贯休原诗“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圣贤遗清风,不在恶木枝。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两相对比,高下立见。最后“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茫茫宇宙,难觅知音,孤独中的坚守,令人感佩叹息。这些表达,都形象且深切动人。
作 者: 查洪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内蒙古元代文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姚燧集》(整理)、《元代诗学通论》、《元代文学通论》、《元代文学文献学》(与李军合作)、《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 金元卷》(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