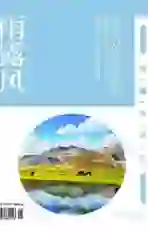读孙犁的《钟》
2021-08-09汪震
汪震


一
《钟》的主角是一个女人,一个叫慧秀的年轻尼姑。慧秀住在林村西边的土庙里。只有穷苦人家才把养不活的女儿送入庙里。慧秀的师傅泼辣狠毒,似乎与佛门不相称,“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她在大士面前那么修福行善,嘴里却有着一大堆尖酸刻薄的语言。就是这些,人们也忘记了。人们所以还提念一下,也不过是因为她的敛化,庙里才有了一个小铁钟。”①(第290-291页)所以,师傅几乎已经是一个被遗忘掉了性别的人,女人、尼姑,都是,也都不是,只剩下性格,好或者不好都不重要,也是因为就是那样。“人们”是谁?“眼前的新事很多,新话柄很多,谁肯再去谈过去的事?这个庙,人们却一时忘不下。”“人们能记得起的庙里的尼姑,也只有两三代,一般年轻人,就只记得慧秀了。”(第290页)“人们”是林村的老少吧,但只说“人们”却代表了一种感情,一种气氛,一种模糊的印象。这是个含混的群体,但也有放不下的东西,庙、慧秀、师傅、钟,就是这含混之中可以辨认、记忆的。人们是人物活动得以成立的必要的背景,观众以及亲历者。
尼姑们的住处和平民家没有什么区别:“凡是女人们用的东西,爱好的东西,她们都有也都有爱好。”(第291页)孙犁习惯于这种概括性的白描,尽管不露痕迹。“那时候,师父老了,瞎了一只眼睛,抽着一口大烟。慧秀才十八岁。她不久就交接了村里的一个年轻人。”(第291页)“这个年轻人叫大秋。是村里麻绳铺里的一个工人,才二十八岁。因为一个穷人既是仗着手艺吃饭,他就学会了各种在农村里有用的手艺,并且样样精通。这个年轻人成了村里顶有用的人,也是顶漂亮的人。人缘好,好交朋友,可是一直娶不上媳妇。”(第291~292页)“媳妇都给有地的人娶去了。地多的娶个俊的年轻的;地少的娶个丑的年岁大的。在农村,女人和土地结合,没有一垄园子地,就好像没有犁耙绳套一样,打光棍没女人。”(第292页)这里所传达的阶级情况也是长久以来的事实,穷人没有办法面对性与婚姻,是没有土地的边缘人。“可是对于慧秀,她需要的只是一个真心的人,一个漂亮的人。她和他好了。并且立时就怀上了身孕。”(第292页)这里是逻辑和情理的自然灌注,一个庙里年轻尼姑,只是因为无法做主的穷苦才如此,她自然可以简单地面对情爱,这种简单是年轻的生命独有的:“既是爱上了,就真心爱,慧秀第一次对那年轻人的誓言是我要为你死。”(第291页)
至此为止都是正常而自然的,然而这“自然的爱”被带到了具体的历史之中。慧秀怀孕的这一年,是抗战的第一年。队伍来了,林村成了人民自卫团的大队部。慧秀师傅敛化来的铁钟成为了集合的号令,大秋被一村的长工选为了村工会主任。
怀孕的慧秀正经历着艰难。师傅要她吃药弄掉这个孩子,她是不愿意的。孙犁在这里有长长的五段关于慧秀心理和情状的描摹,还有深情而不显露的评论,这里有一种知识分子的人道与良心,我忍不住要引用:
“那些幸福的人,那些红媒正娶有钱有主的人,那些新婚不久就怀上了孩子的人,身体的膨胀和突出对于他们是一种多么新鲜,多么幸福的感觉。就是在母亲的身边,她们也会微闭着眼睛,用手抚摸着肚子,心里微笑着,去感受那里面小小的生命的跳动。她们默默祝告着这个小生命快快地平安出世吧!那是她的一场天才的创造,光荣和名誉的源泉。她们比任何人都急着看一看自己身上分裂下来的这一块骨肉的可亲的面貌。他是个什么长相呢?他的眼睛是像爹还是像娘呢?一个年轻美貌的小媳妇,怀里再抱一个肥胖的大娃娃,该是多么冠冕呀!
可是对于眼前这个女人,这个时时刻刻要在人面前掩饰着自己的肚子的女人,这个带着黑色比丘帽的,还不到二十岁的女人,却为这肚里的小小生命折磨得快死了。她自己怀上了这个东西,整天整夜地焦心慌乱。她忘记了一切,她曾想到过,把他打下来吧!她想,既然为幸福冒了险,为不幸也可以冒险,她什么痛苦不能忍受呢?她可以用一只很长的铁针把这块东西扎下来!”
女人的決绝和迅速组织的逻辑“为了不幸也可以冒险”,为了不幸她也可以变得坚强,这是一种心理平衡,一种对于外部的攻击性的环境的一种抵偿,以一种通过忍受苦而变得强大的方式。但是终究这是消极的自我摧残的方式。
这里慧秀把自残的方式取消了,她是个女人,具有母亲的本能,具有为他人的本能。她自己承担“死”,“死”还不应留给孩子,对于大秋她也不埋怨,她归之于“命苦”,爱的苦果和这“命”的苦果是重叠的,大秋的“罪”就这样被接受、被替代、被忽略了。慧秀现在可以接受和体会腹中的小生命了,慧秀采取了一种面对自我的和腹中生命的诚实方式。孩子从来就不是罪恶的渊薮,他应该坦然呈现在太阳下。
但是,慧秀周遭的环境还是恶劣的,师傅是没有爱的,师傅的相好——地主乡绅林德贵想打她的主意。对于师傅和林德贵,孙犁也有一些白描,师傅当年也是风流过的,林德贵排挤了竞争者,霸占了她,尼姑、女人与男人,“那些年间,女人,就是一个尼姑,着重的也是势力和财帛。林德贵给她撑腰,就没人敢来招惹她的庙产。尼姑在社会上并没有特殊的地位,可是因为她既是林德贵的知己,她竟能调词架讼,成了村里的政治舞台上的要人。”(第293页)性和乡间政治、财产的关系在这里透露出来,“可是她渐渐地老了,并且瞎了一只眼,她和林德贵的关系就剩下了那一小包大烟土的情分了。”(第293页)
林德贵对于慧秀的性压榨的企图无法实施,在抗日战争面前,人民举起了武器,天地变了颜色,林德贵的力量无法制服慧秀。大秋是他的手下,也反对起他来了,工会的成立,接二连三的事让他不顺眼不顺心。这是历史将作恶的乡绅地主逼到了死角,“一个人感觉到别人要动摇他的根基,他的统治的时候,他最怀恨也最恐怖。”(第298页)他到庙里,是夜慧秀产前阵痛,他觉得便宜让大秋这一伙占了,他把她的痛苦当作热闹看,当把柄捏,“他从台阶上掀起了一个砖,在那钟上连击了三下。钟发出了嗡嗡要碎裂一样的吼叫,大地震动起来,风声却被淹没了。正在生产的女人的心被震碎了,栽倒在地下,血不住地从她下体流出来,婴儿降生在那冰冷的地上,只微弱地啼哭了两声。”(第301页)
钟声当然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一种仇恨的报复,婴儿成为了这些行动和心理的苦难祭品。慧秀没有死,昏迷了,苏醒后挣扎着爬到炕上去,又接着昏迷地睡去,“师傅狠狠地骂着,从地上捡起孩子来,不管死活,隔着墙就丢到苇坑里去了。”(第302页)
母亲总是比父亲,或者女人比男人往往承担的苦难更为深重些,夜里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大秋是缺席的,也很难想象他如何能够到场。也在这个夜晚,和女人个人化的身心遭遇相对的是大秋被历史性的行动所裹挟的情景:
“大秋正和他的工人同志们挤在一间牲口棚里听一个上级同志的报告。他们都红着脸,流着汗兴奋地听着。我们工人这样重要吗?我们工人的力量这样大吗?只要我们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村里的封建势力吗?他们从没经过别人这样看重自己,这样的知心和爱护。这样一来,大秋更自重起来了。他想,自己要一切都积极,一切都勇敢,一切都正确,不要有一点对不起上级。他无比激动地向上级说明了他的志愿。”
男人为获得了尊重和力量而兴奋雀跃,这里有三个“一切”:勇敢、正确和忠诚,但是真的能够一切都正确?都勇敢?都忠诚吗?对于上级、对于抗争,也许可以,但对于慧秀对于女人,男人大秋无法做到。
“当散会回来,他听到了那震耳的钟声。从这钟声他想起了一个女人,一件事情,和一个日子。他想去看一看,她快要生产了。但是走了几步以后,他又想:这不正确的,不要再做这些混账事;就转到他的住处睡觉去了。”(第302页)
男人全然不知女人的苦难,他将和慧秀的事看作一件混账事,他选择了忘却、忽略,不勇敢、不正确,也不忠诚。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混账的,但他觉得他有相对混账的事,更为重要的事要做。相对于女人,或者在女人的问题上,男人总是自私的。孙犁抓住了这一点真实,他敏感于上述细微和宏大,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差异,对他来说历史或许只是男女之间关系和交往的背景,这个背景可以换,但是人的感情以及古老的两性差异似乎保持着惊人的稳定性。
二
慧秀从心身伤痛中逐渐恢复起来了:“人民狂热的战争扫荡了人民心里悲哀的回忆,和大地上那些冤屈的血迹。老尼姑死了,慧秀大病一场,但不久就恢复了健康,分种了几亩田产,算是还了俗。她还是那么安静聪明,一头新生的油黑的头发把她以前苍白的面孔,衬托得更美丽了。”(第302~303页)
慧秀一人独住,也没有嫁人,大秋也没有娶她,她笑着拒绝别人的说媒。慧秀和大秋之间也没有直接的交流,就像男女之间无法知道如何打破沉默进入新的亲密阶段。在沉默之间就会有丰富的猜想和误解,必要的隔膜。孙犁是这样白描的:
“慧秀参加了村里的抗日工作,每逢遇见大秋,她总是那么不动声色地望一望,眼睛里充满一种在别人看来莫名奇妙,在大秋却深深感伤的热情。这是对过去的珍惜,不是引诱,是一种鼓励,不是责备。大秋却常常低头走过去了。他不是薄情,他也打算把慧秀娶过来的,他又觉得这样做影响不好,不正确。在这个事情上,他总觉得对不起慧秀,总觉得对她负着一笔债似的。他害怕当面遇着她,却好在背地里问她的生活,到地里去,首先注意慧秀那块地种了没有?锄了没有?粮食能打多少?能拉多少柴禾?
至于慧秀,却一向没到他家里去过一次,也没求过他的帮助。她在村里工作很好,人缘很好,人们愿意给她帮忙。”(第303页)
孙犁的这种白描潜入作品人物的心理,成为他小说的一部分。小说很难有一个定义,它总是一个类别,一种展开的合理又模糊的具有一定文字体量的东西,这种体量的极小化就是诗了。有的作者擅长对话,擅长对各色人物的把握,但是孙犁显然是无能为力的(他在很多地方都承认自己写不了长篇小说,写不了小说),在这些类似的片段里,一种散文化的白描替代了对话、行动、陈述和心理,成为了过渡、衔接的方式。这种陈述也許来自采风、访谈、交流,也有可能是添加了一些想象和自己的体会。这些构成了一种孙犁的风格,他在对话上是节约的。
慧秀和大秋,女人和男人终归需要相遇,未终结的爱(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需要一种释放、确认和回赠,所以这种交会是必然的。促使这种交会的是外部环境:“日寇在冀中平原上进行的‘五一扫荡。环境是恶劣的,人们在习惯上甚至说冀中变了质,其实想起来,只要人心不变,就是质没变。事实上,人们对‘五一以后的环境,不是害怕而是重视。是‘五一以后的这几年,冀中区的人民才真正锻炼了出来,任凭它再来什么事变吧!”(第304页)
“人心”不是辩证法的对立物,而本身就是孙犁的辩证法,一种相对的却又极为稳固的常项。这里的“人心”是冀中人民的总体风貌、抵抗和生活的意志,在这大的常项之下,孙犁看到了细节,从大到小的这种叙述的蒙太奇是这样来完成的:“从夏天到秋天,林村的人民是在风里雨里、毒气和枪弹里过的。慧秀整天东奔西跑,当尼姑没给她别的好处,只留给她一双天然的脚。常常在半夜里,突然被枪声惊醒,爬起来就往野外跑,在那伸手不见掌的黑夜,在那四面都有枪声的黑夜,她跑到远远的野地里,坐下来,才望着低垂的星星喘口气。有时候也觉得心里一酸,滴两滴眼泪。人家那有丈夫的人们,就是扶一把拉一把,在这个危险的时候做作伴吧,抱抱孩子吧,就是受苦受难吧,也觉得甘心啊!”(第304页)
相对于集体的抗争意志,还有那些自然的无法压抑的角落里的微观的人心,慧秀的心,“心里一酸”是一种内部的描摹,无人可见,作家看到了。
两个人的再次相聚也是由于环境。慧秀想起了钟,她要藏起来,以免敌人掠作它用,她搬不动,需要一个有力气的男人的帮助。这是一种必然和偶然的重叠。两人把钟藏到庙外的苇坑里去。苇坑当然勾起了慧秀的痛苦记忆:
“他俩抬上,拿了一把铁铲,天很黑,那一片苇子更是黑得怕人。现在苇坑里灌满了水,依着大秋,埋在坑边就算了……
她先脱下袜子,卷起了裤子。大秋和她把钟抬到苇子密,水又深的地方,埋到污泥里去。
几只藏在苇坑里过夜的水鸟,叫他们惊动起来飞走了。
慧秀忽然觉得一阵心酸,回到屋里,她再也忍不住,伏在炕上哭了。”(第304~305页)
黑色的苇丛,惊起的水鸟,这样惨淡的夜。当然,伤痛是无限的又涌上来了,自然和心绪的结合,没有一丝错乱,这是传统的赋比兴的手法。这三者向来不是孤立起作用的因素,而是三个平行的层次,描述、隐喻和情感的整体化。当然这么说有点理论的无趣,孙犁靠的是一种感情和语言直觉来把握。
“见他进来,慧秀赶紧坐起来,把眼泪擦了。
“为什么哭?”大秋靠在迎门橱上,望着门帘说。
“我看见那口钟,我就难过起来了。你记得我那场病吗?”
“记得。”
“那个孩子呢?”
大秋凄惨地不自然地笑了笑。
“这你该忘了吧?我把他生下来,又把它埋了。我一醒过来,就挣扎着到野地里去找他,他躺在那苇坑里,我用两只手抛开土,把他埋了。我一看见那钟就难过起来。”慧秀说着,还是那么看着大秋,“我净想,一个女人要只是依靠着男人,像我,那就算是白费了心。”(第305页)
慧秀起身拭泪,不愿让他看到她的眼泪,这是一个矛盾的动作吗?她想吐露痛苦,又不想给大秋带来痛苦。大秋不了解细节,但他了解自己的愧疚,他不敢直视慧秀,他害怕那种来自私人的、一个女人的情感上的谴责。慧秀发现埋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之前她埋过孩子,现在埋钟又提醒她这痛苦,然后她望着大秋说出了那句具有普遍性的女性箴言:
“一个女人要只是依靠着男人,像我,那就算是白费了心。
“你说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大秋的脸惨白了。(第306页)男人在辩白,他想辩解自己对她的感情,但他无法体会她的心情,她所遭遇过的至暗时刻。女人说:
“谁说你来呀?丢人现眼是我的事,你不会为我去得罪人。”(第306页)女人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怪大秋的,一个尼姑有了身孕,又肚子大了,孩子夭亡了,周遭的眼光是她所在意的,男人没能支撑她。“你不会为我去得罪人”,这里的“人”指什么呢?这是超脱了战争、存亡之外的慧秀指向大秋的怨怼,这里的人是工会、是游击队、是抗日组织,女人不管这些,她只关心大秋待她的态度,只关心大秋是否爱她,她已经游离于战争和民族存亡之外,甚至历史之外,就像林德贵敲钟的那一刻,他的仇怨纯然的发泄一样,这是个体化的瞬间,历史显得像个背景,情绪、感情成为了主角,成为了永恒性。在我看来这是最具“唯物主义时刻”:情绪化的真实。
“你说什么?”大秋转过脸来盯着慧秀的眼睛。一种光在他眼里跳动着。是受了刺心的侮辱以后,混合着仇恨和毒意的光。这种光的燃烧的是那么的强烈,慧秀有些害怕起来。她赶紧笑着说:
“你看。我知道你没忘了我的冤仇,你记着哩!我全知道。在这个时候,就是你要报仇,我也不讓你去。工作重要,工作比你重要,你又比我重要。我可不能叫你去瞎闹……”(第306页)
大秋的仇恨和毒意指向谁呢?是让他难受,让慧秀痛苦的那个旧世界,是以林德贵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但是大秋显然转移了自己的责任,在慧秀痛苦的时候,他不在,慧秀生产的时候,昏迷的时候,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遭遗弃的时候,在慧秀埋葬孩子的时候,他都是缺席的。他在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兴奋的时候,慧秀正经历着昏暗,他却把与慧秀的关系视为“混账事”,慧秀生产的当夜大秋选择了逃避,现在他也是转移了慧秀的私人谴责。他错过了、也理解不了慧秀的心思,她只是在谴责他没有在她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但是,现在慧秀看出他想找林德贵复仇,这固然是没有错的,但慧秀爱他胜过他爱慧秀,慧秀体贴他怕他因私仇而误了更重要的和抗战有关的工作。“工作重要,工作比你重要,你又比我重要”,慧秀认识得那么清晰,她知道斗争的大局,知道这重于一切,重于自己所爱的人,自己是可以排在末后的,这是女人的牺牲,她知道一切事物各自的分量。她的爱终究是博大的、无私的。她把自己的苦楚承担起来。我想理解她的或许只有孙犁,他是如此敏感。女人的生命在他的笔下比一切都重要,她们是牺牲的那一个,一切荣耀和壮怀激烈背后的那个支撑者。奥德修斯固然经历跌宕,但阿尔帕弗涅在蛮长的时间和狭小的空间里与环境周旋却是更为艰难的。
在叮嘱大秋小心之后,大秋出门对她说的话是:“闹情况的时候,你净往哪里跑?我总是找不着你。”(第306页)这是大秋表达爱的方式,一种轻微的半谴责式的口气,间接地传达关心和爱意。
慧秀笑着说:“你不用管我,好好小心着你自己吧!”
大秋出去,她无力地关上了山门。(第306~307页)
为什么是无力的关上山门呢?慧秀心里还是有些不满,有些遗恨,与大秋的交流就这样戛然而止,自己和大秋的未来会如何呢?这当然都是我的猜想,这里形容(“无力地”)不会随意安插,复杂的难以描摹的有点沮丧意味的感觉。
三
接着陈述这些人物之间紧密的对话,是一段稍微舒缓的描写:
“外面静得可怕,人们逃了一天难,摸回村来,望一望炮楼枪眼里射出的蓝色的灯光,轻轻推开门走进家里,胡乱吃点东西,躺到炕上休息了。只听墙角里蟋蟀断断续续地叫两声,苇坑里那个老青蛙,像人在梦里突然惊醒一样,叫了一声又停止了。”(第307页)
这是人们在侵略阴影下的生活,然后又是一段近景式的指向慧秀的描写:
“慧秀睡着了没有,自己也不知道。天一扑明的时候,她起来,开开房门,院里还是那么静,夜里下了一些露水,天空还残留着几粒星星。她去开山门,山门一开,门外站着一个汉奸两个鬼子,用刺刀又把她逼进来。村庄和她一时大意就陷在敌人的网里了。敌人在半夜的时候封锁了各家的大门。敌人逼她到屋里去,各处搜查了一下,就逼到街上来了。”(第307页)
村庄和她的陷落是“大意的”,我注意到了这处写法,这是作着想像着当时的情形,村庄连同人物都是他的孩子,成为他感受的整体。
村民们被集中到大街的广场上,里面有大秋,“她(慧秀)身上有些冷,不住地抖颤”(第308页)敌人要抓抗日村长,汉奸走到慧秀背后,突然向里面一指说:
“他就是抗日村长,他叫大秋,是不是?”
慧秀的心立时停止了跳动,她知道她会这么一闭眼就死去了。可是她又立时清醒了。她的头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推着,越想不往大秋那边看,它却越想往那边扭。她明白了,这是计,这是敌人和汉奸的诡计。他们不认识大秋的,她放心了。她安静地低着头。
全场的老百姓全低着头,全都用眼睛看着自己的心。他们暗暗问自己:“你坚定吗?你想出卖大秋吗?你想当汉奸吗?”这样一问,他们全坦然了。因为他们全在心里生起这样一个根,长起这样一棵树,就是死也要光明正大的死。
这是在民族心灵里交流着,生长和壮大的一种正气,一种节烈感,一种对灵魂的约束力量。这么一种力量,使得哪一个坏蛋也不敢再群众面前,伸手指一指大秋。(第310页)
这里是孙犁直贴着从慧秀到百姓全体的心理进行的情境拟状。大秋对慧秀来说是特殊的,他没有暴露,她也就无比心安。对于民众来说,保守秘密是一种基于节烈感的灵魂约束力,强大的群体力量使得众人战胜了恐惧与死亡的胁迫。在我们的历史里多次可以看到这种群体的荣誉和伟力,但是个人的坚定决绝,在这个情境中是由一个女人来担负的。
汉奸被惹恼了,把慧秀提到场子里,一脚踏到在地上,汉奸说:
“‘她是庙里的姑子,她和大秋把钟坚壁起来,还说不知道。早有人报告了,她不说,别人指出大秋来,叫她看看!
慧秀听说,用一只手支起身子来,望了林德贵一眼。林德贵在人群最前面,刚刚抬了抬头,看见了慧秀射过来的冷冷的子弹一样的眼光,赶紧又把头垂下。
慧秀的脸焦黄,她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我看看,大伙也看着,看看谁敢当汉奸!”(第310页)
慧秀指向林德贵的目光,表明了她清楚知晓那唯一的背叛者是谁,她担心大秋,提防着那个卑劣者的卑劣,她直接拷问他,也邀约着大家作为一种监督和警示力量。就在最后的那个句子中,她把个人的牵挂、担忧、愤怒和集体的牵挂担忧和愤怒融为一体了。我有时想,这种句子也是复杂的、不可归约的、具体的、鲜活的句子,比真生动,比情深入,超出了表义和行事的功能,这是文学的唯物主义瞬间的意向(本雅明叫它“辩证意向”)。
“难道这个女人就这样死去?带着林德贵给她的伤害、侮辱,带着汉奸敌人的打骂和刀痕,就这样死去?
她不会死的。当她的血留在地上,这就是一声号令,一道檄文。全场的百姓都不能忍耐,大秋第一个站起来,从背后掏出了火热的枪。在他后面紧跟着站起来的,是一队青年游击组。
一场混乱的、激烈的战争,敌人狼狈退走了。人们救起了慧秀,抬到大秋的家去。
不久,慧秀伤好了,身体还很弱,但是大秋提出来和她结婚。组织上同意,全村老百姓同意,就在一天晚上,吹打着举行了婚礼。”
这里,孙犁又忍不住带入了自己的情感,他无法忍受这个女人的死去,她还未得到正名。慧秀需要血作为一种牺牲、一种重生的仪式,而且这个仪式是集体参与的,面对着入侵的外敌,他的男人率先为她使用暴力,然后缔结婚姻,这个女人在世上的生存便得到了稳固和磐石般的安全,她得到了祝福(同意),伴随着吹打和奏乐。孙犁压缩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古老的不断重复的。然后他写了婚后女人的状态:
“那时情况还很紧张,敌人经常到这村来‘扫荡,人们还要经常到地里去过夜。结婚以后,慧秀身子软弱,变得很嬌惯,她一步也不离开大秋。现在她活像一个孩子了,又贪睡,每逢半夜以后,大秋警觉地醒来,叫她推她,她还是撒迷怔,及至走到沟里了,走到野地里来了,大秋走在前头,她走在后头,她还是眯着眼小声嚷脚痛、腿痛,大秋就拉着她走。”
这当然是沉浸在爱中的女人的状态,她享受着此前逆境中缺失爱的补偿,像孩子可以淘气可以贪睡,无需表现得坚强。但这又绝不是懒惰。
“他们在远远的密密的高粱地里,自己有一个洞。洞是大秋一手建造的,又秘密又宽敞,里面放了水壶干粮,铺着厚厚的草。洞口边还栽上几颗西瓜,是预备一旦水短,摘下一个来就吃。一到洞里,她才醒了,也精神了,她强要大秋睡一下:‘不!你得睡一觉,我给你站岗。”(第311页)
在那个战争的危险年代中,男人还是建造了一个避难所,尽量设置得接近于家,一个躲藏的“洞”,这其实也是最古老的家,秘密而宽敞,饮食无缺。这是伊甸园的形态。慧秀也用站岗的方式表达着爱和警觉。之前的懒惰就自然显得是故意娇纵了,被宠的感觉,现在这种半自由的状态代之以爱、警觉和责任的混合体。
这样安置着大秋睡着了,盖好了,她就坐在洞口侧耳细听着。是那么负责任,风来她背着身子给大秋遮风,雨来,淋湿她的衣服头发,也不叫淋在她丈夫的身上。
小说在这里也就到了尾声。
“抗战胜利以后,林村又实行了清算复仇,土地改革,土地复查和平分,彻底斗倒了汉奸恶霸地主豪绅的林德贵。”(第312页)
林村的复仇,也是此前弱者的复仇,这是抗日背景下的土地改革工农的集体复仇,伴随着的是慧秀这样的女人在这一阶段上的解放。私仇和历史境遇下的公仇结合为一体,这中复仇很难用正义、解放、翻身来概括其全部,但这里只考虑慧秀,她的委屈或许平复了。
“慧秀的身子也结实了,和大秋一同做林村里的工作,还是那样活泼和热情。”(第312页)
婚后的男女总是会结实、发福一些,这是什么缘故也不得而知,也许是共同的饮食起居的规律感,或者家庭带来的放松感,这里也伴随着和平带来的环境的滋养。作为女人的慧秀成熟了,表现在身子变得结实。生活也变得更加具体、深入,但是她的性情还是如一的。所有事实性的描述,都是情感性的。
小说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大庙那地方,改成了农民开会、议事、演戏、跳舞的大广场。广场前面长起一颗枝叶繁茂的小榆树,这颗小树向南伸出一个枝干,它顽强地伸出又固执地微微向上,好像是专为悬挂什么东西的。悬挂什么呢?村里的人把那口小钟挂在上面。这样,不管在平原秋天的夜晚,还是冬天的早晨,春季的风,夏季的雨,它清脆洪亮的响声,成了全村男女老少的号令,是鼓励和追念,是在祝贺一个女人,她从旧社会火坑里跳出来,坚决顽强,战胜了村里和村外的仇敌。”(第312页)
庙宇在变迁中蜕化成了民主娱乐的村中广场,这是新的稳固的林村人的精神中心,集体生活的放松和严肃都在这里。小树在广场的前面,是政治群体生活的另一个指向,它是一个自然生命,是政治群体生活所不能全然主宰的自足的领域,但是这个树也是一个精神象征物,伸出的枝干注定是要悬挂着精神的指示物的,不是别的,而是“钟”。悬挂什么呢?这也是在问,以什么作为生活和政治之上的最可敬畏的神圣物,就是这个即是地方性的又超出了地方性的钟。看来人们的生活还是围绕着一个女人的境遇,鼓励、追念、祝贺一个女人。无论四季何时,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以返祖的形式,围绕着,古老生命力或男女爱情的图腾。钟除了纪念还有警示,“钟”从预警、号召、战争、仇恨、痛苦中蜕变而来,是历史变动的沉积。
孙犁没有这样作冗赘的遐想,他只是在一九四六年的河北蠡县刘村静静地写下了这篇小说。我也只是为慧秀,为孙犁的敏感而感动,而做了如上赘述。
注释:本文的引文及页码来自人民出版社2004年《孙犁全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