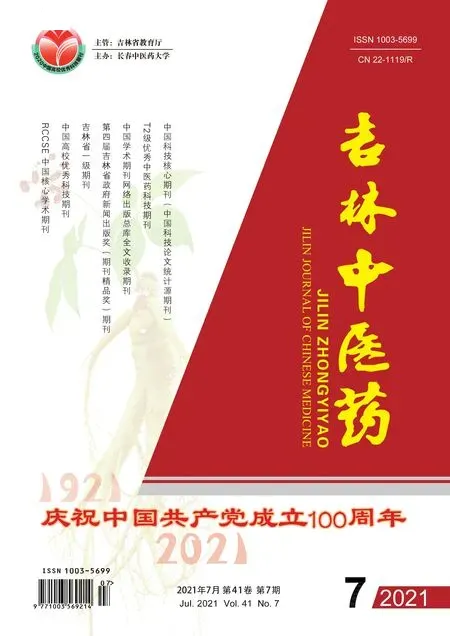《内经》“辛以润之”思想临证运用探析
2021-03-27李翠娟巩振东孙理军佟雅婧
李翠娟,巩振东,孙理军,佟雅婧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
辛味药是指五味属性中属于辛味的中药,其主要功效是能行、能散。行指通行、运行,行气、行血以调节气机,通畅血脉;散指发散,散表邪、散里寒、散结滞[1],即具有发散、行气、行血的作用。解表药、行气药、活血药中多有辛味,如紫苏叶之散风寒,木香之行气,川芎之活血等。中医理论认为,辛味药五行属金,与肺关系密切,故一般认为其主要作用是归肺,但同时又有“辛以润之”的观点,认为辛味药可以治疗各类燥证[2]。笔者就“辛以润之”的学术思想及临证运用辛润之法的心得进行简要探析。
1 “辛以润之”思想探源
“辛以润之”的思想最早见于《内经》《素问·藏气法时论》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提出了“辛以润之”的观点,认为辛味药可以开腠理、致津液、通气化而治疗肾燥证,实乃独树灼见。但对此理论历代医家亦有不同的看法。有医家认为“肾燥”指肾阴虚火旺[3],主张以黄柏、知母润之。如张元素《医学启源》:“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黄柏、知母。”《汤液本草》:“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知母。”苦能坚阴,泻火存阴,以黄柏、知母苦寒、甘寒之品治疗肾燥[4]。有医家认为“燥”指肾阴虚燥证,主张补肾养阴药中佐以细辛、肉桂等润之。肉桂、细辛味辛而入肾,辛开通气,促进肾之气化而达到化生和输布津液、治疗肾燥之证的效果[5]。有医家认为肾所苦之燥为肾的阳气不足,导致肾阴凝结,即阳不化阴、气不化津之证,治以辛味药,如肉桂、附子大热大辛之品,辛以散之,热以行之,温补肾阳,鼓舞肾气,使津随气布而得以调润[6]。肾之功能的失常导致津液不足或输布障碍,失于濡润而形成燥证,临床可配伍应用辛味药治之。正如张介宾所注:“肾为水脏,藏精者也。阴病者苦燥,故宜食辛以润之。盖辛从金化,水之母也。其能开腠理致津液者,以辛能通气也。水中有真气,惟辛能达之,气至水亦至,故可以润肾之燥。”[7]认为辛之所以能润,因其辛能通气,促进气化,气化行则腠理开,津液通,奏润燥之功。
肾主水应冬,冬令时节,阴寒偏盛,阳气内敛,寒气当令,寒性凝滞,腠理闭合,津液运行不畅,从而化“燥”。因此肾之苦燥多是因为阳气不足,鼓动无力,阳不化阴,气不化津,以致肾阴犹如死水一潭,失去了正常的滋养濡润作用,从而表现出干燥之证。此燥是一种病理结果,是继发于腠理闭合,津液运行不畅、失于濡润的一种病理表现,而不是一种致病因素[8]。《素问·逆调论》云:“肾者水藏,主津液。”人身行水之权全在于肾。若寒伤阳气或阴气内敛太过,肾之气化失司,则水液不行,失于输布。水液内停,临床可见小便不利、水肿等症状;水停不布,机体失润,可见口干、口渴、大便干结、皮肤毛发干燥之象[9]。此时用辛味药,因其能利气化,开腠理,通津液,从而奏润燥之功。
由此可见,“辛以润之”的思想对临床相关疾病的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凡因外感或内伤各种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影响到津液的输布代谢出现脏腑、组织、器官、经脉失于濡润的情况均可配伍应用。
2 “辛以润之”思想临证运用
笔者在临床实践中继承《内经》辛以润之的思想,并进一步引申发挥,将辛味药广泛地运用于外感病、口干症、水肿、糖尿病、脾胃病等疾病过程中出现的口干、口渴、皮肤干燥、便干尿少、筋脉拘急等相关干燥症状的治疗,临床效果颇佳。
2.1 辛散解表、开津布液除外感 外来燥邪侵袭人体最易伤津耗液,出现口鼻干燥、咽干口渴、皮肤干燥、脱屑、尿少便秘、舌干少津等症,临床治疗除了遵从“燥者濡之”的原则以滋润药物缓解其干燥外,更重要的是治病求本,祛除燥邪。此时常须在滋润之品中配以辛味药[10],一方面轻清宣透,使燥邪从表而解,另一方面辛行宣散,开发津液,助滋润药缓解干燥症状,并防其滋腻太过。临床常用辛味药如紫苏叶、桑叶、生姜、桔梗、豆豉等,代表方如杏苏散、桑杏汤、清燥救肺汤等。
若风寒之邪侵袭人体,客于太阳经脉,致使经气不畅,气血失和,津液受阻不能正常敷布,经脉失于濡养、拘挛急迫,可出现汗出或无汗、恶风、项背强急不舒等症状,此时常选用辛温之药辛散解表,开发津液,如麻黄、桂枝、葛根、生姜等,代表方如桂枝加葛根汤、葛根汤等。如《伤寒论》云“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方中除了运用麻黄、桂枝辛温发汗解肌、祛风和营,更配以葛根升津液、舒经脉,驱除经脉中的邪气。诸辛散药物合用既能解表又能通郁,使津液得透,筋脉得润,故诸症得除[11]。
2.2 辛宣发散、化气行津治咳喘 《素问·宣明五气》曰“辛入肺”“辛走气”,说明辛与肺、与气之间关系密切。肺在五行属金,具有主气司呼吸、宣发肃降、通调水道等功能。《灵枢·决气》曰:“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如果肺失宣降,宣发布散功能失调,可导致主气司呼吸、水液输布障碍,出现咳嗽气喘、水肿而渴等症状,此时可用辛味药治之。正如《临证指南医案》所云“辛以开之”“微辛以宣通”“辛通能开气泄浊”,认为辛入肺走卫,具有辛散之功,可宣通肺卫,助阳化气,开达腠理,布散津液,从而纠正津液不足[12]。笔者在临床中对于肺失宣降,水液输布代谢障碍,水饮内停,机体失于濡润所致之咳喘而渴常根据病情选用麻黄、桂枝、细辛、薄荷、生姜、紫苏叶等辛味药以宣通表气,发散水气,通行津液,针对肺失宣降、水饮内停之病机,代表方如小青龙汤。正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所云:“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2.3 辛通温阳、化气行水缓消渴 人体的水液代谢依赖阳气的蒸腾气化,如果阳气亏虚,气化失常,气不化津,津无以生,失于濡润,可出现口干、口渴甚至消渴等燥象。此时纯用养阴增液之法只能缓解一时之症状,并不能完全根治,若治病求本,当选用肉桂、附子等辛温助阳之品,从改善气化功能方面入手,代表方如五苓散、肾气丸等。
五苓散为治疗太阳蓄水的代表方。张仲景《伤寒论》中指出“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均用五苓散治之。本证之渴是由于膀胱气化不利,水蓄下焦,津液不能输布上承所致。故治用五苓散以利水渗湿,温阳化气。方中桂枝辛温,温阳化气,以“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具有助气化、布津液之用。正如《神农本草经疏·卷十二》所云:桂枝“辛甘大热……辛以散之,热以行之,甘以和之,故能入血行血,润肾燥。”对于五苓散的服法,仲景还提出“多饮暖水,汗出愈”,其意即在借助暖水助发汗,借汗出之机令阳气振奋,使膀胱气化复原,小便得利。冉雪峰注释曰:“观伤寒多饮暖水,汗出愈,里气化则外气化,外气化则里气化,内外豁然,亦活泼泼一片化机。”
肾主水液,内寓真阴真阳,肾阳为人身气化之动力,若肾阳虚衰,蒸腾气化无力,津无以生,失于濡润,即可导致口干、口渴甚至消渴病的发生[13]。临床常选用肾气丸等加减治疗,方中用辛热之附子、辛温之桂枝温振阳气以行气化。正如孙一奎《医旨绪余·卷下》所云:“若下有暖气,蒸则气润,若下冷极,则阳不能升,故肺干而渴,譬如釜中有水,以火暖之,又以板复之,则暖气上腾,故板能润,若无火力,则水气不能上升。此板终不得润。火力者,腰肾强盛也,常须暖补肾气,饮食得火力,则润上而易消,亦免干渴之患。”因此,此时加入附子、桂枝等辛温助阳药物即犹如釜底加薪,复其蒸腾气化之能,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达到治疗消渴的目的[14]。
2.4 辛温通脉、活血润燥祛瘀血 血主濡润,血虚失于濡养而瘀血闭阻,血运失常亦可失其濡润之能而现口渴、皮肤干燥、脱屑,甚则肌肤甲错等燥象[15]。如《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篇指出瘀血的病人可出现“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的症状特点,此时的口干燥而渴并非阴血不足所致,而为瘀血的症状之一。《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亦指出“瘀血在少腹不去”时,可见“暮即身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之证。《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所载大黄䗪虫丸证有“肌肤甲错”,即是瘀血内阻,肌肤失润而现干燥皴裂之症。可见,瘀血内停,新血不生,失于濡润,临床亦可表现出一系列干燥粗糙之象[16]。对此,临床治疗时多选用辛温通脉、活血化瘀之品,如桂枝、姜黄、川芎、当归、延胡索、红花、乳香、莪术、泽兰等,代表方如大黄䗪虫丸、温经散、桂枝茯苓丸、丹参饮等,通过辛行宣散、活血化瘀之法使血行通畅,瘀血得去,瘀去则新血得生,津始能布,脏腑、肌肤自得濡润而燥证得解。
2.5 辛温通阳、化气燥湿清湿热 人体饮食物的消化过程依赖于脏腑的气化功能,饮食物的腐熟、消化、吸收、转输均离不开脏腑阳气的蒸腾、气化和推动。若脏腑亏虚、气化无力可导致饮食物消化吸收不良,蕴结体内,酿湿生痰,湿浊内蕴,日久郁而化热,又可伤津生燥,临床表现出胸闷脘痞、纳呆腹胀、舌苔厚腻少津、口中黏腻、口干口苦等症状。湿热之邪,非辛不开,非苦不降。湿热蕴结之人若见湿化湿,则湿凝而不流,见热清热,则欲速而不达[17],故常于清热剂中佐以辛开之品以开湿壅,通气机[18]。临床治疗常选用苍术、厚朴、藿香、佩兰、砂仁、白豆蔻、半夏、陈皮等辛味药物,辛温通阳以达利气化而渗湿、气行津布而液生之目的。常用代表方如平胃散、六和汤、三仁汤、半夏泻心汤等。
2.6 辛行温散、布津灌溉缓内燥 精血津液是人体重要的阴精物质,具有滋润和濡养作用[19]。全身各脏腑、组织、器官无不依赖于精血津液的滋润和濡养。若阴血亏虚、津液不足则不能充分发挥濡润作用,临床可表现出口咽干燥、渴而欲饮、便干尿少、肌肤粗糙等一系列干燥枯涩之征。虚者补之,燥者濡之,阴血津亏致燥,法宜滋补濡润。但滋阴之药多重着黏滞,守而不走,临床若纯用滋补之品容易滞脾碍胃,临床疗效不佳。笔者在治疗此类疾病时常在滋阴养血药中佐以走而不守的辛味之药,如肉桂、桂枝、川芎、当归、香附、木香等,代表方如四物汤、炙甘草汤、十全大补汤等,使其滋而不腻,补而不滞,并促进阴血津液流行灌溉,发挥濡润作用[20]。
2.7 辛行辛润、行气布津解便秘 便秘的发生往往与肠燥失润密切相关。一方面,阴血不足,肠失荣润,传导失司,可导致便秘的发生;另一方面,肠道津液不足,液亏肠燥,“水不能行舟”,或痰湿凝滞,津液不布,肠失濡润,都可导致便秘的发生。正如《景岳全书·秘结》中所述:“秘结者,凡属老人、虚人、阴脏人及产后、病后、多汗后,或小水过多,或亡血失血、大吐大泻之后,多有病为燥结者。盖此非气血之亏,即津液之耗。”对于其治疗,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便闭》云“液耗便艰,进辛甘法”,倡用辛润之剂。笔者临床在治疗此类肠燥便秘时亦常常遵从叶氏经旨,选用当归、桃仁、杏仁、火麻仁、郁李仁、柏子仁、紫苏子等辛润多脂之品。对于津液耗伤、液涸肠燥、传导失司者配伍运用养阴生津、增液润燥之品,如增液汤之属;对于阳气不足,阴寒凝滞,不能蒸腾气化,使津液不布、肠失濡润者则配伍应用木香、香附、小茴香、肉桂等辛行之物,行气布津,调理气机,促进津液的输布,达到润肠通便的目的。
3 结语
综上所述,《内经》提出了“辛以润之”的思想,临床上对于各种燥证,不论是风寒侵袭、燥邪郁肺之外燥,抑或是阴液亏虚、失于濡润,阳气亏虚、气化失司及痰饮水湿、瘀血阻滞之内燥,均能藉辛温药开达腠理、疏通气血、振奋阳气、促进气化的作用而得以治之。笔者在临床实践中将《内经》“辛以润之”的思想广泛地运用于外感病、内伤水肿、糖尿病等相关疾病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由此可见,“辛以润之”的思想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值得临床医家进一步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