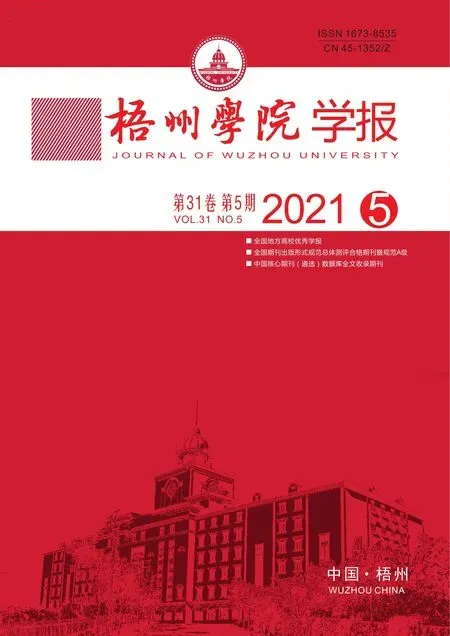隐却可见的叙述者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中的叙述策略
2021-03-08雷成佳
雷成佳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1)
洪子诚教授于2016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材料与注释》面世以来,热议不断,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共举行了2次研讨会,各位专家学者对该书的贡献予以充分的肯定,分别在材料的选取与运用、对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经验、如何处理当代文学史研究中面对的“难题”、客观史料中作者的主观性、作为文学史家在“时间优势”上的把握、“含混”的避免胶着一端的学术态度等方面做了精透的分析。本研究主要针对《材料与注释》中洪子诚教授的叙述策略进行论述分析。
一、注里含“思”
《材料与注释》共分为2辑,其中的“材料”与“注释”集中在第一辑,“材料”主要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尤为重要的一些会议记录和人物检讨书,可以说揭开了封尘已久的神秘内幕,在一些重要的历史研究、作家作品评价与研究、文学史研究等方面的关键节点处充给了核心要素,这与之前文学史研究中搜罗与展示的多边材料共同发出了丰富多元的立体声音。
这几组材料隐藏着作者直面文学史研究难题的勇气与声音。因涉及到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真相还原与评价等复杂问题,当代文学史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深层文艺问题研究一直是很多文学研究者不敢触碰或缠厘不清的痛点,或因材料的不足、研究视角的拘囿、研究勇气的缺乏等多种原因而导致研究成果有隔靴搔痒之感。然而,对于以周扬为中心的权力阶层和文艺政策、活动的深入剖析又是阐释当代文学史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创作规律和面貌、甚至与“新时期”以来文学关系避之不及的关键一环。洪子诚教授对这个问题一直未曾逃避过,而是以一名历史亲历者拨冗掉驳杂的枝蔓干扰,从而保持研究者尊重原始语境的姿态做出了示范和方法借鉴。这些“材料”本身就构架起了丰富而鲜活的历史语境,比任何一种主观推断、传闻考据都有说服力,十分有力地驳斥了二元对立的简单判别模式。“材料”的公布意味着作家等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形象被公之于众,而随着社会语境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对他们的价值立场和言语抉择的评判也会相应改变,如他在《材料与注释·自序的几点补充》中所说:“这些材料比较特殊,它们是特定情境下的产物;这些检讨书的作者,他们处在人身、表达的自由受到剥夺的情况下”[1]。
这样的解释和补充说明在突显洪子诚教授谦虚谨慎的同时,更显示了他跳脱出学术研究对生活中人的理解和同情,即使有着这样的理解和貌似公开他人负面形象的“愧疚”,他在学术的研究上最终坚定地站在“材料”的立场上,尊重历史语境,勇敢地抛出这些隐含个人情感价值评判的重要史料,将“材料”里显示的重要名家名人的形象公之于众,突显了他治学的莫大勇气和原则。
《材料与注释》中“材料”的选取与组合隐藏着洪子诚教授理性的辩证思维。如何将如此丰富驳杂而交织纵横的材料爬梳清楚又妥当地有机组合、调配安置,体现了作者学术积累的扎实丰厚、学术研究的谨严有致。从其成书的工作量来看,需要作者具备极大的耐心来咀嚼、吃透所有材料,才能使一则则“材料”发出有情感、有思想、启人深思的“声音”。谈及写作想法,作者虽然说“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2]47然而,“材料”说话的背后仍然是作者的独立思辨与探寻,这背后的思考和操作过程正是洪子诚教授的理性辩证,在“材料”的喋喋争论或者默默独诉背后都隐藏着作者努力辩证后的观点立场。洪子诚教授在剖析《文艺报》改版“阴谋”中萧乾当替罪羊一事的时候,附上了张光年和萧乾各自的说法,然后结合所积累的材料分析到“张光年和周扬一样,尽管在文艺界已居于高位,但还是属于‘不能预判变化无常的路线’的人”[2]138。接下来又结合萧乾的历史“污迹”分析了其被选为《文艺报》副主编的原因。整个分析客观理性,成为了对“材料”纠偏的重要话外音,形成了客观“材料”与主观分析的有机统一体。类似的,《材料与注释》运用的均是以较长篇幅为“材料”作“注释”的方式,将“材料”中所呈现的同一个事件和不同人的声音置于对比的视野下,从而还原客观的原初语境。让“材料”并置互证构成对话,显示的是作者还原历史语境和带领大家更深入地理解人物的良苦用心。对于当下的文学史和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而言,客观史料的呈现与合理严密的阐释这一学术研究范式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二、释里藏“情”
“材料”背后隐藏着洪子诚教授复杂的感情,既有对“材料”的左右为难之情,又有对“材料”所涉及到的人物的复杂感情,恰是这种复杂的情感,最令人为之动容。
在《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另外的大批判写作”中,洪子诚教授坦言曾经不知为何地参加到对自己喜欢的《早春二月》等影片的批判之中,并认为这种“人格分裂”心里现象肯定也在其他人身上出现过。洪教授深入地剖析自我面对被批判对象的矛盾心理与行为的同时也在剖析那些深重“材料”背后的人和事,他在左右为难而又互相驳斥的情绪中撕裂屏障,直抵心灵深处,将研究者引入到事件最为核心的部分,以类比和同理心的情怀引领研究者以开放和多元的视角看待“材料”及背后的人和事。
“记不清了”这句话既出现在林默涵自我检讨的材料里,同时也出现在洪子诚教授对其做的注释里。林默涵在描述夏衍发言时候的会场情况时称自己不记得是否在夏衍发言之前看过他的检讨书和发言内容,洪子诚教授给出注释“但林默涵在事情过去不到十年的1966年,对这样爆炸性的场面却没有记忆。”[2]47一个“却”字显示了作者对林默涵表述的质疑,同时也有自己的辨别,隐隐表露出讥讽的态度。当林默涵回忆《鲁迅全集》第六卷的注释是编辑部写的还是周扬或是他要求别人这样写的时表示“记不清了”,洪子诚教授在注释里说到“周扬对这个注释策划、修改的经过,似乎也记不清了”[2]55,与评给林默涵的“却”字相比,这里似乎感受不到洪子诚教授的明显的语气和情感,也可能有将两人事件串在一起一并调侃之意,但洪子诚教授对周扬的情感判别里明显没有对林默涵的“讥讽”,即使是周扬佯装“记不清了”,也许他更愿意相信周扬是真的记不清了,是对那个对待文艺无比热情受到复杂历史包袱裹挟的周扬的理解和同情,是对周扬50~60年代提出和执行各种文艺理论政策和活动前后不一致、“左右摇摆”的理解和同情,并没有单纯地从道德层面来评定。“和现在‘知识分子’的道德状况相比,当年的情况并不见得就那么不堪。”[2]214可见,洪子诚教授是站在更广阔更高远更人性化的视点上来看待周扬的。
相比之下,对邵荃麟,洪子诚教授予以了较为明显的态度和情绪上的表露,对他的处境与遭遇表示了同情和对他的文艺认真执着表示了赞可。对邵荃麟看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而在大连会议上十分精准地指出那段时间短篇小说创作存在的“人物的类型很少,有些千篇一律”[2]69的创作症结时,洪教授为邵荃麟那份对文艺事业纯粹的文学理想和责任心而感动,对其为文学发展前景的焦虑和责任心表示了极大的赞可。在描述邵荃麟被捕入狱后病逝于狱中的遭遇时,洪教授引用了黎之的记述“我看到邵荃麟那位老前辈心情那样沉重,我也感到压抑。我望着这位前辈,望着他那瘦弱的身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这是诀别……”[2]104这里的“材料”和情感都是不容置疑的,前后“材料”的连接帮助叙述者勾勒出了那个为文学发展殚精竭虑却惨遭批判的丰满的邵荃麟的形象,其行为表现和遭遇的对比更是帮助叙述者完成了深沉的情感表达。“材料”不仅是枯燥的“说话”,更是深情的诉说。
洪子诚教授在全书中非常明显的表露态度情绪的只有一处,那就是读到牛汉的《为冯雪峰辩诬》这篇文章,在80年代冯雪峰研讨会上,作为协助周扬修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注释的林默涵在实情早已披露后竟再次公开污蔑冯雪峰,洪教授用“惊诧而失语”表示自己看到这篇文章的情绪状态,随后评论说“虽说不应将‘道德’问题与社会环境剥离,但也不应将一切推到外部环境,认为个人无需担责”[2]230。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在尽量克制的语言语气下压制着作者愤怒而鄙夷的情绪,这是他对作为人的个体道德的看重,是对行为主体历史责任和承担意识的看重。洪子诚教授在这里表现出的“愤怒”似乎与对周扬等人的“同情”有些矛盾,似乎并没有用统一的“个体道德”标准来衡量二者,因为两者情况确有不同,周扬、康濯、郭小川等人的“左右摇摆”、前后不一是特定社会情境、制度压力下的挣扎,洪教授在这里避免了狭隘的个人道德的审判而脱离对社会情境与权力运作的考察,因此给予了极大的“理解”。相比之下,林默涵所做出的反应显现的是个人品质方面的败坏,社会环境已不能成为他恶行的推脱屏障,这也就不难理解洪教授为何对他进行无情的批讽。
三、“注释”求变
《材料与注释》中的学术研究范式令人耳目一新,如何运用与编排“材料”无疑凝聚了作者深刻的考究,为了让“材料”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作者文学研究回到“原初语境”的想法从而最大程度地展现效果,洪子诚这部学术著作采用了“材料”+“注释”的特殊编排方式,这确实为“材料”的打开方式提供了借鉴,但却是不容易效仿的。原因有二:一是这些“材料”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并不是每一个研究者都能有机会得到类似材料;二是研究者对“材料”独特的情感浸润无法复制。洪子诚教授以历史亲历者和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来把握这些材料,其中既有亲历者的“感同身受”,又有研究者的客观冷静。“材料”成了抑制作为亲历者的叙述者感性而滔滔不绝的倾吐与评论的工具,在感性与理性、生活讲述与研究论述之间徘徊和驳斥,最终呈现出这样冷静与克制、严谨与谦逊的叙述体式,呈现出那颇具文学性而又饱含情感浓度和认识深度的“注释”。
其实,洪子诚教授对于研究文体的求变一直都在身体力行着,随着研究主题突出的不同重点而采取不同的表达策略,游刃有余地做到了“随物赋形”。唯一不变的是他在研究中对于文本与原初语境、文学与体制及场域等联系的高度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是这方面很好的实践,它扭转了单纯或者重点剖析作家作品的文学史书写的局面,将原来习以为常的作为背景材料参考的文艺政策和体制、社会情况等提升到主体地位上来,打通了文学创作现象与社会综合状况的紧密联系,将创作现象放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而拒绝抽离语境的主观好恶,保持着文学史家的可贵品格和立场,也正是这样,才使得中国当代文学有了“史”。《材料与注释》中的文体明显是洪教授的另一种探索与尝试,这种探索与尝试已经突破了已有的学术规范形式上的褊狭,如果说如此严谨细密、“言之有物”的一部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学术著作因找不到符合现有学术规范的形式要求,而无缘面世的话着实可惜。针对这样的尝试,洪子诚教授谦逊地表示由上述“材料”形成的研究成果“不符合现在学术规范的文体”并向破例发表这些文章的几种学术刊物致谢。这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突显了当下学术规范的狭隘。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个学科都形成了自身学术上形式的规范性与确定性,然而有些时候这样的形式框架并不能承载研究者问题聚焦与解决相契合的策略想法,对于研究者来说形成了思维与形式创新的窠臼,而洪子诚教授的《材料与注释》正是这样一种在研究方法与叙述方式上具有探索性与创新性的学术著作。温儒敏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个体的研究视野和思维被规训的现象,“进入1950年代,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最突出的变化,是研究者职业化了,学术生产‘体制化’了。”[3]“就体制组织而言,其存在形态首先带有无人格性的特点,体制化的存在往往表现为超然于人的结构。”[4]一个真诚的研究者,总会在其研究成果中倾入全部的责任与理想、创新与激情,因为学术的灵魂是对问题的趣味与深思,没有这独具个性的灵魂,也就无谈学术。作为形式的学术规范是否可以灵动一些,不让这份真诚落空呢?
洪子诚教授在1967年就已经掌握了《材料与注释》中的“材料”,然而他并没有对此间有违“材料”的研究判断做倨傲的否定,谦逊、谨慎是这位文学史家一直葆有的高贵品格。冷静思考、尊重史料、不轻易下判断是他的研究态度和特点,这对于一些习惯站在制高点进行必然性的阐释、真理式的宣誓等研究观念是一种无声的回击,那些饱含沉思和情感的“注”与“释”是对那些缺乏历史感和人文性研究的有力驳斥,对于强化和提升文学研究者的史料意识、助推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具有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