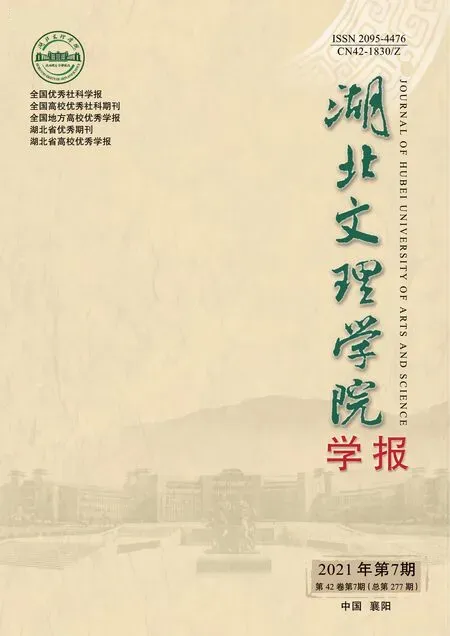由“动物群像”书写看“五四”启蒙主义的局限性
——重读鲁迅《示众》
2021-01-15朱玉川
朱玉川
(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00)
钱理群先生认为鲁迅有两篇小说是代表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艺术最高水平的,一篇是《示众》,一篇是《孔乙己》。[1]40关于《示众》,以往研究者多认为鲁迅通过“看与被看”权力秩序的表达,隐喻出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与相互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折射出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对人灵魂的吞噬和生命力的扼杀。这种求其本质的解读属于阿尔都塞所说的“直接的阅读”,它注定永远只能看到鲁迅已经看到的东西,而看不到“所谓的‘看’及由看的空缺所造成的被忽视问题,以及可见领域与未见领域间潜在的且必然的联系”,它实际是一种“直接阅读宗教神话”。[2]事实上,《示众》里的“看/被看”世界正是鲁迅眼里旧中国的症相,反映出的正是鲁迅作为启蒙者的立场以及启蒙中心视角下的“动物群像”书写。由此出发,探讨鲁迅《示众》中折射出的启蒙主义立场及其时代局限性,便属于“另一种阅读”。
一、《示众》中的“动物群像”书写
《示众》中描写的更像是一幅“动物群像”,而非人类群居图。人物无名无姓,相继片段式地出场,没有故事的前因后果,也没有情节的起承转合,像失声的蒙太奇电影镜头的无序拼接。故事的核心在于首善之区的大街上一个犯人被示众,但重点并不在这个犯人身上,而在于作为犯人的“看客”的民众。这些民众无名无姓,只有一些代称——“胖孩子”“白背心”“秃头”“红鼻子”“胖大汉”,它们成为符号化了的某一类人的代表。其中所呈现的话语都是碎片式的,全篇除了“一个工人似的粗人”所问的一句“他,犯了什么事啦?”[3]是属于完整的表达之外,其余的语言要么是单个词语或定中/状中短语的迸出,如“什么”“这孩子”“好”,要么就是单个拟声字的罗列,“嗡,都,哼,八,而,……”这些不完整的语言实则指向了无意义和无目的,语言能指与现实场景中的所指并没有实际对应关系,碎片化的语言失去了其指涉能力,甚至连情绪表达的功能也难以实现。与这种语言相对应的,是其中的人的思维方式与思考能力。语言或言语是思维的表达,如果这种言语表达失去了指涉能力,那么人物也就成为没有思维能力的存在。就文本来看,其中的人物确实是无反思能力的,其所有的行为只有一个:看。既无看的缘由,也不问任何结果,是一种未经思考的本能式的反应。不妨援引马克思的话来做参照:“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4]”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理论来看,《示众》中的人物的确呈现出动物般的存在状态,其行为既没有建立在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又没有任何的目的、计划与能动性,无原因、无目的、无意义的“看”指向的是其动物本能式的反应,呈现出人与其作为“看”的生命活动的直接同一。事实上,鲁迅在《示众》中确实用了很多形容动物的词汇:文中“钻”这个词一共出现了四次,其余如“挤”“塞”“奔”“冲”“探”“溜”等更是相继出现,这些动作语汇并非文明社会的人们之间相处时的行为,更像是弱肉强食的动物丛林法则。鲁迅更是用了“死鲈鱼”“小鼠子”“猫脸”这样的借代来直接形容里面的人物,一幅旧中国的动物群像跃然纸上。鲁迅的弟子萧红曾说:“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起受罪。”[5]这无疑是对鲁迅小说中“动物群像”书写的最好注脚。
二、鲁迅启蒙视角下的“被启蒙民众”
鉴于前人汗牛充栋的本质化解读,我们要问的或许不是“动物群像”书写本身表达了什么,而是:鲁迅何以如此表达?
与“示众”这一中心意象直接对应的是《藤野先生》中的“幻灯片事件”,这一事件在鲁迅自叙如何走上文艺之路的《〈呐喊〉自序》中亦有提及。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解释这一导致自己弃医从文的关键转折时,明确提到了“示众”二字,使得我们能够把二者直接联系起来:“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6]”——其中所说的“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显然就是《示众》中的“动物群像”,也即体格健壮、精神愚弱的国民。因此,“幻灯片事件”是鲁迅转向文学启蒙主义的出发点,而其文学表现正是《示众》。由此可知,钱理群先生所说“可以把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里的许多小说都看作是《示众》的生发和展开……可以把《示众》看作是鲁迅小说的一个‘纲’来读”[1]39,正是基于鲁迅的启蒙主义立场而得出的结论。《示众》可以说是启蒙者鲁迅的文学创作原点和“首推文艺”的蓝本,作为《示众》中表现核心的看/被看模式几乎渗透于鲁迅的每一篇小说中,贯穿于鲁迅长达十多年的创作生涯。
而《示众》中“动物群像书写”的目的,不仅文学化地表达出了鲁迅何以走上启蒙之路,更重要地是为了凸显启蒙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王富仁先生认为鲁迅的《呐喊》《彷徨》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鲁迅所试图证明的是:中国需要一次深刻的、广泛的思想革命”[7]32“鲁迅所孜孜不倦地反复表现着的,是不觉悟的劳动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这表明鲁迅始终不渝地关怀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醒,并把它当作自己文艺创作的唯一神圣任务”[7]40,而《示众》中的这种“动物书写”则以一种极端的姿态展示出了民众亟待被唤醒的蒙昧状态——民众越是麻木、愚昧、无反思和进化能力,被启蒙的紧迫性就越强,也就越凸显了思想革命的重要性。正如竹内好所说,“作为表象的鲁迅,始终是一个启蒙者”[8],示众世界的书写形式,可以看作是鲁迅最低的启蒙策略。
不可忽略的是,“动物群像”书写的背后,隐含着鲁迅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启蒙/被启蒙之间的张力。将《示众》中的人物与鲁迅笔下的其他人物进行比较即可见端倪:鲁迅笔下有众多不同的人物系列。有以魏连殳为代表的觉醒知识分子系列、有以孔乙己为代表的下层知识分子系列、有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统治者系列、有以祥林嫂为代表的下层民众系列,等等。但纵观这些人物系列,可以发现,作者与其笔下人物之间的心理距离最远的,乃是《示众》。在以觉醒知识分子为主要表现人物的小说中,有不少是以第一人称“我”来进行书写的,如《狂人日记》《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等,这种视角的书写方式表明作者深入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与笔下人物达成了某种心理同构;在地主阶级统治者人物系列中,“上等人”通常成为作品中的一个背景,或者是作为小说中主人公的生活环境来呈现的,但诸如赵七爷、慰老爷这种人物,也表现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三言两语即能由外而里地透视人物的内心;而在以单四嫂子、祥林嫂等为主角的故事描写中,她们有自身不觉悟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作为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受害者而遭受被“吃掉”的不幸命运。她们作为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完整、立体、丰满的形象,有自己的喜乐忧愁和习焉不察的一套固有的思想观念。相比之下,《示众》中的人物既看不出其有任何的内心世界,其行为即等同于其本身,亦看不出作为“看”的主体和“被看”的客体的民众是受何种思想所驱使、操纵,他们在作者的叙述下成为扁平化、纸片化的人,展现出抽象的符号属性。因此,“动物群像”书写所反映出的作为作者的鲁迅与其笔下人物心灵世界的遥远距离,实则展示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巨大沟壑——作为被言说的他者,这种不自由、不自觉的状态正是叙述者眼中的被启蒙民众形象的呈现。在看与被看的“动物群像”世界之上,有着启蒙者的“第三人”的眼睛——被启蒙的姿态正是在启蒙者的目光凝视之下形成的。作为被表述的底层民众和鲁迅眼中封建的、落后的、愚昧混沌的旧中国世界的一个缩影,“动物群像书写”隐含着“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关系,或者说,也许可以反映出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智识者在启蒙问题上的某种局限性。
三、何为启蒙以及“五四”启蒙的局限性
何谓启蒙?康德的回答堪称经典。在《什么是启蒙》中,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9]这段经典的启蒙宣言昭告世人,启蒙是为了让人类脱离这种“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的状态,也就是说,要让人类达到一种不经别人引导也能运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自立状态,这与鲁迅“立人”的文学启蒙目标是一致的。无论是“示众的材料”还是毫无意义的看客,书写“动物群像”正是为了达到由自在性的“动物”到自为性的“人”的转变,或者说是由动物性到大写的“人”之转变。但细究之下,《示众》的书写所折射出来的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思想,与康德所定义的启蒙又有着某种程度的偏离:
首先,从前提上看,康德所言“不经别人引导”所蕴含的思想即是“去权威”。启蒙者并非引导者、教育者,而是启发者、对话者。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平视的关系,而非自上而下的引导/被引导、俯视/被俯视的关系。由《示众》来看,“示众世界”是鲁迅小说世界的一个微缩,是鲁迅眼中封建的、落后的、愚昧混沌的旧中国世界的一个缩影。无论是示众者,还是被示众者,所有人都处于看/被看的社会权力网络之中,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启蒙者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眼光,那么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就形成了审视/被审视、批判/被批判的二元对立之关系,而非平等的、真诚的对话关系。民众在《示众》中所呈现出来的符号化的单薄形象,某种程度上正反映出启蒙对象的主观精神意志被忽视。或许还可作进一步思考:民众是否真的无反思能力,无法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如《示众》中所描绘的那样,愚昧、麻木、冷漠到动物般的存在?正如有研究者指出,那个“大约只是觉得苦,又形容不出”的闰土“在自己的乡亲和子女之间完全可能知无不言,侃侃而谈”[10],那么《示众》中的老妈子也完全可以像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一样抱着自己怀里的孩子。被表述的民众呈现出无法进行完整语言表达的状态,原因可能是他们拥有一套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的自己的语言。启蒙者与被启蒙者语言、思想上的隔膜造成了二者之间的对立而非平等的关系,“动物群像”书写所反映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上的不平等。
第二,从过程上来看,要区分“启蒙”与“引导”二者之间的关系。启蒙之前的状态是人类必须要经过别人的引导才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启蒙的归宿是让人类不经别人引导也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在人类由“经别人引导”之状态到达“不经别人引导”之状态的这个过程,即为启蒙。因此,启蒙并不等同于引导。“引导”侧重于直接告诉对方什么是对错和如何去做,而“启蒙”则是让人自己能够主动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意识所谓的善恶是非——这正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区别。康德说启蒙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9],可见启蒙的重点不在于向被启蒙者灌输理性,而是唤起被启蒙者运用自己理性的“决心和勇气”。但《示众》视域下的民众沦为动物般的存在状态,毫无任何思维能力可言,对他们的“启蒙”无异于灵魂的再造和生命的重塑,这显然远非真正启蒙意义上的“唤起决心和勇气”所能解决的问题。失去了主体性的启蒙,只能变成居高临下的降维灌输,而非精神平等之上的共识行为。再者,“五四”启蒙所强调的“改造国民性”与康德所言“唤起决心和勇气”之间相去甚远。先撇开国民性是否可以改造的问题,“五四”启蒙者未认识到国民性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唤起决心和勇气的前提是对于人和人性的一种正视、肯定与接纳,而“改造国民性”则意味着对于人或者说对被启蒙者的一种否定,一种鄙弃。“改造国民性”中的“国民”二字几乎成为除知识分子外的大多数底层民众的特指,但智识者又如何保证自己能够永远占据“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呢?如研究者所言,“五四以来,启蒙者们把启蒙简单地看成是一种思想改变过程,以为大众有了某种思想,社会就进步了,启蒙的任务也就完成了”[11]。这实则把启蒙简单化乃至激进化了,无论是国民性的改造还是精神的改变,都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本身的主体性和独特的存在价值,只有把被启蒙者当作真正的、独立的个体来平等对待、交流探讨,他才能够被赋予勇气和决心,才有可能被唤起理性自觉能力。决心和勇气的生发当始于内在,是从内而外的自发行为,而非从外而内的打破或灌输。笔者赞同林非所说:“在深受专制主义蹂躏的整个民族生存的土壤之上,无论通过多么激进的主张,都无法迅捷地完成启蒙的任务,而且愈益趋于激进,就愈不能容纳相左的意见,这样不就是在充满良善动机的无意识状态底下,滋长出具有专制主义色彩的思维惯性了?[12]”激进化的启蒙取消了与启蒙对象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未能认识到实际的启蒙运动当中所应当具备的理论原则和应该注意的方式、方法,有可能让民众从一种权威里逃脱出来之后又陷入另外一种权威,这就远远背离了启蒙主义运动的初衷。
第三,从目的上来看,真正的启蒙是无功利的。启蒙并非是让被启蒙者按照启蒙者的“旨意”行事,以完成启蒙者自身的某种使命,也不是为了达到“治国安邦平天下”的世俗目的,启蒙的目的在于让人类(当然首先包括自己)摆脱先天的“懒惰和怯弱”,能够有勇气和决心来运用自己的理性,除此之外的任何内容都不能成为目的。因此,启蒙正如邓晓芒所言是一个“追寻自我、建构自我、完善自我”的永远未完待续的过程。而在“五四”及后“五四”情境下,“启蒙只不过是救亡的工具而已”[13]。于鲁迅而言,以《示众》为代表的文学书写是其进行思想启蒙的一种主要方式与手段,但这种写作直接指向的是“改变精神”,“改变精神”的目的是“改良这人生”,最终指向其社会意义,思想启蒙由此成为工具理性和实用价值的追寻,而其价值理性的真正要义却被忽视了。周作人也言,鲁迅的“动手写小说”“其主要目的还是在要推倒封建社会与其道德”[14],这就无可置疑地将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相联系了,或者说,“思想启蒙恰恰是其介入政治的另一种途径”[15]。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早期的启蒙知识分子后来大多投入了革命的洪流,投向了政治的怀抱。
从“五四”启蒙主义运动的结果来看,启蒙的实际效用确实有限。从认识到自己“绝非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到感到自己如同陷入“无物之阵”,鲁迅本人也产生了关于启蒙的反思与焦虑情绪。他在《答有恒先生》中不无自嘲地说:“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16]“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启蒙主义者们曾经振臂高呼的奋斗理想,到后来理想的失落与转向,这其中所包含的人生况味和时代命题是值得深思的。这并非是对于“五四”启蒙主义者的历史功绩的否定,也不否认在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鲁迅等先驱者为探寻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而做出的艰难又果敢的探索。《示众》中的“动物群像”书写,正是当时的智识者们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对一切所做的“价值重估”,也是“五四”启蒙主义者们面对停滞、“硬化”的古国文明而奋起呐喊、寻求蜕变的精神足迹。更何况,一个社会的思想的进步和观念的改变不止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更需要好几代人的接力,甚至需要生产力的变革、技术的发展等等其它因素的共同作用。只是,当历史已过百年,我们回首上个世纪,也许才更能够看清楚当时难以看清的全貌,也让今天的我们再次思考:何为真正的启蒙?如何才能让底层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发出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声音?如何才能有效地开启民智?这对于我们当下钻研学术、传播思想,乃至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平等的人际关系,也无不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另外,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化的宝库,鲁迅的小说本就充满了多样化阐释的丰富可能性。“只要不断地从新的理论层面,对鲁迅小说进行不断的关照与细致剖析,就会不断地发现新的意义。”[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