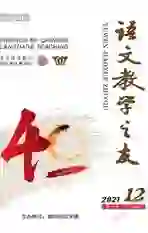以两个数字演绎生命史:祥林嫂形象塑造的特殊手法
2021-01-03谷兴云
摘要:《祝福》采用“四十上下”和“二十六七”两个数字演绎祥林嫂的生命史。这是其形象塑造艺术的杰出处之一,应予以重视和研究。
关键词:《祝福》; 祥林嫂;数字艺术;形象塑造
《祝福》长期以来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必学的经典作品,如何让学生深入理解祥林嫂的形象是课堂教学关注的重心。笔者从鲁迅对其小说创作的自评中得到理解祥林嫂形象的一个小角度,分享给大家,期盼各位的批评指正。
鲁迅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自评其小说创作,作为其经典作品的《祝福》,即为一例。比如,从数字艺术这一视角,即可看出《祝福》“格式的特别”。小说讲述的故事,是祥林嫂一生的凄惨遭遇,包括她的生存和死亡,實系由两个数字演绎而成。遍览鲁迅诸多小说,只有《祝福》一篇关注并写明人物的年岁。祥林嫂的生命表现为两个年龄约数的演变:一个是“四十上下”,一个是“二十六七”。
一、“四十上下”
“四十上下”——祥林嫂的生存时间,即最终岁数。
文本开头(3段),外出5年的“我”,回到故乡鲁镇。第2天下午,去镇东头访友走出来,在河边遇见祥林嫂:
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画面,5年后所见的祥林嫂,居于画面中心。“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透过“我”的目光,巧妙地点出对方年龄。故事紧接着,在“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祥林嫂“老了”(“死了”)。如此,“四十上下”就成为她死时的年龄。
一个“四十上下的人”,竟然“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而且随即“老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四十上下”就“老了”?有关祥林嫂的这个疑问,于小说开篇,即令读者心存疑惑,产生追问实情的阅读欲望。
读者疑惑的,正是文本要揭示的。在后文,有一系列人物和情节,表现祥林嫂被逼一步步走近死亡,直至“四十上下”终了。
初到鲁镇,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干活,仅3个半月,就被她严厉的婆婆绑回卫家山,强迫她嫁进深山野墺,给贺老六做老婆。任由她嚎、骂,一头撞在香案角上,等等,也阻止不了。再嫁两年多,贺老六意外病死,孩子被狼吃,大伯乘机收屋,她再也无法在贺家墺立足。
祥林嫂第2次到鲁镇做工,被四婶勉强收留,四叔虽然不大反对,但告诫四婶:这种人败坏风俗,祭祀时不许她沾手。而此时的祥林嫂,“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常常忘却了去淘米”……终于又被他们打发走,“叫她回到卫老婆子那里去”。
在灶下对话中,柳妈警告她,再嫁第二个男人是一宗大罪,将来到阴司去,两个男人争,阎罗大王就把你锯开分给他们,而补救办法是:捐门槛赎罪。祥林嫂照办,捐了门槛,却赎不了罪,祭祀的时候四婶仍然不许她沾手。为此,她精神更不济,很胆怯,成了一个木偶人。
在四叔家宅子外,因祥林嫂再嫁、克夫、克子,全鲁镇的人都歧视她;灶下对话的内容,被柳妈传扬开去以后,鲁镇人换了一个话题,专注于她额上的伤疤,更加起劲地嘲笑、挖苦她。一个说:“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肯了?”另一个说:“可惜,白撞了这一下。”
以上,一桩桩一件件,对祥林嫂都是沉重的打击,甚至是致命一击。打击持续发生,相叠相加,雷霆万钧,最终摧毁祥林嫂,夺走她“四十上下”的生命。
二、“二十六七”
“二十六七”——祥林嫂初到鲁镇时的年岁,文本开始记述她生命史的时间。
“我”确知祥林嫂“老了”,于是回想起往事,“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
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卫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说是自己母家的邻舍,死了当家人,所以出来做工了。
“我”的回忆(这是关于祥林嫂的第2个画面)从祥林嫂“二十六七”开始。这一年,她“死了当家人,所以出来做工了”;也就是这一年,祥林嫂出现在鲁镇。“二十六七”有什么重要性?回述祥林嫂的半生事迹,为什么由此开始?这也是引起读者关注的问题。
“二十六七”是祥林嫂命运转折点。
此前,祥林嫂受婆婆虐待,生死大权掌控在婆婆手中。祥林嫂对人说,“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比她小十岁”。表明祥林嫂是童养媳,上有“严厉的婆婆”管束,下有“比她小十岁”的祥林,以及“十多岁”的小叔子,两人配合其“严厉”的母亲,祥林嫂能有好日子?何况,婆婆是“三十多岁的女人”,她与祥林嫂近乎同龄人,婆媳“相生相克”,所谓“多年媳妇熬成婆”,遭罪的只能是祥林嫂。
此后,祥林嫂挣脱婆婆魔掌,走上自谋生存之路。先在四叔家做工,既不愁吃住问题,还有收入,“每月工钱五百文”。这是破天荒的好事。所以干起活来,“力气是不惜的”。以至于年底的重活,“全是一人担当……然而她很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可惜只有3个半月)后再嫁贺老六,因“上头又没有婆婆”而交了好运,“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新年就两岁了。”“母亲也胖,儿子也胖……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为时仅两年多)
从“二十六七”写起,是艺术构思的需要。
“我”对祥林嫂的了解,仅限于“先前所见所闻”(并非熟知一切),所以只能回述“她半生事迹的断片”。这是艺术构思的生活依据。所谓艺术构思,这里指题材取舍,详略安排等。祥林嫂的一生,以“二十六七”为界,分两个时期,采取不同的艺术手法。
前期(“二十六七”以前),祥林嫂生活于卫家山。这一时期包括:一是,婴幼儿及童年阶段——家境贫寒,早早被娘家割舍,无福享受父母亲情,成为婆婆家的童养媳;二是,做童养媳阶段——为时十几年,苦等祥林长大,在祥林十五六岁时成亲。文本对前期生活,虚化处理(略写),不作为故事现场,或以“比她小十岁”一句带过(何以成为童养媳),并未明写;或通过叙述语言(卫老婆子与四婶的谈话),交代做童养媳期间的情况,也没有细述。
后期(“二十六七”以后),祥林嫂在鲁镇求生。这一时期约十三四年(从“二十六七”,到“四十上下”),其间,有两年多时间,因再嫁而生活于贺家墺。其余十年多,包括她两次到鲁镇,并最终死在鲁镇。这里是祥林嫂故事的现场,也是故事的重点所在(细写)。她作为来自山里的寡妇,生活在形形色色的鲁镇人中间。文本通过她与这些人的交集,细致描述了四叔、四婶、柳妈,以及鲁镇的男男女女,如何以不同的形式伤害她,而她怎样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
不论前期的略写,或后期的细写,均服务于文本整体构思,即反映社会现实,表达小说主旨,藉以增强艺术表现效果。
三、总结
以两个数字演绎生命史,艺术效果独特。
其一,更突出悲剧的惨烈性和命运的严酷性。祥林嫂的悲剧是命中注定的,這与她的家庭出身、山村环境等有密切关系,但悲剧的决定原因是她“二十六七”时瞒着婆婆出逃鲁镇。卫家山如是狼窝,那么鲁镇就是虎穴、是火坑。这里更凶险,所有人都是她的“死对头”,是他们层层加害,步步紧逼,夺去她“四十上下”的生命。
其二,更充分暴露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阴冷。鲁镇为什么更凶险?这是一个小社会,充斥着禁锢、凉薄和伤害。理学(以鲁四老爷为代表)、迷信(以柳妈为代表)、冷酷(以鲁镇人为代表)等合成的精神暴力,仅用十多年的时间就将一个“四十上下”的壮年村妇摧残成身心俱废的乞丐,以致于倒毙街头。足见软暴力杀伤力之可怕,引发世人深思。
最后,更宜于压缩篇幅,突出重点。祥林嫂的悲剧生命史,未尝不可以写成“全传”“大传”,但作者以“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按,即速写),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的精神,仅追述祥林嫂“半生事迹的断片”,即剪去“二十六七”之前的细节,而加强其后的遭遇,直至“四十上下”惨死。文本的艺术剪裁功力,可谓上乘。
应予补充的是,数字毕竟只是抽象符号,可以用来说明道理,却无法描绘生活实景。文本不是单靠两个数字说话,而是辅以两个画面(形象描绘),以细描形象配合数字演绎。前一个画面,显示祥林嫂“四十上下”时的外观:“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后一个画面显示祥林嫂“二十六七”时的相貌:“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 。前一个是将死的衰老婆子;后一个是不乏美感的山村女人,构成强烈对比。形象对比和年龄对比,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祝福》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成为新文学的典范。就祥林嫂形象塑造而言,采用两个数字演绎生命史,即为其艺术手法杰出处之一。
作者简介:谷兴云(1935— ),男,安徽省阜阳电视大学教授,主研方向为鲁迅与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