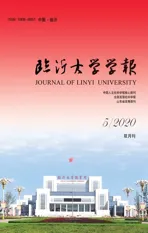先秦神道设教的情感向度及现代价值
2020-12-20刘朝阁黄开国
刘朝阁,黄开国
(1.唐山学院 会计系,河北 唐山063000;2.四川师范大学 哲学研究所,成都610068)
“神道设教”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周易·观卦·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凸显着神道为人所用的人文精神,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突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神道设教有着久远的历史,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就出现了,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神道设教释义
准确把握“神道设教”的含义,需要把这一词汇置于它产生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还原当时社会嬗变的样貌。同时,要对与之相关的两个概念“神道”和“教化”做出澄清和界定,以便寻找两者结合的内在依据。
(一)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在先秦时代,人们刚刚从蒙昧的原始社会走来,文明初见,知识欠缺,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有太多的不理解、不明白,存在诸多由异己的力量所带来的焦虑和难题。由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发展到天帝、祖先神、鬼怪,尽管在夏商周不同的时期尊崇重点有所差异、内涵不断演变,巫觋文化、祭祀活动的流行体现着先秦时期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这不仅是理论上的逻辑推演,如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的理论阐释得到的结论,近世的考古发掘亦提供了大量的文物证据,如陶寺遗址证明了早期的祖先崇拜。真实的历史既包括社会上层、知识精英所记录的部分,也应包括民间大众的生活部分,可惜这部分在古代一般不能记载下来。从道理上说,了解先秦的宗教文化,除了把握思想家、上层社会“敬天法祖”的历史景象外,普通民众的宗教意识、宗教活动亦应在考察范围内。《山海经》作为上古的奇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普通百姓对于异己力量的畏惧。“当人类对于自然的矛盾不能克服的时候,必然在意识上寻求安慰,使矛盾在宗教上寻求解决。”[2]原始宗教与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在血缘宗族的圈子里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为人们提供着心理的释放。从整体上看,先秦时代的主流意识仍然处在宗教神学的控制之下,生产生活中充满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
(二)“神道”的神秘色彩
对于“神道设教”这一概念的理解从古至今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其中存在分歧的关键就是对“神道”的把握。正确把握文献中词语的内涵,一方面要从上下文的语境中推测,另一方面需要放到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分析。“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周易·观卦·彖传》),从文本来看,这就是一个祭祀的场景,所以“神道”应当具备神秘莫测的宗教意味,是对外在于己的神秘力量的敬畏、侍奉之道。《周易正义》对“神道”的解释是,“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3]“神道”本是指天地自然生生不息、变幻无穷的奥妙,不能为人所把握却也自然而然地发挥着作用。古人正是因为对于一些现象的不理解,而心生畏惧。从商周的社会文化看,当时普遍认为天神、地祗、人鬼具有奖善罚恶的功能,具有神秘的力量,如“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诗经·大雅·皇矣》)《尚书·洪范》指出,上天会通过“休征”(吉祥的征兆)、“咎征”(灾祸应验)来表现君主的言行举止是否合乎规制,因此需要通神、娱神,以便祈神降福。因此,商周时期如何处理与“神”的关系、怎么与“神”沟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具有普遍的心理认同,从整体而言并不是如后人所推测的仅仅是不可道破的统治术,尤其是殷商对鬼神深信不疑。“神道”的神秘性还体现在只有圣人才可以把握,而普通民众只有遵从的份,圣人是神和人沟通的中介。“神道”虽是人们人文世界的一部分,但这部分却笼罩着神秘色彩,是人所难以把握、不可控制的部分。尽管学界对于“神”的内涵存在着分歧,有的学者从世界阴阳相互激荡交融而不可测的自然规律方面把握,有的学者倾向于从天帝、鬼神、祖先的角度去阐释,但是,这两方面的涵义都出现在《周易》之中,其共同之处则在于“神”所具有的超越世人掌握范围的神秘力量。
(三)“设教”的公开特质
《礼记·学记》篇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化是历代统治者一个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在私学兴起前,学校为官府所垄断,教育是王权的一部分,宗教、宗法、政治、教育紧密不可分,是为统治者培养直接管理人才和意识形态建构者的。从根本上说,古代教化的目的就在于增强政治认同,使统治阶级的意志得以贯彻,维护王权,让人们做忠臣、孝子、顺民。对于先秦的思想家来看,教化也是整饬道德人心的责任担当,是为实现王道乐土而提出的施政之方。“设教”是人事,是人道,体现着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为了实现自身目的的积极作为。当然这里的“人”作为教化的主体,是相对于普通民众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思想家。既然“设教”追求教化的效果,这就得考虑教化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从学校教育而言,“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尤其到了西周形成了成熟的教育体系,如《周礼·地官司徒》界定了大司徒的职责,其中就把“教化”的内容和预期效果分为了十二个方面。春秋战国,人文主义勃兴,宗教氛围有所减弱,同时也是战乱不已、社会动荡的时期。墨子把当时社会乱象的原因归结为人们对于鬼神信仰的缺失,因此高扬“明鬼”“天志”的旗帜,主张统治者应大力宣传宗教,以此教化人民,实现家国和谐。他强调了鬼神信仰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墨子·明鬼下》)对于“设教”的原则,管子有过精到的论述:“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因此开展教化也就要顺应人情、人心,通过“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管子·七法》)潜移默化地实现良风美俗。古代设教虽以学校为重点,但又不限于此,至今仍然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做法就是把教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营造场景、优化环境,在潜移默化中熏陶、感染、塑造人们的思想。
(四)两者的结合
进入东周时期,随着人文理性精神的觉醒,一些思想家把本来就密不可分、实质却差异很大的“神道”与“教化”,视为手段与目的关系,把两者都作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方式。今人在研究两者关系的时候,很多的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但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看法。“将‘神道’与‘教’视为手段与目的关系的理解,在《观卦》‘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的语脉中,虽或有所据,也颇能说明后世的某些具体的文化与政治实践,但这种理解也有流于表面化与简单化的危险。”[4]以人类史的角度而言,当时的“神道”现象是人类认识所限的客观事实,是宗教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必然结果,因此并不能把先秦的“神道”简单地归结于统治阶级出于教化民众的治国策略。从“神道”的功能来看,其本身就具备一定的教化功能,可以规范约束君主、官员、民众的行为,使其反省自身的行为是否符合礼仪、神意,以便获得现实人生的福祉,而避免灾祸的降临,从客观上也为王权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从教化的目的和实施来看,教化族人、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使之成为利于管理的顺民,这就要求依据民众的情感、社会环境氛围。因此,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不论统治者是否有意为之,两者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有内在的契合性。因此,先秦各家思想家均对神道设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记·乐记》)、“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管子·牧民》)。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因“神道”符合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需求,用以“设教”则也体现了古代统治者顺应时代特征以加强思想统治的自觉。借“神道”为王权统治提供合法性的来源,主动把政治观点、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融入相关活动,从而起到约束、凝聚民心,巩固统治的目的,这是古代统治者主动采用的为政方略。把高高在上的“神道”引入世俗人间的“教化”,成为教化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警示行为、敦化风俗的作用。从人性的角度,我们可以找到两者结合的依据,那就是双方共同具有的情感向度。
二、神道设教情感向度的四层意蕴
情感向度是神道和教化的共同基础,成为两者结合的内在因素。作为一种深刻影响人们意识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历史现象,神道设教正是因为指向人的情感,其理念才可以深入人心。先秦神道设教以异己的力量培养敬畏,以内在的亲情激发感恩,以真心实意贯穿其中,最后达到人们心悦诚服的理想效果。
(一)敬畏天地:神道设教的情感起点
敬畏,是人对于异己力量、神圣事物的尊敬、畏惧的情绪,有敬畏则有做事的底线,可以引导出虔诚、谦卑的品格。先秦时期,人们震撼于大自然的力量,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动、风雨雷电的交替、四季景物的轮换,经受地震、洪水、干旱、虫患等自然灾害的袭扰,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随之归结于冥冥中的主宰,自然万物皆有神性。在当时人们认为“帝不仅主宰天时,也掌管人间祸福,可以保佑人王,也可以降祸人间”[5],于是就要通过祭祀祈福于神灵,表达对于天地神灵的敬畏,“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左传·昭公元年》),通过各种祭祀仪式和不同的祭祀名目以与天神地祗进行沟通。孔子把“畏天命”作为理想人格君子的一项基本素质,“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崇尚敬畏特别是对神秘莫测的“天命”的敬畏,敬畏成为认可天命、大人、圣人之言的基础。正是这种敬畏,人性中朴实的情感,确定了处理与外界关系时原始的情感起点,成为神道设教的内在驱动力,失去了敬畏则丢失了虔诚,更罔谈信服,古今中外莫不尽然。为了增强对神灵的敬畏,改变“民神杂糅”导致的对神的亵渎,《国语·楚语下》记载了上古时期的宗教改革,那就是“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绝地天通”是通过从顶层制度设计把“神事”与“民事”分而治之,剥夺一般人与神秘力量沟通的权力,以便恢复到“神事”和“民事”各得其位、不相干扰的和谐秩序,从而增强对于神灵的敬畏。在信仰领域,敬畏之情是基础性的存在,如果失去了敬畏之情,则任何仪式活动都是徒有其表、流于形式了。
(二)怀念祖先:神道设教的情感基石
怀念祖先的亲情,基于血缘关系,维护宗法系统,为神道设教奠定了情感基石,带有强烈的人文情怀。从蒙昧的原始社会进入父子有亲的文明社会,人伦关系的确立在文明的演化过程中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先秦的神道设教抓住了人性中的质朴情感,立足于伦理关系最根本的亲情,直指人心深处,最易引起情感的共鸣。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均大量记载了祭祀祖先的场景,追忆祖先的音容笑貌、丰功伟绩。在《论语·学而》中曾子说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指出了由神道而教化的逻辑进路。对此朱熹解释为:“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为,则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则其德亦归于厚也。”[6]朱熹的解读恰当地展现了由对祖先的谨慎态度、思慕行为到培育道德、敦化风俗的过程。先秦儒家把怀念祖先的亲情称之为“孝”的一种表现形式,视“孝”为所有德行的根本,是教化产生的基础。孔子虽然对神秘的“天命”“鬼神”关注不多,但是这并不影响其对于丧祭之礼的重视,这里体现着其对于血缘亲情、人伦道德的态度。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极为推崇丧祭之礼的原因就在于其认识到丧祭之礼所提供的场域有利于醇化人们的德行,是实施道德教化的绝佳时机。丧祭之礼是联系过去、现实、未来三个维度的中介,是维系家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寄托着今人对祖先敬畏、依恋、感恩、怀念的情感。这种把自然流露出对已逝亲人的真情实感融入丧祭之礼各环节的思想,使得丧祭之礼不再是徒有虚表的外在形式,而是有着深厚情感支撑的实实在在的教化载体。
(三)真心诚意:神道设教的情感底色
先秦时期,从事占卜、筮法、祭祀等活动是与神灵沟通的行为,其中把握从事这种活动的人保持什么样的态度是了解神道设教的一个关键。殷商“率民以事神”,西周“敬鬼神而远之”,东周儒者一再强调祭祀的真诚,重视鬼神之事、祭祀之礼是先秦一以贯之的主线。《尚书·洪范》论述了占卜、筮法在君主处理治国理政中重大疑难问题时的决定性作用,“汝(指王)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如果占卜、筮法显示所问之事不可行,即使君王的想法也不可以实施。《国语·楚语》描述了君主作为祭祀的主祭虔诚行礼的场景,“圣王正端冕,以其不违心,帅其群臣精物,以临监享祀,无有苛慝于神者”,君王、王后以上率下,不存私心杂念,以诚心隆重祭祀群神万物,进而引导百姓以诚意祭祀自己的祖先,这里体现着祭者的真诚。这种真诚,既是人们朴素的宗教意识的反映,更是人们内在人性的真实表达,是规约自身行为、求福免祸、思慕亲人的真实诉求。尽管后世学者指出神道设教的虚伪性,祭者的真诚与否不再重要,重要是此举可以神权为王权辩护,有利于国家治理,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时期祭者的真诚是绝对的主流,怀疑之声只是极少数,对于祖先的祭祀至今仍然体现着人性中的至真至纯的情感。先秦儒家看到的这种“神道”中蕴含的真情实感,正是与教化的契合之处。“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礼记·祭统》),先秦儒家对祭祀的情感生发过程进行了描述,视作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一种表达,反对徒有形式、缺乏真情的祭祀。
(四)心悦诚服:神道设教效果中的情感追求
“在儒家看来,包括祭祖、祭天等在内的神道设教,实质上是一场连贯过去与现在,让人们承继传统的诗化教育过程,是使人们通过真挚情感的表达与宣泄从而达到道德品格升华的有效办法。”[7]对神道这种取得道德品质升华效果的前提就是对神道中教化内容的由衷认可,由敬畏到认同。在这个思想的转变过程中,既有对外在力量的感性认知,由恐惧而生敬畏,也有对神道内在依据的理性认同,由心悦而诚服。尽管先秦神道设教表现出很多违反人性的行为,如杀害奴隶、巫师以祭祀神灵,这在今天看来是需要认真检讨的野蛮行为,但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先秦的神道设教符合当时人们的情感需求,是人类认知水平的进步,对于凝聚人心、统一思想、维护宗族、国家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祭祀过程中,相应的礼乐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祭祀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分别贵贱、陶冶情操、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如《春官·大司乐》所描述的“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通过运用不同的乐舞礼仪,使参与者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体会祭祀的意义,激发心理的认同。相对于政治中的刑罚而言,神道同样具有惩戒的功能,但不同的是神道更加侧重“软”的方面,突出引导人向善的指向性,而刑罚则在于当下见效的后果,与是否认同无关。
三、神道设教情感向度的现代价值
先秦神道设教所表现出的情感向度,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其中有些方面与今天民主社会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这是需要认识清楚的,如君主以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威慑公卿、士大夫和百姓,使其对所谓僭越行为心存恐惧。然而,除却局限性,先秦神道设教的情感向度依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可以为现代社会的教化工作提供借鉴。
(一)因情立教:依据情感以创设教化
“先秦时期的‘神道设教’,其目的在于通过祭祀祈祷等曲折迂回的道路以达到教化效果,它在迷信外衣下隐藏着理性因素。”[7]这种理性因素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神道设教所蕴含的情感因素,依据了当时人们普遍的心理状态和认知水平。神道设教虽充斥着宗教信仰的意味,表达着人在神灵面前的渺小和卑微,却包含着尊从人的情感,从人性的角度审视神道,从而为神道设教确立哲学依据。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认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在这里“道”可以理解为儒家所倡导礼乐制度或从更宽泛意义而言的教化,为教化寻找到了人性基础。在任何时代,创设什么形式的教化方式必须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结合这是设置教化的基本原则。只有能够深入人们内心,可以激发人们情感共鸣的教化形式才是有效的,而脱离现实的风土人情,单纯的理性灌输,是不易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的。神道设教成为宗法社会、王权时代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最佳载体,统治阶级的意识观念以大众容易接受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规约、形塑着被统治阶层。当今社会启发人的心灵,建设人的精神家园,首先就是要考虑到人群的实际情感需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实施相应的思想教化,从而提升教化的针对性、有效性。
(二)导之以情:围绕情感以实施教化
在具体的教化过程中,要围绕着人的情感而实施。“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性自命出》),指明了真情实感在教导人们信服中的积极作用,是悦心之教、可贵之教、不言之教。神道设教之所以在先秦能够充当教化的最重要的角色,其中一方面君王、公卿、大夫、士人、百姓等不同人群在侍奉神灵中表现的真诚功不可没,其以不自欺而影响周围的人,以上率下、由近及远。另一方面,善于利用教化对象的情感需求,以当时人民普遍关心的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为切入点,祭祀不同的神灵以表达利益诉求。当今教化工作,同样需要从事教化工作的人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诚挚之心投入工作,高度认同自己的教化内容,起到表率作用。在具体的教化过程中,认真研究不同层次的教化对象的情感需求,真正进入教化对象的生活世界,充分发挥文艺的育人功能,为其情感满足创设条件,使其在耳濡目染中潜移默化。而脱离人们的情感的思想宣传只能沦为空洞的说教,其效果将大打折扣。
(三)感化认同:基于情感以评价教化
先秦神道设教把人们感化认同作为教化效果的评价标准,由情感而理性,对情感进行了升华。固然在科学日益精细化的今天,对于“教化”这种工作的评价标准可以是多维度的,如教化人员配置、制度建设、资金支持、量化成果等,但是基于教化情感变化以评价教化的标准抓住了教化的本质,那就是教化最终是落实到人思想意识的改变,而不是外在的物质层面的东西。感化认同是对教化内容的真实表达,不是摄于外在影响而做的表面承诺,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正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工作,不能仅仅以人们了解理论为旨归,更重要的是让理论成果进入大众头脑、为大众所真心接受,这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人们的思想困惑、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弘扬国家主导性的价值观念,要以民众的接受程度为根本评价依据,要追问民众是否感化认同,不能仅停留在完成一项具体工作的层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