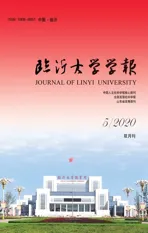从在场的身体到世界性的人:老庄视界中人的存在方式
2020-12-20魏微
魏微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230039)
学界关于老庄思想中的人的探讨往往直接集中在人的体“道”、悟“道”上,而对于老庄世界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在生活世界里的存在方式与存在意义,却不常有人追问。实际上,当我们聚焦于老庄视界中人具体可见的身体,人的生存便得到了基本的确证,而将目光进一步拓宽,便可发现由人的生存联动而成的一个个交织的情境,当察觉到“道”在情境中的显豁时,人的存在则拥有了联通万物的世界性意义。老庄视界中人的生存方式展现着老庄哲学对人现实处境的深沉关切。
一、在场的身体
老子尝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1]108关乎生命、生存的祸患堪称“大患”,老子慨叹无身则无患,即以身体的存亡勾连了人的存亡。从这一记述中不难看出老子对身体非同一般的重视,这种重视不是刻意、极度地爱重,而是意识到身体于人之生命、生存的关键作用。就此,老子奠定了道家的一个基调,即以身体的存在为人生存于世的一切之前提,为人可以为人的基本条件。
《庄子·田子方》记载:“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2]635在庄子的这则寓言中,普通画师与“真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受揖而立”可以看出众画师对宋元君的态度是恭敬的,符合尊卑秩序和世俗的礼仪,“舐笔和墨”也是作画流程中的正常举动,说明众画师受专业常规技术与习惯的约束,而那位姗姗来迟的画师却与众不同,“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他并没有遵从通常的人际礼仪,甚至离开了规定他出现的环境,接着,他“解衣般礴,裸”,反常的解衣赤裸与叉腿而坐的姿态也展现着他不受习俗、规范的制约。概之,众画师的中规中矩藉由他们的身体语言得到呈现,而后来的那位画师也是藉由他异于常规、免于困缚的身体形象、身体行为展露着他的洒脱真性,让宋元君赞叹他“是真画者也”。即是说,到了庄子这里,人的身体不仅代表生命与生存,也总是在一定的场景中展现着人的生命情态、生存状态。
可见,老庄都没有首先将人视为异于禽兽的伦理道德承载者,也没有空泛地将人上升至文化层面的象征符号,在老庄眼里,人首先应是真切活着的生命体,即是有喘息、能活动的生命体,老子从生命的存在切入,庄子在这一基础上从生命的表达与呈现入手,将具体的生命自然而然地落实在具体的身体上。而老庄语境下的身体也不等同于被动的肉体、形骸、躯壳,不只是一个载体、媒介或连接物。老庄思想里,身体是能动的,即身体是“活”的,同时,身体是具体的、形象的,即身体也是直观的,它直观且连贯地存在、活动于时间之流的一个阶段里,也直观且确切地存在、活动于空间之中的一个位置上,更是始终有所处境的。即是说,身体在这里存在、活动就意味着生命在这里存在、活动,在场的身体——一个人在一定时段内存在与行动于一定场域之中的“活”着的身体,是他的生命与生存状态最直接被察觉与领略的焦点,也是他实现生存意义的起点。
二、生存的情境
当我们聚焦于人在场的身体,萦绕周身的现实处境便也成了无从回避的信息之流,此时,人连带着他的生存情境便也一并跃然而现。
人身体的在场其实也意味着人的现实局限,即人在这里的同时就不能“生活在别处”,作为行为主体的人总处在一个具体的生存范围里,与其中的人和物形成互动、有所联系,构成他生存的情境。西方现象学思潮中,胡塞尔超越传统哲学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将其理论旨趣回归“日常生活”,提出“生活世界”的观念,随后,海德格尔指出,世界可以有先于存在论的生存上的含义,即可以指“‘自己的’而且最切近的‘家常’的周围世界”[3],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对世界的理解都包含着人直接、现实、确切活动着的“部分世界”,与老庄思想中主体的生存情境存在相似性。如此看来,老庄思想中人生存的情境也就直观地表现为他日常生活着的“周围世界”,展现为他自身及他周遭存在的一切和他自身同他周遭发生的一切。
老庄视界里,人生存的情境主要可分为三类:动作情境、趋向情境、物与人是其所是的情境。
动作情境是最直观、最显见、最易捕捉的生存情境,简而言之,它就是人与周遭的物或人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动作,从而构成了以动态形式呈现的情境。《庄子·养生主》记载:“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2]110“触”“倚”“履”“踦”都是庖丁的身体动作,且都是及物的动作,直接呈现着庖丁的“手”“肩”“足”“膝”与牛的接触和作用,同时,“奏刀騞然”是庖丁对刀的使用,也就是庖丁将自身的力量与手之将往的方向倾注于刀而作用于牛,庖丁解牛就是一个经典的动作情境。
动作情境之外,趋向情境也是老庄思想中的一种常见情境。趋向情境即人与物、与人虽然没有正在发生着显而易见的活动,但因为传递出了人的意向,同样构成了人与物、与他人有所联系的情境。《庄子·达生》中,粘蝉的佝偻者在练习之时,“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2]567,待粘蝉之时,“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2]567。这里,粘蝉的佝偻者身如植株、如枯枝,“不反不侧”“不易”,即便如此,我们仍能在佝偻者的静定与专注中,在佝偻者手中粘竿的不偏不倚中,在蝉对自己将要被捕命运的无知无觉中,感受到紧张的气氛,这正是因为佝偻者手执粘竿趋向着他的目标物——蝉,所以,即便佝偻者的粘竿还未向蝉伸去,他自身对于其意向性的呈现也同样构筑了鲜活的情境。
动作情境、趋向情境都易于理解,因为它们都直接由某些事件的发生和流程的展开显明着自身,而最后一种情境,物与人是其所是的情境,则被蕴纳到了更深的层次。所谓物与人是其所是的情境,即物与人始终在其是这样而非那样的呈现与交互中传达着自身的定义。《老子·二章》:“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1]60老子的这句话展现的就是是其所是的情境。梅洛·庞蒂曾就颜色展开情境化的探讨:“颜色在另一种变化的维度中才是不同的,在它与周遭联系的维度中才是不同的:这种红色只有从其自身位置上与周围其他红色——与这些红色构成灿烂的一片颜色——相联时,或者与被它支配或支配它的、它所招引或招引它的、被它排斥或排斥它的其他颜色相联时,才是其所是。”[4]即梅洛·庞蒂认为,某种颜色只有置身于与之相同和不同的颜色组成的情境之中才能真正显现出同与不同,才能显现出此颜色是此颜色而非彼颜色。这种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分析老子的这句话中蕴含的情境。以长短为例,长短首先在物的对照中才能显现不同,它直观地表现为一物比一物在等长的部分之外仍有盈余,或一物不足以与另一物等长,在长短的最初界定上,必然出现过这样的两个同时在场的物构成的对照情境,在长短的观念闪现时、被提起时、被使用时,也必然能对应出一组长短之物的对照情境,或者说,这种一组长短之物的对照情境就总是蕴纳在长之物之所以是长之物而短之物之所以是短之物的判断、界定、使用之中。
不难发现,在老庄思想里,物与人是其所是的情境是一切情境的基础。如庖丁解牛的情境里,因为牛通过如是的大小、体型、骨骼构架、肌肉纹理呈现着牛是其所是的情境,庖丁才能顺利地与牛作用,完成他解牛的工作,建构解牛的情境。再如佝偻者粘蝉,因为蝉翼轻薄如此,蝉的习性如此,蝉正呈现着它是蝉而不是鱼、鸟等其他物的情境,佝偻者才能攀援着蝉是其所是的情境而训练自身,熟执粘竿,构成粘蝉的情境。而庖丁解牛、佝偻者粘蝉同时也是庖丁、佝偻者是其所是的情境,庖丁行云流水的解牛动作、解牛流程正是呈现庖丁是一个熟稔解牛之道的人的情境,与之相同,佝偻者粘蝉也是展现佝偻者是一位拥有高超的粘蝉技艺的人的情境。
这就是说,人身处在情境里,就必然要将生存活动落实到物与人是其所是的情境,要自身展现着他是其所是的情境,且对周遭之物与人是其所是的情境有所注目、有所了解、有所领会。这种对周遭之物与人是其所是的情境有所注目、有所了解、有所领会的行为,也就是老庄思想中的“观复”行为。
《老子·十六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1]121人所“观”之“复”也就是芸芸万物“各复归其根”。王博认为,“‘各’字表明万物乃是分别地返回自己的根源处,如同人返回婴儿状态一样”[5],我们可以缘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推论:首先,仅一物或几物复归不能称“各”,此物复归而彼物非然也不能称“各”,“各复归其根”必然意味着万物“皆复归其根”;其次,万物在“皆复归其根”的应有之义上,“各自”“每个”进行其复归的使命,它代表着此物之复归不能替代彼物之复归,此物之复归所通过的具体方式、方法也未必适于彼物,即物各自有着适用于自身的复归的具体方式、方法。因此,老子的这句话意为,人“观”万物皆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返回到自己的根源处。《老子·六十五章》:“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1]65《庄子·天地》:“生非德不明。”[2]371在老子这里,“德”昭示的“与物反矣”与“各复归其根”形成了一致的指向,到了庄子这里,“德”被直接界定为使人与物的存在明朗、明晰、明显的特性,可以说,老庄思想中万物将“德”显豁也就是万物“各复归其根”的演绎,同时也是对万物各是其所是的情境的呈现。至此,我们便可以判定,物与人是其所是的情境也就是物与人“各复归其根”,即物之每一物、人之每一人通过自己的方式返回到自己的根源处,呈现自己在根源处的样态。
安乐哲曾说:“没有其来自无的观点,没有全然外在的看法,也没有非情境化的立场。我们都身在其中。在事物之中获得的那种内在的、构成性的关系,使得那些事物都是反省性的,并且在流动中相互承担、彼此共处。”[6]正如安乐哲所言,老庄思想中,作为行动主体的人总是要以情境化的方式出现,人始终基于他的在场而身处于一定的生存情境中,且无论他身处于怎样的情境,也都是应以物与人是其所是的情境为基本。换言之,人既以他的生存活动展现着他是自身而不是他人,也通过注目、了解、领会着物与人是其所是的情境不断构筑着自身是其所是的情境。此时,这种在情境中统一的根源指向意味,又使我们不得不延展视野,在物与人是其所是的情境里往更深邃处追索。
三、世界性的人
从情境的纷呈中我们看到人与他人、与物联结的丰富可能,它提供了一种暗示——在人身处的情境之下,人还身负着更加深沉广博的意义。老子为我们指示了一条寻访答案的道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225缘此路径,着眼于人周遭的万物,我们得到了一个反向追溯的可能,即由万物中发现了“三”的存在,循着“三”的来路看见“二”,经“二”又抵达“一”,最终,由“一”看到了那个更深邃之处——“道”。
出于“道”与情境的关联,康中乾将老庄之“道”界定为“情境本体”,他认为,“‘道’并非对象性的、已成为死的(即已经形成好了的)那种概念,而是正在形成、构成、产生中的活的道路,这就是‘道’境!所以,庄子的‘道’与老子的‘道’一样,不是对象,不是概念,而是境遇、情境。”[7]藉由“正在形成、构成、产生中”不难看出,“形成、构成、产生”一定伴随着“形成、构成、产生着什么”,即它一定是及物的、及人的、及事的,是“道”通过那些“形成、构成、产生着什么”的境遇、情境而体现自身的存在,体现它的本体作用,即体现它的“使形成”“使构成”“使产生”,且一直、正在、始终“使形成”“使构成”“使产生”。所以,“道”作为万物存在的根源,使物与人能在最初的层面上是其所是,而作为这样的“情境本体”,“道”的作用、“道”之所以为“道”的理由也必须通过物与人展现着其是其所是的情境得到实现。由此可见,“道”在创生万物的同时,在让物与人于最初的层面上是其所是的同时,也必然无法离开万物,无法离开那些呈现着物与人是其所是的情境,这也就是詹剑峰所说的“道物不二”[8]的景象。
于是,因为“道”的创生与“道物不二”的关系,万物与人便有了天然的内在关联,即物与人是其所是的种种情境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进而,由情境的交织、展布、运动而构成的世界有了不可否弃的内在关联性,世界就此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非零碎、散落着的事物拼凑的总和。如此一来,身处其中的人便成为了世界性的人,即人的存在与他人、与万物的存在构筑了由“道”统通的世界,人的行为也具有了关联世界的意义。
因此,在老庄思想中,人若要发觉自身存在的世界性,领悟行为的关联性意义,积极建构与周遭世界的和谐关系,投入世界的有序展布,唯有使自身合乎于“道”的内在引导。
人如何能合“道”?老子给出答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159老子的“道、天、地、人”常被拿来同海德格尔“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作类比分析,二者都是关于世界结构的设想与阐释,但刘小枫指出要点所在:“存在的显现中上帝必得到场,否则存在就仍然是茫昧的;与此相反,在‘道’的显现中,神不在。”[9]海德格尔四重整体的世界留有着神性的幽影,却正是老庄所要消解的,在老庄看来,“道”生万物,“道物不二”,同时,“道”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1]93,使以“道、天、地、人”为框架的世界在由“道”而来的内在关联之外,不再受什么外在的力量掌控,这也就是“道法自然”的意义所在。进而,人合乎于“道”的内在规定即让人同“道”达成一致,和“道”一样遵循“自然”,如罗安宪所说:“自然是道之本性,亦可为道体;无为是道之作用,是人之所应效法者,亦可称为道用”[10],遵循“自然”直观的表现也就是“为无为”[1]67。
我们发现,在“道、天、地、人”的结构里,老子并没有将万物拎出来,让万物去“法自然”,这是因为万物本来“自然”,是人的不“自然”才导致了物的不“自然”。如《庄子·秋水》中北海若所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2]524牛马四足是天生如此,是“自然”的,给牛马戴上镣铐则是人的行为,破坏了牛马的“自然”,改变了牛马的本然。所以,必须由人,也只能由人在生存中维护万事万物原本的“自然”,为世界的内在联结和基于联结的运转保留可以维系的空间。
老庄视界里,人实现其世界性存在的意义,维护内在关联着的万事万物的“自然”,就具体展现在人与自然交互、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和人自身的内在协调上。
在与自然相处的方面,老庄极力警惕“以人入天”[2]762的情况出现,即杜绝以人为意志、人为目的强行扭曲自然世界的情况,主张“顺物自然”[2]268。所谓“顺物自然”也就是顺应自然事物、自然环境原本的性状、习性。《庄子·至乐》中记载了鲁侯养鸟的寓言:曾有一只海鸟歇息于鲁国的郊外,鲁侯十分珍爱,将它圈养于庙堂,为它演奏九韶之乐,又以祭祀用的牺牲作它的膳食,可这只海鸟却目眩不已,忧虑悲伤,不进饮食,三日而死。鸟本应出现的情境在深山间,茂林里,而非被束缚于人类以为的尊贵之地,享人类眼中的供养与荣光,庄子以为,发生这一悲剧的原因在于“非以鸟养养鸟”[2]552,也就是没有按照鸟本身的习性与休养生息的方式养护它,强行建造了异于鸟之“自然”的生存情境。鲁侯养鸟就是“顺物自然”的典型反例,他割裂鸟与本然生境的联系,剥夺了鸟实现自身“自然”与自由的机会,也辜负了自身作为体“道”者的人的能动性。
为了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持守“自然”,老庄表达了对礼乐制度和仁义价值观念的怀疑,认为应将其让渡于“道术”,还原人与人之间归根于“道”的联结。《老子·三十八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1]209“道”行于世的世界本是和平恬静的世界,失“道”才会退而求其次追寻“德”的整全,而连“德”也不全备了,人才会将人际之间的和平关系诉诸于“仁”的伦理规范,失于“仁”后又做了“义”的行动要求,尽失之后方有“礼”这一人为制度的应运而生,留有礼制发挥作用的余地。即老子发现,礼制的诞生蕴藏了“道”层层残败的过程,而这同时也是泯灭同源之“道”,割裂人与人天然联系的过程。为此,庄子提出“人相忘乎道术”[2]248的交往方式,以求恢复人与人的本然亲缘。
而在人自身的内在协调上,老庄呼吁溯回朴性,保有澹然的生活态度。与芸芸万物复归其根一致,若要通达于“道”,人也要将复归的动向内化于自身,反映在人性上,就是“复归于朴”,复归朴性。较之于儒家为人性寻求向善的基调不同,老庄抱持的不是性善论而是性朴论,追回朴性也就意味着与生存情境中的事物的交互中,避免“趣舍滑心,使性飞扬”[2]407,即避免将自身生命的意义寄托于占有外物上,进而规避在与物相接的过程中使承于“道”的本真之性偏移消散。这就直接导向了现实生活中“少私寡欲”[1]134的行动方式和司马谈所评价的“赡足万物”[11]的态度。“少私寡欲”基于的是人欲望、欲求的角度,“赡足万物”基于的是人满足的切身体验,二者实际是一而二的关系,都在于尽可能降低对象化地看待万事万物的频率,将人与自身的关系作为人与万物关系的节度,以自身为原点,由己及他地保全身处的情境达成是其所是的境地,完善自身及周遭之物同世界之整体的联系。
总之,老庄的视界里,现实的人经由他活着的肉身、在场的身体,构筑了一个又一个交织流泻的生存情境,人始终在情境中呈现着他的生命样态与生存状态,也应在种种行动中,透悟“道”的内在统通,在与自然、与他人、与自我相处的过程中持守“自然”,维护万物的内在联系,助化世界的和谐发展,至此,人的行动对万事万物联结流转的过程担负了责任,即人的存在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可以说,人成为了世界性的人。
四、结语
如颜世安所说,“人自身的问题就在人的生存方式中”[12],在老庄视界里,人所卷入的困境,如人与自然无法和睦相处的生态危机、人与人矛盾频发的社会纷争、人自身无法自恰自得的精神虚妄与自我迷失,很大程度上在于人没有找到适于同世界共同发展和同自己和解的存在方式。而从承载生命的肉身到现实所处的情境再到内在联系着的整体世界,人在老庄视界中自在场的身体这一焦点出发,拥有了世界性的存在意义和担负其世界性存在的可能。它展开了一条人内心成长并与他人、与万物和谐发展的道路,通过模铸自身,贯注行动,由周围世界敞开向整体性世界意义的构筑与领悟。与此同时,老庄视界里人的存在方式也提供了一个哲学研究与哲学发展的必要向度——虽然哲学思考具有超越现实的抽象性,但哲学是“属人”的,它不为全然的理性而存在,它所为的是对人的生存及人生存的世界真实不虚的眷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