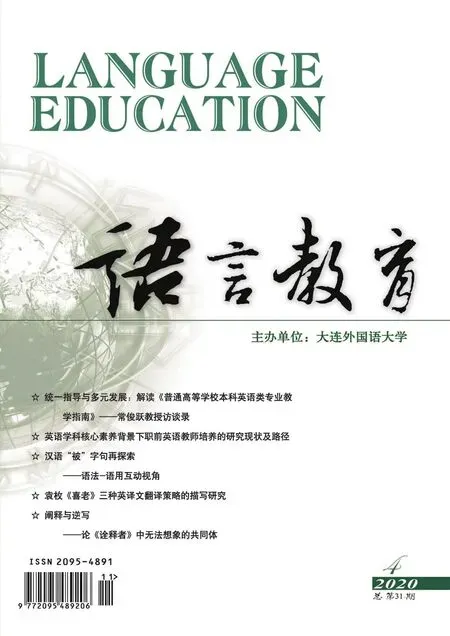汉语“被”字句再探索
——语法-语用互动视角
2020-11-28张绍杰
薛 兵 张绍杰
(1.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辽宁大连;2.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
1.引言
汉语中以“被”为标志的被动构式通常也称作“被”字句(邢福义,1996),其研究长久以来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关注。先前研究(Li & Thompson,1981;Shi,1997;Huang et al.,2009;Wu,2013;Cook,2018;石定栩 胡建华 2005;庞加光,2019等)从不同视角揭示了“被”字句的结构特征、意义属性以及语用功能。不过,汉语被动表达形式复杂多样,如何对各类“被”字表达式进行统合性解释,并从理论上对“被”进行词性语法界定,学界依旧没有达成共识。
近年来,随着语法与语用界面或互动关系研究的持续升温(参见Green,2004;Huang,2004;Ariel,2008, 2017;Wu 2017;张绍杰,2010, 2017;薛兵,2018),同时也受汉语学界的“句法·语义·语用”三平面语法分析的影响(参见范晓,1985等),学者们(Huang,2004;Wu,2017等)不断呼吁从语用的维度,更加准确、全面、系统地考察汉语语法现象的本质内涵,关注其中揭示的语法-语用互动关系。因此,本文将进一步从语法-语用互动的视角出发,考察、分析并阐释语用因素如何影响汉语“被”字句的选择与理解,以期拓展并完善汉语“被”字构式研究的理论视角与分析路径。
2. 汉语“被”字句研究概览
文献显示,汉语“被”字构式研究的核心争议在于如何界定“被”的语法属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该构式本身的复杂性。大体而言,汉语中存在两种“被”字结构①本文主要讨论句法构成为“被+(名词)+及物动词”这类典型直接“被”字句(庞加光 2019),并从理论上给予解释。关于“被自杀”等新“被”字句,以及“他被人家打断了一条腿”这类“保留宾语”被动句(Wu 2017)等非典型被动构式,我们将另文详述其整体意义的识解机制。,即长、短“被”字句。
(1)房子被那些人拆了。
(2)房子被拆了。
如(1)所示,“被”前后各有一个名词成分——“房子”和“那些人”,分别充当动作的受事和施事,呈现为以“NP1+被+NP2+VP”标志的长“被”字句。而当NP2隐去,构成(2)那种“NP+被+VP”结构时,就体现为短“被”字句。先前研究致力于对其中“被”的词汇属性和语法意义进行统一界定与解释②此处主要评述对长、短“被”字句进行统一解释的理论方案。事实上,王还(1984)、石定栩(2005)、石定栩、胡建华(2005)等曾提出对长、短“被”字句分别进行不同解释,即“被”的双重属性分析。不过,有学者(Wu,2017;庞加光,2019)指出长、短“被”字句之间的差别本质上只体现为施事论元的隐或现,而“被”的句法位置并未发生改变,双重分析割裂了长、短“被”字句间的内在系统性关联。,并呈现为以下几种观点:
● 介词观
“被”字句研究的主流观点是将“被”归入介词类别(Li & Thompson,1981;李珊,1994等)。这是因为在长“被”字句中,“被”后接表达成分引导出动作的施事论元,其语法功能类似于英语中的介词by。不过,短“被”字句中施事论元的隐去会导致介词“被”的“介词搁浅”(stranded)现象,即介词直接与动词连用。这显然有悖于语法规则(参见石定栩 胡建华 2005)。
其实,“介词观”在解释长“被”字句时其实也存在问题。如果“被”确实等同于by,“被”和其之后施事论元的结合应该与by引导的介词短语一样,充当可以在句中自由移位的句法成分(constituent)。
(3)张三昨天被李四打了。
(4)*被李四张三昨天打了。(Huang et al. 2009:116)
但如上所示,原本(3)中处于句中的“被李四”移动到句首构成(4)这种表达形式并不符合语法规范,不可接受。可见,介词观的解释并不成立。(参见Huang et al. 2009)。
● 动词观
受生成语法研究影响的一些学者(Huang,1999;邓思颖,2008等)倡导将“被”看作是一个与“挨”“遭受”“经受”等动词类似的特殊动词或轻动词。
对于长“被”字句而言,动词“被”后面接由名词引导的补足语小句。小句宾语是空算子,移动到主句句首位置与主语同指并获得具体的所指;而短“被”字句中,“被”后接动词短语充当谓语补足语(Huang,1999;石定栩,2008)。因此,动词观不仅同时解释了长、短“被”字句结构特征,也有效回避了“介词观”面临的理论问题,体现优越性。
但正如石定栩(2005)所指出,“被”并不能像动词那样带表示体态的助词、不能重叠、不能以“V不V”的形式充当问句的主要疑问成分等。可见,“被”与动词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句法特征差异,将其视作动词依然不妥。
● 助词观
除了以上两种观点,也有学者(Goodall,1992等)曾提出将“被”解释为语态助词,类似于英语中屈折形态标记-en,专门用以标记被动语态(转引自Shi,1997)。但如果“被”完全等同于英语-en,长“被”字句中的NP2则插入动词谓语内部,无法解释。因此,这种观点也被认为是存在问题的,并很快被学界废弃。
不过,近年来“被”的“助词观”被给予新的阐释(参见戴耀晶,2006;Wu,2017)。在评述“介词观”和“动词观”理论问题的基础上,Wu(2017)提出“被”是一个“没有任何语义内容”的语态助词(voice particle),其语法作用只体现为标记其前面论元为“动作的目标”或“动作的接受者”(98)。由于“被”不再与施事论元发生关联,该方案似乎同时回避了原“助词观”、“介词观”和“动词观”的理论问题。但是,纯粹的语态助词解读似乎忽略了“被”字句默认表达的遭受致使性结果或负面影响(施春宏,2010;Xue & Zhang,2018;Jing-Schmidt,2019等)。
上文在评述先前理论方案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分析中面临的困境。我们认为以上三种对“被”字句语法界定方案的局限本质上源于没有充分考察语法构式使用中语用因素的影响。当前语法-语用界面研究(见下文)已经证明,语法阐释无法割裂于语用因素的考量,语法形式既有语法规则的属性,也顺应于语用目的,体现语法和语用的兼容性。同时,日常语言交际中,语法形式的选用本身就服务于更大程度上传递言者意欲表达的交际意图。因此,为了更加合理地解释汉语“被”字句的性质,必须进一步切实考察其使用中语法与语用之间的相互作用。
3. 语法-语用互动视角
语法与语用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学界热点。大量研究致力于挖掘影响语法结构形式使用中的语用因素,其中包括关注语法形式的语用制约和语用价值的句法-语用界面研究(Green,2004;Huang,2004;Hedberg & Zacharski,2007等),探究句法不确定性(syntactic underdeterminacy)引发的语用充实(pragmatic enrichment)过程的动态句法(Dynamic Syntax)理论模式建构(Kempson et al.,2001)及其应用研究(Marten,2002;Wu,2017),以及语法与语用分工关系“编码与推论(code and inference)”模式探索(Ariel,2008,2010,2017)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证明语法结构形式无法割裂于语境语用因素的考察,转换生成语法所提倡的“句法自治”(syntactic autonomy)并不存在。大部分语法规则实际上来源于长时间的语用推理驱动的语法化过程(Hopper & Traugott,2003;杨国萍 向明友,2018),因此,语法形式中存在对语用信息的标记,体现为规约化了的语用意义成分(Ariel,2010:234)。
前人的理论发现也促使我们进一步综合考察语法与语用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形式,系统探究源于语用的语法形式如何编码语用信息(语用价值)以及如何受到语用条件的制约。籍于此,我们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言顺应论相关思想提出语法-语用的互动关系体现的“选择与顺应”过程,意在强调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上语法与语用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历时层面上,语法规则体现为语用推论逐渐演化顺应的结果。因此,语法在编码语法规约意义的同时也必然编码大量语用规约意义,体现了从语用推论到语用法规约,再到语法规则的逐渐演化过程。在共时层面上,语法和语用之间的互动体现为语法所代表的规约性和语用体现的意向性之间的相互制衡。语言的具体使用就是遵从语言的内部和外部规约,对语法所提供资源系统的动态顺应性选择过程,以及依据语用规约对语法所编码意义的推论性识解过程,体现为语法形式选择顺应于策略性的语言使用或交际目的需要(参见张绍杰,2010,2017;薛兵 张绍杰,2016,2018;张绍杰 薛兵,2018;薛兵,2018)。因此,语法构式的语法-语用互动关系可以简化为下面图示:

语法构式的语法-语用互动阐释框架
4. 语法-语用互动视角下的汉语“被”字句
上图所示,由于语法与语用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历时层面的语用法语法化过程,语法构式编码的意义中既包括语法规约意义,也包含语用规约意义,体现语法构式中形式与意义的统合(Goldberg 2006)。其中,语用规约意义既有规约性的一面,又有区别于语法规约意义的可取消性。可以说,语用规约意义构成了理解语法与语用之间相互作用的关键概念。因此,下文将首先基于“语用规约意义”对“被”进行语法层面的理论界定,并围绕“语用规约意义”展开汉语“被”字构式的语法-语用之间“选择与顺应”的互动分析和阐释。
4.1 语用规约意义与“被”的语法属性界定
上文指出,当前学界“介词观”“动词观”以及“助词观”在解释“被”字构式使用时均存在一定问题。“助词观”的倡导者Wu(2017)明确指出“被”体现为一种带有语用凸显性(pragmatic salience)的语态助词,强调主语遭受到的影响(103),因而汉语“被”字句是语用语态(Klaiman ,1991)①Klaiman(1991:34)曾提出语态的三分方案,即基本语态(basic voice)、衍生语态(derived voice)和语用语态(pragmatic voice)。其中,基本语态对应主动和中动语态形式,而衍生语态主要是被动语态形式。语用语态则重在强调句中某些论元成分解读中的语用凸显性(pragmatic salience)。的表现形式。不过,令人感到疑惑的是,Wu(2017)同时提出“被”是“没有任何语义内容”(92)的语态助词。
根据语法与语用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尤其是语法(部分)来源于语用的历时演化,从而编码语用信息的理论认识,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被”的助词语法属性而否认其本身编码语用性质的负面“遭受”(affectedness)意义。事实上,王力(1943:497)早就明确指出被动语态标记“被”来源于表示“遭受”的动词“被”的语法化过程。“被”原本表示“寝衣”的名词,后来引申为动词,表达“覆盖”的意思。“覆盖”义一方面引申出“施及”的意思,并一般用于指涉好事,如“功被天下”;另一方面,引申出“蒙受”“遭受”的意义,主要用来叙述不幸或不愉快的事情,如“秦王复荆轲,被八创”。现代汉语“被”字句中的“被”就源于其中的第二种,因为绝大部分含有“被”的语例都是叙述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王力,1993:497)。例如:
(5)我们被人欺负了。
(6)老太太也被风吹病了。(王力 1943:88)
网络处理技术。网络处理技术主要包括话题发现与追踪技术、网络分析技术等技术类别。话题发现与追踪技术是指舆情监测系统能够从网络世界中寻找到热点话题,根据发言频率、信息源权威度等指标,准确识别热点话题、敏感话题,并对相关话题的发展变化加以追踪,及时捕捉相关信息,抓取舆情数据。网络分析技术对抓取到的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具体包括自动分类、相似性排重、自动生成热点、负面舆情研判、转载计算、统计图表自动生成、自动抽取关键词、自动摘要等。
以上所示,“被”字句的主语构成句中动词动作的受事论元。(5)、(6)分别表达了受事“我们”和“老太太”遭受了“欺负”“生病”等不如意的、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遭受语义是对于主语而言的,因而“被”字句的语法意义可以概括为“主语遭受”义。这种观点在学界影响很大,受到吕叔湘、朱德熙等老一辈语法学家的广泛支持。之后展开的对“被”字句概念内涵的各类探索基本都以此作为基础(李珊,1994:20)。例如王还(1984)研究指出“被”字句总体上描述的是针对主语而言不愉快、不如意的事件。即使有些动作事件并非不愉快,但也是在某种情况下某人不希望发生的,或由这个动作产生了不愉快的结果。
可以说,不论具体情况如何,“被”字句的选用似乎都默认地表达并凸显“遭受”语义,体现为来自其源动词的语义残留。换言之,“被”在编码“施事提升”(patient promoting)被动语态语法意义的同时确实也编码了一定的负面遭受类语用意义,即“被”的编码意义体现为“被动语态(语法)+负面遭受(语用)”意义。换言之,“被”是一个同时编码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的语用语态助词(pragmatic voice particle)。
4.2 语用规约意义与“被”字句的选择
语法与语用的相互作用也同时体现于“被”字句使用中的“选择”与“顺应”过程。由于对语法和语用意义的同时编码,对“被”字构式的选择不仅是对“被”所编码语法意义的选择,也是对其编码语用意义的选择或凸显。
上文指出“被”字句一般表达主语遭受的语用意义,但这种“遭受”是否一定局限于主语?实际上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李临定(1990)曾观察发现“被”所编码的“遭受”语用意义并不一定针对主语,也可以针对说话人,甚至是相关事件的参与者。李珊(1994)进一步指出“被”表示的不如意实际上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针对受事主语说的,也就是传统上的理论认识;另一种是对说话人或者关系者说的。可以说,这种对“被”所表达“遭受”语义的宽泛化理解在当前逐渐被学界接受。这是因为大量的“被”字句的主语并非相应动作的受事,甚至并非有生命的论元。例如:
(7)我还最害怕夜间上厕所,因为上一趟厕所回来后,我的位置又被同床的情人们不自觉地舒展一下身子而侵占了。(李珊,1994:20)
以上两个例子共同特点是“被”前面的句子主语是没有生命的“位置”“池塘里”等表示方位的词语,在传统的生成语法中被称作附加语(adjunct)。这类成分所遭受到的影响不同于有生命个体那种切实的影响,具体的遭受关系可能“需要通过推论才能获取”(Wu,2013:71)。事实上,本文认为这类表达中真正遭受影响的主体并非句中主语所示成分,而是说话人或者语境中其他利益相关者。很明显,(7)凸显的是同床侵占位置给“我”而不是给“我的位置”带来的消极影响,而(8)中池塘里养了鳄鱼可能给其他人带来安全隐患。换言之,“被”字句表达的遭受意义本身是不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其识解需要基于特定语境信息进行考察,体现语用推论和语法-语用编码意义的相互作用。不过,“被”所编码的负面遭受语用意义无疑是后续语用推论或充实的起点。
可见,不论“被”字构式表达的具体话语意义为何,“被”本身编码的语法-语用规约意义体现为一种言语社团内部共同享有的语言使用规约。对“被”字构式的选择就是对其编码语法-语用意义的选择,体现为一种普遍的行为规范(Huang,2012),或者语用规约(张绍杰,2017)。
事实上,本文对“被”编码语义内容的界定同样适用于解释新近出现的“被自杀”“被捐款”“被结婚”等“被XX”这一新型“被”字构式。在“被XX”构式中,无论XX体现为何种语法成分,何种语义内容,该构式都体现为一种被动遭受的不良影响,而这正是“被”本身编码的负面默认语用意义所触发的。以“被结婚”为例,“结婚”本身并无好坏之分,“被”在此处不再仅仅体现为被动语态标记(Cook,2018),而是同时默认性地表示相关者受到“结婚”这一事件不良影响的语用意义。这种负面遭受可能是由于不实新闻的报道,也可能来自于父母包办导致的不情愿(具体负面遭受意义的确定需要语用推论的参与)。总之,新“被”字构式的出现和广泛使用①关于新“被”字构式的结构和意义特征以及其识解机制,参见熊学亮、何玲(2012),黄正德、柳娜(2014),庞加光(2018)等众多相关文献的分析与讨论。再次印证了上文对“被”的语法界定与解释,体现了对“被”的选用也是对其编码语用意义凸显的过程。篇幅所限,我们将另文论述新“被”字构式使用中所体现的语法与语用之间的互动关系。
4.3 语用规约意义与“被”字句选择的顺应
如图1所示,对语法形式的选择本身也是顺应交际意图需要的过程,本节进一步分析“被”的选用如何顺应语用目的,并侧重考察“被”所编码的不具备语法强制性的语用规约意义,如何顺应交际目的而在特定语境下被取消。
与上文讨论的负面遭受语义相对,王力(1958)等学者曾发现汉语“被”字句很多时候也可以表达一种主语受到恩惠的意义。例如:
(9)他被选为会长。(王力,1958:354)
上例中与“被”连用的动词是“选为”。很明显,被选为会长并非不幸的遭遇,而是体现主语所示个体受到的爱戴或推崇。此类表示积极语义的“被”字句被邢福义(2006)称为承赐型“被”字句,并具体表现为三个类别:“授予”类、“列入”类和“评为”类,如下所示:
(10)范氏梅芳最近刚刚被授予了一项奖学金,可以前往英国攻读工商管理。(邢福义,2006:374)
(11)刘诗白……被列入美国传记研究所《国际名人录》。(376)
(12)侯义斌……1993年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评选为“全世界5000著名人物”。 (377)
上例(10)是典型的“授予”类“被”字句。根据常识推断,不管是谁,被授予奖金都既是一种精神上的荣誉,也是一种物质上的回报,体现明显的获益。同样,(11)所示的“列入”类“被”字句表示主语某方面的成就被公众所认可,得以被列入某一个名录,因而也是体现积极的语义倾向。这种通过外部认可获得的积极语义在(12)所示的“评为”类“被”字句也得以体现,表示主语由于某些成绩显著,而所受到不同类型名誉上的认可。
诚然,这些所谓的承赐型“被”字句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主语的受益,呈现对于主语而言称心如意的事情,与传统上表示消极、不幸遭受意义的“被”字句形成了鲜明对比。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被”字句是否真正体现了王力(1958)所言汉语语法的“欧化”,“被”字句的“去消极化”。换言之,汉语中真的存在两种(语义倾向的)“被”字句吗?
对此,我们持否定观点,并认为所谓的承赐型“被”字句与传统“被”字句不存在本质上的对立。汉语“被”字句在本质上只存在一种语义类型,即上文所提出的编码了语态语法意义和凸显一定“遭受”语用意义的语法构式,这种语用意义体现了在认知层面上主语所示论元受到的控制(庞加光,2019)。那么,如何解释承赐型“被”字句的积极语义呢?
仔细观察邢福义(2006)文章中语句,我们发现真正表达所谓“承赐”意义的并不是“被”或者被动构式本身,而是其后跟随的动词。可以说,邢福义先生对承赐“被”字句的划分在本质上只是对句中主要动词具体语义特征的划分。换言之,承赐“被”字句所揭示的并非被动构式的意义特征,而是可以与“被”进行搭配动词的语义倾向。可以说,承赐“被”字句的产生恰恰证明了本文对“被”语法词汇属性的界定。“被”编码的被动语态语法意义具有强制性,一般不可以取消;而“遭受”语用意义尚未彻底语法化,不具有强制性。因而在与表示积极语义动词连用并发生冲突时,动词标记的词汇-语法积极意义会抵消或压制“被”所编码的负面语用意义,从而体现承赐型“被”字句的非消极语义。
总体而言,各类“被”字句的表意过程揭示了语法形式选择就是对特定语用交际意图的顺应。当说话人意欲表达主语的不良被动遭遇时,“被”作为一个语用语态助词顺应于这一意义表达需求,充当意义表达的资源手段,体现为在没有特殊语境情况下的默认意义表达(如4.2部分所述);而当说话人同时需要表达主语的一种受益被动行为时,又可以使用表示积极影响的动词来消解“被”所编码的消极语用意义,从而使整个句子体现为一种非不幸的积极语义。因此,本文提出的“被”对语态语法意义和遭受语用意义同时编码的理论观点,可以统合性地解释传统长、短“被”字句和表示积极语义的承赐型“被”字句,揭示了这类语法构式使用中的选择与顺应过程。
5.结语
本研究分析指出“被”是一个由实意动词经语法化过程演变而来,并保留一定原动词意义的语用语态助词,同时编码了被动语态语法意义和负面遭受语用意义。对“被”的动态选择就是对其编码语法-语用意义的同时选择,同时,这一选择过程顺应于特定交际目的。“选择与顺应”语法-语用互动视角更为合理地解释了汉语“被”字句的语法结构特征和意义表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