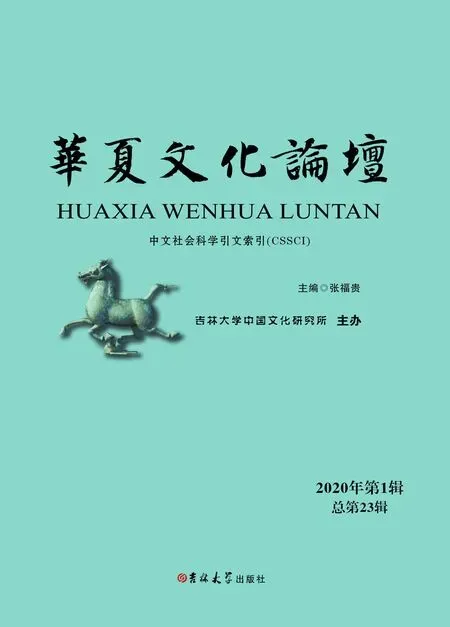“他者”的祛魅
——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立场与“汉学心态”的反思
2020-11-17贾雨薇
贾雨薇
【内容提要】随着海外学界对中国“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提升,“海外汉学”对中国学术形成的挑战与冲击也愈加引起广泛关注。我们在这一背景下提出要对“汉学心态”予以警惕和检讨的同时,也要深入挖掘“汉学心态”出场的特殊历史机缘,并以李欧梵、王德威等炙手可热的海外学人的研究为典型个案,揭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逻辑悖论以及历史细部的盲区。通过多维度的总结剖析,反观“本土”研究应从自身理论框架的完善、“泛文化研究”的抵制、本土立场的坚守以及自身文化自信的建立等方面应对“汉学心态”带来的学术惶惑,摆正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立场与学术心态。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我们已不再可能孤立地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海外汉学”研究的后起之秀,作为观察研究本土文化的“他者”,有着异于“本土”的身份与角色,在与“本土”研究的互补与互动中,一方面构成了在研究方法、学术理路、理论设置、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另一方面,也与“本土”形成了互文关系,“本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可以开掘的学术资源,海外汉学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给“本土”研究带来了强劲的震撼和冲击,共同建构了维度开阔的学术共同体。
学术不分国界,但对于人文学科来说,理论背后存在自身的学术谱系和政治、经济或民族的“场域”;同时,一些国外学者存在着理论上的预设和过度阐释,使其对中国文学及其背后的文化传统、历史源流等问题的剖析和表述上依然存在“隔”的感觉,也缺少“本土”研究者真切的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因而,在肯定“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一些学者及评论家极端地将“汉学视角”建构成权威性的学术高地,甚至形成了“惟海外至尚”的风气,产生了“汉学心态”的新偏向。所谓的“汉学心态”并不是绝对的崇洋媚外,而是不加选择和过滤地“拿来”,形成了盲目的“逐新”风尚,这将非常不利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对“汉学心态”的学理性反思,祛魅被神化了的“汉学视角”已成为学科发展的需要和必然。
一、特殊历史“机缘”下的“海外汉学”冲击
自上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和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Prusek),分别在美国和欧洲开始对晚清到当代的中国文学和文化动力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考察。60到70年代,海外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不断增加,中国文学研究也逐渐演化为名副其实的“学科”阶段,不再附属于传统汉学。①可参考刘若愚《中国文学研究在西方的新发展、趋向与前景》和戈茨(Michael Gotz)1976年的研究报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等文中观点。此后,理论背景不同、学术立场各异的海外学者们,依据自己的思想方式、价值取向和学术个性,发展出形态丰富、内涵深刻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叙述。但这一时期并不是“海外汉学”冲击最为强烈的时代,“海外汉学”真正在国内备受推崇,应该追溯到80年代的特殊历史“机缘”。
80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在这一“拨乱反正”的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工作也因贴近社会现实而备受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在经历了“填补空白”以及对思潮流派脉络进行系统性梳理的阶段后,80年代中期,在大力倡导“思想解放”、“回归‘五四’和强调启蒙主义立场使现代文学研究更加超越意识形态的制约”②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等学术理念的引领之下,人们在相对自由活跃的学术氛围中急于打破惯性思维的束缚,重新重视文学的人性表达、审美价值和作家创作的“个性化”与“自主化”;同时,国内学者对于新鲜的汉学译著、外来的理论和方法的企及也已经变得非常迫不及待了。如此一来,来自西方的存在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法以及各种现代主义理论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掀起了一轮“观点热”“方法热”“理论热”,这样的一种“升温”与理论冲击,的的确确给许多年轻的学者带来了“精神松绑”的快感与学术的灵感与冲动,也为整个现代文学学科研究带来了新的学术气象。而作为外国人或身在海外的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各个维度的研究所形成的“海外汉学”也在这一时期大受追捧。这其中,夏志清及其文学史叙述首当其冲。
许多关注“80年代”的学者都曾提出,对80年代现代文学史写作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海外70年代出版的两本文学史: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集中探讨了1917—1957年间中国新文学中成就最高的小说一门的创作历程,其英文版于1961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中文繁体字版于1979、1985年分别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出版,并在80年代初,在“众声喧哗”之中进入了大陆学界的视野,③据考,《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进入大陆早于中文版的,作者在《重会钱钟书纪实》一文中曾对此有过表述,但从当时一些国家级图书馆并未有此书的馆藏记录以及一些学术权威对此书的英文版知之甚少的情况判断,此书的英文版在当时的大陆影响甚微,待到香港的中文版进入大陆后,其影响力及知名度才逐渐扩大。对大陆学界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据陈思和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大学毕业后不久看到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一阅之下,感到‘轰溃’”④吴越:《他提供了文学史另一种写法——海内外学者缅怀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文汇报》,2014年1月2日,第006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波及的绝不只是小群体,这种“轰溃”甚至撼动了学界,当时的现代文学研究权威唐弢等也早在其1983年发表在《文学评论》《社会科学战线》上的《复信》与《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中分别提及了夏志清及其《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的最大贡献在于“寻找到了一种更具备文学意义的批评系统”,他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①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页。;他打破了“鲁郭茅巴老曹”的传统格局,独标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凌淑华、师陀、端木蕻良等此前现代文学史中被忽视的文学大师和文学名家,建立了以“文学审美”为旨归的批评原则,“对80年代大陆重评作家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②贺桂梅:《“现代”“当代”与五四——新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变迁》,《历史与现实之间》,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同时,夏志清的著作是一种个人表述,他并不十分热衷于理论,表达的是个人观点,并成一家之言,为当时单一的“教科书”式的文学史研究界吹来了一股新鲜之风,展示了一种与之前统治大陆文学界的政治标准完全不同的“纯文学”准则,不再以政治的“正确”为取舍的唯一标准,表现在其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道德感的关注,以及对阶级分析的自觉远离,而这便是其影响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在学科的复原及“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起到了“催化与促助”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示范作用。当然,对于这种外来的“新鲜之感”,学界的态度也非莫衷一是。据考,1981年6月,时任鲁迅文学馆馆长的李何林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的演讲中,“着重提到了夏志清及其《小说史》,将其作为海外污蔑鲁迅先生的典型例子”③万芳:《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重写文学史”思潮为中心》,《华文文学》,2016年01期,第18页。;王瑶也曾表示,“就对作家的评价来说,国外学者的某些观点也同我们有很大差别,他们常常重视一些我们注意较少的作家而忽略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家……当然,对一个作家如何评价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不能笼统地认为国外学者的观点就一定是科学的……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写出正面的好的文学史,以抵消错误影响”④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2005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在大陆正式出版,随着“学术环境”与“学术策略”的开放与变化,对于夏志清本人及其文学史观的论争也一直不曾停息。由此观之,综合各家之言,无论是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还是90年代之后的多元化思潮,夏志清及其《中国现代小说史》都作为一种“他者”的存在,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变化中,与各种文学思潮展开了激烈对话。《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炙手可热可谓是一种“生逢其时”,但其偶然之中存在着必然,它使得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学科及文学史的表述中开辟了新的批评维度,并为李欧梵、王德威等有着师承关系的“哈佛学派”,以及以刘禾、孟悦、黄子平等为代表的所谓的“第三代”海外学者的有关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观点言说及其传播与接受提供了成长与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也是在特殊的历史“机缘”之下,“海外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首次重大的冲击。在此之后,以德国汉学家顾彬等为代表的非华人海外汉学家也因其“现象式”的横空出世而备受关注,也使其在评判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时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从对微观的事件所窥探出的“本土”与“他者”之间的互动来看,我们能够看到,国内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接受态度虽然“褒贬不一”,但仍是以肯定和赞扬为主,“本土”与“他者”的学术交融与往来日益密切、深入,海外学者介入大陆学界的积极姿态也愈加突出。而这样的历史机缘与历史现状也是“汉学心态”衍生的重要前提。
二、海外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悖论与盲区
无可厚非,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确有其优长,也有许多新锐而有价值的著述,并在比较文学的视阈下,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的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的研究也比比皆是。但对于“他者”的冲击我们不应该失却应有的学术反思与警醒。如果说,我们可以大致将海外汉学家依据是否拥有中国国籍而进行分类,那么就不难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就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在这样一个“本土”与“他者”互动的过程中,存在最大影响力的并不是外国汉学家,如从事萧红研究的葛浩文、从事沈从文研究的金介甫、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叶维廉、从事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耿德华等,他们对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界提供了不同的参考维度,但却并未构成所谓的“挑战”,而真正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是主要来源于“二战”后由华人地区迁移至美国的华人学者,在当代以李欧梵、王德威等最为突出。李怡曾表示,“观察分析这些美国华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与其说他们所反映的是当代美国的学术姿态或汉学主流,还不如说是呈现了一个生存于美国社会的中华文化的亚文化群落的特殊心态”①李怡:《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7页。。对于这一研究对象的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对“何人的汉学”的追问也是对“海外汉学”反思在本体上的追根溯源。可以说,在海外,尤其是西方,汉学仍是一个相对冷僻寂寞的领域,而如果坚持传统汉学家只专注考察某一个文学领域的研究方法,那么其研究成果只会在其活跃的学术圈子里有一定的反响,更别说对“本土”产生冲击或重大影响了。因此,海外的华人学者会加强研究的“可操作性”,加深对理论和方法的剖析,进而与现代文学现象研究相结合,实现对中国文学的“想象”。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迅速被大陆学界所接受并应用。
举例说明,于2001年在大陆正式出版的《上海摩登》一书中,李欧梵将成熟于20世纪的“颓废”美学的概念引入到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之中,完全挑战了传统的审美标准。《上海摩登》一书中,单独设计了一章(《色,幻,魔》)的内容,从“现实之外”“历史小说”“内心独白和阿瑟·显尼支勒”“都市的怪诞”等角度专题讨论了施蛰存及其实验小说,对施蛰存的研究也从此大量“出土”。据统计,在《上海摩登》出版的前一年(1980年),关于施蛰存的研究文章数量仅有25篇,而在其出版后的十年间,同类研究文章数量的总和已达到751篇,到了2010年,当年度的相关论文数量已达960篇,甚至超过了前10年的数量总和。①本节以上数据参考万芳:《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重写文学史”思潮为中心》,《华文文学》,2016年01期,第75,76页。无独有偶,最早于1996年刊登在《学人》第十辑上的王德威所撰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同样在国内产生了强烈的撼动,充分说明海外学者对作家与文学现象的打捞工作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界对海外研究似有“跟风”“逐新”之嫌。
那么,对于我们追捧的“学术高地”我们是否需要存有“问题意识”及质疑的权利?事实上,一些学者已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对于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说,不可否认的是自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进入大陆学界以来,引起了大陆学界对作家评价以及文学史标准等方面的学术地震后,再也没有哪个海外汉学家的观点能在“重写文学史”框架下像“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一样被反复讨论。②李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 1期,第81页。对于这一观点,我们从字面理解,其想要突破的是“现代文学起点”的问题,王德威认为,与“五四”相比,“晚清”所存在的“现代性”萌芽显然要丰富得多,而“五四”只是一个“窄化了的收煞”,甚至是对“现代”的终结,因此,从“现代”意义的角度上分析,现代文学的起点势必要前移。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但却并非王德威的首创。在此之前(1996年,《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首次发表),80年代中期,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等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追溯以“五四”为标志的“现代”,并将戊戌变法看作“五四”的前奏;80年代后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也已普遍兴起“晚清”热和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热,陈平原也曾在其《清末民初小说理论概说》(1988年9月)等文章中多次提出晚清“新小说”对“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和铺叙;1991年,由范伯群、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外文学比较史:1898—1949(上)》中共用了两编十一章,十几万字的篇幅,从“‘西化’,还是现代化”“现代对传统的认同”“‘新小说’: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开端”等多角度对现代文学的缘起、发生,以及晚清的戊戌变法使得中国文学产生的呼应世界潮流的变化,促成了“现代文学”的大变革等问题进行说明,列举了大量关于思潮、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实例,表明现代文学的开端在“五四”之前已经存在。在此基础之上,王德威进一步在时间和理论的向度上推进了前人对于“现代性”的研究,确立并巩固了“晚清现代性”的文学价值。但不得不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标语式概念的提出是很讨巧的,造成学界几乎“一边倒”的现状,也不乏有着“广告效应”之嫌。同时,王德威自身对于“现代性”的阐释也存在着一些矛盾,诸如其对“现代性”标准的界定问题的观点,他主张不能唯西方现代标准马首是瞻,但另一方面又以西方理论的话语体系为界定“现代性”的准绳,忽视了“五四”及其后来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作用,窄化了中国文学场域的民族性等。再如,李欧梵在1986年在京举行的“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做了题为“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的发言,在发言以及其后来发表的《铁屋中的呐喊》中都反复提到了在上海大陆新村鲁迅故居卧室中挂着的两幅描绘裸体女人的德国木画:《入浴》与《夏娃与蛇》。李欧梵认为,这两幅画的意趣与其会客室中较有社会意义的油画和剪纸画形成了鲜明对比,并得出结论:“我认为鲁迅一生中在公和私、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存在了相当程度的差异和矛盾……他在个人的内心深处,甚至个人的艺术爱好上,似乎并不见得那么积极,那么入世,甚至有时还带有悲观和颓废的色彩。”①李欧梵:《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鲁迅动态研究》,1986年第11期,第41页。作者甚至还将鲁迅最著名的小诗《自嘲》也沿着这一理路去分析,认为所谓“小楼”便是“鲁迅在上海的居所”,“那么,当他一个人躲在小楼二层的卧室的时候,也许偶尔也会有点兴致鉴赏镜台前的裸体版画吧”②李欧梵:《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鲁迅动态研究》,1986年第11期,第52页。。乍看之下,“鲁迅颓废”的论断在那个时代的学界听来确实很新锐先锋,甚至有些惊世骇俗,但从审美对象和形式的角度分析,这一观点显然有失偏颇。我们承认鲁迅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后的几年,确实有过“荷戟独彷徨”的迷茫与颓唐,但他似乎并未躲在S会馆去鉴赏裸体绘画,我们可以判断鲁迅对于性与爱的审美角度也是加以取舍的,由此将鲁迅片面地冠之以“卫道之士的纯系颓废”恐怕也未必妥当。
从这些进入历史细部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出,在海外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在那些阅读的快感之余,以及那些精彩的理论话语背后,缺少了一定的“分寸感”与历史同情,也存在着学术的悖论和理解层面的盲区。对于这些问题不辨真伪地一味神化,甚至将其当成“本土”的学术标准,就会愈加走向“汉学心态”引导下的学科误区。
三、直面祛魅后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汉学心态”的惶惑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被我们奉若圭臬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依然存在论证的逻辑漏洞和偏差。再以以上二位学人为例,事实上,李欧梵并不是一定要走入“鲁迅颓废”的这种文化的“偏执”,他对于鲁迅在“颓废”上的打捞是试图挖掘在我们所阐释的政治意识形态抑或是思想革命之外的、非政治的鲁迅,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是将所谓的“颓废”看成了现代主义的核心;王德威也同样熟稔于用宏观的问题理论去阐释一些文学规律,尤其是一些后现代理论,再结合从夏志清至今延续的“感时忧国”的文学传统和理念,有时就会形成对文本和作家理解上的“两张皮”。对此,国内学者对此现象也进行了一番总结和清理,发现很多“海外汉学”的研究,是在颠覆意识主导下对问题的挖掘,再加上不受限制地对资料进行占有,并带有预设性质地、运用各种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解读,就可以不断推陈出新。
当然,对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祛魅”并不是狭隘地尊己卑人,我们对“汉学心态”产生的历史前提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在特殊历史语境下对“他者”的介入进行镜像的反观,而这种“汉学心态”以从“他者”初介入时的冲击与互补时的萌芽状态,不断地从边缘走向中心,从90年代至今已呈愈演愈烈之势,需要我们结合学科,准确查找存在问题的表征及根源,直面“汉学心态”带来的“惶惑”。
我们的“惶惑”首先来自我们对具有整合力量的理论有所欠缺的迷茫。李怡就曾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一直缺乏足够的理性框架的支持”①李怡:《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05期,第9页。。我们的学术长期以来就是出于一种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判断,常常是进行非黑即白、非革命即反动的价值判断。而为了增加学术理性的说服力,我们也曾借鉴苏联的一些批评术语,似是而非地运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术语解释一些“本土”的较为复杂的文学现象。进入新时期以来,学界也致力于寻找完整的理论模式,而理论模式的缺失也导致了学科边缘化的焦虑。就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文学评论来说,“多元的标准”相对于用一个既定的政治标准去压抑学术的生长来说的确是一种解放,但如果缺少了这种最基本的理论模式和标准,那么也只能是在众声喧哗中随波逐流。那么如此,我们就可以将海外汉学长期受到追逐的现象理解为其更多地源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努力实现“‘从边缘到中心’位移的强烈诉求”②张江:《切实反思“汉学心态”》,《人民日报》,2017年2月17日,第24版。。因此,站在中国学者的角度,我们在对时代转型和学科的边缘化保持一份平常心的同时,更应该坚守自己的本体立场与文化自信。
其次,文化研究的侵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缺陷,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戳中了学科的软肋。从90年代开始,“国学热”“通俗热”等现象层出不穷,而既有的文学资源在解释这些前所未有的精神现象时已显得很吃力,甚至一度陷入“失语”的地步,因此,借助文化研究的转向也就顺理成章了。而与此同时,也为强调“文化性”研究的“海外汉学”释放了有利的介入空间,形成了多元多维的研究视阈。但目前的学界也出现了一股“仿汉学”的解读,将其立场往往立足于批判而忽视真正的真实的历史,更加关注的是历史文本背后的“权利关系”,舍本逐末,造成了“泛文化”的研究倾向。同时,一些海外学者对中国的国情和民族性知之不多,也缺乏本土学者真切的生活感受、社会情怀与问题意识。这需要站在“本土”和“文学”自身的立场去反思,不可人云亦云。另外,很多海外汉学家所编纂的文学史受众是外国人而非中国人,势必会以其受众所熟悉的话语体系去表达观点,巨大文化背景差异下的文化侵入也会导致文学研究的偏差。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回到闭门造车的时代,对于西方文化的研究经验我们需要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客观看待海外汉学研究的同时,主攻自主创新的探索,相信从自己的中国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审美与价值观,建立起应有的文化自信。
质言之,“汉学心态”很大程度上也是“本土”与“他者”的研究双方对彼岸研究的语境和现状的隔膜造成的。因此,我们不仅要对“汉学心态”予以警惕,也要防止我们“本土”研究的话语霸权,要看到我们存在的硬伤与海外学人的优长。例如,王德威等学者的文章行文风格独特,内蕴深厚,旁征博引,“有古代雅士之遗风”,也曾被学界同仁评价为“就像四六骈文,华丽得很”。这与其从小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与专业的学术训练有着直接关系。“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正所谓“质待文也”,我们如何用干瘪枯燥的“消费性”文字去对抗绮丽丰赡的评论语言,怎样打破隔膜,如何让我们“本土”的最富同情和社会意识的学术瑰宝体面地“走出去”,也是我们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