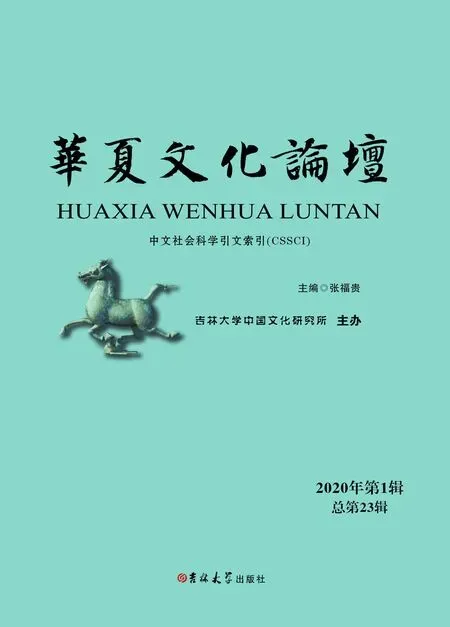挥不去的文化乡愁
——《现代文学》杂志海外华人生活小说研究
2020-11-17徐英春
徐英春
【内容提要】《现代文学》小说作家以跨文化的笔触描写了华人们在异域文化环境中的挣扎与辛酸,字里行间透露出浓郁的文化乡愁。固守文化形式者在文化形式的保持和坚守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渴望融入异域文化者在主观态度和外在行为上都是积极的,但是没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荣辱与共的归属意识,他们只能被视为异族客居者;缅怀往昔盛景者曾经拥有过灿烂人生、辉煌历史,而背井离乡到美国的寄居生活,不仅使他们与曾经参与建设的现代中国社会严重脱节,而且在侨居之所也只能作为旁观者、边缘人寂寥生存。
《现代文学》①台湾《现代文学》杂志创刊于1960年3月,公开发行了13年,51期,于1973年因经济原因第一次停刊。1977年得到经济支持复刊,出版了22期之后,于1984年第二次停刊。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李昂、施叔青等一大批年轻作家都是从这个刊物起步并成长起来的。他们在该刊发表了大量的重要的作品,对于整个台湾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除了诸多优秀的原创性的小说,《现代文学》还系统地、大量地介绍了西方现代艺术学派和文学潮流。卡夫卡、劳伦斯、福克纳、加缪、沃尔芙、乔伊斯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大陆广泛推介的西方现代派作家在当时都曾经以评介专号的形式被郑重介绍过。是1960年在台湾创刊的一份文学杂志,曾因经济原因两度停刊。第一阶段发行期间,刊载了70位作家的206篇小说,对台湾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生活给予了非常前卫的关注与思考,对推动台湾现代派小说的创作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小说描写的是华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经以《乡愁》为题,描写了海峡两岸人民隔海相望的离别之苦,而在《现代文学》的此类小说中,作家们以跨文化的笔触,描写了漂洋过海的华人们在异域文化环境中的挣扎与辛酸,字里行间,透露出浓郁的、充满悲情的文化①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涵盖所有一切人类的活动成果。而中国文化则指中国创造并传承数千年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所有一切成果,既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制度、行为方式,也包括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乡愁。
具体来看,《现代文学》小说中所展示的文化乡愁主要源自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尊崇既有文化传承,固守中国文化形式者,如《约会》②欧阳子:《约会》,《现代文学》,1964年第21期,第1页。中的留学生美莲、《安乐乡的一日》③白先勇:《安乐乡的一日》,《现代文学》,1964年第22期,第50页。中的家庭主妇依萍、《秋叶》④欧阳子:《秋叶》,《现代文学》,1969年第38期,第59页。中的东方历史学权威教授王启瑞等;第二种人是竭力调整自我社会定位,渴望融入西方文化而不得者,如《芝加哥之死》⑤白先勇:《芝加哥之死》,《现代文学》,1964年第19期,第1页。中的吴汉魂、《瓷马》⑥从苏:《瓷马》,《现代文学》,1968年第36期,第41页。中的魏建、《钟鸣鼎食之家》⑦张北海:《钟鸣鼎食之家》,《现代文学》,1971年第44期,第198页。的刘时等;第三种人是曾经跻身于中国社会文化主流,当下只能在西方社会边缘缅怀过去者,如小说《弟弟》⑧叶灵:《弟弟》,《现代文学》,1964年第19期,第70页。中的弟弟、《谪仙记》⑨白先勇:《谪仙记》,1965年第25期,第111页。中的李彤、《冬夜》⑩白先勇:《冬夜》,《现代文学》,1970年第41期,第127页。中的知名教授吴柱国、《蛹》⑪刘大任:《蛹》,《现代文学》,1970年第41期。中的莫老等。
《现代文学》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形象在文化形式的保持和坚守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似乎唯有文化形式的存在才能证明自己在文化归属和精神归属方面的坚定立场。尽管背井离乡,选择了西方文化环境作为生存地和发展空间,但在他们心中,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传承,泱泱中华大国的情结仍然根深蒂固。对于祖祖辈辈传承与尊崇的中国文化传统、观念,他们无法忘却,无法抛开。对他们来说,中国独特的文化传承,中国人独有的思想意识观念已经融入了自己的生命血脉中。而他们这种执着,在中国历史上传承已久,“在孔子用被发右衽和束发右衽的习俗区分华夏夷狄的行为中,已明显流露出华夏民族的优越感。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开拓,这种民族优越感最终发展为一种民族自我中心意识”⑫邴正:《当代人与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9页。。这种优越感,即使是在中国上个世纪遭受了几乎灭顶的挫折后也未曾湮灭。经过了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这种意识已经潜移默化为无数中国人的血脉传承,根深蒂固,牢不可摧。
小说《约会》中的台湾留学生美莲爱上了美国同学保罗,在保罗面前,她总是刻意强调自己的东方文化特征,喜欢保罗叫她的中文名字。她喜欢在保罗面前穿中国女性的典型服装旗袍,“以前,在台湾的时候,除了毕业谢师会那天,她从没有穿过旗袍”。但是,“保罗第一次跟她约会那天,她把临别台湾时她母亲强迫她订制的几件旗袍,全部从箱子底翻了出来,一件一件挂进衣柜子里。保罗首次看到旗袍,就欢喜得不得了”。对于保罗来说,穿着旗袍的美莲展示现出来的是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东方美,而对于美莲来说,“她穿旗袍,主要原因并不是讨他的喜欢。她的目的是要强调她的不同;她是中国人,不同于美国女孩”。旗袍成为美莲在西方文化中心彰显个人精神文化归属的一种符号象征。
小说《安乐乡的一日》中的依萍因为丈夫伟成的格外优秀而跻身于美国中上阶层,作为一名全职的华裔家庭主妇,她住的“是最时兴的现代建筑……厨房一律是最新式的电器设备”,然而,完全西式的家庭装饰和配套设施,让依萍找不到家的温馨感觉。这个堪称豪华的家对于她来说,“像一间装满了机械的实验室一般。依萍一天大部分时间,便在这所实验室的厨房中消磨过去”。左邻右舍也不是她熟悉的旧日面孔,邻居们“总争着向依萍指导献小殷勤儿,显出她们尽到美国人的地主之谊。这使依萍愈感到自己是中国人,与众不同,因此处处更加谨慎,举止上常常下意识地强调着中国人的特征”。依萍保持着高度的民族自我中心意识,对她来说,传承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即使遭遇了近现代的挫折也依然是璀璨夺目的,她刻意强调自己的民族特征,希望借此回击左邻右舍言谈举止中对华裔华人流露的鄙视。
小说《秋叶》中的东方历史学权威教授王启瑞,在美国谋生,与美国女人结婚生子,可是“生活方式和思想方面,一点都不肯洋化”。他很疼爱他的儿子,可是疼爱的方式却是中国传统家长式的“爱之深,责之切”。在他的儒家传统方式教育下,“敏生的发色和眼珠,是属于东方人的。但他白皙的皮肤,高凸的额头,深邃的眼神,挺直的鼻梁”显示出他与中国人的不同,然而,“这个在美国长大的男孩,居然讲得一口极流利的中文。而且,他的进退举止,知礼能让,也像是个孔孟传下的纯粹的中国人”。
尽管性别、年龄、身份、职业各不相同,但生活在美国的美莲、依萍和王启瑞似乎都陷入了同一个怪圈——我要通过身体力行让美国人知道并相信我是中国人。而这种怪异行为,带给他们的结果并不是他们期待的。美莲因为固守中国文化形式导致美国男友茫然不知所措,自己也在纠结中痛苦伤心。依萍因为固守中国文化形式并强迫女儿说汉语使得自己在左邻右舍中永远是客居者,女儿也宣称自己只是爸爸的女儿。王启瑞因为固守中国文化形式,导致美国妻子抛弃家庭与人私奔,儿子迷茫、痛苦,不知道自己到底算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渴望在跨文化冲突中找到自我,但是却因既有文化背景的强势导致了自我意识错位。“自我意识通过文化自我认同的活动得到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肯定,体现了人与文化在精神上的一致性。文化使人脱离自然,使人成为自我,使个人和社会成为一个整体。”①邴正:《当代人与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7页。而对于美莲们来说,附着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他们跨越两种文化之间藩篱的根本障碍。
与美莲们固守原有文化形式,拒绝融入当地社会环境不同,第二类文化乡愁的所有者在主观态度和外在行为上都是积极的。他们渴望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并身体力行,竭尽所能去争取。然而,作为异族文化的高级人才,背负着深刻的中国文化烙印,他们想要融入当地社会,并不是单方面采取积极行动就可以的。
《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自从踏上那片土地,就开始积极努力地为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生活而奋斗。他在美国苦熬了6年,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在获得奖学金之前,为了满足基本物质需求,他所有的时间是按分秒计算的,然而,如此勤奋,如此努力,最终换来的却不是他所想要的。在他准备博士资格考试的时候,远在台湾的一直期待他学成归去的母亲去世了;在他求学的第三年,女朋友寄来了结婚喜帖;在他终于学成毕业的典礼上,同乡们都跟家人一起兴奋地拍照留念,而他是孤单并孤独的。因此,毕业当天,没有丝毫成就感的他落寞地回到地下室,唯一的感觉是茫然无所适从。当基本的生存需求问题解决之后,当生存的基本条件满足之后,高层次的情感需求、精神需求都需要同源文化的支撑,仅有的亲人离世,爱人转投他人怀抱,未来是看不到希望的一片迷茫……在经历了六年的苦熬之后,吴汉魂彻底失去了精神文化的支撑。他想在妓女萝娜身上找到一点点自我存在的意义,然而,肉欲宣泄之后留给他的是加倍的绝望。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死亡,他默念着自己工作申请上的自传:“吴汉魂,中国人,32岁,文学博士,1960年6月1日芝加哥大学毕业……1960年6月2日凌晨死于芝加哥,密歇根湖。”
《瓷马》中的魏建与吴汉魂经历相似,也在异国他乡全力以赴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二十八岁的魏建,文学学士、硕士,爱好文学、古典音乐、社会学、心理学。如此博学而才华横溢,但他却要跟本土一群靠救济生活的人一起排队争取端盘子的机会。他在美国努力奋斗期间,他国内的女朋友成了别人的妻子和妈妈。他却一直保留着女朋友送给他的那件礼物——断腿的瓷马。收到那份礼物的时候,还没有打开包裹,他就把马的后腿摔断了。后来他看着这瓷马就好像看到了自己——想飞跑却断了腿。而压倒他精神支柱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同为侍者的异族同事对中国人的整体谩骂和污蔑。尽管他努力想证明自己跟当地人一样有人格尊严,但是在他的同事眼中,他身上集中了他身后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集体劣根性——懦弱、虚伪、贪婪、低贱。沉重的物质负担和经济压力,被异族蔑视的屈辱,几近崩溃的精神信仰,使孤军奋战的他身心疲惫。于是,他选择了在异国他乡放弃生命的挣扎,以自杀结束自己短暂人生的所有苦难。
同样是留学生身份,《钟鸣鼎食之家》中刘时的生活虽然也不轻松,但是有温馨家庭作为精神支撑,所以状态要比吴汉魂和魏建要略好一些。即使如此,一周25个小时端盘子,还想门门功课拿A,早日还清家里的债务,这对刘时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为了多一些时间看书,并且多练习一下英文,刘时接受了一份帮佣工作,搬到了山上貌似有钱人的桑特太太家住。然而,从进入桑特太太家开始他就有一些说不出的感觉,“绝不是自卑,刘时没有理由感到自卑……家里虽然不富,但也不穷”,他把这当成一份正常的、按劳取酬的工作,但桑特太太却把他当成了低贱的可以被肆意剥削和驱使的下人。初次见面,她就非常婉转地表达了不希望同他一起吃晚饭的意愿;希望他注意房间的清洁卫生;把佣人的制服挂在他房间的壁橱里;让他住窗户面对着车库的看不到外面的房间。而以俯视姿态面对他的不仅仅是桑特太太,桑特先生对他的侮辱和打击更为彻底,他视刘时为出卖肉体的娈宠并付诸实际行动。
在《现代文学》小说所描写的那个年代,能够背负着亲朋好友的殷切期待远渡重洋求学的,都是具有精英能力和素质的佼佼者。能够从莘莘学子中脱颖而出,他们无疑是优秀的。到达大洋彼岸后,他们的心态和行为也都是积极上进的,然而,现实生活却使他们连连受挫,打击不断。刘时属于其中的坚韧者,即使遭受了严重的民族歧视和同性骚扰,也仍然愿意背负着压力继续前行,而吴汉魂则因为灵魂上的绝望投水自杀了,魏建也因为物质贫困和精神孤独的双重压力放弃了生命的挣扎。积极努力却无论如何也融入不了当地社会,除了物质上的贫乏所带来的艰难,更多的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所致。“文化指的是共享的系统。正是这种共享系统使文化成员能够相对有效地进行交流。”①[美]布拉德福德·J.霍尔:《跨越文化障碍——交流的挑战》,麻争旗等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6页。显然,类似吴汉魂、魏建、刘时那样的华人是无法与当地人共享同一文化系统的。没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没有荣辱与共的归属意识,他们永远只能被视为异族客居者,而且是可以被俯视,甚至被蔑视的对象,因此,即使他们已经算是国内的精英人物,可是在异域的土地上也会被恪守本土社会文化规则的当地人所排斥。
作为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美国在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方面也是举世瞩目的焦点。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无数的中国精英排除万难,前赴后继地踏上这块土地求知问学,甚至终生滞留于此。美国本土居民因此具有无比的群体自豪感和优越感。因此,也就有了无数跟桑特太太同样论调的美国人:“又要住在我们的国家里,享受一切自由、平等、民主,以及最现代的文明,又要反对我们的一切。他们要是不喜欢美国,随时可以回去!”也正是由于本土居民对外来者的排斥和蔑视,《约会》中美莲与保罗在饭店才会遇到拒绝有色人种用餐的事件。而《瓷马》中,魏建的同事之所以会由魏建的失误推衍至所有中国人,也是因为在当地人心目中,即使落魄如他们需要救济端盘子者,也比魏建这样“低等民族”的华人要高贵、诚实得多。
第三种文化乡愁来自曾经拥有过灿烂人生、辉煌历史的华人。他们或者在父辈福荫下得到过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享受,或者本身是曾经参与过国家、社会发展变化的精英、栋梁之材,于是,当他们在大洋彼岸那片陌生的土地上找不到文化归属感的时候,缅怀往昔就成为一种自然选择。
小说《弟弟》中的主人公弟弟和《谪仙记》中的李彤属于前者,他们的父辈作为主流社会的权威人物,为他们提供了优渥的物质条件,让他们能够衣食无忧,早早地踏上高层次精神追求的路途。小说《蛹》中的莫老和《冬夜》中的吴柱国教授则是跟李彤、弟弟的父辈属于同一层次的,都曾经在国内主流社会拥有一席之地,是在自我人生价值方面得到较高程度满足的精英人物、领袖人物。
弟弟在父爱宠溺中长大,他在中学时期的作文中写道:“在这世界上,没有比父亲更伟大的了。”父亲是他心目中巍峨不可攀缘的高山。然而,一朝突变,“在弟弟快要完成大学的学业那年,像午夜的山崩一样,父亲突然被牵进一件巨大的案子里被告发了”。弟弟的世界彻底毁灭了,他无法接受父亲沦为阶下囚的现实,也无法忍受周围人的议论。更重要的是,弟弟的精神世界垮塌了,“在中国人看来,没有比道德价值更高的价值。中国人的自我多是道德自我,即人格理想和良心”①邴正:《当代人与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3页。。因此,当父亲被定罪之后,他在孩子的心目中高大完满的形象顷刻间被摧毁。父亲的形象与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相重合,象征着弟弟精神世界中的伟大、崇高,而这种形象一旦幻化为虚伪、丑陋,则弟弟一直以来信赖和追求的就全部变成了从来都不曾真正存在过的假象。因此,当父亲被宣判在狱中度过余生时,弟弟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对弟弟来说,他失去的不仅仅是父爱,同时失去的还有自己的自信、尊严和人生信仰。于是,他荒废了学业,离开了女朋友,选择了在异域他乡结束自己的生命。
同样享受父辈福荫,同样在精神世界垮塌之后选择自杀的李彤在小说叙事的时间点上要比弟弟早一些。在小说《谪仙记》中,“我”的太太惠芬和李彤、张嘉行、雷芷苓四人都是来自上海官宦人家的小资,属于享有各种特权的上流阶层。她们一起来美国留学,凭借着父辈的资历和财力,一度成为校园中引人注目的群体。然而,由于国内战争的缘故,原本家世显赫的李彤突然间失去了一切。没有家人亲情的呵护,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身处异国他乡的李彤从物质到精神都经历了一场震荡。曾经风靡校园的四人组合中其他三人先后都结婚生子,有了平凡但安宁的生活,可是李彤却始终孤身一人。“李彤不仅自以为漂亮,她着实美得惊人。像一轮骤从海里跳出来的太阳,周身一道道的光芒都是扎得人眼睛发疼的。”因此,即使失去了国内上流社会的背景,她的追求者依然不乏其人,有多金者,有智慧者,有专情者,可是李彤都没有放在心里。她拥有高薪的工作,过着可谓奢侈的生活。然而,国家民族的衰败,父母亲人的枉死,异域他乡的文化冲突,使她愈发感到孤独、忧郁。尽管依然年轻,可是她已经失去了人生信仰,找不到能够让自己停靠、休憩的精神港湾。大家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坐在一个白人的敞篷跑车里呼啸而过,没有多久,在雷芷苓给孩子办满月酒的聚会上,大家得到了李彤在欧洲旅行时自杀的消息。她是在威尼斯游河时跳水而死的,没有留下遗书。警察从她的包里发现了地址才通知到了她的朋友。一个光芒四射的美人就这样孤独地消失了。
无论是弟弟还是李彤,他们在家庭剧变之后颓丧的根本原因都源自信仰和思想的精神层面。弟弟和李彤都是传统官本位、特权阶级文化的受益者。他们出国留学的机会均来自优越的家庭条件和高位的父辈权势。到达美国之后,他们生活、学习的交际圈也依然与心中默认归属的文化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个圈子里,基于文化共享性的原因,他们的背景和资历被完全认可和接受,从而使他们能够得到与国内同样的、属于精神层面的愉悦感和优越感。“我家的门第和产业,加上父亲在那所学校的声名,使得他(弟弟)在海外过着安适的生活。”李彤也同样因为父辈的资历和财力,成为校园内令人瞩目的存在。而家庭变故的发生,除却伤及他们引以为傲的亲情,更重要的是摧毁了他们曾经的精神文化信仰,造成精神大厦的垮塌,以至于他们抑郁、颓丧、消沉、崩溃,直至完全丧失活下去的勇气。
相对于年轻的、无法继续享受前辈福荫的弟弟、李彤等人来说,衣锦还乡的旅美学者吴柱国教授和在美国安度晚年的莫老是时代背景大致相同的一代人。不同之处在于,吴柱国教授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而莫老则属于亲身参与了现代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实干派。他们曾经都跻身于中国社会的主流,亲身参与了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运动和历史事件,都曾经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享有精神层面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优越感。然而,背井离乡到美国寄居生活,他们不仅与曾经参与建设发展的现代中国社会严重脱节,而且在侨居之所也只能永远作为当地社会发展的旁观者、边缘人寂寥生存。他们在精神层面产生失落、抑郁情绪是自然而且必然的。
吴柱国教授凭借自己前期的个人奋斗成果在美国落寞度日。回首往事,当年跟他一起在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的朋友有官运亨通者,有碌碌无为者,也不乏枉死或病逝者,总之,都已英雄迟暮,韶华不再。虽然吴柱国对自己堪称轰轰烈烈的青春岁月是感到骄傲的,然而,在美国讲学期间,他却一直回避讲自己曾经参与建设过的民国的历史。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影响,而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锋人物,能够亲身参与国家发展变化的历史事件,吴柱国的确有着很多同龄人不可比拟的优越感和自豪感。然而,这种精神愉悦感,在他背井离乡之后,渐渐湮没在了数十年如一日的庸碌的日常生活中。当他曾经参与过的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被后人抨击时,作为世人眼中的著名学者、历史专家,他竟无言以对。那位哈佛的学生在论文中彻底否定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徨、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负着重大的罪孽,开始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投入极权怀抱,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有的奔逃到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他们的运动瓦解了,变质了。’”在那个哈佛大学的学生眼中,吴柱国就属于“奔逃到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因此,尽管不认可对方的观点,但是,吴柱国却无颜与之去论辩:“我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在那种场合,还有什么脸面挺身出来,为‘五四’讲话呢?”
吴柱国对于往昔岁月有骄傲,有愧疚,而耄耋之年的莫老,则更愿意在熟悉的社会人际关系中回忆自己曾经亲身参与过的、国家民族的荣辱兴衰。居住在美国西海岸的“莫老退休已经十几年了,至今常来探望他的人当中,大多数仍是当年喧嚣一时的闻人、政客。这批人虽然早已在这块异乡的土地上生了根,重起了炉灶,他们还是隐然以莫老这里作为另外一种社交活动的中心”。作为曾经亲历并参与了国家荣辱兴衰大事的重要人物,即使背井离乡,客居他国,即使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莫老仍然具有相当的凝聚力。然而,实现自我价值的那种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对于身处异域他乡的莫老来说却早已成了奢望。虽然,在国内的参政道路并非坦途一片,但是,寄居于大洋彼岸之后,参与政事,探寻社会发展的方向等属于社会主流的大事就成为遥不可及的历史了。他在垂暮岁月中为搞历史研究的最小的女婿口述自己亲身参与过的、重要的历史生活,但是,对于能否发表公布于众,他却并不在意,因为“发表不发表都无所谓,反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逝去的已然逝去,未来岁月却只能在完全陌生的异域度过。垂垂老矣的莫老,作为忧国忧民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典型,只能怀着渺茫的希望,给小女儿刚刚出生的孩子起名“乃瞻”。①“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出自魏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意思是看到以横木为门的房屋(自己简陋的家),我兴奋不已地跑着。
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现代文学》小说所描写的那种挥不去的文化乡愁,既属于小说人物,也属于小说创作者。其中很多作品人物身上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和经历。上个世纪中叶,在《现代文学》这类小说创作的年代,台湾地区当时正处于社会剧变时期。由于地理位置远离大陆主体,加之经历了荷兰、日本等异族占据统治时期,台湾在历史、文化传承方面都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而国民党收复台湾后,台湾文坛原有流派因为政治、文化的原因处于萎缩状态,而迁到本地的文学队伍与大陆完全隔绝,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学传统也被彻底隔断,反共抗俄文学统领文坛,主流文学陷入了僵化、教条的模式。在政治方面,国民党所进行的高压、独裁统治,也使台湾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波动和社会变革。这一切都为《现代文学》杂志的产生埋下了伏笔,也为后来刊载于其上的蕴含着文化乡愁的文学作品埋下伏笔。
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随着岁月的流逝凝结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给亿万华夏儿女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生活习俗;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行为准则,中国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判断标准。中国人的血脉里充斥着中国文化的基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负载着中国文化的点点滴滴。然而,生活在异域他乡的华人却不能背离人的根本性质,“人属于社会性动物,人必须与他人结为一体才能生存,没有人能够脱离社会单独生存。‘社会’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也是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方式”②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无论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还是小说创作者本身,都需要在当地社会中生存。《现代文学》小说的作家们以感性的文学形式记录了海外华人在大洋彼岸的社会生活,通过小说,让人们了解了在与当地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华人华裔所遭遇的各种挫折、艰辛。由于身上所背负的深刻的中国文化印记,华人华裔在世界各地的跨文化生活都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文化产生了隔阂。无数华人华裔的生活,都与《现代文学》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因为自己所背负的文化乡愁而无法彻底融入当地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