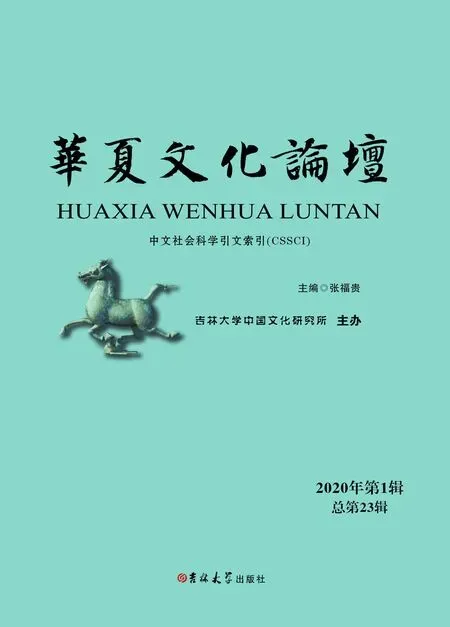一幅伸展着的文学地图
2020-11-17叶周
叶 周
【内容提要】我自己的文字里,人物不仅来自我常年生活过的中国上海和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他们还散布于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我与我笔下的这些人物或许曾经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遭遇过,也可能我们其实跨越着世纪的鸿沟,本不可能见面,却在一种文学想象的氛围中相见了。我把这些人物故事发生的地方在地图上标出来,便形成了一张有趣的地图。我的文学地图,恰如其分地构成了我的文学创作的想象空间。而这份私人地图只有放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宏观图景中才更具意义。海外华文文学对于华语文学的贡献,就是为世界华语文学和中国文学提供了一幅地域广大同时又内容丰富的人文景象。这些丰富的内容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史学上都会逐渐彰显出其意义和价值。海外华文文学不仅给本土的中国文学增加了多元化的丰富内容,并且使华语文学走出了国境的疆域,发散延伸到世界的广大区域。
我所撰写的文学作品中,人物行动和生活过的地方逐渐增多。我是一个喜欢行走的人,在中国的时候就因为工作之便,去了很多省份。到美国留学后,即便在生活尚十分艰辛的自费留学生时代,稍有积蓄就从美西去了美东,开始了自驾游,访遍了多所常春藤名校和人文名胜。近年来也去了欧洲的一些国家。我的大部分出行,都是自由行。买一张飞机票,自己在网上订了酒店,然后去到那里自由自在地东走走,西看看。除了当地的名胜古迹,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当地的人文风情,尤其关注当地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生活和我的有什么不一样。我要用自己的脚走在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体验他们真实的生活。经过这些实地体验后,再去瞻仰他们的古迹,听他们的故事,静态的历史遗存才会变得栩栩如生。
积累了那么些年,我发现我文字里的人物不仅来自我常年生活过的上海和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他们还生活在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我与笔下的这些人物或许曾经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遭遇过,也可能我和他们其实跨越着世纪的鸿沟,本不可能见面,却在一种文学想象的氛围中相遇了。我把这些人物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地图上标出来,便形成了一张有趣的地图。这就是我的文学地图,它恰如其分地构成了我的文学创作的想象空间。而这份私人地图只有放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宏观图景中才更具意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的行走还在继续,因此,我还会在不同的区域中与我文学想象中的人物们相遇,他们也许是我生活中的旧友,也许是我的先辈,而更多的一定是曾经的陌生人。而这就是我的文学地图的意义。
一、迁徙对于作家的意义
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譬如:上世纪二十年代时海明威等一批美国作家,成群地离开美国本土,聚居巴黎;后来的马尔克斯离开哥伦比亚,移居墨西哥和欧洲;米兰·昆德拉离开波兰,移居法国……他们的迁徙都为自己的创作带来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人生旅途的迁徙,使这些作家们的文学地图得以扩展,在之后的创作中,不论是描写新生活,或是回看过去,文学想象的翅膀为作家拓展出崭新的视野。
在去巴黎之前,未满十九岁的海明威先已离开了美国,于1918年5月开始了他的探险。他先志愿去意大利前线当红十字会车队的司机,到达前线的第一个星期,就在战场上受伤,动了十多次手术才活下来。此后两年,海明威成了《星报》驻欧洲的流动记者,住在巴黎,撰写关于日内瓦与洛桑国际会议的报道和战争的电讯。在巴黎的生活,铸造了成熟的海明威。战争的经历形成了他对世界的看法;而在巴黎的写作也逐渐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文体风格。1926年10月,不到三十岁的海明威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从此声名鹊起。侨居巴黎的美国作家格·斯泰因曾对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①[美]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张承谟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页。海明威把这句话作为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题词,“迷惘的一代”从此成为这批虽无纲领和组织但却有着相同创作倾向的作家的集体称谓。这种迷惘的情绪引起战后不少年轻人的共鸣,海明威由此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20年代末,海明威回到美国,居住在佛罗里达州,并以此为据点进行广泛的游历:去西班牙看斗牛,非洲打猎,古巴钓鱼。这个时期,他的作品创造了刚毅不屈、视死如归的“硬汉”典型。1954年,海明威以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老人与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富有说服力的叙述,以及对现代文学艺术创作风格的精通”。
回顾我的小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爱情》(江苏文艺出版社)叙述的是美国留学生的感情生活变异,聚焦留学生陶歌三段充满了戏剧性的感情生活。我在后记中写道:“到美国那些年,看惯了一个现实:生存环境的变化改变着人们的感情生活。据我观察,爱情是脆弱的,也没有可塑性。爱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温度、湿度对爱情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制约。环境的悬殊变化,脆弱的爱情受不了!爱情变质,夫妻反目的事,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不论是在美国的中国人,还是中国的中国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爱情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纯真。爱情本应该以情和性相辅相成:有真情相依恋,有两性相吸引,才是真正的性情投合。现代社会中,爱情的内容和含义已经被偷梁换柱,真情被‘更新’,纯粹物恋的婚姻可以连性的吸引都放弃;纯粹原始的结合则完全堕落成一种互相玩弄的低级游戏。” 该作品入选南开大学美国华文文学选读《华人的美国梦》。
2014年,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丁香公寓》(上海文艺出版社),描写的是上海一座文化历史名楼中的故事,丁香公寓里发生的故事,是中国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生活的缩影。唐小璇和袁京菁,一对孪生姐妹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父母离异后天南海北,互不相识。等到成年后,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她们相会在电影厂的摄影棚里。《丁香公寓》里的故事从“文革”前开始,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末,跨度二十多年。这二十年的历史,既是我的成长史,也是共和国历史中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与共和国一起走过来,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我们成长中所流的汗水和泪水中融合着成长的悲欢和付出。即便我已身居异国二十多年,可是在我的记忆中,曾经在那里发生的故事总是那么鲜活地出现在眼前,父母和许多熟人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我依然可以清晰地看见他们的身影和足迹,看见我逝去的青春年华。可是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我的视角始于美国旧金山,又止于美国旧金山。这个故事的叙述角度是一个旅居者,一个远行者的回顾,表现的是一个远行者心灵上的归来。同样的生活,如果我在出国之前写可能会很不一样。
这两部长篇小说写的都是自己生活中熟悉的人和事,是人生经历中沉淀下来的岁月风尘成就了我的小说。创作完成后,我又时常思考,如果只限于身边熟悉的人和事的写作,我的创作能够走多长走多远。当然,真正的创作并不能理念先行,可是有一种清醒的创作意识的推动,可以使作者走出自己所谓的舒适圈,并有助于获得很大的收获,也许正是这些思考开始引发了我创作思路上的拓展。
二、窥一斑而见全豹
我很喜欢一位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他的创作对20世纪崛起的现代派及后现代派文学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将来到欧洲的美国人的天真烂漫与欧洲人的世故奸诈进行了比较,向读者真实地展现了新美国和旧大陆之间的道德文化冲突。我看过他的一系列作品,如《使者》《黛西·米勒》《阿斯彭文稿》《螺丝在旋紧》《丛林猛兽》等。他擅长对人物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进行细致描写,从而对读者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冲击力。
詹姆斯认为小说家应具有“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想象能力,这是一种“由所见之物揣测未见之物的能力,揭示事物内在含义的能力,根据某一模式判断事物整体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全面感受生活的条件,有了这一条件,你就能很好地全面地了解生活”。而在作家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与创作间的关系时,亨利·詹姆斯曾经有过精彩的叙述。他以一位女性小说家的创作经历为例:那位小说家成功地描述了一位年轻法国清教徒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而这仅仅是依据她曾不经意间在巴黎瞥见的一些清教徒吃饭的场景。通过生活中的细节来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观真实,而并非客观真实性,这才是詹姆斯的兴致所在。詹姆斯认为,那位女作家得天独厚地具有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才能。“那一瞥产生了一幅画面,它虽只持续了一刹那,但只一刹那就是经验,这种现实生活中的经验给作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经验才能与创作环境或社会地位等偶然因素相比,是一种大得多的创作源泉。”在詹姆斯的论述中,“窥一斑”与“见全豹”颇有深意,前者道出了小说艺术的先决条件,而后者反映了他对小说本质的看法。詹姆斯一直认为“小说就是个人对生活的印象”,“艺术就是选择,可是它是一种以典型性和全面性为主要目标的选择”。此外,詹姆斯用一个艺术类比来描述小说的真实性,即“如同图画就是现实,小说就是历史”。詹姆斯认为,小说对现实的富有想象的转化发生在艺术家的思想里,他把小说定义为“个人对生活的直接印象”,突出了小说创作中作者的经验和主观性。在这个定义中,“个人”和“印象”强调主观性,而“直接”和“生活”强调了小说的真实性,即小说与生活的对应性。①[美]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巫宁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305页。
多好的“窥一斑”与“见全豹”。如果说我的小说以我所窥之一斑——邂逅的某些场景和细节为起点,最后孵化出来支撑起整篇小说——全豹,显然许多故事中的情节来自我的想象和虚构,可是这些想象和虚构的依据却是我所窥见的最真实的“一斑”。那种来自生活的原生态的真实在我心里扎根发芽,衍生出我努力构筑的“全豹”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构筑出被我所认为最为真实的人物的关系和心理的发展方向。
也许正是这些创作意识上的跨越,促成了我近年来创作的一系列中篇小说。我的这些小说的内容已经离开了我生活的舒适区,是我多年来作为电视制作人的职业特性引导着我的文学创作走入了一个原先陌生的领域。这些小说也引导着我走进了中国文学的大家园,我先后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广州文艺》《小说月报》和《上海文学》发表了若干个中篇,这些作品中描写的人物遭际不是来自原先我熟悉的生活,而是我作为一个职业电视制作人观察到的别人的生活,可是这种发生在别人命运中的故事,却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我用一个新闻人的目光对社会进行关注,同时,我所具备的文学的眼睛又导引着我看见了比新闻所能探究到的深藏于事件之中的人的性格变异。通过文学想象,对新闻事件中的人物命运进行探究,构筑起这些社会事件的文学空间,那么这种逾越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发表于《北京文学》的中篇小说《布达佩斯奇遇》讲述了我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旅游中遭遇的一个故事。就在我准备搭火车离开布达佩斯前往奥地利的那个早上,我在布达佩斯火车站遭遇了从中东涌入欧洲的难民潮。布达佩斯是进入欧洲各国的第一个关卡,在火车站受阻,不能继续前往柏林的难民滞留在火车站,阻碍了火车的正常驶发。当我看见纷乱的人群中一个神态安详的母亲带着几个幼小的孩子,精彩的故事便在我心中种下了种子。几天下来与难民们的近距离接触,使我每天在酒店电视新闻中看见的一波接一波来自边境的报道更为具体化了。电视屏幕中的难民与边防警察的冲突已经不是那么遥远,一个个形象都会与我交谈过的难民直接发生对接,我对他们逃难的路径和离开故国前的生活和经历从新闻报道和相关资料中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况且,布达佩斯是这样一个充满历史的城市,河西岸的佩斯,河东岸的布达,两个城市组成了布达佩斯。尤其是在二战时期,当苏军和德军最后决战时,多瑙河上的所有桥梁全部被德军炸毁,为的是阻止苏军跨越多瑙河,攻占德军占领的佩斯。走在处处都可以引你驻足凝视的历史古城,在我的脑海中历史与现实,新闻所见和亲身经历,更有兴味的是以前读过的一些欧洲文学作品也一起从记忆深处涌了出来。伏尔泰的《憨第德》中的老实人憨第德,被逐出皇宫后,一路上经历了多少苦难。可是他的老师还是一直对他说:世上要是没有因就不会有果,因为上帝创造各种东西都有一个目的,一切都为的是最完善的目的。这样说下来谁要是说什么事情都合适,他的话还不够一半对,他应该说什么事情都是最合适的。可是在我的小说中,女记者与女儿的对话中却达成了共识:所谓的一切存在的都是最合理的,这显然是荒谬的。……这个世界上很多事都不合理,不论从布达佩斯这座城市所展示给你的历史记忆,还是女记者目睹的此情此景。
在这篇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我所经历的自我局限的跨越,其实是一个以往阅读积累和现实生活经历,加上新闻人的职业训练相加所得。这篇作品发表已是我去布达佩斯的两年后,可是依然引起了较好的反响。《小说月报》《长江文艺》都先后转载。
在这些年中,我还写了数篇深度表现华人在美国生活的小说,如《肤色》《谋杀者的逻辑》《线人》。《肤色》讲述的是美国大学中留学生和本土学生相处的故事,两个祖籍上海的女孩,一个在中国出生,一个在美国出生。不仅个人的肤色不一样,她们对于肤色这个话题的敏感度也完全不同,因为她们成长在不同的国度,所接受的熏陶来自不同的文化氛围。特别是为了表演一个致敬美国黑人歌手的节目,来自中国的女孩们把脸涂成黑色上台演出,结果造成了极大的争议,甚至被误解为种族偏见。
《谋杀者的逻辑》中,一个中国留学生被杀害,却引来网民们对于“富二代”炫富的批判。而凶手在法庭上陈述犯案的动机时,却声称“中国人都很有钱”。可是被杀的中国留学生陈晓曦不是富二代,那天他的钱包里只剩五元钱。在抢匪追抢的过程中,陈晓曦死抓着他的新手机不放,导致抢匪最后击碎了他的颅骨。为什么?因为那不仅是一只新手机,而且里面刚刚拍摄了记录他第一段美丽恋情的照片。凶手、网民的误判造成了对于陈晓曦的二度伤害,前者是肉体上,后者是名誉上。两者都可以杀人。
《线人》涉入了一位旅美中国女士的人生经历,侧重的是中国大陆女性觉醒的艰难历程。美国洛杉矶月子中心被搜查后,来自哈尔滨的孕妇黛布拉被禁止离境,等待法庭传讯。一件突如其来的风暴使黛布拉陷入无法自拔的漩涡,她的人生中突然出现了许多对手。月子中心的老板顾赛菲对她阴一套阳一套;FBI的探员对她紧逼不舍,硬塞给她一个律师,要她做线人,引律师翟大卫触法;还有她在国内的情人戚同梧,与她相识于发廊,随后将她包养,使她怀孕,将她送到美国生产,她遭遇了麻烦,对方也忽然对她若即若离……孤身独处时,黛布拉回想自己过去几年中做的许多事,不论是出国、生孩子,还是做了美国政府的线人,出庭去指证律师,等等,都是别人指了一条路让她去走。可是最终顺着这一路走下来,她却发觉自己彻底地迷路了。这是一个女子心灵成长的历史,这一回她尤如一个新生婴儿,要重新学会走路,这回她一定要自己选择一条路走下去。可是要摆脱这些困境,别人又帮不了她,还是要靠她自己。一个人并不是自愿存在于世的,然而一旦存在,他/她就是相对自由的;但同时他/她要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在这些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我在生活中所窥见的“一斑”促发了我的文学想象,每一部小说都有一个核心的细节支撑着整部作品:在布达佩斯火车站与难民的邂逅,当我看见那一个神态安详的母亲带着几个幼小的孩子,精彩的故事已经在我心中产生了。最后母亲坚持把七岁的儿子交给陌生人,让他们长途步行带他到柏林去。这既是一种可能导致母子永不相见的人生赌博,也是二十一世纪人类历史遇到的最大挑战面前,一个母亲所能做的最好选择(《布达佩斯奇遇》)。在洛杉矶,一个被害中国学生照片上充满对未来憧憬的眼神,与他所遭遇到的一个拉丁裔街头混混的“中国人都有钱”的偏见产生了激烈对撞,正是这位留学生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眼神激发了我要剖开事实真相的愿望(《谋杀者的逻辑》)。在《肤色》中,我所见过的两个不同的上海女孩相对着困惑,用哪种语言交流的场景,以及来自同样的祖籍,但是对于肤色的认知却因为文化差异而迥异。《线人》则来源于我制作的新闻节目始终跟踪报道的一件在洛杉矶侨界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庭审。这些生活中的场景那么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在我的想象中幻化出精彩的故事,人物的命运在这些故事中孵化演绎开来。
上述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始终身处两种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之中,不论是《布达佩斯奇遇》中的中东女教师,还是旅居美国的华裔女记者;不论是《谋杀者的逻辑》中被害的中国留学生,还是拉丁裔的凶手;不论是《肤色》中出生在美国的女孩,还是来自上海的女学生,还有《线人》中来自中国的孕妇黛布拉遭遇的美国月子中心和美国司法的陷阱……这些人物的经历和故事正是两种文化遭遇时发生的撞击,因为来自不同的文化环境,于是必然产生碰撞,或许是电闪雷鸣,也可能是和风细雨。这些过程那么值得我去细心揣摩,其中深埋在人们心灵里的那种微妙关系更是小说最善于表现的。而这些都是今天这个世界复杂关系中的一部分,谁都逃避不了。
三、发现一个作者自己的世界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从1983年到1988年,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艾奥瓦大学做了三年的访问学者,这段经历更加深了他对西方文化与环境的理解。帕慕克认为:“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在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①帕慕克诺贝尔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原载瑞典文学院官方网站。
创作对于作家来说,不仅仅是对外界的关照,而且是一种自身的内省,只有当来自外界的信息投射在心灵中那面具备独特视角的镜子中,才能反射出属于作家自己的独特性。那是一个“他的世界”,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近年来,我的笔和思绪,越来越多地随着自己的足迹进入到一些曾经陌生的区域,那些故事有些是我不曾经历的,或是我读到了,想象出来的。而在想象之中,有些是那样的,而更多的是我以为应该是那样的,这是我对于自己在作品中所描绘的故事的文学想象。今年7月,在《上海文学》发表的《忆想神田川》则飞跃去80多年前的日本东京,讲述了一个父辈留学日本的故事。这是我正在进行的一个致敬父辈系列中篇小说中的一个。
开始有想法写《忆想神田川》,缘起于2017年一次日本之行。在一个无花的冬季来到东京,不是为赏花,而是为了寻找先父年轻时的足迹。那时父亲只有18岁,只身来到日本留学,考取的学校就是神田川岸边的东京法政大学经济系。我抬头四顾,希望还能从校舍中找到历史的踪影,陪同我前往的友人看出我的心思,急忙解释:历史的校区因1945年二战中美军空袭,大部分校舍被烧毁,后来在原来的区域内又重新造了新校区。难怪抬眼四望,河川两岸立起了许多幢高大的建筑,高处悬挂着法政大学的名字。
父亲1930年在日本组织了左联东京分盟,次年中日战争爆发,他参加并组织了在日学生的抗日示威,被迫停止学业回国。我从史料中获知了这段父辈的生活,可是史料是干枯的标本,能够让我了解那颗植物的筋脉,却未必能够形象地呈现出当时的生活状态。
旅日作家华纯女士特别安排了我与旅日的文坛前辈郭沫若和田汉的后人相见,我们还参观了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纪念馆,晚上,又应日裔教授深雪的邀请一起吃饭聊天。深雪教授了解了我父辈的故事,特地推荐了一家位于有江户时代特色小巷中的日式饭店,餐后又导引我们踏着夜色中的石板小巷漫步。虽然天有些冷,我却感受到了父辈们曾经经历过的日本街道和民居的韵味。木制的门楣,数盏灯笼和门帘之后是洁净的和室,走进去可以闻见灯芯草的味道。赤脚走在以灯芯草做成的叠席上,有如徜徉在大自然一样。而环顾街头,一家连着一家的木制建筑,石板的路面,在暗黄的灯光辉映下,散发着江户时代的气息。我想象着正逢壮年的郭沫若、田汉和叶以群曾经走在这样的石板小巷里,他们的脚步匆匆踏过那儿,最后走进了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
这些实地探查所收获的直感带给我一种全新的对于那个时代的质感。为了了解更多当年留日学生的生活,我细读了郭沫若、周作人等前辈作家的一些回忆录,了解他们在日本居留时住房的结构、生活习惯,甚至是家庭琐事;同时,还读了一些日本作家的作品,从中了解艺妓的历史,以及为什么有些日本女孩自愿地去做艺妓。还有中国徽州男权主义下女性生活的困境,为什么徽州的村落中,总能看见高高矗立着的贞节牌坊。等到作品完成后,我才发现正是这些方面知识的积累,在自己的想象中熔于一炉产生的化学作用,才促成了一篇小说的完成。
作家肖克凡在《从往事开始》一文中有一段论述,我颇有同感:“关于写作者往事,除了属于自己的真实人生经历,更为重要的应当具有不真实的人生经历,或者说虚假的人生经历。你虚假的人生经历与你真实的人生经历相比,它才是文学意义上的‘往事’。写作者需要的正是这种并不真实的‘往事’。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的写作才逼近于文学的本质。”①肖克凡:《从往事开始》//《何似在人间》,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353页。
我觉得这段话讲得颇为透彻,把作者的真实经历和文学想象的关系,真实和虚构的关系,以及如何从自己的经历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进入更高层次的文学创作空间的重要性都点了出来。小说的作者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不仅仅是他所经历的真实生活,而应该是作者想象中的、经过他创造的独特世界,这个独特的世界是与众不同的,这才是真正属于作家的文学世界。而小说家最具价值的功能,就是为读者构筑和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
海外华文文学对于华语文学的贡献,我想最大的意义就是为世界华语文学和中国华语文学提供了一幅地域广大同时又充满了丰富内容的地图。摊开这幅地图,不仅发现作者们笔下的华人们生活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他们更远足千万里,足迹遍及全世界所有有人的地方。海外华文文学蓬勃发展,积累下丰富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人物活动的区域遍及全世界。当这样一幅丰富多彩且富有世界各国人文色彩的地图展开之后,读者就会由衷地感谢海外华文文学成果的贡献和意义。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中有多元文化的冲突和交流,有对母语文化的眷恋和反思,有遭遇异域文化时的震惊、惶恐,到后来的接受、和谐相处,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史学上的意义和价值。海外华文文学不仅给本土的中国文学增加了多元化的丰富内容,并且使华语文学走出了有限的国境疆域,发展延伸到世界的各个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