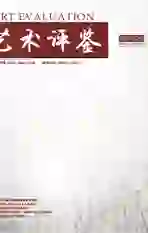南桑村德昂族水鼓乐舞考察
2020-10-12李广鑫
李广鑫
摘要:水鼓作为德昂族精神象征的物化标识,其声音“纹样”体现出德昂族自我身份认同的心理建构,具有超越日常语言功能的感召性,由其衍生的水鼓乐舞共同组成了德昂族精神与物质相互涵化的水鼓文化。文章依托民族音乐学的相关研究方法为学理支撑,以单点民族志的视角,完成了对南桑村德昂族水鼓乐舞与文化持有者日常生活关系的持续考察,构建了“他者”立场的文本描述。
关键词:水鼓乐舞 物化标识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17-0001-03
一、德昂族概况简述
德昂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族群。“德昂”若以汉语释义,为“古老的茶农”①之意。据史料记载,德昂族先民早期居住在怒江两岸的广大地区,是永昌郡(现云南西部地区)古老的民族之一,杜亚雄的《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一书中记载“德昂族较傣、景颇、阿昌等族先進入怒江两岸这一地带,傣、景颇、阿昌等族人民一致公认德昂族是今日德宏州内各民族中最早来至此地居住的民族,他们是怒江两侧的主体民族”②。
由于历史的制约,德昂族属无文字民族,加上各支系生活环境的差异性,因而语言也有所不同,但均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从民族识别的立场来看,德昂族支系较多,自称有“布离”“阿亮”“来弄”“若卖”“若团”“若薄”“若因”等支系。为了便于识别,外界常常根据他们的服饰,特别是妇女的统裙颜色和花纹,称他们为红德昂、花德昂、黑德昂、白德昂等。作为跨界而居的民族,中国境内的德昂族主要有三大支系,一为黑德昂,德昂语自称为“若卖”,即笔者此行所考察之地南桑村的主体族群;另有红德昂,德昂语自称为“布离”;再为花德昂,德昂语自称为“若薄”。由于历史的原因,传统时代的德昂族主要居住在山区,生存环境较为闭塞,这也导致他们仍然保留着本民族较为完整的生存经验和文化习俗。作为一种精神符号,水鼓便是德昂族标志性的物化标识。为了获得对水鼓文化更多的了解,阳春三月,笔者一行特地前往德昂山寨,拜访了红德昂支系的水鼓乐舞传承人岩翁和水鼓制作人毛砍三,观看了他们现场的鼓舞展示和水鼓制作工艺,并探访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同时,通过口述的方式,体验了德昂族与水鼓音声相互间的互动关系。
二、德昂族水鼓物质属性概述
“水鼓”一词,属于他者视野下的客位称谓,而非文化持有者的自称。事实上,作为一种物质属性的符号标识,德昂语称其为“格楞当”。我们若将“格楞当”进行象声词意义上的解读可以发现,德昂族的“格”音同比邻而居傣族发音“光”相近,均为“鼓”之意。这或许缘于过去的时代,德昂族长期隶属傣族土司管辖,族群之间的文化交往充满着横向的族际互动,因此,德昂族在文化或语言等文化习俗方面,颇受傣族强势文化的影响。同时,由“格楞当”分化的“格楞”或“格当”,则属于德昂民众对水鼓声音一种象声词的具象表意,而非特指某件乐器,体现出民族文化创造独有的诗性智慧。
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在南桑村开展田野作业时,笔者特地向水鼓制作人毛砍三和水鼓乐舞艺人岩翁等人了解了水鼓制作的相关流程。他们介绍:“以前我们在制鼓的时候,先去山上挑一棵上好的树(椿树),然后,要请佛爷念经后,才能把树放倒。再把最好的树桩拉回寨子,就开始制作水鼓了。鼓面必须用黄牛皮蒙制,鼓身有时也用水牛皮制作。水鼓做好以后,必须拿铓、镲去跟水鼓的声音进行调配,就是调节鼓皮的松紧,使鼓声与其它物件的声音相融合。最后还要用蚂蚁拱出的土拌成泥浆涂抹在鼓的全身,由佛爷开光后,在打鼓之前用‘bo suo en(椿树的树枝)来祭鼓,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根据两位艺人的描述笔者得知,水鼓鼓身用较软的椿木挖成中空形制,并在表面绘以花纹,使用椿木的目的是利于乐器的保存,绘制花纹是突出自身民族文化符号标识,在特定场域中演奏时以此获得民族成员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水鼓由于使用的场合与功能不同,因此,鼓身的大小有异,从形制观察,并不统一,一般水鼓,长约100厘米,头大尾小,两端使用牛皮蒙于鼓面之上,而后鼓面与鼓身连接处用牛筋或剩余的牛皮反复扎紧,用以调节鼓面松紧。大水鼓,德昂族称“格楞当”又称为“格本旦”,“旦”为“大”之意,因此“格本旦”的称谓就作为大水鼓的特指;小型水鼓“格本嘚”“嘚”,为“小”之意,“格本嘚”的称谓则作为小水鼓的所指。水鼓制作完成后,用蚂蚁窝中的泥土糊满鼓面,此种现象从科学的立场来看,蚂蚁在筑窝时,体内会分泌一种叫做“蚁酸”的物质,而蚁酸会产生防虫的作用,以利于水鼓的存放。鼓身中部留有一圆孔,在敲奏前会灌入一定数量的清水或米酒,使鼓身、鼓面湿润,如此,在敲奏时才能产生文化持有者听觉习惯能够接受和认同的音色。折射出具有神性的水鼓,其之于山地农耕民族祈盼雨水这种“以己度物”的思维模式。
三、水鼓乐舞展演的场景描述
上述仪式中被称为“法器”“民俗”中被称为乐器的水鼓,作为德昂族精神象征的物化标识,在传统保留的时代,其敲奏的时序必须限定在特定的空间与时间中进行。如只能在与南传佛教有关的关门节(入洼)、开门节(出洼)、泼水节、龙阳节等重要的场合及特殊的时间节点敲奏,以示其神圣的隐喻。当然,随着社会的变迁,特别是当下为了实现“自我他者”的文化传播、让德昂文化符号更多地被外界所认知的背景下,德昂族青年一代艺人主动跨越了许多规矩、突破了传统的制约,在文化的选择中构建了“传统的发明”。
“格楞当”作为特色性乐器,在展演时,还需铓、镲等伴奏性乐器与之配合。在这样的场景,各式“配角”如同众星捧月搬将“格楞当”置于中间位置,以象征其地位的重要性。演奏开始,岩翁高喊一声“喔~嘿”,以提示演奏人员准备之意,随后所有乐器进入状态。却见岩翁右手持鼓槌,左手掌四指并拢,虎口大张,双腿微屈,双脚稳健的立身于鼓前准备击鼓;敲奏时,左手跟随右手同时放收,右手鼓槌落于鼓面,左手随之收入,右手鼓槌离开鼓面,左手亦与之张开,双手同身体呈现一种平角的流线型角度,为下一次击鼓做准备;每敲击鼓面一次,左脚抬起,小腿与大腿约呈垂直角度,随之放下,再敲一次,右脚抬起,与左脚做相同动作。或许为了突出“表演”的可视性,演奏“格楞当”的艺人,动作更是夸张,大开大合的舞蹈语汇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彰显出德昂族集体精神与民族力量的张扬,体现出一种人鼓合一、鼓通心灵的力量之美。岩翁身旁,毛砍三和玉恩二人手持大镲,岩吞与岩旺两人左手提铓、右手执鼓槌,四人围绕“格楞当”作逆时针走步并敲击手中的物件为水鼓伴奏,他们的舞姿都会随着“格楞当”的节奏变化而随之转换,体现出群体的心理默契,使得演奏产生此起彼伏、层次分明的韵律之美。
若将演奏节拍予以记录,节奏为:咚 铛|咚 铛|咚 铛|或咚 铛铛|咚 铛|咚 铛铛|咚 铛|。演奏即将结束之时岩翁再次呼喊一声“哦~嘿”,全体人员完成演奏。笔者的考察虽然不是德昂族的任何民俗节令,但作为一种文化推广的“展演”,笔者却仍然可以感受到节日的气势、感受到“格楞当”音声中所塑造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民族之魂,展现出一个古老民族为生存与发展而努力进取的历史脉络。
四、“格楞当”的身体表达——“噶格本当”
(一)“噶格本当”基础形态表述
原始时期的乐舞是根据原始崇拜的仪式所创造的具有娱神功能的舞蹈范式,“噶格本当”本质便是德昂族民众根据原始崇拜仪式发挥祭祀神灵功能,围绕“格楞当”符号化意义而创造的一种民俗性舞蹈形式,汉译称为“水鼓乐舞”。在传统保留的时代,其展演的时间和场域具有较为严格的规定性,多在出洼、入洼、泼水节、龙阳节等与农耕节点相勾连的时段举行,这体现出族内群众欲通过此种行为来达到敬天通神的意图,祈求上苍神灵保佑今年或来年庄稼能有好的收成。作为以“格楞当”为介质进行身体内空间与外空间相互结合发挥相应功能的身体艺术,完整“噶格本当”的舞蹈动作代表水鼓制作的整体流程,包括砍树、拉树、制鼓三大部分,民族成员在跳“噶格本当”时会将“格楞当”作为置于广场中心位置,既凸显“水鼓”主体,同时展现“水鼓舞”主题,发挥作为“人”和“舞”之间的介质作用。“噶格本当”展演时,族内男性舞者会佩戴砍刀(演出佩刀为道具),展现“噶格本当”步骤之一“砍树”部分,在“砍树”动作中同时融合德昂族拳法,以此增加演出观赏性、增强乐舞审美化,具有表达身体语言的功效;族内女性在跳“噶格本当”时则是模仿本民族生产劳作方式“采茶”动作,动作平稳、舒缓且基本保持不变,望以此达到敬天通神、祈求丰收之意。因笔者所考察时日并非民俗节令点,由此水鼓乐舞传承人岩翁等人只进行“格楞当”及“噶格本当”部分展示(男性“砍树”动作及女性“采茶”动作),并未进行完整展示,笔者一行人着实感至万分遗憾,只得与岩翁等人约定相关节令时分再次进行考察采访,以探究完整水鼓乐舞之于德昂族民的重要性及地缘感知性。
(二)“嘎格本当”共时性发展
在做“格楞当”传承人访谈期间,笔者以“局外人”的视角推测“噶格本当”的基本动作是不能改变的(因部分民族动作步伐不能改变),为求证这一推测观点,笔者便询问水鼓传承人岩翁。据他表述,“噶格本当”的动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种种因素进行适当调节,如:族内老年人在跳“噶格本当”时因年龄、身体及自身观念等原因会遵守“老祖宗的规矩”,“格楞当”鼓点节奏、速度相应放慢,基本动作较少,且脚下动作基本固定不变;年轻人可以在乐舞原有的基础及遵守“老祖宗的规矩”之中产生变化,没有上述因素限制,因此基本动作较多,且脚下或手上动作会伴随“格楞当”的音乐形式及节奏速度变换而不断产生变化。经过族内青年的“艺术加工”,“噶格本当”的舞蹈动作亦渐渐趋向“艺术审美化”角度延伸发展,在彰显出本民族成员对于自身民族文化认同与自我认同感的同时,使自身民族的文化符号不断产生新的活力,使其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是一个民族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不断坚守,折射出一個民族巍峨不屈的民族意志。
五、结语
德昂族的水鼓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是德昂族先民在历史变迁的岁月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过程中心理物化的神器/乐器,是他们区别于“他文化”独特的物化与声音标识,对文化持有者来说,只有这样的声音,德昂族民众才能体会到强烈的身份认同及自我确证。正如申波教授在《审美意识与音乐文化》③一书中指出“大凡从事过创造性劳动的人都会有这种体验:无论他们从事的创造具有多么艰难的过程,充满多少危险,但他们仍能从中获得无法形容的愉悦”。的确,正如笔者在考察中所见,由于历史与地缘的缘故,德昂族民众在物质生活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贫困,但当他们敲响水鼓、跳起水鼓舞时,他们的腰板却挺得那么的直、双脚踏在土地上显得那么的从容有力,从这里我们看到,在“文化化人”的过程中,德昂族通过自己对生活的创造感受到了世间的快乐、他们在乐舞的互动中,获得了情感的交流、形成了民族的高度凝聚力。这种通过乐舞获得的心理感召并以肢体音声彰显出对未来生活的坚韧期盼,对局外人或许是难以理解的,但这样的精神力量,又是主流文化所缺少感知的一种心理体验。
可以说,水鼓的符号化存在,它不仅体现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多样性活态传承的样本,也以生动的个案彰显出文化差异中不同文化存在的当代意义,展示了一个古老民族,在族际互动与不同文化相互涵化中,对自己文化传统在身体实践中所透露出的民族尊严。
参考文献:
[1][美]艾伦·帕·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
[2]杜亚雄.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
[3]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4]洛秦.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5]申波.审美意识与音乐文化[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6]申波.德昂族“水鼓乐舞”的符号化意象考察[J].民族艺术研究,2019.
[7]孙家显.论德昂族“水鼓”和“水鼓舞”文化[J].民族音乐,2014.
[8]赵书峰.传统的发明与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基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身份认同变迁问题的思考[J].民族研究,2019,(01).
[9]张应华.宏观与微观: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认同研究的双重视角[J].音乐研究,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