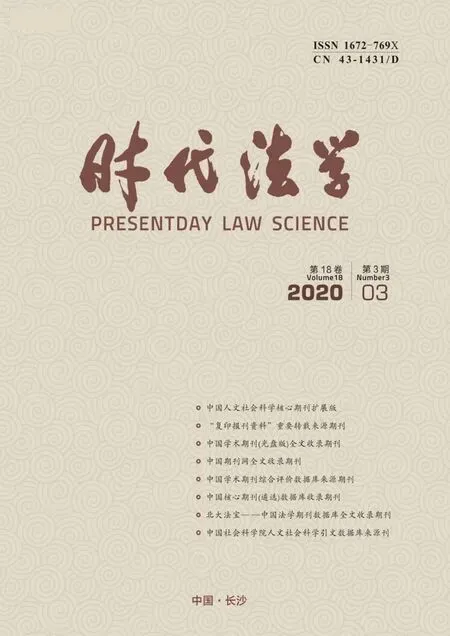论可避免的构成要件错误
2020-07-21陈尔彦
陈尔彦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1;德国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德国 弗莱堡 79100)
一、构成要件错误与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不同处理方案
无论是否将故意从罪责阶层中抽离,区分构成要件错误和违法性认识错误,并为两种错误设定不同的法律后果,这一理解在今天已经基本取得了共识。故意的认识内容是客观构成要件,违法性认识则属于罪责的组成部分。当行为人对客观构成要件没有认识或发生误认时,即存在构成要件错误;而当行为人未对构成要件产生认识错误,但却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此时即成立违法性认识错误。尽管对于构成要件错误和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区分基准,理论上存在不同看法。但大体而言,从形式三段论的角度看,构成要件错误是对小前提的误解,即对具体案件事实情况特征的错误,而违法性认识错误则是对大前提的误解,是对法定构成要件的概念性要素的错误。换言之,如果行为人的认识错误是通过对事实的认真观察、仔细判断就可能克服的,那么这种错误就是构成要件错误;如果行为人的认识错误是通过对刑法规范的进一步了解就可能克服的,那么这种错误就是违法性认识错误(1)[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 刑法总论教科书[M] .蔡桂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51-253.张明楷.刑法学[M]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325.。
对于构成要件错误和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法律后果,通常认为,构成要件错误具有排除故意的效果,而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影响犯罪的成立,理论上则经历了从“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到“违法性认识必要说”再到目前已成主流的、相对折中的“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说”。而对于违法性认识的体系性地位,理论上又存在故意说和罪责说两种基本主张。故意说认为违法性认识是故意的组成部分,罪责说则认为违法性认识属于罪责要素。德国刑法在实定法的层面上采取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说”之下的罪责说,即认为违法性错误与故意成立无关,该错误不可避免时阻却责任,具有回避可能性时则可以减轻责任。
我国《刑法》对此未作出具体规定,但主流观点认为,犯罪故意不包含违法性认识。因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表现为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显然是仅要求行为人明知其行为及行为结果的危害性,而没有再要求行为人明知行为及结果的刑事违法性。但通说同时也承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果行为人确实不了解国家法律的某种禁令,从而也不知道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就不能让其承担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08.124.。这一结论在处理效果上已和上述“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说”相似。我国学者也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4条进行不同的解读(3)蔡桂生.论故意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双层定位 [J].环球法律评论,2013,(6):70-71.,试图从教义学的立场,为采纳“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说”及罪责说寻找解释论上的连接点。但总体而言,“构成要件错误阻却故意(但在刑法处罚同一行为之过失犯的场合,仍须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过失),违法性认识错误在不可避免时阻却责任,具有避免可能性时可能减轻责任”的处理方案,目前已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接受。
在承认上述基本结论的前提下,颇为令人犹疑的问题是:为何通说对于构成要件错误采取认识原则,即不论错误之原因,一概认为应阻却故意,而在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场合下,通说则认为应当采取责任原则,即不仅要求行为人不知法律,同时还进一步考察行为人不知法律的原因、探究该原因是否为行为人所可能避免的,而这一点对于构成要件错误是否能够阻却故意的判断而言,则全然无关紧要。既往学说对两种认识错误的处理方案差异并未予以充分关注,似乎认为既然构成要件错误和违法性认识错误分属犯罪论体系的不同阶层,因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模式亦属理所当然。但本文认为,这种形式性的区分并不能从根源的意义上对这一问题作出妥善的回答。为了澄清这一困惑,挖掘这一结论上的断裂在体系或机能上的合理性,以下将尝试从存在论和机能论的进路分别予以探析。
二、存在论进路:意志活动与意志形成的分立
自目的行为论者将故意从罪责阶层中提前到构成要件阶层时起,故意作为一种以目的性操控为内容的行为意志活动,就和作为意志形成之可谴责性的罪责完全区隔开来了。故意是被评价的对象,涉及的是一个既定的犯罪意思引导事件因果流程、实现不法结果的活动过程及其与客观事态之间的联系。而罪责考虑的则是可谴责性这一评价本身,关注的是某个特定行为意志形成的过程和原因(4)[德]汉斯·韦尔策尔.目的行为论导论[M] .陈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2-54.。
依据这样一种存在论层面上对意志活动内容和意志形成过程的区分,可以进一步检视故意和违法性认识之间的关系:故意是对行为构成要件存在属性的认识,但这一认识只是评价的对象、是针对行为人作出谴责的内容;而违法性认识则是可谴责性评价的组成部分,是说明为何要就违法的故意对行为加以谴责的根据——因为行为人能够认识到违法性,并据此不去做合法的行为决意,所以人们可以就该决意而对行为人进行谴责;行为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违法性意识得以现实化,并形成用以决定意义的对抗动机,这是人们就违法的故意对行为人进行谴责的根据所在(5)[德]汉斯·韦尔策尔.目的行为论导论[M] .陈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81.。日本学者川端博亦在区分意志活动和意志形成的基础上,对故意和违法性认识的差异性进行了阐述:“刑事责任系指行为人从事符合构成要件之违法行为,因而受到社会的非难。而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刑法规范藉由命令、禁止一定的行为,课加行为人作成符合规范的意思决定之义务,行为人虽然必须作成合法行为之决意,竟违反义务不作成合法行为之决意,却作成违法行为之决意……易言之,就‘意思之形成,亦即决意违反法秩序之要求’而言,责任乃是反价值性、反价值判断之意思,基此,在作责任判断时,行为人意思形成之过程被纳入判断对象,违法性的认识在奠定责任之基础问题上具有重大意义。准此,违法性的认识并非故意,其所具之机能完全是在为‘责任’奠定基础。”(6)[日]川端博.刑法总论二十五讲 [M] .余振华译.中国台北:台湾元照出版公司,1999.206.此外,福田平等人也指出,“事实性故意是构成要件要素,是已经在构成要件中被确定的事实的认识,是从意思形成的角度来把握这种心理事实;与此不同,违法性认识不能看成是单纯的心理性违法的认识,而是应该看成是抵抗犯罪性意思决定的规范性意识。反对动机的形成是在规范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来把握的。”(7)冯军.刑事责任论 [M] .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18.
按照意志活动对应于心理事实而意志形成对应于规范评价的分野,似乎可以为构成要件错误与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不同处理方案给出一种有力解释。“对于构成要件的实现,行为人绝非仅是一个因果链的启动者,而是引导控制着事件流程走向之人,所以,必须在行动当下对于客观构成要件之诸多要素有所认识,否则无法主宰其行为而实现构成要件。”(8)徐育安.亚里斯多德于刑法主观归责之影响与启发[J] .东吴法律学报,2009,(2):54.因此,从故意所具有的存在构造上的意志支配特性来看,当发生构成要件错误时,不论错误的原因为何,行为人对犯罪即欠缺意志支配,故意因而也就被阻却了。相对地,违法性认识作为意志形成中的一个环节和组成部分,其形成原因以及该原因是否应当在规范上被赋予相应谴责,就是重要且有意义的。
但是,这种解释可能会面临两层在逻辑上存在递进关系的质疑。
第一层质疑是就意志活动与意志形成的分立本身而言的。一方面,从意志形成和发展进程的角度看,意志形成是意志活动的前提,行为人只有在形成了某一具体意志之后,才有可能基于该意志,而展开相应的意志活动,对不法事态进行操控。也即,当行为人未能正确地利用其理解能力形成回避不法的反对动机,并将这样一种已然形成的具有可谴责性的意志现实化为故意的意志活动,那么,便是故意且有责地行为。因此,在事态发展的意义上,应当是先有意志形成,再有意志活动。另一方面,从犯罪认定的角度看,故意又是违法性认识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当行为人对行为符合于构成要件的状态有正确的认识,或对此能够正确认识时,他才可能对行为的违法性具有正确的认识(9)[德]汉斯·韦尔策尔.目的行为论导论[M] .陈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74.。换言之,“若对具体的案件事实情况之情状发生认识错误(构成要件错误),也会导致禁止错误。因为若行为人陷入对某一构成要件的事实性前提条件的认识错误之中,那么,他也就必定针对相应的构成要件之实现的不法产生认识错误。”(10)[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 刑法总论教科书[M] .蔡桂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58.因此,在阶层审查的意义上,先审查的是意志活动,后审查的是意志形成。这样一来,审查顺序与事态发展顺序恰恰就是背道而驰的。表面上看,这种做法似乎并不会造成任何问题。因为在通常的犯罪检验框架下,人们往往也是先检验在时间上靠后的结果,再从结果向前回溯,进一步检验在时间上靠前的行为。但问题在于,这种从结果向行为的回溯,在体系上是通过因果关系或客观归责建立起沟通纽带的;而在意志活动和意志形成之间,由于不法和罪责在阶层构造上的截然断裂,恰恰就缺乏这样一种回溯的桥梁,充当将意志活动内容的瑕疵归属于意志形成之可谴责性的管道。
这就产生了第二层次的质疑:当意志活动的内容瑕疵(构成要件错误)本身就是基于一种应受谴责的原因而产生之时,囿于从不法到罪责的阶层审查顺序的限制,有关可谴责性的规范评价就根本无从展开了。从故意的构造上看,故意是对法益侵害因果流程的目的性操控,当存在构成要件错误时,表面上看这种意志性的支配力就丧失了。但问题在于,如果这种认识欠缺本身,同样也是行为人意志支配的产物,那么,是否还能当然地认为构成要件错误就一定导致行为人丧失意志支配、进而排除故意?
在此,可以类比原因自由行为的构造。原因自由行为是指具有责任能力的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使自己一时陷入丧失或部分丧失责任能力的状态,并在该状态下实施了不法行为。刑法理论上普遍是在坚守责任主义原则的基点上承认原因自由行为具有可罚性,因为结果行为的无责状态恰恰是原因行为有责地造成的,因此,结果行为同样是行为人有责支配之下的应受谴责的行为。这样一来,如果构成要件错误本身就是行为人有意所导致,而并非是行为人基于无知或对自己行为支配力的误判而无意造成的一种认识上的空白,那么是否还能因为欠缺意志支配而排除故意,则是颇令人怀疑的。但是,按照现有的犯罪审查体系和前述对构成要件错误的处理方案,在出现构成要件错误时,不问原因,一律排除故意,而如果该罪行不处罚过失犯,则犯罪审查即告终结。这样一来,对于意志形成过程中行为人使自己陷于无知的可谴责性,也就再也没有讨论的余地。
因此,以存在论构造的不同形态为立足点,并不能有效解释对构成要件错误和违法性认识错误采取不同处理方案的原因,反而会引发新的质疑,让人重新省思严格区分心理事实和规范评价、将意志活动和意志形成截然分开并采取不同判断基准的做法是否合理。
三、机能论进路:以一般预防为核心
与上述存在论进路相对,另一种解释构成要件错误和违法性认识错误之处理方案进路,可以被表述为一种机能论的进路。
(一)故意的一般预防机能
从故意的角度看,故意是一种主观构成要件要素,构成要件具有保障机能(罪刑法定机能)和动机机能(一般预防机能)。“动机机能和保障机能是同一刑事政策之目标构想的两个方面”(11)[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M] . 蔡桂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4.,在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之下,构成要件阶段的刑事政策任务就是实现法的明确性(罪刑法定),并通过罪刑法定原则来实现一般预防。
据此,德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应当从保障机能和动机机能的关系出发,证成为何构成要件错误一律可以排除故意。具体而言,在此应当关注的是构成要件故意的呼吁和警示功能(Appell-und Warnfunktion):一个对于其行为情状和社会与法律意义缺乏认识者,法律的导向作用也最难对其生效。换言之,一个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人不可能产生放弃犯罪行为或实施必要的救助行为的动机(12)Vgl. Rönnau/Faust/Fehling, Der Irrtum und seine Rechtsfolgen, JuS2004, S. 668.。这里所谓的故意的呼吁功能和警示功能,对应的实际上就是一种预防性考量。
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能与构成要件的保障机能相联系,因为对于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来说,给予其在法律上的优待是有理由的。但是问题在于,仅从形成反对动机的意义上而言,一个欠缺对违法性的现实认识的行为人同样不可能产生抑制自己不法行为的反对动机。奠定罪刑法定原则并以一般预防作为刑法理论核心的费尔巴哈认为,行为人只有同时认识到构成要件事实和违法性,才能产生心理强制作用;如果一件事被行为人认为是不违法的,行为人当然不会知道应该停止(13)徐育安.费尔巴哈之故意理论及其影响——以德国刑法为核心[J]. 政大法学评论,2009,109:17.。
对此的一种解释是,“一个知道他在做什么,但错误地以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人是更不值得被原谅的”,鉴于行为人对于行为情状的认知,他有充分的机会对其行为违反禁止规范或命令规范的性质进行考虑。因此,如果行为人未将对构成要件行为情状的认知运用于其不法意识现实化的进程之中,那么,只有在这种禁止错误具有不可避免性的情况下,他才能免除故意犯的责任(14)Rönnau/Faust/Fehling, Der Irrtum und seine Rechtsfolgen, JuS2004, S. 669.。然而,对行为情状无知的行为人在从事行为之前也并非总是没有充分机会去审查、确认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行为人之所以丧失机会,恰恰是其蓄意造就的——但学理上在故意认定阶段却从不考虑行为人不运用此机会的原因,而是将之转化为预见可能性,置入过失犯的判断中进行考量。
(二)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一般预防机能
从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角度看,为何行为人存在违法性认识错误时并非一律免责,而是要进一步考虑行为人对此是否具有避免可能性,这一点必须结合机能论的思考,才能得到充分解释。既往的观点认为违法性认识和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不存在质的差别,只有量的差别(15)[日]野村稔.刑法总论[M] . 全理其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05.,只是可谴责性的高低度关系,“行为人知道行为违法,仍然实施类似行为,当然值得非难;行为人如果稍加注意,就能够认识到违法性,但行为人却疏于认识,藐视法律的存在,就是具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也值得加以非难。”(16)周光权.违法性认识不是故意的要素[J] .中国法学,2006, (1):168.但这一说法可能是存在疑问的。欠缺违法性认识者事实上也欠缺反规范态度,即便这种意识欠缺本身就是可谴责的,这也和谴责一个认识且有意敌视法律的人不可等同视之。“无论是将两者归入同一个谴责根据之下,还是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作为现实的违法性认识的上位概念,这在逻辑上都存在重大断裂。”(17)车浩.法定犯时代的违法性认识错误[J] .清华法学,2015, (4):30.
因此,有论者认为只有从机能性思考的角度出发,才能有效揭示为何可以“将在教义学结构上明显不同的具备违法性认识的情形与因陷入可避免错误而不具备违法性认识的情形放在同一个责任层面”(18)车浩.法定犯时代的违法性认识错误[J] .清华法学,2015, (4):30.。
一方面,拒斥“不知法者不免责”的“违法性认识不要说”是责任主义原则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轻纵犯罪、避免漠视法律的犯罪人以不知法律为由逃避制裁,又有必要借助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可避免性作为管道,以实现一般预防的刑事政策机能。因为“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违法性认识,但他本来有机会和可能认识到法律时,那么他就不能再根据违法性认识错误而享受免除责任的优惠。这不仅是部分地由于这种不去认真对待法律本身也具有可谴责性,更主要是基于刑事政策或规范效力的理由,如果这种因为漠视法律而犯罪的人也能得到充分的原谅,那么刑法呼吁公民忠诚于法或警告潜在犯罪者的一般预防的目的,就无法得到实现”(19)车浩.法定犯时代的违法性认识错误[J] .清华法学,2015, (4):31.。换言之,(积极)一般预防反对的是对规范的敌对、无视和疏忽,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规范信赖被动摇,因而需要刑罚重新确立规范的威信。故一般预防理论所要求的只是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而不是违法性认识这种心理事实。这是一种规范层面的要求,而不是一种事实层面的认定。这也足以防止某些人通过故意“无视”规范而逃避责任(20)陈金林.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198-199.。
然而,为何对法律的漠不关心具有可谴责性和预防必要性,而对于行为事实及控制行为所需的知识的漠不关心则能受到排除故意责任的优待,从而被排除出一般预防的视野?
行为人在作成一个故意有责行为的意思决定之时,实际上同时作了两部分的决定:一是违反某种禁止规范或命令规范的决定,二是采取某种具体行动的决定。前者以行为人对规范的认识为基础,即行为人必须知道法律禁止他为或不为特定行为,而后者则以行为人对行为事实和控制行为所需的知识(例如自然因果法则)的认识为基础,即行为人必须知道对人开枪射击的行为依据通常的自然因果法则,有着致人死亡的风险性。换言之,行为人在决意背离刑法规范和法秩序时,必然要同时运用到这两方面的知识。那么,为何一般预防功能的实现,只要求行为人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努力去学习法律规范,禁止行为人以不知法为借口无视规范、逃避责任,却对于行为人有意地不运用其认识事实的能力、对事实情状漠不关心的心态丝毫不加理会,反而还予以排除故意的优待?例如,行为人由于丝毫不在乎他人死活而对于某个生活上十分寻常的经验法则或自然法则根本不加思索,这难道不同样是一种背离法忠诚要求、因而应当被作为某种负面典范的表现吗?
由此观之,分明同样是在进行一般预防的机能性思考,但学理上却在构成要件错误和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处理方案上,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在存在论进路和机能论进路都难以充分解释这种处理歧异的情况下,有必要重新反思,作为问题出发点的两种处理方案,其标准设定究竟是否合理;尤其是,在构成要件错误的场合下,为何能够不问原因地一律排除故意?
四、不减轻责任的可避免违法性认识错误
事实上,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是一种对法的预见可能性,而“预见可能性”恰恰是过失犯的核心——所谓过失就是对法益损害结果的预见可能性,而故意则是预见可能性之上的、对法益损害结果的现实预见。因此,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构造中实际上同时嵌套了故意犯和过失犯的结构,差异仅仅是认识的对象由侵害事实变成了法规范而已。并且,在违法性认识错误可避免性的判断之中,实际上所考虑的具体标准——如行为人(21)对于违法性认识错误可避免性的判断应采取行为人标准抑或一般人标准,理论上存在不同看法。主流观点认为通常情况下考察的应当是具体状况下行为人本人的个人能力,但在特定领域中,也须对此标准进行一定的调适,参酌该领域之下一般人的认识能力进行判断。参见车浩.法定犯时代的违法性认识错误[J] .清华法学,2015, (4): 32-36. 孙国祥.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及其认定[J] .中外法学,2016, (3):707.的教育背景、特定的生活情况和职业情况、获取法律资讯的机会与可能等——与过失犯中预见可能性或注意义务的判断已经相差无几。例如,采取一阶层过失模式(个别化理论)的金德霍伊泽尔(Kindhäuser)即主张,“在考虑具体的行为人在其角色中相应的法律义务的前提下,其个人能力和知识便是判断可避免性的标准。这个标准和确定过失犯中所需要的(内在的)谨慎标准,在本质上是互相吻合的。”(22)[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 刑法总论教科书[M] .蔡桂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72.这也就意味着,在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场合,基于处罚和预防必要性的刑事政策考虑,一部分(无认识的)“过失”实际上便被擢升为(有认识的)“故意”,而不能获得免责的宽待。
当然,在可避免的违法性认识错误场合,通常认为仍应当给予行为人一定程度的责任减轻,因为“在通常的案件中,这种有意识地违法的人,比无意识地逾越法律的人,要承担更重的罪责;罪责理论也能够通过一种从轻处罚来考虑这个法律”(23)[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 [M]. 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611.。但这并非是当然的,而应当视行为人不知法律的具体理由而定,这即便是在实定法上已经规定了“对可避免禁止错误‘可以’减轻处罚”(德国《刑法典》第17条(24)德国《刑法典》第17条规定:行为时欠缺不法意识且无法避免者,无罪责。可避免者,可依本法第49条第1项之规定,减轻其刑。)的德国亦是如此。
德国学者认为,法官在对陷入可避免禁止错误的行为人量刑时,应当考虑是否使用减轻处罚的条款,在此,起决定性的因素是可避免禁止错误的罪责含量。通常情况下,可避免禁止错误中的罪责含量少于现实的不法意识中的罪责含量,因此前者应当适用更轻的刑罚。但是,当“这样一个错误并不比现实存在的不法意识更不严重”时,减轻处罚的条款就不应当适用了。这指的是如下情形:当错误显露出一种对“标准的”法忠诚(”normale“ Rechtstreue)的极为严重的偏离时,而这种偏离系由于法敌对或法盲目而产生。这也是德国《刑法典》第17条的规范含义之所在(25)Roxin, “Schuld” und “Verantwortlichkeit” als strafrechtliche Systemkategorien, Henkel-FS, 1974, S. 171, 188.Neumann, in: Kindhäuser/Neumann/Paeffgen, 4. Aufl., 2013, §17, Rn. 83. Joecks,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3. Aufl., 2017, §17, Rn. 80.。另外,当错误极其容易避免时,刑罚的减轻也是不适用的,例如,一个律师认为,即便是长年不结算律师费也仅仅只是违反了民事的或者职业伦理上的义务(26)Vgl. Neumann, in: Kindhäuser/Neumann/Paeffgen, 4. Aufl., 2013, §17, Rn. 84.Joecks,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3. Aufl., 2017, §17, Rn. 80.。此外,当行为人始终知道,其行为是违反社会伦理的,甚或在民法或行政法上是被禁止的,那么刑罚减轻的条款同样是很难得到适用的(27)Joecks,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3. Aufl., 2017, §17, Rn. 80.。
总之,在具体个案中对于可避免的禁止错误是否可以减轻行为人的责任,必须结合错误类型的特征进行个别化判断。不法的程度并不是拒绝适用减轻条款的充分理由,而充其量只是判定错误是否极其严重地偏离于法忠诚的一个迹象(28)Vogel, in: Leipziger Kommentar, 12. Aufl., 2014, §17, Rn. 92.。总体上,在进行具体判断时,应当同时考虑罪责原则和平等对待原则(29)Neumann, in: Kindhäuser/Neumann/Paeffgen, 4. Aufl., 2013, §17, Rn. 85.。而所谓的平等对待,指的便是“一个损害了基本社会道德规范的人,他在毫无良心地完全不考虑一种违法的可能性时的罪责,并不轻于他必须先不理会对法的顾忌时的罪责”(30)[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 [M]. 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611.。反过来说,“有所顾忌之人,对于禁止规范的逾越会有所犹豫愧疚,如果,对于漠不关心之人在处遇上比这样的人优渥的话,这就将会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结论。”(31)Günther Jakobs.主观的犯罪层面[A] .徐育安译.国际刑法学会台湾地区分会主编.民主·人权·正义[C].中国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75.
换言之,如果行为人是基于一种直接的、令人难以容忍的法敌对性或对法及公众利益的蔑视而产生了违法性认识错误,则虽然他在实施行为时并非有意识地违法,但仍可不减轻其责任。在此,所纳入的规范性思考无非是认为这种严重偏离于法忠诚的违法性认识错误具有高度的可谴责性和预防必要性,因此在最后的法律评价效果上仍要赋予该行为人和具备违法性认识者同等的法律后果。
上述对于构成要件错误和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处理歧异及对照,如下表所示:

认识对象侵害事实法规范有认识(预见)可能性有认识无认识严重偏离于“标准的”法忠诚非严重偏离于“标准的”法忠诚无认识(预见)可能性故意过失意外事件不阻却责任减轻责任免除责任
根据上表,不难发现,所谓构成要件错误和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处理歧异,从认识对象和主观心态的对应关系上看,在最终的处理效果方面,其差异最为显著地落脚于基于不可容忍的法敌对性或法盲目性、严重偏离于“标准的”法忠诚的对侵害事实或法规范的无认识之上:在有认识(预见)可能性的情况下,非严重偏离于“标准的”法忠诚的对侵害事实的无认识阻却故意,在本罪处罚过失犯的情况下,仅能成立过失,若本罪不处罚过失犯,则直接以主观构成要件不该当为由结束审查,作无罪处理;而严重偏离于“标准的”法忠诚的对法规范的无认识则不能起到减免责任的效果,因为这种漠不关心的意志内容本身即具有高度的可谴责性和预防必要性,基于平等对待原则的考虑,应当和具备违法性认识的行为人予以同等处罚,即不减免其责任。
五、故意概念再检视:无认识之故意?
(一)规范故意概念的提出
在承认上述违法性认识错误处理方案的合理性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为何严重偏离于“标准的”法忠诚的对侵害事实的无认识,可以毫无疑问地阻却故意?正如传统观点所主张的那样,即便对事实的无认识本身是具有可谴责性的,故意仍旧可以一概被排除(32)Sternberg-Lieben/Schuster, in: Schönke/Schröder, 29. Aufl., 2014, §16, Rn. 11.。也即,如果一个认知过程在事实上未能发生或是最终失败了,那么这里就欠缺一个与犯罪行为相匹配的正犯性认知。对于构成要件要素的无认识而言,重要的仅仅是这种无认识在事实上的确存在,至于个案中的具体情状则无关紧要(33)Sternberg-Lieben/Schuster, in: Schönke/Schröder, 29. Aufl., 2014, §15, Rn. 50.。
然而,前文论述已经充分表明,无论是存在论进路抑或机能论进路都不能为这一处罚罅隙提供圆满解说,相反,还会造成新的困惑。归根结底,此处存在的最为本质性的问题实际上是,人们坚持采用一种心理性的故意概念,因此在故意的认定中,就无从考虑各种规范性的评价。尽管人们认为在建构故意时同样需要考虑构成要件的呼吁和警示功能,但受制于对现实认识内容的过分强调和对意志活动与意志形成的物本逻辑式的僵化区隔,实际上在理解故意的一般预防机能时,人们还是倾向于以行为人心理事实层面的认识内容,作为判断一般人据此是否足以认真看待该风险关系、从而习得对法规范的忠诚或被法规范所威慑的资料和依据。与此相对地,在违法性认识错误层面,规范责任论和功能责任论的引入则使得人们在进行有责性判断时可以脱离上述窠臼,摆脱心理事实内容的约束,正面、直接地考虑导致“无认识”之原因自身的可谴责性和预防必要性。
自目的行为论提出以来,心理性故意与规范性责任的分化就成为理论上一种惯常的思维模式。但伴随着故意理论的发展,学说上也对心理性的故意概念提出了诸多批判,各种规范性的故意理论也随之诞生,如风险故意理论、故意危险理论、未受防护危险理论等等。但大多数规范性故意理论对心理性故意概念的攻击主要集中在意欲要素上,即认为“为了区分未必故意及有认识过失而将故意与一个特定的(但事实上不存在的)个人心理学状况相连结是一个失败”,不应“仅仅透过语言学的造作去假设一个事实上根本自身是不存在的(心理学)实在”(34)[德]许迺曼.由语言学到类型学的故意概念[A] .林立译.许玉秀、陈志辉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迺曼教授六秩寿辰[C].中国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473.。而在认知要素的认定上,规范化的触角似乎仍尚未全面入侵。然而,既然我们能够认同对意欲要素进行规范化的改造,用行为风险和行为决意所彰显的法敌对性、行为人所认识到的行为风险在规范上是否重要、行为人是否认识应该认真看待的危险等标准,规范性地判断行为人是否是基于故意而行为,那为何在认识要素的建构上,就要绝对地排斥此种规范性的思考?
实际上,上文的所有分析都意在揭示,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未认识到构成要件行为事实的行为人和现实地认识到构成要件行为事实的行为人,在对抗规范的法敌对态度上并不存在质和量的区别。而故意行为之所以总是比过失行为要受到更重的刑罚,原因在于故意行为人表现出了更高的颠覆法忠诚的态度(35)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 [M]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79.;换言之,“故意和过失的作用,只在于标示行为人遵法动机的强弱,并基此显示出法敌对性的高低,从而区分行为人不法内涵的高低。”(36)周漾沂.从客观转向主观[J] .台大法学论丛,43,(4):1506.如果行为人对构成要件事实的缺乏认识,正是源自于一种严重的、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法敌对态度,那么,其法敌对性并不会低于其他不存在构成要件错误的故意行为人。这就如同在责任层面上,严重偏离于“标准的”法忠诚的对法规范的无认识和现实的违法性认识之间,在评价上不存在差别一般。概括而言,“故意、过失以及对于不法最低的认识可能性,它们一定都涉及心理的事实或取向,亦即自然,但是这在刑法上并非必然具有重要性,它们其实是一个在刑法归责上重要要素的指标,这个要素就是所欠缺的法忠诚。”(37)Günther Jakobs.主观的犯罪层面[A] .徐育安译.国际刑法学会台湾地区分会主编.民主·人权·正义[C].中国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78.
(二)漠不关心的无认识作为一种故意形态
实际上,本文在此所试图讨论的,是一种由于漠不关心所导致的对构成要件的无认识。本文的基本立场是,如果某种构成要件错误是由于行为人可谴责的漠不关心而产生,则该错误并不必然排除故意。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漠不关心,并不是通常在间接故意中所讨论的对于结果实现与否的容认——因为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所说明的那样,在行为当时尚不存在的结果不可能成为故意认识的对象,行为人只可能对未来发生的结果进行某种预测,而这种预测仅仅是行为人所认识到的行为风险中的一部分。相反,这里所说的漠不关心,指的是对这种特定的认识欠缺本身毫不关心在意,甚至这种无认识的状态原本就是行为人在意志形成的过程中有意地、可谴责地造成的。
在这一意义上,德国学者雅各布斯(Jakobs)将漠不关心(Gleichgültigkeit)也视为是一种间接故意的形态,并反对德国多数学说将故意的成立与否完全取决于行为人的认识。他认为,故意不是一种完全仅取决于认识的心理状态(38)Jakob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 Aufl., 8/22.。若行为人由于漠不关心他人所可能受到的侵害,所以对该可能性从未放在心上时,行为人将因欠缺认识而获得评价上的优待,亦即仅成立过失,这将导致评价体系的错乱。因为,关心注意他人而将其权益放在心上的人,却反而会由于具备认识要素,成立较重的故意犯,这是一个规范评价上的自我矛盾(39)Jakobs, Über die Behandlung von Wollensfehlern und von Wissensfehlern, ZStW 101 (1989), S. 516, 529. 转引自徐育安.间接故意理论之发展[J]. 东吴法律学报,21(3): 85.。雅各布斯批评德国刑法典中关于错误的规定,认为刑法典只顾及了对于法律漠不关心的问题,而未考虑对事实的漠不关心。但是无论是对事实抑或法律的无知,都反映了行为人对规范效力的否认,他虽然未认识到行为的客观意涵,但不法的发生并不会让他感到惊讶,因为无论发生什么对他来说都是无关痛痒的。换言之,“行为人对于其行为所带有之特定性质并未予以留意,因为他对于此事并不感兴趣。这些所涉及到的行为性质,决定了行为的犯罪属性,或者是构成要件要素,抑或是行为的不法本身。”(40)Günther Jakobs.主观的犯罪层面[A] .徐育安译.国际刑法学会台湾地区分会主编.民主·人权·正义[C].中国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75.
德国学者帕夫利克(Pawlik)从公民义务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进一步补充。他认为,“考虑到公民对共同体的义务,与忠诚义务相符的行动当然是他可以期待的。由此,为了给一项义务配置忠诚的行为,即一种唤醒忠诚印象的行为,而赋予相关公民以法律上的不利,这同样是受容许的。……将上述义务模式同样延伸到故意阶段及责任阶段,公民的归责体系就会得到融贯的执行。谁要是以可谴责的方式(“行为漠视”)忽视合法控制行为所需的行为事实知识,则他在刑法上能够得到的免责与那些放弃得到必要法律知识的人同样少。”(41)[德]米夏埃尔·帕夫利克.人格体主体公民 [M] . 谭淦译.冯军审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9-70.
类似地,我国学者冯军教授也主张,应当特别注意防范“仅仅心理地理解犯罪故意的内容”,“从规范论的立场出发,认定不存在犯罪故意的标准,不是行为人没有认识到结果的发生,而是行为人对没有认识到结果的发生不具有负责性。……在规范的故意概念之下,不应该依行为人的恣意认定故意”(42)冯军.刑法的规范化诠释 [J] .法商研究,2005,(6): 64-65.。
对于上述观点,可以进一步从故意犯和过失犯的构造差异上加以证成。前文已论及,故意犯和过失犯在规范意义上的本质差异即在于,相比过失而言,故意对法忠诚和法秩序不容破坏的信赖的动摇更为严重。而这一本质差异,又可以被细化到如下两个层面上:
一方面,在心理事实的层面上,通常而言,阻却故意的构成要件错误产生于某种无知(Ignoranz),而这种无知与无能(Inkompetenz)在社会的评价上是相当的,因此,社会选择给予这种无知一定程度的宽恕,因为无知并不会给行为人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造成麻烦,破坏行为人的行为计划。无知所可能诱发的有害的自然流程(poenanaturalis)风险,就是无知的报应(43)Vgl. Jakobs, Die subjektive Tatseite, Nomos, 15 (2004), S.70.。易言之,当行为人没有认识到事实情状和自然、逻辑、数学的法则,他就不可能对这些法则加以利用,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目的的落空和行为人所不欲之结果的发生,就已经让无知者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这也解释了为何对过失犯的处罚总比故意犯来得轻。然而,对于漠不关心的行为人而言,虽然他对事态全无认识,但是此后事态究竟如何发生,对当下的他而言是毫不重要的,即便发生了不法,他亦不会感到惊讶,因此他的目的没有落空,有害的自然流程风险并没有发生在他身上,那么对他并没有给予刑罚优待的理由。
另一方面,在行为的客观构造层面上,尽管按照目的行为论的观点,故意行为和过失行为中都包含一种以目的性操控为内容的行为意志,但是,过失的事实结构,是行为人在追求某个非负面的目标时,由于未尽必要的谨慎义务,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这意味着过失行为人对于结果是缺乏支配的,结果的实现只是自然因果律作用的后果,而并非源自行为人对因果流程的操纵。换言之,过失犯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只有因果,没有支配。相较之下,故意行为是一种目的性行为,是行为人基于自己的认知支配世界、对世界所实施的负面规划。因此,故意行为人对风险及风险的现实化是具有意志和目的上支配力的。漠不关心的行为人的无知本身就来源于其意志和目的上的自我支配,在此实际上隐藏了一个类似于原因自由行为的结构,只是这里行为人有责导致的并不是一种欠缺责任能力的状态,而恰恰是一种对客观构成要件的欠缺认识。这一意志支配结构也证成了为何漠不关心导致的无认识不能阻却故意,而应该被视为是一种特殊的故意形态。
(三)对可能质疑的回应
将漠不关心的无认识作为一种特殊的故意形态,可能会面临以下两个质疑:其一,将罪责阶层的可谴责性评价引入构成要件阶层的故意认定中,是否会导致体系阶层之间的错位,进而退回到传统上不区分故意和罪责甚或是认为不法意识也是故意之组成部分的体系构造?其二,将漠不关心导致的构成要件错误规范性地评价为故意,是否会与我国《刑法》的规定相冲突?
对于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首先,故意的双重定位在理论上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尽管对何为罪责故意,学说上尚存在不同看法,但这至少有力地说明了“故意和过失之间的界限,不仅表明了一种不法的差异,而且表明了一种重大的罪责差异,这种差异使这两种举止行为方式承担了不同的惩罚:决定——即使不过仅仅出于可能发生的情况——侵犯受保护法益的人,显示出一种比——尽管是轻率的——相信结果不会发生的人具有更敌视法律的态度”(44)[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 [M]. 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93.。这种出于机能性考虑而对故意要素所作的灵活的体系安排和拆解也符合目的理性的要求。类似地,德国学者许乃曼(Schünemann)所建构的类型学的故意概念将故意的认识要素保留在构成要件阶层,而将意志要素纳入罪责阶层中,因为意志要素是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因素,无法被纳入故意。但与此同时,他又主张“意志性的故意之成分必须被回溯到一个确定的认知上”,而这种认知应当如何被确定,又要从处罚故意的目的中推演出来(45)[德]许迺曼.由语言学到类型学的故意概念[A] .林立译.许玉秀,陈志辉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迺曼教授六秩寿辰[C].中国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467-468.[德]许迺曼.刑法上故意与罪责之客观化[A] .郑昆山,许玉秀译.许玉秀,陈志辉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迺曼教授六秩寿辰[C].中国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484.。可见,以罪责层面的评价对故意中的认知要素进行规范性地把握,并不会导致体系阶层的错位,而恰恰是一种合目的的、符合刑事政策要求的安排。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一规定看似对故意的认识要素进行了明确限定,要求只有在“明知”的情况下,才可能成立故意。但是,事实上,现有的部分立法和大量司法解释已对“明知”的内涵进行了扩充,将一部分事实上不知、但同时“不知”的原因具有高度可谴责性的情形,也规范地评价为等同于“明知”的故意。例如,《刑法》第219条第二款规定:“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这里的“应知”,在心理事实层面上即为不知,但刑法却将不知和明知的情形规定在同一个条款中,同等地认定为故意犯罪,并配置相同的法定刑。为避免突破罪责原则和平等对待原则的边界,避免将可谴责性和法敌对意思较弱的过失犯擢升为可谴责性和法敌对意思较强的故意犯,有必要根据该条文的规范目的对这里的“应知”进行一定的限定,即要求只有在对构成要件行为的无认识系出于行为人的漠不关心之时,此种事实上的不知才能被规范性地评价为此处的“应知”,由此和“明知”的故意作同等处理。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许多司法解释中。例如,《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机动车解释》)第17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明知’,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视为应当知道,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一)在非法的机动车交易场所和销售单位购买的;(二)机动车证件手续不全或者明显违反规定的;(三)机动车发动机号或者车架号有更改痕迹,没有合法证明的;(四)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机动车的。”又如,《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刑法第345条规定的‘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中的‘明知’,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应当知道,但是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一)在非法的木材交易场所或者销售单位收购木材的;(二)收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的木材的;(三)收购违反规定出售的木材的。”(46)类似的司法解释还包括《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第2款、《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第2条、《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2款等。这些司法解释均将“应当知道”和“知道”并列,同样作为故意犯罪加以评价。目前的主流观点普遍认为“应当知道”其实就是不知,而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应当被理解为“推定知道”或“实知”(47)参见张明楷.如何理解和认定窝赃、销赃罪中的“明知”[J] .法学评论,1997,(2):88. 陈兴良.“应当知道”的刑法界说[J] .法学,2005,(7):80.周光权.明知与刑事推定[J] .现代法学,2009,(2):109. 王新.我国刑法中“明知”的含义和认定[J] .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1):66.。但这种观点存在如下三方面问题:
首先,严格地说,司法解释的表述是将所列举的特定情形“视为应当知道”,而非“视为明知”或“视为知道”。如果非要说这是一种推定,那也是对“应当知道”的推定(48)实际上,这里与其说是一种“推定”,不如说是一种“认定”或“规定”——实际上,司法解释也从未使用过“推定”的表述,而仅仅用的是“视为”——也即规定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忠诚于法的行为人“应当”对客观构成要件的事态有所认知。但根据前文讨论的故意犯与过失犯区分的一般原理,这里的条件应当比过失犯中注意义务的门槛要更高。——是在具备某些特定情形的前提下,据此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相应的客观构成要件——而非对“知道”的推定。但“推定知道”的观点显然是作了后一种理解,跨越了“应当知道”和“知道”的界限,反而是将“应当知道”推定为“知道”,这与司法解释的条文表述不符。
其次,主流观点将“应当知道”理解为“推定知道”或“实知”,会导致推定基准和结论的不稳定性。因为推定结论的作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者的个体认知。进一步而言,所谓的“推定知道”,其实是一种刑事证明层次上的故意客观化。但既然故意所涉及的仅仅是行为人的主观内在事实,那就不能用客观的外在事实对之加以全面替换,换言之,证明层次的考虑无论如何不能取代规范设定层次的考虑,否则会沦为一种单纯的故意假定(49)Kühl,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7. Aufl.,§5, Rn. 88.Sternberg-Lieben/Schuster, in: Schönke/Schröder, 29. Aufl., 2014, §15, Rn. 79.周漾沂.故意犯之主观归责范围 [J] .月旦法学杂志,2014,232:62.。
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应当知道”意味着在事实上并不知道。既然如此,将事实不知的“应当知道”理解为事实上知道的“推定知道”或“实知”,其实就已经偷换了“明知”的心理事实内容,分明是在事实层面强行为空白的心理状态填充进了认定故意所必需的对客观构成要件的认识。
实际上,按照本文的观点,完全可以对上述司法解释作出另一种在结论上同样具有合理性的解释。正如主流观点所正确地认识到的那样,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实际上就是一种不知,也即对客观构成要件的认识欠缺。但这种无认识之所以能与其他有认识的情形并列,并同样地被评价为故意犯罪,理由就在于,造成这种无认识状态的原因本身,严重地偏离了法对于守法公民的忠诚要求,因而是具有高度可谴责性的。例如,根据前引《机动车解释》,“在非法的机动车交易场所和销售单位”购买机动车的行为人,对于所购买的机动车是否是盗窃、抢夺所得机动车毫不在意,因为在这样的非法场所购买机动车本身就有极高概率买到盗窃、抢夺所得机动车,但对行为人来说,这根本不重要、不值得为此而操心。一方面,选择在非法场所买车,就说明买到盗窃、抢夺所得机动车并不违背行为人的本意。一个忠诚于法秩序、心怀善意的普通人不会在非法场所买车,如果有人在买车之前告诉他车是盗窃、抢夺所得,他必定会大为震惊并放弃买车。但在非法场所买车的行为人则对此根本漠不关心。这种由“在非法场所买车”的行为表现所透露出的对构成要件行为事实漠不关心的态度是严重偏离于法忠诚要求的,因此应当和其他具备事实明知的故意行为人在规范上作同等评价。另一方面,行为人踏入非法场所买车的举动已经使他陷入了一种难以辨识所购车辆是否赃车的状态,因为非法场所中的商品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一般消费者根本不可能辨识出购买的车辆是否赃车,换言之,一般消费者只要涉足非法场所买车,就难免陷入对构成要件事实的无认识。但是,进入非法场所买车本身就是行为人有意且有责地自我选择的结果,是行为人意志支配的产物。既然这种无认识也是行为人有意识自我规划的一个环节,那么行为人就应当为这种有意识规划导致的、在行为时点他毫无兴趣——因此当然也不反对——的法益损害结果承担故意责任。因此,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其实就是一种规范故意的表现形式,是将严重偏离于法忠诚的事实不知,规范性地评价为和“明知”等价的另一种故意形态。
此外,司法解释在对“应当知道”的情形进行列举时,同时还规定“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本文认为,这也并非是对“可反驳推定”的明示。行为人在被蒙骗的情况下,其认识欠缺就不是其有意识自我支配的结果,不是由其漠不关心所造成;“蒙骗”一词即意味着行为人对于其认识欠缺状态的反对态度,因此,行为人不需要为自己的“不知道”负故意之责。
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结论是:故意和违法性认识最终指向的都是行为人对刑法规范以及规范所保护的法益的反对态度。当行为人是基于一种直接的、令人难以容忍的法敌对性或对法及公众利益的蔑视而产生了违法性认识错误,则尽管在实施行为的时点,行为人欠缺具体的不法意识,但考虑到他对法规范漠不关心的态度,对他也应当给予和具备违法性认识的行为人相同的评价。这一结论转用到构成要件错误上也是如此。并非所有构成要件错误都能一概地、无条件地阻却故意,必须考虑产生错误的理由和错误是否可避免。但可避免性仅仅只能导向过失责任,尚不能充分地说明以故意犯之罪责谴责行为人的全面根据。在构成要件错误具有可避免性的前提下,行为人对构成要件事实的无认识,还应当产生自一种严重偏离于法忠诚要求的漠不关心态度——只有满足这一条件,行为人才必须对其“不知道”负故意之责;也唯有如此,对“不知”与“明知”作同等评价,在规范上才是符合刑事政策诉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