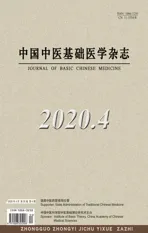《素问·六节藏象论篇》“六六”“九九”考辨❋
2020-07-17陈仁寿
梅 雨,陈仁寿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 210023)
《素问·六节藏象论篇》通篇1426字,除篇尾谈及藏象计353字外,通篇用1073字探讨各种“数”,涉及的数字有六六、九九、三百六十日法、三百六十五节、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三、五、四时、六、九。 历代皆有对这些数的注释和解读,以唐·王冰次注《素问》为最早、宋·林亿等补注、元末明初·滑寿《读素问钞》,清·黄元御《素问悬解》 都对这篇中的数字做了注解。这些注解指出数字来自“对天的度量”,“对天的度量”就是天文历法。 为何从古至今对这些数字的解读一直都有,今人却仍然不知所云?本文尝试从古代历法角度对此进行探讨和解读。
1 “六六”
1.1 “六六”的历代误读
《素问·六节藏象论篇》开篇:“黄帝问曰:余闻天以六六之节,以成一岁,人以九九制会,计人亦有三百六十五节,以为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谓也?岐伯对曰:昭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夫六六之节、九九制会者,所以正天之度、气之数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
对以上“六六”的注自王冰始注为:“六六之节,谓六竟于六甲之日,以成一岁之节限。”自王冰之后,历代医家对“六六”的解读皆不是其本来数值“六六=三十六”,而是理解为“六六=三百六十”。但是将“六六”理解成三百六十,将六六之节理解成一岁之节限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古书用字精准,六六当为三十六,而非三百六十;二是原文“天以六六之节以成一岁”,字面意思直接理解为“六六”是一节,节节相连以成一岁,不是王冰注解所说的“一岁之节限”。以“一岁之节限”解释原文“天以六六之节以成一岁”的“节”,属于“曲解”。
问题在于三十六代表什么意思?由于三十六所代表的含义在历史的长河中模糊了,王冰以降的注释者才做出“六六=三百六十”的错算。
1.2 “六六”之正解
1.2.1 “羲和生日”与十月太阳历 六六、三十六、七十二、五行、历法和《山海经》,这些看起来没有关联的事,其实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关于“十日”的记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羲和“生日”的实质是观测太阳运行规律,以太阳运行规律来确定一岁四时的节律,此为太阳历。《尚书·尧典》中记载羲和是尧时“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负责天文历法的历算之官[1]。羲和的“十日”历法在《山海经》中有一线痕迹,由于远古而被以为神话。古老的文明记录在文字中,比文字更远古的文明在神话中。羲和生“十日”这种历法与月亮的运动周期没有关系,是纯太阳历。对人类生存影响最大的天体就是太阳,地球上其他古老文明最早的历法,大都是以太阳周期运动为依据的太阳历,今天仍然使用的二十四节气历就是纯太阳历。《山海经》记叙的羲和之“十日历法”与月亮无关,与今天众多研究者探究的“十月历”或为同源。
1984年出版的《彝族天文学史》[2],三位学者的研究揭示出在古代中国曾长期通行过一种历法,这种历法以太阳运动定季节一年分为十个时段,每段固定三十六天剩余的五或六天称为“岁余日”为过年日。这种历法由彝族民间保存下来被重新发现,故称为“彝族十月太阳历”。陈久金对《夏小正》记述的天象、星象及物候进行研究发现,《夏小正》所记述的正是一部以太阳周期运动为依据所制定的十月太阳历[3],由此证实了夏代曾通行过一年只有十个月的太阳历。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李维宝说:“十月太阳历,首先是在彝族中进行实地口头调查获得,继而在哈尼族、傈僳族中均有发现。随后有人认为口头调查不可靠,从未见有彝文和汉文记载,进而提出彝族自古使用的就是十二月历。但近年来经多方发掘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有关十月历的彝文典籍,发现了《天文历法史》《十月兽历》《裴妥梅妮》《日月星辰书》和《彝族创世志》,均已译出汉文公诸于世。汉文古代文献《周易》《管子》《内经》和《太平经》中也发现有十月历的记载。”
除了彝族[4],在苗族[5]、哈尼族[6]、古蜀国[7]、羌族[8]等地方民俗研究中,都有十月历法的出现。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十月历”不是偶然仅仅在彝族曾经使用, 在其他众多古老民族中也曾经是广泛使用的历法形式。
“彝族十月历”的构成是这样的:把一年分为五个季节,每季两个月。五个季节分别用土、铜、水、木、火来表示,每季分雌雄。这样一年的十个月分别称之为:雄土、雌土;雄铜、雌铜;雄水、雌水;雄木、雌木;雄火、雌火。雄土月定为岁首,在夏至以后;雌火月定为岁末,在夏至以前。这样的排列中医人十分熟悉,即五行和阴阳。
1.2.2 “五行历” 社会科学学者研究发现的“十月历”如同一束光,告诉人们中医的“五行”不是虚的,不是哲学出来的,它早在“哲学”这个词出现数千年之前就存在了。五行是远古的历法,是祖先对一岁寒暑变化的生动表述。彝族“十月历”中的“月”与月亮没有关系,作为一个时间量词,为何太阳一个运行周期分成十个部分中的一份采用“月”?纯太阳历法被称为“十月历”而不是“十日历”或五行历?这就不得不面对数千年的“习惯”:或肇始于尧舜时代的阴阳合历是华夏民族在天文历法方面伟大的创造,将一岁四时以太阳周期为基础,同时协调月亮周期,数千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于将一岁之中的段落以“月”称之。 一岁太阳周期称为“年”,一岁之内则以月亮周期为基准,分为十二段或十三段,称之为“月”。自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到如今,都是采用“阴阳合历”,一年分成数“月”这个说法乃习惯成自然,却不适合以太阳周期为基础的太阳历法。十月历或许应该叫做五行历更合适。
以五行为历法,在古籍中也是有迹可循的。如关于天以六六为节的“节”。《白虎通德论·卷三·五行》有这样的解释:“行有五,时有四何?四时为时,五行为节。”
“四时”是一种更为远古的历法,是对一岁阴阳寒暑交替更迭的描述,以“四时”描述一岁的历法,以“时”为时间单位,四个时组成一岁。“五行历法”描述一岁以“节”为时间单位,十个节构成五行,五行为一岁,这是对“天以六六为节”的“节”最准确的解释。《白虎通德论》这一段的解读为,五行与四时一样是历法的一种,六六三十六日为一节,两节为一行,五行成一岁。
《管子·五行第四十一》明示五行历法的排序:木行72日、火行72日、土行72日、金行72日、水行72日,是为了“作立五行以正天时”[9],能够“正天时”的就是人间的历法。这是一个古代的日程表,所遵循的历法是五行历。
探寻远古历法的目的,对于学习中医的学者来说在于正本清源,把五行从哲学的、虚的筐里捡回来,落实到一岁之内自然界的木生、火热、湿土化、金肃杀、水归藏的5个阶段。五行是关于天道、人与自然周期变化形象且客观的描述,是祖先认识世界、表达自然周期属性的工具。
“黄帝问曰:余闻天以六六之节,以成一岁。”从五行历法的角度再解读这句话,黄帝说的是我听说历法是以六六三十六天为一节,累积成为一岁。
2 “九九”
2.1 “九九”的历代误读
《素问》原文中六六是天,天以六六为节以成一岁,九九是人,人以九九制会。岐伯的回答解释天的六六之节和人的九九制会说的是同一回事。“夫六六之节、九九制会者,所以正天之度,气之数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岐伯说无论是六六之节还是九九制会都是用来度量天的,是气之数,是用来规制日月运行的。所谓“气之数”在《中医大辞典》中的解释是:气数为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常数。气之数描述的是地面接受日光辐射的周期性变化,是根据天象标记时间的方式,所以六六、九九是不同时期历法中用到的数。

王冰的次注《六节藏象论篇第九》对“九九制会”的注解是这样的:一是九九制会,谓九周于九野之数,九九制会,气之数也。所谓气数者,生成之气也。周天之分,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十二节气均之,则气有三百六十日而终兼之,以制人形之会通也;二是小月日又不足其数矣,是以六十四气而常置闰焉。何者?以其积差分故也。天地之生育,本阯于阴阳,人神之运为,始终于九气,然九之为用,岂不大哉。《律书》曰:黄钟之律管长九寸,冬至之日,气应灰飞。由此则万物之生成,因于九气矣。古之九寸,即今之七寸三分,大小不同,以其先柜黍之制,而有异也。新校正云:按别本三分一作二分。
王冰除了以九州九野之数以制人形之会通来解释九九制会之外,又增加了邓平、落下闳制定《太初历》的指导思想,即以律制历的说法。
黄元御《素问悬解·卷十·运气》在“岐伯对曰:昭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夫六六之节、九九制会者,所以正天之度、气之数也”这一段下的注解是这样的:“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岁六六三百六十日,是为六六之节。其法原于黄钟之管,黄钟之管九寸,一寸九分,九九八十一分,三分损益,上下相生,律度衡量,莫不由之,是为九九制会。以九九之数,推六六之节,所以正周天之度,测四季之数也。[10]”
黄元御的注解将六六、九九混在一起统统用律法来解释,复述了王冰所提及的“黄钟之律管长九寸”,同时进一步阐述了黄钟律管与“九九”之间的关系:“一寸九分,九九八十一分”,给出“九九”即“八十一”。并阐明“九九八十一分,三分损益,上下相生,律度衡量,莫不由之,是为九九制会”。王冰的次注只是说:“九九制会”与黄钟九寸之管有关,到黄元御的注释六六、九九都归到黄钟之管上,让人更加不知所云。
以律为历法的基础,甚至以律为万事的基础,同律度量衡:用乐律标准音来规范度、量、衡制度,在历代史书中比比皆是。度、量、衡器的标准件用任何材质都会发生热胀冷缩的变化或磨损,如果真能而用黄钟标准音来规范度量衡标准,实在是最合理最先进的思维。但是如何使这个理想落实到实际中,今天已经找不到具体方法了,究竟是古人的想当然和附会,还是具体做法的遗失已经无法得知。
2.2 “九九”之正解
当代内经研究大家王玉川认为,“九九制会”以律制历是附会攀援[11]。所谓“九九制会”是一种以八十一为根本数据推算历法法则的概括,而且八十一这个数据也是来源于朔余,而朔余的根本在于天象,在于月亮运行的规律而不是黄钟,九九制会与音律、三分损益等没有任何关系。笔者认为,王玉川的观点还原了“九九制会”的本来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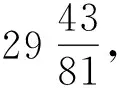
尽管八十一分法并不是当时最精确的天文数据,《太初历》不够精确,只用了189年(太初元年夏五月至后汉章帝元和二年二月甲寅,B.C.104-A.D.85)就废除了[12],但它却是现存第一部有较完整文献记载的古代历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后世制历的范本一直影响到今天。如以正月为岁首、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等。太初历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到王冰注内经时(唐宝应年间,A.D.762-764),距离《太初历》设立的太初元年已经过去近900年,能指明九九制会与黄钟之律有关联,为今人探究《黄帝内经》提供了一条线索的同时,也将后人带进音律漩涡1000多年。
3 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再来解读《素问·六节藏象论篇》开篇:黄帝问,我听说天以六六为一节,以成一岁,人以九九制会,人也有365节,这就是天和地,这是很久以前的说法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岐伯回答:您问的太英明了!所谓六六三十六日为一节,九九八十一制会都是用来规范天的度量,用来标志万物化生时间节律的,所谓天的度量是标志太阳、月亮运行规律的。
通过对五行历法的研究,找到了中医基础五行、阴阳的来处。 中华文明的久远,在中医中得到体现,中医所用的文字、词语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越是基础的词句如历法约定的时间节点、周期,使用者默认无需解释而人人理当知晓,在当时的时空确实如此。然而斗转星移,时空变换,到了后世再去解读久远之前的基本词句,会自动“代入”后人所处时空对这些词汇的理解,歧义和模糊由此累积,以至于今天读中医经典会出现不知其然更不知所以然的情况。
《太初历》采用朔策八十一分法,由八十一分法制定出的《太初历》的精度并不高,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45年)就废止了。这也许是后人在注释八十一分法时,忽略《太初历》只强调尧舜时代同律度量衡,以九九黄钟音来强调其正统和正确性的原因。在《内经》中,解读“人以九九制会”,在明确人与天相制会,天的表现形式是历法,同时可以得知《内经》这一章的这一个段落的出现不会早于西汉。
通过对《素问·六节藏象论篇》六六、九九的辨析可以看出,梳理《素问》中的历法知识的重要性。历法具有指导人们生活却日用而不自知的特点,而且历法又在持续的变化中。如今天的元旦已经不是西历1912年之前的元旦,今天的春节才是那时的元旦。《内经》成书具有不同年代文献汇集的特点,在历法的使用上具有不同时期、不同历法的现象。尤其在《素问》的七篇大论中,由于对历法背景的不清楚造成的迷惑更多,故此梳理《素问》中的不同历法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