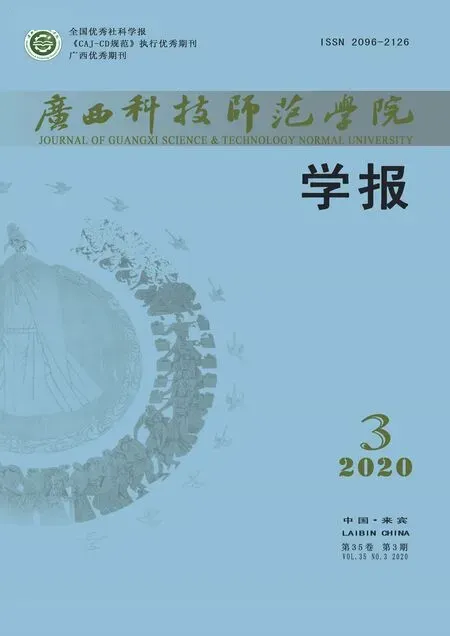域外悲音
——汉代疆域外的楚歌创作
2020-03-17刘亚旭
刘亚旭
(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宝鸡 721013)
楚歌,即“楚地传唱的歌诗”[1],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它多用“兮”字调节诗歌节奏,句式参差不齐,形式上较为活泼自由,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汉代初年的帝王将相大多是楚人,楚歌这种豪迈奔放而利于抒发个人情感的艺术形式也传遍了全国。到汉武帝时期,朝廷屡次进行对外军事活动,让大汉王朝的声威有了坚实的保障,使汉王朝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2]551,尤其是汉王朝的老对手匈奴人,也因连年作战而“孕重堕㱩,罢极苦之”[2]933。随着汉王朝疆域和国力的不断扩大,楚歌这种便于抒发个人内心真实情感的艺术形式也随之传到了域外。
一、将军百战声名裂:李陵的《别歌》
李陵是汉朝名将李广的长孙,为人“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2]547。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他率部出击匈奴,以五千余步兵对抗匈奴数万骑兵,浴血奋战,毫不畏缩,杀伤匈奴军无数,但终因奸细叛变,后援不至,在伤亡惨重、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李陵长叹了一声“无面目报陛下”,被迫投降匈奴。
十七年后的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冬,在冰天雪地的漠北,一场气氛悲壮的酒局被载入了史册。对酌的双方一位是名满天下,清操可嘉,即将归还汉廷的苏武;一位是身败名裂,妻离子散,此生难回故土的李陵。两个同样不同凡响的豪杰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命运。“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2]552
再饮数杯,两位老友便从此永诀,至死也再未谋面。最终,八年后的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一代名将李陵带着无尽的遗憾,病死在了离长安万里之遥的匈奴地界。李陵半生的心事,都化作了这一首《别歌》,飘荡在了异域的长空中。两个同样豪情万丈的英雄志士,最终的人生结局却有着天壤之别,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慨叹。
李陵在诗作一开篇就回忆起了那个他人生中最为豪迈、最为光彩的时刻,“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他自言“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2]547,以悬殊的兵力向处于绝对优势的敌人发动了进攻,“垂饵虎口,横挑强胡”[2]620,展现出了自己突出的军事才能。而后,诗作以一句“路穷绝兮矢刃摧”把这次英雄行动的悲剧气氛渲染到了绝对的高潮。当时“矢尽道穷,救兵不至”[2]620,李陵部败局已定,然而他“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2]620,可见李陵部的最后覆灭是悲壮的,故而让他在十七年后想起当年的场景仍旧意不能平。而后一句“士众灭兮名已颓”让情绪一落千丈,懊悔、屈辱的情绪与前面的悲壮场景形成了巨大落差,这两句一起构成了李陵内心情感活动的真实写照。最后一句,李陵仰天长叹“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绵长的句子显现出了李陵蕴含在内心深处的多年的悲凉与愤慨。既有自己英雄失路的苍凉之感,又有对汉武帝刻薄寡恩的愤怒控诉,正是“陵虽孤恩,汉亦负德”。“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2]549,“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3],这成为了李陵心头挥之不去的血色的阴影。
李陵言:“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2]552这应当与他的这首《别歌》一样,是他内心想法的真实表述,而非托辞。这首《别歌》是李陵积聚多年的悲愤情感的最为真实的表达,体现了他从豪言出师到身败名辱的巨大落差,是一个粗犷质实武人的心声在异国土地上的真情流露。同时,通过这首楚歌也可以见到,在汉武帝击败匈奴的辉煌的赫赫武功背后,无数像李陵一样的个人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痛苦。
二、独留青冢向黄昏:刘细君的《悲愁歌》
刘细君是江都王刘建之女,刘建因企图谋反不成自杀后,她以罪臣之女的身份被汉武帝封为公主,前往乌孙和亲以密切两国关系,共同对付来自北方的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匈奴。刘细君作为第一位嫁往乌孙的汉家公主,留下了“乌孙公主”的雅号。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刘细君从汉地出发,远嫁乌孙异域。到了乌孙以后,刘细君便发现自己的生活陷入了一场巨大而无尽的悲剧之中。“穹庐毡帐,羊肉酪浆”,这种日常生活上的不适应,一遍遍地提醒着刘细君她已远离故土,加剧了她本就敏感的内心的悲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悲愁歌》才得以以楚歌这种刘家皇室较为熟悉的形式在刘细君的口中吟唱出来。
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2]971身在异国他乡的汉家的公主只能以楚歌这种在汉地宫廷中就已熟悉的形式来尽情排遣着内心深处的愁闷。
《悲愁歌》一开篇便直接叙事,“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点明了自己生命悲剧产生的根源。刘细君“悲愁”的是,她嫁的乌孙王“年老,语言不通”[2]971,她只是“岁时一再与昆莫(即乌孙王)会”[2]971而已,没有任何情感可言。更可“悲愁”的是,她又被昆莫“使其孙岑陬尚公主”[2]971,“远托异国兮乌孙王”之“乌孙王”变成了祖孙两代,这完全背离了汉朝的伦理道德,使得刘细君的内心深处愈发难以接受,她“上书汉武帝言状”[2]971,却被汉武帝命令要“从其国俗”,为“欲与乌孙共灭胡”[2]971的国家战略服务。作为一个无力把控自己命运的贵族女性,刘细君心灵上的巨大痛苦可想而知。接下来一句“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刘细君将这份痛苦通过具体可感的形式描绘了出来。无论是居住环境还是饮食习惯,都与刘细君自幼习惯的汉宫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可感的具体生活愈发加重了刘细君内心深处的不适感。乌孙本就是一个“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2]970的国度,这让一个来自农耕文化王朝的贵族少女很难适应,于是“居常土思兮心内伤”,魂牵梦萦的是自己生长多年的祖国,希望能够化身“黄鹄”,飞回万里之外的故乡。全诗也就在这无尽的思念与遥想中戛然而止,给人体味刘细君内心无尽的哀愁留下了丰富的空间。
可悲的是,刘细君化作“黄鹄”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在她写作《悲愁歌》之后仅仅四年之后的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便客死他乡,随着《悲愁歌》这首凄婉的楚歌一起,长眠在了西域的土地之上。
刘细君的《悲愁歌》没有运用过于绮丽的语言,纯是家常话般的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和实际生活场景的描写,难怪能够收到“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2]971的艺术效果。全诗从平直的叙述到客观的描写,再到最后抑制不住的内心情感的表达,句句真实,以一个“真”字打动了后世读者的心灵。它是历史上和亲政策最为生动的写照,作品从个人视角而不是历史的视角出发,由一个贵族少女在异域的土地上唱响,这歌声绵延千年而不绝,流入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田。
三、关山阻修行路难:蔡琰的《悲愤诗》(其二)
蔡琰,是东汉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她因东汉末年关中地区大乱,被匈奴人趁乱掳走,在匈奴的土地上生活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直到建安十一年(公元207年),才被曹操用金璧从匈奴赎回,再嫁于董祀。《悲愤诗》共有二首,一为五言,一为骚体,当皆为蔡琰归汉之后追忆愁苦岁月而作,是以楚歌形式对自己异域苦难岁月的生动记述,是那段动荡历史的艺术再现。其中《悲愤诗》(其二)尤为真实动人,是蔡琰苦难人生经历的结晶①关于蔡琰之《悲愤诗》(其二)的真伪问题,学者们争论不休,迄今尚无定论。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言“这一首楚歌,无支辞,无蔓语,全是书写自己的生世,自己的遭乱被掳的事,自己的在胡中的生活,自己的别子而归,踟蹰不忍相别的情形。而尤着重于胡中的生活情形,全篇不到三百个字,是三篇里最简短的一篇,却写得最为真挚”,论述十分有力。他着眼于诗歌本身内容与情感表达,肯定了其真实性。加之自《后汉书》始,《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选》注,《太平御览》皆有引用,《古诗纪》也加以收录,故本文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出现的情况下,还应将其视为蔡琰的作品,不可轻易视为伪作加以否定。。
关于蔡琰的《悲愤诗》(其二)首见于《后汉书·列女传》:“(蔡琰)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二章曰: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门户单。身执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羌蛮。山谷眇兮路曼曼,眷东顾兮但悲叹。冥当寝兮不能安,饥当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眦不干,薄志节兮念死难,虽苟活兮无形颜。惟彼方兮远阳精,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窈停。岁聿幕兮时迈征,夜悠长兮禁门扃。不能寐兮起屏营,登胡殿兮临广庭。玄云合兮翳月星,北风厉兮肃泠泠。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乐人兴兮弹琴筝,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愤盈,欲舒气兮恐彼惊,含哀咽兮涕沾颈。家既迎兮当归宁,临长路兮捐所生。儿呼母兮号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追持我兮走茕茕,顿复起兮毁颜形。还顾之兮破人情,心怛绝兮死复生。”[4]824-825《后汉书》全文收录了这首优秀的楚歌作品,把它作为了蔡琰这一段苦难人生经历的真实而生动的艺术写照,代替了平直的史笔记述,更能让读者真切体味蔡琰的人生悲剧。
诗作一开篇先简要交代了悲剧发生的背景:“兴平中,天下丧乱。”[4]824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弱女子就更加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惨遭劫掠,被迫流落到了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而后,蔡琰在诗中重点渲染了初至异域时内心真实的心理状态。思念故土,惶恐不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与激烈的心灵斗争中,蔡琰陷入了生存的挣扎。接下来,她具体描写了异域不同于中原的风景民俗。从万里冰雪,沙尘飞扬,不见生机的自然环境到食物腥膻,语言不通的完全陌生的人文环境,都给这个出身士族的女性以巨大的考验。这幅真实而生动的胡地生活画卷,是蔡琰透过苦难的滤镜用诗笔细腻而真切地勾勒出来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她自然是“不能寐兮起屏营”了。接下来的笔墨,使人如闻其声。蔡琰本“妙于音律”,在这段文字中,她又将一幅画卷变为一首乐曲了。在乐曲中,有胡笳,有马鸣,有雁声,有琴筝,这种种地域色彩浓厚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为蔡琰奏出了一首诉说她十二年来不幸命运的交响曲,乐律感极强,动人心弦。最后一段,写的正是著名的“文姬归汉”的场景。可怜天不遂人愿,得返故土的代价是与亲生骨肉永远分离,再不相见。作为母亲,自然要“念我出腹子,匈臆为摧败”[4]825。在对别离亲生骨肉的难以消解的悲痛之中,全诗也有了一个沉重的收尾。“心怛绝兮死复生”,悲痛无穷无尽,异域的苦难岁月和别子的心酸场景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抚平,反而在这首《悲愤诗》(其二)的笔端显得愈发清晰。
《悲愤诗》(其二)语言生动,概括能力极强,以三十八句的篇幅为自己十二年的苦难作了一个高度浓缩的艺术概括。全诗“无支辞,无蔓语”,图画、声音并茂,充分地调动了读者的多种感官,非身临其境,心历其悲者不能道。在这首诗创作后的十余年,大汉王朝也走到了尽头。可以说,这一首反映东汉末年流离异乡孤女悲惨生活的纪实性楚歌,为两汉四百年楚歌诗发展史画上了一个沉重的休止符。这首《悲愤诗》(其二)与它的作者蔡琰的不幸命运,被后世读者反复言说、评论,这首写于汉土却描述胡地悲欢的楚歌,也成为了一首楚歌诗史上的经典之作。
楚歌,这种以“兮”字为明显标志的“有着极强的抒情性和感染力”[1]的艺术形式,被富有开拓精神的大汉子民带到了异域,书写着他们在故土之外的种种离合悲欢,发挥了其表达内心情感的作用。作者本身在创作过程中没有刻意进行艺术上的修饰,只是随着内心情感的流露进行自然表达,但却具有打动读者心灵的力量。李陵《别歌》是失意名将无限悲愤的外化,从豪情出塞、奋勇杀敌到长留异域、身败名辱,巨大的落差让一个强悍武人的心灵也难以承受,故发为悲歌。刘细君《悲愁歌》是一个为王朝利益牺牲个人幸福的贵族少女的悲吟,貌似平实的叙述之中包含着无限身不由己的无奈和回归故土的渴盼。蔡琰《悲愤诗》(其二)是一个士族才女在王朝末世屈辱经历的见证,除了个人命运的一落千丈,还有一个王朝盛世的付诸东流。
无论是将门之子,还是贵族少女,抑或是士族才女,都以楚歌这种便于抒发真实情感的艺术形式在汉朝疆域之外发出了动人的歌声,可见楚歌的影响之大。它已不再单纯为楚地这一地域所局限,而是成为了一个时代优秀文学形式的代表之一,见证着异域土地上汉家儿女的离合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