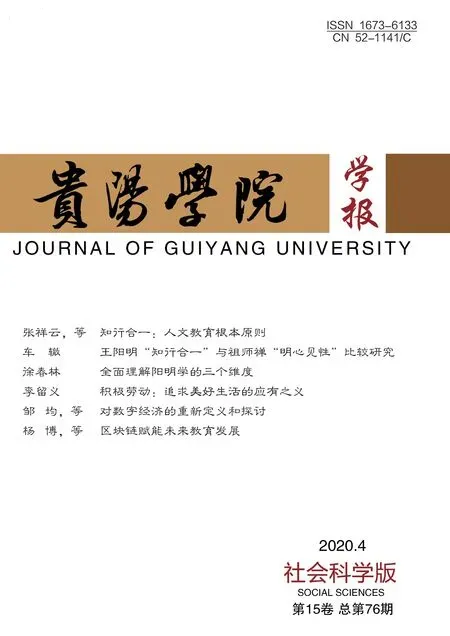清代牛痘术在华推广赞助路径探析
2020-03-15王彬
王 彬
(1.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海淀 100089;2.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史上,国际范围内医学文化的交流有力助推了人类传染病预防事业的发展。天花预防的中外交流促成了人类在世界范围内成功消灭了肆虐数千年且危害极大的天花病毒,成为世界传染病学交流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也为人类传染病学交流事业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人体内的天花病毒很可能是由某种野生或家养动物的痘苗病毒进化而来的[1]。天花病毒最初只局限于亚非地区,后来随着人口迁移、战争和世界贸易的发展,被传入其他地区。天花是人类历史上传染性最强且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死亡率一般在15~25%之间。中世纪,天花在世界各国广泛流行,几乎有10%的居民死于天花[2]。天花危害之巨甚至连中外的帝王也无法幸免,仅中国清代的12位皇帝中就有两位(顺治和同治)因天花而去世,两位(康熙和咸丰)虽劫后余生,却在脸上留下麻点。鉴于天花病毒给各国人民带来的危害之巨,各国人民同天花病毒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仅就中国而言,明清两代医家留下的大量痘症专科的著作可谓是中国人民抗击天花斗争史的最好见证。在人类抗击天花的历史上,各国人民非常重视汲取他国的宝贵经验。天花在世界范围内的消亡正是由于中国人痘术海外传播后被改良成牛痘术,并在世界范围内强力推广的结果。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 1749—1823年)在中国人痘接种术的基础上发明了牛痘接种术,牛痘术被范行准誉为人类“人工免疫法的开始。它在预防医学史上是一件惊天动地之事”[3]。和人痘接种术相比,牛痘接种术操作方便,危险性更低,效果甚佳,很快被传播到其他国家。牛痘术传入中国后由于其显著的预防效果而备受推崇。光绪之后,牛痘术代替传统的人痘术已成趋势,晚清昆山医家王德森曾言:“近年(光绪年间)牛痘盛行,痘科专家,几同绝响。”[4]牛痘术的中国推广有力助推了中国的天花预防事业,也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史学界对牛痘术中国传播的关注基本上聚焦于对史实的考证,如邹振环[5]71-72、侯毅[6]针对《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中牛痘接种法在中国推广助推的考证,董少新[7]和陈朝晖、郑洪[8]157对岭南医家邱熺推动牛痘在华传播史实的梳理,廖育群[9]从传播始末、重要人物及方书、官吏乡绅的作用、所采用的技术手段、理论问题等方面对牛痘术在近代中国推广的系统考证等。上述学者对清代牛痘术在华传播史实的梳理有助于学界清晰认识牛痘术传华史实,但学界不应忽略的是清代牛痘术在华推广的成功主要是基于商人、医生、士绅、官员、传教士等社会力量的赞助,对清代牛痘术在华推广赞助路径及其得失所做的系统梳理,对当前传染病预防先进技术的国际交流和推广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清代中外社会力量对牛痘术在华推广赞助的路径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能对中外传染病学交流事业有所裨益。
一、牛痘术在华推广赞助的缘起
天花在中国医学中被称为“斑疮”“痘斑”“痘”“天痘”等。中国天花源于国外,有关天花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见于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 :“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后,疮瘢紫黑(当做‘黯’),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世人云:永徽四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煮葵菜,以蒜齑啖之,即止。初患急食之,少饭下菜亦得。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仍呼为虏疮。”[10]据李经纬[11]和马伯英[12]806考证,上述“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指公元44年马援征交趾从越南传入。由于传染性强且致死率高,天花传入中国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据粗略估计,在清代,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儿童死于痘症[5]73。出痘在当时几乎成为人人必过的鬼门关,在当时的各种文献中,常常可见如下说法:“然自有痘以来,贤愚贵贱,罕能坠免。”[5]73中国医史上治疗天花专著之多,除“伤寒”专著外,罕有匹敌,也从侧面证明了天花对国人的危害之巨。天花的巨大危害甚至催生了清政府专门针对天花的检疫工作。清朝入关初期就设立“查痘章京”一职,专司检查痘疹,一经发现,就责令患者迁移他处,以防传染他人。对乘船来华者,也派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如有,则需待平愈后入港[13]438。中国历代医家为防治天花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据考证,人痘接种法在明代隆庆年间已盛行于世。清代俞茂鲲的《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又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家之传,由此蔓延天下。”[12]811清初,由于康熙的大力提倡,人痘法得以流布四方,但当时种痘费用高昂,且存在一定的风险,虽经改良技法,人痘法在寻常百姓中难以普及。中国的人痘术是人类天花预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革命性进步,后经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并启发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发明了牛痘接种术。和人痘法相比,牛痘术操作方便,危险性更低且效果甚佳。英国东印度公司医官皮尔逊(Alexander Person,1780—1874年)所著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中对牛痘术相较于人痘法的良好效果进行了清晰的阐释:“天花之症,定必发寒发热,大小便结闭不通,或昏迷不醒,喉干舌燥唇焦乱话不等,虽用针薰药法,亦不能保其无虞;但其牛痘种在于所种之处,只出一颗,如小指头大,至寒热各症不能相染,内中或有微寒微热。虽服药不服药,与病无干碍。”[14]鉴于天花危害之巨和牛痘术相较于人痘法的显著优势,牛痘术传入中国后受到了社会力量的大力推广,商人、医生、士绅、官员、传教士等社会力量对牛痘术传播事业的赞助有力助推了牛痘术的中国传播。
二、牛痘术在华推广赞助路径
1.技术推介
牛痘术在清代中国的推广首先归功于中外社会力量对技术推介的赞助。牛痘术传入中国首先起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对外交往态势下,为了扩大中国市场,东印度公司努力增加与中国民众的交往,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认为医学是扩大与中国民众交往的捷径。由于广东天花流行,东印度公司总督在1803年收到一份急件,希望将英国在印度推行的牛痘术同样推行于中国。同年8月,东印度公司孟买总督寄往中国的疫苗两个月后到达中国,但已经失效。1805年春,英国东印度公司高级外科医生皮尔逊和澳门医生一起使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许威氏(Hewit)由马尼拉带来的“活牛痘苗”后“照法栽种华夷童稚不下数百,俱亦保全无恙”[3]134。鉴于需要接种牛痘的人数太多,为更好地在华推广牛痘术,自1806年起,皮尔逊开始雇佣中国助手并教给他们种痘技术。皮尔逊在自己的报告里说:“为了使牛痘传播更加广泛,我采取了最好的方式。我已经培训了几个中国人,教他们种痘的细节。他们在我的监督下为人种痘,同样也在其他地方为人种痘。”[7]140除传艺于中国助手之外,皮尔逊还编写了《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的小册子,对牛痘接种方法和注意事项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该手册由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年)译成汉语后广为流布,对中国的天花预防事业影响深远,被邹振环录入《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15]。皮尔逊通过传授中国助手牛痘施种技术和编写手册把牛痘术成功引入了天花流行的广东,在中国的天花预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皮尔逊的第一批中国助手中最出色的是南海人邱熺(字浩川,1773—1851年)。邱熺自言“素不知医”,皮尔逊把牛痘术引入澳门时,因自己未曾出过天花,见牛痘术有“不择天时,不烦禁忌,不延医,不服药”的优点,且易于掌握,便以身试之,果然效果很好,在家人和亲友间推行也“无不验者”[16]。邱熺学成牛痘术之后终身以传种牛痘为业。邱熺在广州十三行商人的资助下开设牛痘局,施种牛痘,且把牛痘术又传授给他人,亦常被延请至各地施种并传授其法。邱熺于牛痘局免费施种并传授牛痘术的做法被后来各地的牛痘局纷纷效仿,且以条文的形式加以公布,如《京都牛痘公局条约》规定“种痘之法,人人可学”[3]162。除向学徒传授种痘技艺外,邱熺还推出了《引痘略》一书。作为中国人推出的论述牛痘术的第一本专著,该书以中医理论对牛痘术的文化顺应性阐释极为成功,大受国人欢迎,成为当时中国推广牛痘术最主要的方书,“迄今各直省广种牛痘,皆祖是书也”[8]161。在邱熺的《引痘略》之后,以其为基础的专论牛痘术的医书日渐增多,如《洋痘释疑》 《种痘法》 《引种牛痘方书》等。以《引痘略》为代表的专论牛痘施种的书籍为国人按法施种牛痘提供了便利,有力助推了牛痘术的中国推广。广东香山人翰林院编修曾望颜(卓如)在《创设京都牛痘局叙》中指出:“因将邱氏书详加校订而并弁翻译夷医原说于前,以存其始。合而刻之,遍告于世,仁人君子益能广其传也。”[16]690除痘师传授技艺和刊印书籍外,一些国内的大众媒体也对牛痘术大力推介,如1894年《申报》对牛痘术进行了如下介绍:“用人痘浆不如用牛痘浆之为妙……种时以小刀轻轻刮之,不可多见血,……其便易盖有如此者。”[17]691免费传授技艺、刊印书籍、报刊推介等赞助手段有效助推了牛痘术在中国的推广。
2.资金支持
技术引进与推介为牛痘术在中国推广创造了先决条件,但牛痘术在中国能否得到更好的推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事实上,自明代出现人痘法之后,经过医家的不懈努力,清代时人痘法危险性高的缺点已经被克服,种人痘的死亡率已经极低。大力推介牛痘术的邱熺曾言,施种人痘虽然事捷而功巨,“然尤失十一于千百”。力主通行牛痘,禁止人痘的金东也说:“每见素业吹种者,虽号称国手,但种至百人,即不能不失一二。”[4]215力主推广牛痘术的人士都承认人痘法的成功率可达98%以上,足见在痘师技术有保障的情况下,人痘法的安全性是可靠的。人痘法虽然成功率很高,但由于种痘费用高昂,中国的一般家庭难以承担,以致虽然天花危害巨大,但施种人痘的比率却很低。牛痘术虽然相较于人痘法操作简单,安全性高,但鉴于中国普通民众中贫困者较多的状况,牛痘术能否得到有效的推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支持是否充足。有鉴于此,有志于推广牛痘术来造福国人的各界人士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如通过免费施种来助推牛痘的中国推广。皮尔逊培训的以邱熺为代表的第一批中国助手是由广州十三行中会隆商行主人郑崇谦资助的,邱熺等人学成之后在广州十三行商人资助设立的牛痘局免费施种。源于广东的社会力量筹资设局以推广牛痘的做法受到各地的效仿,牛痘局由南向北逐渐得以普及,有力助推了牛痘术在中国的推广。商人、士绅和地方官员的鼎力资助可谓是牛痘术在华得以流布的重要推手,对此,各地方志中多有记载。光绪年间的《广州府志》对牛痘术初入中国时商人及地方官对牛痘局的资助有如下记载:“即以其小儿痘浆传种中国人,洋商潘有度、卢观恒两都转、伍秉监方伯共捐银三千两,发商生息,以垂永久……至道光壬寅二十二年(1842年),经费为当事者所亏,伍方伯崇耀遂独力支柱者十年。至同治壬戌元年(1862年),制府劳文毅公崇光札谕惠济义仓,岁拨银约百五十两,仍稗当事者,后人分董之,以永其传。”[17]18由上述可见,为推广牛痘术以造福国人,十三行商人捐银三千两。在商人筹资所设的种痘经费不足时,制府劳文毅为助推种牛痘事业的继续,命惠济义仓每年拨付白银一百五十两,且令后人“分董之,以永其传”。商人们不仅热心于造福乡里,还致力于推广牛痘术于他乡。1828年,十三行巨商潘仕成出资购买大量牛痘疫苗并亲运至京师,设立种痘局并任命邱熺弟子余心谷主持种痘事务,北方大批人士前往学习,有力助推了牛痘术的普及[18]。源于广东的免费施种并传授技术的牛痘局在地方官员的直接介入下纷纷设立。地方官员为设立并维持牛痘局,除地方政府拨款外,往往还自己捐银,甚至饬令下属拨款或捐款。除商人和地方官员在城市筹资设立牛痘局外,在乡村,地方士绅也筹资设立善堂来推广牛痘术。民国《香山县志续编》第四卷中对乐善堂有如下记载:“乐善堂在四大都,光绪初,痘症流行,夭折者众。里人陈德周、简桂芬、严鸾明、程鹏万发起,设一赠种洋痘局,名曰乐善堂,众踊跃捐助,集款二千五百六十两,购置田产,历年延痘师赠种。”[17]140官商士绅们筹资设立牛痘局或善堂进行牛痘免费施种的举措,对广大贫困的国人极具吸引力,有力助推了牛痘术在中国的推广。
3.文化认同与调适及舆论引导
牛痘术传入中国之始,国人普遍抱有怀疑心理或抗拒心理。国人的怀疑和抗拒心理造成施种牛痘难以为续,痘种失传较为常见。光绪年间的《广州府志》有如下记载:“蕃商哆林呅携牛痘种至粤……顾粤人未深信,其种渐失。”[17]18为消除国人的怀疑和抗拒心理以助推牛痘术的中国推广,中国的精英人士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文化认同与调适及舆论引导等举措。为了使牛痘术顺应国人的认知心理,精英人士从传统医学中寻找出理据进行文化调适与认同。兵部侍郎温汝适指出:“《本草纲目》有稀痘方,用白牛虱,以此虱扑缘牛身,食饱自坠,用之能稀痘。该取其中有牛血也。牛虱尚能稀痘,则牛痘必稀用其苗以种,百无一失,理其固然。是中国人已发其端,而外洋人遂触类引伸耳。”[17]86温汝适的牛痘术源中观点的科学性虽未经证实,但却有效拉近了牛痘术与中国民众的心理距离。邱熺在《引痘略》中也用中医学理论对牛痘术进行了本土化调适。中医传统理论认为天花是人体内“胎毒”感染“时行”所致,去病在于引毒外透。《引痘略》书名中的“引痘”就彰显了邱熺对牛痘术的文化调适与顺应态度。邱熺还利用经络学说对牛痘施种于上臂相较于中国人痘法——鼻苗法的安全快捷优势进行了深度阐释。他指出施种牛痘的消烁与清冷渊二穴属于手少阳三焦经,“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牛痘术施种于上臂把握了三焦经这一“关要之府”,所以比传统鼻苗法更为快捷安全。邱熺上述理论的科学性虽值得商榷,但就消解国人对牛痘术的抗拒心理而言可谓功不可没。该书对牛痘术的本土化调适顺应了国人的认知心理,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牛痘施种工具书,其他医家后续推出的痘症专科书籍大都以《引痘略》为宗。为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各界力量还通过报刊发文、发布公文、撰写诗文等举措对牛痘术进行了弘扬。基于传播西学的办报动机,《遐迩贯珍》《中西见闻录》《中外新闻七日录》等传教士中文报刊都在牛痘术的推广方面进行了舆论引导,但由于发行量有限,读者群较小,对牛痘术在华推广的助推作用有限。就社会影响而言,晚清报刊中对牛痘术推介的舆论引导以《申报》的影响最大。该报在《劝各乡镇施种牛痘说》中指出:“用人痘浆不如用牛痘浆之为妙……其便易盖有如此者。尝谓泰西医法虽极精微,用以医华人或不奏效,唯收生及种痘之法,百发百中,千万人中无一二人偾事者。”[16]691由于《申报》发行量较大,读者范围广,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该报对牛痘术的推介所收到的舆论引导效果是不言而喻的。除了作为公共传媒的报刊对牛痘术的舆论引导外,具有官方背景的地方政府的公文对牛痘术的推介也极具引导力。同治年间《冈州公牍》所载的《施种洋痘示喻》中明确晓谕民众:“为出示晓谕事,照得人生莫不出痘,天行最属险危。先民乃以种相传,后世得流祸渐减。然总不如洋痘之一法,可以保童稚于万全……不用避风服药,效奏数天。”[17]144-145官员和文人等社会精英所做的赞颂牛痘术的诗文对于民众而言也起到了很好的牛痘施种引导作用。两广总督阮元在其裔孙种痘之后题诗赠与邱熺云:“阿芙蓉毒流中国,力禁犹愁禁未全;若把此丹传各省,稍将儿寿补人年。”该诗中的“阿芙蓉”指的是鸦片,“丹”指的是丹苗,即牛痘苗。阮元把牛痘术在中国推广之功放在了与鸦片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同样的高度,足见其对牛痘术在中国推广的影响评价之高。鉴于其两广总督的政治地位,该诗对牛痘术取信于广大民众的舆论引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很多官员和文人在家人受益于邱熺的牛痘施种后都赠以诗文或匾额。道光三年,邱熺将113名作者的130余篇题咏文字汇集成册取名《引痘题咏》刊行,以便让读者知晓牛痘术“取信之众,此法不巫”。由于官员和文人等社会精英在舆论引导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所题写的诗文是对牛痘术强有力的宣传,为牛痘术赢得了更多的民众信任。社会精英们所采取的文化认同与调适及舆论引导策略,有效消解了国人对牛痘术的怀疑或抗拒心理,有力助推了牛痘术在中国的认同与接受。
三、结论
清代牛痘术的中国推广是中国天花预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为中国的天花预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面对广大民众的心理疑拒,经济困难等传播困境,商人、医生、士绅、官员、传教士等社会力量通过技术推广、资金支持、文化调适与认同和舆论引导等路径对牛痘术传播事业的赞助,有效消解了推广困难,有力助推了牛痘术的中国传播。清代牛痘术在华推广多元互补的赞助路径,对当前各国传染病预防先进技术的有效推广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