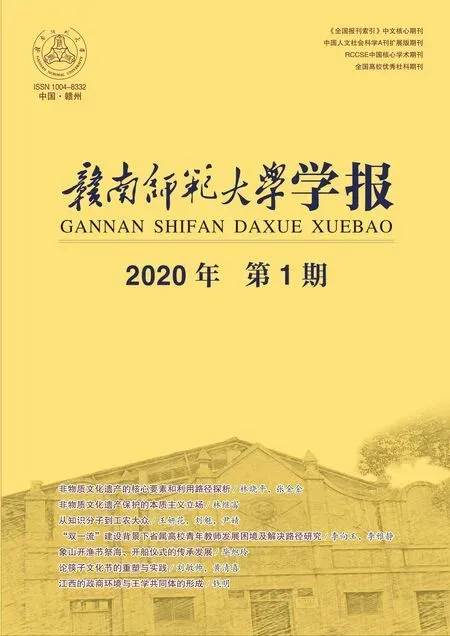江西政商环境与王学共同体的形成
——基于赣州、吉安比较论的视角*
2020-03-15钱明
钱 明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杭州 310030)
赣州对于本人来说,曾有一段相当特殊的情缘,值得回味。1992年4月9日至5月19日,由日本斯人会与浙江省社科院组织的“日中联合王阳明遗迹学术考察团”,对广西、广东、江西三省区的王阳明遗迹进行了长达41天的实地考察和调研。4月28日,考察团翻过九连山脉,从广东和平进入江西龙南,从山顶俯瞰山腰成片的客家土楼或围屋,令人印象十分深刻,更让日本学者惊叹不已,然苦于“未开放地区”之规定,而全体人员被要求不能下车参观,故而留下莫大遗憾(一路考察,因“未开放”而碰到的各种麻烦,一言难尽)。当天下午就赴玉石岩考察,记得十来里的路,竟然开了1个多小时,而且汽车还不能直达山脚,徒步走了近20分钟。洞中的石刻,大部分字迹清晰,其原汁原味性,可以说是41天考察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崇义的茶寮碑,赣州阳明遗迹的完整性和原汁原味性,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29日上午10时左右,我们从龙南到达南康,下午即去了大余。因为29日是王阳明逝世之日,于是考察团便特地选在这一天赶到大余。30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我们抵达大余青龙铺的章江岸边举行祭奠仪式。5月1日抵达崇义,2日考察思顺乡桶冈村的茶寮碑。3日从崇义出发路经南康抵达赣州市。5日上午离开赣州前往吉安遂川县。[1]考察团共在赣州停留了整整一周时间,是整个考察活动中用时最长的,足见赣州地区对中外学者的巨大吸引力。在这一周内,虽然龙南只住了一晚,并且只考察了玉石岩一个点(当时并不知道还有太平桥、栗园围、南武当山、九连山等阳明文化遗址,以及阳明在龙南留下的乡约、传说故事等诸多阳明文化遗迹),但收获满满,尤其是其文献实物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复制性。后来,本人又于2016年4月23日,趁广东河源参会并考察和平县的机会,会后与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林月惠一起,由周建华、张贤忠、董华等先生陪同,时隔20余年后再次来龙南考察玉石岩等阳明遗迹。这次是本人第三次来龙南考察并参会。27年间,三次考察、参会,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每一次都留下了深刻印记。
一、事功性的地缘因素
在传统中国的学术传承系统中,地缘因素和血缘因素最为重要,学缘或师缘因素则往往建立在地缘和血缘之上。这里所谓的“地缘”,是指自然地域和人文地域的分割、沿革及衍变;所谓“血缘”,主要是指同宗、同族、同姓意义上的自然血缘关系;(1)这种自然血缘或纯血缘的社会结构,在明代因朱元璋提倡孝道而特别受到重视。从周代开始的“拟血缘”关系,以及董仲舒所主张的养父母高于生父母的理念(参见李若晖:《儒学与血缘》,《当代儒学》第1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反倒在日本的幕藩体制下得到了贯彻。这也是江户时期的孝道文化区别于明朝孝道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阳明学在传播过程中会常常借助宗族网络系统,在个别地区甚至出现“血缘”重于“地缘”的重要原因。所谓“学缘”,是指各种学说、学派的形成、演变及传承。如果说“学缘”是以“地缘”为物质载体的话,那么“地缘”便是以“学缘”为精神脉络。血缘关系可以把一个地方的人织成大网,大家都是亲戚朋友,靠宗族系统维持社会秩序;地缘关系同样也可以把某一个地方的人织成大网,人们在某一特定的自然空间和文化生态中,靠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维系社会秩序。
基于王阳明及后阳明时代的明代中后期江右地区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缘环境,我们似乎可以将赣州归入以“新界”“流民”为主动脉的阳明学的地缘系统,而相对应地把吉安等地归入以“族群”“人缘”为主动脉的阳明学的血缘系统。
“赣州、吉安地理相连,水路不过一日之程”。[2]342王阳明在赣州以其卓著的军功、事功而彪炳史册,赣州的赣县、大余、南康、上犹、龙南、于都、瑞金、崇义、信丰、安远等地,不是他南来北往的必经地,就是他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主战场,更是他创建政权、治理乡村、教化民众的实践场,或者说是他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及教育文化和道德教化活动的践行地,故而赣州在阳明学的地缘系统中更多的属于“事功性地缘”(2)调整区划,因地建县;人口配置,民族怀柔;鼓励开发,促进商贸;社学教化,乡村自治;城堡防御,军民融合……;这些都可以说是“事功性地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吉安等地的师承性和家承性地缘有不小的区别。
以这种“事功性地缘”为背景,王阳明治理南赣时及后阳明时期的赣州,在商业活动上没有形成如同吉安等地那样强大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在学术活动上也未形成像吉安等地那样强大的群体合力和学脉纽带,因而也就很少出现像吉安等地那样的“聚族问学”“同族同门”的传承模式,而更多地表现为以军事组织、乡村建构、山民教化为导向的传承模式。加之当时赣州出生的士大夫相对较少,在朝为官的赣地阳明学者更是无法与吉安等地比肩,在与中央政府乃至地方官府的维系上要比其他发达地区弱势许多,而其因又盖在于科举落后、人才不旺,以致于在上缺乏政治保护伞,在下缺乏乡野知识人。故而在后阳明时期,赣州王门显得并不那么活跃和持久,较之阳明时代,无论影响力还是辐射面都大有递减之态势。吉安的情况正好相反。因其师承性、家承性的地缘文化特征,在阳明尤其后阳明时代成为全国传播和发展阳明学的中心。
二、王门主导地位的转移
元明更迭之际,战乱波及南赣地区,社会动荡之下,导致赣州人口锐减。到了明中叶,南赣巡抚所辖之地区又因匪患猖獗,社会经济严重萧条,人口进一步减少,从而使得占地接近明代江西全省之面积的南赣地区,人口密度极低,与吉安地区相比,完全不在同一数量级上。加之族群分散、成分复杂,文化传统的根基较为薄弱,致使王阳明到任后,首先采取的是“社学”即山民教化,加“乡约”即乡村治理的方式,以图通过渗透进自己心学理念的思想教化手段来暂时弥补行政管辖之短板,让山民们意识到社会失衡、生活无序的危害性及自虐性,从而为逐步建立良性的社会生活秩序铺平道路。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指出:由于规模因素,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中央政府的官僚体系在信息的传递、税赋的征收、政令的统一等诸方面都遭遇了艰巨的挑战,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儒家道德话语和意识形态的辅助,来形成较为抽象的文化与道德层面的自我认同。[3]而依笔者之见,这个所谓的“自我认同”,似主要表现在“自我约束”也就是软性的“自律自觉”上,而非刚性的法律他律上。于是,便出现了犹如出生赣州于都的蔡仁厚先生所说的“自汉及唐,赣南地区之人文,未见大盛。及理学兴起,方广受惠泽,人文蔚起……至今史迹犹在,流风犹存”(3)引自周建华:《蔡仁厚先生唁函》,2019年6月6日于赣州阳明书院。之现象。只不过,所谓“广受惠泽,人文蔚起”,当主要显于明中叶以后,而非“理学兴起”之宋代。
然而,与赣州相邻的吉安地区,由于有赣江及其支流所组成的水路网络,包括相当完备的宗族体系,社会网络健全,经济文化发达,从而为形成“互联互通”的学术共同体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其结果便导致了赣、吉两地的王学影响力,在王阳明时期与后王阳明时期表现出较大的反差,即赣州王门出现递减乃至衰微,而吉安王门出现递增并日趋繁荣,两地的主导权随之形成互换,即王阳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赣州被后王阳明时期的吉安所取代。
在后阳明时代,曾有人以越州(绍兴)、洪州(南昌)、广州来定位王学传播的核心区域,如马一龙的《竹居薛先生文集序》即称:“当世道学之宗,有阳明王公者。其后门人,吾所交游,王龙溪畿、钱绪山德洪传于越州,欧阳南野德、邹东廓守益传于洪州,二薛中离侃、竹居侨传于广州。天下一时昌明斯道,贤士大夫以致良知为学,而得所见性真道体。”[4]而所谓越州、洪州、广州,实代指浙中、江右、岭南也。然而,较之于浙中和岭南这两处王学传播的主要区域,以吉安为代表的江右区域则几乎可以说是处处皆留下了王阳明及其弟子们的足迹,县县都有阳明学分布流变之学脉,其强势表现是岭南乃至浙江两地难以企及的。
浙中王门巨匠张元忭曾对江右王门作过如下评价:“盖江右自昔称盛矣,至如吉州二罗先生(指罗琛、罗洪先)、进贤舒先生者(指舒芬),辟之祥麟威凤,世不常有,而并出于百年之内,可不谓尤盛哉!”[5]这一评价与黄宗羲等一致。尽管张元忭所列举的罗琛、罗洪先、舒芬三人,实际上并非江右王门中最优秀的,但是他称吉州(即吉安)二罗是江右“尤盛”者,则部分揭示了吉安地区王学人才辈出,且几乎都是王门中的领军人物,势头可覆盖整个王门的基本史实。
笔者有一不太成熟的判断,即,若以绍兴为代表的浙中王门曾出现过从阳明学演变为“阳明禅”的倾向和趋势的话,那么以吉安为代表江右王门则可以说曾出现过从阳明学升格为“阳明教”的倾向和现象。(4)参见李伏明:《阳明学、阳明教和阳明禅》,《江西省王阳明研究会——周年纪念会论文专辑》,2017年10月。“教”即教化之意,有宗族化、大众化之特征;“禅”即枯禅之意,有宗教化、玄虚化之特征。前者是从宗族化、平民化而走向大众化,后者却是从宗教化、玄虚化而走向精英化。浙中王门后学与江右王门后学,在后阳明时期的确曾出现过这两种向度,其中所透露出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态信息,值得深究。
三、赣吉两地的政商环境
江右为什么会成为王门中最为繁盛并源远流长之地的呢?王阳明长期居住或短期停留过的地方,要数江西最多,他的足迹几乎遍及江西所有地区,所以江西自然可排在阳明学传播、发展之首位,几乎可以以县级乃至乡级为单位来细梳其支脉,其中尤以阳明居住时间最长(以江西为界)、建功立业最著的赣州地区为代表(赣州几乎每个县都留下过阳明足迹)。江右位居王门之首,主要还在于“后之为阳明之学者,江右以吉水、安福、盱于江(5)即盱江,古称“汝水”,为江西省第二大河流,发源于广昌县血木岭,流往南丰、南城,注入抚河。此处疑指王学大家罗汝芳的故乡南城。为盛”[6]51这一判词,也就是说,主要看的是阳明后学的活跃程度和传承时间。基于此,吉安地区理所当然地后来居上,超越赣州,而成为江右乃至全国的发声地。
阳明后学王士性(6)王士性(1547-1598),字恒叔,号太初,浙江临海城关人,万历元年(1573)举人,五年(1577)进士。其叔父王宗沐尝师承江右王门学者欧阳德,系阳明再传弟子。王士性深受王宗沐影响,既是一位人文地理学家,也是一位阳明学者,曾至杭州天真书院游学,并向王畿等资深阳明学者请益(参见张宏敏:《阳明学与台州》,载钱明主编:《中国地域社会文化中的王阳明》,孔学堂书局,2020年预出)。的两句话对于我们了解江右何以会成为王学最繁盛地区的原因颇具启示意义。第一句是:“阳明先生发良知之说,左朱右陆,而先生勋名盛在江右,古今儒者有体有用无能过之,故江右又翕然一以良知为宗,弁髦诸前辈讲解,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6]51所谓“左朱右陆”有朱陆合流、兼备之意;所谓“弁髦”意指鄙视、蔑视;而所谓“诸前辈讲解”则意指不以汉儒、宋儒之解经为的。第二句是:“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俭而安简朴,盖为齿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6]52“务啬”即务农、耕种收获之意。关键是“愁苦之思”,心中有愁苦,故宗教情结较浓厚,而阳明学的乐学精神、活泼之性格正好可以化解愁苦之心结。不难看出,王士性的第一句话说的是学风、文风,后一句话说的是民俗、世风,两者相辅相成,形成合力。明代中后期,江右地区宗教氛围较为浓厚,宗法势力强大,自然经济发达,虽有江右商人商帮,但以经营南北杂货为主,势弱力微,社会风气大异于江南地区。(7)明末浙江遗民张斐的《秦人谢殷男于吴市买得宝刀,作宝刀歌赠之》诗云:“吴中有宝刀,秦中有壮士。一朝相配合,各自增意气。”(张斐著,刘玉才、稻畑耕一郎编纂:《莽苍园稿》,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45页)暗喻吴中(实代表江南地区)商贾云集,各类商品齐备,且重点是海外贸易(宝刀是当时的主要进口品,江南地区有足够的商品出口海外,而从海外进口的则主要是香料、宝刀等),而江右地区的商贸环境则可谓与江南有天壤之别。而这种地域性的人文环境,恰好为大众化倾向极强烈的王学共同体的形成和壮大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对外通商,汉唐时代以古丝绸之路陆路为主,国际市场多在西域;宋明以后,逐步发展了海路,明朝沿海地区对外联系日益广泛。从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番货上岸后,大部分需通过古驿道翻过五岭进入内地,地处南赣区域的南安府大庾岭梅关古道是当时最大的“咽喉”贸易通道,邻近梅关的横水、桶冈等地的贼寇作乱数十年,经常抢劫商队,为朝廷心头之患。当时同属南赣区域的漳州象湖山的詹师富部,也直接影响到海上贸易的畅通和发展。朝廷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为维系一方平安,选派既懂军事,又有贵州龙场偏远多民族杂居地区工作经历,曾经在庐陵做过县令,对南赣地区有所了解的王阳明前去平乱,体现了明王朝对南赣地区之特殊地位的高度重视。主张安抚教化为重的王阳明,在劝降诸贼时用的虽然是历代兵家常用的心理战法,但又根据当时南赣地区的特殊环境而使出了鼓励商贾经贸之手段,这在以往的兵家中是不常见的。比如他曾在《告谕浰头巢贼》(嘉靖《崇义县志》名《军斗榜文》)中诱降道:
闻尔等辛苦为贼,所得苦亦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岂如今日,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潜形遁迹,忧苦终身;卒之身灭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尔等好自思量,若能听吾言改行从善,吾即视尔为良民,抚尔如赤子,更不追咎尔等既往之罪。如叶芳、梅南春、王受、谢钺辈,吾今只与良民一概看待,尔等岂不闻知?[2]595
他还把《告谕浰头巢贼》张贴在赣州城的各个交通要道上,试图通过发展经济、鼓励商贸等致富手段来实现富民、安民、保民最后亲民的政治蓝图和理想设计。因为阳明心里很清楚,保境安民的重要保障是要让老百姓生活富足,而生活富足的最好手段,在南赣地位便是以农为本,鼓励商贸。
然而,与当时的吉安商人以私人性质为主的小本经营,[7]并带有明显的经济利益诉求有所不同的是,(8)对此,我们可假借明人李乐《见闻杂录》中的一则轶事来加以说明:“陈广海山先生,时为江右督学,使此老真率,肯训诲后学,促膝教乐,曰:‘江右人钱财难得,汝与他省得银子三分时,彼百姓夫妇睡在枕上也说汝好。’余时念其言不忍悖也。”(《见闻杂录》卷六,收入《笔记小说大观》(44编),第8册,台北:新兴书局,1987年,第569页)赣州商人可以说是从事以官商为主、官方主导,并带有明确的政治、军事目的的商业活动。这一点,甚至从布满南赣地区的客家土楼、围屋中也能感受得到。土楼、围屋显然不适合私人性质的自由贸易,而适合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以相对而言,吉安商业能真正体现在富民安民、社会繁荣上,而赣州商业则更多的是发挥扩军费、稳社会之作用。因此,王阳明所倡导和鼓励的“运之于商贾”的致富门路,在赣州实施的效果并不显著,也并未带来整个地区的商贸繁荣,而这大概也是赣州王门不振于后阳明时期的重要原因。
黄宗羲说“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8]377首先固然是因为王阳明在江右的事功、学术卓著于别的地区,然而江右地区固有的历史文化环境亦不可忽视。只不过黄宗羲此处所说的“江右”,我以为主要是指吉安地区。明代吉安地区虽离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较远,但并未被边缘化,其在思想文化上,既有被朝廷当作首善之区、被树立为典范的一面,又有多元化、自由化的一面,因而使得该地区的绝大多数知识精英虽然都把读书做官作为自己的唯一选择,但并未放弃自我张力和个性追求。于是,在官学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地方士绅遂大力兴办书院,并且在服务于科举文化的同时,还致力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设和文化教育的普及。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直以来“谨婚姻而重氏族”[9]57“以举进士为业”[9]57的吉安地区,讲学风气开始大盛,以至于处处办讲会,族族倡教化,家家重教育,从而为阳明学在该地区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创造了极佳条件。
想当年,王阳明及其浙中高足王畿等人为什么要如此重视吴中、浙西地区以及宁国、滁州地区的王学传播?就是因为当时的政治中心是金陵,而这些地区都环绕着金陵。当时一些非在朝的学术精英们,要想对金陵形成舆论压力和学术影响力,在不大可能直接讲学金陵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布局于其周边地区的学术圈和舆论圈,以影响甚至控制在朝士人。他们的目的,除了要对思想舆论乃至政治环境产生在野压力外,更主要的还是想形成对于科举考试的控制权或影响力。正如南宋时期的学术精英集中于金华地区,而非政治中心的临安。政治中心非学术中心的现象,在历朝历代都有,尤其是文化南移后,南方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都会逐渐形成这样的学术文化圈。明代的江右地区,虽非政治中心,但却发挥了学术中心的作用,其因亦盖在于此。
以上所述之人文生态条件,在江右其他地域可以说也表现得比较充分,但吉安地区尤显突出。相比吉安,赣州地区在这方面要显得薄弱很多。王阳明在赣州的3年多时间,是其建功立业最为关键的阶段,也是他居住时间相对较长的时期。(9)王阳明居住两年以上的地方,若按时间长短排列,大致上为余姚、绍兴、北京、杭州、赣州、南昌、贵阳和南京;其中余姚、绍兴、赣州是单次居住两年以上者,北京、杭州、南昌是合计居住两年以上者,贵阳(包括路经的黔中之地)则是居住近两年者。而所谓“住南京”,还要包括滁州等地,因为阳明就任南京太仆寺少卿,衙署就设在与南京一江之隔的滁州。但是,由于当时赣州地区的开发要比江西其他地区晚许多,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教育水平都要相对滞后,而且作为客家人的主要聚集区,从北方迁徙来的宗族文化传统的重建尚未完成,族群断流(相对于中原祖居地)、人脉稀疏、教育不旺、开化迟滞的人文环境,以及交通蔽塞、省际交界、民族杂居的自然条件,都给赣州阳明学的传承和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四、王学共同体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地域分割、学派分化并不能否定在一定条件下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及彼此间的互动、交流与融合。比如吉安地区王学共同体的形成,实际上主要有赖于王阳明在赣州时期的授徒讲学,其领袖人物大都曾赴赣州问学于阳明。吉安地区虽然不是王阳明居住讲学时间较长的地方,前后加起来,他只在吉安工作、生活了大概一年不到的时间,但却是阳明学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地区。王阳明于正德五年(1510)三月至同年十月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有近大半年时间;正德十四年(1519)他又在“吉安地方调兵讨贼”,一举平定了宸濠叛乱;后但凡经过吉安他都要设坛开讲,如正德十五年(1520)六月十八日,阳明“至吉安,游青原山,和黄山谷诗,遂书碑。行至泰和,少宰罗钦顺以书问学”,[2]1280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答罗整庵少宰书》。阳明最后一次在吉安讲学是在嘉靖六年(1527)十月下旬赴两广途经吉安时。据《阳明年谱》记载:“(阳明)至吉安……诸生彭籫、王钊、刘阳、欧阳瑜(10)这几位都是当时吉安地区的大族代表。等偕旧游三百余人迎入螺川驿(11)螺川即螺山,形状似螺,在江西吉安县北十里,南临赣江。中,先生立谈不倦,曰:‘尧、舜生知安行的圣人,犹兢兢业业,用困勉的工夫。吾侪以困勉的资质,而悠悠荡荡,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岂不误己误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虚,变通不居。若假以文过饰非,为害大矣。’临别嘱曰:‘工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2]1320这些观点可以说是王阳明继绍兴“天泉证道”、桐庐“岩滩问答”、南昌“南浦请益”后最后一次阐述自己的核心思想,也是他对“天泉证道”的最后总结。(12)所谓“岩滩问答”和“南浦请益”,即王畿《绪山钱君行状》中记载的其弟子一路追随阳明前往两广途中,阳明与弟子间的讲学问答:“夫子赴两广,予与君(指钱德洪)送至严滩。夫子复申前说,二人正好互相为用,弗失吾宗。因举‘有心是实相,无心是幻相;有心是幻相,无心是实相’为问,君拟议未及答,予曰:‘前所举是即本体证功夫,后所举是用功夫合本体。有无之间,不可以致诘。’夫子筦尔笑曰:‘可哉!此是究极之说,汝辈既已见得,正好更相切劘,默默保任,弗轻漏泄也。’二人唯唯而别。过江右,东廓、南野、狮泉、洛村、善山、药湖诸同志二三百人候于南浦请教,夫子云:‘军旅匆匆,从何处说起?我此意畜之已久,不欲轻言,以待诸君自悟。今被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吾虽出山,德洪、汝中与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诸君只裹粮往浙,相与聚处,当自有得。待予归,未晚也。’”(钱明编校:《徐爱·钱德洪·董澐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08页)
除此之外,吉安地区王学共同体的建构与传承,还与王阳明的吉安弟子后学尤其是他们的家族网络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黄宗羲《明儒学案》62卷,其中江右占9卷;江右王门33人中,安福籍学人13人,占39.4%。黄氏论江右王门,说“姚江(阳明)之学,唯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8]377其所提代表性学者6人中3人为安福人,即东廓、两峰、塘南。而阳明学在此三人家族内一直传承了三四代人,形成了庞大的家族式王学群。据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附录资料统计,明代全国阳明学者人数为244人,安福籍26人,占10.7%。又据吴宣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附录资料统计,江右王门人数260人,安福籍45人,占17.3%,是故同门中即有“阳明夫子生平德业著于江右最盛,讲学之风亦莫盛于江右,而尤盛于吉之安成(即安福)”[10]之论。若再深加考证,则安福阳明学者当时至少有五六十人以上,如果把普通崇信者、跟随者也算上,则难以计其数矣。若以县为考察单位,那么在一个县出现人数如此多、成就如此高的阳明学族群,实属罕见。所以说,安福不仅是江右王学重镇,也是全国阳明学的中心之一。(13)耿宁先生《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商务印书馆,2014年)一书称吉安府及其安福县为全国三大阳明学中心之一。
概而言之,家族宗法组织不旺,地方乡绅社会松散,在官场尤其朝廷的势力较弱,乃是赣州地区相比吉安地区在后阳明时代处于明显下风的三大原因,而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对于阳明学的传承与流布所产生的影响乃是不可估量的,因而导致赣州阳明学不盛或持续性不强亦是很自然的。
还需要强调的是,王阳明讲学教化及其门人后学传播阳明学的重点地区,大都集中在几个水系的沿岸及附近流域,并且又因这些水系所形成的“网络”具有地域、跨地域的特性,而使得这些水系的沿线文化表现出具有“共同体”特征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沟通性。这一“网络”不仅跨越了江南、江北的自然区域,而且覆盖了燕赵、齐鲁、中原、江南、华南、西南等不同文化圈,同时还在宁波等出海口与东海相交汇,从而把中国的阳明学“输送”到了东北亚。[11]以吉安为中心的赣江流域(赣江在吉安境内全长264公里),在某种程度上也具备了这样的“学术共同体”特征。
从这一意义上说,仅仅将水路、陆路系统简单地放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将其看作是某种运送人口和货物的方式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我们同时也要有将水路、陆路系统放在社会学、文化学乃至思想史上的意义加以解读,将其网络地带看作是传播信息的便捷通道和沟通平台,是会对该地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因产生重大影响的载体和媒介。以吉安为中心的江右王学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就与遍及该地域的赣江主支流系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五、结语
近年来,随着国内儒学热、国学热尤其是阳明热的兴盛,加上国际史学界出现的结合地方社会史与学术史的研究取径,使地域阳明学再度受到重视,发出强音,各种地方性活动日趋活跃。作为江右王门最早兴盛、活跃地的赣州阳明学亦不例外,其兴旺之势正日益凸显。在这一过程中,上下联动、政经结合、凝聚人气、延续学脉实为诸地域阳明学的必然诉求,然挖掘资源、爬梳文献、疏通史脉作为基础性的工程亦不可忽略,唯如此,方能彰显地域特色,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需要。正是本着这样的共识和心愿,赣州市及下属诸县在“赣南师范大学王阳明研究中心”的协助下,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与阳明学有关的文创文旅活动。此次在龙南县举办的“王阳明在龙南暨阳明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尽管与全国其他地区包括赣州其他县区相比稍显迟至,但盲羊补牢,犹时未晚,因为龙南毕竟是赣州乃至全国保存阳明遗迹最丰富、阳明文化沉积最深厚的地方之一。在这样的地方开展阳明文化资源的挖掘和阳明思想学说的普及工作,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众所周知,王阳明在赣州大余的章江船上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或称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重点在此心光明)!”仔细推敲,这则遗言其实与阳明早年在贵州修文时所说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重点在吾性自足)”即著名的“龙场悟道”存在着一定的前后关联性。道与性、心与性、自足与何言、圣与吾、本体灵明与此心光明这一系列概念,关联性都非常强。“吾性”即“此心”,悟得吾性自得的圆满性,即可达到“光明”的高远之心境。因此可以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进一步熟化就是“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吾性自足”更为洒脱的表述就是“此心光明”,这两句前后相距20多年的名言,实质上并无差异。借用王畿的“解悟、证悟、彻悟”之概念,则可以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是“证悟”,而“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是“彻悟”。因此我以为,“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与其说是王阳明的临终遗言,不如说是他的“章江彻悟”。相对于绍兴会稽山阳明洞的“修悟”(利用道教)和修文龙冈山阳明洞的“证悟”(运用《周易》),内心“乐山”的“仁者”阳明先生,在走到生命尽头时,在章江上与“乐水”的“智者”(泛指其部分江右弟子)进行了对话,最终实现了与早年的绍兴“会稽修悟”、中年的贵阳“龙场悟道”分量不相上下的晚年的赣州“章江彻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