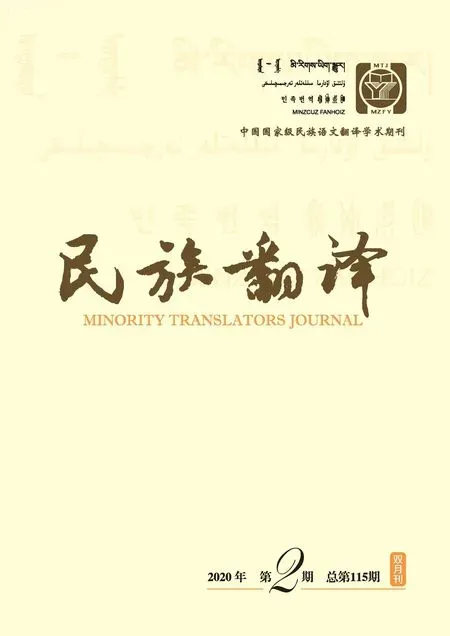浅析羊本加的“仓央嘉措诗歌”新译本
——评《心儿随之而去:仓央嘉措诗歌新译》*
2020-02-28荣立宇
⊙ 荣立宇 崔 凯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三河市第一中学,河北 三河 065200)
一、引言
仓央嘉措诗意三百年,流传至汉地,产生了诸多的汉语译本。自1930年于道泉《第六代达赖喇嘛仓洋嘉错情歌》首开全译先河,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译本频出,仓央嘉措诗歌的汉语译本已有24个。2013年,由羊本加①翻译、编辑的新译本《心儿随之而去:仓央嘉措诗歌新译》(以下简称为《新译》)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发行。按照出版时间先后顺序来说,这是仓央嘉措诗歌第22个汉语译本。该译本的标题出自仓央嘉措诗歌第58首诗意,“箭矢射中靶子/箭镞钻入土中/遇见少恋情人/心儿随之而去”。[1]77其中收录有诗歌共132首,藏汉对照排版,译诗统一按照四句六言的格式译出。以译者的族属而论,该译本是仓央嘉措诗歌汉译历史上第三个出自藏族译者之手的译本②;以译诗的六言体制而论,该译本可算是仓央嘉措诗歌三个同类译本中的第二个③。总体而言,这个译本是21世纪以来,仓央嘉措诗歌汉译呈现出趋向创译而远离忠实的背景下兼顾了翻译求真与诗歌求美的译本,特色鲜明、弥足珍贵。鉴于此,笔者撰写此文,对该译本略做介绍,为译者宣传、为读者导读。
二、关于译本
《新译》中可圈可点之处颇多,现选取比较重要的一些,列举于此,以便探讨。
(一)关于底本
仓央嘉措诗歌目前流通较广,其中影响较大的为藏文底本包括于道泉的66首整理本,王沂暖的74首整理本以及庄晶的124首整理本。[2]另外,索伦森(Sorenson)在其著作《神性的世俗化:论六世达赖喇嘛诗歌的本质与形式》(DivinitySecularized: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formofthesongsascribedtotheSixthDalaiLama)的附录部分还提供了一份包括459首诗歌手稿的拉丁字母转写。[3]
《新译》的底本正如标题所示,是译者自己新编的一个本子。其中收录诗歌共132首。就底本来看,《新译》底本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124首,这些诗歌基本是庄晶整理本的规模和顺序。庄晶整理本前面的65首又是基于于道泉的整理本,不同之处在于去掉了于道泉译本中的第45首——这是由于该诗存在宗教题材和三行诗句两处问题,再者又对于道泉译本的第50A,50B,50C三个小节中的后两个进行了诗句的重新组合,组合之后的版本与Sorenson整理本基本相同;第二部分为第125-132首,这些诗歌底本是王沂暖整理的74首版本多出于道泉整理本66首的部分。综上,可以说,《新译》的底本直接基于庄晶与王沂暖的藏文整理本,间接参考了于道泉的藏文整理本。
(二)关于结构
就《新译》结构而言,“序”“关于玛吉阿玛”和“译后记”构成该书的副文本部分,诗歌译作是该书的主体。“序”属于自序,是由作者在几个时间点上对仓央嘉措诗歌的感悟连缀而成。“关于玛吉阿玛”可以看作是译者对这一名字的考证,颇具学术性。译者先是大胆地假设,认为“玛吉阿玛”或与古印度的“未生怨王”有关,有可能指向第斯·桑结嘉措,进而小心地求证。一番检索之后,尽管并无定论,但这种提法与做法颇能启发人们做进一步的思考。“译后记”由镜子、边界、中观三个小节构成。译者由对仓央嘉措诗歌的个人解读说起,指出理解这些作品存在多种的可能性,“仓央嘉措的诗歌,就像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色狼看见淫欲,政客看见博弈,情人看见忠贞,哲人看见真理,上师看见佛性。”[1]167继而通过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宗教与宗教、星球与星球之间存在的边界问题,谈及语言之间的边界问题——引出翻译中不可译性的问题,最后指出中观之路。所谓中观,简单地说,就是“远离生灭、常断、有无、现空等极端的侧边,持这种观点,即是中观道路。”[1]169通过提出对仓央嘉措评价者的四分法,即“懂藏文而不懂汉文者,懂汉文而不懂藏文者,两种文字都懂者,两种文字都不懂者。”[1]170,特别指出“按着这个方法去看仓央嘉措,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可以认识,可以理解仓央嘉措大师那捉摸不定的传说。”[1]170如此,仓央嘉措诗歌解读的多样性便获得了佛理上的依据。
(三)关于译诗
诗歌译作是《新译》的主体部分,或者叫正文本部分。该书正文的设计包括三个部分,藏文、汉语译文以及赏诗花絮。仅就译诗的体制来说,四行六言的建制构成此种译法的第二次尝试。就节奏来说,基本是每行三次停顿。就押韵来说,虽有韵脚,但却是十分稀疏。如仓央嘉措诗歌第24首,“若随美女心愿/此生法缘将尽/若去漫游山庙/又违姑娘心愿”。[1]35四行六言三顿的体制,无韵脚,这些特点在这首诗中一目了然。
汉语六言译诗其利在于与原诗形式特征的相似④,然而,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即译者在闪转腾挪的过程中受到译诗格局的限制,很多表示信息的实词与表示关系的虚词在译诗中不得不去掉。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些场合,一些用于凑足音节的小词又会被凭空添加进来。
如仓央嘉措诗歌第33首,《新译》译为“爱人被人摄取/应了卦算结果/那位善良姑娘/梦中反复出现”[1]48。三四两句之间表示明显的位置关系的“在”字,由于译诗格局的限制而不得不被省去。再如第56首,《新译》译为“白色丹顶鹤啊/请借羽力一用/不去很远很远/转转理塘便回”[1]75这里“很远很远”一词很明显是为了凑足音节在字面上所做的重复与添加。
事实上,汉语六言译诗格局的限制是毛继祖、羊本加与无患子翻译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三位译者在很多地方选词用字的差异彰显了不同译者在同样的锁链束缚下舞出的不同舞姿。如仓央嘉措诗歌第33首⑤,无患子的译诗为“姑娘不是娘养/怕是桃树所生/为何她的恋情/快过桃花凋零”[4]76,同一首诗毛继祖则译为“姑娘不是养的/怕是桃树长的/喜新厌旧无情/比花开谢还急”[2]397,羊本加的译诗为“姑娘非母所生,难道长在桃枝?喜新厌旧劲头,堪比桃花一现。”[1]51我们可以看到前两个版本译诗中的押韵倾向,如第一个版本译诗中的“生”“情”“零”,第二个版本中的“养”“长”,同时也可以看出在译诗格局限制下不同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如第一个版本译诗中的“快过桃花凋零”是出于押韵考虑对于“比桃花凋零还快”所做的句式改造,而第二、三版本译诗中成语“喜新厌旧”的引进则是为了译诗在体式限制下的内容丰满。
(四)赏诗花絮
赏诗花絮部分是《新译》正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设计上来说十分新颖。译者在每一首诗的赏诗花絮部分提供了汉、藏、外多种典籍及民间传说中关于仓央嘉措及其诗歌的描述、分析与评价。这部分涉及的典籍覆盖面十分广泛,其中汉文典籍包括张怡荪等编写的《汉藏大辞典》,张其勤编的《西藏宗教源流考》,王辅仁编的《西藏佛教史略》等;藏文典籍包括第斯·桑结嘉措著《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喇那巴·益西桑布著《论仓央嘉措退戒的原因》,雷隆杰仲·洛桑陈丽著《持金刚集最殊胜能力者传衍生史·驱逐黑暗之太阳》木刻本等;外文典籍包括意大利杜齐著《西藏中世纪史》,法国石泰安著《西藏的文明》、美国约翰·麦格雷格著《西藏探险》等,共计100多种,可谓是小型的仓央嘉措及其诗歌摘句汇编,既可以直接用作参考资料,也可以间接用作文献索引,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译本不足
《新译》的不足主要包括印刷、体例与解读等。印刷涉及“关于玛吉阿玛”部分,第一段中的“思忖”被印作了“思付”;体例问题主要是一些学者译名的前后不统一,同一个人“第斯·桑结嘉措”在第9页印作“第悉”,第22、27、49页印作“第斯”,意大利藏学家“杜齐”,第18、35、41、42、43页写作“杜齐”,第72页写作“图齐”,而且多数外国学者前面标明了国籍,如第40页[意]依波利多·德西迪利、72页[意]图齐、77页[法]石泰安、88页[美]约翰·麦格雷格,少数则未做任何标明,如65页H.霍夫曼,122页陆莲蒂等。
理解问题比较明显的有两处,其一是第9首的首句,“鸳鸯恋上沼泽”[1]16,此处“鸳鸯”一词似乎值得商榷。此处于道泉译作“野鹅”[5]60;王沂暖译作“天鹅”[2]98;庄晶译作“黄鸭”[2]116;Sorenson译作“野鹅(the wild goose)”。[3]77
可见,几个比较权威的藏学家都将这里的动物意象译作“鹅或鸭”。据Sorenson的研究,“鹅与湖这组意象常用来描述情侣,备受人们青睐。(In this poem another much-favoured pair of figures is introduced which depicts a loving couple:the goose and the lake)(笔者译)”[3]77《新译》在这里的译法“鸳鸯”是典型的汉语文学意象,一来与藏地风物的原貌不符,二来又因为归化的处理丧失了源诗的异域风情,可谓得不偿失。
其二是第56首的首句,“白色丹顶鹤啊”[1]75,此处“丹顶鹤”似乎是译者理解的失误。在于道泉藏、汉、英三语对照译本中,此处鸟儿对字汉译为“鹤”,直译处为“野鹤”[5]156;王沂暖译本、庄晶译本中也均译作“仙鹤”。[2]109,136
据Sorenson考证,“此处提到的鸟很可能是中亚白鹤,也称为西伯利亚白鹤。鹤的这个品种除了黑色翎毛之外,通体洁白。它们在西伯利亚繁殖,秋冬时节成群地飞往印度。春回大地,又由印度折返。这种鹤与日本仙鹤——亦称为丹顶鹤,在日本被视为爱情的象征,是很多艺术家钟爱的体裁——十分相近。(The bird in question is probably the White Crane of Central Asia,also known as the(Great)White Siberian Crane—It is purely white throughout except for the wing-quills which are black.—It breeds in Siberia and visits India in autumn and winter in small flocks.In spring it leaves India again.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Japanese Crane,the Red-crowned Crane,equally a love symbol in Japan,where it is a favorite motive for artists.)(笔者译)”[3]251,事实上,Sorensen这种生物学上的考证十分具有说服力。由此可见,《新译》此处的选词“丹顶鹤”似乎确实不如“白鹤”更加妥当。
四、结语
在国际翻译研究领域存在着“译出”与“译入”的学理讨论,也即“顺译”与“逆译”的问题。“从学术层面讲,理论上来说,应该由外国人翻译,就是所谓的顺译”[6]2,“国外一般不太认可逆译,认为一个人的外语水平无论如何也没有他的本族语掌握运用得好,所以提倡顺译。”[6]2如马悦然、顾彬等一些著名人士就认为“译者最好把著作从外语译入译者的母语”。[7]1就中国国内汉语与民族语言之间、各种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来看,似乎也存在着“译出”与“译入”的问题。羊本加的藏族族属、精通汉藏双语的客观事实令《新译》成为译者得心应手的译入之作。译本的副文本部分体现出一定的学术研究色彩,正文本中四句六言的译诗体制虽然颇令译者掣肘,但是“带着锁链舞蹈”⑥始终是译者在自己诗学理念指导下的不懈追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文中的赏诗花絮部分,这里涉及的藏、汉、外文史料与传说,一方面可以做学术研究与赏析的参考,另一方面可以充当进一步研究的书目索引,具有双重使用价值。总之,这个译本颇具特色,可圈可点,尽管也存在一些小瑕疵,但是瑕不掩瑜,值得学界关注。
注 释:
①羊本加(1976—),藏族,硕士,懂得梵文,谙熟藏、汉双语。
②在仓央嘉措诗歌约略百年的汉译历史中,20世纪30年代的刘希武、50年代的苏朗甲措为藏族。参见中国藏学出版社编,《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意三百年》,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版。
③在仓央嘉措诗歌诸多汉语译本中,通篇按照六言体制进行的译本包括20世纪70年代毛继祖的译诗、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出现的羊本加的译诗、无患子的译诗。参见中国藏学出版社编,《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意三百年》,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版。此外,龙冬的齐言体译诗中有部分六言体制,如第77首、80首,第93首等,但并未将之贯彻通篇。参见龙冬译,《仓央嘉措圣歌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④仓央嘉措诗歌的体式为藏族文学中的“谐体”,其主要的形式特征为:每首以四行为主,偶见六行,每行六个音节,形成三个停顿,押韵偶有,但不常见。
⑤此为于道泉译本的排序,也是多数汉语译本的排序,羊本加译本中此首位列第35,毛继祖译本则无所谓顺序。
⑥闻一多论及“诗的格律”时曾用“带着脚镣跳舞”来形容诗人按照格律作诗,见闻一多,《闻一多说唐诗》,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年,215页。这里稍做改动,用来指译者以格律体译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