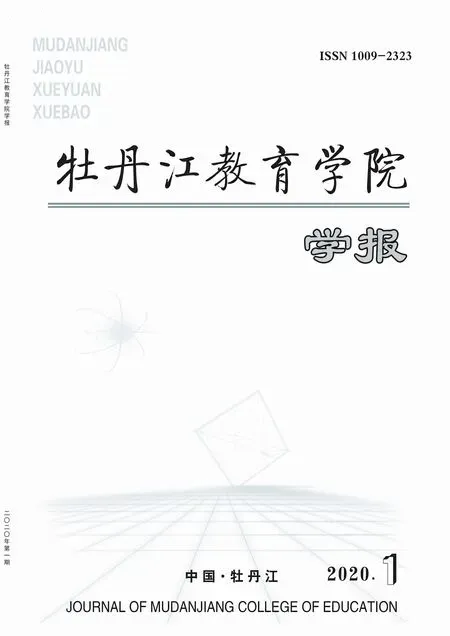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具有作品属性的分析
2020-02-28孙毅
孙 毅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一、引言
科技领域的日新月异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的迅速发展,各式各样的人工智能已悄然影响大众生活[1]。例如,微软公司的“微软小冰”,在分析了519位诗人的作品后可以独立写诗并创作诗集;腾讯公司的Dream Writer,更能实现新闻稿的自动写作[1]。人工智能对创作活动的参与,也带来其生成物是否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问题。目前学界对此并无定论,其争议点主要围绕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构成作品,如果构成作品,其权利主体又是谁两方面展开。其中第一个问题的答复又构成回答第二个问题的前提。本文主要从这两点出发,探讨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作品属性的问题。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属性证成
(一)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
在美国Feist案之前,关于作品的认定标准是主要是“额头冒汗”原则。如果作者在创作作品过程中付出了劳动、技能或判断,就可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但著作权法旨在促进文艺创作领域的繁荣,而不是单纯的机械劳动。显然仅仅单纯的付出劳动、技能或判断,还达不到著作权所应保护的目的。在此案之后,对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便要求至少具有最低限度的创造力。如果仅仅只是按照既定规则机械地完成一种工作,由此形成的成果不认为是作品,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依《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1],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实质是某种可以有形复制的智力成果,而该智力成果又以“独创性”为核心要素。因此一件作品若想获得著作权法保护,关键是要满足“独创性”要件[2]。独创性,包含“独”和“创”两部分[3]。“独”,应理解为“独立创作,源于本人”[4],作品是在不受他人支配下独立完成的结果。而“创”则要满足著作权法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智力创作高度。再结合《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3],可知创作应当是作者某种智力活动的体现。创作的过程,必须给劳动者留下智力创作空间。因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不仅是某种可以有形复制的智力成果,更是作者某种思想情感的表达,以及智力创造的结晶。智力虽不单是人类所享有,就像会结网的蜘蛛,会搭巢的鸟儿,都有一定的智力,但著作权法只有调整的人的智力才有意义。就像南非那头会画画的猪,就算画的再美观它也不可能因受著作权法的激励而多多创作[5]。只有对人的智力成果予以肯定鼓励,才能达到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繁荣的目的。
(二)人工智能创作过程分析
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终极目标是实现对人脑活动的模拟,并帮助人类实现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功能。人工智能既可以实现诸如“虹膜识别”等科技运用,也可以写诗作画模拟人类文学创作。以人工智能生成藏头诗为例,使用者只需把想好的字词输入进去,人工智能便可启动内部程序编码运行,对已建立好的数据库进行一番分析提炼,进而输出藏头诗词。由此例分析,可知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具体分为如下几步:(1)接收人类指示;(2)运行程序编码;(3)分析已有数据;(4)进行数据提炼;(5)输出作品生成。
就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讲,仍停留在弱人工智能阶段,还不具有脱离人的指示即可自动创作的能力。以上文所举生成藏头诗为例,虽然整首诗词是人工智能独立生成的,但一开始也离不开人对它发布命令指示,而人类创作完全可以是自主的、不受他人意志的支配。也许有人认为,即使是人的创作,也要受到之前所有的知识储备影响,与人工智能基于数据库进行创作并无本质不同。不可否认,人工智能的创作,大都是受到已有作品影响,其创作出来的作品,必然与之前所建立的数据库和程序编码有关。但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仍与人类大脑有许多差异。例如,纵使从同一个角度对标的物进行艺术临摹,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艺术观点和想象构思,其创作出的作品也会存在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就同一个角度临摹相同的物品,先后也会存在些许差异。而人工智能基于特定程序编码而创作,只要程序编码特定,其临摹出的生成物也具有特定性和唯一性。此外,人的创作还受情绪、灵感等偶然因素的影响,这点人工智能无法体现。也正是这些偶然因素的影响,才造就了人类不同的情感表达,才有了人类丰富的情感表达形式。
(三)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分析
著作权法保护作品这类智力成果,而只有人的智力成果才受著作权法保护,其蕴含的前提似乎为“作品只能是由人创造的”。尽管著作权法也承认法人或其他组织可成为著作权的权利主体,但作品归根到底仍旧是由人创作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似乎从根本上就排除了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独创性,构成作品的可能。但暂且撇开作品生成的主体不说,即使探讨主体以外的其他要件,也难以得出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独创性,构成作品的结论。
首先,目前人工智能即使数据库与人类的知识储备一样多,拥有特定算法程序,也无法真正像人类一样思考。其只能基于特定算法程序而生成某种类型作品,在数据库与编码程序一定的情形下,创作结果具有必然性甚至唯一性。而人类创作除了受到已有知识储备的影响外,还有诸如直觉、灵感等要素,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启发。纵使不同的人在相同的环境下,因感受不同创作出作品也是不同的。这种创作的偶然性是目前人工智能所不享有的。例如,人工智能在分析诗词的基础上,可以发现“秋”与“悲”等意向紧密结合,“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秋往往带有一种伤感的味道。但难以创作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样别有韵味的佳句。人类创作会因主体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的选择判断,进而带有明显的个体烙印,这种创作上的差异便是不同人格的独特反映。而现阶段的人工智能生成物,只是运行数据库与编码程序对运算结果的呈现,与体现个性化的智力创作存在根本区别[6]。
其次,人工智能生成物满足作品“独创性”要件中“独”的要求,应不成疑问。虽然现有人工智能只是在接收人的指示后才进行创作,但整个生成过程人类却无法干预,均是人工智能本身独立完成。但若满足作品“独创性”要件中“创”的要求,则必须考虑创作的过程。在客观上有作品,但不是通过创作产生,则无法受到著作权法保护。例如某个盲人随机按下相机快门,可能也会拍摄出几张客观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但整个拍摄过程只是在随机生成,因体现不出盲人的智力创造而不能被视为作品。同理,现有的人工智能只是在基于特定程序进行创造,与其说人工智能是在创作作品,更不如说是直接生成了内容更合理[7]。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基于特定编码程序运算出来的结果,不是人工智能具有独创性表达的结果,人工智能本身更是无法理解生成物所具有的含义[8]。虽然人工智能的创作编码程序等是由研发者事先预定好的,但这种编码程序只是一种方法规则,是研发人员的智力体现,而不能将其归属于人工智能本身。尽管也有人提出人工智能具有“先学习再生成”的智能,可以模仿人的大脑学习相关知识,但实际上也只是利用现有程序编程不断优化数据库的过程,与真正意义上人的自我学习尚存一定差距。著作权法激励的是创作行为,而不是机械或偶然的生成过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生成过程没有任何创造性智力劳动,谈不上独创性,也就更谈不上成为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了。
笔者在先后分析著作权法对作品的认定标准,以及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之后,进而分析了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独创性,是否应当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问题。人工智能虽然在单位时间内创作的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依然只是在执行特定算法程序的结果,难以实现更为精细复杂的创作过程,也不能体现人类创作时所具有的独特选择和编排。即使暂且撇开创作主体的因素不说,单纯从创作过程分析,也难以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独创性。因此将人工智能生成物定性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是不合适的。
三、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归属困境
如果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享有著作权,那么该著作权应当有权利归属。可以探讨的权利主体主要为人工智能本身,人工智能的使用者或人工智能的研发者三类。但无论归属于哪一类权利主体,都具有不可避免的逻辑漏洞或不足之处。
(一)权利归属人工智能
如果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本身,会面临私法理论上的困境。首先,作为私法权利主体的只能是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现阶段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出独立的意思表示,其权利行使、责任承担等方面都将成为难题[9]。试问,如果有人侵害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人工智能也能像普通人类一样提起侵权之诉?如果人工智能创作过程中侵害了他人在先的著作权,人工智能又能当作被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次,目前人工智能具有的行为模式与人类行为本身仍存在较大差距。与人类可以做出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相比,人工智能的行为背后都是特定程序运作的结果,人工智能不存在独立意识,更谈不上独立人格[10]。最后,人工智能无法支配享有财富。著作权法激励创作的目的对其毫无作用,人工智能不可能因著作权法保护作品而受到鼓励,从而产生多多创作的动力。真正能受到激励的只能是人工智能背后的人而不是人工智能本身,单纯保护人工智能是没有意义的。此外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也规定了,著作权法中的作者只能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同样没有将人工智能解释其中的空间。
综上,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上的主体地位与现阶段私法原理相冲突。人工智能本身作为法律意义上的“物”,只能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而不能拟制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有学者指出,可以考虑将人工智能仅拟制为著作权法律关系的主体,由人工智能管理者对其日常事务进行管理,并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强制登记[11]。笔者对此持不同看法。首先,如前所述,作为私法权利主体的只能是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人工智能只能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而不能成为主体,应遵循私法的一般原则。绕开整个私法领域单独为著作权法律关系另辟蹊径,并无正当性基础。其次,考虑将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强制登记,无疑登记成本太高,而且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生成速度之快和数量之多,一件件强制登记也仅仅是一种理论可能。
(二)权利归属使用者
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于使用者也是可探讨的选项。再以上文所举的人工智能生成藏头诗为例,使用者完全可以在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几首藏头诗中选择比较满意的作品,从而将著作权归属于自己。可这样做的消极结果也很明显。作品创作的成本如此之低,岂非变相鼓励大家以后多多使用人工智能创作,从而对现行作品生成方式产生巨大冲击。这无疑会危机人类创作的动力,使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人逐渐失去创作作品的热情。例如,以后如果一位作家想出版诗集,他不再需要伏案写作,只需简单操作下人工智能,再选择比较满意的作品,进行简单的编排整理即可。如此一来,著作权法便是在打消人类创作的积极性,与鼓励创作的宗旨相去甚远。
其实我们换个角度分析,使用者单纯操作人工智能的行为,只能归属于简单的劳动,不具有独创性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例如人工智能生成表情包,使用者可能会输入几个特定的词组或图片,以供人工智能创作使用,但人类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所付出智力成本是极低的。单纯搜索提供词组或图片的劳动行为也很难说是创作。依《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如果把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行为解释为创作的话,那么人类也只是提供某种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性工作,而这些工作本身是不能被视为创作的。既然不能被是为创作,也无法谈及生成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唐代贾岛有诗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可见创作的过程无疑凝结了作者本人的心血,是作者本人思想的结晶。一件优秀的作品产生,也可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曹雪芹为创《红楼梦》曾“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司马迁为作《史记》前后花费十四年的心血,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更是长达二十七年的时间。人工智能机械创作的成功,可能对当下作者的创作方式产生较大负面影响。试想,如果大家都追求使用人工智能写作,用一种最快捷的方式让自己获得著作权,又有谁愿静心创作,去凝结人类思想的结晶呢?从法政策的角度来讲,赋予人工智能使用者著作权,其可能引发的不利后果显而易见,对其享受著作权法保护,应持否定态度为宜。
也许有人指出,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在一般情形下与人类创作的作品客观上已并无太大差异。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形下,人工智能使用者若将人工智能生成物挂上自己名字,实际也能当成作品从而享有著作权法保护。因《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现象的产生仅仅是举证规则造成的,是信息不对等的产物,并不能改变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属于作品的本质。[12]
(三)权利归属研发者
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实现自动化创作,甚至创作出媲美人类作品的成果,人工智能研发者对其算法和程序的设计功不可没。但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于研发者,同样存在问题。
首先,人工智能研发者只是就人工智能的研发本身具有贡献,但与生成物的联系十分甚微。[13]人工智能基于怎样的算法程序进行创作,蕴含了研发者的智力结晶,但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生,却没有投入相应的精神劳动和智力判断。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生成物要分别观察。人工智能就好比泉眼,而人工智能生成物就好比泉水。研发者对这口“泉眼”的获得无疑付出了智慧劳动,但对泉眼冒出来的“泉水”,并无值得保护的劳动可言。不可否认,研发者为研发人工智能,无疑要花费大量心血精力,其编写的人工智能运行的算法程序,可以受著作权法保护。但当人工智能研发出来,人工智能再创作出成果的时候,研发者对生成物的内容却缺乏实质性贡献。试问,研发者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体现在哪里呢?人工智能生成物又如何体现研发者独特的选择和编排呢?在生成物最后产生之前,可能研发者也不能确定产生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如果认为研发者就人工智能生成物可享有著作权,无疑是鼓励研发者其坐享其成,一劳永逸,同样对人类创作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如果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属于作品,其著作权归研发者享有,可能引发“版权圈地”的不利后果。可以试想一种诗词创作软件,能将文字随机进行排列组合,理论上讲其具有穷尽所有五言诗、七言诗的可能。如果研发者将该诗词创作软件的生成物置于网络,理论上所有不特定的第三人都有机会接触该作品,以后的作者无论创作出怎样的五言、七言诗,都将与在先的作品实质性相似,满足“接触+实质性相似”的著作权侵权认定标准。如此一来,可能造成大量著作权侵权的事实存在,反而不利于对著作权的保护。
(四)小结
在法理学上,权利客体应当与权利主体相对应。如果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是作品从而享有著作权,那么必然有对应的权利主体。从上文分析可知,无论是将权利归属于哪一类,都有自身的不合理之处。承认人工智能生成物属于著作权法上的权利客体却找不到对应的权利主体,那么人工智能生成物究竟是不是著作权法所要保护的客体便存有疑问,因此可以反推人工智能生成物其实不应具有作品属性,不享有著作权。
四、结论
人工智能作为新事物,其生成物的法律地位如何需要进一步明确。在目前法亟待法律明确情形下,学界观点也是百家争鸣,各执一词。本文认为,判断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作品,不能仅从客观角度入手,还应考虑生成过程本身。仅仅因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外在表达与一般人类作品不存在明显差异,从而认定其具有独创性,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结论显然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