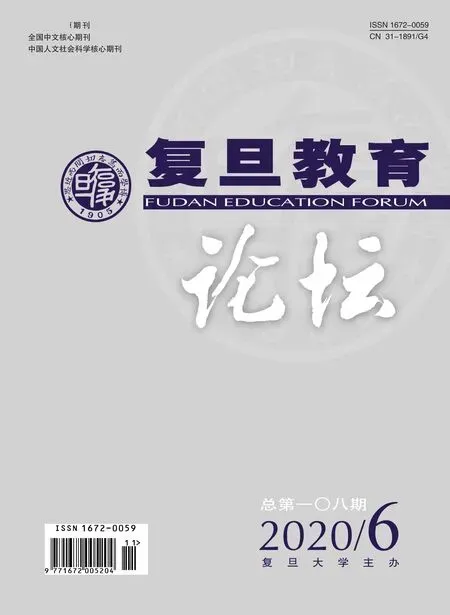澳大利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监管政策变迁的历史沿革与特点分析
2020-02-25朱浩
朱 浩
(湖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北黄石435002)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崛起,为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颇具争议的新途径,也加速了私立高等教育由一元体系向二元体系的转变。我国于2017年9月1日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确立营利性民办教育的合法性,这意味着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改革的国家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但是,在实施环节仍然存在诸多操作性困境,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分析澳大利亚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监管政策的变迁,有助于反思我国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体系与我国有着明显的区别,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科研和教学并重的综合性大学或学院,这种类型以公立大学为主,仅有3 所私立大学;另一类是以教学为主的专门学科的非大学高等院校(NUHEPs),其组成结构更加复杂多元,既有政府所创办的公立非大学高等院校,又有私人或慈善团体捐资创办的非营利性私立非大学高等院校,也有教会创办的各类学院,还有营利性教育集团或私人投资创办的营利性私立非大学高等院校。目前,澳大利亚119 所非大学高等院校中有68 所属于私立性质,这其中有65 所隶属于不同的营利性教育集团。就澳大利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而言,包括3 所私立大学和68 所私立非大学高等院校,它们都能提供高等学历学位教育,但是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不能获得政府提供的经常性公共资金。澳大利亚除了综合性大学和非大学高等院校之外,还有提供高等职业教育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AFE),这类机构是在培训机构(RTO)中注册,并不属于高等院校范畴,因此本研究并未将其纳入研究范围。
2018 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TEQSA)发布的《高等教育机构统计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共有176 所通过认证注册的高等教育机构,共计招收1,482,684 名学生。其中,43 所大学属于“自行认证机构”(SAA),拥有较高的大学自治权,招生人数占到总招生人数的91%;133 所高等教育机构属于“非自行认证机构”(Non-SAA),包括65 所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54所非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和14所高等技术与继续教育机构。[1]澳大利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人数相对较少,但其增长速度非常快。2008 年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率达到20.8%,而公立大学仅为2.6%,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也从2000 年的5 所增长到2008 年的约150 所。[2]2011 年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增长到170 所,其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审核,撤销一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注册,少数机构自行关闭,大型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兼并收购,到2018年澳大利亚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减少了47 所。[3]虽然机构数量明显下降,但是大型高等教育集团发展迅速,如卡普兰高等教育集团、纳维教育集团和IDP教育集团等全球顶尖教育服务机构。值得关注的是,罗瑞特亚洲教育集团(Laureate Education Asia)于2013 年在阿德雷德(Adelaide)中部投资创办的澳大利亚托伦斯大学(TUA),是43 所澳大利亚大学中唯一的营利性私立大学。
二、澳大利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监管政策变迁的历史分析
澳大利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与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并在澳大利亚政府出台私立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中渐次发展。这种变化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和民众的教育选择保持一致,同时,也代表着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过程。
(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形成期的各方博弈:二战后到1988年
1901 年颁布的《澳大利亚联邦宪法》明确规定,教育的具体管理权归于各州的教育行政部门。因此,在二战之前,各州的高等教育机构很少获得联邦政府的资助,联邦政府也无权干涉各州的具体教育事务。直至1944 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沃克委员会提交的《沃克报告》,为联邦政府参与各州教育事务提供了法理依据,联邦政府通过财政资助的方式逐渐控制各州高等教育的领导权。1972 年,惠特拉姆政府采取取消大学学费、实行免费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提供非竞争性联邦政府助学金,[4]并宣布联邦政府单独承担大学和高级教育学院的教育资助。从1974年开始,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拨款占到学校办学费用的90%。[5]这一阶段澳大利亚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征可以总结为由政府主导、国有化和去私立化,而联邦政府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1975 年至1983 年弗雷泽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执政期间,澳大利亚联邦的福利支出增加了46%,而其他社会性支出却下降了27.5%。[6]从20世纪80 年代起,澳大利亚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从各种形式的国家干涉主义转向更具活力的新自由主义,要求政府放松对教育的管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私立教育的作用。这种转变直接导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为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机遇。
1983 年,霍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于在高等教育领域是否发展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政府内部存在极大争议,前后两任就业、教育与培训部部长苏珊·瑞安(Susan Ryan)和约翰·道金斯(John Dawkins)持有不同的态度。苏珊·瑞安坚决反对发展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认为这种机构仅是消耗联邦公共资金,但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甚至会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统一的高质量标准产生损害。[5]相比之下,约翰·道金斯并不将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视为对现行高等教育体系的威胁,因为“在一个以广泛和高质量的公共供给为主的高等教育制度下,私立高等教育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收益很少甚至没有回报,因为仅靠收费实际上不能平衡其办学成本”[5]。20 世纪80 年代末到90 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对待私立高等教育的政策导向从国家化和公立化转向鼓励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创办来扩大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以满足民众不断增加的高等教育需求,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制度环境开始形成。1988 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高等教育资助法案》,明确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合法地位,从国家层面的法律上赋予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自主管理的权利。[7]
(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发展期的政策调整:1989年到1995年
1988 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高等教育——一份政策声明》,合并原有的高等教育双轨体制,建立统一的国家高等教育体系,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也被纳入其中。此时,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法律文书中都将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称为“其他机构”,“高等教育私人提供者”“私人提供者”“私立高等教育提供者”等称呼交替使用来形容此类高等教育机构。[8]1989 年,联邦政府出台《高等教育贡献计划》(HECS),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促使高等教育机构进入市场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资助方式和政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1985 年,霍克政府正式实施对海外留学生全额收费制度,鼓励大学用海外留学生的学费收入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并允许公立大学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共同开发市场化课程。在1987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政策讨论稿》中首次提出教育是一种产业的观点,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拓宽办学经费来源渠道。此时,联邦政府对待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采取“权力下放”的政策,将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权归于各州政府,而州政府通常仅要求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符合公司法的规定、通过州或者地区的课程认证即可创办。因此,20 世纪80 年代末到21 世纪初,澳大利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沿着两条路径快速发展:
一条发展路径是在州政府扶持下创办高质量的非营利性私立大学。坐落于昆士兰州黄金海岸的邦德大学是澳大利亚第一所私立大学,在澳大利亚邦德公司创始人亚伦·邦德(Alan Bond)和日本电子工业国际公司总裁高桥·原森(Harunori Takahashi)的共同倡议下,于1986年创建,并获得昆士兰州总理约翰·彼得森(John Beark Peterson)的大力支持。1987 年4 月9日,昆士兰州议会通过《邦德大学法案》,确保邦德大学的合法地位和独立性,邦德大学成为澳大利亚第一所非营利性私立大学,打破了公立大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之后,新南威尔士州和西澳大利亚州政府也出台了鼓励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政策。
另外一条发展路径是与公立大学合作、承接学位课程或共同开发特定课程的混合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随着海外学生逐年增加,公立大学的教育资源无法满足其对特定课程的需求,例如英语、商业和经济学等课程,部分公立大学将过剩的课程需求外包给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来完成,可以说这类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是满足过剩需求的产物。1985 年,位于西澳大利亚的盐池国际校园(WA)最早提议发展混合式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随后澳大利亚商业和技术研究所(AIBT)以及国际管理研究中心(ICMS)开始承接公立大学的外包课程。[5]
企业投资高等教育的愿景和联邦政府“自由放任”的政策导向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但是,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教育质量低下问题以及盲目扩增低端私立商学院和预科学院的“烂苹果”现象引发了澳大利亚社会各界的担忧,呼吁联邦政府出台全国统一的教学规范与标准。1991 年,联邦政府颁布《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教育提供方登记和财务规章)法》之后,出于维护国际声誉和保护海外学生利益的考虑,要求各州和地方政府负责监督课程注册,保障教育质量。另一方面,随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逐年增加,对于获得政府财政补贴和统一认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91 年10 月,澳大利亚政府颁布《高等教育:90 年代的质量和多样化》,要求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和高教机构之间的学分转换系统,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政策基础。
(三)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监管体系形成期的质量保障:1996年到2009年
1996 年3 月11 日,自由党的党魁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在大选中获胜,其为政举措之一就是极力推行公共部门私有化改革,认为公共服务应该处于竞争的环境之中让消费者进行选择,而教育改革势在必行。1997 年1 月,教育部长阿曼达·瓦恩斯通(Amanda Vanstone)上任之初就委任罗德里克·威斯特(Roderick West)组建教育研究委员会,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进行广泛调研并提供政府咨询报告,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对高等教育市场化影响重大的政策文件——《大众定制时代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9]该文件着重探讨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拨款方式改革,从而提升高等教育机构的市场化水平和竞争力,提出发展成为“完全的经济市场”,根本宗旨是提高联邦政府拨款的使用效益。随后,霍华德政府放开了高等教育机构自主设定学费的权力,加大了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资助力度。2003 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我们的大学——支撑澳大利亚的未来》,提出两种新型的联邦助学贷款方式:一是面向公立高等院校和通过认证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中全额支付学费的学生提供“全额自费—高等教育贷款计划”(FEEHELP);二是面向到海外接受学位教育的学生提供“海外学习—高等教育贷款计划”(OS-HELP)。该改革方案在同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支持法案》中得以实施,从而明确联邦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给予资助的基本政策。
随着联邦政府介入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澳大利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职能分化和多元化趋势更为明显。一方面,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获得来自联邦政府的直接拨款。创建于1989 年12 月的澳大利亚圣母大学(UNDA)是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联邦政府在1998年按照《高等教育资助法案》(HEFA)批准其与公立大学同样拥有获得联邦直接拨款的权益,紧接着邦德大学也获得同样的权益。另一方面,公立大学的市场化倾向进一步推动混合式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随着《高等教育贡献计划》的深入推行,联邦政府不再对大学增加经常性拨款,而引进竞争性拨款方式,鼓励高等院校自主寻求非政府资金来源,这进一步促进了公立大学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
在这一时期,澳大利亚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资本市场联姻,开展大量合并和收购活动,形成大型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集团,与此同时,国际资本也涌入澳大利亚教育市场。2004年12月,由悉尼商业与技术学院(SIBT)、墨尔本商业与技术学院(MIBT)、昆士兰商业与技术学院(QIBT)、珀斯商业与技术学院(PEBT)、伊迪斯·考恩大学(ECU)和艾恩斯勃利商业与技术学院(EIBT)这6家小型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合并组建的IBT 教育集团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成功上市,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家公开上市的大型营利性高等教育集团。[10]2007 年11 月,IBT 教育集团更名为纳维教育集团(Navitas),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旗下拥有8 所营利性私立非大学高等院校。在澳大利亚国内资本涌入私立高等教育市场的同时,国际资本也开始进入该市场,进一步加剧澳大利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整合与竞争。2006 年5 月,隶属于《华盛顿邮报》旗下的卡普兰教育集团(Kaplan Inc.)以5600万澳元成功收购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翠贝卡教育集团,之后进一步收购布拉德福德学院(Bradford College)和田庄商学院(Grange Business School),开启国际资本收购澳大利亚本土教育集团的先例。从整体上看,澳大利亚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并购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进而提升高等教育行业品质和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澳大利亚政府对其进行监管。2003 年,《高等教育支持法案》将非营利性私立非大学高等院校纳入联邦政府直接资助的范围,将营利性私立非大学高等院校的学生也纳入“全额自费—高等教育贷款计划”(FEE-HELP)的范围,这一扶持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
2000 年3 月,澳大利亚文化、教育、培训和青年事务部理事会设立了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障署(AUQA)。该机构定期对澳大利亚境内所有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质量审核,将审核结果反馈给联邦政府并对民众发布审核报告,以此确保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质量、办学声誉以及政府财政资助。同年3月,澳大利亚文化、教育、培训和青年事务部部长签署《全国高等教育审批程序议定书》。在此之前,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评审和批准注册都由各州政府自行进行,没有统一的标准,实际执行情况也良莠不齐。《全国高等教育审批程序议定书》颁布之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准入门槛和教育质量明显提升,通过审批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可以按照《高等教育支持法案》的规定获得“全额自费—高等教育贷款计划”的资助。从2005 年到2011 年的六年中,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获得联邦助学贷款资金的比例从2005 年的联邦助学贷款总资金的9%增加到2009年的总资金的28%,在2009年之后,该比例保持相对稳定。[11]
(四)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监管体系完善期的政策变化:2010年至今
在2008年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澳大利亚私立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背后产生的问题渐次显现,过分依赖国际生源、学生学业成就不理想、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监督不协调等问题影响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2010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署对32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包括20所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外部质量审计,包括机构治理、综合战略规划和质量管理、跟踪和改进绩效机制、学生入学情况、政策执行的一致性、学生学业评估等八个指标,审计结果发现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质量和学术标准问题突出。[12]
2007 年,陆克文政府委任布拉德利教授(Denise Bradley)组建调查委员会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进行审查,并于2008 年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布拉德利评论》(The Bradley Review)。该报告为澳大利亚国内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展奠定基础,并将发展目标设定为“到2020 年澳大利亚国内25 岁到34 岁的青年人拥有学士学位或以上的比例从2006 年的29%增加到40%”[13]。为实现这一总体目标,报告明确提出“未来高等教育行业的政策、监管和融资都必须考虑到通过私立部门所提供的高质量服务来发挥作用”[14],调查委员会建议联邦政府成立全国统一的、独立的国家监管机构负责所有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监管工作,实现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体系的可持续发展。随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2011 年颁布《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法案》,成立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TEQSA)。该机构具有更加充分的行政权,不仅对所注册的高等教育机构具有教育质量的建议权,而且对未达标的高等教育机构可以撤销注册和课程认证申请,通过质量审核、专业认证和风险评估三方面来实现全方位保障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质量,并根据《高等教育标准框架》制定不同层次的统一认证标准,依据高等院校注册认证的类别,对所有注册的高等院校分别进行统一认证和分类评估。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正式纳入国家统一认证的分类评估体系,也意味着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权通过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从州政府正式过渡到联邦政府手中。
自2011年成立以来,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对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监管和认证要求。从2011 年到2017 年,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共计收到130份高等教育供应商的认证注册申请,其中绝大多数是希望通过认证注册为非自行认证的私立职业培训学院,2016-2017 年度仅有8所新增机构通过认证注册。[3]2011年到2018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的统计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机构数量逐年下降而入学人数逐年增加的矛盾现象。这种新现象之所以出现,原因可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更充分地利用在线学习模式吸引非全日制学生和海外留学生参与在线课程学习,通过线上课程发展离岸教育已经成为新增长点。仅在2014年,澳大利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招收在线方式学习的人数增加了20.4%,而传统大学仅增加8.4%。[3]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公立大学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形成深入合作的伙伴关系,合作范围包括协助预备课程的教学任务、共享师资和校园设施、监督教育质量与学术标准、提供国际生生源以及确保双方的经济效益等。目前,纳维教育集团与8 所公立大学建立了伙伴关系,攻读学位教育的学生首先在纳维教育集团旗下的高等教育机构完成一年制的预备课程学习,再到其合作的大学完成两年的本科教育,获得学士学位。这种合作模式每年为合作大学提供超过7500 万澳元的办学收入和超过3000 名生源,其中70%以上为国际生。[2]发展在线课程和公私合作办学模式已经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支持,并在澳大利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中普遍实施,也对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的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澳大利亚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监管的特点分析
澳大利亚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与其他国家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公立高等教育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都经历过从“排斥”或者说“边缘化”到“被动接受”再到“标准化引领”的过程。我们在审视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相似性的同时,也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地缘政治、区域经济和传统文化对私立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不同的影响,以至于同处于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监管方式具有其不同于欧美各国的独特性。
(一)通过间接管理方式控制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逐利行为的度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无论是“完全脱离经济市场”模式,还是“完全经济市场”模式都并不符合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理想的状态是政府通过间接管理方式将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发展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是澳大利亚政府推动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产物,办学性质具有逐利性与公益性并存的特征,澳大利亚政府最终采用间接管理方式来引导其公益性和控制其逐利性。自2000 年澳大利亚政府设立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障署以来,以“质量标准驱动”为基础的联邦资助体系开始形成,澳大利亚政府利用非营利性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联邦资助经费以及竞争性拨款项目来引导和间接控制澳大利亚高校的发展,其中也包括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引导。
2011年3月,澳大利亚政府颁布《高等教育标准框架》,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提供者注册标准、高等教育提供者分类标准、教育提供者课程认证标准以及学历资格评定标准。[15]《高等教育标准框架》是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对高等教育提供者进行注册评审和绩效评价的重要政策参照,也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分类的标准,其分类标准是以学历框架的不同层次来进行划分,而不是以公立或私立的高校属性进行分类,因此学术质量标准是按照同一层次内保持一致性的原则来进行评估。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从申请、评审、获批再到课程认证有一套严格的质量标准和程序,对其教育质量的监管比对大学教育质量的监管更加严格,因为大多数私立非大学高等院校都属于非自行认证机构。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资助政策已经形成包括联邦资助政策、奖学金政策、学生助学贷款政策、捐赠政策以及税收优惠等在内的相辅相成的政策体系,非营利性私立大学和其他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获得政府资助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取得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的注册资格,以此来确保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质量。申请联邦政府资助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与政府签订资助协议,确立任务书,公开财务与办学成效信息以确保经费的使用效率,一旦发现私立高等院校举办者未能满足资助的相关要求,联邦政府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削减或追回资助经费。澳大利亚2014-2015预算案规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想为本校学生提供联邦资助项目的条件之一便是要公开学校的财务和办学成效信息。[7]联邦政府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签订资助协议,制定严格规范的信息公开、经费审核和绩效评估制度,不仅可以保证资助经费的投入成效,还可以防范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以非营利之名行营利之实。
(二)通过诱致性制度强化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竞争与合作
鉴于澳大利亚教育管理体制的特殊性,联邦政府采用强制性制度的运行方式通常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教育政策的预期效果,而采用诱致性制度来实现其目的。澳大利亚政府除了经常性拨款和基建拨款之外,还有种类繁多的竞争性资助项目。不同的资助项目有着不同的目的,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和申报资格,例如研究性资助项目、促进教育公平的资助项目和发展特定目标的资助项目等,实质上这些竞争性资助项目是政府向高校购买教育服务,以实现其发展目标。这些资助项目对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性质并没有严格的限定,主要的限定条件是申请高校必须符合《高等教育标准框架》并且通过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的认定。竞争性资助方式有利于向优质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发展所需的经费支持,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导和促进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和竞争能力,进而提升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公益性。
随着澳大利亚政府鼓励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实施,澳大利亚不仅拥有了像邦德大学和托伦斯大学这样著名的私立大学,更发展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利性高等教育集团,这些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不仅与公立高校在某些领域产生竞争关系,更可以推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市场化运作。澳大利亚政府除了鼓励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展开竞争,同样也支持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深入合作来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加强社会服务。1994 年,伊迪斯考恩大学与纳维教育集团旗下的珀斯工商技术学院签署第一份合作协议,开启了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深入合作的新模式。由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衔接课程和基础课程、合作大学提供专业课程的联合培养模式成为澳大利亚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合作的一种通行做法。
澳大利亚政府除了在制度上支持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合作,还根据需要设置各种专项经费项目来激励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共同合作。例如,为扩大弱势群体的大学入学机会,澳大利亚政府专门制定了“高等教育公私合作计划”(HEPPP),提供专项财政资助激励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参与特殊群体学生的预备课程教学。高等教育公私合作模式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而是政府以资助项目的形式控制着私营部门可能出现的高额利润,使得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共享合作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并确保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获得相对长期、稳定的教育投资回报,形成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稳定的伙伴关系。
(三)通过分类资助引导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质量优先发展
《高等教育支持法案》颁布之后,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获得申请联邦资助项目的资格;《我们的大学——支撑澳大利亚的未来》发布之后,联邦政府将符合资格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全额自费生纳入高等教育贷款计划。2016 年1 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教育预算案中第一次规定,在所有通过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认证的高等教育机构就读高级文凭或副学士学位课程的本土学生都可以获得联邦直接财政资助,以扩大本土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换而言之,本土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而不受联邦资助政策的限制。例如,在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就读学位课程的本土学生与公立高校的学生一样可以申请“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救助计划”(HECS-HELP)“、学生服务及设备费用补助计划”(SAHELP),这些资助项目原来仅提供给公立高校的学生。
2018 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发布的《高等教育机构统计报告》显示,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经费来源中,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直接拨款占54%,远高于欧美国家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拨款;国内外学生学费收入总和仅占18%,其中海外学生的学费收入占7%;非高等教育服务收入占5%,其中包括向海外学生提供英语专修课程(ELICOS)、职业教育与培训(VET)以及学历课程(Non-Award)等;其他收入占23%,包括捐赠收入、第三方服务收入和商业收入等。而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经费来源中,国内外学生学费收入达到其总收入的61%,其中海外学生的学费收入占34%;非高等教育服务收入占24%;其他收入占15%;并未获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直接拨款。[1]从统计报告中可以发现,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办学经费最大的来源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直接拨款,而学生学费收入还排在其他收入之后,由此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政府鼓励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倾向,并提供了公平的政策环境。同时,也可以发现澳大利亚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非高等教育服务项目收入来源最少,由此可以推断此类教育服务主要是由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完成。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经费来源中,虽然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拨款,但是实现了办学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学生学费收入是最主要的办学经费来源,同时非高等教育服务收入所占比例也很高,这与澳大利亚政府所提供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有着密切相关性。除此之外,在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就读高等教育文凭课程的学生同样有资格获得政府的助学贷款。
随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快速发展和民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澳大利亚政府高等教育资助政策中对公私立性质的区分和界限更加模糊,但是对于拨款经费的使用效率和效益要求更加严格。目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引导更趋明显,无论是通过项目形式直接对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拨款,还是通过鼓励公私合作项目的形式间接资助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都可以反映出澳大利亚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资助政策正在从“机会公平”转向“质量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