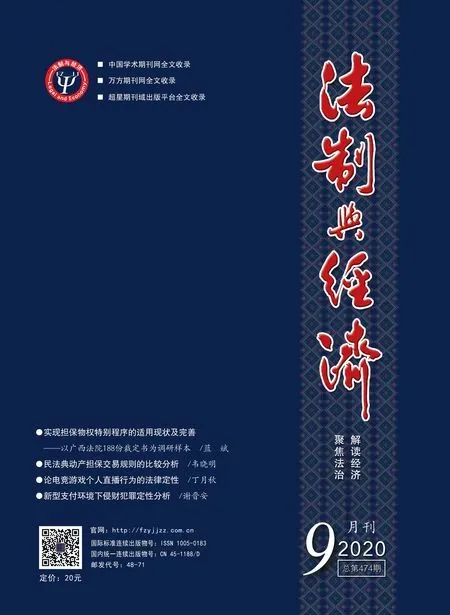论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责任承担与数额认定的关系
2020-02-25齐浩天
齐浩天
(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江苏 南京210094)
在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犯罪的成立、罪行轻重以及民事赔偿责任的计算均牵涉数额的计算问题,那么数额对于刑事和民事承认的承担究竟有何不同?刑事和民事程序中数额的计算又有何不同?
一、刑事责任的确定
(一)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数额的认定
1.数额认定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的作用
数额是区别民事侵权行为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标准。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大多要求达到一定的数额等。只有达到一定的数额才属于刑法调整的范围。未达到一定的数额则不构成犯罪,由民法来解决。首先,在某些犯罪中,刑法明确将数额作为犯罪成立的构成要件。例如: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等,都明确规定只有在相关数额达到“较大”或者“巨大”的情况下才构成该法条规定的犯罪。其次,在另一些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中,尽管并未直接将数额作为构成要件,但是数额是判断是否满足其构成要件的重要依据。例如:假冒注册商标罪、假冒专利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等都将“情节严重”和“造成重大损失”作为构成要件,而一定的数额正是“严重”和“损失”的判断标准。
数额是轻罪和重罪的衡量标准。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数额越大,对法益的侵害性就越大。数额的大小不仅是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同时也是区分轻罪与重罪的界限。首先,在确定所适用的刑法档次中,数额具有重要作用。在明确将数额作为构成要件的一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一般分为“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两个档次。在另一类未明显将数额作为构成要件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同样根据数额分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造成重大损失”“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两类。2004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于上述两类犯罪的两个档次的判定都是从数额上进行认定的。其次,数额对于具体刑罚的确定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的刑法量刑具有一定的幅度,采取的是相对确定刑的标准。在某一档中,如果数额刚刚达到该档的基础线,法官往往会采取从轻处罚的方式。如果在某一档中,数额远超该基础线并要达到该档上限时,法官往往会采取从重处罚的方式。
2.数额认定之非法经营数额
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数额的种类规定了很多种,非法经营数额只是其中一种。在判断是否构成某罪时可以从多个数额来进行判断。这些数额分别有:非法经营数额、销售金额、违法所得数额、犯罪行为直接涉及的物件数量以及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解释》规定:“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也就是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所涉及的侵权产品的总数额。《解释》在对该概念作出定义的同时也对其计算方式作出了规定:“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二)采用“非法经营数额”的刑法依据
在刑事程序中采取“非法经营数额”作为数额认定标准的原因是受到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约束。《刑法》第三条对罪刑法定原则作了如下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确保刑法的稳定性。即便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在此处也要让位于刑法保障人权的更高价值追求,变得可以被确定。《刑法》第五条对罪刑相适应原则作了如下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该原则要求,法院在对犯罪分子量刑时,应当根据其行为危害性的大小以及犯罪情节、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影响刑事责任的因素来确定与之相适应的刑罚,做到罪行、罪责和刑罚三者相适应。罪刑相适应原则在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的体现在于对被告的定罪量刑必须严格依据法院确定的非法经营数额来进行。在具体的案件中,一旦对于“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出现变化,被告的定罪量刑就可能出现相应的变化。
二、民事责任的确定
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民事责任的认定并不是和刑事责任一样,特别是涉及知识产权的侵权赔偿问题时,侵权人的获益和受害人的损失往往难以确定。
(一)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难确定性
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使得权利人对其占有、支配不同于有形的物。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的特征,在性质上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权利人欲证明其所受之具体损害,殊为不易。[1]所以,对于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处理,民事责任的认定并不像刑事责任那样具有明确的标准。刑法责任的确定可以简单地从非法经营额出发,但是民事责任的确定则不得不从诸多方面进行考虑。吴汉东教授曾指出,知识产权意义上的损害,实质上是对知识产权所蕴含资产价值的损害。[2]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中,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是容易确定的,但是损害的数额却往往难以确定,主要是因为知识产权的价值变量具有不确定性。要确定损害的数额就得从知识产权的价值变量中计算出合理的数额来填补权利人的损失。此种侵权案件损害赔偿额的确定难点在对损害事实如何量化,以及合理化和损害事实无法通过诉讼手段客观再现两个方面。[3]前者涉及对于损害评价的客观标准的问题,后者则关注诉讼中如何对其进行举证证明。鉴于以上原因,实践中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损害变得难以评估和难以确定。
(二)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方式
我国法律在确定知识产权赔偿数额时主要按照顺序考虑数额: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以及法定赔偿。《专利法》和《商标法》还在第三顺序的位置设置了“许可费的合理倍数”这一项。我国法律对上述计算方式适用顺序进行,而有的国家则赋予了当事人对计算方式的选择权。
处在第一位的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此种计算方式得到各界的认可,因为此种方式完全符合侵权法损失填补的理念和完全赔偿的原则。对于这种实际的损失可以从销售量、价格的减少以及成本的增加来进行确定。域外很多国家在权利人实际损失的计算上达到了比较成熟的水平。美国和日本强调侵权行为和实际损失之间的关系,对此的关注度不足会造成对于权利人的过度保护而影响法律的公正。
第二顺序的是违法所得。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的争议。首先,利用违法所得来计算损害赔偿额的方式与侵权法的填平规则不一致,将着眼点从受害人转移到了侵权行为人。其次,有学者认为,完全可以通过不当得利返还的方式来实现权利人向侵权人违法所得利益的索取。所以我国在实践中应当慎用这种计算方式。
第三种方式是许可费的合理倍数。这种方式相当于让侵权人强制性交纳其擅自使用知识产权的许可费。采取合理倍数的计算方式目的在于使得计算出的损害赔偿额更加接近于实际损失,如果仅仅对侵权人处以许可费一倍的处罚,那对于侵权人来讲就毫无侵权成本可言,相当于在鼓励从事侵权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合理倍数并不具有惩罚性,仅仅是为了实现侵权法的损失填补功能。在美国,本方法是其专利法上损失赔偿数额的两种计算方式之一,可见其重要性。
最后一种方法是法定赔偿的方法。该方法是在以上方法都无法适用或得不出合理结果的情况之下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这种方式的极高适用率也说明了知识产权领域损害赔偿数额计算的难度很大,同时以上几种计算方式在我国的适用结果并不理想,可操作性并不强。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在适用自由裁量权时就应当十分谨慎,同时也应当尽量少用这种不确定的法定赔偿方式,尽量适用以上几种计算方式解决问题。为了保证判决的公正性和可预期性,应当在判决书中对数额的确定进行充分的说理和论证。
我国司法目前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上操作比较简单,难以对损害赔偿额给出一个相对明确的计算结果,判决书中大多也未能就如何认定给出合理而详尽的论证和解释,存在严重的缺陷。这可能也是知识产权领域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不足所在,体现在法官的审判重点在于刑事责任的认定,而对于民事责任的具体细节之处缺乏关注。
三、结语
基于罪行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对被告的定罪和量刑,必须严格依据法院认定的非法经营数额来确定。但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由于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的特点,绝大部分侵权案件无法确定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受到的损失,故相关法律作出了人民法院依法酌定赔偿数额的规定。所以,在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依据不同的法律责任承担原则分别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