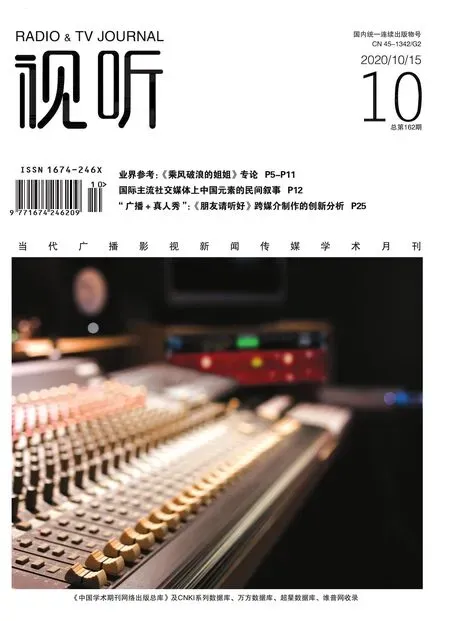电影《苏州河》的后现代性分析
2020-02-24段雪菲
□ 段雪菲
现代社会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如偶像剧、商业电影、网络小说、流行乐曲等,它们占据了市场的主流,与此同时还承担着特殊的社会功能,即“民众参与的社会意义的生产和流动”,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思潮或文化形式,它是一个兼具结构性与批判性的理论。茱迪·威廉森曾说,“在我们的文化批评实践里,存在着偏爱一个文本胜过另一文本的现象,我们已经制造出了自己的经典。尽管高级艺术和低级文化之间的分界已经模糊,我们还是没有完全放弃艺术的概念”。我们从中可发现,在后现代社会,高雅与通俗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不再有明显的分界。在后现代社会,一切似乎都无章可循和变幻莫测。
娄烨在电影《苏州河》中讲述了一个颇具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是影片并未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满足和情节上的期待。观众在影片中并未看到缓缓流淌着的美丽的河流,影片中呈现了一个非自然的现实。人类掌握了主动权,居住在河流两岸的人们控制了河流,由于严重污染,苏州河已不再具有观赏性,流淌着污浊的浑水。上海是一个兼具中西方特色的国际大都会,在这里,流淌着这样一条浑浊不堪的河流。城市的发展、经济的腾飞在都市中处处可见,但是苏州河却代表着发展中的城市的真实景象,即人们的生存现状。导演娄烨拍出了一条流淌着的苏州河,摄影机摇晃的画面呈现了苏州河的真实面貌以及沿岸人们的生存状态。虽然晃动的画面使观者感觉到不适,但是这种摆动与眩晕给观众以视觉上的冲击,引导观众进入故事,切身体会主人公的悲欢喜乐。导演娄烨并未遵从影片艺术的说教这种古老的艺术功能,也没有告知观众如何走出迷途,而是通过影片传达了现代城市青年人的情感状态与生活现状。
一、《苏州河》中的解构主义
在《苏州河》中,并没有传统影片中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只有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见到的普通人。他们没有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举措,他们仅仅是生活中的人,导演告诉我们生活就是表面光鲜亮丽却隐藏一条流淌着浑浊污水的苏州河。《苏州河》讲述了一个关于寻找的浪漫的爱情故事,马达与牡丹因送货而相识,后来成为恋人。马达绑架了牡丹,当牡丹得知被绑架的目的是为了巨额赎金后,万念俱灰跳入了苏州河。马达失去了爱人,与此同时,更失去了自由。马达出狱后,在苏州河沿岸寻找牡丹,追寻曾经失落的爱情。在找寻过程中,马达发现了一个几乎和牡丹长相一模一样的女子美美,便将美美当作自己的爱人。在这里,外貌的本真性受到了质疑。鲍德里亚曾提出“镜像理论”,试图解释人们在镜子中看到的自己并非真实的自己,而只是一个镜像的呈现。后现代文论家对真实性提出质疑,在娄烨的作品《苏州河》中,我们同样发现了后现代主义文论对于我国文化生活形态的渗透。
影片《苏州河》中,同样的能指并不代表同样的所指,即相似的外貌并不等同于同一个人物。后现代主义中的解构主义认为,最初的解构是从语言开始的,通过阐述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来进一步阐发解构主义。德里达认为,符号所表现的意思并非两个符号之间差异的结果,语言并非像索绪尔所描述的那样是能指与所指恰恰相对应的统一体,每一个符号的意思实际上是因为这个符号不是其他所有的符号,也就是说,符号意思就是在所有符号之间无限的差异中,它只能是潜在的、无休止的相互差异的产物,语言就是一个无限差异、无限循环的系统。德里达提出了延异等几个概念。延异是在语法差异的一词的基础上替换第七个字母E为A而改造得来的,糅合了“差异”和“延迟”这两个词义。一方面存在意义存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由于意义的差异而带来的传达和理解的推延和阻隔。
当偏执的马达确定美美并不是牡丹时,又开始继续寻找牡丹的旅程,最终在一家便利店中找到了牡丹。也许此时观众期待影片结局将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导演却没有给观众预期的期待,而是以悲剧收场,马达与牡丹死于车祸。在电影末尾,美美看到了长相酷似自己的牡丹,导演以此呈现出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美美离开了苏州河,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正如德里达所提出的“延异”,即对于意义的不确定性。德里达认为,词语永远没有一个终极的确定的意义,一个所指指向其它的能值,又由这些个能指指向更多的所指。因此,意义是不确定的。娄烨让美美得知现实之后,独自离开,开始她的故事,这同样是对“延异”的阐述与诠释。娄烨所设定的不完满的结局是对传统电影结局的解构,娄烨告诉观众,电影并非都有美好的团圆,悲伤的结局往往发生于现实生活当中,也许更能体现现实。
二、《苏州河》中的互文性
互文性指的是文本之间的“互文见义”,即文本经常凭借和模仿其他文本,或者无论有意或是无意以其他的方式与其他文本相互联系。这种借用和影响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简单复制,而是一种动态的拼凑。互文性要以具体的语境为依据,也许是作者刻意而为,也有可能是作者记忆深处的某一个片段。娄烨说,“这些被看成是在‘模仿’中长大的一代人,他们的‘模仿’实际上是真正独创的。”模仿并非照搬或复制,而是一种经过了创造的再现,能够在中国的具体社会语境中恰当地应用文本样式。在电影《苏州河》中,可以窥探到对《维洛尼卡的双重生活》这部电影的模仿,这是欧洲著名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在这部电影中,呈现了两位容貌相似但生活环境不同的女性。波兰和法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社会语境却造就了两颗能够相互感应的心灵。电影《苏州河》中的牡丹与美美同样有着惊人相似的外貌,但是二人成长于不同的环境。有着相同外貌的二人看待对方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审视着自身,因而在电影《苏州河》中互文式地显现出《维洛尼卡的双重生活》的影子。
三、反主流文化
这类题材的电影作品并不是企图以题材上的禁忌来赢得关注,长久以来,观众似乎有一种观影的盲目性,追寻梦想中色彩斑斓的幸福世界,而这恰恰蒙蔽了灰暗的现实。德里达曾提出“‘揭秘’批评”,他所揭秘或对抗的是人们通常称之为“信条”或“神话”的观念,即流行的,已成为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他认为这种神话的产生是由于迷失了事物的历史本质,即忘掉了事物的构成性,这就使得最后产品成了一种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东西。但是作为艺术家,有责任将现实生活呈现在银幕上。在娄烨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处于社会底层,这是一群被所谓主流群体排斥的人,大多数观影群体的生活环境与这些主人公不同,导致了受众群体与影片人物的距离感,因此很难获得认同,即不能满足观众的期待视野。这类作品回避了通俗电影中精致的画面与浪漫圆满的期待,而是以电影为媒介讲述了国际大都会中青年人真实的生活现状,观众很难找到常规的叙事模式,更多的是一种非线性的叙事手法以及破碎地拼接。冷峻残酷而又直面现实的影像正冲击着人们的神经,虽然未能给受众带来以往的期待与快感,但使大众敢于直面现实的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