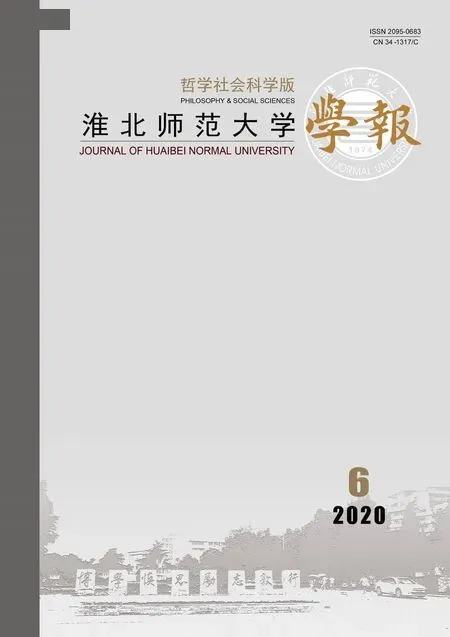桐城方氏研究中的“连理”之谜探析
2020-01-18陶善才
陶善才
(中共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安徽 合肥230091)
以方以智为集大成的桐城方氏学派,因其推陈出新、独树一帜于明末清初大时代,为中国哲学发展史写下了精彩的篇章,被近代以来的研究者称为“中国十七世纪时代精神的重要的侧面”[1]15,方以智更被誉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2]1。近年来桐城方氏学派暨方以智研究趋热,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丰硕喜人,但被方氏学人频繁书写的“连理”一语,尚未引起充分重视。溯源“连理”,最初与方学渐庭前“枫杞连理”及其所创连理亭有关,此后“连理”就频频出现在方氏学人著述中,连理亭成了方氏后裔世守的精神支柱,而“连理”甚至成为桐城方氏家风家学的图腾符号。本文通过溯源和梳理“连理”相关问题,就方氏“连理”家风家学的积淀与传承进行探讨,进而深化对“连理”在建构并贯通桐城方氏学派中意义的认识,这对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不无启示。
一、连理亭及其旧居由来
方氏连理亭的创建,源于明代的一起祥瑞事件:“明善公讳学渐,与兄白居公同居。时庭有杞枫二树,自本及枝,纠结如一,因亭其下曰连理亭。”[3]卷五十一90方学渐(1540—1615),字达卿,号本庵,桐城桂林方氏(方氏因科举兴盛、折桂如林而称桂林方氏,学界一般直接称桐城方氏)第十一世,明代理学家黄宗羲《明儒学案》将其归入“泰州学派”,学者世称“明善先生”。白居公,即其兄方学恒。之所以兄弟同居,是因为父母早逝。当母亲去世时,学恒十八岁,学渐十三岁;父亲去世时,学恒二十二岁,学渐十七岁。兄弟二人因此同居相守。此时,庭前出现了“枫杞连理”的祥瑞事件。
古代视为祥瑞的所谓“连理木”“连理树”“连理枝”,本是一种并不鲜见的自然现象,但古人往往惊叹为天地恩泽,并赋予祥瑞内涵。尤其是方学渐庭前的枫杞二树,“覕然连理,既开复合,观者以为昆弟之祥。”[4]卷十六24此事在当时格外引人注目。一般认为杞树是低矮的灌木,而枫树是高大的乔木。可能方学渐庭前这两种树都长得高大,且既开复合了三次。所以方以智在《慕述》中说“维枫与杞,三交连理”[5]第十册366。明代崇祯朝礼部尚书叶灿《方明善先生行状》也有这样的描述:“枫杞二树连理者三,人以为孝友之祥。”[6]2(需要指出的是,学者彭君华校点的《桐城方氏七代遗书》,将这句话校点为“枫杞二树连理者,三人以为孝友之祥”,显然有误)这株杞树是否真的也很高大?这是很有可能的。沈括《梦溪笔谈》里就描述过一种枸杞树:“枸杞,陕西极边生者,高丈余,大可柱,甘美异于他处。”这就可以解释方学渐庭前连理树为什么受到从官方到民间的格外重视,以致后来被载入多种史志文献。方氏后裔也不断咏叹,如方以智在《慕述》中就提及:“白沙手植枫杞,成连理之祥。”[5]第十册366白沙是指连理树所在的白沙岭。
由于出现了“杞枫连理”祥瑞,方学渐“因亭其下曰连理亭”,这就是连理亭创建的由来。其曾孙方以智《合山栾庐占》第八首诗云:“连理堂传断事薪”,自注曰:“先曾祖明善先生讲学传经,敦善不息,家有杞枫连理之祥,号连理堂”[7]第十册344。断事,即方氏五世祖方法,为桐城方氏科举崛起第一人,曾任四川都指挥司断事。在朱棣发起“靖难”时,方法毅然自沉长江,以殉建文帝。方学渐为方法的六世孙。在《慕述》中,方以智又说“连理堂稿,志林仪之”[5]第十册366。《明诗纪事》则指出:“堂有枫杞二树,连理而生,因题堂曰连理”[8]2131。而方学渐文集就是《连理堂稿》。可见,连理堂是“题堂”得名,非新创建,且曾为方学渐的自号。
二、连理亭究竟建于何时
与连理树“既开复合”“连理者三”一样引人注目的是,方氏连理亭也成为白沙岭当地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桐城桂林方氏家谱》卷四十九指出,连理亭为“明善公(方学渐)旧居,数传而归引除公,重葺连理亭于墓(方中履墓)之东”[9]71。引除公,即方学渐的来孙方正瑗,号方斋,又号连理山人,诗集《连理山人诗钞》有多首诗写连理亭。其中《金石集》卷第一“连理亭”诗前序曰:“亭在白沙岭,明隆庆间先明善公旧居。”[10]157虽是介绍连理亭,却强调为明善公旧居,实际上等于说“连理亭边的连理堂旧居”,毕竟亭子是不能居住的。所以方氏后人提及连理亭,实际上不仅指连理亭,也包括亭边的连理堂旧居。
方正瑗《连理山人诗钞》中,又有《潇洒集》卷第一记录“重葺连理亭落成”之事,重葺的时间在乾隆戊午(1738年)。诗中注解曰:“连理树自隆庆至今犹存”[11]328。可见,方正瑗认为连理树形成于明隆庆年间。他既然强调过连理亭是“明隆庆间先明善公旧居”,这就等于认为连理树的形成与连理亭的构建差不多同时。
但如果依据其前辈方文(号涂山)的一首诗,则连理树形成的时间应该更早。因从侄方豫立画了一幅“连理图”,方文写了首七古长诗《启一子建作连理图赠予赋此答之》,诗中有句曰:“我祖明善真大贤,白沙旧有桑麻田。”“今年与我重过白沙岭,栖息连理亭之偏。仰思二木发祥日,到今七十有九年。”[12]2方文此诗作于崇祯戊寅(1638 年),往前倒推七十九年,正好是嘉靖己未(1559 年)。这意味着连理树的形成时间,并非隆庆年间,而是更早的嘉靖己未(1559年)。
方文,原名孔文,字尔止,号涂山,是方学渐之孙、方以智的从叔,距方学渐时代最近。他出生直到四岁,祖父方学渐还在世。因此他关于连理树形成时间的记载最为可靠。方文的“涂山体”诗自成一格,与“梅村体”“虞山体”并驾齐驱。而画“连理图”的方豫立,字启一,又字子建,擅绘画。他虽是方学渐曾孙,却比方文年长五岁。崇祯十二年(1639年)春,方以智携方豫立、左国柱等里中亲戚学友游龙眠山,写成《龙眠后游记》,文中称“子建素工此(指绘画),十倍我”[13]第九册355。方豫立所绘的《龙眠山图》,也得到方以智的题款。家谱载方豫立“以事亲得旌表”,称“孝子”[14]卷五十二16。可见他也是孝友模范,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绘《连理图》。方文以诗名,方豫立以画显,两人以不同的形式歌颂先祖“白沙手植枫杞,连理成祥”,必然使得白沙岭连理树故事传播得更远。
既然连理树形成于嘉靖己未(1559 年),但方氏后裔为什么着重强调连理亭为“明隆庆间旧居”?笔者认为,很可能方学渐创建连理亭的时间在“明隆庆间”。因为连理树于嘉靖己未(1559年)形成时,方学渐才十九岁,父亲去世不久,他还在守孝之中,家境又贫寒,不可能有构建连理亭的经济条件。而方学渐是“与兄白居公同居”的,所以当时只能“题堂曰连理”。到了明隆庆间,方学渐不仅成了郡诸生(府秀才),且已成家,其岳父赵锐先生乃致仕知府,因无嗣,所以给爱女的嫁礼丰厚。方学渐此时与兄割宅而居,由于其兄贫甚,乃将赵氏奁田(陪嫁田)也全部赠给其兄,说:“弟笔耕足自活,藉是以奉兄耳”[4]卷十六24。说明方学渐这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连理亭正是构建于此时。
三、白沙岭究竟位于何处
由上文可知,亭在白沙岭。那么,白沙岭究竟位于何处?有学者误认为在桐城东乡浮山,如李圣华《方文年谱》就误认为“白沙岭在枞阳浮山北麓”[15]102,却并未指明出处和依据。而遍检桐城史志文献及前代诗文,也未明确指出浮山有白沙岭。《桐城桂林方氏家谱》卷四十九则明确记载:“白沙岭在县北三十二里”[9]71。查清道光七年《桐城续修县志》“桐城县全图”,便知“白沙岭”距今桐城“三十里铺”(今为桐城北乡重镇大关镇政府所在地)只有二里,与方氏家谱记载一致。
清人姚兴泉《龙眠杂忆》小令也指出了白沙岭的具体方位:“桐城好,岩峡古重关。北通齐鲁开门户,南控沅湘集市寰,雄峙万松间。”下有小注:“入小关十里为北峡关,又里许即白沙岭,为余外家发祥地。苍松数万株,由关连荫,皆数百年物也。”[16]卷二11可见白沙岭距北峡关仅里许。姚兴泉的外家即桐城宰相张氏,也发迹于白沙岭一带。
姚鼐是姚兴泉的族侄,乃是桐城派集大成者,有诗《雨行白沙岭至旵冲遂宿》写道:“北望双阙门,硖石何苍然。”其下注曰:“白沙岭在西北,逾岭乃至大关、小关,古所谓峡石关也,关外则入舒城县境矣。”[17]68这就明确指出,白沙岭在北峡关(即今大关)附近,关外即舒城县。
方以智《从舒还宿白沙》诗曰:“入关度岭见莲峰”[18]第八册286,从标题到内容,都准确指出了白沙岭的位置所在,也即从舒城县返回桐城,进入北峡关,过了白沙岭,就能看见莲峰。方以智年轻时经常跃马出游,这次由舒城返桐就住宿在白沙岭,所宿必然是其曾祖父方学渐的连理亭旧居。
方以智所见的“莲峰”,即道光七年《桐城续修县志》中所称“莲花尖”,今仍称莲花尖,“自莲花尖东北五里即麒岭”[19]卷一7。明代学者赵釴写北乡大关一带山水的“助山堂杂咏”,有题为“莲华峰”诗曰:“欲住青莲宇,冥心玩玄化。只是云雾多,白日在山下。”[20]卷五174诗人将莲花尖比作“青莲宇”。而方学渐写白沙岭一带山水的诗也较多,他称莲花尖为“莲华屋”,这个比喻与赵釴几乎同出一辙,诗曰:“晚日照芙蓉,烁灼青云里。秋色不朦情,天光净于水。”[21]卷七230表明从白沙岭南下,莲花尖颖出于他山,最先进入人们的视线。
四、方学渐缘何曾居白沙岭
方学渐的祖居本来在城中凤仪坊(又称凤仪里)。令人不解的是,他的旧居何以在距城三十里开外的北乡白沙岭?虽然未有文献直接指出原因,但从《桐城桂林方氏家谱》中八世方印、九世方敬、十世方祉的一些记载来看,或许可以作一些线索探析。
方印本来与弟弟方塘同居城中凤仪坊,当弟弟请求“析而两之”时,方印说:“吾子一耳,弟子四,岂令我目诸子之厚薄其室也?”然后“五分之而自取白一磽确者以居。”于是将家产分成五份,他携家及独子方敬选择了较为偏僻而又贫瘠的一份,即离城八十里远的白。但方印很快外出为官,九个月后因病逝世于天台县令任上。[22]卷五十一18他的独子方敬因乐于助人挥资若弃而家道中落,以致于“岁徙无宁所”[23]卷五十一30。这既是他孝友的表现,也很有可能正是他迁居白沙岭的原因。
当时,白沙岭一带作为联南接北的交通要塞,市镇密布,商贾云集,物流繁茂。北峡关还专门设有巡检机构,为全县四大巡检机构之一。而众多后来赫赫有名的桐城文化巨族,正在这一带耕读传家,甚至开桐城科举先声。桐城历史上首开讲学之风的理学大师何唐,就曾讲学于附近的旗岭(又称岐岭);著名的桐陂赵氏文学家族赵锐、赵釴兄弟(都是何唐弟子)致仕归来也聚徒讲学于此。加之这里环境优美,生态宜居,诚如姚兴泉所描写的那样,“苍松数万株,由关连荫,皆数百年物也”[16]卷二11。这可能是方敬将家从偏僻贫瘠的白迁居白沙岭的另一个原因。
而方敬之子方祉的孝友事迹,不仅被载入家谱,康熙版和道光版《桐城县志》也专门有记。可惜他与夫人吴氏先后早逝。及至第十一世方学恒、方学渐兄弟,孝友事迹更是传为美谈,这时庭前出现了“维枫与杞,三交连理”的祥瑞奇迹。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初新发现的桐城北乡叶家河《南阳叶氏支谱》(祠堂在白沙岭附近的天马山之阳)也提及方学渐居于白沙岭。据1942 年六修谱序云:“吾邑自前明何省斋先生(即何唐)倡明正学,开理学之先声,实居吾里之小旗岭。继之者有方明善(即方学渐)、孙麻山(即孙学颜)两先生。一居里之连理亭,一居里之荆冲。三先生者,世相去不过百余年,地相去不过里许或十里许,而能相率讲明圣贤之学,蔚成善俗,俦为风气。故居是地者,类皆人文郁发,士习端向,自前明以迄今日四五百年,卓然称仁里焉。”作序者乃原北平大学教授、浮山中学校长姚孟振,其家世居大关镇白沙岭附近的笃山,与序中所称小旗岭、连理亭、荆冲,“相去不过里许或十里许”[24]卷一1。此序还表明,连理亭已不仅是一座亭子,由于太出名,它甚至取代白沙岭成了地理名词。
五、方学渐究竟何时返城
既然方正瑗强调:连理亭是“明隆庆间先明善公旧居”,而隆庆间方学渐才二十多岁,那么方学渐究竟何时离开白沙岭,此后更多的时间是生活在什么地方?据方孔炤于万历庚申(1620年)跋其父方大镇《宁澹语》云:“先大父(祖父方学渐)居崇实居近五十年”[25]252。崇实居(又称“远心堂”)即今城中潇洒园的前身。方学渐逝世于万历乙卯(1615 年),上推五十年,正好是嘉靖四十五年(1565 年)。而隆庆时代(1567—1572)仅六年,如果方学渐万历元年(1573 年)才离开白沙岭,则居崇实居仅四十二年,就不符合“近五十年”之说。
而方学渐也不可能是嘉靖时代(即1567 年之前)离开白沙岭,否则就不会有“明隆庆间旧居”之说。因此他只能是在隆庆时代离开白沙岭返城。究竟于隆庆时代哪一年离开白沙岭的?方孔炤在《宁澹语》跋语中又说,“家大人(方大镇)居宁澹居近二十年”[25]252。方大镇在外为官三十余年,但调迁不定,包括休假回桐、辞官归里,都从未固定居于某处近二十年。因此,其居于宁澹居近二十年,必然是为官之前,且其宁澹居必然在城中方学渐的府第内。已知方大镇出生于嘉靖辛酉(1561年),中进士外出为官则是万历己丑(1589年)已经二十八岁,减去宁澹居二十年,表明其从出生到八岁的童年时代不居城,是随父母居住在白沙岭,而方大镇八岁时是隆庆二年(1568 年),这一年距方学渐去世万历乙卯(1615)正好四十七年,符合方孔炤所称祖父“居崇实居近五十年”之说。
又据叶灿《方明善先生行状》:“先是伯兄废箸更贫甚,即割宅而居,割奁田而膳。二十年怡怡无间。”[6]2方学渐与其兄割宅而居,则至少要在结婚成家之后,且只有成家了,才能“割奁田而膳”,也即将外家的陪嫁田割送给其兄方学恒。由方大镇生于嘉靖辛酉(1561 年)十一月,方学渐已经二十一岁,可知方学渐至少在二十岁(1560 年)左右成家。且割宅时,兄弟二人的宅子必然是相连的。也即割宅后,到了隆庆二年(1568年)、方大镇八岁时,方学渐还住在白沙岭连理堂(已与兄割宅而居),故其所居为后裔所称“明隆庆间旧居”。
综上,方学渐最有可能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离开白沙岭,回到城中,构建了崇实居。大约过了一年,方大镇九岁到了“教数之年”,应该为其请塾师了。不久,方学渐专门为他创建居室兼书斋的宁澹居。因方大镇此时尚年幼,宁澹居必然在崇实居庭院内,不可能距离太远。方大镇在其中读书、结婚、生子,住了将近二十年,直到万历己丑(1589 年)二十八岁中进士、外出为官。当方大镇官迁大理寺时,被里戚尊称为廷尉公,其父崇实居和他自己的宁澹居又被统称为廷尉第。此外,还有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值得重视:一是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年),方学渐“应岁升廷试毕……归后构桐川会馆。”[6]2桐川会馆也在县城,焦竑《桐川会馆记》明确指出,“馆负城临临,据一方之胜”[26]829。方学渐城居并专门创建用来讲学的桐川会馆后,桐城的学术中心就转移到了县城,但白沙岭方氏连理亭仍然为方氏后裔世守。二是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 年)秋,方学渐应顾宪成之邀赴无锡东林书院讲学,归来时,适曾孙方以智出生于廷尉第。据方以智十世孙方叔文所撰年谱:“是年十月二十六日密之公(即方以智)生于安徽桐城方廷尉第。时公曾祖明善公尚健在,命名曰东林。”[27]1
六、“连理学脉”梳理中的方氏别业辨疑
诚如方以智所言,“吾桐素多游宴园林。”[28]第九册120明清时代的桐城,世家巨族别业园林众多,桐城方氏家族也不例外。仅方学渐这个房头,在方以智的生活时代就有五大读书别业:北乡白沙岭连理亭、城后龙眠山廖一峰游云阁、城南泽园、东乡浮山在陆山庄、南乡小龙山白鹿山庄。这些别业是构成方氏“连理学脉”不可或缺的链条,但也导致当今学者对方氏“故里”多有误判。如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就误以为方学渐的崇实居、方大镇的宁澹居等都在北乡白沙岭,进而误认为方以智出生于北乡白沙岭。[29]34-38罗炽后来出版的《方以智评传》可能受蒋国保这一观点影响,也持相同观点。[30]29由于方以智晚年号“浮山”,曾受邀主持浮山华严寺(未成行),去世后葬于浮山,一些学者又误以为白沙岭在东乡浮山,进而误以为浮山为方氏“故里”。如李圣华《方文年谱》就误认为“白沙岭在枞阳浮山北麓”[15]102;曹刚华《方以智晚节考补》进而误认为“方以智出生于浮山”[31]。罗炽甚至还误以为龙眠山廖一峰(又称寥一峰)也在浮山,写方以智年少时“在浮山的龙眠山廖一峰下课读”[30]30。如此误判必然导致“方氏名人故里”之说混乱,也为溯源和梳理桐城方氏“连理学脉”带来困惑。实际上,方氏五大别业的创建有着一条清晰的时间轴线。本文很有必要对此进行辨疑。
白沙岭连理亭创建最早,即创建于明隆庆年间,为桐城方氏“连理学脉”之源头。由前述可知,北乡白沙岭连理亭本来是方学渐的居所,自方学渐于隆庆二年(1568 年)返回城居后,连理亭旧居就成了方氏后裔的读书别业和讲学重地。如其长子方大镇《田居乙记》小序云:“壬寅既归,则向白沙山中扫室问药。”[32]万历壬寅(1602年)方大镇病休归来,就在白沙岭读书养病。崇祯己巳(1629年),方大镇在白沙岭连理亭讲学,乃作“白沙䎸语”[33]13。方氏学人不仅以连理亭为读书别业,还以此为讲学阵地。方学渐的来孙方正瑗在“连理亭”诗前序中就指出:从方学渐开始,历经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到他父亲方中履、伯父方中德、仲父方中通,“皆尝讲学此亭,今及不肖正瑗居六世矣。”[10]157实际上,从方学渐讲学连理亭开始,一直到清末方昌翰还时常来白沙岭连理亭闭关读书,并有诗曰:“飞泉夜鸣白沙岭,开门晓对洪涛山。”[34]卷一而洪涛山正是前述桐城儒宗何唐的世居之地,与白沙岭相对,距小旗岭、荆冲等地不过里许或十里许。可见,连理亭为桐城方氏传承了三百余年,其不惟方氏故里,亦是桐城方氏“连理学脉”之源头。
龙眠山廖一峰游云阁创建于万历末期,是桐城方氏“连理学脉”不可或缺的接续环节。龙眠山因宋代画家李公麟隐居于此并号“龙眠居士”而闻名。桐城的县治在龙眠山麓,故桐城又称“山城”“桐山”。龙眠山上的廖一峰,又称寥一峰,距城约六里许,有碾玉峡,方氏家族多人在此有读书别业,其中方大铉(方学渐仲子,号玉峡)就有“听峡斋”,并筑有“玉龙亭”。[35]卷二15方孔炤(方学渐孙)有诗不仅称碾玉峡为“龙眠高士地”,而且“唤作小三峡,中藏大九州。”[36]卷二4他亦有“游云阁”别业在此。方以智极爱这里的寥一峰,称其为“寥一洞天”,他在《龙眠》随笔中这样记述:“碾玉峡瀑流最壮,叔祖户部公(即方大铉)取以为号。寥天一峰,即老父(即方孔炤)跨涧之游云阁也”[37]第十册195。而在崇祯十二年(1639 年)所写的《龙眠后游记》中,方以智则明确指出:“余幼读书处,在寥一峰下,有涧石急湍,可以流觞。”且“先曾王父(即方学渐)及王父(即方大镇)生平所著,寿诸木者,尽藏于此。”他幻想着战乱尽快平息,“使得竟返故乡,于此枕石漱泉,读先人之书,岂不乐乎?”[38]第九册356但随着战乱,这里的读书别业逐渐毁弃,直到清代承平后始为方氏其他族裔继承。由此可见罗炽所言“浮山上的龙眠山廖一峰”之误。而廖一峰别业作为方氏学人读书和著述藏板之地,又距方学渐城居后所创建的城中讲学重地“桐川会馆”较近,因此其在梳理桐城方氏“连理学脉”中是不可忽视的接续环节。
东乡浮山在陆山庄创建于明末天启时期,为桐城方氏“连理学脉”的重要一环。浮山又称浮渡、苻度,在当时属于桐城东乡,距县城九十里,为本县著名华严道场。据方大镇《归逸篇》云:“癸丑(1613 年)丰城黄山人为余指浮渡,戊午(1618 年)贵池王山人指白鹿。余并爱其山水,並因其旧室葺治之为考槃之居。”[39]卷四可见,浮山与白鹿(在南乡小龙山)的别业都是方大镇晚年分别听取了黄姓与王姓朋友的建议后创建的。天启甲子(1624年),朝廷党争剧烈,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惨遭迫害。方大镇与东林党人讲学的首善书院也被魏忠贤阉党捣毁,他遂借口筮得“同人于野”卦辞职归隐,回桐城后于浮山创建“在陆山庄”,辟作读书别业,命其中堂曰“此藏轩”,又在游山时,兴手题书“野同岩”。[40]231携孙方以智读书岩下,此时他已六十四岁,孙子方以智已十四岁。[41]18可见所谓“方以智出生于浮山”之说不确。“此藏轩”毁于明末战乱。方以智晚年逃禅驻锡江西青原山净居寺时,桐城合邑士绅邀请方以智归来主持浮山华严道场,他的三个儿子曾在“此藏轩”故址建庵,并请施愚山题之曰“报亲庵”。[42]221但因受江西学人极力挽留,方以智未能成行,不久又因粤难牵连而自沉于万安惶恐滩,后归葬于浮山。因此,浮山“在陆山庄”读书别业在桐城方氏“连理学脉”梳理中是重要的一环。
南乡小龙山白鹿山庄约创建于明代天启到崇祯初期,为桐城方氏“连理学脉”中的重要链接点。方大镇在创建东乡浮山读书别业的同时,还通过形家帮助,卜选南乡小龙山(今属罗岭镇,距城一百余里)的一处山场,因“并爱其山水”,遂创建“白鹿山庄”,作为百年归隐之地。他在“归逸篇”里说:“百年衣冠则愿藏白鹿,以其局势宏敞,法度颇合,且与枞阳邻近,可随侍先君招呼于白云颠也。”[39]卷四由于其父方学渐卜葬在离城百里之外的枞阳镇松门岭,方大镇每年正月元旦都要行程百里去拜墓:“问余何时当元日,年年雨雪奔枞川。余言不独省荒垅,实如世俗拜新年。假令先君今而在,独意徙居百里外?”[43]卷23这正是他晚年创建白鹿山庄的重要原因,而白鹿山庄所在地与枞阳镇相距不远,“可随侍先君招呼于白云巅也”。正因为如此,方大镇对白鹿山庄的构建很用心,“山本程氏鬻於他姓,今次第而得之”。他又说“並因其旧室葺治之为考槃之居”[39]卷四,这说明白鹿山庄的产业与浮山产业差不多同时购建。所谓“旧室”应该是购买的他人旧业园林,进行了重新修葺扩建。明清鼎革之际,方孔炤率全家隐居于白鹿山庄,在这里完成毕生“随时拾薪”的易学思考结晶《周易时论》,凝结了方氏几代学人心血,被认为是明代易学集大成之著,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顾炎武《日知录》具有相同的时代意义。[44]68随着清初乱平,方氏后裔逐渐返回城居,白鹿山庄则为方以智的弟弟方其义的后裔继承。由此可见,在梳理桐城方氏“连理学脉”时,南乡白鹿山庄因方大镇、方孔炤两代学人均于晚年隐居于此,其与东乡浮山在陆山庄的地位同等重要。
城南泽园创建于崇祯二年(1629年),是桐城方氏“连理学脉”中的又一个学术起跳点。周岐在“泽园永社十体诗引”中指出:“泽园临南河,取丽泽之义。方潜夫(即方孔炤)夫子玺卿告假还乡所建也。”命其子方以智读书其中,“学耕会友,而歌以永言,不枯不乱。”[45]卷二十三14查方孔炤《职方旧草》“乞假疏”,知方孔炤于尚宝司卿任上告假是崇祯二年(1629 年),可见泽园正是创建于此时。方孔炤还在园中构建了“雾泽轩”,其父方大镇为此专门作《雾泽轩诫》:“盖取玄豹藏雾雨,泽其文章之义。”要求子孙“一定品,二慎交,三惜时,四尊闻,五持戒”[46]48-49。方以智也有诗记录他在泽园的读书时光:“南郊有小园,修广二十亩。开径荫松竹,临水垂杨柳。西北望列嶂,芙蓉青户牗。筑室曰退居,闭关此中久。晨起一卷书,向晚一尊酒。河梁如嚆矢,风骚为敝帚。聊以写我心,何暇计不朽。”[45]卷二十三14方以智在泽园与周岐、孙临、方文、吴道凝、钱澄之等结为社友,共同研经习史。而其母吴令仪英年早逝,从天启二年(1622 年)到崇祯九年(1636年)一直厝于泽园附近。所以他在泽园读书,实际上就是读书于母亲墓侧。正如他在《慕歌》诗前序中所说:“余读书其侧,时朔伏临,非敢曰孝思,亦以识慕云尔。”[47]第九册272泽园不仅离城中方氏藏书楼“稽古堂”和方氏家塾“东郊慧业堂”近,且城中讲学重地“桐川会馆”也近在咫尺。作为桐城方氏学派的集大成者、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方以智在这里度过了极为重要的读书时光,奠定了其一生的学术基础。因此,梳理桐城方氏“连理学脉”,决不可疏忽城南泽园。
七、“连理”在建构方氏家风家学中的价值意义
嘉靖己未(1559年),桐城北乡白沙岭连理树的出现,仿佛是一个隐喻。正是从方学渐于树下创建连理亭开始,桐城桂林方氏方学渐这一支,迎来了家族振兴、人才辈出的曙光,颇具影响的桐城方氏学派从这里发微并逐渐崛起,蕴育了旷世奇才方以智。不仅连理亭成为方氏后裔世守的精神支柱,“连理”二字也被方氏学人不断书写,成为桐城方氏家风家学的图腾符号,也是探索桐城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首先,方氏连理亭具有“克变俗习”之风气开先意义。桐城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春秋桐国、秦汉桐乡,但宋元以前的漫长时期几乎都冥冥默默,直到明清才风气大开、人文蔚起。诚如清代学者方东树感叹:“桐城在江北号为望县,然自宋以前故无人物,稽之史传,寥寥如也。及明以来,乃有世家大族数十百氏蕃衍迭兴。”[48]卷四66而这不能不提何唐与方学渐的风气开先作用。清末马其昶为何唐作传时曾谓:“先生勇毅任道,不顾众嘲,风声流播,竟亦克变俗习。吾乡讲学之绪由此起,至方明善先生益昌大矣。”[49]52何唐世居之地洪涛山、讲学之地小旗岭,都与方学渐所居白沙岭近在咫尺。但何唐致仕归来的讲学时间并不长,且积劳成疾,不幸于四十一岁就英年早逝。作为何唐的再传弟子,方学渐继其余绪,接武讲学,仍以“克变俗习”为使命,倾其一生都在大张何唐学风,倡明圣贤之学。他不但被邑中学者奉为牛耳,大江南北的邑外学者也翕然宗之;还被东吴学者顾宪成、高攀龙等视为旗帜,将其所创的“桐川会馆”与东吴“东林书院”并称为华山、泰岳。[50]69自方学渐筑连理亭以来,白沙岭乃至桐城因此蔚成善俗,俦为风气,“人文郁发,士习端向,自前明以迄今日四五百年,卓然称仁里焉。”[24]卷一1
其次,“连理”学问具有桐城方氏学派大厦之奠基意义。“五四”前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方以智的学术思想逐渐受到海内外学人关注,“桐城方氏学派”开始进入学术研究视野。1987年,台湾学者张永堂出版专著《明末方氏学派研究初编——明末理学与科学关系试论》,明确提出“方氏学派”的命题。[51]同时期香港学者冯锦荣也发表《明末清初方氏学派之成立及其主张》。大陆学者蒋国保在国内首次以方以智研究为题完成硕士论文,并于1987 年出版《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一书,论及方氏学人群体。尚智丛于2002 年完成博士论文《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也讨论了“方氏学派”。还有诸多学者论及“方以智的学派”。直到2004蒋国保发表《方以智与桐城方氏学派》,主张冠以地域名称,即“桐城方氏学派”。[51]总体来看,桐城方氏学派是以方学渐为开创者,以其“连理”学问为构建整个方氏学派的地基,建立了一个宏大的以易学为主、独树一帜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思想史写下了重要篇章。如果我们从方学渐“藏陆于朱”的学术旨趣出发,可以把枫树比喻为“程朱”,把杞树比喻为“陆王”;从其子方大镇“藏悟于学”的学术旨趣出发,可以把枫树比喻为“悟”,把杞树比喻为“学”;从其孙方孔炤“藏通几于质测”的学术旨趣出发,可以把枫树比喻为“质测”,把杞树比喻为“通几”。而其曾孙方以智会通三世之学,并在此基础上“坐集千古、会通中外”,成为集大成者,被侯外庐称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如此,则“枫杞连理”,不仅是昆弟之祥,更有桐城方氏家风家学的深刻喻意,而“连理”学问则具有构建整个桐城方氏学派理论大厦的奠基意义。
再次,“连理”学脉具有“实濬其源”之文化寻根意义。桐城明清时期文教发达,科举兴盛,有“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之誉,尤其是桐城派虽肇始于桐城一隅,却流衍于海内外,引领有清一代文坛数百年,影响直至今日。究其原因,清初大学士张英一言以蔽之:“明善先生以布衣振风教,食其泽者代有其人。至于砥砺名节、讲贯文学、子弟孝友仁睦,流风余韵,皆先生穀诒也。”[52]卷一清初浙江学者、诗词大家朱彝尊也有类似的观点:“方氏门才之盛,甲于皖口。明善先生实濬其源,东南学者推为帜志焉。”[53]卷十四425可见早在清初,方学渐就已被公认为桐城文化的“实濬其源”者。而方学渐崛起于白沙岭,从连理树到连理亭,再到方学渐的《连理堂稿》,“连理”二字几乎成了方学渐学问的代称。其子方大镇曾明确指出,论学必须“清其源、正其本”,因为“源清然后千流万派从兹皆清,本正然后千枝万叶从兹皆正。”[54]203故而,寻根桐城文化,梳理方氏“连理”学脉,从“清其源,正其本”出发,必然要寻根桐城方氏学派,寻根白沙岭连理亭,因为连理亭可谓“实濬其源”之源。
最后,“连理”符号具有“子孙世相守”之文化传承意义。翻阅方氏各类家藏文献发现,“连理”一语已成为方氏学人累世频繁书写的图腾符号。因方学渐的著述有《连理堂集》,其子方大镇“绍连理堂本庵先生之学”[55]75,荷薪续火,著述宏富,其中就有《连理集》。从方维仪写其父方大镇“庐中七十征连理”(方维仪《慕亭》诗),到方孔炤“以连理之祥而号仁植”[55]75,方孔炤还在《名儿以智其义》诗中云:“连理著易蠡,荷薪以意释。两儿念此名,根本在学易。”[56]卷二4诗中“连理”代表其祖父方学渐的学问,“荷薪”代表其父方大镇的学问,他冀望两个儿子方以智、方其义能够传承方氏家学。而方以智童年时代,与年纪相仿的从叔方文“乌石托竹林,共读连理书。”[57]388-389流寓他乡时,方以智还随身携带“连理亭”印章一枚[58]第八册496。明清鼎革后,方以智子中通、中履仍在白沙岭盘桓,方中通有诗曰:“连理亭前树,而今尚连理。”[59]卷一11表达不忘传承先辈学问和精神的意志。方以智孙正瑗还以“连理山人”为号,著《连理山人诗钞》。一直延续到清末的方昌翰,虽居城中,仍时常赴连理亭闭关著书,其有诗曰:“我祖筑亭云水间,忆昔著书曾闭关。飞泉夜鸣白沙岭,开门晓对洪涛山。波澄蘋沼见鱼戏,月上松林招鹤还。频来愿共荷锄侣,谈笑忘归桑者闲。”[34]卷一方以智六世孙方宝仁还搜集先世著作精心整理抄写成《连理亭方氏著述》,后裔方鸿寿先生历尽硝烟,千方百计将其保护下来,解放后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是今天研究桐城方氏学派及其集大成者方以智的重要文献。诚如方正瑗强调的那样:“子孙世相守,清露九霄深。”[10]157方氏子孙在世守和传承的基础上,不断积淀、不断阐扬,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方氏“连理”家风家学,也极大地促进了桐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八、余论
溯源和梳理方氏“连理”学脉,可以看出,由方学渐所肇始的方氏家学,自白沙岭连理树下的连理亭奠基,以方氏家传易学为根本,在“连理”这一线索的贯穿之下,经方大镇、方孔炤两代的接力阐发,到方以智“坐集千古之智”而集大成,再到方以智三子(中德、中通、中履)分传父学,渐与清初考据学合流,历经二百年之久,形成了别开生面的桐城方氏学派,体现了“吾道一以贯之”的传承特质,并坚持崇实黜虚、经世致用,冀图克变俗习、匡救时弊。
考察方氏“连理”家风家学,还可以看出,桐城方氏学派对桐城一邑崇文尚学的良好风气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后来桐城文派的崛起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清人谭献在《桐城方氏七代遗书序》中就明确指出:“桐城方氏七世之家学,不独灵皋侍郞文辞授受之先河,抑阎、顾之流一代经师之先河也已。”[60]叙2针对明代理学家重道轻文、作文害道的弊端,方氏学人特别是方以智力求回归孔子“志于道而游于艺”,强调“道不自见,而见于文”,在“会通千古”的基础上形成了集大成的古文思想,为桐城派后来的崛起播下了“文章薪火”。[61]50-51从这个角度来看,桐城方氏学派是“藏文于道”,强调学术上的“会通”和“通变”精神;而清代崛起、以方苞为鼻祖的桐城文派则是“藏道于文”,在辞章中坚持以义理与考据贯穿。
“ 最爱池边连理树,白沙亭子旧家风”[62]卷三十四21-22。总之,“连理”不仅是桐城方氏家风家学的图腾符号,也是梳理和溯源“连理”学脉的关键线索。而探讨方氏“连理”家风家学的积淀与传承,进而深化对“连理”在建构并贯通桐城方氏学派中意义的认识,也启示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要世代传承,更期望能够“会通”而“通变”,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既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也是彰显地域文化魅力、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