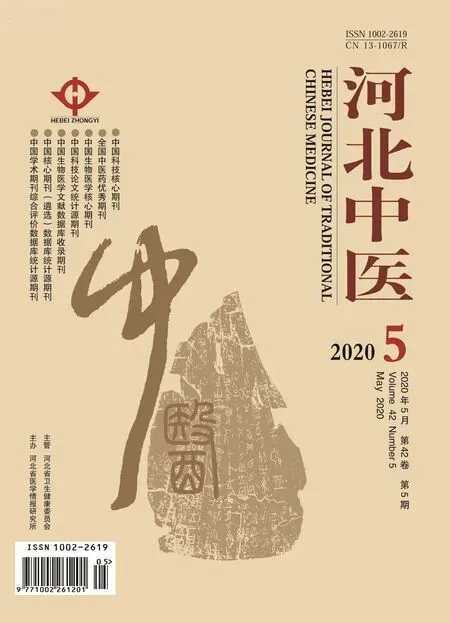李桂贤教授辨治呃逆经验
2020-01-10古展鑫刘华盛
古展鑫 刘 锐 刘华盛
(广西中医药大学2017级硕士研究生,广西 南宁 530001)
呃逆最早见于《内经》,称作“哕”,作呃逆义,现代临床是指气逆上冲咽喉,喉间急发疾声不能自止的一种病症,可单独存在,亦可与其他病互见。生理性呃逆常见于多食过饱、急促进食或摄入过冷过热食物、酒水饮品等,为一过性呃逆。而频繁呃逆或间歇性发作>24 h者,称为病理性呃逆,多与中焦虚寒、气滞、胃热、食积或下元亏虚摄纳无权有关[1]。中医学认为,呃逆病因有虚有实,或虚实夹杂,究其根本在于气机失调。中焦脾胃为气机升降枢纽,呃逆之作,总属胃之浊阴不降,脾之清阳不升,上下不能交泰。欲使气机升降得序,治疗呃逆频作,全在“调”法。
李桂贤,广西中医药大学教授,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届广西名中医。李教授从医40余载,尤擅治中焦脾胃诸病,多以中焦脾胃为切入点,屡获佳效。兹将李教授辨治呃逆经验总结如下。
1 呃逆病位、病因、病机
1.1 病位 《素问·宣明五气》云“胃为气逆,为哕为恐”,《灵枢·口问》载“谷入于胃,胃气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于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于胃,故为哕”,可见呃逆病位在胃。
1.2 病因 呃逆病位在胃,病理性质有寒热虚实之分,实证者多寒凝、气滞、火郁、食积;虚证者多胃阴不足、中焦虚寒、肾气亏弱或久病体虚。若呃逆声高有力,连续频作,多属实证;若遇年老及大病久病之际,其声低缓,气不接续,多属虚证;若呃声高亢,口臭酸腐,多属热证;若呃声沉缓有力或无力,口中泛吐清水,或口淡无味,惧饮冷,畏寒,则为寒证[2]。
1.3 病机 呃逆一证,总由胃气上逆动膈所致,中焦乃脾胃气机升降之枢纽,为呃逆之作关键。呃逆发病还与肺、肾、肝有关。《临证指南医案》提出“肺气郁痹,亦能为呃”,肺居膈上,其气以通降为顺,《灵枢·经脉》说“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灵枢·口问》更提出了“补手太阴,泻足少阴”及“肺主为哕,取手太阴”的治法。肺胃相连,肺气与胃气共同构成三焦气机通道,皆以通降为顺。膈居肺胃之间,若肺胃气机不能宣发通降,可使膈间气机失于和降,逆气上扰引动喉间,发为呃逆。《灵枢·杂病》首次记载取嚏宣肺以止呃逆的方法,“哕,以草刺鼻,嚏,嚏而已,无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惊之,亦可已”是为其法。肾主纳气,主脏腑气化,《类证治裁》云“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可见气的生发及肺胃之气升降,有赖于肾气纳摄。若久病及肾,或体虚,肺胃之气失于肾之摄纳,则冲气上逆,气逆动膈而成呃。脾胃气机升降还有赖于肝气条达,《古今医统大全》认为“凡有忍气郁结积怒之人,并不得行其志者,多有咳逆之证”,若肝气失于疏泄,郁滞中焦,必横逆犯胃,使胃气不能降浊,胃失通降,从而导致胃气上逆动膈,发为呃逆。因此,呃逆病位在胃,基本病机为胃失和降,膈间气机不利,胃气上逆动膈,并与肺气是否通降、肝气是否条达、肾气是否摄纳有关。
2 辨治特点
2.1 病证结合 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为中医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李教授认为,辨证与辨病结合才能全面认识疾病。只有证而病不立,则无法有的放矢;只有病而证不明,则无法从根本解决问题。李教授临证首先“辨病”以确诊,辨病是对病的总体把握,然后再“辨证”以定证,明白疾病的阶段或类型,此所谓“以辨病为先,以辨证为主”,坚持辨证与辨病结合。由于诱发因素、病理原因及疾病发生机制不一,导致疾病具有时空性、动态性特征,因而中医有“同病异治”的说法[2]。呃逆基本病机为胃失和降,膈间气机不利,胃气上逆动膈,但也与诸脏腑有关,故须病证结合来遣方用药。
2.2 重视舌诊 中医学认为,心开窍于舌,舌为脾之外候,苔为胃气上蒸所成,吴坤安在《辨舌指南》云“舌之苔,胃蒸脾湿上潮而生”,可见舌苔诸象与脾胃关系最为密切[3]。呃逆病位在中焦脾胃,重视舌诊是李教授辨治呃逆一大特色。李教授认为,岭南地区地卑雾障,雨水充沛,阳热炽盛,湿受热而蒸腾散发,天暑下迫,地热上蒸,湿气弥漫,人常困于湿热之中,凡所病多夹湿。呃逆为病,亦不例外。临床见舌苔厚而腻者,其湿郁内蕴,胃之浊阴不降,脾之清阳不生,李教授常先以燥湿理气、芳香化湿之品豁达脾胃为先。凡所治病,须先求脾胃运化得司,能受药汁,而舌苔厚腻者必先从湿解。中焦如沤,若湿浊不除,蕴结体内,缠绵难愈,内毒丛生,加之纳药不受,药力不可触达中病,反助诸邪,恐闭门留寇。气味芳香类药物能行能透,善调气机,能散表邪,可宣化、透化湿浊,故李教授常用芳香化湿之藿香、佩兰、苍术、厚朴、砂仁、白豆蔻、扁豆宣化湿浊,调气和胃。
2.3 以“调”求和 呃逆总体病机为胃失和降,膈间气机不利,胃气上逆动膈所致,而气机通畅与肺气是否通降、肝气是否条达、肾气是否摄纳有关。脾气主升,胃气主降,斡旋诸气于内,为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气机失调,诸疾相应而生,有气机阻滞或不能外达,或离散太过不能内守,或上升不及、下降太过而为“气陷”,气上升太过、下降不及则为“气逆”。中国古代哲学有“阴阳贵和”的思想,阴阳自和是人体自我协调和自我恢复平衡的能力,阴阳合和,万物自生[4]。国医大师颜正华临床治疗呃逆,亦以疏导“气机”为要义,注重理气调气,用药多采用疏肝理气、和胃降逆之品,与李教授“调气和中法”不谋而合[5]。李教授认为,对于气机失调,不应一味扶正或祛邪,更不应一味重降逆气,而当以“调”法求和为贵,常用自拟方调气降逆汤调和上下,通达内外。药物组成:柴胡9 g,升麻9 g,淡豆豉15 g,姜半夏12 g,厚朴12 g,陈皮9 g,砂仁6 g,木香6 g,丁香3 g,柿蒂15 g,赭石30 g,甘草6 g。李教授受李东垣学术思想影响颇深,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调气降逆汤方中先入柴胡升提肝脾之气,治气者用药宜轻,故柴胡皆从质轻,6~9 g为宜。升麻升阳举陷,《本草汇言》谓“升麻……此升解之药,故风可散,寒可驱,热可清,下陷可举,内伏可托”。半夏姜制,取其止呕逆下气之意,《名医别录》言其“消心腹胸膈痰热满结,咳嗽上气,心下急痛坚痞,时气呕逆”,《药性赋》更言其“大和脾胃气”。淡豆豉有除烦宣郁之功,《本草纲目》认为其“下气,调中,治伤寒温毒发痘,呕逆”,张仲景在《伤寒论》“栀子豉汤”证即为其用,《外台秘要》云“但闭气抑引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亦载有简单验方“煮豉三升,饮汁佳”,结合呃逆病机,若因气无所发而为逆,配伍轻宣之淡豆豉宣肺气。厚朴、陈皮、砂仁、木香虽皆为行气理气之品,但其所主诸气有所不同。厚朴疏导下行之气,陈皮理中焦之气,砂仁、木香相须为用,斡旋中焦气机,兼醒脾和胃,诸理气药合用,意求三焦气机得畅。结合“辨病”气机上逆脾胃动膈一症,加丁香、柿蒂、赭石取义《卫生宝鉴》中丁香柿蒂散,降逆止呃为治其标。和之以甘草,调和诸药,缓其气逆。全方立意在于“调”,以达气机升降有序为本,而非一味降逆。李教授认为,一味重用降逆之品,气机下陷,物极必反,当求上下交泰,寓降逆于宣畅。
2.4 穴位点按 《灵枢·刺节真邪》认为“用针之类,在于调气”。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刺激不同腧穴,可激发外周自主神经性生理传导作用,这些神经信号传入大脑皮层的高级中枢后,通过神经信号的反馈作用,整合体液或神经等途径实现对靶器官的调节[6-7]。由此可见,刺激特定穴位后中枢神经传导机制所产生的抑制迷走神经兴奋的作用可缓解膈肌痉挛,是穴位点按法治疗呃逆的基本原理。李教授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常选攒竹作为降逆止呃的经验用穴,众多临床工作者也常用攒竹治疗呃逆[8-9]。攒竹为足太阳膀胱经穴,能疏泄太阳膀胱经气,而足阳明胃经与足太阳膀胱经相交,经络相通,间接疏导脾胃经络气机;因足太阳膀胱经挟脊,故与膈、脾胃相连;此外,攒竹位于眼胞,是中医的“肉轮”,又属鼻针的胸穴,可调理胸胁气机,予重刺激可宽胸利膈,降逆止呃。太冲,足厥阴肝经之原穴,常用于平肝胃之逆气,取“上病下治”之意,配攒竹引气血下行。操作上,嘱患者仰卧或坐位,闭目以集中精神,将注意力聚于丹田,配合呼吸运动作吞咽动作,刺激强度因人而异,但多行重刺激手法。除此之外,内关为手厥阴心包经的络穴,而心包经下膈联络三焦,通过内关可调节全身气机;合谷乃手阳明大肠经穴,其与肺膈相连,合谷、太冲相伍,一阳一阴,一升一降,相互为用。因此,李教授常选合谷、内关与之相伍,相得益彰。此法对一过性呃逆、单纯性呃逆效果颇佳,同时对顽固性呃逆患者亦可起到缓气降逆作用。
2.5 调畅情志 呃逆常伴胸膈痞满、胃脘胀闷、情志郁结等症状,此为气机不调所致。“忧思则气结”,思虑太过,最易伤脾,脾胃既伤,脾气运化失司,气机失调,呃逆愈甚。《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怒伤肝”“思伤脾”,但“喜胜忧”,说明情志可致病,也可治病。李教授治疗肝郁气滞型呃逆时,常配伍使用郁金、醋香附、合欢花等解郁调气,嘱患者放松心情,调节好心态,与人积极沟通,也建议家属营造愉快轻松的生活氛围,此所谓“以情胜情”法。
3 典型病例
李某,男,35岁。2017-03-25初诊。主诉:反复呃逆1年余。患者1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呃逆、嗳气频作,餐后甚。自觉胸中气逆上冲咽喉,时反酸,胃脘时有胀闷不适。平素多熬夜,嗜食酸辣。刻诊:口苦,口干欲饮,两胁痞闷,乏力气短,五心烦热,汗多,寐可,纳欠佳。大便偏干,每日1行,小便调。舌红,苔少,脉弦数。西医诊断:浅表性胃炎伴胆汁反流。中医诊断:呃逆。证属胃气阴不足,虚火上逆。治宜益气养阴和胃,调气降逆止呃。方用生脉散合调气降逆汤加减。药物组成:太子参20 g,麦冬15 g,五味子10 g,海螵蛸15 g,柴胡10 g,升麻6 g,淡豆豉15 g,木香6 g,砂仁(后下)6 g,厚朴15 g,丁香3 g,柿蒂30 g,赭石30 g,甘草6 g。日1剂,水煎2次取汁300 mL,分早、晚2次服,服用7剂。同时取双侧攒竹、鱼腰、太冲行点按手法,共点按30 min,每日3次。嘱饮食有度,调畅情志。2017-04-01二诊,患者诉服药3 d后,呃逆基本消失,口干欲饮、五心烦热亦减,惟觉胸胁满闷不舒,初诊方去丁香、柿蒂,加旋覆花15 g、白芍25 g、沙参15 g、川楝子10 g,服15剂,病愈。
按:本例患者胸中气逆上冲咽喉,时反酸,胃脘时有胀闷不适,平素多熬夜,嗜食酸辣,导致阴液不足,无以滋养肝络,肝气横逆犯及胃腑,胃失和降发为呃逆,此所谓“胃汁竭,肝气逆”[10]。李教授尤重舌诊,患者舌红,苔少,脉弦数,其因为夜不得寐则伤肝阴、耗肝血,久嗜酸辣则生内热,内热郁久则伤胃之气阴,所谓津血同源,而肝血愈耗、阴液愈亏,肝络失养,则见口苦口干、两胁痞满不舒;胃之气阴亏虚,则见乏力气短、五心烦热、口苦口干、舌红苔少之象。四诊合参,此为胃伤阴虚,阴液不足,木挟相火直冲清道而上,造成虚火上逆。故治疗以益气养阴和胃、调气降逆止呃为法。李教授效仿张锡纯益胃养阴法,取太子参、麦冬以益气生阴为本;用五味子酸涩之品养肝荣阴,以充养肝络为次;海螵蛸、砂仁、木香、厚朴以制酸理气和胃;辅之柴胡、升麻、淡豆豉疏肝发郁调气,丁香、柿蒂、赭石降逆调气,甘草调和诸药。诸药相伍,共奏益胃生津、降逆止呃之效。太冲为足厥阴肝经之原穴,常用于平肝胃之逆气,取“上病下治”之意,配攒竹引气血下行。攒竹、鱼腰为治疗呃逆、嗳气经验用穴,点按二穴收降逆平冲之功,助理气和胃之效。同时嘱患者治疗期间尽量保持情志畅达,此所谓“以情胜情”法,使脾胃气机升降有序。二诊时患者呃逆基本消失,故去降逆力强之丁香、柿蒂,加药性趋下之旋覆花兼收余功;其余诸症好转,惟觉胸胁仍有满闷不舒,加白芍、沙参、川楝子以疏理胸胁气机,固补阴液。继进15剂,病愈。
4 结 语
李教授对呃逆辨治精要,注重辨证与辨病结合,尤重舌诊,以舌象和病症辨方药,结合穴位点按手法,注重身心同治,协调脾胃气机升降,调理肝脾气血,治病立法以和为贵,创立“调气和中”辨治方法,丰富了呃逆诊治理论。
(指导老师:李桂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