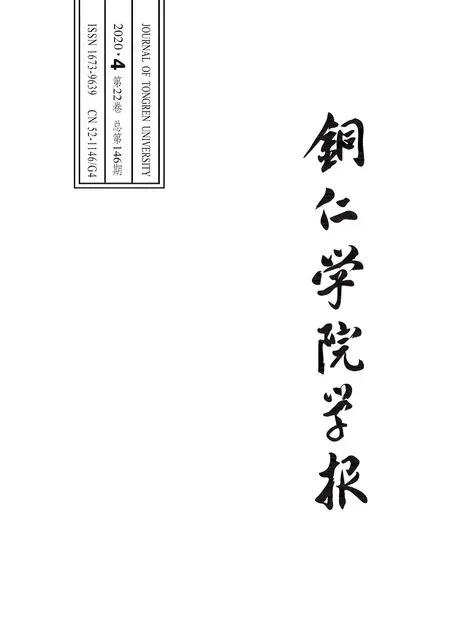沅陵传统龙舟“偷料”习俗探究
2020-01-09李金晖刘冰清
李金晖,刘冰清
沅陵传统龙舟“偷料”习俗探究
李金晖,刘冰清
(三峡大学 民族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偷料”是沅陵传统龙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习俗之一,其缘起与沅陵地区悠久的龙舟竞渡历史、传统的农渔兼作经济背景、丰富的水林自然资源以及当地民众的心理和性格密切相关。“偷料”以“玩”的形式展开,富有娱乐性、开放性和竞争性,发挥着沟通维系、知识教育和生活协调等功能。
“偷料”习俗; 缘起条件; 特征; 功能
沅陵县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湖南省最大的传统龙舟竞赛基地、国家体育总局指定的全国传统龙舟大赛赛场。沅陵传统龙舟赛事是融民俗与竞技为一体的传统游艺体育项目,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偷料”是沅陵传统龙舟文化当中的一项独特习俗,是当地民众在农历四五月间筹备制作龙舟的时间段之内,默许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偷取”各自区域内的树木或木料的活动,且不限制次数、数量和范围。
通常情况下,“偷”都有违道德和法律,不被人们所接纳。但在特定的场景当中,人们会在已经约定的规矩之内默许这一行为。这种被允许的“偷”,也就是“偷俗”,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广泛存在。如武陵山片区土家族至今还保留的偷梁树、偷南瓜、偷狗、偷扫帚等多种“偷俗”;四川凉山地区的“偷矿”;云南迪庆一带的“偷婚”,等等。学界对“偷俗”研究大多将“偷”置入当地文化体系中去理解。如代启福认为凉山彝族的偷矿之“偷”不仅是一项族群内外有别的社会事实,还是一个国家之间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问题[1];訾小刚、赵旭东从产权角度阐释“偷树”行为,指出“偷”与“不偷”背后有着当地人的分类体系[2];陈红将土家族诸多“偷俗”归纳为原始心理遗存和原始思维反映,其“偷”是一种由含有浓厚巫文化因子的人生信仰观念而形成并保存的行为方式[3];彭秀祝则通过对湘西保靖县夕铁村偷梁习俗的考察,认为偷梁中之“偷”事实上确是一种礼物互惠的文化表达和一种特有的社会整合方式[4]。综观这些成果,或对某“偷俗”进行了解释性研究,或对某“偷俗”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以及延伸探析,或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偷”这一行为的原因和观念进行了分析。这无疑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多参考价值。
笔者拟在民俗学视野下,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沅陵县传统龙舟之“偷料”习俗之缘起、特征及功能进行剖析,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偷料”习俗概况
沅陵传统龙舟又俗称为划龙船、扒龙船,是一项集健身、娱乐、竞技于一体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其形成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文化底蕴十分丰富。据了解,当地龙舟竞渡活动时间跨度很大,从农历四月中下旬便开始准备,一直延续到农历五月底六月初。就龙船赛事而言,用当地的话来说,是“半个月准备龙船、半个月赛龙船、半个月谈龙船”。更有甚者,第二年龙舟大赛之前当地民众还会激动地谈论划龙船的经年往事。经过漫长的发展,沅陵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龙船经”,包括“偷料”“关头”“清桡”“赏红”“抢红”“砸船”等一系列习俗[5]。
“偷料”是沅陵“龙船经”众多习俗当中颇让人津津乐道的一种。这种“偷俗”,在沅陵县境内,除了龙舟竞渡文化中的“偷料”外,还存在“偷梁木”的习俗,即当地在建新屋的过程当中,造房者可以不经过树主同意砍他的树木作为梁木。树主不但不会追究,反而还要表示祝贺,以示吉利友好。显然,在这种特定的情景之下,“偷”这一行为是被允许的,和正常法理当中的“偷”是两个概念。“偷料”与“偷梁木”相类似,即在准备制作龙船的时候,通常是农历四月,允许三五成群“偷”制船用的树木或木料。被偷的对象——“料”,主要是指杉木。因为杉木制作的龙舟轻便,可以有效提高船的行驶速度。即谓“船一以杉木为之,取其性轻易划”[6]。一般偷料者在准备龙舟的阶段会先物色要偷的“料”,往往选取粗壮、高大的杉木作为偷取对象,并根据船的大小,来估算所需料的多寡。如果在制作过程当中,所偷木料不足,会继续进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偷”来补充材料,直到龙舟最终制作完整为止。
沅陵流传着“龙船料要偷,十赛赢九头”的俗语。当地人认为买的料笨,偷的料灵,龙船要灵不要笨[7]。因此,迷船的汉子平时就会格外注意较好的树木。到了制作龙船的时节,便成群组队开始“偷料”。据当地人说,“偷料”有“明偷”和“暗偷”之分。“明偷”,顾名思义,就是名目张胆地“偷”。通常是在白天进行,动静很大。除了在砍树前,在树木旁边焚香烧纸祈祷外,还会在砍下树木之后,燃放鞭炮,以提醒树木的主人家。一旦主人家听到鞭炮声,就会来追赶偷料者,并大声“吼骂”他们。而“暗偷”,则是在晚上进行,大多只焚香烧纸不放鞭炮,相对来说动静小一些。倘若被树木的主人家追赶一程并骂上一顿,是偷料者求之不得的。因为偷料者跑在前,失料者追在后,意味着龙船在比赛时也会被别人追着跑,这样就有赢船的把握。
偷料者将木料运回之后,大都会立马请木匠尽早赶制龙船。一是出于安全考虑,怕被别人偷走(有的不怕“偷”来的料被其他人“偷”走,是因为他们可以再度去“偷”别人的,觉得乐在其中);二是“销毁证据”。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赶急造船进行比赛。《沅陵千年龙舟》一书中,就记载了“当夜偷料造新船”的故事:龙船迷杨德全在龙舟竞渡失败后砸烂了龙舟,为了第二天的比赛,组织了很多人员偷料制造新船。一夜之间将龙舟制作完毕,并在次日比赛当中获取胜利[8]。
可见,“偷料”是沅陵传统龙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那么,“偷料”习俗是如何缘起的呢?又有什么特点和功能呢?
二、“偷料”习俗的缘起
民俗的形成并不仅仅由单一的某个因素决定,“一个民族的民俗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心理的、地域的、语言的等因素都有可能决定和影响民俗的产生和发展”[9]。沅陵传统龙舟“偷料”习俗的形成也不例外,其缘起与特定的社会历史、自然条件以及民众心理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一)与传统龙舟竞渡历史及传统经济生计相关
“偷料”习俗与沅陵传统龙舟竞渡的历史紧密相联。龙舟竞渡在沅陵百姓心中是极具地位的一项集体活动,其历史源远流长。《湖南通志》中载“竞渡最早始于武陵”,刘禹锡的《竞渡曲》小序当中有“竞渡始于武陵”之说[10],杨嗣昌《武陵竞渡略》中亦有“竞渡事,本招屈,其始沅湘之间,今洞庭以北武陵为沅,以南长沙为湘也”[6]215,这充分说明武陵地区的竞渡起源很早,发展时间很长。而沅陵地处武陵,有人更是进一步提出传统龙舟运动起源于沅陵,远早于祭祀屈原的龙舟竞渡,还指出屈原在《湘君》《东君》等诗中对沅陵龙舟进行过描写,将龙舟的发祥地、中国龙舟的故乡定于沅陵[11]。《沅陵千年龙舟》一书也提出“沅陵龙舟赛,是旧楚遗风的延续”,“沅陵龙船发源于远古,祭祀的对象是五溪各族共同的始祖盘瓠”,认为龙舟赛是荆楚巫祭习俗的再现,是作为根植于祭祀活动的原始形态以及宗教文化而延续的[8]18-19。而“偷料”习俗作为沅陵传统龙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历史悠久亦然。
同时,“偷料”习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产生与其经济基础有密切联系。据1993年版《沅陵县志》记载,“县内有天然水面19.82万亩,可捕捞水面13.22万亩,其中沅水、酉水干流可捕捞水面10.5万亩”,“民国初期,县内有从事捕鱼业渔船400余艘”,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统计有渔船136艘,捕鱼劳力414人,年捕量65吨[12]。民国十九年《沅陵县志》对于各地渔户的船只数目有明确的记载,最少的也有二十多条船[13]。这说明该地区渔业的发展条件比较完备,舟船作为交通工具的同时也兼具生产工具的效用。而从这些数据当中又能够看出:即使到近现代,当地渔业也颇为盛行。民众在从事渔业的过程当中和水有密切接触,能够对舟船以及江河水有较多认识,这对于龙舟竞渡的发展极为有利。“偷料”作为沅陵“龙船经”的一部分,自然也与此分不开。
又据民国十九年《沅陵县志》记载:“邑中渔户,兼营农业。农时则耕,闲时则渔”[13]147,“乡居之人,莫不有田,莫不自耕”[13]138。1993年版《沅陵县志》记载:“解放前,沅陵县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12]265。依此看来,沅陵地区传统的经济基础主要是以农业为主,渔业为辅,属于农渔兼作的经济模式。这种生计模式互补性比较强,能够避免单一仰赖农业或者渔业,有利于扩大当地民众的活动范围。人们在交替从事农业和渔业的过程当中,密切接触了大山和江河,对周边的自然环境比较熟悉。“偷料”习俗所偷之料主要是山中的杉木,其目的又是制造水中的舟船。这就使得“偷料”习俗的产生成为可能。
无论是久远的历史起源,还是一直以来的农渔兼作经济模式,都使得龙舟竞渡得以充分发展。而“偷料”习俗隶属于龙舟竞渡文化当中,可以说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偷料”习俗的社会基础,为其培育了生长土壤。
(二)与境内广阔水域和丰富的森林资源相关
“任何民俗的源起不可避免地受到生态小环境的影响,而且不少的民俗事象直接导源于当地的生态小环境”[14],沅陵传统龙舟运动的开展也取决于其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沅陵位于东经110°05'31″~111°06'27″,北纬28°04'48″~29°02'26″,地处“五溪”流域,属于亚热带气候,一年季节分明,雨水丰沛,水能资源相当丰富。据1993年版《沅陵县志》记载,有沅水、舒溪、杨溪、荔溪、蓝溪、深溪、朱红溪、怡溪、大宴溪、洞庭溪和夷望溪等流经县境。水系以沅水为主干,呈树枝状,纳大小溪河910条,总长3888.55千米。县境水域总面积23.24万亩[12]94。这广阔的水域为龙舟运动的孕育、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创造出一系列的龙舟文化。一方面,沅水一带的先民因依水相伴、以水为生,创造出了木舟这样的水上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另一方面,也在“水”的背景下衍生出了划龙船之“偷料”“关头”等相关故事和系列活动,通过种种民俗活动直接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同时,沅陵境内丰富的森林资源也为龙舟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形依托。龙舟的制作必定不能缺乏木材。沅陵素有“天然林国”之称,是湖南水电、林业生产基地之一。“偷料”习俗中“偷”的“料”,即沅陵地区的杉木。民国十九年《沅陵县志》记载,“环邑皆山也。岭阜纷错,林壑阻深,诚天然林国也”“林木种类甚繁,其大宗输出者,则以杉、松两种为最;柏木、椿木、梓木次之。”[13]157这些资料反映的虽然是近现代的状况,但是由此也可以反映出历史上的沅陵具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其中,以辰杉(属于黄杉,是杉木当中木质最好的一种)名满天下。据《湖南工业概况及展望·森工》记载,辰杉“树干通直圆满,尖削度小,节少,木质纤维细腻,结构紧密,气味醇香,经水浸泡,全身发红”,其耐腐力很强,“辰杉,在沅陵的产地较广,以兰溪、深溪、明溪和朱红溪的中、上游较为集中,木质也更为优良[15]”。《湖南风物志》中也提道:“其木以生岩石间,心有红晕而锯屑甚香,谓之‘油杉’,最能经久不坏”[16]。除了耐腐蚀的特性之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即民间俗传杉木可以“镇水”,以前扎排、枕、坑木必须以此做底排[17]。而辰杉,正是“偷料”习俗当中“偷”的“料”。
可见,广阔的水域为沅陵龙舟竞渡提供了空间,满足了“偷料”的间接条件;丰富的森林资源,极佳的树木品质,则共同构成了“偷料”习俗的物质基础。
(三)与地方民众的好胜心理和好斗性格相关
“偷料”习俗还与沅陵民众好胜心理和好斗性格有关。沅陵地处湖南西北部,是一个少数民族人口过半县。沅陵人普遍具有湖南人的人文个性。《湖南省志·民俗志》对湖南人的心理性格进行了详细描述,在历代记载当中不难发现“轻剽”“喜斗好讼”“决烈”“尚勇”等字眼[17]20。宏观来看,湖南人具备尚勇好战的性格特点,而沅陵人则更有刚直勇猛的特点。《辰州府志》即载该地“杂以蛮夷,率多劲悍”“辰俗劲直而朴茂”[18]。这种争强好胜的个性在《沅陵千年龙舟》一书中提到的两则故事得以印证:一则是“张大哥”和他的妻子洪氏因为所属龙舟派系不同而产生矛盾;还有一则是李老倌因为自己的“白龙”阵营失败受刺激而病倒[8]69-70。尤其以前者夫妻“反目”故事最能说明问题:龙船迷“张大哥”和妻子洪氏因所属龙舟派系不同而产生矛盾,“张大哥”采取了比较过激的行为,“摔烂了盛满红烧猪蹄的炖钵”,洪氏也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后来经过调和,双方达成协议,即龙舟赛前,夫妻分居,各自归属于自己的派别,等到龙舟赛后,洪氏才能从娘家归来。除了文字记录的此类故事,在田野调查中采录的口述资料也可以作为佐证,如受访者盘古乡荔溪口村朱某说:
龙船分几种颜色,红的、黄的、白的都有。各个地方的龙船颜色都不一样,有的是黄船,有的是红船,都有区别的。老话讲“你站在谁的船上”,就是说你要坚定立场,是黄船阵营就要为黄船尽力,是红船阵营就要全力支持红船。在龙船比赛期间,要是老公是红船这一边,而老婆是黄船那一边,那两口子就要分家!①
可见,即便是夫妻,如果归属的阵营不同,也会因此产生矛盾,从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沅陵人在龙舟竞渡中的争强好胜心理。
也许正是因为好胜好斗,沅陵人才特别重视龙舟竞渡的输赢。据了解,沅陵龙舟竞渡因为输赢产生纠纷,还曾发生斗殴事件,“起初为家庭间的实力赛、荣辱赛,因‘宁输一甲田,不输一年船’的宗族思想作祟,常引起残酷械斗”[8]56。田野调查当中,受访老人——盘古乡双溪村背坡组的刘某这样说:
沅陵的龙船,有红、黄、白、花等多种颜色,我听我父亲讲,在解放前,红船和黄船在扒龙船时常有冲突,会为输赢而发生打架的事情。②
因输赢可以动手打架,胜负在沅陵人心中的地位毋庸置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制造坚固、稳定和轻巧的龙舟是竞渡取得胜利的首要大事。如何制造重量轻、吃水浅、速度快的精良龙舟?至关重要的是选取最适合制作龙舟的材料,而“偷料”习俗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追根溯源,“偷料”习俗的产生,是与沅陵人的好胜心理和好斗性格分不开的。
另外,沅陵民众还具有朴实活泼的性格特点。《辰州府志》即载“其性淳朴,其用俭啬”[18]267。1993年版《沅陵县志》亦载,旧时县内有斗鸡和养鸟两种独具地方特色的游艺民俗[12]615,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沅陵人活泼好玩,开明有趣的性格。那么,突破法理束缚的“偷料”习俗,以“玩”的形式展开,自然也与沅陵人这种性格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沅陵民众争强好胜的心理和好斗活泼的性格,也是生发出“偷料”习俗的重要因素。
三、“偷料”习俗的特征
沅陵传统龙舟“偷料”习俗长期流播,且深受民众喜爱,主要在于“偷料”习俗内在所具备的娱乐性、开放性和竞争性。
(一)娱乐性
从“偷”的字源来看,它有着“愉悦”的意思。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曾对“偷”做过考证:“偷者,愉之俗字……偷盗字古只作愉也。传曰:愉,乐也。笺云:愉读曰偷,犹取也。”[19]就“偷料”习俗来说,“偷”的形式能够让参与者体验到愉悦感。
“偷料”的“玩”味十足,无论是“明偷”还是“暗偷”,偷料者都期盼树主察觉追赶并“骂”上一通。这意味着龙舟在比赛的时候也会被后面的龙舟所追赶,最终取得胜利。“偷料”本就需要一群人团结起来共同进行,再加上这种追赶和“骂”,就格外增添了乐趣,更加热闹。
一般情况下,参与其中的民众都会选择去邻村“偷”。这种跑到他人领地上进行“偷”的行为,比较刺激,也颇有趣味。“明偷”表现出“抢”的意味,当地人活泼豪爽的性格在此过程中充分表现出来。“暗偷”一般是在晚上,一群人夜里偷砍其他村子的树,真切体会去偷的“玩”味。这在日常生活当中根本是不被许可的,但在此特定情景当中却得以轻松实现,无疑增添了调节单一生活的新鲜感。并且,树主追上“骂”,加强了偷料者与树主之间的互动,更进一步增加了群体间的“玩”味。在特定时期,团体行动带来的热闹和乐趣体现出“偷料”的娱乐性。
我参加过三次偷料,记得有一次是到舒溪口去偷,那个时候电杆还是木质的,我们就把准备作电杆的木料给偷了,哈哈哈哈……,后来有人反映到相关部门那里,当查清是被我们偷去做龙船了,也就没有怎么追究了,只是对我们进行了警告。②
受访者盘古乡双溪村背坡组刘某已经70余岁,对于年轻时参加的“偷料”活动念念不忘,讲起当年的经历自然流露出的愉悦之情无不映射出“偷料”的娱乐性。
(二)开放性
“偷料”,各个村的上好树木,都在允许“偷”的范围之内,还不限次数。如果头一次偷的木料不足,还可以进行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偷”,直到龙舟完全做成为止。这种不限范围、不限次数的民俗约定,极大程度上增强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并因此促进了各个村落间的交流。
“偷料”时,“偷”的过程当中也不需要繁琐的仪式,简单开明的规则充满了开放性。盘古乡双溪村背坡组刘某口述的“偷料”经历可以直观地说明这一点:
以前造龙船都是要偷料的。去偷料呢,也不要举行什么仪式,只是提前相约一群愿意参与的年富力强的人去就行了。当然罗,偷料是要踩点的,先要看周边山上有没有合适的木材;如果没有,就跑到更远的地方去偷。不管是哪个村子的,当晓得木料是被偷去造龙船了,都不会去追究的。这都是民风习惯。
我印象中记忆最深的一次偷料,那还是集体的时候,为了造龙船,我们邀了几个人去乡政府林场去偷杉木。那个守林员到乡政府去告我们,偷国家林场的木材,这可是违法的哦。村里干部晓得后,为这件事情伤透了脑筋,跑到乡政府去求情,讲我们是为了造龙船才去偷杉木的,希望从轻处罚我们这些偷料的人。后来,乡政府对我们几个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警告我们下不为例。②
从刘某的口述来看,即便是政府林场的木料,为制龙舟,沅陵人也会冒险,抱着尝试心理大胆地“偷”!而对于这种触犯法律的“偷”的行为,当地政府亦会顾及民风民情,根据实情从轻处罚,予以一定的宽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偷料”习俗的开放性。
(三)竞争性
沅陵境内流传着“宁荒一年田,不输一年船”的说法,当地民众将龙舟竞渡的胜负看得比农业生产还重要,足见胜利在沅陵人心目当中的地位无可取代。与“偷料”共同属于“龙船经”的“砸船”习俗正是输家不愿意接受失败事实的行为表现。所谓“砸船”,是指龙舟竞渡输的一方总会用打碎桡片、砸烂龙舟的过激方式来表示输船不输人。正因为当地民众不能轻易接受失败,又一心求胜,才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胜算。
那么,在获胜的诸多因素当中,质量好的龙舟是不可或缺的,而其前提自然是具备上好的造船材料。沅陵人用“偷”的方式来获取高质量的木材,盘古乡荔溪口村朱某对“偷”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为什么要偷呢?一是好玩,去偷料的人被主人追赶还骂上一顿,大家都觉得很好玩;二是为了获取造龙船最好的木料。因为我们这里流传着“龙船料要偷,十赛赢九头”,认为“偷”来的料更灵一些。确实哦,偷来的木料,都是经过选择的,很多都是粗壮老树,这类木材造出来的船的质量要高一些,就可以增加扒龙船的胜算。说白了,“偷料”深层次的目的还是为了选取好木材来造龙船。①
造龙船的好材料在沅陵人看来,是要“偷”的,所谓“龙船料要偷,十赛赢九头”,“偷”的“料”灵。主要原因在于“偷料”者对“料”的地方比较熟悉,可以在更大范围寻找到制作龙舟的合适树木或者木料。一般是在周边,也有专去林场“偷”的,选择余地比较大。如在交通还不太发达、信息比较闭塞的1957年,时任沅陵县太常乡瓦溪高级农业合作社主任的杨德全竟从朝瓦溪跑到25里外的二酉山林场“偷料”![8]66相对而言,买的料并非一手直接获取,选择范围小,比起“偷”来的木材在质量上肯定稍逊一筹。
另外,在“偷”的过程当中,树的主人追赶偷者,即蕴含着所造龙船也会被追赶,越赶越赢之意。盘古乡荔溪口村陈某说:
追着骂是传统,意思是有人赶,就说明你这个船很好,肯定得赢,实际上就是说比赛的时候船划在前面别人在后面追,越追越快。没得人骂呢,那就差很多,不热闹也没得意思。没人追着骂,心里总感觉差点什么!要是树的主人赶着骂,大家就都高兴,认为获胜的把握就大。所以嘛,这样一来就很好玩,也是继承传统。③
这是当地民众热衷“偷料”的另一原因,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心理暗示,最终赢得龙舟竞渡的胜利。“偷料”既能够保障龙舟材质出众,也可以获得赛前心理暗示,兼顾了现实物质和精神心理两个方面,自然能够大大增加胜算,因此备受青睐。“偷料”的最终目的是获取龙舟竞渡的胜利,这正是其竞争性的体现。
四、“偷料”习俗的功能
“民俗功能的发挥是保证民俗事项传承和流播的基本条件和内在根源”[14]91。沅陵传统龙舟“偷料”习俗所承载的沟通维系、知识教育和生活协调等功能,使该民俗得以传承和流播。
(一)沟通维系功能
“偷料”习俗是地域性的集体活动,《闲话沅陵》一书说:“在众多的龙船经中,‘偷料’是沅陵人独有的。”[7]14从“偷”的对象来看,相对宽泛,“料”既包括山上的自然树木,也包括经过砍伐加工的木料;从“偷”的规矩来看,相比其他“偷俗”,其“偷”的开放性很大,不限数量和范围,并且不需要繁琐的礼仪。“偷料”习俗在众多“偷俗”当中,颇具地方特色,发挥着沟通维系功能。
一是“偷料”习俗,可以实现群体内外的沟通交流。一方面可以在大范围内,使参与“偷料”的民众对合作者以及同地方的成员产生一种地域认同。因为“偷料”大都是“偷”其他地方的“料”,简单点说,可以用“我偷你、你偷他、他偷我”来概括。这就为各个地方之间的接触创造了条件,同时深化了本村的民众对于自己生活地域的认同,对于自己的亲朋邻居产生“自己人”的看法,巩固了彼此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小范围民众间的情感,使生活在同一村落的人在“偷料”过程中加强沟通相互认同。这是因为如果要高效地完成“偷料”活动,参与者在筹划、组织的时候一定要在内部做到沟通顺畅,达成共识。
二是“偷”与“被偷”双方,在“偷”这一活动的联系当中能够拉近关系,在“骂”这一行为中实现了彼此间的特殊交流。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偷料”前的物色准备也扩大了当地民众平时的活动范围,间接加强了交流。“偷料”活动结束之后,又为整个大地区增添了谈论话题,无形中为区域间民众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
要言之,“偷料”习俗能够加强沅陵地区部分社区成员间的沟通,从而保持地方群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20],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表达、交流方式。
(二)知识教育功能
“偷料”习俗还承载着一定的知识教育功能。“偷料”一般包括前期的物色树木和组织人员去“偷”。在此过程当中,参与民众实际上接受了知识教育。单就前期的物色树木来说,就包含有很多学问,如杉木的辨别、大小的估量和路程的计算,这些方面都需要考虑到位。对于物色者而言,要求具备一定的观察和思考能力,事实上也是一种生活知识的教育。
而组织人员去“偷”,作为“偷料”活动的核心部分,对于参与者来说也有诸多教育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和合作能力的教育,二是体能上的锻炼。因为在“偷”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者必须经过商量达成共识,并齐心协力进行“偷”的活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商量,这能够锻炼参与者的组织、沟通和思考能力;行动时的合作,能够让“偷料”团体中的成员在实践中注重具体和实际问题,使得整个团体加强彼此之间的团结。此外,“偷”的过程要求参与者(多半是年轻力壮的中青年)一定要在体能上过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一种体育和劳动技能的锻炼。
简言之,“偷料”习俗的知识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必须学习辨别杉木的知识并具备一定观察能力以及在“偷”的过程当中所具有的团结和实践能力。
(三)生活协调功能
“偷料”所具有的娱乐性特征,体现了其中的生活协调功能。“偷料”以玩乐的形式让参与者实现了身心放松,参与“偷料”的人能够在此之中轻易收获快乐,实现心理放松。
尽管沅陵人娱乐方式众多,但是对于长期劳作者而言,过年过节仍旧是最佳休息娱乐时间。据了解,沅陵大部分地区民众都只过春节、元宵、端午和中秋等传统节日,还有部分地区过“跳香节”。在这诸多节日当中,端午和“跳香”两个节日的娱乐性更为突出。端午主要活动是龙舟竞渡,在整个“龙船经”一系列民俗当中,“偷料”是一项娱乐性极强的民俗。可以说,“偷料”的娱乐性不亚于竞渡。而“跳香”虽是当地民众庆祝丰收的狂欢,相较于龙舟竞渡参与范围要小很多。因此,端午龙舟竞渡是沅陵诸多节日当中,民众觉得最为“好玩”的活动。而“偷料”是整个竞渡活动当中的最为重要且独特的民俗事项。在“偷料”过程当中,参与的民众可以借此机会到新的地界进行探索,既可以享受“偷”的愉悦感也可以体会“抢”的刺激感,并且能够和树木的主人进行交流互动,从而得以身心放松。
可以说,“偷料”这一习俗,使长期在枯燥单调的日常劳动和工作当中的人们,能够有超脱束缚的全新体验,满足了人们娱乐放松的需要。还加强了各地民众彼此之间的联系,发挥其协调人际关系的功能,促进个体与个体、团队与团队间的和谐关系。
五、结语
“偷料”是沅陵龙舟文化当中独具地方特色的习俗,其缘起与传统龙舟竞渡历史及传统经济生计、境内广阔水域和丰富的森林资源、地方民众的好胜心理和好斗性格密切相关。蕴含其中的娱乐性、开放性和竞争性使得当地民众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活动之中,在体验“偷”的愉悦感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群体内部的合作与团结,增强了群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龙舟制作不再沿袭传统方法,“偷料”这一习俗也已日渐式微,但该习俗所呈现出的文化魅力却丝毫未减。有关“偷料”习俗的诸多文化意义的阐释,尚待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 该内容为荔溪口村书记朱某口述,口述时间为2019年7月19日,口述地点为荔溪口村委。
② 该内容为双溪村背坡组村民刘某口述,口述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口述地点为双溪村刘某家中。
③ 该内容为荔溪口村村民陈某口述,口述时间为2019年7月19日,口述地点为荔溪口村陈某家中。
[1] 代启福.“偷”的逻辑:四川凉山G县彝区矿产资源的分割与重置[J].上海大学学报,2017(1):130-140.
[2] 訾小刚,赵旭东.“偷”与林权——以赣南某村落林权状况调查为例[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6):105-118.
[3] 陈红.土家族“偷俗”的文化人类学阐释[J].三峡论坛,2014(6):48-51.
[4] 彭秀祝.盗亦有“道”——湘西土家族“偷梁”习俗的文化逻辑[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4):149-156.
[5] 刘昌林.沅陵历史文化丛书民俗风情[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79.
[6] 梁颂成.杨嗣昌诗文辑注[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215.
[7] 刘健安,石煌远.闲话沅陵[M].北京:长城出版社,2001:15.
[8] 张大强,主编.沅陵千年龙舟[M].2002全国龙舟邀请赛暨湖南沅陵传统龙舟大赛筹委会,2002:66.
[9] 陶立璠.民俗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20.
[10] 杨俊,杜红政.沅陵传统龙舟竞渡的发展[J].湖北体育科技,2016(11):1015-1022.
[11] 金陵,金克剑.中国传统龙舟竞渡从湘西起航[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4):56-58.
[12] 沅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沅陵县志[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302.
[13] 沅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沅陵县志(民国十九年)[M].娄底:湖南省娄底湘中地质印刷厂,1999:147.
[14] 林继富,王丹.解释民俗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9.
[15] 湖南省沅陵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沅陵文史[M].大庸:湖南省大庸市民族彩色印刷厂,1988:230.
[16] 黄本骥,编纂.湖南风物志[M].长沙:岳麓书社,1985:109.
[17] 李跃龙,主编.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26卷民俗志[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168.
[18] 席绍葆,谢鸣谦.辰州府志[M].长沙:岳麓书社.2010:267.
[19]张亚超.“愉”“偷”“媮”考辨[C]//国家教师科研基金管理办公室.国家教师科研专项基金科研成果(六).2017:4.
[20]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4.
Research on the Custom of “Stealing Materials” in Yuanling's Traditional Dragon Boat
LI Jinhui, LIU Binqing
( School of Nationality,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tiy, Yichang 443002, Hubei, China )
"Stealing materials" is one of the unique customs in Yuanling's traditional dragon boat culture. Its origin is related to the long history of dragon boat races in Yuanling area,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background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y, rich natural resources of water and forest, and the psychology and personality of local people. "Stealing materials" is carried out in the form of "playing", which is entertaining, open and competitive, and plays the functions of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life coordination.
the Custom of “Stealing Materials”, dependent condition, feature, function
C953
A
1673-9639 (2020) 04-0077-09
2020-06-12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武陵民族地区多宗教并存现状调查与研究”(19BMZ066)。
李金晖(1996-),男,土家族,湖北宜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遗产学。
刘冰清(1969-),女,苗族,湖南沅陵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遗产学,民间信仰。
(责任编辑 车越川)(责任校对 黎 帅)(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