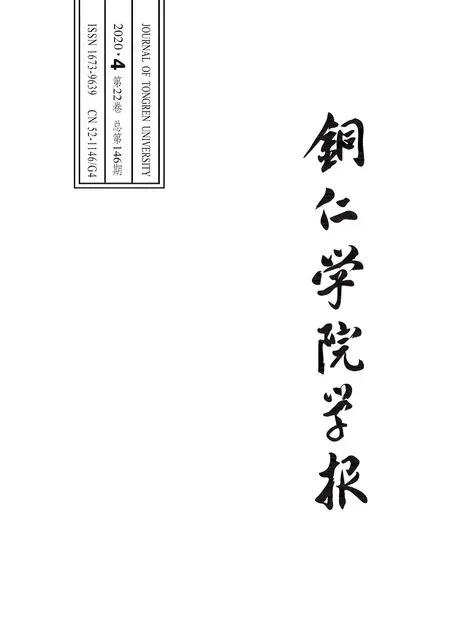论“辞”“赋”意义的递变——兼论学界定义“楚辞”的偏失
2020-09-14冉魏华
冉魏华
论“辞”“赋”意义的递变——兼论学界定义“楚辞”的偏失
冉魏华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辞”的定义经历了讼辞—解说—言辞—文辞等递变的过程。“辞”的“解说”“文辞”之分反映了古代诗歌发生、发展的两个阶段,即口传文学、文人文学阶段。“辞”“赋”兼具“文采”“文辞”等特点,被汉人连称或混用,属同文异题现象,体现出文学在从民间文学转变为文人文学的过程中方法与文体之间的混乱。注重辞、赋的文辞之美是古人的固有观念,黄伯思强调楚辞的地域特色,对于推动楚辞脱离经学的制约具有积极意义,但忽视了楚辞重铺陈、文采的事实。
辞; 言辞; 文辞; 辞赋; 楚辞
当我们讨论“辞”“赋”“楚辞”等概念时,事实上已置于文体学的语境中。考察“辞”“赋”意义的演变过程,对于深入理解“楚辞”定义或有裨益。但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似乎仍存在不尽圆通之处,在此基础上对“楚辞”定义的把握也有偏失,故本文对此试作再探,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1]《汉书·朱买臣传》则称为“楚词”:“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2]2791朱买臣所“言《楚词》”是否包括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有学者曾表示怀疑,但《汉书·地理志下》全面记载了楚辞在汉代的传播情况:“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2]1668两段话都明确提到朱买臣,说明这个“楚辞”确已包括了屈原作品。而且从《史记》《汉书》所载可知,汉人“辞”“词”不分,二者无甚区别。
一、“辞”义由本义到引申义的演变
笔者认为,上述第二义项恰好是我们把握其演变过程的关键。《礼记·表记》:“故仁者之过易辞也。”郑玄注:“辞,犹解说也。”[7]902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颐部》云:“辞,分争辩讼谓之辞。”[8]朱氏所谓“分争辩讼”就是辩解、解说之义。因“辞”有辩解、解说义,古人也有直接以“说”释“辞”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辛部》:“引申之,凡有说以告于人者谓之辞,而辞令之义生焉。以谢于人亦谓之辞,而辞受之义生焉。古通作词。”[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辞,说也。今本说伪讼。《广韵》七之所引不误。今本此说伪为讼,讻字下讼伪为说,其误正同。”[10]742段氏谓“讼”伪为“说”,盖因两者形近而致误,未必合理,但认为“辞”有“说”义,则有其道理,因为辩讼、解说的实质是“说”。《周礼·大祝》谓“大祝掌六祈”,郑玄注:“类、造、禬、禜、攻、说,皆祭名也。……攻、说,则以辞责之”,又引董仲舒救日食时的祭词“炤炤大明”等语解释“说”,[7]439可见,举行祭祀时祷告甚至责之于鬼神之辞即“说”。因此,朱骏声、戴震二氏谓“辞”有“说”义当无疑问。《汉书》载朱买臣“说《春秋》,言《楚词》”,笔者揣之,盖因辞(词)有“说”义,班氏为了避免表达上的重复,不说“言《春秋》,说《楚词》”。
“辞”义为何会从“解说”义转向“言词、文辞”义呢?说即言说、言辞,具有口语化特征。将言说的内容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书面语,就是“文辞”。章太炎先生云:“文辞之称,若从其本以为部署,则辞为口说,文为文字。”[11]77马积高先生云:“争讼必有言语与文辞,故辞又有言辞、文辞之义。”[12]2二氏所说的“口说”“言语”,代表着古代诗歌的发生阶段。在这个阶段,诗、乐、舞结合,兼具娱神、祈雨、祭祀等宗教职能和实用价值,处于解说、言辞阶段。随着记录言语交流的符号——文字(尤其是极具象形特征的汉字)的出现,“文字”之“文”与“言辞”之“辞”组成“文辞”也就势在必然①。这是诗歌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文人参与创作的“文辞”阶段。诗歌发生、发展的这两个阶段经历了集体无意识吟唱、“祝史陈辞”、行人辞令等漫长的历史过程。
“辞”从“解说”转向“文辞”,标志着文学从民间文学转向文人文学,这可从《汉书•艺文志》区别对待《诗》与“赋”得到佐证。《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除“乐”外,其余均称为经(因《乐经》彼时已失传),如“《易经》十二篇”“《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诗经》二十八卷”等。从班固的表述来看,《诗经》实质上可称为《诗古经》,亦即他在《两都赋序》中说的“赋者,古诗之流”的“古诗”。但班固却在“诗赋略”中先列赋,后列诗,赋以屈原赋发端,诗以《高祖歌诗》发端。原因或许在于班氏认为屈原赋实乃文人文学之始,这种观念在后世仍有体现,如《文选》将“赋”排于最前面,之后才是文人诗②。《隋书·经籍志》“集部”也以“楚辞”发端。可见,自辞赋以后,文学进入了文人参与创作的“文辞”阶段。
二、汉人对“辞”“赋”的连称或混用及其原因分析
“辞”从“解说”转向“文辞”,标志着文人文学的到来,但“辞”为何具有“赋”的意义而致汉人混淆不分,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如前所论,“辞”具有“讼辞”“解说”“文辞”等义,与“赋”的意义迥然有异。《说文》:“赋,敛也,从贝武声”,[3]131段注:“《周礼·大宰》:‘以九赋敛财贿。’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与人曰赋。”[10]282又,《说文》:“敛,收也。”[3]68可知,“赋”的本义虽是“敛”,但段氏尤其强调其“班布”义。又,《说文》:“班,分瑞玉”,[3]14段注引《尚书·尧典》:“班瑞于群后”,[10]19即舜将玉圭颁发(班、颁义同)给四方诸侯。颁发时陈列于庭,故“班”有分、铺、陈、列等义。《周礼·春官宗伯下·大师》郑玄注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7]430近人马积高先生说:“知贡赋之赋乃其本义。古时贡赋必陈之于庭,赋、敷、布、铺古同声,韵部亦同,故赋又有铺陈之义。引申之,遂称作诗言志或诵诗述志为赋。”[12]2可见,“辞”与“赋”的意义差别很大,要从语言的源流探究两者之间的关联,似乎很难。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中国古代文献的“同文异题”现象导致的,因此汉人既称“楚辞”或“楚词”,又连称或混用辞、赋。前者如陈广忠先生统计,《史记》称“楚辞”1处,《史记》三家注称“楚辞”5处,称“楚词” 26处,《汉书》称“楚辞”2处,称“楚词”1处,颜师古注称“楚辞”13处,称“楚词”4处。[13]后者如《史记·司马相如传》云“会景帝不好辞赋”,《汉书·地理志》说屈原“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等。这种情况历代均有,甚至近现代仍有使用“楚词”者,如刘师培《楚词考异》、谢无量《楚词新论》等,也仍有称屈辞为赋者,如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刘永济《屈赋通笺》、汤炳正《屈赋新探》等。
“辞”与“赋”属“同文异题”,虽从语源学上难以考辩,但其演变的脉络还是有迹可循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该句中的“辞”当指文辞,即谓宋玉喜好文辞、辞采,故《文心雕龙·时序》篇云“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强调屈、宋的藻彩,而“赋”是文辞的书面表现形式,是一种文体。《报任安书》又云:“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赋”指创作方法,《离骚》为用“赋”这一方法创作而成的作品。《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诵谓之赋”,《王褒传》又说宣帝时“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所谓“不歌而诵”,即不像古《诗》那样可入乐歌唱,而只是诵读之。《周礼·春官宗伯下·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7]424由于辞与赋连称或相混,楚辞也是不歌而诵的,因此宣帝才召九江被公诵读之,这体现出辞赋是文学从集体吟唱的乐歌阶段转向文人独立创作的不入乐阶段的产物。
汉人连称或混用辞、赋,体现出文学在从民间文学转变为文人文学的过程中方法与文体上的混乱。从诗歌发展的进程来看,应是先有一定形式的诗歌,故今传“诗六义”中的“赋”即为诗歌的表现形式。孔颖达《毛诗正义》云:“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14]所谓“诗文之异辞”,即针对其表现形式而言。如前所论,“赋”有铺陈义,由赋(铺陈)这一表现形式逐渐固化而成的创作范式,就是赋体。赋作为汉代的代表性文体,其形式上的本质特点即铺排。
马积高先生在《赋史》中归纳了有关赋的起源的四种说法:“源于诗的不歌而诵”“出于诗的六义之一”“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本于纵横家言”,[12]2后在《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作了一定修正:“古诗之流说”“原本诗、骚,出于战国诸子说”“本于纵横家言说”“源于隐语说”。[15]从文学发展的进程来看,“古诗之流说”当最得要领。但今人钱志熙先生引《毛诗·鄘风·定之方中》叙君子有九能以为大夫之说,以及《国语·周语》中载“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等语,认为“这些都昭示赋并不仅是从六义之‘赋’发展而来,它其实是一种古老的修辞方法,同时在口传文学阶段已成为一种文体之名,为后来的荀卿、宋玉等人所本。汉儒班固等人,从以《诗经》为正宗的文学观念出发,专标赋出于古诗之义,而忽略了赋体自身的古老渊源。”[16]班固虽有以诗律辞(赋)之不足,但有其合理处。钱先生的说法与班固的说法并不矛盾,各有侧重。“赋”作为古《诗》之流,是孔颖达所说的“诗文之异辞”,是诗歌的表现形式之一,亦即钱先生所说的“古老的修辞方法”。用这种“古老的修辞方法”作为主要表现形式创作而成的文体即为赋,它经历了从“方法”到“文体”的漫长过程。这种情况与其他文体的逐渐确立在原理上是一样的。如《尚书·盘庚》:“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曰……”,“矢”逐渐凝固为一种专门的文体,即“誓”。《左传·昭公六年》所载之“书”、《左传·哀公十六年》所载之“诔”,均是如此。吴承学、李冠兰二先生说:“这里的‘矢’、‘书’、‘诔’等,表面看来只是记叙一种行为或言语方式,但本质上是对这些行为或言语方式的认定与称名,体现了古人对于文体的某种集体认同”。[17]“赋”也如此,故《史记·屈原列传》说宋玉等人“好辞而以赋见称”,在《报任安书》里又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屈原以“赋”法创作《离骚》代表着汉人对《离骚》作为赋体的集体认同。
“赋”从古诗的表现形式逐渐凝固为一种写作范式,实现了从方法到文体的转变。如果这个说法能成立的话,那么就可以解释学界的某些困惑了。如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旧本《楚辞》亦题‘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集部之名,盖始此。惟《班志》无《楚辞》,岂以原本《七略》而从略耶?”[18]猜测《七略》原有《楚辞》一书,只是班固沿袭刘歆之法而删掉了。朱东润先生认为刘向集《楚辞》有“六可疑”,其第一条理由是《楚辞》未见录于《汉志》[19]。今人黄灵庚先生说:“朱买臣、九江被公等当年所‘言’、所‘诵’的‘楚辞’,果真是屈、宋辞赋类的作品,则为何在《汉书·艺文志》未别立一‘楚辞’的文体,而统以‘赋’称之?”[20]其实,诸家的疑问并不难理解,第一,如前所述,汉人辞、赋不分,而屈原是楚辞之开创者③,故以屈原赋二十五篇发端,列“赋”就没有必要再列“辞”。且班固之时,“赋”早已是多人实践创作的文体,班固也作赋,故称其为赋;第二,根本原因在于,《汉书·艺文志》中,古《诗》乃六艺之一,而“赋”是古诗之流,因此对于辞赋体,自然以“赋”称之。刘永济先生云:“盖《七略》之作,在明学术源流,屈子之文,刘、班皆以为源于六义之赋,故曰赋也。”[21]刘氏之言可谓确解。部分学者竭力为“刘向集《楚辞》”一说寻找理由,虽不乏合理之处,但仍较牵强,或许正是不明白文体变迁之故。
文辞之“辞”与铺陈之“赋”有何关联而致汉人混用,这是值得深究的重要问题。人类思维的发展遵循着由形象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文学是思维的表现形式,而思维是大脑对概念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联系的符号系统的操作过程[22]。简言之,文学就是经思维制约下的对符号系统的编码与组合。在文字发明之前,这一组合的形式是停留于口头语言层面的传说时期文学,即口传文学(后世流传的上古神话是文字发明以后人们用文字记载的上古时期的口传文学。简言之,上古神话应先于文字而存在)。这种文学的最大弊端在于口耳相传,转瞬即逝,不具有文献保存的意义。文字发明与应用后,其组合的形式就是以文字为载体,兼具形、音、义,形成书面文学。这种文学克服了口传文学只能诉诸口耳的缺陷,具有文献保存、传播的意义。章太炎先生云:“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故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言语司之。及夫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足以成面,故表谱图画之术兴焉,凡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文字司之。”[11]80-81
刘晓明先生认为,中国文学思维经历了单文思维——合文思维——语文思维三个阶段。先秦是中国文学的单文思维阶段,两汉以降直至元以前是中国文学的合文思维阶段,六朝时虽已出现语文思维,但“至元朝方始登大雅之堂,仅仅在刚刚告别的上个世纪才成为文学思维的主流。”[23]刘先生此论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文学思维的演进颇有启发意义。笔者认为,楚辞作为汉代方才见诸史传的先秦文献,也表现出明显的合文思维。以下试以《离骚》首四句为例,划分楚辞的音步: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上述分法,高阳、摄提等名词似乎不能拆分(因为拆分后其意义不甚明显或完整),但其他还可细分,如亦可将“苗裔”“皇考”“孟陬”“贞于”分作两个音步。这种既可分又可不分,恰好体现出合文思维的到来④。又如《九辨》: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为气”“草木”“摇落”“变衰”等词也是可分可不分的。可见,楚辞作品中的复音词不少。这恰好体现出单文思维向合文思维过渡过程中的交叉、混乱情况,与汉代辞、赋混用的情况是同步的。合文思维的出现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就辞赋来说,其最大的影响就是作为“文辞”意义上的“辞”与作为“铺排”意义上的“赋”逐渐合流为“辞赋”,较之《诗经》具有了更多“辞采”的因素。朱光潜先生云:“诗所以必流于赋者,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观察,渐由粗要以至于精微;对于文字的驾驭,渐由敛肃以至于放肆。”[24]这是符合诗歌的发展规律的。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蒍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25]
刘勰认为赋的首要特点是铺摛文采。楚辞之前,虽有“大隧”“狐裘”之篇,但只是“结言短韵,词自己作”,实质上仅是赋之表现手法而已,故“虽合赋体,明而未融。”所谓“受命于诗人”,即发源于作为表现形式的“六义”之“赋”;“拓宇于楚辞”,即楚辞改变了古《诗》的朴质形态,而拓展了诗歌讲究辞采、藻饰的特征。刘勰所云虽不乏宗经色彩,但与班固“古诗之流”“雅颂之流亚”之说正相符合,道出了赋最真实的本源。
章太炎先生云:
《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然言赋者,多本屈原。汉世自贾生《惜誓》上接《楚辞》……淮南、东方朔、刘向之伦,未有出屈、宋、唐、景外者也。[11]128
章氏准确把握了楚辞与汉赋在“古诗之流”这一发展脉络上的上、下游关系,辞为上游,赋为下游,而其总的源头是《诗》。可以看出:辞即赋,赋即铺,铺即摛,铺摛者何?文采也。扬雄《法言·吾子》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26]不管是主张诗人之赋雅有典则,还是批评辞人之赋言过其实,“丽”是其首要特征,铺摛文采是其创作手段。刘安评价屈原及《楚辞》“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班固虽认为这个评价“过矣”,但仍然肯定楚辞“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楚辞》“弘博丽雅”的特点,是辞赋脱离朴质形态走向注重铺排与藻彩导致的。
三、古人对辞、赋特征的固有观念
汉人注重辞赋的铺陈文采、繁辞丽藻,在后代的文学观念中依然如此。如曹丕《典论·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27]曹丕对“诗赋欲丽”特征的要求正是踵武汉人而来。
皇甫谧《三都赋序》云:
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28]9-10
皇甫谧所谓“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就是描摹物状时穷形尽相,极尽铺陈之能事,与刘勰所谓“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文心雕龙·夸饰》)颇有共通之处,唯其如此,赋才堪称“美丽之文”。这个说法与扬雄、班固、曹丕等人一脉相承。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
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后,情志逾广。[28]23
沈约所谓“义”与皇甫谧所谓“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扬雄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相类,亦即辞赋创作应以《诗》义为准绳,但其谈论屈宋作品时,首先肯定其“英辞润金石”。
《隋书·经籍志》云: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29]
汉人“嘉其文彩”才会“拟之而作”,说明汉人首先看重的是楚辞的文采,这与《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说颇有吻合之处。《时序》篇在论及汉初百余年间的文学创作情况时说:孝惠、文景之时“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武帝时“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总的来说是“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勰说的“祖述《楚辞》”即《隋志》说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
宋人晁补之重编《楚辞》,朱熹因循晁氏做法。朱氏云:
近世晁无咎以其所载不尽古今辞赋之美,因别录《续楚辞》《变离骚》为两书,则凡辞之为骚者已略备矣。[30]258
又云:
晁氏之为此书,固主于辞,而亦不得不兼于义。今因其旧,则其考于辞也宜益精,而择于义也当益严矣。”[30]265
可见晁补之、朱熹等人首先看重的依然是楚辞的“辞采”义。
古人批评辞、赋者甚多,这也反映出他们对辞、赋特征的体认。如扬雄批评“辞人之赋丽以淫”。最著名者当首推挚虞“文章四过”说:
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繁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28]11
挚虞认为“古诗之赋”注重情义,“今之赋”注重事形。以情义为主则言语简省、行文有规可依,而以事形为本则言语固有妥当,但文辞浩漫无常。“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作为“今之赋”的缺点,却是“古诗之赋”不具有的。挚虞所说的“古诗之赋”,即扬雄说的“诗人之赋”,他们都力图让文学回归到注重讽喻、政教等现实功用的儒家诗教上去,因而反对辞赋“铺采摛文”的做法。
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云:
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31]
王勃此论实为对齐梁奇靡文风的反拨,但他正是看到了辞赋的文辞之美,故将“斯文不振”的原因上溯到“屈宋导浇源于前”。古人对辞赋的不同看法,本质上属于文质之争,即“文”可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于经学(质)。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实用理性特征,因而常表现出重质轻文的特点⑤。加之古《诗》作为“六艺”之一被奉上神坛,文学作品一旦表现出文胜质的倾向,便会遭到儒家经义的批判与反拨。这种观念直接影响到近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从传统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后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认识。
四、学界定义“楚辞”的偏失
认为辞赋具有“丽雅”“铺排”等特点,几乎代表着中国古代人们对辞赋的共识,但宋人黄伯思是一个例外。目前学界(如多部文学史著作)解释“楚辞”时,常援用黄伯思“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诸语。事实上,黄伯思这段话较为片面。为准确理解黄氏观点,现将其《东观余论·挍定楚词序》摘录于下:
楚词虽肇于楚,而其目盖始于汉世。然屈宋之文,与后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陈说之以为惟屈原所著,则谓之《离骚》,后人效而继之,则曰楚辞,非也。自汉以还,文师词宗,慕其轨躅,摛华竞秀,而识其体要者亦寡。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苹、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汉以还,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概。而近世文士,但赋其体,韵其语,言杂燕、粤,事兼夷、夏,而亦谓之楚辞,失其指矣。[32]
可以看出,黄伯思的目的是批评陈说之以屈原所作为《离骚》、后世拟作为“楚辞”的做法。历史地看,陈说之的做法虽不尽全对,但也有其合理之处。《汉书·地理志》云:“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以“离骚”二字统摄屈作。郭璞注《尔雅》时曾三次引屈作。《尔雅》:“正月为陬”,郭注:“《离骚》云‘摄提贞于孟陬’。”[7]902《尔雅》:“暴雨谓之涷”,郭注:“《离骚》云:‘令瓢风兮先驱,使涷雨兮洒尘’是也。”[7]1645《尔雅》:“蜺为挈贰”,郭注:“蜺,雌虹也,见《离骚》。挈贰,其别名,见《尸子》。”[7]1645均用“离骚”指称《楚辞》。刘勰《文心雕龙》直接以“辨骚”为题讨论楚辞,但事实上讨论了《离骚》以外的作品。《隋志》也明确说屈原“著《离骚》八篇”,可见古人以“离骚”指代《楚辞》是渊源有自的。按照黄伯思的叙述,陈说之的不足在于将后人依仿者称为《楚辞》,而将屈原所著单列于《楚辞》之外。汤炳正先生曾将《楚辞》的成书分为五个阶段[33],其分法虽有猜测的成分⑥,但认为《楚辞》分阶段成书,却堪称卓识,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因此,不能以静态的《楚辞》观念将后人拟作称为“楚辞”而将屈作排斥在“楚辞”之外。
黄伯思看到了文师词宗“慕其轨躅,摛华竞秀”的合理性,但又认为自汉以来“识其体要者亦寡”。事实上,文师词宗的观念与黄氏所云并不矛盾:自汉以来的文师词宗看重的是楚辞的辞采,代表着古人的一贯观念。黄氏从“楚”字着眼,强调楚辞的地域文化色彩,较之班固、王逸、刘勰等人经学观念制约下以诗解骚确是一大进步,但却忽视了楚辞重铺陈、讲文采的本色之美⑦。
五、余论
楚辞之“辞”经历了“讼辞”——“解说”——“言辞”——“文辞”等演变过程,而“解说”“文辞”之分正反映了古代诗歌发生、发展的两个阶段,即口传文学、文人文学两个阶段。文辞因具有描摹、修辞、辞采等特征,故汉人称楚辞为“辞”,而不称为诗。“赋”作为古诗之流,是诗之用,其本义即“铺”。铺者,陈也;陈者,阵也,列也。铺陈者何?文采也,故刘勰说“铺采摛文”。“辞”“赋”具有“文采”“文辞”的共同特征,故汉人辞、赋连称或混用,体现出文人文学诞生之初方法与文体之间的混乱。古人充分认识到辞、赋的文辞之美,部分论家对辞赋尤其是对汉赋持批评态度,恰好体现出辞赋的形式、辞藻之美。黄伯思强调楚辞的地域文化色彩,对于推动“诗骚相承”到“诗骚相别”的转变具有积极意义,但其明显忽视了楚辞本身重铺陈、讲文采的特点。今人研究楚辞,需综合考察古人固有的辞赋观念和黄伯思“因楚言楚”之优点,方能更加准确地把握“楚辞”的定义。
注释:
① 细分之,“文”与“字”仍有区别。许慎《说文解字序》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盖,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简言之,“文”盖指独体字,“字”盖指合体字。“文”处于初级阶段,“字”处于高级阶段。由于“文”处于初级阶段,故与“辞”组合成“文辞”,而不是处于高级阶段的“字”与“辞”组合成“字辞”。笔者此说未必合理,望学界商榷之。
②《文选》别立骚、赋两体的做法历来为人所不解。笔者认为,原因或在于后人误以王逸所辑《楚辞章句》是包含了宋玉及汉人的总集。事实上,据《隋志》以及王逸注楚辞的情况可知王逸所注《楚辞》原本只是屈原之别集,不可能是总集。萧统编《文选》时《楚辞》很可能仍是别集,而《楚辞》总集本应在梁陈之际(大约顾野王时)方才出现,从郭璞注《山海经》引《楚辞》时常称《离骚》等文献来看,古人常以《离骚》指代《楚辞》,因此萧统自然将辞与赋分家,笔者对此将另文探讨。
③《隋志》云:“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作者,起也,始也。《易•乾卦》:“圣人作而万物覩。”以近代人眼光观之,屈原未必是楚辞的开创者,如胡适认为《九歌》远在屈原之前,是湘江民族的祭歌。但这不代表古人观念,在古人观念中,屈原几乎等同于楚辞。
④ 按:《离骚》等文献存在着明显的合文思维,结合楚辞在汉代的流传情况以及班固《离骚序》等,可证《离骚》经历了先秦时期屈原初创、汉代刘安等人增损改易的动态过程。拙文《试论民国时期科学与人生的疏离与对峙——以闻一多参与屈原论争的情况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曾讨论《离骚》的生成过程。
⑤ 孔子虽主张“文质彬彬”“尽善尽美”,但后世儒家多表现出重质轻文的态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却非常明显。
⑥ 如汤先生猜测宋玉曾将屈原《离骚》和他自己的《九辩》辑录成集,此为楚辞成书的第一阶段,但找不到任何支撑材料,故流于臆测,且历史上多有主张《九辩》乃屈原作品者。
⑦ 诚然,地域特征有助于楚辞“美丽”的形成(即“江山之助”),但黄伯思强调的是自汉以来的文师辞宗“识其体要者亦寡”,亦有其片面之处。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43.
[2]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六卷[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4043-4044.
[5] 汤炳正.渊研楼屈学存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79.
[6] 洪兴祖,撰.黄灵庚,点校.楚辞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09.
[7] 上海书店出版社.十三经[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8]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M].武汉: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1983:166.
[9] 徐灏.说文解字注笺[M]//陈建华,曹淳亮,主编.广州大典•第二十五辑•经部小学类:第三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683-684.
[10]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11] 章炳麟.国故论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2] 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3] 陈广忠.“辞”非文体论:与褚斌杰先生商榷[J].学术界,2011(4):113.
[14]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566.
[15] 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8.
[16] 钱志熙.论辞与赋——从文体渊源与文学方法两方面着眼[J].文艺理论研究,2014(2):58-59.
[17] 吴承学,李冠兰.命篇与命体——兼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发生[J].中国社会科学,2015(1):163.
[18]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69.
[19] 朱东润.楚歌及楚辞[M]//作家出版社编辑部.楚辞研究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366.
[20] 黄灵庚.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辨[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3.
[21] 刘永济.屈赋通笺•笺赋馀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7:3.
[22] 蔡俊生.人类思维的发生和幻想思维形式[J].中国社会科学,1997(1):49.
[23] 刘晓明.“语”“文”的离合与中国文学思维特征的演进[J].中国社会科学,2002(1):182-189.
[24] 朱光潜.诗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56.
[25]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34.
[26]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49.
[27] 魏宏灿.曹丕集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313.
[28] 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29] 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055-1066.
[30] 朱熹,撰.黄灵庚,点校.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31] 王政,沈泓,选注.王勃文铣[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107-108.
[32] 黄伯思.新校楚辞序[M]//李诚,熊良智.楚辞评论集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139.
[33] 汤炳正.屈赋新探[M].济南:齐鲁书社,1984:92-106.
The Gradual Change of the Meaning of "Ci" and "Fu":On the Deviation of the Academic Definition of "Chu Ci"
RAN Weihua
(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Duyun 558000, Guizhou, China )
The definition of "Ci"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change from litigation-explanation-speech-literary speec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xplanation of Ci" and "literary speech" reflects the two stages of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poetry, namely, oral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literature. "Ci" and "Fu"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ry talent" and "dictation", which are used consecutively or mixedly by the Han people. They belong to the phenomenon of different topics in the same text, reflecting the confusion of the methods and the styles of literature changing from folk literature to literati literature. It is an inherent concept of the ancient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beauty of Ci and Fu. Huang Bosi emphasized the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u Ci, which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Chu Ci to break away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Confucianism, but ignores the fact that Chu Ci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elaboration and literary grace.
Ci, speech, literary speech, Ci and Fu, Chu ci
I206.2
A
1673-9639 (2020) 04-0102-09
2020-05-27
冉魏华(1982-),男,土家族,贵州德江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楚辞学,近现代学术史。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肖 峰)(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