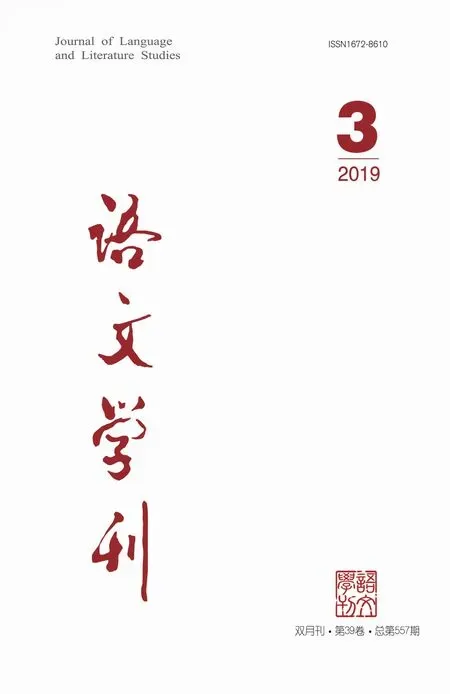从威廉·戈尔丁《蝇王》看社会秩序的重建
2019-03-05蒋华娟
○蒋华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以其冷峻的目光和深沉的思考探寻人类千百年来相互屠戮的根源,于198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蝇王》(1954)是一本哲理小说,讲述未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故事。一场核战后,一群六至十二岁的儿童在撤退途中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一开始还能和睦相处,后来由于恶的本性不断膨胀,最终把乐园变成了屠场。[1](译本序)3小说以血的场景触动人的灵魂,设置了善与恶、罪与罚、理性与兽性、文明与野蛮、秩序与混乱等一系列矛盾冲突,令人信服地展现出文明的脆弱、人性的险恶,并怀着一丝希望探讨建立社会秩序的可能。
一、文明的陷落
美国人文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在《语言与沉默》一书的序言中描述了文明的悲剧:“我意识到历史学家没有说错,野蛮和政治暴行是人类事务中的流行病,没有时代可以幸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2]《蝇王》通过生存的孤岛刻画赤裸裸的人性,渐进式地展现令人触目惊心的文明陷落过程。
(一)无处不在的歧视
小说中的猪崽子(Piggy)出生低微、充满自卑,他在谈到自己的父母时,脸红得低下头。他自幼失去父亲,可能又遭到母亲遗弃,被开糖果店的姑妈拉扯大。“猪崽子”是别人给他的绰号,他被视为异类,大家嘲讽他为“胖子”,模仿他蠢笨的动作,甚至不让他发言。“有件事总能产生点乐趣,那就是取笑他。”[1]69-70而那些年龄大约六岁的“小家伙们”更是被歧视的对象。“拉尔夫统计自己一派的力量时把小家伙除掉,认为他们不算数,他在危急关头希望‘野兽’拣小家伙吃;而杰克(Jack)则把小家伙称作‘哭包和胆小鬼’,如果被‘野兽’吃掉,那‘真是活该’!”[1](译本序)6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所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只是一句空话。
戈尔丁借此表明即便身为同文同种的人,对较低阶层、弱势群体也充满歧视,更不要说不同族群、不同人种了。
(二)脆弱不堪的文明
戈尔丁笔下的人物并不完美,除了凸显人性的灰色地带,更重要的是质疑所谓的“文明”。《蝇王》中的杰克,一开始拥护文明与规则,后来却用五颜六色的涂料彩绘在自己白皙的皮肤上,以“面具”摆脱身为“文明人”所拥有的“羞耻感和自我意识”[1]68。其他人争相效仿,“拉尔夫还瞥见了其中一个,涂着一道道褐色、黑色和红色的条纹,他判断那是比尔(Bill)。但事实上这不是比尔,拉尔夫想。这是一个野蛮人,他的外貌跟过去的比尔——一个穿着衬衫和短裤的孩子——的形象很难一致起来”[1]214。由于环境的驱使,比尔已经由一个文明人蜕变成不折不扣的野蛮人。而坚守文明底线的拉尔夫,也一直在进行内心痛苦的挣扎,甚至一度产生动摇:“感到迫切地要加入这个发疯似的,但又使人有点安全感的一伙人当中去。”[1]176戈尔丁由此质疑文明的生命力,无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还是拥有高度文明的国家,人的残忍、邪恶与善变都大同小异,文明和野蛮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或许只在一念之间。
(三)社会缺陷的归因
戈尔丁“力图从人的本性上来认识人类社会”[3],因此,他在《蝇王》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如拉尔夫、杰克、猪崽子、西蒙(Si mon)等,几乎都没有特别好、特别坏的性格,而是好坏相间或黑白莫辨。拉尔夫虽然有领导魅力和责任心,但对自己所下的决定过于善变,导致人们认为他反复无常,没有公信力;虽然他坚守文明,但也加入了对西蒙屠杀的狂舞中。杰克是小说里最年长的孩子,还是合唱队的领唱,是岛上唯一有领导经验的孩子,偶尔也能检讨自己的失误,但他却高傲自大、心狠手辣,缺少拉尔夫的魅力与温和。猪崽子拥有聪明的头脑、科学的视野,对于未知事物,比如:鬼魂、超自然力量等,他都认为是无稽之谈,但难免有些故步自封、刚愎自用。至于在小说里,和“蝇王”(恶魔)对话的西蒙,看清了人性,但不会表述,无法说服众人,最后反而招来杀身之祸。由此可见,所谓的“完美人格”并不存在,人类性格中包含着与生俱来的天然缺陷。而这种人的缺陷必然导致由人组成的社会的缺陷。
二、人性的拷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摧毁了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子孙后代也造成了难以弥合的伤痛。因此,人类开始思考冲突的根源,并反思战争中的暴行,正如戈尔丁所说:“这场战争不同于欧洲历史上所经历过的任何其他战争,它给予我们的启迪不是关于战争本身,或国家政治,或民族主义的弊病,而是有关人的本性。”[4]
(一)内心的邪恶
戈尔丁认为,人类内心的那头野兽(邪恶),始终是造成人与人冲突的主因。虽然在《蝇王》的结尾处,一位军官的出现阻止了岛上的猎杀游戏,并帮助孩子们脱离血腥的猎人头现场,将他们送上巡洋舰,然而,他的巡洋舰却正要去猎取敌人的性命。这样的情节安排,戈尔丁一方面呈现出人类的残忍与年龄是毫无关系的;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一个问题,在《蝇王》中,戈尔丁将人类的战争、冲突、贪婪等状态,指向人内心的邪恶。他将多年来的人生感悟融进小说中,他目睹人类在天性的驱使下,注定要与自我作战,因此痛苦是人类的常态。戈尔丁借助西蒙的话“大概野兽不过是咱们自己”[1]99以及蝇王的话“我就是你的一部分”[1]166,传达出“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的邪恶以及这种邪恶的巨大破坏力。”[5]
(二)无尽的恐惧
然而,这头邪恶之兽是什么呢?根据《蝇王》中的描写,这头野兽在黑夜吞噬孩子们的美梦,一到白天却又无影无踪,不可捉摸、无法言喻,它令岛上的孩子们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一方面是出于对野兽的无知,人类往往将它视为威胁自己的假想敌;另一方面则是害怕自己的生命和所拥有的一切被剥夺,正如杰克在小说中说的:“你会感到好像不是你在打猎,而是——你在被谁猎捕;在丛林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跟着你。”[1]56看似肆无忌惮的杰克也被一声鸟叫吓得“倒抽一口冷气,缩作一团”[1]51。而较为无知的小家伙们莫名“感受到黑暗中的难以言传的种种恐怖”[1]63。可见“恐惧”始终来自人类本身,戈尔丁通过塑造蝇王,尝试表达“别梦想野兽会是你们可以捕捉和杀死的东西!”[1]166当孩子们讨论野兽到底是什么时,戈尔丁描述了拉尔夫心中的疑惑:“咱们开始得好好的;那时咱们很快活。可后来……他想起小野兽、蛇、火堆……”[1]90而相信科学的猪崽子则一语道破了天机:“除非咱们害怕的是人。”[1]93由于众人的恐惧,导致拉尔夫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使原本就觊觎其位的杰克,得以借助猎杀动物、献祭食物等行动安抚众人,并趁机篡夺了领导权。
(三)疯狂的暴力
“因为急于消除内心的恐惧,孩子们迫切希望自己强大起来,但在远离文明世界的荒岛上,这种对自身强大力量的追求蜕化为对武力、杀戮的崇尚。”[6]
小说中的屠杀、伤害比比皆是,如杰克、罗杰(Roger)虐待同伴、砸死猪崽子、追杀拉尔夫等。我们从西蒙的死,可以看到这个唯一能揭开“野兽”秘密的人是如何被当成“野兽”残忍杀害的:“一条条木棒揍下去,重新围成一个圈圈的孩子们的嘴发出嘎吱嘎吱咬嚼的声音和尖叫声。……他们从岩石上涌下去,跳到‘野兽’身上,叫着、打着、咬着、撕着。”[1]177
戈尔丁曾经说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参加战争的过程中,看到声称同为手足的人们相互残杀。也亲耳听到曾是纳粹成员的人们,在战后反过来批评纳粹的血腥。[7]35甚至在二战结束后,英国人庆幸自己并不像德国纳粹是“邪恶”的一方,但实质上,如果回顾一下英国的殖民史,其残忍与血腥程度并不在德国纳粹之下。
三、社会秩序建立的可能
“戈尔丁对人性的这种基本估价,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为大背景的。”[8]人性的缺陷使掌握权力的人变得非常危险,防止滥权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对掌握权力的人,通过内在的道德培养,达到所谓的完美人格以净化权力。二是寻求制度上的防范,通过分权制衡或者避免权力过度集中,以防止暴政或者专制。第一条途径是中国传统儒家及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理想国》(The Republic)所采取的方法;第二条途径源于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以美国宪政制度为代表。对于第一点,若从“人性恶”角度出发,人根本不可能达到所谓“完美人格”,也就不可能因此而“净化权力”,因此第一点很难行得通。对于第二点,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Ja mes Madison,1751-1836)认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9]一方面表明人类的利害冲突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则提供了一种通过强制力建立社会秩序的可能。戈尔丁在《蝇王》中,借蝇王(邪恶)与主角的对话,提醒人类必须正视人性的阴暗面,并时时对抗那些无处不在的罪恶,因为这些阴暗面,导致了人类的冲突和仇恨。然而,在这样的假定下,戈尔丁如何看待社会秩序的建立?
(一)权威的建立
海螺,在小说中是拉尔夫用来召唤孩子们集合、开会的,可以看作秩序的象征。海螺的外表有着细致的花纹,吹出来刺耳的声音可以穿透杂乱无章的林海,使许多动物惊起、奔跑。在岛上,它的主要功能是召集众人开会,如果想在会上发言,必须像在“学校”一样举手并拿着海螺。因此,海螺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社会规范”的作用。所谓社会规范,是指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内容,目的是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包括风俗习惯、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社团章程、法律规范等。换句话说,如果海螺被看作岛上众人愿意服从的准则,其价值是通过岛上每一个人的认可而确立的。但是,根据戈尔丁的描述,海螺之所以让众人接受,“一来因为是拉尔夫吹的;二来是因为他们喜欢聚在一起”[1]64。然而,这将引申出以下问题:人们为什么因为海螺是拉尔夫吹的就选择服从拉尔夫?为什么将拉尔夫与权威的大人相提并论?人们把聚会当成娱乐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什么影响?首先必须从拉尔夫如何获得权威谈起。
戈尔丁在《蝇王》中以“权威的大人”,描述儿童与大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大人(父母、老师等)出于儿童对公平、正义、法律的无知而通过言传身教使之愿意遵守;另一方面,规范、准则之所以行之有效,不可能完全依赖孩子们的自觉遵守,必须辅以一定的奖惩措施。那么,拉尔夫是如何建立其“权威”的呢?政治学认为,权威是一种“正当的权力”或者说“极具公众影响力的威望”。从《蝇王》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权威,是指对小孩行为有影响力的人。如,“珀西佛尔(Percival)因一只眼睛弄进沙子呜呜地哭了,莫里斯(Maurice)赶忙走开。以前莫里斯曾因把沙子弄进一个小孩的眼睛而受过惩罚。眼下,尽管不会有爸爸或妈妈来严厉地教训他,莫里斯仍感到做了错事而忐忑不安。”[1]64-65
显然,拉尔夫并非大人,其权威和影响力如何获得?回顾小说内容,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在孩子们当中,拉尔夫年龄较大,其他年龄较小的孩子容易将“大人”的想象,诸如:认为大人懂事、不怕黑暗、会造一条船、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等[1]104,投射到拉尔夫身上,因而自愿服从。
第二,拉尔夫所具有的某种特质。“拉尔夫坐在那里,身上有着某种镇定自若的风度,与众不同:他有那样的身材,外貌也很吸引人;而最最说不清的,或许也是最强有力的,那就是海螺。他是吹过海螺的人……他就是跟大家不同。”[1]19-20
第三,拉尔夫善于演说,给人以得救的希望。“‘咱们要得救,当然咱们会得救。’……给大家带来了光明和欢乐。”[1]38
第四,选举程序。戈尔丁在《蝇王》的第一章就交代了拉尔夫是“众人选举”出的领袖。在政治学中,选举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基本形式,也是领导权力正当性的来源和解决冲突的有效机制。《蝇王》中,众人通过选举将部分决定权托付给领袖拉尔夫,使其具有行使权力的正当性,一方面可以通过权力解决纷争,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他的领导获得救援。
(二)秩序的瓦解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支配的类型》中指出:“支配是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的(或所有的)命令的可能性,可能会基于非常不同的服从动机:由最单纯的习惯性服从,到最纯粹理性的利益计算。被支配者对卡理斯玛之承认是由被支配者自由给予,并由具体事实——起初通常是一项奇迹——来保证。如果领袖无法继续使跟随者受益,他的卡理斯玛支配很可能因此丧失。”[10]
在《蝇王》里,代表秩序的海螺,最后坠落在坚硬的石头上被摔得粉碎,象征着秩序的瓦解。按理说,拉尔夫因为具有“正当性”,可以有效管理岛上的众人,却因为宣称即将得救的希望一再落空,并且无法管控孩子们对于食物、生存和游玩等的欲望,导致领袖地位逐步丧失,戈尔丁在《蝇王》里这样写道:
(拉尔夫)“我敢打赌,要是我现在吹起海螺,他们准跑着过来。你知道,然后咱们就煞有介事地开会……可一开完会,干不了五分钟,他们就东游西荡开了。”[1]53
孩子们之所以选择聚会,并不是理解“开会”“选举”等形式的价值或意义,而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或者从众行为。因此,当会议一结束,大家便一哄而散,对会议中要求在固定的地方方便、轮流看守火堆等规范置若罔闻。更重要的是,拉尔夫的规范毫无约束力,当他抱怨其余的孩子都没有来帮忙时,西蒙提醒他“你是头儿,你训训他们”[1]53。拉尔夫却没有任何作为,继续放任众人的欲望而随意侵犯他人。
此外,虽然拉尔夫一味宣称只要怀抱“得救”的希望,就可以返回到原本美好的生活,却忽略了当下的生存处境。于是,杰克(Jack)在会议上对众人宣布:“拉尔夫不是个猎手。他从没给我们弄来过肉。……拉尔夫只会发号施令,指望别人任他摆布。”[1]145
拉尔夫只在意“火”,因为“火”是获得救援的信号,在苍茫的大海上,这是一种渺茫的希望,与当下的欲望相距甚远。他忽略了人类必须依靠食物才能继续活下去的现实需求,并且不愿面对众人恐惧的“野兽”,一味执着于“得救”却又无法兑现承诺,导致他的话不再有说服力;反观与他争夺领导权的杰克,了解人类在孤岛上的迫切需求,带领众人打猎、获取食物,并辅以恐吓、威胁,使众人纷纷向他靠拢,而拉尔夫的权威逐渐瓦解,造成原有的秩序分崩离析、陷入混乱。
(三)秩序与强制力
一方面,秩序需要强制力。拉尔夫制定的规则毫无约束力,即使破坏了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因此,这些形同一纸空文的规定屡屡被违反。如:发言并未拿着海螺、以大欺小、开会时大声反抗拉尔夫等,这些行为拉尔夫都听之任之,最终导致局面失控、不可收拾。从表面看,这是拉尔夫建立的规范与权威的失败,但如果进行深层次探究,我们可以发现人类的欲望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人类欲望的膨胀和暴力的滋长,将必然导致相互侵犯,仅有制度并不能节制人性的贪婪。因此,如果缺少了强制力,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过度的强制力将导致专制和暴政。虽然强制力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但过度的强制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滥权问题。
《蝇王》表明了人一旦掌握权力,就可能会侵犯、压迫他人。戈尔丁曾指出,尚未落难到荒岛前,杰克生活在一个由成人建立了规范的社会里,并未表现出自身的邪恶,是因为认识到惩罚犯罪的可怕后果,为了融入社会,他必须遵守这些规范。[7]48但流落荒岛后,杰克脱去了文明的外衣,以野蛮的方式从拉尔夫手中夺得领导权。虽然杰克以专制、高压的手段暂时达到秩序的目的,由于缺乏制衡的力量,导致他为所欲为,最后造成恐怖统治。由此可见,不受限制的权力,无论落到什么人手里,迟早都会造成灾难。因此,人类不断在反抗这些统治者、压迫者,旧的统治者被推翻了,新的统治者又开始压迫,又被后来者推翻,如此循环往复了几千年。造成压迫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统治者的好坏,而是这种绝对权力存在的本身,注定了早晚会导致专制和暴政。因此,戈尔丁提出了他的疑虑:虽然社会需要强制性规范以维持秩序,但大多数身处统治阶层的领导,在拥有权力后,往往最终走向杰克一般的残暴。[7]49
上升到国际层面,即使一个国家内部可以通过强制力规范节制人性的缺陷,以维持秩序井然的群体生活,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仍可能因为缺乏更高层次权力的约束,而造成人类本性故态复萌,使国家间陷入冲突与战争。比如二战时期的日本、德国,国内秩序相对稳定,却对邻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当前的美国,利用其政治、军事、经济等优势,动辄绕过联合国对主权国家发起军事打击、经济制裁;肆意践踏世贸组织规则,自私地强调“美国优先”,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挑起对中国、欧盟等的贸易战;蛮横擅闯中国南海,插手台湾问题,极限施压伊朗、朝鲜……在倡导和平与发展的当今世界,美国的种种劣行正是人性恶的典型丑态。
四、危机与希望共存
(一)冲突无法避免
“人性善”者认为人类具有良知与自觉,某些“红线”虽然没有人为划定,但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已深入人心,因此,每个人应理所当然地知道并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违反,就是不正常、不人道的行为。然而,在贪污腐化、世风日下的当今国际社会,尤其是超级大国的巧取豪夺、横行霸道,不禁让我们困惑,是否道德规范真有如此大的约束力?历经战火洗礼的戈尔丁在《蝇王》中描写了孩子们遭受杰克拷打或者杰克下令众人追杀拉尔夫时道德的缺位。按理而言,这些破坏规则、不文明、不人道的行为,理应受到众人的反对而停止,但小说中,在拉尔夫最绝望的时候,道德规范并未适时地发挥作用去制止暴力,而是任由杰克继续追杀他,甚至将暴力演绎到极致,用火烧的方式,将他驱赶以斩尽杀绝。
戈尔丁在《蝇王》中通过拉尔夫的叫喊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哪一个好一些?——是法律和得救好呢?还是打猎和破坏好呢?”[1]211答案不言自明。然而,无论是拉尔夫毫无强制力而放纵孩子们为所欲为,导致冲突不断、一片混乱,还是杰克以暴力、恐惧控制每一个人的行为,以达到所谓的秩序,对于戈尔丁而言,人类几乎无法避免人性所造成的冲突,因为人类在群居生活的过程中,欲望(如财、权、色等)大致相同且不断膨胀,而资源又极为有限,相互争夺成为必然。
(二)希望始终存在
在《蝇王》中,尽管道德规范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人们在面对非人道行为时表现得那样冷漠,但戈尔丁仍未对人类全然感到绝望。他通过绝境中拉尔夫的心理状态表明了他对这种希望的执着:“不。他们不会那么坏。”[1]215一个人,即使被人无情追杀至末路,仍相信人的良知,这正是《蝇王》从弥天黑暗中射出的一道闪电,环境越是黑暗,这道闪电越发显得光亮。
“在人类历史大方向上,先进的社会制度战胜落后的原始制度是不可阻挡的社会历史潮流。”[11]戈尔丁虽然看似否定了人类拥有的道德观,或者根据他参与战争的经验,道德观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效果并不大,但戈尔丁还是想通过《蝇王》告诉人们,“人类应该对自己的同胞投入更多的爱和关怀,当然,也不要忽略人性中所带有的罪恶”。[12]我们从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晚宴上的演讲,可以看到他对这种希望的呼唤:“我要对所有的当权者说:‘止步回头吧!现在就向回走。你们之间的协议不需要聪明机智、周密策划和调动演习。它需要常识,尤其是,一份真心的慷慨。给予!给予!给予!它必将成功,因为它附和了全世界的信仰、赞同和欢欣,而所有的后代们将赞颂你们的姓名。’”
“戈尔丁之所以揭示人性的残暴。是因为他爱人类、希望人类进步。”[13]戈尔丁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使命是医治“人对自我本性的惊人无知”。[1](译本序)6相对于以往的政治哲学著作往往生冷、僵硬地说明人性中的灰色地带,戈尔丁以小说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现人性的贪婪与欲求,更能触动读者的生活经验和切身体会。尽管戈尔丁并未在小说中架设建立社会秩序的宏伟蓝图,也没有直接给出规范权力运行的具体做法,但他却像晨钟暮鼓一样,时刻提醒人们“人无完人”,必须警惕内心的邪恶并设法加以控制,只有这样,人类才可能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