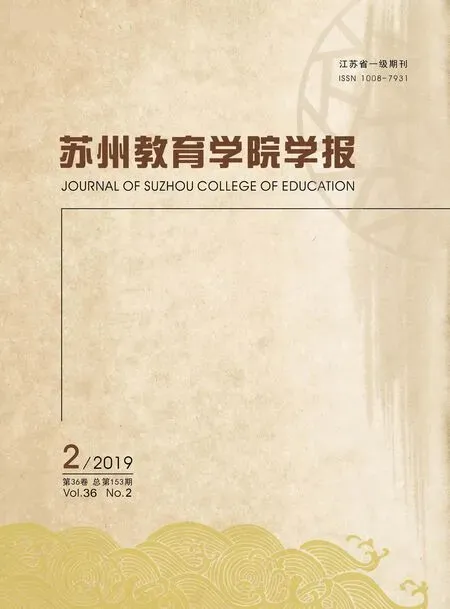黄与坚《愿学斋文集》“书序”类文献价值举隅
2019-02-21陈开林
陈开林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太仓学者黄与坚著有《愿学斋文集》四十卷,内容丰富,极具文献价值。然而,该书因系抄本,流布不广,以致湮没无闻,隐晦不彰,迄今尚未被学界关注。本文以《愿学斋文集》中“书序”类文章为研究对象,对其文献价值略作说明,以便引起进一步的研究。
一、黄与坚及《愿学斋文集》
黄与坚,《清代学者象传》、《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八、《清史列传·文苑传》均有传,《清代学者象传》称:
黄与坚,字庭表,号忍庵,江南太仓人。顺治十六年进士,授知县。康熙十八年,召试博学鸿词,授编修,纂修《明史》。告成后,复命分修《一统志》。二十三年,充贵州乡试正考官,迁赞善。未几,乞病归。先生童年颖悟,诗文过目即记忆。三岁能识字,五岁能诵诗。八岁酷好唐人诗,录小本携之出入,辄为蒙师所禁抑。年十四,慨然有志于古学,欲遍读周秦以下书。甫三年,读周末诸子及六朝以上者几尽。生平究心经术,辑解甚多,《易学阐》其一也①按:朱彝尊《经义考》卷68著录黄与坚《易学阐一》,并录其自序一篇。检《愿学斋文集》卷二五,有《易学阐一自序》两篇,《经义考》所录乃序二。两序题目明言《易学阐一自序》,且序二明言书名“曰《阐一》”,知《清代学者象传》所载书名脱“一”字。。诗词俱工,特其余事。钱遵王叙其诗,谓“《长安》、《金陵杂感》诸篇,顿挫钩锁,缠绵恻怆,风情骨格,在韩致尧、元裕之之间。盱衡抵掌,后来不得不推此贤。久之,学殖益富,才力益老,散华落藻,惊爆都市,梅邨先生叹为知言。”②按:“顿挫钩锁,缠绵恻怆”等语,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六、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八《文苑》、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四二均作钱谦益语。检此语实出《黄庭表忍庵诗序》,载《有学集》卷二十,《清代学者象传》误作钱遵王语。性落落少所合,惟与人交,当生死患难,不渝初志。年七十余卒。所著有《忍庵诗文集》等各若干卷。[1]
而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载:“字庭表。顺治十六年进士,授推官。旋以奏销罣误。康熙十七年应博学鸿词征试,授编修,擢赞善。典贵州乡试。原衔充讲官,以葬亲乞归。与坚工诗,以性情胜。年八十二卒。有《愿学斋集》四十卷。”[2]409与《清代学者象传》所载多有不同。
关于黄与坚的生卒年,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3]据《明清江苏文人年表》,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明末清初卷)[4]据钱仲联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均作1620—1701年。而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载其生于1624年,依据为:“黄与坚《愿学斋文集》卷三十一《张南郭先生知畏堂集序》:‘余年十五为张南郭、张西铭两先生所知,余屏迹未之见。越三年,西铭死,余始哭其墓,因以识南郭。’可知张溥卒时黄与坚十八岁。溥卒于崇祯十四年,逆推十八年当为本年。”[5]《吴梅村年谱》乃据黄与坚之自述立论,可能更接近真实。至于其卒年,或说“年七十余卒”,或说“年八十二卒”,尚不能确知。
关于其著述,秦瀛《己未词科录》卷三记载较为完备,传云:
黄与坚,字庭表,号忍庵,江南太仓人。顺治己亥进士,候选知县,由江宁巡抚慕天颜荐举编修,官至詹事府赞善。著有《大易正解》《易学阐一录》《诸经论说》《月令辑要》《愿学斋集》《太仓州志》《忍庵文集》。[6]
就文集而言,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卷六称:《愿学斋集》四十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内阁文库藏清刻本,为《忍庵集文稿》二十卷;台北“中央”图书馆藏《忍庵集文稿》不分卷,雍正五年(1727)娄东谢浦泰钞本。[7]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七十四册收录《愿学斋文集》四十卷附录一卷,系娄东严瀛抄本。依次为经解四卷、论一卷、议一卷、考一卷、说一卷、策问一卷、志略一卷、赋一卷、表颂一卷、书三卷、记七卷、序十一卷、传诔二卷、墓志铭三卷、碑版行状一卷、题词跋赞一卷,共计三百九十七篇。[8]
二、《愿学斋文集》“书序”类文献价值举隅
就文体而言,《愿学斋文集》中内容最多的是序。从卷二十三到卷三十三,共十二卷,一百零三篇。
其中卷二十三所收文十篇,加之卷二十四第一篇,均为赠序。其余部分均为书序,共九十二篇。这些序文为前修时贤的著述而作,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特别是一些序文,未被所序之书载录,沉埋至今,亟待发掘。兹就已有刊本传世的五种颇为有名的典籍为例①《愿学斋文集》另有一些序文,亦未被所序之书收录,如卷32《金石录补序》。检《丛书集成初编》本《金石录补》,卷首仅有魏禧序、钱嘏序、 叶突苞奕序。,加以说明。
(一)《经义考序》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经以约为要,经义盖详说而反于经者也。诸经自孔子编纂以为教弟子相指授,迄于五六传。周末诸子,诐辞横作,及于秦火。而诸经之毁也,则不于秦而于楚。时非博士所议天下诗书百家语,杂烧之,是秦时经尚存。迨楚烧秦宫室而殆尽,而民间所藏未之或绝也。汉时隶书随出,诸儒证解蜂洒坌集,而经义乃极全。然魏晋以降,古疏不行。至宋而经学大昌,疏复不用。嗟乎!经以秦废之而义始兴,以宋兴之而义始废。废兴之间,亦甚可感已。有宋诸儒,专以圣人意指挈之流俗,务使人人为说,可实践行之,而一切古疏,辄以为其义蹖驳,恣其去取。时以诸经取士,犹率其臆见而高下之,有大经中经小经之别。而领行训诂,观以一时所好尚,驱天下功名之士役,泛然奔走,出其涂而迄于今亦逐,荡然不能复古。悲夫!此太史朱锡鬯先生循观往昔,喟然而叹,有《经义》三百卷之辑也。夫道之大犹海也,海者汪洋浩瀚,莫之纪极,而一勺可尽诸海之变,以一可推万也。若拘于一水,乌足以知沧海之大哉。淹中稷下,笺解繁黟。其后聚徒讲学者,代不乏人。而历宋元明,说以滋众,以经之为道,渊微浩大,故其为说,举古今上下洪纤之数,包括靡遗。若能六通四闢于其间,义疏虽多,而犹莫之能尽也。先生究心于此,发其藏书,汇而辑之。苟义与经焉,虽只字单词,必为掇取,使数百年间异采精光毕观于残编残简之际。非先生博识宏材,为之采择,何以有此巨艺哉。从文才智之士,其抱遗经而矻矻焉竭其心思,欲以一言附不朽者何限。而以观《汉艺文志》、唐《崇文馆书目》,莫传于后者,百无二三,况并其目而堙没者,又不可胜数乎?先生于此,力为搜致,即其书不传,必大标其目,稍稍记载其为人,使观之者知夫穷经之子,虽累劫沉灰,不知磨灭,而后世有所感兴焉。思深哉!先生之所以裨益经教亦大矣。若夫经义之要,博犹约也。王文成有云:“经,常道也。无有弗具,无有弗同,无或变者也。”今先生所撰述已博矣,约不已,在是乎,非穷其变得其常者乎?我知后之学者,其必有省是编而抉微钩奥,反之于道者。虽然,道非余言之所能毕也,故以先生之属序,而仅取先生之所以为兹考者,厓略书其概,而于道弗之详。[9]242-243
按:文载《愿学斋文集》卷二十五。《经义考》共三百卷,朱彝尊(1629—1709)所撰,“通考历代经义”,是经学文献的专科目录,也是辑录体目录的集大成之作。据张宗友《〈经义考〉研究》可知该书版本众多,有初稿本、初刻本、卢见曾补刻本、《四库全书荟要》本、《四库全书》本、汪汝瑮补刻本等[10]4-6。今有林庆彰先生等整理本,名为《经义考新校》,是迄今最为完备的版本。诸本之间时有差异,就卷首而言,出入颇大。《经义考新校》汇录诸版本卷首所载序跋题识,依次为卢见曾序、卢见曾奏状、陈廷敬序、毛奇龄序、朱稻孙识语、卢见曾识语、乾隆御制诗、乾隆上谕、三宝纪文。
此序,诸本《经义考》均未载。文中称“故以先生之属序”,可知乃因朱彝尊“属序”而作。朱彝尊请求黄与坚为《经义考》作序,但刊行的《经义考》又不载此序,其原因不详,有待进一步考究。序中提及《经义考》的撰述缘由,因感于前人经学作品“荡然不能复古”,而“有《经义》三百卷之辑也”,则黄与坚亦认为朱彝尊因“惧经学遗编放失而作”[10]8,与其后的朱稻孙观点一致。
另外,《经义考》卷六十八著录黄与坚《易学阐一》十卷,附载自序,但未介绍其生平。但观此序,可知二人有交谊①按:张宗友《朱彝尊年谱》(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72页)中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末附载“送黄与坚归里”,称“《腾笑集》卷四有《送黄赞善与坚归里四首》”,并附按语,云:“朱则杰《〈曝书亭集〉辨正》据‘谁耐京华久索居,入春我亦返田庐’二句,断其为庚午(1690)复官以前之作,但不能定在何年(《朱彝尊研究》,页160)。故系于此。”后据《清史列传》卷七十、《愿学斋文集》卷前小传,附载黄与坚生平,称其生卒年为1620—1701。其生年,前文已辨。关于朱彝尊此诗作年,据《清代学者象传》黄与坚传“二十三年,充贵州乡试正考官,迁赞善。未几,乞病归”之记载,加之《送黄赞善与坚归里四首》第一首“长店岗头雪正寒”、第二首“梅花人日草堂开”之句,似当系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冬为妥。,阙载其生平殊不可解。
(二)《左传纪事本末序》
古者惟有史而经即具于是,所谓记言记事,皆后世之强名也。周自武成以下至于春秋,为一代之史而编年,则自《春秋》始。时左丘明奉之以为经,虽自为传,仍以年月次于经,本末已具见。若荀悦、袁宏韪戒之不立,徒以汉事冒昧编年,谓之左氏体,皆不知传之有本末者也。夫《春秋》义为大,而其本末则见于事,公、穀二氏传义不传事,叶梦得犹以为义未必当而非之,以《春秋》之义体常合变,不易窥测,而事则人人可以稽覈也。孔子于《春秋》书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丘明亲得其咨承,举列国大小事,该综櫽括,或先经以发之,或后经以补之,不辞繁琐,必期合乎圣人之大指。若其经无与者,则以入外传,而本传弗录焉。故观左氏所书事,可以知列国之所以盛衰。即左氏所书,以经文寻按之,某事书,某事不书,又有以知圣人用心之所至。盖事见而义亦见也。夫《公》、《穀》二传,非汉儒所傅会为经术者乎?然公孙弘用之以绳下、张汤用之以决狱。其深文峻刻,非圣人之所以为教也。故宋傅明良撰《三传纪事本末》,卒以二传牴牾,与经义相蒙晦,岂若一《左传》之能著本末哉?宫詹高澹人先生湛学精思,审其若是,于是为《左氏纪事》一书,以《左》为主,取《外传》、二《传》暨周末诸子附于后,而又条分缕次,大为别白。其残缺者纫缀之,舛错者批补之,乖戾者删削之,繄蔽而不明者次第而剖豁之。而复出之以己见,论断其终始,至以列国各从其类。先王国,次诸侯国,率仿徐得之之《国统》,划疆剖界,皎如列肩。其汇诸家,包括众美,以辅经翼传而有余,诚古今之所莫也。尝考春秋纪事,唐太和中有《分国要略》,宋天禧嘉祐中有纂《列国类纂》,俱以其时经学未兴,著述浅陋,不足以垂后世。今我皇上秉神圣之资,而又圣学日新,以勉厉诸臣,兼以《春秋讲义》风厉海内。先生服习有素,并纂是编,所以扬扢昌时者至矣。宋洪兴祖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言与古所云“事为《春秋》”甚相脗合。今先生即所事事,穷其本末,俾后之学者得以尽心焉,不几于圣教直指津途,予之轨辙哉。某材识弇浅,特以生当盛世,并见先生诠解之精,有裨末学为赞叹,故不揣而次其大略如此。[9]243-244
按:文载《愿学斋文集》卷二十五。《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高士奇(1645—1704)所撰,今有中华书局点校本,卷首有康熙二十九年(1690)韩菼序,未载此序。
关于《左传纪事本末》,《四库全书总目》卷49著录于史部纪事本末类,称“因章冲《左传事类始末》而广之,以列国事迹,分门件系”。[11]四库馆臣认为其是历史著作,代表了主流观点。但黄与坚之序,从经学眼光入手,认为高士奇改编《左传》,并非只是单纯地将其变成纪事本末体,而是通过“辅经翼传”,期“于圣教直指津途,予之轨辙”。这就为深入探究《左传纪事本末》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文中称“宋洪兴祖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实则此语出自《礼记·经解篇》,出现较早,非洪兴祖之说。
(三)《逊志斋集序》
呜呼!此明方正学先生遗集也。先生有志乎古帝王之道,能于千百年治乱,推究本末,灼知其当。建文时,将以生平所学表见于世,而以国难灭族死。先是,姚广孝有言:“孝孺死,读书种子绝矣。”夫所谓种子者,非吾道所谓的传乎?传道之士,旷世一见,而遽歼灭之。其后文皇时,辑《性理》一书,使饾饤诸儒发明载道之故,埇垣昏途,使举世相率而为瞍瞽,所疑误不甚可痛乎?夫圣人之道,举世以为迂阔而莫之行,独先生以为必可行。《周礼》一书,文武周公成宪具在,间尝推举其说,以为孰真孰讹,而确求其义理之所寓,素所模述,皆能养其刚,大以浩然之气,发之于元,畅达而后止。先生之于文也,可谓由中而发外,得其本源矣。文皇于抗节诸臣,备加惨毒,举先生七年之内所以致君泽民者,一旦而反之,至于身既死而尚禁锢其文字。天顺中,始间出,迨其后三四搜,辑集稍具,而后知先生之于道也,体之真,言之切。其求道之志,耿耿不磨,若犹见于斯。呜呼!岂天欲存其道而得戔戔者于水沉未穰之后乎?明初,文以宋濂溪为称首,然濂溪之文纯杂互见。以先生文较之,迥然超出,而况先生之死节,又古今希有乎!夫先生不有其生,何有于文。然而文以见道,先生之所以不死者在乎此。若因其文益以知先生吾道之传,使先生虽死而犹生,则固我等之志也。[9]247
按:文载《愿学斋文集》卷二十五。《逊志斋集》乃方孝孺(1357—1402)之别集。检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知《逊志斋集》有成化本、正德本、嘉靖本、万历本、崇祯本、康熙增刻本等[12]。此序似为康熙年间增刻《逊志斋集》而作。
张常明编注《逊志斋外集》卷一,广搜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刊刻《逊志斋集》时的相关序跋[13],然未及此序。
(四)《日下旧闻序》
余尝至关中,揽秦汉遗迹而有叹也。史言秦据崤函以成帝业,汉有天下亦以三秦为根本。故自故推大势者,必有关中,诸东京以下莫及焉。而余观之,西京地势萦纡窈折,利于固守已耳,图大其可乎?历秦汉隋唐建都于此,遂以百二之说为固然。是以文章之士辄加扬厉,往往过当,而世之论者或未之察也。我国家定鼎于燕,总蔺丘上谷之胜,以临御天下,薄海内外,举骈趋叠,迹萃于兹土,而燕都遂为万古所不建顾。揆之往昔,记载鲜少,即有编辑二三,而义例残缺,无以极古来形势之大。以及典章文物先后之繁黟,余窃惑焉。秀水朱锡鬯先生方闻淹洽,踰于常等,与余同应召,受史职,兼得供奉内廷,览金匮石室之藏。于是蒐辑所见,以类次之,共得四十有二卷,名之曰《日下旧闻》,以示余。因叹曰:嘻!斯非时当极盛而以成巨观欤?夫燕自战国时始闻中国,唐宋中,范阳燕山仅列边陲,金元明缔造都邑,始大建土宇。盖燕国,固天作之以留于后,佑启我国家者也。假令当日知其后有圣人宅于斯,则督亢一图亦将兴龙图,同不朽。乃千百年间,必圣人起而文章以先显,何耶?余以是知平阳蒲坂虽曰帝都,必俟尧舜而始著。此纂述之时,亦累世而一遇,不可以或失也。汉班固张衡诸人摅文绘藻,其得于史氏者为众。今观锡鬯所采择,其言至一千二百种之多,而抽秘聘妍,若为前人所未睹。穷林而伐艺,不尤以见匠者之能乎。陶此囗囗,班张其人者欤?因京师之盛大以颂国家宪中之徽美,必将于兹取材焉。其曰三都两京,当亦有勃然而兴者矣。[9]258-259
按:文载《愿学斋文集》卷二十七。《日下旧闻》,朱彝尊所撰。鲁颖称:“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存两部康熙年间六峰阁藏版所刊《日下旧闻》,每部二十四册,行款、牌记相同,均题有‘朱竹坨太史辑’。不过一书钤有‘竹坨著书之一’阳文印,一书钤‘曝书亭藏’阴文印,此两方印均见于《清仪阁藏名人遗印》,为朱彝尊之印。两书最大的不同在于文前诸序的排列:前者依次是唐梦赉、张鹏、冯溥、徐乾学、王原、陈廷敬、朱彝尊自序、高士奇、姜宸英、徐元文;后者分别为徐乾学、徐元文、张鹏、唐梦赉、高士奇、姜宸英、朱彝尊自序、王原,缺少冯溥和陈廷敬之序,疑为装订之差异。”[13]可知为该书作序之人较多,然刊本未载黄与坚序。上文《经义考序》中研究黄与坚与朱彝尊有交谊,此文中则言二人“同应召,受史职,兼得供奉内廷”,足见交谊之深。
(五)《钱遵王注牧斋诗集序》
余尝乘舟过洞庭,聘望而有叹也,曰:太白之诗其何以说哉?西望楚江与蜀江合,而云“楚江分”;长沙距东南三百里日出所,而云“日落”。是沙是势皆违反也。杜甫之奇李白曰“细论文”,其亦以此类而云然乎?故余尝以为李诗可不注,杜诗不可以不注也。胡宗愈云学士大夫谓杜曰诗史,而以今诸诗家论之,虞山钱牧斋先生其诗史之续乎?少陵所为诗,自天宝至大历,三十余年而止耳。牧斋自神庙以降,党局纷拏,至于盗贼蜂起,宗社虞烂,五十年间,举古今未有之奇遇,志寓于诗,殆千百变而史犹不足以尽之。且吾观先生和苏诸诗,其体格如苏。苏固以史而为诗,未尝不以是而贾福。以是知少陵之后有东坡,东坡之后有牧斋,固诗史之一再传而千百续也。而注诗之难亦在此。钱子遵王之于诗学也,密造深思,稔知其故,乃取先生之诗而训解之,其义该,其事核,其词櫽栝而昭晰,余反覆而观之,喟然曰:嘻!至矣哉!夫昔之注诗者黟矣,注杜诗有千家,若黄鲁直、吕大防犹纰缪屡见;苏注亦不下数十家,若吕伯恭、王龟斋者差称善本,而后人犹不尽以为然。诗注之难如此,而余独于遵王有深信,以为超诣者和耶?盖昔之所以为注者,率臆而为之,或以古割裂而就诗,或以诗改窜而就古,迁就多而凡傅会穿凿以滋甚,皆由鞭前策后,不能相反而妄加控揣之故也。今遵王趋侍于先生者有年,饫闻绪论,疏而录之,如房融笔记,不隔一手,故能一字句皆得之诒承,迥愈于昔人拟议之为,而先生亦以发皇心曲属之遵王也。先生之生平岁概郁纡未发者,得注而发之激烈如石大之夺雷,萧条如霜颺之富叶,而以按之家国之间,则皆文笔也,讵非大观乎?若藏海澜翻,机锋凑泊,较李善之注《头陀寺碑》而犹过之,则尚以为诗人之绪余,不足深论也。嗟乎!先生之冀遵王也深矣远矣。其竞年亘,以此心两两豫照,以故记莂懃拳,有把臂之托者。此中有死生未之磨灭者,是岂他人所能测量哉。即遵王于此,或不能罄沥而书之,而余欲以语言文字少竭其衷藏,恐犹未概百一也。先者,遵王以诗注属余序,余诺之,三年不及为。比复以申请,余笑曰:余之于斯编也,得无如中山之辟千日乎?而今者仿佛言之,亦以为刘元石之乍醒而已矣。[9]261-262
按:文载《愿学斋文集》卷二十七。钱遵王,即钱曾(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园,虞山(今江苏常熟)人。钱谦益(1582—1664)族曾孙,清代著名藏书家,著有《述古堂藏书目》(亦称《述古堂书目》)、《也是园藏书目》、《读书敏求记》等。
钱曾另一贡献,就是注解钱谦益之诗。钱谦益在《复遵王书》中指出自己作诗“于声句之外,颇寓比物托兴之旨。廋辞讔语,往往有之”,因此“居恒妄想,愿得一明眼人,为我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以俟百世”。在看了钱曾之注解后,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今不意近得之于足下”,“今一一为足下拈出,便不值半文钱矣”。[15]这也正如《牧斋遗事》所云:“遵王博学好古,注《初学》、《有学》两集,牧翁深器之,谓能绍其绪云。”[16]
序中对钱曾注牧斋诗之优势、成就多有指陈。但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牧斋杂著》,卿朝晖辑校《牧斋初学集诗注汇校》附录相关序跋多篇,均未收录此文,则黄与坚之序并未附刻于钱集。序中称“遵王以诗注属余序”,则为钱曾委托作序,但后来又未被钱曾收入书中,未知何故。
三、《愿学斋文集》“书序”类文献价值总结
前文条举了黄与坚为五部传世典籍所作序文,现结合其他书序,以便总结《愿学斋文集》中“书序”的文献价值。大体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补充目录之阙失。比如《愿学斋文集》卷二十五有陆翼王《礼记集说辨疑序》[9]245-246、卷二十六有王仲昭《太极图说序》[9]250-251、陶石篑《四书要达讲义序》[9]252、陈挥奇《四书心印序》[9]253,可知有《礼记集说辨疑》《太极图说》《四书要达讲义》《四书心印》诸书,为经学著作。检《经义考》,并未载录这些典籍,可为补充。又如,卷二十七有《朱遥岑先生集杜序》,称“朱遥岑先生负异才,精诗学而酷嗜于少陵……今所集者,累累成帙。读之者以为少陵之句而不知其为遥岑之诗,以为遥岑之诗而又不知其为少陵之句”[9]270,知朱遥岑有《集杜》之作。检《杜集叙录》,未载朱遥岑其人其书,亦可补其阙。
2.增益文学批评史料。《愿学斋文集》中为友人诗集、文集所作之序颇多,集中体现了黄与坚的文学批评思想。比如卷二十四《范羽园寤言堂诗草序》,称:
屈原之文本乎忠孝,其志洁,其情挚,其文瑰……汉魏以降,言诗者率乎本于《离骚》,或咀其精华,或采其菁藻,沿晋而为六季之学。几百年间,诸家杂陈言之,害道者庸有之,或遂以其书为不可读,其说似矣而非也。夫诗,贯道之器也。得其道而性情以疏瀹,志气以发抒,无往而非诗也者。否则,诗虽美,不可以为诗。《诗三百》皆古人之饾饤糟粕也,何有于六季独以其言为訾諆哉?[9]237
序中对《诗经》、屈赋、六朝诗学均有论说,并着重提出了诗乃“贯道之器”的文学主张。《愿学斋文集》卷首有熊赐履、陈廷敬二人所作序,熊序开篇称“文也者,道之著也”,又称黄与坚之文“实有道焉存乎其间”[9]1;陈序则引黄与坚自白,称“始吾为学,因文以见道”[9]2,均可与《范羽园寤言堂诗草序》合观,以见其文学观。
另外,卷二十八有《沈昭于文集序》,篇首提出了“世之为文者,其途有二:行世之文、传世之文而已”[9]266,并对这两种类型进行了详细的区分,这也为文学作品的评价提供了新的视角。
3.把握学术演进历程。比如卷二十五有《经学杂考序》,历叙了经学自“秦火之后”的演进情况,言简意赅,宛如一篇浓缩的经学史。特别是其中提及的汉儒、宋儒治经之特性,如称汉儒“祇于一事一物证据之微末,而不知其所本,是以道逾言而逾不明”,而宋儒“一以理为断,比物丑类”[9]244,可谓洞悉个中三昧,切中肯綮,见解深邃。
4.梳理了一些典籍的相关情况。黄与坚的很多书序是为其友人之书而作,这些书部分已经失传,详情难以确知。而通过其序,一方面可以知晓黄与坚与他们的交往情况,同时,借助序中的记载,可以知道这些典籍的相关情况,比如书名、卷数、编纂过程、刊印情况,以及书之得失,等等。卷二十七有《学文堂史论序》,称“毗陵陈子椒峰著《学文堂史论》成,自庖羲迄明末,得一百五十卷”[9]259,陈椒峰即陈玉璂。检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2]441、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17]等书,在介绍陈玉璂生平著述时,均未提及此书。《清史列传》卷七十一《文苑二》有其传,称“著有《史论》数百卷”[18],不明其实际卷数,可据此序补充。
5.其他方面的文献价值。《愿学斋文集》中还有一些书序比较专门,如卷二十四《吴中开江书序》论吴中水利[9]234、卷二十五《易学阐一自序》论《周易》[9]240-242、卷二十七《太仓州志序》论方志[9]262-263、卷三十二《番禺彭氏家谱序》论彭氏[9]296-297、《蜀郭氏家谱序》论郭氏[9]297-298、《太仓顾氏家谱序》论家谱[9]298-299、《巢松乐府序》论乐府流变[9]300-301,等等,对于了解相关的情形也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最后,对于其他门类的作品的文献价值,亦附带论及。如“经解”类四卷五十三篇,数量颇多,这在文集中是不多见的。针对经书中的相关问题,如《五行说》《洪范五行论》《九畴论》《唐虞历法考》等,为探究当时的经学议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传诔”类二卷十八篇、“墓志铭”类三卷三十篇、“碑版行状”类一卷八篇,也为了解相关人物的生平提供了较为完备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