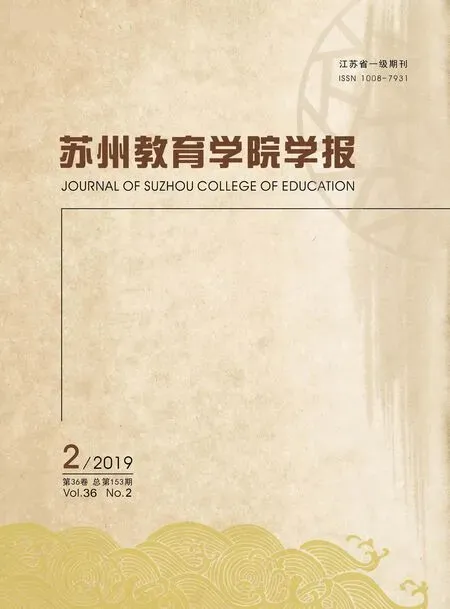日本救世动漫中人物的自我认同与主体意识研究
——以《心理测量者》为例
2019-02-21李梦茹
李梦茹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在日本动漫《心理测量者》描绘的未来中,人类的心理状态和性格倾向都能被数值化,所有的感情、欲望、社会病态心理倾向等全部被西比拉①《心理测量者》中是指一种管理体制。记录并管理。它通过扫描个体的脑电波来计算其心理状态和个性倾向,并对此进行数值化,这类数值统称为“色相”。通过计算色相,西比拉可以自主断定个体的感情、心理压力、犯罪意图,甚至可以断定个体最理想的未来。
一、《心理测量者》中个体的自我确立
常守朱是一名监视官,她是一个天真烂漫、活泼开朗的女性,虽然有时缺乏一些魄力,但自身拥有强烈的正义感。她也是剧中除了“免罪体质”②个体自出生起,无论何种情况下,其色相都处于纯白状态的一类体质。人群之外,极少数能够始终保持自身色相在清澈级别的普通人。狡啮慎也是一执行官,在追查槙岛圣护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西比拉的真相,于是他果断抛弃了西比拉。他的内心有着不同于西比拉的正义所在,为了贯彻自身的正义标准,他不惜背负杀人的罪名,也要制裁槙岛圣护。槙岛圣护是拥有“免罪体质”的人,他当着常守朱的面杀害了她的好友,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常守朱性格、价值观发生了巨大改变。槙岛圣护出场的次数虽然不多,但在剧中,他是推动剧情发展十分重要的人物。
主角的自我定位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建立的:首先,是对西比拉的态度。常守朱并无选择的余地,但也坚信西比拉终将被淘汰,而狡啮慎则成为反抗者,远走海外,与西比拉作最彻底的斗争。其次,保持色相的能力。出色的保持“色相”的能力,是常守朱自我定位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她强韧的保持色相的能力来自于她对法律的忠诚和对正义的坚守。这一特点在槙岛圣护身上经过变奏与延伸之后,就发展成了“免罪体质”。最后,个体生存价值的彰显。常守朱成为一名监视官的初衷也是想要找到只有自己才能完成的生活方式,抛开正义的角度不谈,槙岛圣护的所作所为,是个体作为一个人的主动选择。
二、工具理性语境中个体的自我认同困境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直接的渊源便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的概念。韦伯将理性分成了两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过程从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动,但这种推动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1]
(一)工具理性语境中自我的消解
工具理性是指个体受名利价值观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以达到自身的目的,漠视个体的情感需求和精神价值。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个体对于宗教的需求日渐消失,金钱和物质成了个体驱动的直接动力,工具理性也由此发展到了顶峰。工具理性中最重要的两个特征便是契约性和功利性——契约性即是将个体异化成契约成本或契约规则,忽视契约执行个体的差异性和其主体地位;功利性则是将个体异化成夺取最大利益的工具。
在《心理测量者》中,人类和西比拉签订了一个契约,他们努力保持自身身心健康,改善“色相”,以达到西比拉的标准,以此换来西比拉所安排好的幸福生活。而改善“色相”的代价就是自我的消解,所有能够彰显自我的事物——艺术、情感、欲望以及幻想等——都成了工具理性的他者,在剧中则成了西比拉的他者。“希腊时期对身体最直接、最真实的爱永远成了神话。工具理性把人类还原为一种物质实体,不允许任何情感和神话留存。”[2]西比拉是工具理性发展的极致,在西比拉之下,个体将直面人生的无意义性。
在这种极端的统治形式之下,剧中看似平静的社会,实则弥漫着一种由紧张、期待和压抑交织的紧张的气氛。大部分个体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选择了顺从,在西比拉的牢笼内,个体不需要有自我,只需要理性地维持自身的色相,个体的情感遭到放逐、扭曲,但也有一些逸出常理之外的他者。剧中提到了杰里米·边沁提出的“全景监狱”①边沁于1791年首次倡导眺望塔的塔墙上安有一圈对着环形建筑的大窗户,环形建筑则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圆形监狱,即全景式(敞视式)监狱,它的基本结构是:监狱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间是一座眺望塔。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的眺望塔,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panopticon),并以此来象征西比拉与个体的关系,这种全景监狱在剧中也有相对应的机构。西比拉建立了隔离机构来驯服那些“潜在犯”②西比拉认定的色相值在100~300范围内的具有犯罪倾向的人群。。这些隔离机构通过限制自由以及药物的方式来净化潜在犯的色相,使其符合西比拉的规定。由此可见,西比拉不仅要驯服个体,还要改造个体。这种规训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规范化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的道德力量。“工具理性在意识形态上对现代性扩张,主要通过确立‘自我’中心和‘自我’主导的同化机制的合理性与排斥‘他者’(相异者、否定因素等)的合理性推动现代性对总体世界的分化,推动现代性之‘吞进’与‘吐出’机能的实现。”[3]
潜在犯成了这个世界的“异质”,他们终其一生都在隔离机构中度过。他们或在隔离机构中长时间地将神经激发到最强的反应状态,直至完全停止;或残忍地撕扯着神经,直至精疲力竭。他们的自我在西比拉的统治下,趋向消解,自我认同也陷入难以救赎的困境之中。
(二)现代性的反身性与个体的自我认同困境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反身性”的定义是:“现代性的反身性指的是一种敏感性,具体指社会生活的大多数面向及其与自然的物质关系对受到新信息或知识影响而产生的长时性修正之敏感性。”[4]21
这种自我反身性的敏感性与色相指数息息相关。在《心理测量者》中,除了“免罪体质”者以外,几乎每个个体的“色相”均会因为自身的反身性导致的落差感、负罪感、羞耻感和焦虑感等而有所变化。而常守朱的色相指数之所以能够保持纯白,是因为她身上极少有因现代性的反身性而导致的一些负面情绪,尤其是焦虑感,几乎不曾出现。剧中的个体最常出现的焦虑感便是自身的色相无法满足西比拉的标准,个体渐渐沦为潜在犯,在这个世界中成为他者的存在。这种焦虑感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剧中的个体心中,在西比拉营造的看似幸福自由的社会中,他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这种焦虑感延伸至现代性的反身性的核心部分,便导致了虚无感——一种何为人生,何为灵魂的虚无感。这一核心部分要求个体和社会的变迁双管齐下,一旦个体的变迁与社会的变迁脱节,便会导致自我认同的困境。这一困境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时间经验中的间断性,个体被切断了与传统经验的联系,从而使得自我认同的连续性无法形成,进而陷入自我认同的困境,伴随这种困境而来的还有被摧毁或倾覆的焦虑感。
罗丹认为,艺术具有将个体从生活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能力。但纵观全剧,潜在犯的数量可谓与日俱增,究其原因,乃是他们对于“纯粹运动的艺术永恒性”的沉迷。剧中,艺术被认为具有蛊惑人心的力量,尽管西比拉规定了“官方艺术”,但“地下艺术”仍然难以断绝,它实质上反映了极端不稳定的现代性。“从生活的焦虑和重压下的的艺术解放,不仅通过逃离到它的对立面而实现,而且通过其自身内容最完全的仿效和不断增加的纯度而实现……”[5]但在剧中,个体无法逃离到西比拉的对立面,他们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没有了西比拉,他们将直接面临无休无止的战争。在和平与自我的消亡之间,个体选择了西比拉,选择了和平。
因此,剧中的个体,尤其是潜在犯,大都无法形成并保留自我感,他们甚至不清楚自己来自何处,也不知去往何方。他们是西比拉判定的社会的他者,他们无法吸纳当前社会发生的事情,并将它归入自我之中,也找寻不到与之对立的另一种生活模式与制度。与主角不同,他们的自我趋向消解,在消解中,陷入自我认同的困境。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潜在犯的对比,主角主体性确立的艰难过程,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三、工具理性语境中主体意识的确立
救世动漫主题存在的特殊性,是围绕着拯救世界而展开的。正是因为主题的严肃性,因此尽管动漫中的个体(尤其是主角)面临着自我消解、自我认同的困境,但其最终都会走向主体的崛起和重新确立主体意识的道路。
(一)本体安全感的动摇
与永恒的时间相比,个体永远生活在“存在性矛盾”(existential contradiction)之中。这种存在性矛盾具体表现为:“作为具有自我意识并认识到生命有限性的本质存在,个体乃是无生命世界之一部分,然而却要从这无生命世界中开启自身的生命。”[4]52在西比拉统治的世界中,个体正是因为客观世界的无生命性和永恒性,所以敬畏着这个由工具统治的世界。但是个体若想在这个客观世界生存下去,必须放弃自身人性,只保留工具理性,并希望以此来保持自身色相的纯洁。但是这个社会却依然诞生出了众多的潜在犯,对于他们,西比拉则采取了将其立刻隔离治疗的措施,由此可见,潜在犯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异质”,同时隔离机构也成了西比拉排除异己、打击僭越的国家机器。正如福柯所说的:“这些制度机构中没有任何实质变化,但隔离和禁闭的意义却开始发生变化……非理性回归到虚无的状态。”[6]这些非理性象征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
隔离机构消灭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心理测量者》中西比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它不仅征服了所有的异质,也征服了全体个体的社会有机体。主体失去了与周边环境的所有直觉联系,所有的执行官和监视官丧失了对正义、罪恶的最基本判断。工具理性摧毁了主体间沟通的一切桥梁,主体陷入了独白式的孤立,其他的主体只有站在冷漠观察的客体位置上才能保全自身。监视官和执行官之间的关系既是主体与主体相互联结的关系,也是主体与客体相互关照的关系。
在《心理测量者》中,西比拉作为工具理性、国家机构的象征,它对个体情感、人性的压制,使得社会上充满了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同时,西比拉的迅猛发展导致了个体的精神贫困与非人化后果,人性与理性的统一破裂,个体的精神世界与情感生命成为一片荒原,情感关系因此变得残忍无情,由此他者的存在也成了影响主体存在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他者”的存在与主体意识的确立
对于“他者”品性的认知,直接与个体对客观世界的早期探索相关联,同时也与个体的自我认同和主体存在性息息相关。个体并非在突发状态下偶遇他者的本质存在,相反,他是以一种包含情感的认知方式去“发现”他者,这在自我认知的形成初期占据着核心地位。常守朱和他者(狡啮慎也和槙岛圣护)之间分别在第一集和第十一集发生了较为激烈的冲突,也正是这两次冲突使得常守朱的主体存在性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这两次冲突当中,常守朱的内心世界有着极大波动,她是以一种丰富的情感去发现、认知“他者”的。
“他者”的存在与本体安全感相联系,本体安全感依托于一种实践性意识,这种实践性意识则深藏于日常的行为和话语之中。常守朱在与槙岛圣护产生冲突之后,本体一直处于不安全的状态。吉登斯认为,本体意义上的不安全的个体倾向于表现出以下特性:“首先,个体缺乏有关其生平连贯性的前后一致感,进而无法形成一种存活于世的持久观念。其次,在充满变迁的外部环境中,个体会专注于那些影响其存在的可能性风险,进而陷入行动上的瘫痪。最后,个体无法形成对自身的正直品行的信任。”[4]42与槙岛圣护的冲突可以说切断了常守朱生平连贯性的前后一致感,她陷入了行动瘫痪、内心倾覆的双重焦虑之中。她自身的警察身份受到了质疑,导致她无法形成对自身正直品行的信任。
槙岛圣护这个“他者”存在的意义不仅仅使常守朱的自我身份认同产生了困难,也导致了常守朱无法使用过去的经验去认识这个社会。在这种状态下,个体要么被迫转向从具体经验中抽象出来的信息作为替代物,要么寻找其他方式去体验“没有收益的个体”。常守朱勇敢地选择了去体验存在于西比拉之外的“没有收益的个体”,她用这种异乎寻常的勇气,再一次对没有希望的未来赌上了自己的信任。但可以想见的是,常守朱内心受到的刺激是难以想象的,她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无力整合这些令人震惊的冲击,因此“槙岛圣护事件”在她的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创伤。
的确,在现代社会,信任本身也意味着赌博与创新,它需要个体时刻将自身的主体存在和瞬息万变的新事物相连接,能够敢于融入未知领域之中。之所以说常守朱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因为她并没有让自己长时间地处在这种本体不安全状态中。她很快接受了“他者”(槙岛圣护)的存在,再一次与外在世界建立了新的联系。她相信槙岛圣护的“异质”情况,也相信着西比拉丑恶不堪的真面目。她用一种近乎绝望的心态,努力建构着自己“存活于世”的真实感,并且在绝望的夹缝之中倔强地相信着法律和正义,相信着西比拉系统终将覆灭,理想社会终将到来。
四、结语
公平、公正、自由、平等的法治社会是人类的永恒追求。日本著名救世动漫《心理测量者》尽管并没有像寻常救世动漫一样,摧毁了腐朽的制度,建立了理想的社会,相反,整部剧风格阴郁、压抑,它并没有许诺人类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好,但它在绝望中展示出了一片广阔空间,塑造了常守朱这样一个战士形象。常守朱坚韧的保持“色相”的能力,与她顽强地保持自我认同和主体存在性不受颠覆有着密切的关系。她是作者给处在西比拉统治环境下的个体以及当今社会的人类开出的一张药方。无论所处的环境多么险恶,遵守法律、坚持正义、满怀希望才是个体在这个社会中的唯一出路。尽管第一季的常守朱时常会陷入“哈姆雷特式的犹豫”,但她在第二季中成功地进行了蜕变,强大的正义感和行动力使得她这个人物的形象愈发理想化。常守朱的存在值得每一个生存在当今社会的个体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