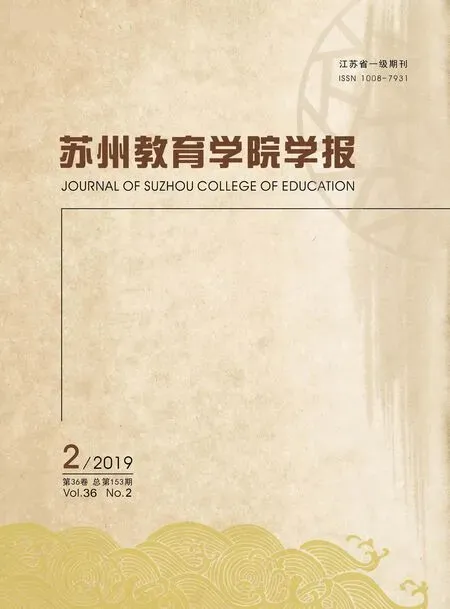格律:昆曲之魂—一《习曲要解》研读一得
2019-02-21顾聆森
顾聆森
(中国昆曲博物馆,江苏 苏州 215006)
“俞家唱”是近代以来仅存的昆曲正宗演唱流派,因俞粟庐得名。俞粟庐是清末民初著名清曲家,与王季烈齐名,以讲究曲唱格律著称。大师吴梅称俞粟庐:“得叶氏正宗者,惟君一人而已。”[1]1叶氏,即清中叶“著有《纳书楹》各谱,总曲剧之大成,为声家之圭臬”[1]1的叶堂。叶堂创“叶派唱口”,于清乾隆年间传予“集秀班”班主金德辉,又传长洲韩华卿,再传俞氏。1953年,俞振飞先生为其父俞粟庐编印《粟庐曲谱》时,作《习曲要解》附于书前。1982年,《振飞曲谱》问世,俞先生对收入书中的《习曲要解》作了补充、修改,使之成为了当代昆曲习曲者的必修教材。
《习曲要解》对昆曲唱念要领作了全面又精到的阐述,内容围绕唱曲艺术的技术要素—包括咬字、吐音、用气、节奏和腔格运用等—展开,而贯穿于全文的,乃是一个“律”字。有人以为唱曲乃至演戏当以表现“人物情绪”为唯一根据,而格律束缚了表情达意,因此主张填词或唱演只须以“人物情绪”为依据,无需顾虑格律乃至唱字的阴阳四声。对此,俞先生反诘道:“所谓四声、阴阳等等是从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是昆曲界别出心裁地杜撰出来的吗?”他断然作答:“都不是。”他说:“这是汉语通过千百年社会实践而形成的,是从人民生活中积累而成的!”[2]2如果演唱发生了因“以字害意”或淡化了人物情绪,“也只能批评写词或谱曲的人,怎么能责怪汉语的音韵规律而贸然废弃它呢?”俞先生又说:“如果违反这些规律,其实质就是违反生活。”[2]2
众所周知,汉语字声在抑扬顿挫之中表现了很强的音乐性,昆曲载歌载舞的形式与昆曲舞台字声的这种音乐性互相配合,可谓天衣无缝。即便是京剧,如需边歌边舞时,也往往要运用昆曲的曲牌来演唱。正是阴阳四声对于昆曲演唱具有关键意义,曲家们创造了许多字声腔格。这些字声腔格,除了美听外,就是用来保证阴阳四声的正确无误。如俞先生在《习曲要解》中例举说:“撮腔用于平声或去声字”[2]16,“罕腔用于阴上声及阳平声浊声字”[2]21,“凡上声字出口后的落腔用嚯腔”[2]21,“豁腔只限于去声字”[2]21,等等。昆曲所谓的“依字行腔”,指的就是以阴阳四声作为行腔的格律。故俞先生下笔论断:阴阳四声调停得好,可“令情意宛转、音调铿锵”,不仅有美听之效,更能使“唱曲艺术和表演艺术相互促进”,从而保证“人物情绪”之充分实现,并在传情达意中实现音乐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艺术的感染力。[2]24
因此,阴阳四声与“人物情绪”并非对立,反而可以相辅相成。俞振飞先生认为,对“人物情绪”的把握,说到底就是演唱者对曲情的把握。至于什么是“曲情”?乃父俞粟庐在《度曲刍言》中说:“大凡唱曲,须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解明情节,知其意之所在,则唱出口时,俨然一种神情。问者是问,答者是答,悲者黯然魂消,不致反有喜色;欢者怡然自得,不致稍见瘁容。”[3]23高手唱曲,是把自身融入曲情,与人物合一,“宛若其人自述其情,忘其为度曲,则启口之时,不求似而自合,此即曲情也”[3]23。
那么,昆曲格律与“曲情”有什么关联?
昆曲以曲唱见长,曲情的表达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唱腔,而唱腔的基础恰恰就是阴阳四声。中正的阴阳四声是“曲情”在浓郁的昆曲韵味中推进的必备条件。曲牌乃是字声格律的组合,而曲牌格律并非只是一个僵死的公式,它们是有生命的,是具有相应的感情色彩的。所以曲牌可以以清新绵邈、感叹悲伤、高下闪赚、富贵缠绵、惆怅雄壮、健捷激袅、凄怆怨慕、陶写冷笑、拾掇坑堑等不同色彩,归属于仙吕、南吕、中吕、黄钟、正宫、双调、商调、越调、般涉调等九宫十三调。为什么字声格律会在曲牌体式中具备感情色彩?就声韵学的常识而言,大凡平声主悲、主柔,仄声(指去声、上声)主怒、主愤。入声虽然也属仄声,但由于它们的字声出口便断,因而在曲中(指南曲)可作平声,也可作仄声用。明代曲家王骥德说:“大抵词曲之有入声,正如药中甘草,一遇缺乏,或平上去之声字面不妥,无可奈何之际,得一入声便可通融打诨过去。”[4]一支曲牌中平声、仄声的布局安排,并非曲家随意为之,取决于字声背后的音乐旋律。凄怨哀伤的调子,一定频用平声,而激昂愤怒的曲牌则仄声较多。以《琵琶记·吃糠》【山坡羊】的声律安排为例:
赵五娘唱:
乱荒荒不(丰稔)的年岁(韵),
远迢迢不回(来的)夫婿(韵),
急煎煎不耐(烦的)二亲,
软怯怯不济(事的)孤身己(韵)。
衣尽典(可韵),
寸丝不挂体(韵),
几番(要)卖奴身已(韵),
(争奈)没主公婆(教)谁管取(韵)?
思之(韵),
虚飘(飘)命怎期(韵),
难捱(韵),
实丕(丕)灾共危(韵)。
全曲有12句,除衬字(以括号标示)以外的64个正字中,有43个为平格(其中“不”“怯”“没”等字系“入声作平声”),加上还有三处字声处于可平可仄字位,使得平声在此曲中占了压倒性优势。尤其后面三句,“思之虚飘飘”连用了五个平声;“难捱”连二平。诚如前述,平声主柔,连用平声,文句声调便显得阴柔有余,阳刚消衰。这支【山坡羊】在它的最后四句,总共十四个正字中,安排了十个平声,这样的格律,不仅唐代近体诗中绝无先例,宋词中也极为罕见。显然,这种特殊安排,完全是出于声情的需要,即把前面已经由平声造成的抑塞、凄婉之情进一步向高潮推进。另外,本曲大多数唱句的韵脚如“岁”“婿”“已”“体”“取”等都用了仄声韵,使声情在悲凉中透出怨愤来。【山坡羊】属于南曲商调。商调是一种“凄怆怨慕”之声。昆剧中凡要表达或宣泄悲愤心绪,烘托凄切氛围,常选用此曲。显然,违背了曲牌固有的情感色彩,还要体现所谓的“人物情绪”也就勉为其难了。又如果作曲者只知道按牌谱曲,演唱者只知道“依字行腔”,填词者不懂得按“曲情”选择曲牌,就将“造成不符合人物感情”或“曲词内容与音律不协调”的毛病和缺陷。故俞先生告诫说,就这些毛病和缺陷,应对症下药,给予补救和改进,“不该得出一个可以不管四声阴阳而任意为之的结论”。[2]2
《长生殿·哭像》是俞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此出【快活三】曲牌的末句,律为“仄仄平平去”,洪昇词填:“冷清清独坐在这彩画生绡帐”,正字“独坐生绡帐”字字合律,但作者加了许多衬字,其中“在这彩画”四字连用四个仄声。不加衬字,其实文意已经清楚了,但作者为何如此破例地加进四个仄声字?显然,这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意在通过连用四个仄声字进一步撬动文句的不平,以强化此刻唐明皇内心的情感波澜。俞先生在《习曲要解》中这样叙述他处理曲唱的过程:
……“独坐在这”四字,后面三个都是去声字,都有豁腔,如果同一处理,必然呆板无情,并且不好听,我就在处理上加以变化,把“这”字加上颤音,音尾轻轻一豁,紧连一声哭音“呣”,然后重重落在下一个“彩”字(上声)上面,这样字音准确,处理灵活,人物感情也充分表达出来了。[3]24
俞先生的艺术处理是对剧作者格律声韵运用的延伸,不明白昆曲格律的演唱者不可能有此曲唱造诣,如此得心应手地把字声格律巧妙地融入曲情,不但强化了曲情,又加倍浓化了人物情绪与剧场氛围。声和情的并茂与升华在需要达到一个新境界时,离不开度曲者对曲牌文字和字声格律的深刻理解。何为“度曲”?度曲,就是要求演唱者通过正确的口法,把字声和字韵通过“行腔”予以体现,并最终合成完整的乐化字音。
但也有人认为观众大多是律盲、韵盲,他们未必懂得昆曲格律的微妙,故填词、唱曲对于曲律不必太过认真。这种认识是对昆曲格律涵义的真正无知,也是对于昆曲固有传统的一种彻底排斥。
须知昆曲在其近500年的发展历史中几经盛衰,但是,无论在其鼎盛时期,还是衰竭之时,它始终坚持以律治戏,从没有废弃过自己的灵魂:格律。
不可否认,当代昆曲观众大多未尽知律,昆曲舞台上无律的新编昆剧恰如雨后春笋,不知律的导演、编剧、作曲以及无知的评委和媒体的高调介入,已把昆曲格律逼入了可有可无的尴尬之境。
昆曲艺术是否应该迁就不知律的观众和不知律的编导、评委等而摒弃传统的昆曲之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代表作,昆曲以其格律森严的曲牌体立身,这是它区别于全国几百种地方戏的特异之处。昆曲一旦失律,也即失魂,无论导演、编剧如何高明,演员如何超能,它其实已离开了昆曲本体,充其量是一出昆唱(?)的地方戏。即使获了大奖、享了名声,仍将与艺术的“正宗”无缘,最终将贻笑乃至贻害于后世。
无律昆曲的泛滥,造成昆剧失魂之痛,恰恰是当代昆剧的莫大悲哀。
《习曲要解》在当代昆坛之所以显得格外重要,是因为它是昆曲拨乱反正的理论指南,它不仅是习曲者入门的钥匙,更是专业的昆曲音乐工作者、编剧、演员以及昆曲理论研究者的必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