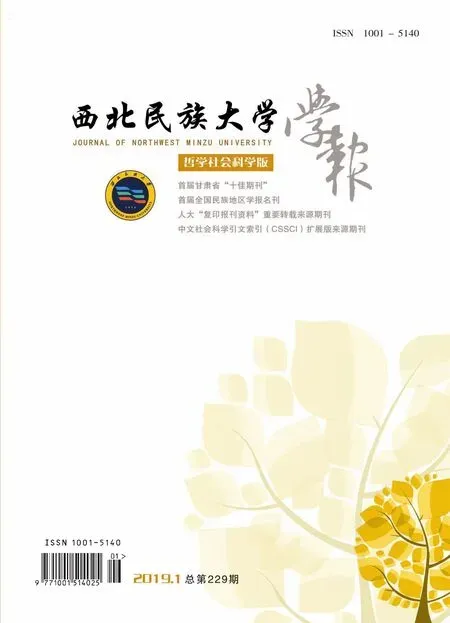庾信前期赋再评价
2019-02-20刁生虎白昊旭
刁生虎,白昊旭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庾信赋是南北朝文学的一颗璀璨明珠,深受学界关注[注]①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有言,庾信、徐陵写作极力追求辞藻、对仗之美,形成“徐庾体”,获得“一代文宗”的赞誉。(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3.222.)姜书阁认为南方的徐陵和北方的庾信都是骈体文发展历史上的高峰,更是特别肯定庾信“是骈赋最后一个大家”。(姜书阁.骈文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425-435.)马积高从赋史流变的角度出发,肯定庾信是“南北朝赋的集大成者”。(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39-248.)。根据庾信的人生经历,学界普遍把庾信一生赋的写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且对其前期赋的评价远低于后期赋。然经仔细研读庾信前期赋后,笔者深感现有结论有待商榷。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前人对庾信赋的评价、庾信前期赋饱受非议的原因以及庾信前期赋不容忽视的贡献等三个方面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力求对庾信前期赋获得新的认知与评价。
一、前人对庾信赋的评价
学界一直对庾信前后期赋作持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对庾信赋整体给予肯定。北周的宇文逌最先对庾信的才华表示赞赏。《北史·庾信本传》有言:“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1]2794其中“滕”即当时的滕国公宇文逌。由此可见,庾信文学上的才华足令当时北周上层社会钦佩不已并与之平等相交,宇文逌作为庾信文学才华的欣赏者之一,不仅为庾信作品集作序,而且对其文学才能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信将山岳之灵,蕴烟霞之秀,器量侔瑚琏,志性甚松筠。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诔夺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扬雄,书同阮籍。”[2]55-56宇文逌所撰写的这一段虽然因朋友之情对其文学才能有夸大的嫌疑,但是也足以证明庾信赋所获得的文学成就。清代陈维崧对庾信非常推崇,在《词选序》中不仅抨击了“齐梁小儿语”的观点,更是盛赞庾信的《哀江南赋》,认为其“仆射在河北诸书,奴仆《庄》《骚》,出入《左》《国》,即前此史迁、班椽诸史书,未见礼先一饭”[3]182。二是对庾信赋持完全否定态度。隋初,政治上百废待兴的新局面影响到文学评论,蓬勃向上的政治风貌使当时的文士对庾信南朝时期文风持有偏见。隋初王通《文中子·事君篇》云:“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4]199初唐令狐德棻有言:“子山之文……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于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5]101令狐德棻是初唐史官,史官身份致使其更欣赏朴素实用的文风,因此将善于“赋丽”的庾信定位为词赋之罪人。李延寿认为:“庾信……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至宋,文坛受到西昆体的影响,崇尚雕琢艳丽之风,讲究声律,因而对庾信作品的艺术风格多秉持宽容的态度,但是却对庾信作品的社会功用进行批评,北宋初年理学家孙复认为:“沈、谢、徐、庾妖艳邪侈之言,杂乎其中,至有盈篇满集,发而视之,无一言及于教化者。”[6]17张戒《岁寒堂诗话》有言:“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7]465金末王若虚受北方文学豪放风气的影响,严厉批评了庾信赋“类不足观”,“堆垛故实,以寓时事,虽记闻谓富,笔力亦壮,而荒芜不工作雅,了无足观”[8]204。至民族矛盾复杂的清初,文士们把庾信作品的文学评价与其人其事联系起来。由于庾信望敌先奔,后来又在北周做官,人们对其为人进行猛烈抨击。清初全祖望认为:“甚矣,庾信之无耻也……后世有裂冠毁冕之余,蒙面而谈,不难于斥新朝颂故国以自文首,皆本自天醉之说也。”[9]405赵成林的《唐赋分体叙论》认为:“其实不仅徐、庾,晋宋骈赋作者,不少由于生活阅历贫乏、情感单薄,写作时堆朵旧事,以繁博相夸,以至故实满纸妨害文意。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骈赋的生命力。”[10]43三是对庾信前期与后期赋作分别评述。杜甫是第一个对庾信作品分时期评价的文学家,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不仅注意到庾信前期作品有清新的特点:“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而且其《戏为六绝句·其一》言:“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他肯定了庾信后期作品恢弘气势与苍茫凄凉风格,同时杜甫对庾信赋给以称赞:“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南宋诗人尤袤继承了杜甫评价庾信的方式,其从音韵学的角度对庾信的文学贡献予以肯定:“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11]6478清人纳兰性德在《赋论》中对庾信前期赋提出批评:“萧氏之君臣,争工月露;徐、庾之排调,竞美宫奁。”[12]432清代《四库全书》对庾信北迁之后的作品进行赞扬:“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13]3838倪璠认为:“夫南朝绮艳,或尚虚无之宗;北地根株不祖浮靡之气,若子山可谓究南北之胜;江南竞写,曾与徐陵齐名;河北呈才,独有王褒并埒。”[6]23倪璠的评价应该是对庾信前后期赋作比较客观的评价,对庾信南北朝的文学地位给予肯定。郑振铎继承了倪璠的观点:“原是齐梁正体,然而到了北地之后,作风却大变了。由浮艳到沈郁,由虚夸变到深刻,由泛泛的骈语变到言必有物的美文……遂在齐、梁中达到了一个未之前有的最高成就象那样又深挚又美艳的作用,是六朝所绝罕见的。”[6]24郑振铎注意到庾信文风之变,并且其在点评用语中明显表现出对庾信后期赋作的欣赏与肯定。傅东华认为庾信前期赋多堆砌故实,针对《春赋》第一段有过感叹:“我们总不明白秦朝的宜春苑为什么要和汉朝的披香殿拉在一起?为什么春衣要等春已归时才赶作?为什么才说‘新年’,马上就接下来说‘二月’?河阳的花和金谷的树有什么相干?才开长安的上林而入,为什么一下又飞到孟津去渡河桥?”钱钟书对庾信词赋前后期的变化也做过相关评述:“子山词赋,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之作皆居南朝所为,及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6]25这种观点比较客观而全面。马积高的《赋史》认为:“令狐德棻是针对齐梁以来的华靡文风来批评庾信的。庾信早年确是这种文风的代表,其晚年之作仍有词藻过于秾丽,用典太多的缺点。”[14]247从这个角度看,马积高认为令狐德棻对庾信辞藻和文风的批评是具有合理性的。谭正璧、纪馥华《庾信诗赋选》认为庾信前期赋内容空虚、轻浮、绮艳;后期赋格调慷慨凄凉、气魄宏伟瑰丽[15]2-21。王瑶的《中古文学风貌·徐陵骈体》虽然没有直接对庾信前期赋给予否定,但是其认为:“和徐陵相较,当然庾信的地位是更高的。他高出徐陵的原因,自然是因为他后半生二十多年来的流离羁旅的生活体验,使他能在注重形式的文体里,输入了一点抒写悲痛的内容。”[6]25
二、庾信前期赋饱受非议的原因
从上述前人对庾信赋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庾信前期赋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占大多数。笔者认为,庾信前期赋之所以不被学界认可,原因如下。
(一)庾信前期赋属于“宫体”范畴,受到“宫体”负面评价的影响
“宫体”最早是在《梁书·徐摛传》中被提出的。其有言:“摛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16]446-447宫体赋是“宫体”的一种类别。宫体赋的创作团体是萧纲及其麾下的儒士文人,《南史·简文纪》有言:“简文文明之姿,禀乎天授。粤自支庶,入居明两。经国之算,其道弗闻。宫体之传,且变朝野。”[17]250在题材上,同一种题材,萧纲与庾信都曾经写过,诸如《鸳鸯赋》《春赋》《对烛赋》,可见宫体赋的创作多是君臣之间唱和应答。宫体赋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隋书·经籍志》对“宫体”的内容做过定义:“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18]101从内容层面看,宫体赋并没有展现出宫廷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而是专注于描写宫廷美人的妆容、姿色、服饰、举止、玩乐,女子闺怨、相思之情以及宫廷春景、器物等。庾信前期赋至今存有《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荡子赋》七篇,此七篇均是宫体赋常见的内容。《春赋》是描写宫廷春景及宫廷美人游春之事,《七夕赋》是描写美人七夕乞巧之事,《灯赋》《镜赋》都是对宫廷器物的描写,《对烛赋》《鸳鸯赋》《荡子赋》都表达了女子的闺怨相思之情。正如倪璠的观点:“若夫《三春》《七夕》之章,《荡子》《鸳鸯》之赋,《灯》前可出丽人,《镜》中唯有好面,此当时宫体之文,而非仕周之所为作也。”[19]47从创作观念看,宫体赋是“清辞巧制、雕琢蔓藻”之作,《文心雕龙·明诗》中对齐梁时期的文学风尚进行概括:“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20]31萧纲更是认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需放荡。”[21]18其反对恪守儒家经典的道德观念,反对仿古,主张遣词造句,缘情而发。与两汉赋相比,宫体赋愈发追求精工巧丽,宫体赋作家喜欢用艳丽的颜色[22]106,如朱、金、粉、碧等装点其文章,使文章愈发明艳。庾信前期赋色彩繁多斑斓,如《春赋》有“争绿”“竞红”“金鞍”“苔绿”“麦青”等,又如《灯赋》有“粉壁”“朱烬”“焰焰红荣”等,再如《镜赋》有“金莲帐”“粉絮”等,运用诸多描写颜色的词语是宫体赋华艳之美的一种体现。庾信同众多宫体赋作家一样,重视赋文语句的平仄、对仗和节奏,如《灯赋》“窗藏明于粉壁,柳助暗于兰闺。翡翠珠被,流苏羽帐”“蛾飘则碎花乱下,风起则流星细落”,再如《春赋》“绿珠捧琴至,文君送酒来”“树下留杯客,沙头渡水人”等句。宫体赋抒发感情比前代赋更加显露大胆,庾信前期赋受到内容所限,多是抒发闺房女子之情,符合宫体赋的抒情方式,如《春赋》结尾处有言:“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美人离去时,望向池水,流连于春景,不觉想到回到宫中的孤独寂寞,屋中衣香不如此刻花香,表达出一种怅然之情,再如《荡子赋》中“况复空床起怨,倡妇生离;纱窗独掩,罗帐长垂;新筝不弄,长笛羞吹”“游尘满床不用拂,细草横阶随意生”。庾信不仅对思妇闺房床笫之情怨进行直接描写,又有“倡妇”“空床起怨”这种比较露骨的字眼,将寂寞惆怅的闺怨之情抒发得酣畅淋漓。
如果仔细考察前人对“宫体”的批判言论,可以发现,其最早起源于政治斗争[23]。东魏的慕容绍宗在武定六年准备伐梁时,以梁武帝“持险躁之风俗,兼轻薄之子孙”[24]2184为出兵借口,后来侯景也以“宫体”文风为起兵反叛的借口:“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25]1069由此可见,最初对“宫体”的批评并非是针对文体风格、文学创作本身而言,而是一种政治攻击。随着梁王朝的颓势至最终覆灭,后来很多梁代遗民文学家将“宫体”与亡国联系起来,将其列为亡国之因,如从梁入陈的何之元在其《梁典》中认为:“至乎文章妖艳,隳坠风典,诵于妇人之口,不及君子之听,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26]3950唐初史学家对“宫体”也多有怨言,但其未必是从文学本身的价值进行批判,而是因为唐初史学家如姚思廉、李大师、李延寿、令狐德棻、李百药、魏徵、虞世南等人都是朝代更迭的幸存者,“宫体”的演变与梁陈朝代的兴亡紧密相连,因此,当论及“宫体”盛况时,他们不仅仅是评价“宫体”,更是伤心故国,“宫体”之怨愈深,麦秀黍离之哀愈重[23]。唐初史学家对“宫体”的批评更多地夹杂了他们对故国倾覆的哀愁情绪,当初“宫体”在梁陈文坛上所创造出的盛景有多么的繁华,梁陈最终覆灭的结局就有多么的凄惨。作为梁陈两个朝代土崩瓦解的亲历者,他们在唐初对“宫体”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梁陈旧朝的一种反思,对新朝的一种警示。《梁书》对“宫体”评价:“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16]151《陈书》有言:“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27]119-120《北齐书》认为:“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沾滞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原夫两朝叔世,俱肆淫声,而齐氏变风,属诸弦管,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28]602由此可见,后世史书多认为“宫体”有伤风化,不合教化,是亡国之音,并从政教的角度对“宫体”进行批评。
“宫体”的政治批评影响了文学评论领域,“宫体”本是诗赋二者共同的风格定义,但是由于诗更加受到历代文士重视,赋逐渐没落,因而提到“宫体”,文学评论家多是以“宫体诗”作为评价“宫体”特点的切入口,批评“宫体”。陈子昂认为:“齐梁间诗,彩丽竞繁。”殷璠认为:“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29]59白居易认为:“梁陈间率不过嘲风月、弄花草而已。”[30]224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认为:“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31]11受到闻一多的影响,刘永济认为:“迨宫体既兴,情思逾荡。绮罗香泽之好,形于篇章;帷闼床笫之私,流为吟咏。”[32]185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评萧纲的“宫体”之作:“以赏玩的态度,沉溺于女性色相的描绘,而缺乏与女性心灵世界的沟通,终不免‘文艳事寡’‘体穷淫丽’,陷于轻薄。”[33]129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认为:“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34]114曹道衡、沈玉成认为:“声韵、格律,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踵事增华,要求更为精致;风格由永明体的轻绮而变本加厉为绮丽,下者则流入淫靡;内容较之永明体时期更加狭窄,以艳情、咏物为多,也有不少吟风月、狎池苑的作品。”[35]241曹道衡、沈玉成虽然对“宫体”进行了相对全面的概括,但是并没有改变对宫体的否定态度。庾信前期赋正属于“宫体”范畴,因而受到“宫体”负面评价的影响。《周书》《北史》《隋书》将庾信赋的艺术风格与“宫体”的艺术风格联系起来,认为其“淫放”“轻险”“意浅而繁”[36],正是最好的证明。
(二)庾信前期赋在内容和功用层面不符合传统儒家观念
庾信前期赋创作于南朝梁时期,“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南朝时期朝代频繁交替,士人心中零落之感过甚,秦汉时期恢宏磅礴的帝国之象,魏晋时期凛然的“风骨”之气,往昔的凌云之志都早已消磨殆尽。梁武帝在位时间较长,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梁朝政治、社会都处于比较稳定的时期。长期的动荡与短暂的安逸交织,导致梁时期的贵族文士更注重当下享乐,《颜氏家训·勉学》言:“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37]200《颜氏家训·涉务》言:“梁世士大夫……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步行;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贲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37]200由此可见梁朝文士身上已经没有横刀立马的男儿气概,取而代之的是类似于女子的阴柔衰颓之气,这就导致文学体验由探寻外在世界向内在情感转化,以闺怨床第、颓靡浮艳之作消磨外在世界的痛苦。其次南朝文学自觉性较前代愈发显露。宋朝设立四学五部,儒学、史学、文学、玄学为四学,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标志着文学从政治、经学中分化出来,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38]。至梁朝,当权者对文学给予极高的重视,《南史·文学传序》言:“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39]190梁武帝常常召集大臣以诗赋互相唱和,对臣子的文章加以点评,《梁书》记载“时高祖着《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丘)迟文最美”[16]687,“(刘)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尝于御坐为《李赋》,受诏便成,文不加点,高祖甚称赏之”[16]591,“及高祖为《籍田诗》,又使勉先示孝绰。时奉诏作者数十人,高祖以孝绰尤工,即日有敕,起为西中郎湘东王咨议”[16]482。萧纲的文学观念生成于六朝文学自觉的环境之中,其主张“诗缘情”,在《与湘东王书》中对典雅舒缓的文风进行批评:“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40]109-110
在阴柔衰颓之气与文学自觉的推动下,梁时,文章越发讲究绮艳,在永明文学的基础上更加追求形式美与写作技巧,形成重形式、轻内容的文学创作风气。王夫之曾评价庾肩吾的作品:“子慎于宫体一流中,特疏俊出群,贤于诸刘远矣。其病乃在遽尽无余,可乍观而不耐长言,正如炎日啖冰,小尔一块,殊损人脾。”[41]309梁时文人写作以引用大量典故为傲,甚至是推崇生僻典故,《南史·刘峻传》记载:“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刘)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17]1219-1220《梁书·沈约传》记载:“(沈)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16]243《南史》言:“(任昉)用事过多,属词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17]1455由此可见,文章中多用典故已然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时尚。庾信前期赋受到梁朝文学风尚的影响,写作中追求形式美,对仗工整,如《荡子赋》有“陇水恒冰合,关山唯月明”,《灯赋》有“舒屈膝之屏风,卷芙蓉之行障”,《七夕赋》有“嫌朝妆之半故,怜晚饰之全新”。庾信常用典故,如《鸳鸯赋》有“若乃韩寿欲婚,温峤愿妇”,以韩寿、温峤的典故表达对美满爱情的渴望;《荡子赋》有“合欢无信寄,回文织未成”,以北朝前秦人苏蕙用五彩锦织《回文璇玑图诗》赠送自己夫君的典故表达自己思夫心切,寄情锦缎难以织成。
从中国儒家传统观念看,南朝梁时期的文学创作有悖于儒家提倡的文学功用。《毛诗序》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强调文学在内容上必须具备社会功效,即“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盛行于梁的宫体赋多是对女性体态、情感的描写,虽然与汉赋内容有相似之处,但是意义完全不同。梁赋中的女性形象多是贵族娱乐消遣的对象,没有过多的社会意义。汉赋中女性形象多为贬低和否定的对象,《汉赋女性描写的思想倾向性》[42]一文中详细地梳理了枚乘《七发》、司马相如《上林赋》、杨雄《甘泉赋》、张衡《七辩》等赋作中的女性形象。如枚乘《七发》:“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燕,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43]16再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先铺陈女性之美,“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娴都,靓庄刻饰,便嬛绰约”[43]66,而后批判包括女色在内的一切享乐诱惑,认为其妨碍“继嗣创业垂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汉赋作品虽有女性,但是女性本身不是描写重点,女性的悲惨经历才为作者所关注,是借女性表达社会现状,比如王粲《出妇赋》,就是表现了一位坚贞、甘于为家庭牺牲奉献的妇女却遭到丈夫遗弃的事情,以批评社会上的负心汉,反映女性的社会地位;再如丁廙妻《寡妇赋》中通过描写一个寡妇失去丈夫之后悲惨的生活现状,反映了对当时汉末军阀混战中的兵役制度的反思。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汉代士人文人层面,对女性的认知具有极其浓烈的道德色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层面,汉代士人文人认为女色会严重影响君子道德修为;二是社会层面,以妇女作为载体,最终目的是为了针砭时弊,反映社会乱象。其次在中国传统文学创作观念中,文学的价值主要在于内容,内容支配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就是指内在的修养,其本质应该是“仁”,“文”就是指外在的礼仪,具体表现为在特定场合着装是否得体,行为举止是否儒雅。“野”是指缺乏文化修养的,远离礼仪社会的人。其虽然言行粗俗,难登大雅之堂,但是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有一颗单纯善良的心,本性“仁善”。“史”是“策祝”,策书祝辞的史官。这种史官往往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善于迎合统治者,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往往滋生奸诈狡猾之徒。清代刘逢禄在其《论语述何》中云:“文质相复,犹寒暑也。殷革夏,救文以质,其敝也野。周革殷,救野以文,其敝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质彬彬者也。春秋救周之敝,当复反殷之质,而驯致乎君子之道。故夫子又曰:‘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野人,而后君子也。”[44]463当“文质”难以统一时,孔子取“质”而舍“文”。后人将这一道德观念引申到文学层面,文质关系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孔子对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也有过阐述,认为艺术不光要具有形式美,更重要的是内容要中正平和,要雅正。孔子倡导美和善要统一,“文”和“质”不能偏废:“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孔子认为《韶》乐不仅曲调优美,更重要的是其内容是歌颂尧舜禅让,这种天下权力和平传递的思想符合孔子“仁”的观念,所以他认为《韶》乐“尽善尽美”。反观《武》乐,尽管曲调优美动听,但是《武》乐是歌颂武王以武力夺取天下,这不符合孔子“仁”的观念,所以孔子并不推崇它。可见形式美和内容美能够统一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但是当形式和内容不能统一时,孔子往往会舍形式而重内容,比如孔子认为写作“辞达而已矣”,只要阐述意思准确,润饰性文字可以不要。在这种传统文学创作观念的指导下,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欧阳修的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都是反对追求文章形式技巧,反对靡丽文风,重视文章的内容与社会功用,在中国古代文坛上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而过于追求辞藻华丽的纯文学作品,往往难以获得好评。
三、庾信前期赋不容忽视的贡献
正如徐宝余《庾信研究》所言:“庾信入北之后,突破与创新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种突破与创新并非是一个自觉自愿的过程,并非是在抛弃旧有艺术风格基础之上所形成,恰恰相反,而是一个艰难磨合的过程。”[45]150庾信前期赋在内容、对偶与诗赋交融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为后期赋的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对后世诗、赋、词等中国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庾信前期赋在内容上的贡献
庾信前期赋作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描写美好春景与宫廷贵族游春之乐,如《春赋》;二是吟咏宫廷常见物象,如《镜赋》《灯赋》《对烛赋》;三是描写风俗节日,如《七夕赋》;四是代当时妇女言闺怨之情,如《鸳鸯赋》《荡子赋》。就纵向比较而言,庾信前期赋的四种题材与后期《愁赋》《哀江南赋》抒写国破家亡、人生零落之深沉哀愁的情绪相比,确实更偏向于描写日常,生活气息更加浓厚。就横向比较而言,同时期“宫体”代表作家梁简文帝萧纲、徐陵等人虽然都与庾信写过同样题材的赋作,但相较之下,庾信的作品现实性更强,思想更深刻。如庾信的《春赋》主要写,在美好的春景中宫廷贵族游春踏青之乐:“移戚里而家富,入新丰而酒美。”“玉管初调,鸣弦暂抚,《阳春》《渌水》之曲,对凤回鸾之舞。”[46]230由此可见,庾信的《春赋》不仅有春景,更有赏春之人。梁简文帝萧纲也写过《晚春赋》,但是在该赋中萧纲写了春水、春风、春荷、春鱼、春鸟等春景,但却没有写到赏春人,与庾信《春赋》相比,写作对象都是物,略显单一,整篇赋的内容也比较单薄,又如庾信的《对烛赋》开头就为整篇赋奠定了感情基调:“龙沙雁塞甲应寒,天山月没客衣单。”[46]235这两句主要描写了戍卒戍边生活,庾信常年领兵于太子宫,和湘东王讨论兵法,熟悉兵营之事,而且曾出使东魏,经历过边关生活,所以才能深刻体会戍边生活之艰辛。该赋接着写了妇人在蜡烛微弱的光亮中为即将离家的戍卒缝补单衣:“灯前桁衣疑不亮,月下穿针觉最难。”[46]235这表达了妇人对即将戍边的夫婿的离愁之情。而萧纲的《对烛赋》则通篇写了宫廷深夜依旧烛火通明,贵族们寻欢作乐的场面:“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灯火不须然。下弦三更未有月,中夜繁星徒依天。于是摇同心之明烛,施雕金之丽盘。”[46]174与庾信的《对烛赋》相比,萧纲立足于宫廷生活,描写宫廷贵族丽人一派奢华享乐的景象,但是庾信将视线转移到下层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虽然都是以“烛”起兴,庾信显然更具有现实性和人性关怀。再如《鸳鸯赋》,据《艺文类聚》卷九十二《鸟部·鸳鸯》中言:“赋凡四篇,首为梁简文帝,次为梁元帝,复次为北周庾信,末为陈徐陵。”[47]2庾信的《鸳鸯赋》借三国的魏明帝为王时,纳虞氏为妃,但是魏明帝称帝后,却抛弃虞氏的故事起兴,接着铺陈了一系列男女之间琴瑟和鸣的爱情故事,如“南阳渍粉”“京兆新眉”“共飞檐瓦”“俱棲梓树”“温峤愿妇”等,最终表现了这些深宫佳人孤苦无依的生活光景,“觉空床之难守”,抒发了失宠女子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之情,表达了作者怜悯之意。此赋虽然内容是抒发闺怨,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庾信当时尽管深得皇帝宠信,身居于高位,如日中天,却存眷现实,尤其存眷身边下层苦难群体,并且对他们给予怜悯。相比较而言,梁简文帝萧纲的《鸳鸯赋》则是表现了得宠宫女的欢愉之情态:“亦有佳丽自如神,宜羞宜笑复宜颦。既是金闺新入宠,复是兰房得意人。见兹禽之栖宿,想君意之相亲。”[48]65徐陵的《鸳鸯赋》借用“炎黄季女”“织素佳人”“少妇生离”等一系列典故,与鸳鸯相对比,衬托出鸳鸯双宿双飞的美好,抒发相恋男女常相伴之意:“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雁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合会,无胜比翼双鸳鸯。”[47]3从思想内容的角度看,庾信的《鸳鸯赋》引发我们对荒淫奢靡的贵族生活造成众多女性成为牺牲品的思考,更具有社会现实性。
(二)庾信前期赋在对偶上的贡献
前期赋不仅内容注重现实,而且重视遣词造句的技巧,尤其是在对偶上取得突破。骈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偶整饬,《楚辞》中有零星对偶短句,建安之后骈赋开始形成,南朝骈赋达到成熟。刘勰《文心雕龙·丽辞》曾列举了四种对偶之法:“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20]235-236除了反对,言对、事对、正对在庾信前期赋中比比皆是。言对如《春赋》中描写贵族佳人出游之景:“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影来池里,花落衫中。”《灯赋》中对后宫妃子屋中之灯的描写:“动鳞甲于鲸鱼,焰光芒于鸣鹤。蛾飘则碎花乱下,风起则流星细落。”《镜赋》中对镜子的描写:“镂五色之盘龙,刻千年之古字。山鸡看而独舞,海鸟见而孤鸣。临水则池中月出,照日则壁上菱生……量髻鬓之长短,度安花之相去。悬媚子于搔头,拭钗梁于粉絮。”事对如《对烛赋》:“秦皇辟恶不足道,汉武胡香何物奇?”《春赋》:“出丽华之金屋,下飞燕之兰宫。”正对如《对烛赋》:“楚人璎脱尽,燕君书误多。”《鸳鸯赋》:“共飞詹瓦,全开魏宫;俱栖梓树,堪是韩冯。”这种对偶精工的特点,对庾信后期赋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庾信《枯树赋》:“将雏集凤,比翼巢鸳。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小园赋》中庾信笔下的小园:“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象戏赋》:“法凝阴于厚德,仰冲气于清虚。”这些都是对仗工整的佳句。
(三)庾信前期赋在诗赋交融上的贡献
庾信前期赋属于骈体赋,骈体赋最初起源于汉赋,姜书阁的《骈文史论》言:“西汉之作骈语虽多,偶对尚少。至东汉,则骈偶遂繁,班固《西都》、张衡《二京》,已极显然;至于《归田》《登楼》,虽号为抒情小赋,却是偶对连篇,已近于俳;至建安、黄初,遂进入骈赋时期了。”[49]13可见骈体赋并不是庾信独创,但是庾信赋却在骈体赋的基础上表现出明显的诗化倾向,完成了新体赋,即诗赋交融的骈体赋。
所谓诗化,徐公持的《赋的诗化与诗的赋化》言,并不是诗变成赋,或者赋变成诗,而是二者之间取长补短,使诗或赋都能满足当时时代的文学需求。庾信前期赋诗化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赋格式的诗化。诗的格式主要是五言与七言,据前人统计,《对烛赋》《荡子赋》《春赋》《鸳鸯赋》《灯赋》和《镜赋》中的五七言分别占全篇的63%、50%、42%、17%、11%和10%[45]172。“大赋六言句式之中,多间有一虚词。虚词存在与否,是诗体与赋体形式上的一个明显标志。虚词多数可以省略,六言省略虚词之后,直接变做简洁的五言诗体。”[36]此一删削不仅消除了古板呆滞,而且因为关系助词不再具有明确指向性,反而扩充了赋文的内涵,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庾信前期赋作多用五、七言,正如明人谢榛所言:“庾信《春赋》,间多诗语,赋体始大变矣。”[50]1163《春赋》开篇连用了八个七言:“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46]230再如其《荡子赋》将五七言连用:“荡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长城千里城。陇水恒冰合,关山唯月明。”“别后关情无复情,奋前明镜不须明。合欢无信寄,回纹织未成。游尘满床不同拂,细草横阶随意生。前日汉使著章台,闻道夫婿定应回。手巾还欲燥,愁眉却剩开。逆想行人至,迎前含笑来。”[46]234-235这些五七言不仅在格式上与诗无异,而且音韵流畅,正如祝尧所说:“盖自沈休文以平上去入为四声,至子山尤以音韵为事,后遂流于声律焉。”[51]378二是赋中采用诗的抒情手法。许结的《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认为中古诗化是“创作上自觉地开始了对先秦诗人之志和骚人之情的归复”,赋长于体物,诗长于抒怀,赋的诗化就是借鉴了诗的抒情手法,作者将自己融于物中,使物具备人的感情,达到“以物观物”。如庚信《对烛赋》首句,“龙沙雁塞甲应寒,天山月没客衣单”,庾信写这篇赋并未到边塞,但是“甲应寒”体现出庾信将心境与外在景物结合起来,接着庾信对烛火进行了细致描写:“灯前桁衣疑不亮,月下穿针觉更难。”它表现了室内昏暗的环境,烛火微弱,正如征夫此去前途渺茫,表达补衣思妇的凄苦。“烬高疑数翦,心湿暂难然”不仅仅是指蜡烛芯受潮难以燃烧,更是指点烛人凄凉心境。“还持照夜游,讵减西园月”是孤独思妇一个人秉烛夜游,孤枕难眠之态跃然纸上。庾信对烛的描写不局限于烛本身,而是将烛赋予了对烛人的情感,借物抒情,使全赋情感洋溢,深沉真挚。
庾信后期赋对诗赋交融的继承不局限于赋格式的诗化,更多是将诗情与赋融合为一,一改摹物之赋专注摹物的特点,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家国之思融入进赋作之中。《枯树赋》中的枯树虽然枝叶繁茂,但是其根已朽,复活已经是无望,只能作为木材尽其用,以期进入人生新的阶段,这种感触也符合当时庾信滞留北方,壮志难酬之感:“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欹卧,顿山腰而半折……木魅睒睗,山精妖孽。匠石惊视,公输眩目。雕镌始就,剞劂仍加……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邛竹杖赋》以竹杖自喻:“夫寄根江南,淼淼幽潭;传节大夏,悠悠广野,岂比夫接君堂上之履,为君座右之铭,而得与绮绅瑶珮,出芳房于蕙庭。”庾信本是梁人,却滞留北方,就像竹杖本生长于江南,传节于大夏,深深寄托了庾信的家国之思。
(四)庾信前期赋对后世中国文学的影响
晚唐赋作家非常重视庾信在对偶与诗赋交融上的贡献。晚唐王棨的《江南春赋》不仅借鉴了庾信《春赋》的题材,而且继承了庾信赋的格式,多五七言句式且对偶工整。如“年来而和煦先遍,寒少而萌芽易坼”“薄雾轻笼于钟阜,和风微扇于台城”“高低兮梅岭残白,逦迤兮枫林列翠”[52]536-537等句;再如杜牧的《晚晴赋》则引诗情入赋,将秋天的美景假托为美人:“复引舟于深湾,忽八九之红芰,姹然如故,敛然如女,堕蕊黦颜,似见放弃。”[53]3将出水红荷比作艳丽少妇、害羞少女、被休弃女子;再如“杂花参差于岸侧兮,绛绿黄紫,格顽色贱兮,或妾或婢”,将野花参差不齐的样子比作侍妾与婢女。这些都表现出作者将自己对秋天美景的喜爱之情融于自然景物之中,以诗情写赋。
宋代苏轼有诗《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故人久立烟苍茫。”清康熙吴兴施元在诗下注:“摇荡寒关,苍茫日晚。”[54]283他认为其可能化用了庾信《荡子赋》的语义。陆游《解连环》词言:“京兆眉残,怎忍为,新人梳掠。”[55]189其中京兆眉在庾信《鸳鸯赋》中也有所提及:“南阳渍粉不复看,京兆新眉遂懒约。”我们可以推测,这首词中“京兆眉”的援引可能也受到庾信的影响。清代陆葇的《历朝赋格》收录了庾信的《灯赋》,并且给予评点:“叙次星列点缀珠悬,言易尽而意悠长,千载服其新艳,末二句似可删。”[56]826清中叶科举试赋促使赋学再度繁荣,当时的文士对庾信前期赋多有拟作,如顾宗泰的《拟庾子山对烛赋》、张惠言的《拟庾子山七夕赋》、姚光晋的《拟庾子山春赋》、黄爵滋的《拟庾子山镜赋》、徐宝善的《拟庾子山镜赋》、方履篯《拟庾子山荡子赋》、夏思沺的《拟庾子山对烛赋》等[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