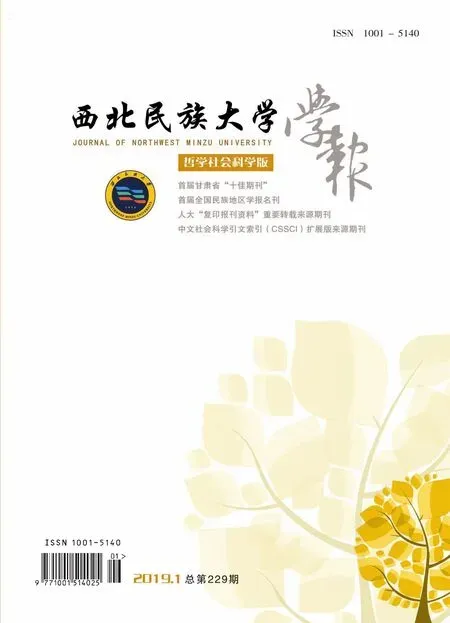试论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中的抵制“印茶入藏”
2019-02-20陈鹏辉
陈鹏辉
(西藏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陕西 咸阳 712082)
“印茶入藏”是晚清至民国时期英国侵略中国西藏的一个既定目标。英印茶叶资本家从早期入藏活动的英国人中获知“藏人奢茶”、西藏是一个“绝好”茶叶市场的情报后,就开始觊觎西藏,以至英国两次侵藏战争都与谋求“印茶入藏”相关。然而清中叶以后,“川茶”对西藏的供应形成了稳固的地位加之“印茶”不适合西藏人民的口味等原因,直到20世纪初,“印茶”只是为数不多地被私运进藏。为改变现状,英国在第二次侵藏战争后急谋取得“印茶入藏”的特权。当时正值张荫棠奉命入藏“查办事件”,他有针对性地采取“教民种茶”与设“官运茶局”以加强“炉茶官营”,并在外交上与英方激烈抗争,坚决抵制“印茶入藏”,给急谋以“印茶”打开西藏市场的英国侵略者迎头一击。张荫棠“印茶入藏”是其藏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反对“印茶侵藏”斗争的重要一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于张荫棠抵制“印茶入藏”的研究,国内外只在“印茶入藏”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有所涉及。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史学家列昂节夫关注到了张荫棠与英方《中英藏印通商章程》谈判中有关“印茶入藏”问题的交涉。国内学界对此研究,民国时期虽有一些相关论著,但大都是揭批当时“印茶”挤占“川茶”的现实,学术价值有限。对“印茶入藏”的专题性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3年陈一石发表的《印茶侵销西藏及清王朝的对策》一文认为,张荫棠在西藏试种茶树、减轻课税,特别是在与英国谈判中坚持重税印茶的措施,“是抵制印茶的一次胜利”[1]。此后,陈一石先后发表了《清末印茶与边茶在西藏市场的竞争》《清末的边茶股份有限公司》等文,对印茶侵藏与清朝的应对等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董志勇发表《关于“印茶入藏”问题》[2]一文,对相关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印茶侵藏”问题的认识,此后有创新性的专题研究鲜有见闻。直到近年,方有学者从中印关系等角度探讨这一问题[注]① 如董春美、赵国栋论文,详见董春美论文《印茶侵藏:中印关系的历史检讨》(《南亚研究季刊》,2013年第1期);赵国栋论文《英印时期印度茶叶输入西藏及其影响》(《东南亚南亚研究》,2016年第1期)。。综观已有成果,大都注重“印茶侵藏”的宏观研究,对张荫棠藏事改革中抵制“印茶入藏”这一具体历史环节大多是一笔带过,尚未深入展开。一直以来,学界对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的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但未见对其抵制“印茶入藏”的专题性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据相关文献、档案等资料,专题探讨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中抵制“印茶入藏”的措施及相关问题,以期对此问题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一、“印茶入藏”问题的由来
“印茶入藏”源于英印茶叶资本家对中国西藏茶叶市场的觊觎。茶叶自唐代由内地输入西藏后,逐渐成为西藏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西藏自然形成了巨大的茶叶需求市场。历史上西藏茶叶的需求主要通过与内地的“茶马贸易”获得,汉藏“茶马贸易”由此成了西藏地方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清中叶以后,四川的打箭炉(康定)与松潘逐渐成了两大边茶贸易中心,西藏的茶叶贸易主要由此输入。乾隆时期随军进藏的周霭联所著的《西藏纪游》载,“由打箭炉入口买茶者,络绎不绝于道。茶形如砖,土人呼曰‘砖茶’”,“西藏所尚(茶叶)以邛州、雅安为最”[3]57-58。光绪十二年(1886年),驻藏大臣色楞额奏称:“藏中食茶一物,仰给于川。”[4]478光绪十八年(1892年),川督刘秉璋向总理衙门报告:“查川茶销藏,岁约一千四百余万斤,征银十数万两。”[5]1621904年,时任英国驻成都总领事霍西(Hosie A)到四川打箭炉调查汉藏贸易情况。据其调查,当年经打箭炉销往藏区的茶叶达11 377 333磅,价值白银948 591两,占当年经打箭炉销往藏区的内地产品价值总额1 052 591两白银的90%以上[6]351-352。总之,至清末中国西藏的茶叶需求主要由内地供给。
西藏巨大的茶叶市场存在的商机引起了英属印度的觊觎。众所周知,商品输出是殖民主义对外侵略的一个重要手段。英属印度在向外扩张中,不断开拓“印茶”市场即是其一个重要的经济侵略手段。早在乾隆时期,英印茶叶资本家就企图将印茶打入西藏市场[注]关于英属印度早期图谋“印茶入藏”的过程,详见董志勇论文《关于“印茶入藏”问题》(中国藏学,1993年第1期)。。19世纪3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试种茶树成功。此后,英印当局不仅在印度北部的阿萨姆等地建起了大片的茶园,并将茶叶种植扩及到了喜马拉雅山区与西藏接邻的一些地区。如大吉岭本系藏属哲孟雄土地,英国人“竟浸淫不已,种树植茶,开行设肆,规模既大,包藏祸心,逾岭百余里至布鲁克巴境,先在噶伦绷,继而广至波栋等处地方”[7]603。19世纪80年代,茶叶种植贸易成了英印最大的产业之一,并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茶叶展开了激烈竞争,这更加助长了英印当局谋划“印茶入藏”的野心,以致谋求“印茶入藏”成了英印蓄意与西藏地方通商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川茶在西藏的地位稳固,英印当局在要求取得茶叶贸易特权的同时,想方设法地排挤川茶。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头目荣赫鹏坦言:“孟加拉政府于一八七三年即力争印茶入藏事。”[8]321880年,英印当局指示英国驻重庆领事馆搜集中国内地各省输藏砖茶样品,供改进印茶工艺,以适应西藏人民的口味[6]150,加紧为英印茶叶打进西藏市场做准备。1886年一位俄国驻华官员指出:“按照英国人的想法,大吉岭茶叶若能向西藏大量倾销,即可把四川茶叶从西藏市场排挤出去。”英国人李通(Litton G)则赤裸裸地指出:“大吉岭的茶叶可以毫无疑问地破坏拉萨和它附近的中国茶叶贸易。”[9]29可见,英印的侵略本性及急于扭转与西藏传统贸易中的逆差地位,排挤川茶以获取“印茶入藏”的巨大贸易利润是其侵略西藏的一个既定目标。
对于英印当局谋求“印茶入藏”,不仅西藏地方政府断然拒绝,驻藏大臣色楞额等官员亦高度警惕。1886年色楞额奏报“近闻印度亦产有茶,一经与议通商,岂能禁其运藏出售”,一旦“印茶入藏”,“必使川省之茶无处营销”[4]478,但其并未能阻止英印当局图谋“印茶入藏”的步伐。1888年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后,英国从1890年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取得了“印茶入藏”特权。鉴于西藏地方群众坚决抵制印茶,英印茶商仿效川茶工艺,试制销藏印茶,“每磅成本二便士”,“成本虽轻”,但“藏人不喜印茶,称饮之腹痛”,因此,“印茶入藏为数极微”[5]163。
为改变现状,英方逼迫清政府继续谈判。1891年参与中英藏印交涉的英国人赫政(James Hart),欲以茶税利诱驻藏大臣升泰允许印茶入藏,向升泰称:“印度现为产茶之区,远近贩运,如设关免税三年,则印度茶叶必运入西藏,大有碍于此处茶税。愚意以为,惟茶叶一项,自开关之日为始,照章收税,不得援照各货免税三年之例,未知是否,请贵大臣详酌核办。”[10]1215升泰向其指出“藏民实不愿食印茶”,“看此情形,万不可行”;同时对赫政咨询川茶在藏销售及印茶入藏情况等,升泰回复“无法探询”,并申明“商上禁茶最严”[11]822-823。这使得赫政的图谋未能得逞,然而英国认为“茶叶应该是他们控制西藏市场的唯一产品。因此,他们竭力争取立即与西藏进行茶叶贸易”[9]29。为筹措抵制印茶,维护川茶销路之策,1892年,总理衙门就相关问题电咨刘秉璋,刘秉璋指出“藏番运川者不下数十万人,藏中穷番藉脚力以谋生,川藏交界处所藉以安谧”,“川省栽茶之园户,运茶之商贩,负茶之脚夫多至数十万人,悉赖此为生活。设使印茶行藏,占却川茶销路,必致中外商情星散,饷运周折,即凡业茶之户势亦无所聊生,何堪设想”,奏呈了“此事关系甚巨,贵署虽议棘手”,仍应“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川省幸甚,大局幸甚”[5]162的意见。总理衙门据此与英国进行交涉,因此在长达三年之久的谈判中,英国虽有通商、划界、游牧等其他侵略要求,但“双方争辩最激烈的是关于印茶输藏问题”[9]29。最终,1893年《中英会议藏印续约》第四款规定:“至印茶一项,现议开办时,不即运藏贸易;俟百货免税五年限满,方可入藏销售。应纳之税不得过华茶入英纳税之数。”[12]178该条规定虽暂时阻止了“印茶入藏”,但该条约的相关规定却也为日后埋下了祸患。
五年之后,英印当局以西藏地方不履行条约为由,迫不及待地重提“印茶入藏”等通商要求。对此,1899年十三世达赖通过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转奏光绪帝,表达了“应请一并禁止”[13]123的坚决抵制意见。但与此同时,英印茶叶资本家为追逐利润,对中方的反对置之不理。1901—1902年印度茶叶协会、印度孟加拉省商会分别向英印政府递交请愿书,请求采取措施迫使中国同意修改1893年有关条款,以便将印茶打入西藏市场[注]关于英印茶叶资本家向英印政府的请愿活动,详见董志勇《关于“印茶入藏”问题》一文。,1903年底英国赫然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可见,谋求“印茶入藏”是英国发动侵藏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1904年,侵藏英军逼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非法的“拉萨条约”后,遭到清廷及其他列强的一致反对,后经清政府与英方一年多的交涉,1906年4月双方重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国虽通过重订条约挽回了一定的权利,但作为附约的“拉萨条约”中关于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地设商埠的规定仍然有效,因此,抵制“印茶入藏”开始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
二、张荫棠抵制“印茶入藏”的措施
张荫棠(?—1935),字憩伯,广东南海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纳资为内阁中书,次年考取海军衙门章京。光绪二十二年随伍廷芳赴美充三等参赞,光绪二十三年改充旧金山总领事,寻调任西班牙代办[14]1287。光绪三十年任直隶补用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奉命以参赞身份随外务部侍郎唐绍仪赴印度与英方谈判重订藏约事宜,始与藏事结缘。次年,因他在谈判中的出色表现及对藏事的深刻见解得到清廷赏识,“著以五品京堂候补前往西藏查办事件”[15],随后“赏给副都统衔”[16]。1906年11月27日行抵拉萨后,在整肃吏治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地开启了清末藏事改革。1907年6月奉命赴印度与英方谈判《中英藏印通商章程》。
前文述及,在张荫棠进藏前“印茶入藏”已成了中英交涉的一大焦点问题。对此,张荫棠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人通商目的,首在于此。”[14]1400在此深刻认识下,张荫棠从内政方面采取“教民种茶”与设“官运茶局”以加强“炉茶官营”的措施,并在外交上与英方激烈斗争,坚决抵制“印茶入藏”。
(一)“教民种茶”与“炉茶官营”
张荫棠通过对茶业贸易的深入调研分析,得出了几点基本认识。第一,由于“开埠”在即,“印茶入藏”势难阻止。他指出“开议商埠,英必要求印茶入藏”,“三埠既准通商,不准运茶颇难措辞”[14]1377,并且他已探闻到两则消息:一是“印商大集公司,仿制炉茶,运藏零售”;一是英印茶商“由噶大克运至后藏茶,值卢比三十二万,将来可望畅销”[14]1401。第二,一旦“印茶入藏”,炉茶难以抵制,炉茶的既有利益链将遭破坏,进而将会引起严重后果。“炉茶市价一钱三分,至藏须购至二两五六钱”,“印茶无税路捷,炉茶运艰本重,万难相敌。炉税固将日绌,且川民岁失茶利数百万,商上岁放茶商债千万,久资为利薮,亦不愿印茶搀夺。然苦无法禁阻”[14]1377-1378。第三,印茶一时不能广销,但有潜在的市场。“藏民素嗜炉茶。印茶苦涩,一时未必能广销,但价廉,贫民乐于购用。数年后习惯自然,茶利必尽为所夺。”[14]1401在分析市场形势的基础上,张荫棠提出“以川茶子输藏,教民自种,以图抵制”[14]1330,即计划采取以“教民种茶”的措施,抵制“印茶入藏”。
“教民种茶”意味着要突破“茶法”对茶种的严格限制。为此,张荫棠向清廷详细论述了“教民种茶”的特殊意义及可行性后,请求“准茶种入藏”。他对西藏此前没有种茶的原因奏报“川素禁茶种入藏,藏愚不知自种,因得垄断居奇,关卡苛征,商上重利盘剥”,并认为“此闭关时愚民之术。今商战交通,物穷必变。藏民赴印度、汉口等处,均能购运茶种”。关于在西藏种茶的可行性,张荫棠报告:“查大吉岭、哲孟雄一带均能种茶,则西藏卓木、工部等处土性亦想能种。”关于“教民种茶”的意义,张荫棠认为,既可“免利权外溢”,亦可保护川茶。他指出:“若以炉茶茶种输藏自种,茶味不殊,而市价稍平,雅州茶利或犹可保……准茶种入藏,教自种,亦免利权外溢。”[14]1378通过充分论证,张荫棠在其全面藏事改革大纲性的“治藏十六条”中,最终确定“宜以炉茶茶种输藏,教藏民自种”[32]。
在“教民种茶”的同时,张荫棠意识到保护川茶是抵制印茶最为直接有效的措施。他认为:“(印茶)谋灌输入藏,恐难禁,炉税将恐日绌。第藏民现仍多不嗜印茶,似宜设炉茶官运局,务减轻成本,以平市价。”[14]1360为切实做到“教民种茶”与“炉茶官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张荫棠会同驻藏大臣联豫设立的推动全面藏事改革的“九局”中,就有“盐茶局”这一专门的职能机构,并制定有“盐茶局章程”五条。“盐茶局”设总办二人,委员八员,文案四员,专职负责“教民种茶”“炉茶官营”以及盐务事宜。“盐茶局章程”对“教民种茶”规定:“由四川省采办茶子,教民间自种。派人往四川、印度学种茶制茶之法。凡种茶宜于天气暖热之地,山坳岩间,当先从拉萨、工部、巴塘毗连洛隅野人一带和煦之地试种。”该章程对“炉茶官营”规定:“设官运茶局于打箭炉,务轻成本,照市价除运脚平沽,以抵制印度茶入口。又须分小包零卖,或每包一加刚,或两包一加刚,以便贫民零买。”[14]1347此外,张荫棠还提出:“至打箭炉茶税,或应豁免,或应酌减,以轻成本。并修理道路,以利转运,而省运费。”他认为只有对炉茶“除苛税,利运道,零售便民”,“庶炉茶数百万之利,或犹可保”。可见,张荫棠设“官运茶局”以加强“炉茶官营”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减税免税、降低成本等整顿措施,增强炉茶的市场竞争力。
为落实“教民种茶”,张荫棠“派打箭炉噶尔琫仔仲洛桑甲错替身,宜玛监参之商人阿旺落布前往打箭炉一带采买茶种,并雇觅通晓种茶工人携同回藏,择地试种”。为获得川督对“教民种茶”的支持,在派人入川采买茶种的同时,张荫棠向四川总督详细论陈了西藏种茶的理由:第一,西藏有适合种茶的土地,“只以风气闭塞,素未讲求”;第二,西藏人民有种茶的愿望,只是以前西藏人民到四川购买茶种时,“山户辄以炒熟之子与之带回,施种不能发生”;第三,当前为“川印茶一商战竞争时期”,西藏种茶可“免利权外溢”;第四,如果印茶入藏,清廷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是不独番商汉商交受其病,即川省茶厘亦将大受影响”;第五,如果西藏早种茶树,“犹足以相抵制(印茶)”;第六,“树艺兴、财赋瞻,他日以藏治藏,力可自给,不烦协拨,蔚为雄番,即尽免茶厘以通商运,俾争固有之利,犹计之得也”。最后,张荫棠请求川督协助采买茶种道:“贵部堂统筹全局,谅必赞成。除禀批示并给护札外,相应咨请贵部堂查照,希即分行司局,转饬打箭炉一带产茶地方文武员弁,暨关卡委员知照。凡遇该番商阿旺落布随带护札前赴该境内采买茶种,觅雇茶工,勿事禁阻。其携同回藏时,经过关卡查无夹带违禁漏税货物,即便验札放行,毋稍留难,以慰藩属向慕之诚,而示抚绥无外之意。实为公便。望速施行。”[14]1368当时,赵尔丰刚任护理四川总督兼川滇边务大臣,鉴于“炉茶入藏,为川省商务大宗”,他也正在为入藏炉茶“营销久已减色”筹措整顿办法。接到张荫棠请求后,赵尔丰立即行动,一面将其意见转发给雅州道府县清溪县,指出“茶为川商大利,一经印茶充斥,商民必致交困,危机可虑”[17]90,令筹议具体措施;一面向外务部建议:“布(茶)种入藏,联络主持茶务之商上为要点。”[17]89
张荫棠深知英国以建立藏印“通商”关系为名急谋印茶入藏的要求,是难以彻底杜绝的;同时,他也深知英国要求印茶入藏的严重后果,不仅意味着其对西藏的经济掠夺,同时也将祸及川茶,尤其是将助长其将西藏变为他们保护下的“独立国”的侵略野心。在此情势下,张荫棠饬立“盐茶局”,采取“教民自种”及设“官运茶局”以加强“炉茶官营”的抵制措施,饱含鲜明的“商战”意识。他向西藏地方上层指出“商战之败,害尤烈于兵败”[14]1334-1335,敦勉他们要积极筹措“不失主权,而兴商利”之策。具体而言,“炉茶官营”旨在保护川茶在与印茶的商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教民自种”则是为“扩充民利,抵制洋商”。总之,在印茶势难阻止的情势下,张荫棠采取的“教民自种”及加强“炉茶官营”的措施,旨在“商战”中打败印茶。他这一积极的应对策略,虽然满足了英国的“通商”要求,但使抵制印茶更具实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其不为传统束缚的“教民种茶”,为后世西藏种茶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影响深远。
(二)抵制“印茶入藏”的外交斗争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间,正值张荫棠推行藏事改革之际,清廷命其赴印度谈判《中英藏印通商章程》。同年七月十五日(1907年8月23日),张荫棠率西藏地方代表噶伦擦戎汪曲结布等抵达印度。同年七月二十二日,清廷降旨:“(张荫棠)著派为全权大臣,以便开议。”[18]随后,中英双方围绕藏印通商事宜展开了谈判,至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908年4月20日)订立章程,双方就“开埠”“撤兵”“关税”“印茶入藏”及“直接交涉”等具体问题进行了近一年的激烈斗争,其中“印政府以直接(直接交涉)、印茶为两大端”[14]1415。
张荫棠对“印茶入藏”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谈判中对英方的要求始终坚决予以抵制,谈判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印茶入藏的时间与征税两个相互交织的问题上。关于时间问题,由于受1893年《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及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等前约限制,张荫棠只能依据1893年条约中“(印茶)不即运藏贸易;俟百货免税五年限满,方可入藏销售”的规定,争取延缓免征百货税的时间而延后印茶入藏时间的策略。因此他拟订的“条款二十二条”中的第十四条规定:“西藏商务萌芽,中国现拟暂免出入口货税,以冀商务日旺。应照十九年旧约,俟征税后,印茶方许进藏。”[14]1385张荫棠也一再向英方申明,“税的问题,不是实质性问题。主要问题是忧虑雅州和拉萨之间的农村丧失生计和因此带来的贫困”,并坚持印茶入藏“无论如何应该给一个时期作为试验”[注]英国政府有关西藏事务函电(F.O.535),全宗535卷,第11卷,第58号文件附件1(1908年2月25日,印度事务部致莫利先生)。。然而英方全权代表戴诺(Sir Louis Dane)及其助手韦礼敦(E.C.Wilton),对张荫棠的“二十二条”,“尽行删驳”,其中对第十四条表示:“英商久图运茶入藏,不能允。”[14]1387后经五次会议,英方“仍坚持于关税印茶,驳之尤力”,张荫棠亦“逐条辨论”[14]1387。
英方的企图不只是印茶即刻入藏,还要求“华茶入印之税”这一很低的税率。当时“华茶入英,每磅征税五本士,起价值约九本士,几值百抽五十五分。华茶入印,估价仅值百抽五”[14]1406-1407。显然“华茶入英之税”与“华茶入印之税”两者“相差悬甚”,然而戴诺所拟订“十六条”中的第十一条提出了不超过“华茶入印之税”的苛刻要求,并在给英国印度事务部的报告中表示:“我们认为,茶叶是一项有希望在西藏大大增长的商品贸易,它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如果不能使我们的建议得到实现,将会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注]英国政府有关西藏事务函电(F.O.535),全宗535卷,第11卷,第7号文件(1908年1月4日,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对于戴诺的要求,张荫棠坚持自己所拟“二十二条”中的第十四条外,还提出“应照十九年通商章程,由今日起,再展后六年,由中国察看商务情形,可征税时即行征税,届时印茶方可进藏。将来所征茶税亦不得过于华茶入英之数”;同时,他向外务部密陈:“戴(诺)重视印茶,似故以关税留为互让地步,关税照陆路章程,由何时起征,系我自主权,英不能干预。”见于张荫棠态度坚决,戴诺又试图以各种理由取得印茶先进入西藏西部噶大克的权利。然而此时在英方利诱拉拢下,西藏地方代表“噶布伦等有愿征百货茶税,准印茶入藏之意”[14]1392,但后经张荫棠“反复晓谕”,他们始终“禀承张大臣训示,随同商议”,使英方“计不得逞”[14]1393。事实上,张荫棠当时得知已有“值卢比六十万”之多的印茶私运进噶大克,但他不受戴诺的征税利诱,表示“中国并不争此小税”,并对其各种借口予以一一反驳[注]英国政府有关西藏事务函电(F.O.535),全宗535卷,第10卷,第118号文件附件6(1907年12月4日,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后戴诺“第二次复稿”中,仍然要求征收百货税一年后即征茶税,印茶即时运进噶大克以及坚持“不得重过华茶入印之税”,张荫棠仍始终坚持“照征华茶入英之税”。鉴于戴诺要求的茶税太低,外务部也电告张荫棠“执约磋商,至要”[14]1406。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六日(1908年2月17日),戴诺向张荫棠递来“末次稿”十五条,其中仍坚持与西藏“直接交涉”等,但删去了“关税印茶”两条。对于此中原委,张荫棠分析认为,“(英印)茶商必不满意,英廷亦难批准。今故借此挑剔,持我所必争,以为要索地步”[14]1415,“揣其意以为照十九年约,五年限满,印茶已有运藏之权利,俟我征税时,再由英使与大部商定茶税也”。“末次稿”虽删去了“印茶入藏”条款,但面谈中戴诺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未抽百货税以前,印茶即可由印度边界运入西藏,其税不得重过华茶入印之税。但此事只准由印边界往噶大克商埠之路运至噶大克,照已定之税完纳,违此章者,应将此货充公,并重罚。”张荫棠当即与之争论,双方“因争论茶税照入英入印之数征收,意见不合”[14]1410;同时,张荫棠奏报:“查茶税照入英之数,十九年约既有明文,未便更改。诚如部电所云,但此次系因拉萨约有更改十九年约之语,则英亦可执此以请我更改。今既将此两节删去,在我似不宜再与提议。俟此次通商章程画押后,则我仍可执十九年约以征茶税。”[14]1411显然,谈判的焦点最终归结到了对1893年《中英会议藏印续约》第四款的不同解释上,英国政府虽也提出,“在支付不超过中国茶叶输入到英国的关税之后,茶叶可以输出去西藏”[注]英国政府有关西藏事务函电(F.O.535),全宗535卷,第11卷,第86号文件附件1(1908年4月23日,印度事务部致莫利先生)。,但戴诺宁可印茶只销往噶大克一地,也坚持“华茶入印之税”,并要求印茶即刻入藏;而张荫棠始终坚持“华茶入英之税”,并坚持征税百货税后印茶方可入藏,双方在印茶入藏时间及“入英之税”与“入印之税”上相持不下。
戴诺递来“末次稿”后限期两日画押,并威胁“若不能照此稿议定,就此告别”。期间“茶税”等问题虽反复争论亦未能达成一致,但清廷认为,“磋商至此,执事已煞费苦心,应即此签押”,同意张荫棠上述建议[14]1412。然而,张荫棠认为“在我已让至无可再让”,拒绝签押。戴诺威逼不成,遂离会返英。在此情势下,张荫棠担心英国驻华公使直接向外务部谈判,遂建议:“倘英使向大部提议茶税,乞查照删啸效电(啸、效两电内容如上述),相机因应。”[14]1411同时,他进一步分析形势后仍坚持“茶税不宜轻减”[14]1416。戴诺以离会相逼并未使张荫棠就范让步,张荫棠亦请示外务部将他撤回,“以示坚持之意”[14]1416。然而,此间外务部与英国驻华公使磋商中,“该使语意坚执,谓即戴签定,英政府亦不能批准”[14]1415,对戴诺“末次稿”中有关“直接交涉”等条“欲翻戴稿”,“几至无可商榷”。鉴于英使的态度比戴诺更为倒退,外务部最终取得了“握定”戴诺“末次稿”字句,“不令更易一字”的结果,并认为“此时实未便再改”,“中国主权似尚无大损”,遂电告张荫棠“与韦礼敦签押见复”[14]1417。按照外务部的指令,光绪三十四年二十日(1908年4月20日),张荫棠与韦礼敦分别作为中英双方全权代表,以戴诺“末次稿”为底本签订了《中英藏印通商章程》。
上述可见,《中英藏印通商章程》虽然签署,但“印茶入藏”问题悬而未决。张荫棠始终坚持“华茶入英之税”这一“重税”原则,使英方要求“华茶入印之税”的企图未能实现。更为重要的是,税则未能议定,从而使印茶入藏时间也无法议定,最终使得英印蓄谋已久的“印茶入藏”经济侵略要求未纳入《中英藏印通商章程》,其要求未取得合法地位。然而,英国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且当时已有印茶私运进藏之情,因此,该章程签定后,仍面临着严峻的抵制印茶入藏形势。如荣赫鹏认为:“中国当局对茶之入口则始终顽强固执,最后始勉强同意许印茶入藏,其税率不超过华茶之输入英国者,惟华茶输英之税率为每磅六辨(便)士……实际上即无异课以百分之一百五十乃至二百之税率,故此一让步直(真)毫无价值可言矣。”[9]39英国政府亦指出:“不能过分强调说我们的占领(春丕)要继续下去,直到对印度贸易有利的有关茶叶的条款为西藏和中国所接受。”[注]英国政府有关西藏事务函电(F.O.535),全宗535卷,第11卷,第1号文件(1908年1月2日,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为此,张荫棠接连向清政府、驻藏大臣、川督、西藏地方等致函,请预筹抵制措施。
在给外务部的建议中,张荫棠坚持“三埠印茶应可照华茶入英之数征收”[14]1419;同时,他从“当时会议情形”“川茶与印茶之比较”“川茶与藏地之关系”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抵制印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现拟办法”,其中指出,“茶税一项,不必因戴诺有存俟后议之言。果与英使有提议商订之事,径直照会英使,告以我国将定于某年月日在西藏起征关税”,“照华茶入英纳税之数办理”。他还就如何与英国公使交涉奏呈对策:“英使或将以另订茶税要求,与我开议,我则姑持初说以应之。倘必不允,然后于入英入印两数之间与议定一酌中税则,以示调合。彼或易从,而我亦不至过受亏损。”[14]1451-1452在给驻藏大臣联豫的叮嘱中,张荫棠强调要加强商埠管治,对英印茶商向噶大克等私运茶叶要派员“查明情形”,“详细禀复,以凭核办”[14]1421,同时要“特议茶税”[14]1422,以为征收茶税做好准备。总之,张荫棠不论是在谈判中的斗争,还是《中英藏印通商章程》签订后建议的应对策略,都是抵制印茶的直接措施。
三、张荫棠抵制“印茶入藏”的意义
英印时期“印茶入藏”的本质是对中国在藏主权的严重侵犯。在经济上,不仅是对西藏地方经济的掠夺,亦挤占“边茶”,严重危害民族茶业,进而割断西藏地方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清末张荫棠在其藏事改革期间,从内政、外交两方面坚决抵制“印茶入藏”的措施与斗争,具有鲜明的反侵略意义,暂时挫败了英印茶叶资本家谋求印茶合法入藏的企图,对维护国家主权完整以及西藏地方经济利益、民族茶业权益等具有积极意义。
第一,张荫棠抵制“印茶入藏”是其开启的清末藏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荫棠藏事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事、文教、卫生以及民俗等领域,他不仅在其改革的整体方案中有所规划,而且在行政过程中专设“盐茶局”,负责“教民种茶”与“炉茶官营”。后来,在外交斗争中,为抵制“印茶入藏”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总之,张荫棠抵制“印茶入藏”的措施兼具经济改革与外事斗争双重意义,在其藏事改革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抵制“印茶入藏”与西藏广大人民的意愿是一致的,这就为藏事改革争取西藏地方的拥护与支持提供了可能,进而对重塑中央在藏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教民种茶”改变了西藏之前无种植茶叶的历史传统。历史上茶马贸易逐渐发展为官营之后,茶法的主旨是“谓茶乃番人之命,不宜多给,已存羁縻节制之意”。清朝继承此惯例,以至四川对藏民购买茶种予以严格的限制,甚至如张荫棠所言,有四川茶户将炒熟的茶种卖给藏民之事。张荫棠积极协调“教民种茶”打破了西藏不能种茶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受此影响,十三世达赖继续派人到内地学习种茶技术,并委任孜仲·帕东群孜主持试种茶树事宜[19]128,获得成功。
第三,设“官运茶局”以加强“炉茶官营”的改革是对输藏边茶市场的一次整顿。清代四川的打箭炉和松潘成为输藏茶叶两大中心后,为汉藏经济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亦为川藏沿途百姓提供了谋生手段。然而,至清末之际,边茶“采制不精,且多搀伪”,加之“(茶)商愚无知”“毫无宗旨”“又狃藏嗜川茶之说”,以致“(川茶)行销久已减色”,且声誉日低。张荫棠规划设“炉茶官运局”以加强“炉茶官营”的改革方案对整顿输藏边茶市场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张荫棠抵制“印茶入藏”,是中国反对“印茶侵藏”斗争中的重要一环。张荫棠通过外交斗争,迫使英国没有通过《中英藏印通商章程》取得“印茶入藏”的合法权利。然而,1913-1914年,英国在其策划的西姆拉会议期间,其全权代表麦克马洪背着中国全权代表陈贻范,与西藏地方代表夏札秘密签订《英藏新立通商章程》,非法获取了包括“印茶入藏”在内的诸多特权。20世纪30年代,“印茶”最终得以侵占西藏大部分茶叶市场。从中国反对“印茶入藏”的斗争看,自英印茶叶资本家图谋“印茶入藏”至民国时期“印茶”侵占西藏茶叶市场,此中虽有清政府的反对,亦有一些驻藏大臣、川督的警惕,但大都未有实质性的措施。张荫棠抵制“印茶入藏”处于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后急谋印茶打开西藏市场的狂热期,其抵制给英方迎头一击。虽然清末张荫棠的坚决抵制措施只是延后了“印茶入藏”的时间,但这在整个中国反对“印茶侵藏”斗争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五,张荫棠抵制“印茶入藏”,是当时“华茶”与“印茶”在国际市场竞争的一个缩影。当中国茶叶停滞于封建的、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之际,印茶蓬勃兴起。19世纪30年代后,英印当局为种茶投入大量资本,并通过改进工艺、采用机器生产,雇佣印度大量廉价劳动力等,使其茶叶产量和销量逐年攀升,严重危及到中国茶叶在国际贸易中居于首位的地位。19世纪80年代,“印茶”已与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发生激烈竞争,“印茶”以其成本低廉、讲求工艺、使用机器加工以及“集各处之茶合归一公司统领”等优势,使“华茶受印茶及锡兰茶叶竞争影响”,“外销逐渐低落”。“从1885年到1900年中国茶叶出口到英国减少了几乎五分之四”[9]30,而“1850年印度茶始贩往英国,仅有四百八十八磅,至1887年核估约有九千万磅左右”,1887年前后“印度茶在英每年多销于中国茶有七百万磅”[5]175。至1905年前后,印茶在国际市场中最终取代了中国茶叶的地位。在“印茶”与“华茶”的国际贸易竞争中,英国始终把开拓西藏茶叶市场作为一个既定目标。
英印时期,英国以藏印“通商”为名要求“印茶入藏”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它不仅严重破坏中国民族经济,更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因此,抵制“印茶入藏”是中国反对侵略、维护主权斗争的一个焦点。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后,其对“印茶入藏”的要求更加迫切,中国的反侵略斗争形势也由此更为严峻。在此形势下,张荫棠在其以“收回政权”为核心的全面藏事改革中,采取“教民种茶”与设“官运茶局”以加强“炉茶官营”,以及在外交斗争中坚持“重税”印茶的抵制措施,切中反对侵略、维护主权的要害,不仅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而言,一方面,张荫棠与英方在《中英藏印通商章程》谈判中的斗争,给急谋以“印茶”打开西藏市场的英国侵略者迎头一击,使其“印茶入藏”的要求未取得合法地位,这就暂时挫败了英方蓄谋已久的图谋;另一方面,张荫棠敢为人先的“教民种茶”,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期间试种茶树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总之,清末张荫棠从内政、外交两大方面采取的抵制“印茶入藏”的措施,二者相辅相成,是其藏事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反对“印茶侵藏”斗争的重要一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