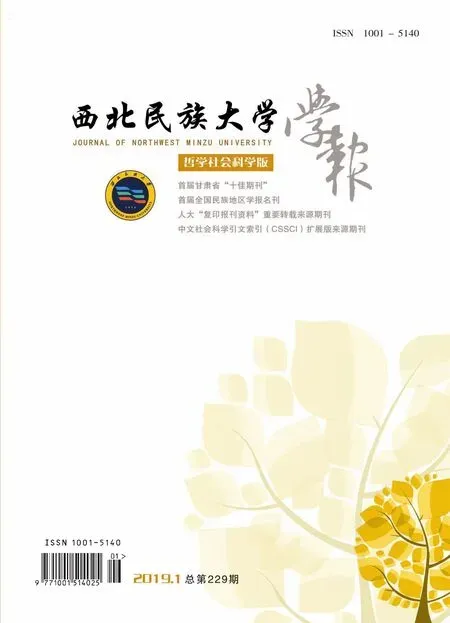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与反思
2019-02-20彭成广
彭成广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文化现代性理论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哲学思想及美学思想中较具特色的主题之一,对此,国内学界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由此出发,集中梳理概括中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的相关研究接受现状和发展脉络,并试图重点指出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既可以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做预期展望,又可以“以点带面”地确立整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本土化研究中的基本经验和核心问题,进而从侧面彰显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文化现代性理论的反思特质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与现代性一样,文化现代性也是一个从内部结构蕴含着张力与矛盾的复杂概念,无法从单一的维度去具体界定。有人主张文化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超越,也有人认为文化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面,是现代性的延续。本文倾向于后一种。因为从文化现代性理论的价值指向来看,它可以视为技术现代性或社会现代性的对立、补充甚至是制衡方而存在,是现代性的另一维度。以此,文化现代性承载着克服现代化进程中重重危机的重大使命而存在。“文化现代性话语的出现既是对社会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批判和补充,也是对它的一种纠补和超越,其根本一点是要克服社会现代化的负面后果,发扬社会现代化的积极方面。其核心思想并不复杂,概括起来说,就是:社会分化固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社会要想全面进化,还必须在分化的基础上进行一次综合,而且,综合的意义要远甚于分化。”[1]换言之,文化现代性既可以视为从文化的总体维度来审视现代性本身,也可以视为是对现代性整体工程作文化层面的批判与反思,包括对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表征、功能、价值、效用和走向等相关问题的思考。台湾学者钱永祥在总结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之后断言:“现代性的批判潜能,系于文化现代性的必须抗拒社会现代性的垄断、也必须抗拒保守倾向的前现代诉求。”[2]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现代性虽然在具体表现时倾向于采用艺术直觉的体悟方式,但它并不是一种有别于从社会、政治乃至经济等理性思考现代性的方法,而是从现代性的综合整体出发而形成的一种总体视野,把人类所有的文明创造乃至社会发展都理解为文化的表征。对此,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现代性从本质上就是文化的存在[3]。这样一来,文化现代性的概念就已经超越了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技术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等诸多局部性概念变成了总体性的现代性概念,进而把人的历史发展放到现代性进程中来,确立了人在社会进程中的主体地位。虽然这种确立方式在张扬人之主体性的同时,由于其过于笼统化而使得人们很难从学理上诊视作为社会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具体表征,但是,它把人之个性、价值的解放与发展放在最根本的位置,蕴含着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立场的凸显与延续,因而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一点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重要一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有着独特的价值内涵和强烈的现实诉求,一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期内,中东欧地区既是西方理性文明自觉的传承者,又是西方文明理性的直接受害者和牺牲者”[4],这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集中营大屠杀等极端体验,因此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是东欧各国遭遇了现代理性文明重创体验之后的现实诉求;另一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理论资源,它既是以卢卡奇为代表的对现代理性文明做深刻批判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张扬,又是以卡尔·波兰尼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批判传统的理论延续;再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思想还是东欧各国在直接遭受集权政治的束缚和压制下,进而切身参与艰难的社会主义变革试验失败之后的理论反思。因此,无论从东欧诸国丰富而独特的历史遭遇来看,还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诉求上来考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思想都具有深刻的体验反思和独特的理论价值。其中,文化现代性思想作为对资本主义理性文明的审视与反思的重要路径,尤其需要特别重视。文化现代性理论内涵非常丰富,无论是通过包含政治、经济、制度的总体性的文化维度来审视现代性的结构、矛盾、张力和内涵,还是通过诸如以文学、艺术乃至审美等价值领域的微观而具体的文化维度来对现代性做精神史的研究,都是文化现代性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于丰富现代性的认识具有鲜活而独特的借鉴意义。这一点在中国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已经引起了充分的注意并形成了普遍的共识。
二、中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研究的现状[注]本小节部分内容请参见拙文《中国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基本主题述评》,载《学术交流》2016年第6期,此处增添了相应内容。
(一)作为文化哲学的现代性批判
以衣俊卿等学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进而把文化置于人类生存实践的总体性位置。以此,他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论述也从文化批判维度给予了解读,这主要体现在《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现代性的维度》《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史研究》等系列著作中。受这一文化哲学思想的影响,黑龙江大学多篇博士论文(部分论文后来在此基础上成为专著)和系列研究文章,均以此为切入点,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文化审美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如孙建茵的《文化悖论与现代性批判——马尔库什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王静的《作为文化批判的审美——赫勒美学思想研究》、杜红艳的《多元文化阐释与文化现代性批判——布达佩斯学派文化理论研究》、员俊雅的《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诉求——斯维塔克文化批判理论研究》、李宝文的《具体辩证法与现代化批判——科西克哲学思想研究》和范为的《历史哲学中的现代性反思——赫勒的后期思想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著作涉及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如下学者或学派的理论著作:布达佩斯学派理论代表乔治·马尔库什(Gyorgy Markus,1934—2017)的《文化、科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阿格妮丝·赫勒(AgnesHeller,1929—)的《现代性理论》《现代性能够幸存吗?》《文艺复兴的人》、捷克哲学家伊凡·斯维塔克(Ivan Svitak,1925—1994)的《人和他的世界——一种马克思主义观》、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ik,1926—2003)的《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现代性危机——来自1968时代的评论与观察》,波兰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的《流动的现代性》《现代性与矛盾性》《作为实践的文化》、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ak Kolakowki,1927—2009)的《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和《理性的异化》,等等。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中国学界虽然主要侧重于从哲学角度解读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但是他们无不借助于文化、艺术等概念,来阐述分析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现代性批判思想。如王静在《作为文化批判的审美——赫勒美学思想研究》中就指出,赫勒的美学思想,是面临20世纪西方文明危机之现代理性主义文化的思考,赫勒从文化革命入手,把审美视为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最终形成独特的以人为解放的重构美学思想[5]。在赫勒看来,“审美维度无处不在,它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居于首要地位”[6]5,以此可以理解为:美与艺术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无关功利”,而是蕴含着否定现存、指向未来的具有强烈价值指向的具体样式,审美和文化是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形式。孙建茵从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现代性文化本身的矛盾特征这两个角度入手,对马尔库什的文化现代性理论做了整体把握,她认为,文化是现代性内在机制的集中体现,可以通过文化来管窥现代性的全貌[7]27。具体到马尔库什的文化现代性理论时,她这样概括:“悖论是现代性文化的基本特征,文化悖论是现代性发展的动力因素,维护文化多样性是解决现代性文化危机的路径之一。”[7]91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认为,以马尔库什为代表的整个布达佩斯学派都以多元化文化诉求为旨趣[8]。李宝文在《具体辩证法与现代化批判——科西克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对现代性批判的几种主要范式做了分类梳理,即语言研究范式、后现代研究范式、文化研究范式三种,这种分类具有代表性。在文化研究范式中,李宝文列举了三种不同的文化研究模式,即作为符号系统的文化、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文化、作为价值与阐释的文化。在他看来,最有效的现代性研究还是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性批判范式,而科西克无疑是这一批判路径的范式代表。科西克哲学思想的现代性内涵主要包括具体总体的、实践哲学的、存在人类学的维度,存在论与辩证法是其核心范畴。在具体论证中,李宝文详细阐述了科西克的“理性”“伪具体”“实践主体”“社会实在”等基本范畴,对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现代性也做了阐释性论述。吊诡的是,也许是由于文化批判强大的包容性所致,他最终得出了科西克哲学思想走向了文化哲学这一结论,并在文章最后以“现代性的文化批判论纲”的章节形式阐述了文化现代性批判理论[9]。杜红艳对布达佩斯学派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探析比较全面,她从价值层面、文化层面、历史层面和政治层面等四个维度做了总结,认为,“布达佩斯学派现代性批判的最终旨趣是为了在现代语境中实现现代性的重建,使之成为适应后现代政治状况的多元主义。”[10]这种认识也比较到位,因为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赫勒就明确承认过“后现代视角是对现代性的自我意识”[11]。彭成广在《现代性场域下的悖论与超越——赫勒文化现代性理论研究》一文中认为,赫勒的“文化话语”概念是文化现代性思想的集中体现,“文化话语”是为了解决现代性悖论之“高级的文化”和“人类学的文化”的矛盾而提出的,它类似于“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具有强烈的积极乌托邦色彩,蕴含着超越和否定现存社会的价值指向,从而具有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超越性意义[12]。颜岩在《现代性及其文化悖论——评乔治·马尔库什的文化现代性理论》一文中指出,“文化现代性是分析现代性的一种独特视角,它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为文化危机,主要关注上帝和一切神圣形象被罢黜后人类何去何从的问题,即世俗化的功利主义引导个体走向虚无主义、使生活的意义丧失、使人类变得无家可归这一问题。”进而认为,马尔库什通过强调“共同体”“公共领域”“信念”“批判的知识分子”等概念,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现代性的文化危机[13]。在《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诉求——斯维塔克文化批判理论研究》一书的导论中,员俊雅则认为:“文化批判其实是一种哲学批判,是从哲学的层面对当代社会从经济结构到政治文化制度、社会精神状态、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批判反思,是文化哲学的重要理论范式,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人化’理论。”[14]以此出发,她进一步认为,斯维塔克的文化批判理论以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为根本价值指向,以社会主义民主思考为现实关怀,是具有鲜明实践特征的人道主义理论。
(二)作为审美现代性的文化现代性
宽泛而言,审美现代性也应该属于文化现代性理论的一部分,所不同的是,审美现代性有两个基本维度,其一,审美现代性作为启蒙现代性,或者是作为社会现代性的补充面,必然要从超越异化和批判技术理性的维度赋予艺术、文学的本体论地位,以此来研究文学、艺术等美学现象的相应规律;其二,审美现代性强调审美感性、自律性和时间意识等特征,它必然不可能像文化现代性所确立的文化概念那样无所不包,审美只是其中的一种路径和一种方式,因此,审美现代性的内涵必然要小于文化现代性,但仍然属于文化现代性理论。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审美现代性思想的批判,目前中国研究界主要以赫勒及布达佩斯学派为研究对象,傅其林的专著《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可以视为代表。该书对审美现代性做了丰富的理论溯源,对审美现代性的内涵特征做了清晰论述,其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在此对其基本框架内容进行复述,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傅其林认为:“赫勒在揭示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特征、困境、矛盾的基础上挖掘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在古代美学、现代美学、后现代视域的碰撞中探寻当代美学的可能性出路,为当代美学的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赫勒把美学研究与对现代人的关注,对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人的可能性等意义的追求联系起来,走向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美学。”[6]215-216把人道主义美学作为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的基调,这种定位是基本准确的。同时,还有多篇论文也对赫勒的文化现代性思想均有提及,如在《论赫勒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想象制度和文化与文明的运动轨迹》一文中,彭成广认为,赫勒的文化现代性理论,可以她的两种想象制度来做类比说明,历史想象和技术想象可分别对应文化现代性和技术现代性,两种想象制度作为现代性的结构根源,他们相互制衡构成了现代性的钟摆运动。彭成广认为,“她既肯定以理性、科学为特征的技术想象的合理性,又反对现代性走向技术决定论的极端,为此必须以提供意义和阐释的历史想象来制衡;她既肯定技术文明的积极性,又正视技术文明的二律背反,凸显了以价值、伦理为特征的道德文明的重要性。”[15]
三、中国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研究的成效与问题
通过分析梳理文献发现,中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的本土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对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功能、价值与意义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或者至少越来越充分认识到,文化维度是现代性工程的重要透视棱镜,现代性的潜能与弊端、成绩与问题、走向与挑战等等都通过文化的形式得到集中体现;尤其是通过对赫勒、马尔库什、科西克和斯维塔克等人的文化现代性理论的研究,学界越来越体会到文化之于现代性具有批判超越功能,具有“总体性”的解放性质,是现代性工程微观透视的路径载体。如果说,以傅其林、孙建茵等人为代表,他们在界定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文化现代性理论时所确立的文化多元、人道主义、重构美学等主题,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主要内容的基本概括,那么,以衣俊卿等学人为代表所确立的文化哲学、微观哲学和日常生活理论等研究范式,就属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与丰富升华,而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融入到了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命运中,是典型的本土化成果[注]详见衣俊卿的系列专著:《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人民出版社,2005年)、《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再版)》(人民出版社,2005)、《现代性的维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等。。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除了中国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整体薄弱等共同问题外,对其文化现代性理论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第一,研究对象和主题有待进一步拓宽。目前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布达佩斯学……客观现实也许是赫勒、马尔库什等人的文化现代性理论最为集中,但是对卢卡奇的文化现代性理论的忽视就特别不应该。目前中国学界主要从社会学或政治学角度研究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总体性和阶级意识等概念,或者把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文论与“人道主义美学”割裂开来,而缺乏从艺术——生存本体论的维度来把握卢卡奇的文化思想,忽视了艺术乃至文化是自律性和批判性、内省性和超越性、特性与普遍的统一[注]“从哲学上论证审美的构成方式,对文学特殊范畴进行推导并界定美学与其他领域的界限”是卢卡奇《审美特性》一书中的主要内容。详见《审美特性·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页。。再比如,国内学界对斯维塔克的相关研究,目前也只停留在他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层面,但是在斯维塔克的著作中,有大量的艺术哲学美学思想集中于对艺术、人与世界之间的实践关系的辨识,以此凸显艺术与人具有本质性的内在关联,对艺术具有反抗异化、解放人性的本质属性的阐释等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充分重视。
第二,文化现代性理论研究的艺术本体论维度缺失。目前,中国学界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相关研究主要依附于政治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等研究,没有从艺术本体论的角度赋予文学、艺术的研究价值和主体地位,这必然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当然,不可否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确实是以社会批判和现代反思等社会学为主要测度,笔者也并非主张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与文学艺术话语割裂开来,而是认为,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丰富体验性而言,他们在如何看待文学、艺术的功能、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是一个充分值得研究的话题,而这些恰恰是文化现代性理论的核心问题。正由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环境的特殊性,即一方面深受西方理性文明灾难的重创,另一方面又在政治文化上受到的集权钳制,因此,文学艺术可以有效地逃避集权社会的政治肃清(当然很有限),文学艺术是担当社会批判的合适媒介。在理性文明毁灭性灾难之后,文学艺术还能干什么,即“奥斯维辛”之后到底还有没有诗,还能不能写诗,该如何写,诗的作用与功能有什么改变,这些问题必然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要思考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诗的外延也如同哲学、思想一样,具有形而上学性,诗的问题也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所以,诗与艺术的存在问题,本质上也是人的可能性问题。而结合这一向度来看,中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思想的相关研究远远不够。
第三,学理探究与鲜活体验的严重失衡。正如文章开头所提及的,由于文化现代性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包容性和总体性,这要求研究者在具体研究时,要从政治、社会、历史乃至文学作品等多维度综合透视,从而结合历史自身乃至所处国家与社会现实的鲜活体验来超越停留于学理层面的剖析推理,当然,这是一项理想式的全民参与工程。目前,单就中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研究而言,在具体研究时就存在学理探究与鲜活体验的严重失衡。具体表现在,由于时间、距离的限制,语言、文化的隔阂以及一手资料的欠缺,在面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时,无法从根本上把握它们产生的根源以及所蕴含的强烈价值指向和现实诉求,因此也无法感知它们的生命本能冲动,这对所有从事外国理论的研究者而言,也许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困境的难题。但是,这里仍然有一个比较直接有效的路径,那就是,从文学作品的体验和感悟出发,结合学理的演绎与分析,从而更好地宏观把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在中东欧国家,由于其特有的文化土壤和历史经历,产生了许多举世闻名的文学巨匠以及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其中就有很多直接以现代性乃至文化现代性批判为主题。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中国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的充分注意。比如,直接以技术异化和理性危机的反思为主题的就有:捷克著名剧作家卡·恰佩克的《万能机器人》《鲵鱼之乱》对技术异化的批判,罗马尼亚著名剧作家尤内斯库的《秃头歌女》《椅子》《犀牛》和贡布罗维奇的《费尔迪杜凯》比萨特的《恶心》还早一年发表,表现了理性文化危机时代的人的存在状况;而奥匈帝国卡夫卡的《审判》《城堡》《变形记》等系列小说又是对现代政治异化状况的反思,是对官僚极权异化体制的深刻揭露,等等。以文学艺术为表现载体对现代性的反思,可以视为文化现代性理论批判的具体再现。因此,如果在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时,能够适度地借助于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一时期、反映同一主题的文学作品来阐释和理解,就会更有说服力,也更能抵达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的实质。因为,毫无疑问,如果把文化理解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那么文学作品就是文化的内在肌理符码,进而融入到人的文化血脉之中。难能可贵的是,很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同时,也是作为文学家而存在的,比如卢卡奇、科拉科夫斯基,乃至宽泛意义上也属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波兰诗人米沃什等。
第四,文化现代性理论研究的本土化路径亟待加强。中国现代性计划的文化维度建设近年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从中国的文化哲学或文化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到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弘扬,乃至中央以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制度设计,无不把文化问题提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确立了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应该正视的是,文化自信还处于建构阶段,如何立足中国传统与国情现实,充分借鉴外来理论资源,找到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的联结点,研究界还需要倾尽全力扎实推进相关研究。在借鉴外国理论资源上,我们看到,中国研究界主要还是停留在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所确立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上,尤其侧重于借鉴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性路径,而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资源宝库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如前文所述,对现代性的文化反思,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最具理论特色和现实价值的部分,而且,东欧各国由于大都亲身参与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试验,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们以此形成的理论反思对于处在社会主义改革深水期的中国而言,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性和鲜活的借鉴参考价值,因此,如何借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来反思乃至重建中国现代性是一个庞大的理论工程,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界充分注意的问题。
总之,本文以中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为例,试图集中表明一个根本问题,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具有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多元的思想价值,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发展还是助推中国现代性的良性运行,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仍需进一步加大推动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