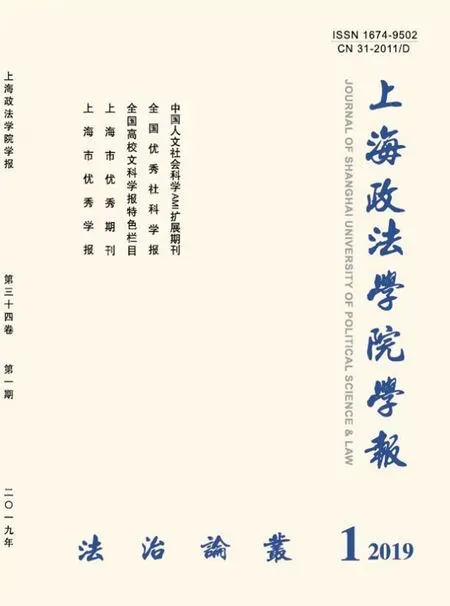政治协商在国家治理中的结构性作用
2019-02-19赵强
赵 强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国家的改革富强之路也已经走过了40个春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我国独特的一项宪法制度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一起诞生的,也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接续传统并且一起继续成长壮大的。21世纪之后,随着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引进和传播,国内学界主要是政治学和法学学者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①参见协商民主理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可参见谈火生的2篇文章:《协商民主:西方学界的争论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7期;《从民主研究的“协商转向”到协商民主的“经验转向”》,《联合时报》2015年3月31日。但是,有些学者在将协商民主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研究时却出现了某种时空的错位:简单地将既有的协商民主理论直接拿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实践,将其广泛地应用于各个制度领域的决策过程的研究;或者将中国既有的政治协商会议看作是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将政治协商直接等同于协商民主,导致在西方社会成长出来的协商民主理论和中国的政治实践出现了时空和理论的错位,给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混乱。笔者认为,正是这种理论的错位为协商民主理论的扩展和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提供了广阔的探讨空间,本文厘清了协商民主理论和中国的政治协商各自的理论和实践传统,为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一、协商民主理论的产生、传播及其理论面向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也有学者将其译作“审议民主”)是西方学术界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一种理论,是对70年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进一步扩展。其理论渊源是一些学者对既有的、以代议制为主要制度形式的精英民主的不满,认为这种民主方式限制了普通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是对民主的“悖反”。为了实现更为民主的社会,必须探索和实践新的民主方式。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就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产生的。但协商民主真正引起西方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两位政治哲学大师加入了讨论之后。①关于协商民主理论的介绍,可参见[美]约·埃尔斯特:《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周艳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澳]约翰·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丁开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协商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庄则克曾经指出:“在1990年前后,西方政治哲学经历了一个审议转向”,正是这一转向,“重塑了我们关于民主的想象”。②参见陈胜勇、何包钢:《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地方民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协商民主含义的关键在于Deliberative一词,其含义是审慎的反思,与中文语境中“协商”一词所包含的协商、妥协之意并不完全对应,因此,有学者将其翻译为“审议民主”更符合其本意。从学术精确性上来说,笔者也更赞同这种翻译。但从学术传播角度来说,协商民主在中国已经广泛地被人们接受和认可,虽有词义的错位之处,但是协商民主也是能够表达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方式的。就其理论来说,协商民主本身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审慎的反思,即个体自身独立地对问题进行审慎的思考;二是个体之间就所关心的议题进行理性的讨论。这两层含义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理性的讨论是建立在审慎思考基础上的。反过来,经过理性的讨论又会促使个体对该问题进行反思,让个体改变对该问题的最初看法。”③谈火生:《协商民主:西方学界的争论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7期。
从实践层面而言,协商民主理论认为民主不仅仅是投票,也不仅仅是参与,而是强调在投票和作出决策之前对公共议题应该有一个公共审议的过程。公民能够通过自由而公开的讨论,一方面深化民众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希望使作出的公共决策更符合公共利益。与参与式民主相比,协商民主不仅强调民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更强调参与的品质和决策的质量。协商民主也正是期望民众通过对公共决策审慎的参与培养出一种更强的公共意识,塑造一种更有活力的公共生活。
在分析和研究西方社会产生的协商民主理论时,我们需要注意以下3点:一是协商民主理论是在反思代议制民主缺陷的基础之上出现的,但是协商民主并不是反对代议制民主,也不是为了取代代议制民主,它是作为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和扩展形式而存在的。代议制民主是西方国家宪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任何一种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都无法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宪法制度的基石。协商民主更多地是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扩展民众的参与程度和提升参与的品质;④[澳]约翰·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丁开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二是协商民主理论作为一种扩展公众参与的民主实践形式,在西方现有的宪法制度中并没有像代议制一样的固定的制度实践场所,其理论诉求也并不是在既有的宪法制度中谋得一席之地。正是由于这样的理论定位,使协商民主在立法、司法、行政以及社会团体的公共决策的过程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实践空间,也获得比较广泛的认同。三是协商民主的扩展,一方面要求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共团体都要有比较强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也要求民众要有比较强的参与欲望,在这两个基础之上,协商民主的目的——提高参与的品质才能更好的达成。
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社会产生之后,关于其协商的主体、参与的方式、达成的目标、适应的范围等方面一直存在着比较广泛的争论,其批评者甚至认为,“协商民主是一个美丽的幻象,很难落实到实践之中,很难以制度化的方式有效运作”。①谈火生:《协商民主:西方学界的争论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7期。而协商民主理论在21世纪之初被引入到中国之后,却获得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和认同。协商民主最早出现时,也是将其翻译为“审议民主”的,但是到中国大陆之后,学者们却普遍地将其翻译为协商民主。“将其译为协商民主,易于与本土资源结合,并更容易在中国推行。关于这一点,几乎所有的人都有高度的共识。”②同注①。这里的本土资源指的就是中国宪法制度中特有的政治协商会议,翻译成协商民主能够使协商民主理论与既有的制度之间达成某种契合,以促进中国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扩展。同时需要注意到的是: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不是在协商民主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在中国的宪法制度中有着独特的起源和地位;而引进到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也并没有将其理论的应用场所局限在政治协商会议之中,协商民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其实践方式上,其理论的内涵和外延都要远远超过政治协商会议所包含的范围。③参见谈火生、于晓虹:《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议题与挑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11月。随着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也进一步加深了学者对政治协商制度的研究。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宪法地位及其功能
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在新中国的革命历史中出现的一种制度形式。这种制度最初的形式是1946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5个方面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其目的就是为了商讨新的政府的组织方式,现在通常被称为“旧政协”。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基本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主要的政治力量,会议本身也取得了不错的协商成果。这次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虽然讨论的都是关于制宪建国的重大问题,但其本身并不是制宪会议,当时的制宪会议是随后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只能算是制宪的准备会议。虽然这次政治协商的成果没有能够延续到国民代表大会中去,但是,这种政治协商的会议形式给当时的社会各界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旧政协的召开为新中国直接采用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完成制宪建国打下了社会基础。④参见高全喜、田飞龙:《协商与代表:政协的宪法及其变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时间转到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告终,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战争的方式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制宪建国的主动权,但是革命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因,其本身并不能完成制宪建国的任务⑤同注④。,能完成建国任务的、赋予新的国家政权以合法性的方式是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当时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召开全国范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不现实的,因此,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了一个可选择的方式。
1949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了与“旧政协”相区分,通常被称之为“新政协”。与旧政协只是作为一种协商沟通机制不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次“制宪会议”,其会议的召开和制定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赋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准生证。①参见陈端洪:《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人民制宪权——论1949年〈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建国宪法的正当性》,《原道》2012年第1期。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之所以能够成为“制宪会议”,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主要在于其具有的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以及当时社会条件下支持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吸纳到政治协商会议中来,而且,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战争的方式将反对力量排除在了制宪进程之外,使其获得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成为一次具有“实质正当性”意义的“制宪建国会议”。
在1949年建立的“政协体制”中,政治协商会议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存在的,但是其最高权力的赋予只是暂时性的,而非永久性的。根据《共同纲领》第13条的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显然,当时的制宪建国者们已经意识到了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形式正当性”意义上的缺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只是作为未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替代性制度载体而存在的。随着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国家最高权力的使命也随之结束,但是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制度遗产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进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制度平台并没有被取消。其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的制度平台仍然具有广泛的社会活动空间,它作为凝聚社会共识和政治认同的制度载体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1982年宪法的制定,中国共产党重新制定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把各民主党派定位于“既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的政治定位。参政党的定位赋予了在革命建国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完成制宪建国任务的民主党派以宪法地位。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按照地域原则,而不是按照党派原则选举产生的,民主党派是不可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体制下活动的,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多党合作制度运行的重要制度平台。但是,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不仅有8个民主党派的存在,还有各种社会团体和各功能界别优秀人士的代表,使其具有了更广泛的功能代表的属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我国宪制中的地位还要从我国宪法的一项最为基本的原则说起,这就是人民主权的原则。人民主权原则是现代各国宪法体制建立的基本原则,在去神化和去魅化的现代社会中,国家权力的基础及其正当性只能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如何将人民主权原则应用到具体宪法制度中,在各国的宪法实践中并没有一定之规,不同国家的宪法制度根据自身历史传统和实践经验发展出了不同的实践方式。虽然具体的制度设计有着各种的差异,但是以代议制作为人民主权原则在常态宪法运行制度中的表现方式则基本上获得了共识,直接民主的方式只在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国家或者是一些特定议题中保留。
在既有的宪法理论和制度设计中,我国宪法体制中的人民主权原则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表现和承担的。我国《宪法》的第2条将这一原则和制度设置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按照代议制原则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普选中采用的是间接代议制,而不是直接代议制。《宪法》第97条规定:“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这使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构成中加入了“科层制”的因素,这里的科层制并不是指官僚制中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科层制,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举科层制。选举科层制的引入主要是考虑我国地方人多的社会情况而选择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代议制所要求的选民与代表的直接联系,使其在功能上不能直接将选民的意志和利益诉求反映到国家权力体系中去。
政治协商制度的存和良好运行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间接代议制原则在功能上的不足。与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按照地域原则选举产生不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原则主要是按照党派和功能界别原则组织构成的,其在中国社会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些组织构成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并不是普选代议制下的代表,因此他们也不需要代表具体的选民。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各个行业、领域的精英,是在各个民主党派和社会行业中产生的“天然代表”,他们能够将自身行业和功能界别的利益诉求和观点反映到公共决策和立法过程中去,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代议制功能的不足。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的参政议政也能够提高公共决策和立法的质量。①参见马一徳,《宪法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及其法治化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存在不仅仅因为其固有的宪法传统和宪法地位,还因为其在我国现行的宪法制度框架下发挥着独特的参政代表和功能代表的作用,这也是每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都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内在机理。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着协商民主理论的理论诉求,因此,将其视为协商民主理论实践的重要场所也未尝不可。
三、作为协商民主理论重要制度基础的政治协商会议
在前面的分析中,分别梳理了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历史传统及其宪法地位和功能,从中可以看出,两者分别有着自己的理论诉求和实践领域,除了中文“协商”一词能够使两者发生关联外,两者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理论上的相关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协商”对应的英文是Consultative,其意为协商、咨询,并没有Deliberative一词所包含的审慎、反思之意。政治协商是中国人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完成制宪建国任务的一项特殊创造,再经过历史改造和沉淀之后成为中国宪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协商民主理论传播之前,中国的官方和学界一般也不将其描述为一种民主方式——协商民主。但正是由于中文构词的巧妙,或者说是大陆学者“有意为之的错译”,使协商民主理论和政治协商制度之间发生了关联,促进了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的快速传播。
由于中国既有的政治协商制度和历史传统,使得中国官方能够接受协商民主的理论定位:一方面将既有的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实践场所,重新深化对既有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定位和功能定位,另一方面也将协商民主的实践扩展到其他政治领域的实践中去。《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首次将协商民主提升到国家战略层次,并将协商民主的实践从政治协商扩展到立法协商、行政协商中去。在促进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落地和实践方面,既有的政治协商会议传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看到协商民主的“错译”促进了协商民主理论的传播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西方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协商民主理论并不等于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或者说其理论的诞生并不是为了解决国家顶级层面的宪法制度问题。其理论是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社会的条件下发展出来的、扩展政治参与的一种民主理论,其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与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都有很大的不同。
协商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诉求就是通过自由而公开的讨论使公众能够参与到公共决策中去,进而提高决策的质量,这一理论诉求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功能定位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在政治协商会议中理论和实践方式的不足难以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每年在政协会议期间,各种“奇葩提案”和“无营养提案”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于这些提案大部分都不是建立在公开讨论基础上的理性建议。①政治协商在我国存在一些问题可参见周洪宇:《政党协商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而协商民主理论所主张的建立在“公开讨论基础之上的审慎决策”,则能够为提高政协委员们的提案质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由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功能定位和产生方式,不仅使其在中国社会中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也使其在立法和公共决策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西方社会中的协商民主理论所没有的制度依托。“与西方相比,中国具有优秀而独特的协商民主资源,即曾经发挥重大历史作用的协商体制”②马一徳:《论协商民主在宪法体制与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这也正是协商民主在中国扩展和实践的基础。协商民主的理论的引入也能够使政治协商会议发挥其在宪法体制中应有的结构性作用。
除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之外,我们也应看到两者的差异和诉求不同之处,从而避免两者之间混乱和错位。
第一,协商民主理论本身并不追求固定的制度实践载体,其作为一种民主的实践方式可以扩展到所有的制度和决策形式中。在西方社会中,协商民主是在比较成熟的宪法制度条件下产生的,其在国家制度层面无法获得自己的政治空间,其理论本身的定位也不在此。协商民主在政治和社会多元领域中的作用主要致力于提高民主参与的水平和公共决策的质量。中国的学界也没有将协商民主理论仅仅限定在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于协商民主制度的定位是“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③《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人民网,访问日期2018年5月20日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只是协商民主实践的重要领域之一,而不是唯一。切不可将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直接等同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实践和发展。从协商民主的理论定位和实践场所来说,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与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是一致的。但由于有政治协商会议的存在,使得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有了特殊的意涵,也有了与众不同的实践场所。
第二,协商民主理论和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弥补既有代议制体制的不足,但其应对策略则是截然相反的。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的产生和扩展,一方面是由于对精英民主的不满,在既有的代议制民主的条件下,民众只能通过选举议员来进行政治参与,无法直接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去;另一方面由于官僚机构做出的公共决策质量不高,不能很好地反应社会和民众的利益诉求,因此,协商民主理论期望通过强化普通民众对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从而提升公共决策的质量,其方向是沿着参与民主的方式向前推进的。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功能定位是提升国家权力的代表性,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外设置政治协商会议,使多元的社会力量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具有“天然的代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选举科层制”在功能上的不足。但这种“天然的代表”仍然是精英民主的属性,能够参与到政治协商会议中的代表基本上都是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中的精英人士,而不是普通民众,但也正是由于这种精英属性,使其提案和建议更能达到协商民主所要求的“慎思”。①参见马一徳:《论协商民主在宪法体制与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第三,协商民主追求的是达成审慎而理性的公共决策,其目的在于能够直接影响和参与公共决策。协商民主中的“协商”并不是协商、妥协之意,而是指将决策建立在公共讨论之上。“协商民主的产生恰恰是试图超越利益博弈的政治观,将政治建立在理性、讨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将政治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考量之上,而不是私利竞逐的基础之上;将政治建立在对共识的追求之上,而不是对政策的控制之上。”②谈火生:《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议题与挑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而政治协商会议本身独特的属性使其不具有决策权,它具有的是参政议政的提案建议权。由于政协委员的提案不是真正的决议案,这也恰恰能够为委员的提案提供更为广阔的审慎思考和理性辩论的空间。要想使政治协商会议更好地发挥其提高公共决策质量的功能,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协与立法技工、行政机关的沟通、联系渠道;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协委员们提高提案的质量,能够为立法和公共决策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方案。
综上,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成为协商民主重要的实践场所,协商民主理论的诉求和功能定位和政治协商会议有很多契合之处,这为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获得了其独特的实践和成长空间。我们在将协商民主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践时,也应注意到中国特有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环境,为协商民主理论的扩展贡献中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