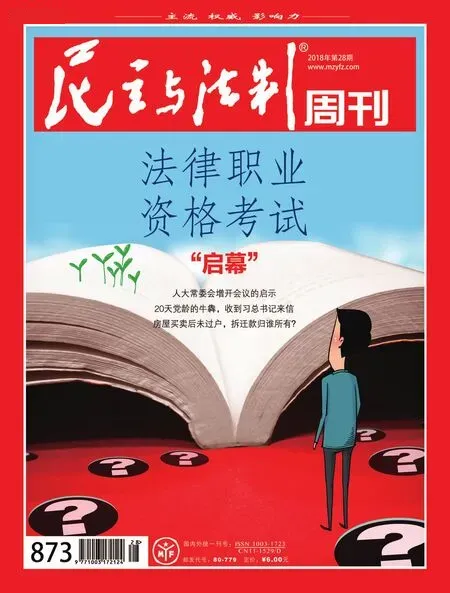人大常委会增开会议的启示
2018-11-17阿计
阿计
7月9日至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并展开专题询问,同时审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此次会议不仅集中聚焦于环保议题,而且打破了每隔两月开会的惯例,距离上一次常委会会议尚不足一个月。这在人大议政史上,极为罕见。
开会,是人大议事行权的基本方式,其时间节点、频率多寡、会期长短等等,决定了国家权力机关能否平稳、高效地运转。追溯起来,改革开放后人大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正是源于开会困境。由三千名左右代表组成的全国人大,虽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人数过多、每年仅开会一次且会期短暂等短板,也导致其难以应对繁重的议政事务。相形之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人数有限且相对专职化,具有便于经常开会、及时高效议事的优势。正因此,1982年新宪法正式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权,进一步明晰了其他重要职权。与这一政治改革相伴的,则是会期制度框架的奠定,1987年出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就明确规定,常委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如有特殊需要,可以临时召集会议。而在实践中,经过历届常委会的不断探索和改进,目前已形成了双月下旬开会、会期4至7天的惯例。
事实证明,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扩容以及会期制度的规范化,彻底终结了开会随意紊乱的历史,根本扭转了人大权力虚置的局面,对于改革和法治事业的前行居功至伟。不过,相对于双月开会惯例的成型,“临时召集会议”的制度设计曾长期束之高阁。具有转折意义的是,上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期间,已经两次激活了这一机制。其一是辽宁贿选案发生后,常委会于2016年9月增开会议,以创制性的应急方案,妥善解决了辽宁省人大的“停摆”危机。其二是为了满足监察体制等重大改革的紧迫需求,常委会于2018年1月再次增开会议,通过相关议案和修宪草案,为宪法的及时修订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上述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增开会议,更多侧重于议题的“紧急性”;那么,此次增开会议则纯粹体现了议题的“重大性”。由此也标示着,这一特别开会机制的实践,正在向更广、更深的维度演进。不难想象,倘若将环保这一关涉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纳入惯常的会期安排,很可能遭遇议事时间不足等困窘甚至淹没于众多议题之中。而以增开会议的方式专注于单个议题,正是为审议报告、通过决议、专题询问等多种行权手段的综合性、全方位运用,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充分验证了集中议政资源、提高议事效率、加速问题解决的效应。
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打破开会惯例,“增开会议”由沉寂渐趋活跃,其破冰色彩和改革动向可谓鲜明。由此也意味着,为了进一步激活、发挥这一开会机制的价值功能,需要将其纳入更加完善的制度化轨道。比如就适用范围而言,目前相关议事规则中“有特殊需要”的表述显得过于粗疏、模糊,有必要采用“紧急性”“重大性”等更为清晰的标准,并对其作出明确界定。再比如就启动主体而言,除了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外,可以考虑一定比例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议,即可增开临时会议。
从更长远的视野看,人大常委会的会期制度还面临着深度改革的挑战。一方面,按照目前的制度和惯例,常委会每年开会总时长仅有一个多月,相较于许多国家议会每年开会时间长达半年甚至9个月左右,差距显著。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常委会所议决的立法、改革等事项日趋繁重复杂,议事时间不足的瓶颈愈加突出。就此而言,近年来有人建议常委会会议由“两月一开”改为“一月一开”,也有人主张将每次会期翻倍增量,均不乏建设性。
同时应当认识到,会期制度改革并非会次、时长的简单增减,而是需要综合考量利弊得失。频率过低、会期过短,固然不利于常委会履职行权。频率过密、会期过长,则会挤压必要的时间成本,对会前准备、议案质量、落实决策等造成负面影响。正因此,如何立足现实国情和政治体制,合理平衡民主的成本与效率、制度的创新与保守、行权的规范与灵活,将是未来改革的核心所在。而由此塑造的更为科学完备、务实高效的会期制度,对于进一步焕发人大的职权功能和行权活力,至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