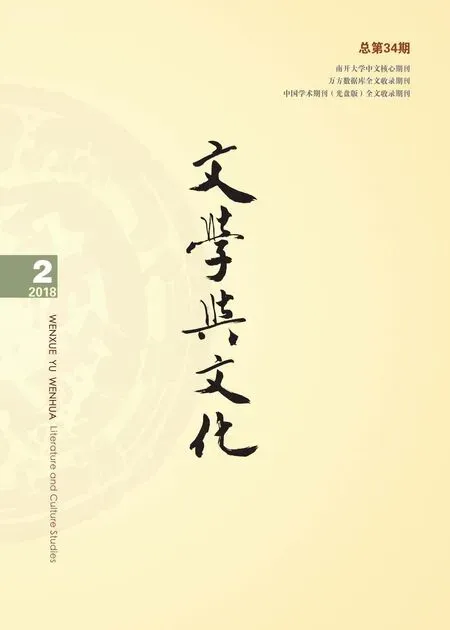欲望政治与文化身份想象
——穆时英小说、流行音乐与跨文化现代性
2018-11-13郭诗咏
郭诗咏
内容提要:1923年1月24日,中国第一家广播电台在上海试播,机械复制声音媒介开始进入上海居民的生活。之后几年,无线电收音机作为一种新的家用产品,开始展现其市场潜力。与此同时,上海的唱片业开始进入黄金时代。随着这些新兴的机械复制声音媒介的普及,流行音乐逐渐成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的重要娱乐。作为“上海新感觉派圣手”的穆时英,不但是当时上海文坛的传奇人物,更是最早跟流行音乐紧密互动的中国现代派作家。过去穆时英的研究,鲜有论及其作品与当时上海流行音乐文化的互动。本文尝试从个案分析入手,考察穆时英小说与外国流行音乐的互文性。本文认为,穆时英对当时欧美和东亚地区流行音乐的征引和转化,不但使其小说呈现出高度风格化的氛围,而且建构小说人物的情绪及欲望。穆时英藉挪用外国流行音乐如爱尔兰民歌、日本流行曲等,成功把歌曲中的感伤情绪、浪漫想象和情欲流动移植到中国新感觉派小说。此外,本文亦将考察穆时英小说中的跨文化互文性,分析作家如何揉合外国流行曲及间谍小说文类来创造出复杂的文化身份想象,藉此了解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世界主义及现代性。
一 引言
上海新感觉派由一群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作家所构成,当中包括刘吶鸥、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邵洵美、黑婴等。这群新感觉派作家大都曾在大学学习外语及研读外国文学,通晓两种以上外语(英语∕法语∕日语),能直接以原文接收外国信息。他们阅读上海外滩上的外文书店所能买到的外国报纸、西方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书籍,在风格和品味上深受西方和日本现代主义影响。在他们心目中,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早已过时,而中国现代文学应当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前卫文学、先锋文学同步。与此同时,他们亦过着西化的都市生活,喜欢看欧洲及荷里活电影,聆听西方古典音乐和外语歌曲。他们常常流连于咖啡店、跳舞场、夜总会和电影院,也喜爱外国香烟、洋酒、荷里活明星、探戈和狐步舞。以上种种,均成为了他们的小说素材,共同建构出文学世界里的上海摩登与颓废。
很多研究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新感觉派是中国最早的现代主义作者。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是汉学界海派文学研究的里程碑。李欧梵从文化史的角度出发,结合作家研究和文本细读,考察了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与现代主义文学生产的关系。在此以后,许多研究者延续了李欧梵的观点和研究方向,使“现代性”成为了相关研究范围里的关键词。这些研究大都围绕上海都市文化、城市再现、地景(landscape)和视觉文化等,而李今、史书美、彭小妍是当中出色的研究者。
李今在《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里,细致地分析了蒙太奇作为电影技巧,如何具体地落实到穆时英和刘吶鸥的小说叙事。史书美在《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中,详细地剖析了上海新感觉派的重要主题,包括心理分析、颓废、半殖民主体性、世界主义和都市文化等。而彭小妍则在《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一九三零年代上海、东京及巴黎的浪荡子、漫游者与译者》里,将新感觉派的写作模式视为一种“旅行”的文类或风格,以法国为源头,经日本再传到中国。彭小妍强调,现代性只有在跨文化场域中才是可能的。按她的意思,所谓“跨文化”,是指打破过去与现在、精英与流行、国族与地区,文学和非文学、内和外等等分野。
受到以上研究启发,本文将通过个案研究,集中讨论穆时英小说中的跨文化互文性与现代性的生成。有别于其他研究者,本文将特别强调流行音乐和机械复制声音媒介在穆时英小说中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随着新兴的机械复制声音媒介如无线电广播、留声机和唱片,以及跳舞场等娱乐事业的兴盛,流行音乐逐渐成为30年代上海市民的重要娱乐。当时被誉为“上海新感觉派圣手”的穆时英,不但是当时上海文坛的传奇人物,更是最早跟流行音乐紧密互动的中国现代派作家。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流行音乐不但使穆时英的小说呈现出高度风格化的氛围,而且同时突显了小说的感伤情绪、浪漫想象及欲望流动,并在跨文化互文性中创造出复杂的文化身份想象。
二 流行音乐与穆时英小说
无线广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新兴声音媒介。1923年1月24日,中国第一家广播电台在上海试播,机械复制声音媒介开始全面进入上海居民的生活。之后几年,无线电收音机作为一种新的家用产品,开始展现其市场潜力。为了配合迅速发展的广播事业,1927年上海有了中国人自建的广播电台。1931至1932年短短两年内,上海就新增了30多座广播电台。到了1934年,上海已经拥有54座电台。与此同时,上海的唱片业开始进入黄金时代。借着无线电广播、留声机和唱片,上海市民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享受全球各地多种多样的音乐。
翻开穆时英的小说,我们可发现里面另有一个流行歌曲的世界。家中会客室里的无线电播音机播着Just once for all time,书室里的小型无线电播送器放送着《春江花月夜》;周末在户外“行Picnic”的时候,年轻的绅士淑女更会带上留声机。如果跳舞场的靡靡之音只对恋人有意义,那么无线电播音机则是属于寂寞的单身者的。在穆时英笔下的世界里,无线电播音机与寂寞的人紧密联系着,是待在家里的独身者的良伴。《Craven“A”》里寂寞的女主角,家中除了养了一只白猫,还有一架无线电播音机。穆时英甚至让他的男主角说:“‘独身汉还是听听音乐吧!’就买了个播音机。”当然,对“穆时英式”的独身汉来说,没有女伴的话,干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新感觉派中,穆时英对歌曲的利用最为频繁,他有一半以上的小说曾出现具体中外歌曲名称或直接征引歌词。这些歌曲的功能几乎可与现代电影里的歌曲叙事看齐,其功能包括烘托故事气氛、作为段落过渡、推进或暗示情节、描绘人物的思想感情等。在他的小说中,乐曲出现的方式也有特别之处,除了作为缩排的引文出现外,它们甚至会有特别的标记,例如《PIERROT》,歌曲前后都加上了“——插曲——”的字样。这些直接抄写歌词的段落出现得相当突兀,有点像默片中的字幕页,突然打断画面,产生出某种类似“间场”的效果。一般而言,一首歌的歌词和乐曲是紧密结合的。对熟悉该首歌曲的读者来说,文本中的歌词就好像一个机关,暗示他在心里跟着唱。就像在电影中途播放插曲,又或早期戏曲电影,穆时英在讲故事时不忘“插播”歌曲,在读者的脑海里奏起流行曲。当时有声电影刚开始在上海上映,穆时英这种崭新的写作方式,着实令人惊异,同时使他的小说走在时代尖端。
以下将围绕《Craven“A”》和《某夫人》两篇穆时英小说作个案研究,以文本分析为起点,考察穆时英如何挪用歌曲来配合小说叙事和人物塑造,藉此探究穆时英小说与外国流行音乐的跨文化互文性,并管窥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世界主义及现代性。
三 《Craven“A”》与《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
《Craven“A”》是一篇浪漫的爱情故事,叙事者为一位男律师,在跳舞场里邂逅了一名神秘的女子。Craven“A”是叙事者对女主角的昵称,也是一款当时流行的外国香烟品牌。因小说涉及香烟的品牌,不少学者在分析小说时,都会将小说的重点放在消费文化及现代都市男女的情色关系。然而,这里我希望从另一角度切入,从小说所征引的流行音乐出发,重读这篇小说。
除了香烟品牌,《Craven“A”》里反复提到的还有一首来自爱尔兰的民谣,叫做《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The Last Rose of Summer)。只要对照爱尔兰诗人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的原词,我们就可以发现整个故事实际上是对原曲歌词的一次重写:
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的开放/所有她可爱的伴侣都已凋谢死亡/再也没有一朵鲜花陪伴在她的身旁/映照她绯红的脸脸庞和她一同叹息悲伤//我不愿看你继续痛苦孤独得留在枝头上/愿你能更随你的同伴一起安然长眠/我把你那芬芳花瓣轻轻散布在花坛/让你和亲爱的同伴在那黄土中埋葬。//当那爱人金色指环失去宝石的光芒/当那珍贵友情枯萎我也不愿和你同往/当那忠实的心儿憔悴/当那亲爱的人儿死亡 /谁还愿孤独的生存在这凄凉的世界上
无论是女主人的美丽、孤独、寂寞和凄凉,还是男主角对她的怜惜和陪伴,甚至那没有清楚交代的死亡,皆由歌词转化而来,俱能在原词里找到线索。歌曲和小说的互文关系,不但构成了故事的框架及人物形象,更为这篇都市浪漫恋曲创造了充满感伤和罗曼蒂克的情调。
在故事里,《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首次出现在男女主角初次相遇的时候。那一刻,夜总会音乐台轻轻飘起的正是这支“很熟悉的”、有“感伤的、疲倦的调子”的老歌:
音乐台那儿轻轻地飘起来的是一只感伤的,疲倦的调子,《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很熟悉的一只民谣。
这是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
独自地开着;
她默默地坐着,我默默地坐着。在我前面的不是余慧娴,被许多人倾倒着的余慧娴,却是一个寂寞的,疲倦的,半老的妇人的剪影。
《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的出现,使小说出现了情绪的转折。在此以前,小说的调子相当活泼佻皮,夹杂大段对女性身体的欲望想象,以及跳舞场内男女客人调情的语句。
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知道女主角在六岁时从母亲那儿学到这首歌,十分喜欢,于是一直记住,后来更把这首歌教给男友及之后的男友们,可惜他们均一一离她而去。“这支歌是和我的一切记忆,一同地存在着的……”小说透过女主角的回忆,初步建立了她和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的连系。
而更重要的是,女主角跟歌曲及歌曲中那朵特别的玫瑰花逐渐建立起比喻关系:
没有人怜惜她颊上的残红,
没有人为了她的太息而太息!
这两句歌词在小说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女主角首次出现时,来自乐队的演唱;第二次是女主角凄凉地向男主角诉苦之后,太息似地唱出了这两句,而男主角亦深深为“这颗寂寞的心”而叹息。在男主角眼中,女主角既是“半老的、疲倦的、寂寞的妇人”(对应民谣的旧),又是“年青的、孩气的姑娘”(对应夏天的玫瑰的美)。在小说的叙事设置中,歌曲是男主角情感的中介,当他随着《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的乐曲,对当中的玫瑰花产生了怜惜之情,因着移情作用,他同时怜惜起眼前的女主角。
在后来的几次见面里,这对男女由单纯的聊天发展出肉体关系,但他们始终没有成为固定的恋人。在故事的结尾,男主角完全失去了她的纵影,只收到她留下的信笺,最后《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的歌词再次出现,表达男主角的惋惜和叹喟:
我坐下来,在桌上拿了支Craven“A”抽着,从烟雾里飘起了一个影子,一个疲倦的,寂寞的,半老的妇人的影子。
这是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
独自地开着。
抽完了烟,我便把那把钥匙放到一只藏纪念物的小匣子里边,我预备另外再配一把钥匙了。
Craven“A”香烟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Craven“A”香烟是男女主角关系的隐喻,暗示那是一种只求短暂欢愉、快速的情欲消费。穆时英聪明地利用了《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去刻意强调叙述者的内在情感。这最终使小说人物及小说文本获得了内在性及情感的深度,超越了其他平面化的通俗小说。
四 《某夫人》与《银座行进曲》
至于《某夫人》,是一篇少受注意的女间谍的故事,而这次穆时英引用的是昭和时期的日本流行曲《银座行进曲》。在这个个案中,我将分析文本里跨文化的互文性,分析作家如何揉合外国流行曲及间谍小说文类来创造出复杂的文化身份想象,藉此了解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世界主义及现代性。
《某夫人》所引用的《银座行进曲》,是1928年(日本昭和三年)的一首日语流行曲,由女歌手沢文子(又名沙轮富美子)主唱。沢文子从大正末年开始在关西走红,是相关受欢迎的歌手。当时在日本十分流行以“行进曲”(March)为名的歌曲,除了《银座行进曲》外,同期还有《道顿崛行进曲》、《东京行进曲》等,歌词内容大多描写这座新兴都市的华丽风貌。以下是《银座行进曲》其中两段歌词:
国贞えがくの乙女もゆけば、华宵ごのみの君もゆく、宵の银座の音匡
“タイガー”女给さん文士が好きで、“ライオン”ウェイトレス淑女気取り、“クロネコ”乙女はお洒落者
两段歌词可意译为:“若国贞画的少女前去,喜欢华宵的你也会去,晚上的银座八音盒/‘TIGER’女接待喜欢文人,‘LION’女侍应作态淑女,‘黑猫’少女是时尚之人。”歌词里的“国贞”指歌川国贞,其为日本江户时期著名的浮世绘画家,笔下的女子颓废好色;而“华宵”则为高畠华宵,是大正至昭和时代的日本画家,经常为杂志刊物和广告提供插画,他所画的美少年、美少女和美人画极受欢迎。至于文中提到的“TIGER”和“LION”,是当时银座相当有名的咖啡店。
《银座行进曲》里的少女们既性感又烟视媚行,而且乐于跟男性打交道。填词人正冈容把当时最新的流行时尚写入歌词,而这首歌后来也成为流行文化的组成部分。歌词中“华宵ごのみ”一句,隐含“现代男子”(モガ,モダンガールの略)的意思,后来更流变为当时的流行用语“华宵好みの〇〇スタイル”(华宵喜欢的〇〇风格)。
一旦理解这个背景,《某夫人》的女主角哼起《银座行进曲》就一点不足为奇了。我们无法确实得知穆时英是从唱片抑或无线声广播的日本音乐时段听到了这首歌,但肯定的是,他觉得这首歌跟女主角很相配。歌词中征引的各种文本,构成了一道洋溢着性感、异国情调和现代感的东洋风景线,呼唤着读者对歌川国贞、高畠华宵和银座咖啡文化的想象,尤其是当中的女性形象的想象。虽然在这篇小说中,穆时英只提到了《银座行进曲》的歌名,并没有如《Craven“A”》般节录歌词,但考虑到这首日语流行曲的流通情况,当时的上海部分读者或许对它相当熟悉。穆时英巧妙地把自己的小说作品置入当时的东亚流行音乐文化语境,藉此开启读者的异国和情色想象。
《银座行进曲》在小说里共出现了四次,其中首尾两次构成了完美的呼应。在故事的开端,日本特务机关调查科科长山本忠贞少佐坐上了一架离开哈尔滨的火车,他听到隔壁的卧室有一个“带一点汉城口音”的女子在唱着《银座行进曲》。这“北国的忧郁的歌声”随即使山本浮想连翩,觉得“那个不知国籍的女人是一个很可怀疑的人物”,同时对女子的身份和身体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但他很快就凭她的歌声作出总结:“总之,不会是一个贞节的女子吧。”
后来在餐车的偶遇使山本更加按捺不住,遂以侦察为名,强行进入女子的卧室并搜查她的行李。在搜查的时候,女子又“丽丽拉拉地唱起《银座行进曲》来”,并接受了山本色情的问询。山本后来发现她企图走私烟土,于是要挟她,要她做三天的“山本夫人”。可是,正当他们到达长春,快要欢好之际,山本收到了宪兵司令冈崎义的一通电话,告诉他这名女子其实是著名的女间谍Madam X。在等候冈崎到来时,女子显得相当镇定,再次“轻轻地唱起《银座行进曲》来”。令人惊诧的是,山本不久后在沈阳再一次遇到Madam X,她向山本暗示自己与冈崎做了身体交易,并以此诱惑山本。山本再次上当,最后被取走了藏有进攻辽东军事密件的帽徽。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她从浴室里拿了一大堆衣服出来:
“你不是说把绯色的亵裤穿了起来,就是印度的禁欲者也没有法子保持独身了么?现在我就穿给你看,报答一下你的过份的称誉。”
她一面嘲笑着他,一面穿好了衣服:“莎育娜拉,特务机关调查科科长山本忠贞少佐!”走了出去,终于在房门外低低地唱地《银座行进曲》来。
《某夫人》在情节和对话设计上都非常露骨和色情。女主角的形象设定显然为典型的蛇蝎美人——非常诱人,同时非常危险。在这篇弥漫着危险气氛、色情想象和异国情调的小说中,Madam X由此至终都是山本的欲望客体。与小说的开端遥相呼应,穆时英巧妙地安排了“视觉的缺席”,突显声音的诱惑性。最初,山本隔着车厢的墙壁,听着歌曲,幻想女子的万千风情,开启了欲望之门;到了结局,山本同样隔着房门,听着歌曲,回味女子的美丽身体。作为全篇色情的顶峰,Madam X穿绯色亵裤的文字描写始终付之阙如。
“视觉的缺席”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我认为,从这个叙述设置中可以观察到,穆时英的小说正在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回应(又或复制)着机械复制时代的流行音乐聆听经验。机械复制时代的音乐聆听经验与古典音乐和戏曲不同,音乐被剥离于音乐的原生环境,听者并不处于演奏者或唱歌者的表演现场。尽管听者仍可看到眼前的东西,但因不是演奏现场,其间的阅听经验是画、声分离的。作为以唱片、无线电为播放中介的流行歌曲,《银座行进曲》所提供的聆听经验,原本并不存在实存的视觉色情元素,需依靠歌词为能指,来召唤与歌川国贞、高畠华宵和银座咖啡女侍有关的文化记忆,来填满色情的想象。正如《银座行进曲》歌词所指涉的少女唤起了听众(包括穆时英)的欲望,由Madam X唱出的《银座行进曲》也唤起了山本(也是读者)的欲望。可是,无论是少女还是Madam X,她们却始终是“只可‘想象’而不可亵玩”的客体。在整个故事中,女子的裸体作为山本的终极欲望客体,最初和最后均处于可“闻”而不可“触”的位置,“名贵的宝物”总是因各种突发情况而失落。至于读者,他们在文本中也只能一直跟随山本的视角,对Madam X的身体浮想联翩,却看不到任何实际描写。机械复制时代的流行曲的聆听经验被置换入文学文本,在“视觉的缺席”的叙述设置中,Madam X的身体作为空洞的能指,一如《银座行进曲》中的各式少女,一直召唤着读者的欲望。
《某夫人》的背景为二战前中国东北的中日谍战,但穆时英并没有把它写成一个精忠报国的故事。Madam X的国族身份是模糊的,她探听日军的情报,其汉城口音却反映她或有朝鲜背景(当然也可能是假扮的),效忠对象亦未能确定。这篇小说的文化身份想象可说是相常复杂的,它摆脱了当时左翼普罗文学敌我二元对立的模式,尝试从一个较为广阔的多边关系中开展其谍战世界。此外,这篇小说的女性人物塑造,也呈现出跨文化的审美趣味,以及开放多元的国际品味,而不局限于同期中国现实主义文学里温柔婉约的女子。一个身份迷离的韩国(?)美女,两个日本军官,一首性感的日语歌曲,一列开往东北的火车,一桩荷里活式的多重间谍案,穆时英最终为读者呈上了非常异国风情的粉红故事,以及面向国际、全球流通的世界主义文化身份想象。
五 结语
以上从《Craven“A”》和《某夫人》两个个案分析入手,尝试考察穆时英小说与外国流行音乐的跨文化互文性。总结而言,本文认为,穆时英对当时欧美和东亚地区流行音乐的征引和转化,不但使其小说呈现出高度风格化的氛围,同时建构小说人物的情绪及欲望。穆时英藉挪用外国流行音乐如爱尔兰民歌、日本流行曲等,成功把歌曲中的感伤情绪、浪漫想象和情欲流动移植到中国新感觉派小说。我期望本文能够证明,流行音乐在穆时英的小说中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而借着了解穆时英小说中的跨文化互文性,我们当能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有更深刻的认识。
从流行音乐的角度出发,我们可看到新兴的机械复制声音媒介,是如何启发穆时英的故事构思和叙述手法。当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些音乐文本有时是源于作者的亲身接触,有时可能来自他们的主观想象,又或跟书本、电影的文本现代性有关。即使如此,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上海新感觉派作家以其独特、尖新的表现手法,在中国本土开拓出一种书写现代都市及生活的新风格。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新感觉派作家在内容上并不力求深刻,反而致力追求时尚的情调。这使他们与当时新兴的、带有通俗性的声音媒介、视觉媒介之间出现了某种亲和性。他们抱开放态度,不避世俗和流行,弹性地把多种新兴媒介纳入其写作实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的作品强烈地带有时代的痕迹。尽管当年的新兴发明和新兴事物如今已是明日黄花,但他们的作品为我们保留了处身现代新兴大都会的作家初次面对资本主义新兴媒介时的惊奇反应,同时显出了极其开放的、敢于与时代潮流同步的世界主义文化身份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