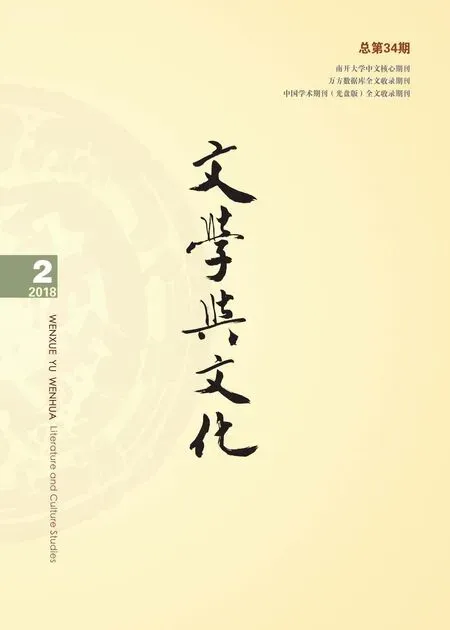“白贲无咎”本义考
——“以白为饰”与“饰极反素”之辨
2018-11-13李沁锴
李沁锴
内容提要:对于《周易·贲》卦上九爻“白贲无咎”的爻辞,后世注家多释之为“饰终反素”的至美,以至成为影响我国古代美学观念发展的重要命题。但是细味《周易》原文,其对“白贲”的占断仅为“无咎”,并非上吉,令人不免生出疑窦。本文即从这一矛盾出发,通过梳理各家观点、分析“白贲补过”之说、辨别“白贲”“素履”之义、解读与“白贲”相关的论述,来探寻该爻辞的本义,得出“白贲”的含义当为“以白为饰”,而“饰极反素”则更可能是后人的误读和演绎而非爻辞原意的结论。
《周易》原为巫史之作,卜筮之书,其目的在于“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周易·系辞上》),以期乎“决嫌疑,定犹与”(《礼记·曲礼上》)。其言辞,既以“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的特色吸引着一代代研易者孜孜不倦的苦思与求索,同时也对中国文学的写作风格与思想观念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其高度简约的表述方式,迷离惝恍的拟象之辞,为后世提供了极大的阐释空间,但也给正确的释义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诚可谓“最多者《易》解,最难者《易》解”。
由于上述特征,导致了《周易》几乎每一卦的卦爻辞都有不止一种解说,《贲》卦也是如此,尤其是对上九爻之爻辞“白贲无咎”的解释,就存在着各不相同的观点。本文拟将考察的焦点集中在对我国审美观念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白贲无咎”一辞上,通过对各家注解的比较分析以及《周易》文本的语义考辨,希望尽可能还原出该爻辞的本义,以校正以往的某些误解。
一 对“白贲无咎”的不同理解
前文已经提到,在阐发“白贲无咎”的意义时,各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现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例引述如下:
王弼《周易注》:“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任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以白为饰,而无患忧,得志者也。”孔颖达疏云:“‘白贲无咎’者,处饰之终,饰终则反素,故任其质素,不劳文饰,故曰‘白贲无咎’也。守志任真,得其本性,故《象》云‘上得志’也。言居上得志也。”王弼认为,“白贲无咎”所表现的是饰终反素、止而还素,即最终回归本真的状态,孔疏也是基于此义而略加发挥。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于“白贲,无咎”下注有“白,素也。此言上九居《贲》之极,‘贲’道反归于素;事物以‘白’为饰,则见其自然真趣,为纯美至极的象征,故‘无咎’。”其说与王弼、孔颖达无异。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贲而曰白,其为物也明矣。若训为饰为文为斑为黄白色,(范望《太玄》视首上九注)为色不纯,(高诱吕觉贲字注)此二字皆不能通。诸儒据绘事后素,曲为之说,无当也。盖艮为贲,贲无色,故曰‘白贲’”。这种说法与其他几种说法区别较大,否定了将“贲”训为杂色、为文饰的解释,将“白贲”与“明”结合起来理解。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认为“白贲者,就素为杂色文采也”,并引《考工记》“凡画绘之事后素功”语及《论语·八佾》“绘事后素”语为证,认为:“此皆所谓白贲也。白贲者,由质而文之象,此自无咎,故曰白贲,无咎。”“就素为杂色文采”就是说先白后贲,在白色的底子上施加各色。在语法上,此说与其他认为“白”修饰“贲”的看法恰好相反,是认为“贲”修饰了“白”,“白贲”就是“贲白”。
除了以上四例,还有许多学者针对“白贲无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此不一一列举。众多说法中,大多数意见近于王弼“饰终反素、任其质素”之说,以“素”解“白”。“白贲”处于一卦之终,意味着返回最为天然单纯的境界中去,不需要加以文饰。这种“白贲无咎”的观念,为后来美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孔子的“思夫质素”、老子的“见素抱朴”、墨子的“尚质”;到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的“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再到苏轼的“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乃至于刘熙载《艺概·文概》的“白贲占于上爻,乃知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几千年的文学思想与审美观念,“白贲”身影隐现其中,可以说它已经成为衡量艺术作品价值的一项很高的标准。
二 “白贲”所补何过?
“白贲”对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如此深刻,以至后世学者纷纷以“白贲”为至美,赞许并追求这种“白贲”之美。但若回过头来,将“白贲无咎”放在《周易·贲》卦的原文中重新审视,则免不了会产生一些疑问。《贲》卦中对于“白贲”的占断辞只是“无咎”,相比其他如“元吉”、“亨”、“无不利”等占断词语,并不算是极好的寓意,在吉凶之间显得更为中性,更为“平淡”。这种“好评度”的矛盾使我们不禁要探寻其中原因。那么,把“白贲无咎”解释为“饰终反素、任其质素”,在后来获得高度评价与认可的这种说法,与最初“白贲”获得“无咎”占断的依据是否相符?也就是说,这个认同度最高的“饰终反素”的阐释究竟是不是“白贲无咎”的本义,抑或是我们的观念同先民出现了如此的差距?在这些疑问的驱动之下,我们有必要重新进行一番考察与辨析。
高亨在《周易古经今注》卷首作有《吉吝厉悔咎凶解》一篇,详细说明并统计了《周易》五种基本占断辞的含义及出现的位置、次数、组合形式。在谈到“咎”时,高亨引《说文》:“咎,灾也。从人从各,相违也。”《尔雅·释诂》:“咎,病也。”并以《吕氏春秋·侈乐篇》“弃宝者必离其咎”及高诱注“咎,殃也”为证,说明“咎”当作“灾祸、忧患”解,《广雅·释诂三》也有“恶也”的说法。接下来高亨还阐述了“咎”在几种占断辞中所指向的吉凶轻重程度:“但《周易》所谓‘咎’,比悔为重,比凶为轻。悔乃较小之困厄,凶乃较大之祸殃,咎则较轻之灾患也。‘无咎’谓无灾患也。”由此可见得“咎”是程度处于“悔”和“凶”之间的占断,而至于“无咎”,就是“没有灾祸与忧患”。《系辞》云“无咎者,善补过也”。可见“无咎”在《周易》中还有着“恰当地弥补了过失,因而免遭咎害”的深层含义。孔颖达疏曰:“无咎者,即此卦象能补其过,若不能补其过,则有咎也。”从这些内容来看,“无咎”自是不比“吉”、“利”、“亨”这些带有好兆头的判定,也不似“无攸利”、“吝”、“凶”明确表示将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作为占断辞,它所表达出的应是介乎吉凶之间的中性意义——补过则无咎害,免咎亦非大吉。
具体到《贲》卦第六爻上,“无咎”的占断辞代表上九本有咎害,所幸“白贲”“能补其过”,因而避免了灾患。那问题随之而来——上九之“咎”为何?“补过”又是用了怎样的方法?前人关于“无咎”的原因与根据所言较为简略,造成了理解上的难度,令人对“守志任真,得其本性”之说可以正确解答前面的疑惑,弥合“无咎”与“至美”间的价值缝隙抱有或多或少的怀疑。
在笔者看来,“白贲”是“以白为饰”,但并非“饰终反素”,而且这两种描述间存在明显差异。前者虽然饰以白色,但终是“有饰”,而后者已然“无饰”。一卦中最上一爻,一般表示了事物发展的最终阶段,《贲》卦中的“白贲无咎”应该是针对前者而发,而后者更像是释者进一步的演绎,或可算作“白贲”继续发展的一种结果,不能作为其本意理解。如果相反而行,将“饰终反素”作为“白贲”本意,就会存在以下矛盾——作为自然纯美至极的“白贲”所蕴含的价值不应只得到“无所咎害”这样非吉非凶、反响平平的判定;因为假如“不劳文饰”便可以“无咎”,那么“不贲”或“无贲”应该比“白贲”更适合出现在爻辞当中。
那么,按照“白贲”即“以白为饰”的推理,上九面临的“咎害”是什么?“白贲”又是怎样“补过”以致“无咎”的呢?首先,《贲》卦核心为文饰之道,上九爻作为事情发展盛极将衰的节点,即文饰过度就会有“文灭其质”之过,为了达到“补过而无咎”的目的,必然要采取措施,这个补救措施就是“白贲”,减少颜色数目而以单一的白色修饰,矫正了“文以害质”的危险,突出的是文质相称而达到的最佳效果。另外,笔者还有一种推测:据梁寅《周易参义》于六四爻“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下有“六四在离明之外,为艮止之始,乃贲之盛极而当反质素之时也,故云‘贲如,皤如’。……人既质素,则马亦白也”的解说,笔者注意到,六三爻“贲如,濡如,永贞吉”且“终莫之陵”,细味之有文以称质、相辅相成之象,而到了六四爻“皤如”“白马翰如”,色彩开始趋于单一,再到六五爻“束帛戋戋”,“戋戋”者,数量减少,有艮止之势出现,乃至上九之时,艮势最强,因而面临“无饰”之过,上九遂以“白贲”补过,用最简单的颜色同一所有“贲”法,终不违“贲”道主旨,既求得了“无咎”的结果,又符合艮卦趋向。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测的一种可能,如有不周密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白贲”所补过错,是“文过其实”之过,也可能是“无所文饰”之过,同时也不排除两种顾虑同时存在,“白贲”取其折中。但无论是哪种过错,“饰终反素”解读下的“白贲”都无法作为“补过”的手段而成为其准确的内涵,“以白为饰”的“白贲”才有“善补过”以实现“无咎”的可能。“《贲》卦所强调的,应该是文饰不尚华艳”,至于“质素”之大美,恐非原文所言及,更非“白贲”本意。
三 “白贲”与“素履”
对“白贲”的解释能由“以白为饰”到“饰终反素”,其原因最可能是在于借“素”来训“白”,从而导致了“饰终反素”的出现。“白”与“素”之间,因为意义的相似性在某些场合确实可以互训,但除了相似性,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二者之间存在的不同以及互训后含义上的细微改变。在《周易》中,除《贲》卦使用的“白”,还有《大过》卦初六爻的“藉用白茅”;使用“素”的有《履》卦初九爻“素履,往无咎”。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曰:“《履》初言‘素’,礼以质为本也。‘贲’,文也,《贲》上言‘白’,文之极,反而质也。‘白贲无咎’,其即‘素履往无咎’与?”“白”和“素”意思的近似,再加上相同的占断辞,令作者察觉到“白贲”和“素履”之间或许存在联系,可以互参理解,但有联系不代表全部同一。接下来笔者就以这两个词组为例,探讨“白贲”、“素履”的不同及“白”与“素”语义着重点的差异。
荀爽曰:“初九者,潜位。隐而未见,行而未成。素履者,谓布衣之士,未得居位,独行礼义,不失其正,故‘无咎’也。”尚秉和评“素履,往无咎”有“言屏去浮华,安常蹈素,循分自守也。能如此,则往无咎”。可见“素”所指的就是不加任何修饰,强调“本色”。至于“白贲无咎”及“藉用白茅,无咎”,占断辞一致,“白茅”本色就是白色,这里为何用“白茅”而非“素茅”,推想其原因当是和“白贲”一样,为了强调“白”的颜色及其所象征的内涵。“洁白”隐喻了为了补救“大过”而极其敬慎的态度,饰以“白色”则是避免“文以害质”或“无所修饰”的弊端而采用的手段,“白茅”、“白贲”中“白”的使用,都有必要目的——为准确表达意义而突出色彩所具有的特征,以致重点表现事物本真的“素”无法替代这种特征。所以说“素履”可以是“不劳文饰”的“本真”,但“白贲”不是“饰终而反”的“质素”,尽管二者一为初九爻,一为上九爻,很容易给人“文极反质”的联想,但“文极反质”更像是“白贲”和“素履”中间的意义内容,而不能指向其中任何一方。“白”与“素”有时候可以互训互通,但在阐释过程中也不能过于大意而将两者完全等同,依然要考虑到有意义差别的情况以防止误解产生。
此外,高亨解“素履”爻引《周礼·屦人》之“屦人掌王及后之服屦。为赤舄、黑舄、赤繶、黄繶,青句,素屦、葛屦”及《仪礼·士冠礼》“素积白屦”,认为此是古人有素履之证。“素履无文采,质而不饰之象也。以质而不饰之度,有所往则无咎,故曰素履往,无咎。”回到《周礼》与《仪礼》对照,“素屦”是指王、王后燕居时穿的鞋,郑玄注:“素屦者,非纯吉,有凶去饰者。”贾公彦疏:“素屦者,大祥时所服,去饰也。”《仪礼·士冠礼》有:“素积白屦,以魁柎之,缁絇繶纯,纯博寸。”素积是加皮弁时穿带褶皱的白缯裳,与白屦相配,白屦要将蜃的粉涂附鞋帮,使之变成白色,鞋头的装饰、鞋缝的丝带和鞋的镶边都是白色的。因此“素屦”并非“白屦”,“素屦”其实才是“去饰”之履,而“白屦”是“白贲”之履,其实是有饰之屦。这两者之别,或可帮助我们理解“白贲”之“白”为何不能与“素履”之“素”相等。
在肖世孟的《先秦色彩研究》中,有一节专门叙述了“素”与“白”的联系与区别,言之甚详,现简要迻录于此:
《说文·系部》“素,白致缯也”,“素”从系,从字形来看,指的是一种色丝织品。很多的时候,服饰的“素”和“白”同义,它们都具有白色的外部效果。
同样是白色的服饰,在先秦时期,“素”与“白”使用的场合是完全不同的。古人在凶事的时候穿着素色服饰,如《礼记·曲礼》“大夫士去国,踰竟,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孔颖达疏:“素衣、素裳、素冠者,今既离君,故其衣裳冠皆素,为凶饰也。”服饰的素色往往是指织物丝绸、葛布、麻布等的本色,《礼记·间传》“素缟麻衣。”郑玄注:“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纯用布,无采饰。”是说制作深衣的麻布是无彩饰的白布,素色麻布制作的深衣的最终视觉效果是纯白色的。天子在吉礼的时候穿着白色服饰,如《吕氏春秋·孟秋纪》“天子居总章右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旅,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管子·幼官》“九和时节,君服白色。”先秦时期,白色服饰在天子贵族的重要礼仪场合穿着,必定和素色的服饰有所差别。
因此,在作为描述服饰的具体颜色时,“素”所指的织物的本色,“白”所指是染白的服饰色彩。
由此可见,“白”与“素”还是有所区别的,“白贲”和“素履”是不能简单等同的。
四 “绘事后素”与“思夫质素”
在《贲》卦上九爻下的说明中,黄寿祺、张善文指出了一个与“白贲无咎”相关的观点——“绘事后素”:
《周礼·考工记》谓:“画绘之事,后素功。”《论语·八佾》曰:“绘事后素。”两者或言绘画程序,或以“素”喻“礼”,与本爻“饰终反质”的意旨自有区别。但就“素”在“文饰”中为“本真”之色这一点看,上两说与本义“白贲”的拟象基础又有可通之处。故刘牧云:“绘事后素,居上者而能正五彩也。”(《周易义海摄要》引)惠栋也认为:“上者,贲之成。《考工记》云‘画绘之事,后素功。’《论语》‘绘事后素。’郑彼注云:‘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是功成于素之事也。 ’”(《周易述》)
“白贲无咎”虽非“饰终反质”,但它与孔子的“绘事后素”确可相通。问题是,自古至今学者们对于“绘事后素”的理解也存在着一些争议,主要集中在“绘”和“素”的先后顺序上,“先绘后素”与“先素后绘”表现出的是不一样内容。《论语》中关于“绘事后素”的对话如下: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 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八佾》)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集中讨论了“绘”与“素”的顺序问题,从语法、文意、词语组合的角度审视,再结合上下文篇章及其他典籍的相关内容推敲,认为“绘后乃素”的解释更为恰当。“绘事后素”的对话强调礼对人的调整作用,礼为了使人的美质有最好发挥,不能使所有品质都任意发展,必须加以一定约束,即“礼以节人”,就好像当时的画绘工艺,最后需要使用素色勾勒形成边界从而令作品达到完美状态一样。子夏从画绘手法之“素”的意义想到礼之别而能彰的内涵,又将二者结合起来,得出“礼后”的体认,也正符合孔子对礼的看法,且子夏应是更先一步抓住了礼与“绘事”后的“素”之间的联系,所以得到孔子的大加赞扬。
这样说来,贲以白色近似于画绘工序中最后用白色描绘的步骤,而“绘事后素”的目的在于使所有颜色轮廓分明、搭配得当,整体效果既不过于乱也不过于空,这一点倒是和“白贲”补救文过害质或是无所修饰之过的道理相像,刘牧、惠栋二人也因此借“绘事后素”释“白贲无咎”。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绘事后素”仅指绘画中在其他色彩后上以白色,而“白贲”的所指更广泛。
《论语·雍也》中还记载了孔子的另一段言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若是从“以白为饰”、“善以补过”等意义看,那么“文质彬彬”的主张应该更贴近“白贲”的内涵。用白色来文饰事物,一方面是“贲”道行进至最终阶段,用白色文饰能够免于出现“文过害质”之“咎”;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了防止“物极必反”的“无所文饰”状况产生。孔子在总结了两种文质不符的特征后,认为“文质彬彬”是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也是将重心放在了“文质相称”上,文和质的恰当配合避免了“史”和“野”这两种极端情况的发生,即类于“白贲无咎”之意旨。
然而在“文质彬彬”外,孔子还有“质素”之思,这也是把“白贲无咎”作“饰终反素”解时时常引用的一例。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白贲”非“质素”的认识,至于“文质彬彬”与“思夫质素”是否矛盾,在此不妨略作辨析:
孔子卦得贲,喟然仰而叹息,意不平。子张进,举手而问曰:“师闻贲者吉卦,而叹之乎?”孔子曰:“贲,非正色也,是以叹之。吾思夫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文质又何也?吾亦闻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说苑·反质》)
丹漆、白玉和宝珠等是对“质素”的比喻,它所表达的应该是不需要刻意修炼,以本真状态就能达到“从心不逾矩”的高度,即“白当正白,黑当正黑”,任意自然的同时又样样合度。但就像丹漆白玉宝珠之难得,如天所赋予一般,人鲜少能像上述那样,理想人格的所有萌芽都能好好发展,再以完全合度的状态自然而然表达出来。因而对于一般人来说,如果有志于此,那么通过对礼乐的不断研习来塑造自己,争取达到上述的理想状态,使自身价值充分发挥,从而成为文质和谐的“彬彬”君子,也是十分值得提倡的。而且,这样的过程也具有“绘事后素”的特点。《贲》卦卦辞有“小利有攸往”,它本于亨通之极的泰卦,却因为九二与上六位置的调换,即“分刚上而文柔”,虽可观“天文”、“人文”,仍不若泰卦之“吉亨”。泰卦象征的是上下天地阴阳交合臻于完美的转台,颇能说明以自然而然的行动原则达到化育万物,彰显德行的“质素”特征。孔子“思夫质素”,表达的是对这最高级之“素”的向往与追求,他希望自己所有优秀的品质都能不假修饰而自行显明,随心所欲而不会超越规范,却占得了意在文饰的贲卦,因而“意不平”。因此,“文质彬彬”、“思夫质素”两种表述看似矛盾,实际上则不然,它们只是孔子针对不同情形所发表的不同意见:“文质彬彬”乃理想人格,“思夫质素”则是为了矫正文过则史的弊端。这并未偏离以“质”为本而又不排斥外在之“文”的根本宗旨。
《序卦》云:“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由此亦可见《贲》卦仍然含有修饰的意义。长期以来,我们把“白贲无咎”提升到“质素”至美的高度,视为以朴素为美的经典命题,但这很可能只是带有误读性质的联想,其根源在于忽略了“素”与“白”之间的细微的语义差异及其语用差异。当然,这一切并不能改变中国古典美学崇尚自然素朴的基本倾向,但是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周易》的本义或不无小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