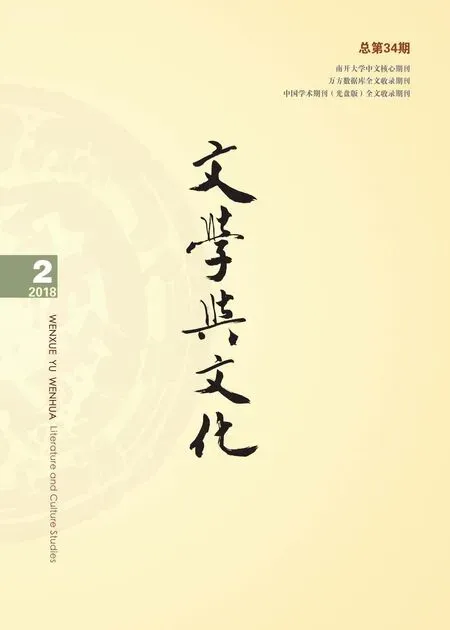先秦文学思想史研究之反思
2018-11-13沈立岩
沈立岩
内容提要:作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滥觞阶段,先秦时期既具有特殊的性质和意义,也面临特殊的问题和疑难。正确地提出问题,对于先秦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具有前提性意义。本文主张悬置现代文学观念的成见和定式,回到中国文学思想发生与演化的独特社会-文化环境,以探索和形成恰当的问题视域,进而确定与之相应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对于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而言,先秦时期既有特殊的性质和意义,也存在着特殊的问题和疑难。如何准确地把握它的性质和意义,并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和疑难,无疑具有前提的性质,但也确实令人颇费踌躇。笔者拟对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如问题的反思和校正、内容的划定和取材、研究的方法和手段等做些初步的思考和分析。因问题复杂,不敢自是,陈述于此以就教于方家。
一 问题视域
真正的研究始于问题,但是问题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况且,“问题”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有待解决的疑难或难题,这个含义在英文中称为“problem”;其二是有待回答的提问或疑问,这个含义在英文中称为“question”。学术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实为上述两种含义的复合,即它首先指实践活动或理论思考中出现的疑难或难题,其次指以恰当的语言形式提出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两者并非简单的等同关系,一个真正的难题(problem)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一个正确的问题(question)。恰恰相反,在难题具体化为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定位的失误和方向的偏差,以至歧路亡羊甚或缘木求鱼。有人把学术研究的这种独特的问题模式称之为“P-Q模式”。对于先秦文学思想史这一独特研究对象来说,该模式同样不乏启发的意义。
“先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颜师古注:“先秦,尤言秦先,谓未焚书之前。”今天所称“先秦”通常有广狭不同的两种含义,广义的先秦包括了从远古到秦朝建立前的漫长年代,狭义的先秦通常限指载籍所称的“三代”即夏、商、周时期,甚至仅指有信史可征的商周两代。但是无论选择哪种含义,对于文学思想史研究都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个时期究竟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或者说,区别文学思想与非文学思想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又如何确定?
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困惑,首先在于如下事实:如果“文学思想”至少意味着“关于文学的思想”的话,那么它已经假定了文学的存在。但在先秦时期有无文学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先秦时期尚无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因此建议用“杂文学”或“泛文学”之类的术语来称之。显然,这个问题若得不到合理解决,所谓“先秦文学思想”终不免于焉附之嫌。
事实上,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出现甚晚。据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研究,在西方,它起源于1770年,最终在1800年斯达尔夫人写作《论文学》之时得到认可;在中国,它的出现无疑还要晚些,因为目前使用的“文学”概念是英语literature一词的对译。不仅如此,近期的争议使它的含义变得更加漂浮不定。甚至在是否存在文学这种东西以及如何划定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上,都有截然不同的意见。其中最为极端的观点认为,文学概念与“杂草”类似:杂草并不指涉任何一种特定的植物,而仅仅表示园林主人出于某种主观好恶意欲清除的东西;文学也是如此,它并不指涉任何确定无疑的属性或实体,而仅仅意味着人们出于某种价值偏好而意欲保留的东西。当然,“文学是否存在”与“先秦时期有没有真正意义上文学”并不是同一性质或同一逻辑层次的问题,但二者的关联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们都与文学的界定及其标准有关。
依我的理解,“什么是文学”或“文学是否存在”并不是伪问题,但应该被一种更准确的提问方式所替代,那就是:“文学”——不是作为一个确定无疑的实体,而是作为一种观念或思想的建构——何以能够出现?为什么此前它没有出现?致使其出现的历史机缘和社会-文化条件是什么?通过它,人们对现实施加了何种干预——选择、排除和分等?这种干预背后的动机又是什么?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而且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不可能在此详加讨论,不过对它略加分疏有助于摆脱“先秦有无文学”之类的理论迷阵,从而将问题导入一个更为清晰和确定的参照框架之中。这种新的提问方式的确有些“唯名论”的意味,但它能够有效地悬置那些先入为主的理论定见,从而接近思想史的实际情况,由此我们不必再拿今天的文学概念去古代按图索骥,而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本身,以求触摸到先秦文学思想发生和演变的真实形态。
不仅如此,这种提问方式的改变可能会引起连锁性的变化。由于我们不再将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作为先秦文学思想史研究的预设前提,所以也就不再把先秦时期的各种思想活动简单地视为朝着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这一理想目标的定向运动。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文学思想史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演化环境和不可重复的演化过程,正如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自成一独立的演化单元一样。因此,它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学思想史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当然,其间必定存在一些共通特点,但是差异仍然无法忽略。例如,《文心雕龙》尽管涉及了很多今天意义上的文学问题,但是仍然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文学理论”、“文学史”或“文学批评”著作。也许我们会为它的不够纯粹而感到遗憾,但是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此。正如不同的语言系统会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不同的分类方法表明不同的概念和逻辑规则,而不同的概念和逻辑规则又意味着不同的文化系统(其核心是传统的思想和价值)一样,从先秦直到整个中国文学思想史,其独特的概念系统、逻辑结构和文化意义正是《先秦文学思想史》和《中国文学思想史》所要揭示的东西。关注而非忽略这些系统性差异,对于文学思想史这种人文学术研究来说无疑应该是首要的任务。
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认为,任何文化中都存在一种普遍性特质,它为整个文化构造提供形式、内聚力和高度整合的稳定内核;某种普遍的兴趣和偏好支配着这个内核,并由此支配着整个文化结构,一如一个晶体结构围绕着核心点开始其结晶过程。换句话说,一种文化的普遍兴趣和偏好赋予此种文化的全部要素以倾向性。我们姑且借用这个比喻,以便形象地说明中国文学思想史独特的发生和演化过程。那么,贯穿先秦时期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的那个独特内核或核心点是什么呢?或者说,支配先秦时期文学思想与众不同的发生过程和演化方向的普遍兴趣和偏好又是什么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找到这样一个术语或概念,它既能够说明先秦时人对于文学——或是类文学的东西——的核心属性的认识,又足以统摄所有与之相关的文化要素,因而可以揭示那个赋予先秦文化与文学发展以特定方向和内聚力的“晶核”。
循此思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比“文”这个词语更为恰当而有效了。理由有三:第一,这个概念标示了先秦时期文化发展的核心理念和理想境界,因而占有极高的价值层位;第二,这个概念具有极强的弥散性和渗透力,因此能够涵摄所有与之相关的文化要素;第三,这个概念构成了文学命名的原初形式与核心特质,并对后续的文学演进施加了持久的影响。且此三点均非出于偶然,而皆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成因,因此考察“文”字的含义及演变对于理解先秦文学思想的独特性质和意义将深有裨益。
二 文化禀赋
“文”字在中国语言文字中出现甚早。1984年,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代号H3403的灰坑中出土一件陶质扁壶残片,其上写有两个软笔朱书文字。对第二字专家有不同的释读,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但于第一字各家均无异辞,皆认为应释为“文”字。据古文字专家判断,该朱书与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今日通行的汉字属于同一系统。
考古学者冯时据文字构形与甲骨卜辞(《甲骨文合集》33243、33242)将此二字隶定为“文邑”。又据传世文献中三代都城皆称为“邑”,谓此“文邑”当指夏代都城。又据殷铜器铭文见有“文夏”之称(《殷周金文集成》3312),结合文献记载(《国语·周语下》、《急就章》注引《风俗通》、《元和姓纂》),谓此“文夏”当为氏名,正承夏后之氏而来,而其中“文”字则与世传禹名“文命”关联密切。其说云:“《大戴礼记·五帝德》引孔子曰:‘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文命。’相同内容又见于《帝系》。二戴礼的编纂虽在西汉中期,但其所据资料则为《汉书·艺文志》所录《记》百三十一篇及《明堂阴阳》等五种,这些孔门后学的研礼心得于近年出土的战国竹书中已有发现,故其形成时代可直溯先秦。《大戴礼记》以禹名‘文命’为孔子所言,这个说法看来并非毫无根据。《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正承其说。唐陆德明作《经典释文》,也以禹名‘文命’为先儒通识。”至于“文命”的含义,冯时认为这一名称或许正是出于后人对夏人文德观念的概括。《礼记·表记》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孙希旦《礼记集解》解释说:“尊命,谓尊上之政教也。远之,谓不以鬼神之道示人也。盖夏承重黎绝地天通之后,惩神人杂揉之敝,故事鬼敬神而远之,而专以人道为教。”由此推想,夏尊文德教命,以人道为教,可能正是“文命”二字的本义所在。
由此笔者想起,殷墟卜辞中亦尝见“文邑”一词(《殷虚文字甲编》三六一四),唯其所指何地尚无从确定。冯说无论是否正确,至少提示“文”字在商代以前的价值系统中可能已有非同寻常的意味。当然,“文”字在夏代的语用情形难知其详,但在甲骨卜辞中却已屡见不鲜,经考证虽多系人名、地名,但卜辞中见有“贞于文室”之辞(《甲骨文合集》27695),“文武帝”“文武丁”的商王庙号亦非仅见(如《甲骨文合集》36168、《殷虚书契前编》1·18·4、28·1、438·2、4·385、《殷虚书契后编》下 4·17、《小屯·殷虚文字甲编》3940、《战后新获甲骨集》2837、《怀特氏所藏甲骨文集》1702等)。贞卜在殷代洵非小事,至于商王庙号更无轻忽随意之可能,因此说“文”在其时已经开始赋有了价值理想的意味,似乎不是毫无根据的臆测。
追索“文”字意义演变之迹,可以为我们提供先秦时期文化价值生发演进的基本线索,并由此略窥中国文学思想的文化基因。徐中舒对于“文”字有如下解说:“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甲骨文所从之×υ―等形即象人胸前之交文错画。”至于其具体释义,则首列“美也,冠于王名之上以为美称”为其三种含义之一。前引冯文亦谓,古“文”字常繁作人形之中复加心形,于金文中最为多见,所象者正是心斋修身之形,反映了夏人以人道为教的朴素思想。史载禹重文德而立纲纪,正是夏兴文教之始。《国语·周语下》记:“(单)襄公有疾,召顷公而告之曰:‘必善晋周,将得晋国。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尊德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质,全部美德皆以“文”字概之,则“文”之为德也大矣!韦《注》以“文”为“德之总名”,是非常正确的。
不过,“文”字的道德化解释尚属后起的引申之义,而且这种道德化的含义仅为“文”义之一端。《逸周书·溢法解》既云“道德博厚曰文”,又谓“学勤好问曰文”,即暗示了“文”义的另外一面,即重知识的一面。而尊德与重知这两方面含义,实则均与“文”字的本义有关。《说文》“错画交文”之解,可谓得其环中,因为它蕴含了语义多向衍生的可能:一是花纹、纹饰之义,虽着眼于外在的视觉形象,但同时隐含了向审美经验和道德评价衍生的可能,因为二者均引发愉悦的情感反应,而造成一美善混融的主观体验。商王之以“文”为庙号,周人之以“文人”“前文人”“文神”“文神人”为先人美称,盖皆属此类;二是错画交文与文字形象相类,因而具有向文字乃至文章学术转折引申的潜力。《左传》中即多见以“文”为“文字”的范例,如隐公元年记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鲁夫人’”,闵二年、昭三十二年皆记成季“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昭元年子产言唐叔虞“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文字乃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它的产生是人类社会革命性的重大事件,《淮南子·本经训》所谓“天雨粟,鬼夜哭”,只是对其深远影响的一个想象性表述。而积字成句、积句成篇,文献载籍由斯而起,典章制度由斯而明。刘熙《释名·释言语》云:“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正道出了其间的关联。《周易》贲卦彖辞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则又将天文与人文、文明与文化骈列并举,大大拓展了“文”字的义界,显示了“文”字内涵贯通天人、无远弗届的弥散性和渗透力,透露了中国文化尚文贵文的基本倾向。王弼《注》云:“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是以礼乐教化而非武力威慑为文,将此尚文贵文的文化倾向表述得尤为清晰。
一种文化之精神内核,对于生长其中的多数人来说,往往是习焉不察、日用不知的,唯少数识见超卓、长于反思的人,方能探赜索隐、洞幽烛微,将其精深微妙的普遍性特质昭示于众人之前。孔子正是这样的人物。“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既是对宗周文化的总体评价,也是对三代文化演进脉络的精准概括,而其核心仍然是一个“文”字,足见其蕴意之深、涵摄之广。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云:“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谓文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其《征圣》又云:“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为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这些论述,将孔子对“文”的认识表述得周至无遗。
无须遍举,仅由上述有限的几例即可看出“文”在先秦思想者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也可以看出“尚文”观念在先秦文化中的弥散性和渗透力,至于该术语与文学的关系,更是显而易见。即便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学概念受到了西方思想的深刻影响,但考之西方的文学概念,却也经历了与我国类似的演化过程。埃斯卡皮在追溯西方“文学”术语演化过程时特别提醒读者:“应该注意到汉语如同欧洲语言那样,也使用了一个词根‘文’,其含义为花纹、字形、文字。”而欧洲语言中的“文学”一词源自希腊语,在罗马时代的拉丁语中则有文字、字母、语法和语文学、学问与博学等含义。这与先秦及秦汉间常见的“文学”一词用法何其相似乃尔。在此后的欧洲历史中,这个词又相继赋有了文化学术、文人团体及其职业、美文学、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科学等含义。不过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显然聚焦在“美文学”这一含义上,尽管对文学的核心性质和标准问题迄今无法形成一致看法,但文学概念的指称明显是以诗歌、小说、戏剧等纯文学体裁为典范样式的,因此,抒情、想象、虚构和审美也成了定义文学的虽不充分但却最为常用的标准。
反观中国,在先秦乃至此后的漫长年代里,除抒情和审美之外,想象和虚构并没有成为定义文学的核心特质。这当然与中西方文学文体演化的历史过程直接相关,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应该还在于双方的文化差异。揭示这种差异,无疑是先秦文学思想史的主要任务之一。
三 思想路向
基于上述原因,我以为先秦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恰当的提问方式不是先秦时期有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文学思想,而是在先秦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华夏先民为中国文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哪些思想资源和理论创造的可能性,更具体地说,这些早期的思考为后世提供了什么样的概念原型、思维模式、价值倾向以及演进发展的路径和方向。
首先,先秦这一特殊的历史断限决定了其时“文学”和“文学思想”的独特存在方式。先秦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决定了中国早期文学活动可能的动机、形式和功能,也决定了人们对文学活动的可能的体验、认知与评价。我们最好不要简单沿袭过去的说法,即所谓先秦时期的文学尚未达到自觉的意识,因为这种说法是站在一个想象中的终点来回顾遥远的过去,并将复杂曲折且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和可能性的历史过程压缩成一条单一的直线。必须强调的是,演化的确存在,进步也同样存在,但是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从来都不是一条不断上升的笔直道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汉赋是楚辞的进化,五言诗是四言诗的进化,正如我们不能说李白是屈原的进化,苏轼是李白的进化一样。因为每一种文体都有其独特的演化过程,有其自身的社会-文化成因,也有其自身的特质、功能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从一种文体到另一种文体,其间的关系常常并不是一对一的传承关系,跨文体、跨门类甚至跨文化的移植始终存在,诗与文、音乐与诗歌、电影与小说以及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等即是如此。至于化支流为主流、以复古为通变,也是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因此,与其不假反思地用进化观念来框限文学的演化历程,倒不如以语境论和解释学的观点,深入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文体结构的内部,探明其来龙去脉和活动机制,揭橥其背后的思想内涵,反而更加切实而富有意义。
文学如此,文学思想何独便不如此呢?孔子可能的确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文学思想,但是这无碍于其兴观群怨之说的深刻与伟大。老庄的思想甚至带有反文学和反文化的色彩,但也同样无碍于其哲思成为最具诗性意味和理论深度的文学思想资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固然无暇于礼乐的研习和传播,但其独步当时的科技智慧和严谨务实的经验主义取向,却使其对语言的逻辑规则和辩论技巧独具会心。韩非子对“以文乱法”深怀敌意,一心要把全部言语活动禁锢于集权的铁律之下,但其思辨之深刻、寓言之精妙,透露了非同寻常的文学素养,实为文学思想之另类别调。至于那些默默无闻的诗人、歌者、矇瞍、乐师,那些审曲面势以饬五材的百工众匠,以及无数以自己的思虑和劳作为文明的大厦添砖加瓦的平凡百姓,他们的思想尽管微若涓滴,但也可能沉积在文化的遗迹之中,或经思想家的采集、提炼,汇聚成思想的川流和峰峦。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便是这种思想熔铸的真实写照。因此先秦文学思想之研究,眼光不能只放在有名有姓的思想家身上,而应该放宽眼界,将所有为那个独特的“人文”世界和“文化”精神的营造有所贡献的人与活动包纳进来。
其次,出于独特的社会语境和文化禀赋,先秦时期的文学思想导源于尚文的核心理念,弥散于生活的各个层面。与其说文学和文学思想尚未从其原初的母体中分化出来,倒不如说,是当时的人们尚没有感觉到将文学从混沌的现实中分离出来的必要。社会和文化的普遍兴趣,并没有聚焦在纯粹的审美目的和相应的活动之上。构成后世文学基本形态的许多文体形式尚未充分地分化和发育,相应的辨识、命名和概念化的尝试还没有成为自觉的需要。但是,这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贫弱的结果,倒不如说,时人的审美兴趣和感知结构有其异于后世的独特之处。徐复观即认为:“礼的最基本意义,可以说是人类行为的艺术化、规范化的统一之物……文质彬彬,正说明孔子依然把规范性与艺术性的谐和统一,作为礼的基本性格。”美国学者郝大维与安乐哲也认为,孔子的思想具有美学的性质,他所要建立的,并非“理性”和“逻辑”的秩序,而是美学的秩序,而且“要理解孔子哲学中‘乐’的地位,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懂得,美学的和谐在人们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因此,“为了实现人际和社会的和谐,就要把握由礼仪、语言、音乐所构成的美学秩序……礼仪、语言和音乐的功能在于促进美学的秩序”。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意见。先秦礼乐文明本身就含有极为丰富的艺术和审美因素。熟悉周礼的人,很容易看出礼仪、礼器、礼乐、礼辞相互交织所包含的神话、诗歌、戏剧、美术、音乐等多元的艺术成分,说礼乐活动实质上带有浓重的戏剧化和艺术化的性质,恐怕也非过甚其辞。这里便触及先秦时期的所谓“文化模式”问题。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曾描述过美洲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祖尼部族对于礼乐仪式令人难以理解的痴迷,及其崇尚节制和中庸之道的生活风格。这种被喻为日神式的生活风格藐视个性而尊重传统,循规蹈矩而排斥改变,以温文尔雅、雍容大度为理想人格,读来令人不自觉地联想到周人。礼乐文化的兴趣和重心,明显地落在无所不在的礼仪上,从时间与空间的结构,到其中的人和物、形状和数量、色彩和图像、言语和动作,无不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要求与规则合若符契。礼乐的制度和仪式,就像精神分析所说的情结一样,将生活中的一切元素都吸引过去。所以要正确地理解先秦时期的各种社会文化事象,就必须置之于礼乐文化的整体结构之中,否则便容易产生移情式的错觉。对于先秦文学思想,也应作如是观。
再次,将先秦文学思想放在礼乐文化的整体结构中加以考察,又必须防止形成新的刻板印象,即将礼乐文化视为静态划一、笼罩一切的铁板。因为礼乐文化也处在生住异灭的变化之中,而且存在着地域的差异。礼乐文化固然可以说是先秦社会的主流文化,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不同的亚文化乃至反文化,这一点不仅见于传世文献,考古发现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例如孔子云:“鲁卫之政,兄弟也。”(《论语·子路》)又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同为礼乐文化,便有这般同异。又如“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左传·襄公十年》),虽为春秋各国所艳称,其礼却有殷周之别。《庄子·德充符》云:“王骀,兀者也,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如果此说尚有虚构成分的话,那么韩非子的“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恐怕便离事实不远了。至于庄子笔下“游方之内”与“游方之外”的儒道殊途(《庄子·大宗师》),“山谷之士”“平世之士”“朝廷之士”“江海之士”“导引之士”的分道扬镳(《庄子·刻意》),更为了解战国时代的社会分化和文化冲突留下了想象的空间。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文献不断涌现,近年更臻高潮,其中尤以楚地简帛为大宗。透过这些简帛佚籍,我们得以略窥战国时代中原与楚地的文化分野。此外考古遗存的陆续发现和深入分析,也使我们对宗周社会礼乐制度的创制、完善与衰败有了新的认识,对《三礼》中精严整饬的礼乐制度有了富于历史深度的体会。凡此种种皆提示我们,先秦时期的文学思想,是在礼乐文化与各种异质文化的相摩相荡中产生和发展,在社会转折和文化变迁的潮起潮落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因此成就了先秦文学思想内在的丰盈和张力。从思想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来看,先秦时期的思想成果尽管带有滥觞期的素朴和简质,但却与其后的文学思想存在源流本末的联系。这种关系至少体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其一,概念和命题的直接传承关系,如气、象、意、味、风、势、形神、文质、刚柔、比兴、自然、虚静、通变、诗言志、发愤抒情、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等。在传承过程中,这些概念和命题的含义或有宽窄不同的变化,但其传承的关联甚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不仅是名词术语的沿袭借用,更存在着思维的模式、向度和方法的深层联系。
其二,审美趣味或思想倾向上的内在联系,诸如文约旨丰、意在言外、尚文尚质、典雅自然,以及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道德教化功能等等。这种联系虽然不像第一种形式那么直观,但是通常更为深刻而持久。它导致了中国文学和文学思想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貌和特质,指示着中国文学的作者群体和文学思想者群体的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
其三,逻辑上的前设与后承关系,如言意观、象意观以及得意忘言、立象尽意、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等思想与后世滋味、神韵、意境等审美理想之间隐含的逻辑联系。两者虽有椎轮大辂之别,但是其影响关系是无可否认的。它们同样造成了中国文学和文学思想与众不同的风貌和特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先秦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需要摆脱旧有的问题模式和视域,尽可能回到先秦时期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语境之中,在其特殊的整体结构和价值倾向中探索文学思想胎息演化的脉络和机理。先秦乃至中国的文学思想有其独特的文化禀赋和演化路向,不能简单地同化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和进化模式,而同样需要在先秦社会-文化的自身结构和价值倾向中去认识。而这正是人文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至于这一问题视域的改变所带来的研究内容和取材范围上的具体变化,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的变化,将在后续的文章中加以阐述。